- +1
当AI真正成为生产力 | 上影节论坛
在院线市场中的科幻电影相对沉寂的这一年,电影世界之外的AI生产力却在飞速狂奔。
落差的现实没有给从业者带来迷茫,相反,科幻电影产业链各个维度上的专家、创作者们都在闷头探索AI与实际工作更多结合的可能。

在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科幻电影主题论坛上,与会嘉宾们没有再过度纠结科幻电影方向上、概念上的是非,而是更多结合自身日常工作经验,向外界分享与AI相处的真实心路历程。通用式人工智能目前绝大多数情况下并非专为艺术创作而开发,与顶尖艺术工作者的思维模式仍有间隙。这道间隙的空间与形状究竟是怎样的,恰恰需要与会嘉宾们的宝贵经验以描摹。
本次论坛邀请了导演,编剧,监制黄建新;动画导演,机甲设计师河森正治;监制,编剧王红卫;电影美术指导霍廷霄;科幻作家王晋康;导演,编剧董润年;人工智能青年科学家戴勃,从科幻电影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各抒己见,共探未来发展之路。
以下是毒眸根据现场论坛发言的整理——
人工智能的应用经验
黄建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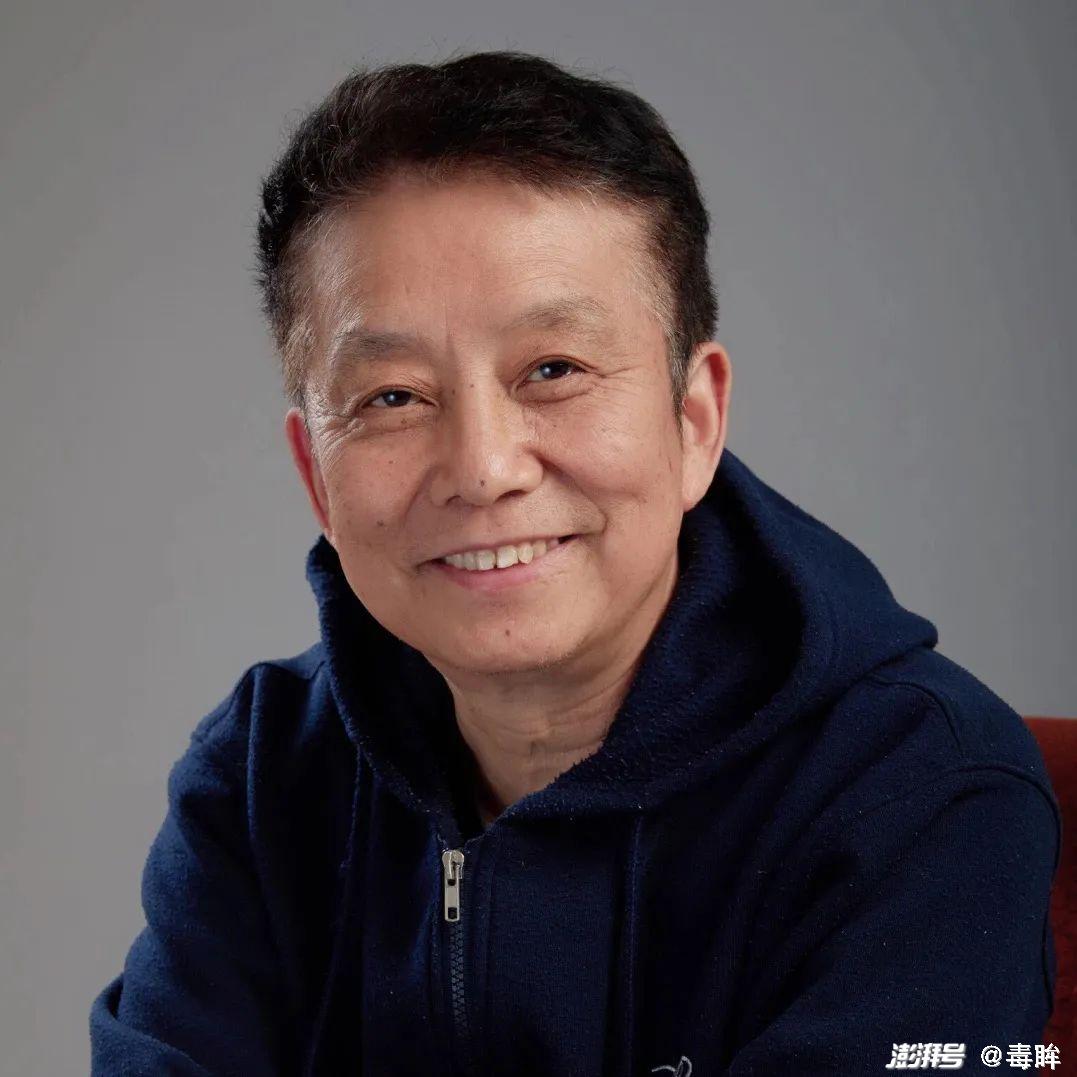
黄建新
电影界对于人工智能的变化格外敏感,其实是因为电影就是虚拟的。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的,是一个梦幻的过程,跟我们现在面对的数字阅读有本质上的一致。因此,电影跟人工智能产生的影像系统有一个联系,这个联系就使我们变得极为敏感,观众极为感兴趣。
如果我们看一个话剧,演员在台上表演的时候,那是一个三维世界真实的人,但是Sora出现以后,演员是再造的人,不是三维世界真实存在的。它可以完成一个破坏维度世界之间区别的认证过程,所以电影可能是最早受益的系统之一。
我自己觉得人工智能是人类整体意识或者智慧的外延,它把我们的智慧扩展了。我记得交通大学的校长说过,个体人跟人工智能比,它已经远远超越了我们的感知和认知。它可能用一年的时间就读遍、记住了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文明记录,它是个全才。因此我们觉得人工智能会给人类带来一次大的智慧的改变,也有人把它叫第四次工业革命。
说到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是有深刻印象的,我们都看电影,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我们知道当大工业来的时候,人们在一瞬间变成了机器的运用者。随着工业的发展,人跟工业之间重新调整位置,它就使人类的物质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变化。

《摩登时代》剧照(图源:豆瓣)
所以我们觉得,新一轮的AI一定会对人类的生活提高产生重要作用。它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困惑,它会给很多企业带来失业,这是一定的,因为它替代你在工作。另一方面,它也符合了人类一个礼拜可以休息三天的梦想。它应该是一个很复杂的感受,我们面对它的时候,充满了好奇和求知欲,这就像人类在小孩子的时候,我小时候对好多事情都充满了好奇。
AI给我们提供了特别多的好奇点,因为我们有好奇,我们就想知道;我们知道了,我们就想使用;我们使用,就跟它产生了很多关系。所以人工智能对电影来讲,它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河森正治
关于AI人工智能,我是在三十年前的《超时空要塞Plus》作品中,就创作了一个人工智能偶像,它叫莎朗·埃普,当时我们的制作团队会跟我说,没有人会喜欢一个AI偶像的。现在的AI偶像已经普及了,比如日本的初音未来。原本我们以为AI是一个我们观赏的东西,而不是实际使用的东西,但如今看到它的发展,我感到十分震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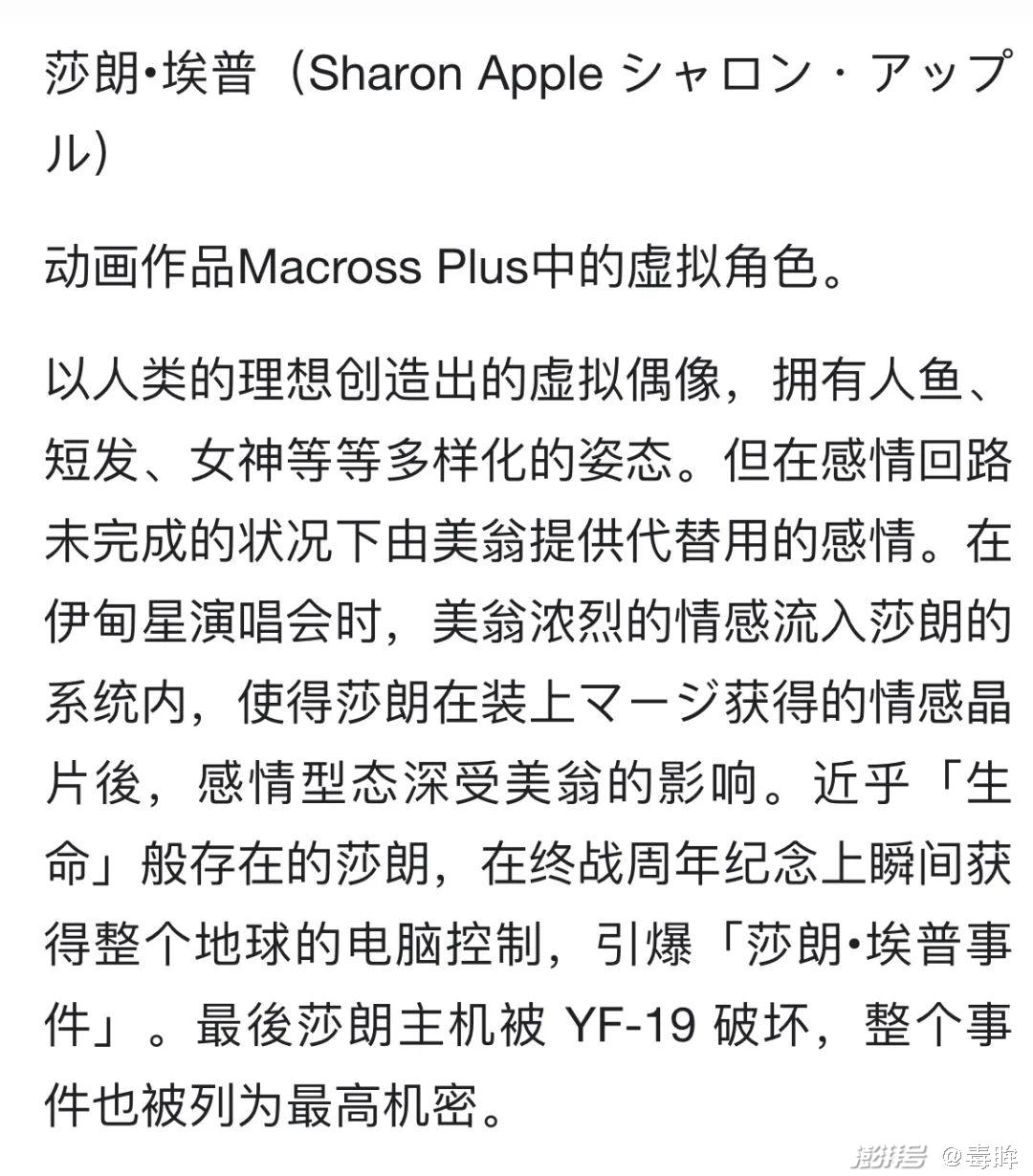
动画制作工作可以分为两类,一个是做创作类工作,如原创故事、人画、动画演出等等;还有一部分类型工作是比较量产化的流水线工作,就像数字化一样,AI应该也是同样的应用方式,可以最初从一些创造性没有那么高的部分,开始用AI技术来加速我们的动画制作。
真人电影的拍摄是很花时间的,而动画的制作主要是要花很多时间在作画方面,如果我们花很多时间在绘画上,很多时候动画的制作进度是赶不上现实世界变化速度的,这是困扰我的一点,希望能改善它。
AI非常擅长伪装成人跟你对话,现在这个技术也发展的越来越好了,但是关于AI自己是否拥有像人类一样的感情,这一点还是尚未明确的。AI今后是否能够超越这一点,是让我很有兴趣的。
目前的操作主要还是将影像的数据和文字的数据提供给AI,让AI生成一些内容。但是影像和文字之外的,比如味觉、触觉、嗅觉,这些难以输入的感觉,今后看看有没有办法输入给AI,看看它能够制造出什么样的东西,我很期待。

河森正治
王红卫
在学校里,对于人工智能的应用,最多的就是学生写论文。他们会用GPT代替以往他们要查阅资料、自己去梳理总结的部分,再用一些方法就可以完成查重。
青年导演对人工智能的应用,反而我在一些青年导演的短片创作中开始看到了一些雏形。比如说前一阵在北京的科幻大会上,我看到一部短片,我问年轻的作者为什么要做这个创意?他说这个本身是一个项目,委托方想要用这个数字人来体现他们的产品的一种特质。所以他去创造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想说这个人是从另外一个世界到我们现实世界中来的。他想找到一种形式,去体现另外一个世界的质感,而不是找一个演员来演一个从异世界来的人。所以当你看到这么年轻的创作者,他已经意识到可以不仅仅是把AI作为一个便捷化、高效化的工具,而是用它创造出来本身就有虚实意味的新形象,这是挺令人欣喜的现象。

王红卫
至于剧本开发、文本创作方面,最新在用的Claude3,我们自己使用起来,觉得比GPT4要好,是更先进的工具。它可以大大地提升我们开漫长的策划会的效率。当我们自己在海量信息里非常辛苦地寻找可能性的过程中,它可以帮助我们找出几条路。
甚至于我们尝试过有一个剧本,里面涉及到一个很复杂的方案,关于从视觉表现到技术、到电影桥段的一个方案,我们试着让它给我们提出一些方案,它提出了数十个方案之后,我们发现其中有一个方案非常好。你冷静地想,那个方案很难靠我们一个编剧,或者说一个编剧加一个相关技术的专家想出来。它有非常好的逻辑推理,根据你喂给它的电影和剧本的理解,可以编出来这个桥段。
霍廷霄

霍廷霄
我也拍了三十多年电影,从传统的电影美术,到前两年的虚拟拍摄,再到现在AI等新技术。通过这几年的创作,我认为AI只是画笔,艺术家还是艺术家。我经常举个例子,前一段时间我刚给华为拍了一个MV《春江花月夜》,我就来拍黄金甲、琉璃这概念,用新的技术做,怎么也达不到我想要的实拍的感觉。
那天我和黄导在聊,未来拍电影可能就是四个人坐在一起,大家聊一聊就成了,这是想象出来的。但未来拍电影,肯定不需要那么多人了。这两年我也在电影学院讲课,美术学院也是有大量的实验人员,未来电影的形态、创作可能要产生很大的变化。不过,我觉得美学电影还是得有一个概念,让绘画的语言与传统的东西相互结合,技术和艺术融合。
我原来拍现实主义题材,拍《白鹿原》《唐山大地震》,这一类题材的电影,用刚才说的技术怎么才能完成真实性,达成所谓的影像质感,这是一个问题。当然,好处是很便捷,我们现在拍片,美术组就三个人。

电影《白鹿原》剧照(图源:豆瓣)
王晋康
有一次在一个活动中间,刘慈欣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这一代科幻作家比较幸运,因为我们没有用AI创作。在我们之后的作家,不管他用不用,别人都怀疑他可能用了AI创作。这是个笑话,这个笑话潜在的前提是,刘慈欣认为从长远说,AI进行创作,将来肯定会超过人类,你还在人类的创作中使用AI,那就属于作弊。就像在围棋领域,假如一个棋手下棋,口袋里揣着无线通话器,用AI来指挥他下棋,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说,我这一代肯定不会用AI来写作。
当然,我不用AI写作并不是我不支持AI,今年我创作了一个长篇,8月份要再一个文学大刊上发,里面有一个主人公,是先知型的AI。我现在和中国科技大学的团队有一个合作,以AI为第一人称来写小说,如果成功了,肯定不以我的名义来发表,就要以AI的名义来发表,将来这个版权怎么分,在这里边人类出了多少力,这些东西我们都准备蹚出一条路来。

王晋康
在我的小说《生命之歌》里,那时候写的AI还是一个孩子,以孩子的目光仰视人类社会,虽然它也很厉害,但它是仰视的。而在我现在写的小说中,AI已经是俯视了。我认为不管从哪个方面,电影创作也好,小说创作也好,AI将来做得比人类更好,只是时间问题。
不过,现在的AI还有一个小问题——它是一个整体性的智慧,通过互联网把所有的智能单元合在一块,它没有作为个体生活在生活中的很鲜活的个人经历,唯有在这些方面我不太拿得准。如果没有这种经历,它就创作不出各位老师说的那些非常有质感、非常鲜活的生活经历。这并不是完全没有补救的办法,通过某种方法可能能补救。但是在其他方面,比如在信息量方面、写作的技术方面等,那些都是毫无问题的。
董润年
在剧本创作中,AI确实掌握了很多技巧,但是它没有呈现出更高超的创造力。我们也在总结这个事,因为在创作中,很多有特点的、有个性化的东西,未必符合我们总结出来的艺术规律,甚至有的时候,按照传统的观念你没有做对的地方,结果反而成了新的艺术探索形式。
这是现在我在使用这些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不太容易得到的,但恰恰这是我需求的。比如在生成一个画面的时候,我希望能生成超出人类想象的东西。最初还有可能出现,现在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少了,它越来越像人类,而且是像一个平均创造力的人类所创造出来的东西,这是一个问题。

董润年
我直觉这些通用人工智能并不是为了艺术家而设计,它是为了拉平所有人,为了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有能力去生成他想象中或者他想要看到的画面。所以它和电影制作的思维方式是不是一致,这可能是我们后边需要进一步探讨的。
我之前跟AI工程师、计算机专家讨论过这些问题,这涉及到双方的隔阂问题,现在程序员们、工程师们并不理解艺术方面的语言。比如视听方面的语言,他们在设计AI的时候,只能是抓取网上能够找到的所有视觉素材,来分析、总结。实际上我们在视觉创作时的思维是怎么样的,程序员和工程师是不了解这一点的,我们进行艺术创作的人又不了解他在设计这种程序时的逻辑思维。
所以我觉得需要双方沟通,互相能够理解对象的思维,才能够使得这种通用人工智能,至少它在其中某一部分更能够理解我们对视觉、对视频或艺术的需求,可能才能达成一致。
戴勃

戴勃
我觉得大家在聊人工智能时,会有两种不一样的角色。第一种是我之前在电影里面看到的那些人工智能的角色——把它当成一个生命体,它有没有情感,它有没有思想,它的知识体系是怎样的,可能能够在创作过程中提供一些它自己的视角,对这个故事应该怎么样发展有一些推荐。另外一种角色更像是一种工具——它能不能在整个流程中真正地起到一些作用,降本增效,将时间周期拉短,不需要人去做非常细节的、脱离创作本身的事情。
从技术角度讲,这两种都挺有意思的。从生命体角度的角色,我们希望鼓励它的创造性,换句话说是随机性,它能不能多一些创意,甚至于超出对于现有的知识,或者人类想象力的一些输出。另外一种作为工具的角度,刚好相反,可能大家期待它按照我的输入给出输出。这二者是有一点点对立的,同时也互相联系,本质上都是人类社会知识的外延,包括思想外延,也包括技术、流程上的外延,本质上是相同的。我个人认为,这两者都要去努力发展。
成为电影的新质生产力
黄建新我的孙子学围棋,他告诉我他学棋的过程是AI教他的。我问他,既然你永远都下不过AI,你为什么还要下这个棋。他说,人类的生命是追求快乐的游戏,这是孩子的回答。这个状态就像我爱看漫画一样,我们跟AI博弈的过程,虽然我知道我赢不了它,但是我还是有快乐。我们知道,如果放一堆小孩,黑人、白人、黄皮肤的人,在3岁以下他们交流得很好,但是一开始进行母语教育之后,他们就交流不了了。所以,人类本质在天生上有一种冲破一切的想象和动力,这是艺术的源泉。而AI是代码、计算、统计、规律,因此,AI跟我说的这中间有一个差距,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艺术家个性保存的最根本的原因。经典哲学有三个问题,大家都知道。经典哲学遇到了一个挑战,我们对终极的追究和认证过程交给了两个分支,一个是交给了艺术家,就是小孩子分不清真假的直觉它只把物质的本质,一个是交给了科学家,科学家用他们严密的计算、推理、考证,完成哲学论证的过程,因此,现代哲学是艺术和技术的结合。

黄建新(图源:上海电影节官方)今天我特别高兴的地方就是艺术和科学的结合,科学家和我们搞艺术家坐在一起,这样人类就会出现哲学意义上一个崭新的阶段。现代哲学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空间——它是包罗万象的。这给我们指明了一个方向,在这个方向的指引下,其实人类最初的创造力、想象力会得到证实。因此,跟AI关系上,我们应该把它看成是人类的意识外延的一部分,而不能成对立的。岁数大的人容易固化思维,可能我们很容易一上来就想给AI下结论,你是什么、你不是什么。我曾经问过很多科学家,能下结论吗?他们说不能,我们只是提供了模型。相反的是,我们这些人爱下结论,说它是一个工具或者是一个什么,为时过早。河森正治让我很担心的一点是,大家会用AI做成很雷同的东西。我觉得我们要多想想AI能够做出什么好玩、有意思的东西。我们不需要寻找一个AI的正确答案,CG技术使用之后,真人电影和动画电影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我常常思考的是,动画跟真人电影的区别是什么?我觉得可能真人的演员,还是会随着时间过去年纪增长,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我们用动画创造出的角色,他们会超越时间,无论什么时候他们都是历久弥新的。

河森正治(图源:上海电影节官方)我现在很希望的一点,是怎样能够创造出没有看到过的角色形象。我们之前都是用人工手绘,很多画师都是设计一些比较好画的形象,现在可以用AI技术让它呈现很多选择、很多独特的设计,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做调整和修改,这个也是我正在尝试的。王红卫当人工智能作为工具,去使用的时候,它对科幻电影创作是否有帮助。但是更有意思的,更开阔的前景是,当人工智能作为人类的现实,出现在人类社会或者改变人类社会,这个会不会对于电影题材和故事带来影响。也就是说,它作为表现对象表现手段,这二者之间的关系。1月份我跟郭帆在成都做了一期编剧训练营,总共30篇写的东西里面,涉及到AI的题材,量是非常大的。无论是写地球的事,还是写太空的事,无论是写外部的世界,还是写人内心的某种经历和波澜,好像都离不开AI了,这其实是大家在创作层面,不可避免要来到的一种境地。当它作为题材的时候,它一定会对科幻电影的发展带来影响,但还有另外一方面,因为我们谈到新质生产力、科幻新视野,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只把人工智能和科幻电影创作这两件事连在一起,可能对于人工智能带来的改变,无论是工具性,还是对象性,都太狭窄了。我们把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技术更新,以及现在所有的受众,对于娱乐方式的新的需求相结合,很可能会催生一些全新的叙事艺术、叙事体验、场景体验的艺术,那个东西可能跟既往有关,也可能跟既往完全不一样,可能跟游戏和所有的这些沉浸式体验更相像,包括特效。我总结这些对于电影的威胁、替代、更新,不管用什么词儿,但是它不像现在我们整天看的短视频已经碎片化了。一个AI的生产力,它能够实现那种全新体验模式的可能性。霍廷霄现在这两年,尤其是谈到数字资产,虚拟拍摄,美术前置,把原来的滤镜换成LED,对于未来的美术人,所谓的大美术时代越来越重要。现在谈科幻,是基于幻想,技术再有什么变化,也是需要你整个视觉体系来完成的。我们讲好中国故事,中国五千年文化的传承、历史渊源,怎么样做的很有意思,其实是需要一代代更新创新的,包括在我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新。今天大家都在思考的是,究竟中国电影怎么走出国门?怎么从大国变成强国?科幻电影在中国是新兴的产业,在美国好莱坞是很多年的产物,国内的科幻电影就是《流浪地球》。但我们找到了自己科幻电影的“根”,不学好莱坞。我想未来中国电影、科幻电影的探讨,交给年轻创作者,产出更好的科幻电影的幻想,指日可待。王晋康从创作上说,我觉得还是要和人工智能分开,只能把它作为一个工具,如果这个时候用人工智能来代替创作,就类似于“抄袭”。这有一个悖论,比如说,我们既要让孩子们尽早地接触人工智能,又一定不能用人工智能代替人做作业,这是完全矛盾的。董润年我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发现现在的学生很明显的一点是——以前我们自己学编剧的时候,要知道潜台词,知道话背后的意思,但现在很多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他们说话是没有潜台词的意识的,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直接表达出来。我有时候很客气地表达了一个隐讳的意思,他确实不理解,思维方式、情感方式都不一样了。包括互联网短视频的流行,大家对于情感情绪刺激的频率和直接的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董润年(图源:上海电影节官方)这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电影创作,包括AI人工智能的创作。因为,AI人工智能在互联网上学习知识的时候学习人类情感的时候,他接触到越来越多年轻人表达的思维,都会让它产生一定的变化。我们一方面在讨论人工智能对电影的影响,一方面要思考整个互联网合众为一的趋势,对于艺术本身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我们自己做艺术创作、科学研究,目的都是想模拟这个世界,想模拟寻找,通过模拟、虚拟的方式来寻找探索找到存在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但是模拟的方式如何变,思维路径如何变对于我们的结果都有影响,我其实挺同意王晋康老师的观点,我认为通用人工智能一定会出现,一定会产生它对于世界的认知,我们提供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素材、养分的作用。戴勃从技术角度来看,现在AI的发展可能是以“天”计,每天都会有新的变化,往往它的技术迭代很集中。我们都不敢睡觉,可能是每一周、每一天起来之后就会有新的变化了。、所以,它的迭代速度是非常难预测的,但是我可以讲一下我自己的期待和理解。我们会希望AI是一个数字世界的模拟,其实就是之前大家常说的“元宇宙”概念,大家能够摆脱现实世界的东西,比如说时间、肉体等等。落实到电影上,一部电影制作周期非常长,成本也很高,所以大家限制了那一段时间的想象力。AI有没有可能让大家不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可以很快的把自己的想象或者创作欲望,想表达的东西,更快地传递给不同的人。最后我认为AI确实服务于我们,用平均的水平,可能对小朋友能够更快地找到定位,更快地有知识储备。但是最前沿的不管是艺术、技术,最终还是希望人来做的,之前的技术途径、艺术的表达,最终都是靠人做的。我今天的启发很大,我也觉得有比较强的责任感、压力感,大家确实对于AI期待非常高,对于AI来讲也是非常好的机遇。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实质性地推进并兑现它的潜力,而不是说大家讲完以后变成了泡沫破碎了,这很重要。

科幻电影的生产周期尤其漫长,在国产科幻电影正处孵化过程中的年份里,有上影节科幻电影主题论坛这样的场合来让外界了解到头部从业者们正在如何与最新的技术相处,是一扇不可多得的窗户。透过2024年的这扇窗,我们看到从业者对AI的全面拥抱,也看到他们在艺术创作上的高要求与不满足,更看到艺术家与科技工作者弥合信息差的努力。相信在这样的趋势下,科幻艺术创作会沿着正确的道路走下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飞的”真的来了
- 联合国拨500万美元用于缅甸救援
- 缅甸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644人

- 时代中国控股:预计2024年度股东应占净亏损160亿-175亿元
- 赴港上市持续升温,前2个月共有41家内地企业递交上市申请

- 罗马帝国的建立者,元首政制的创立者
- 核反应中,轻核结合成较重核的过程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