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党成孝读《哈耶克论哈耶克》|哈耶克的观念铁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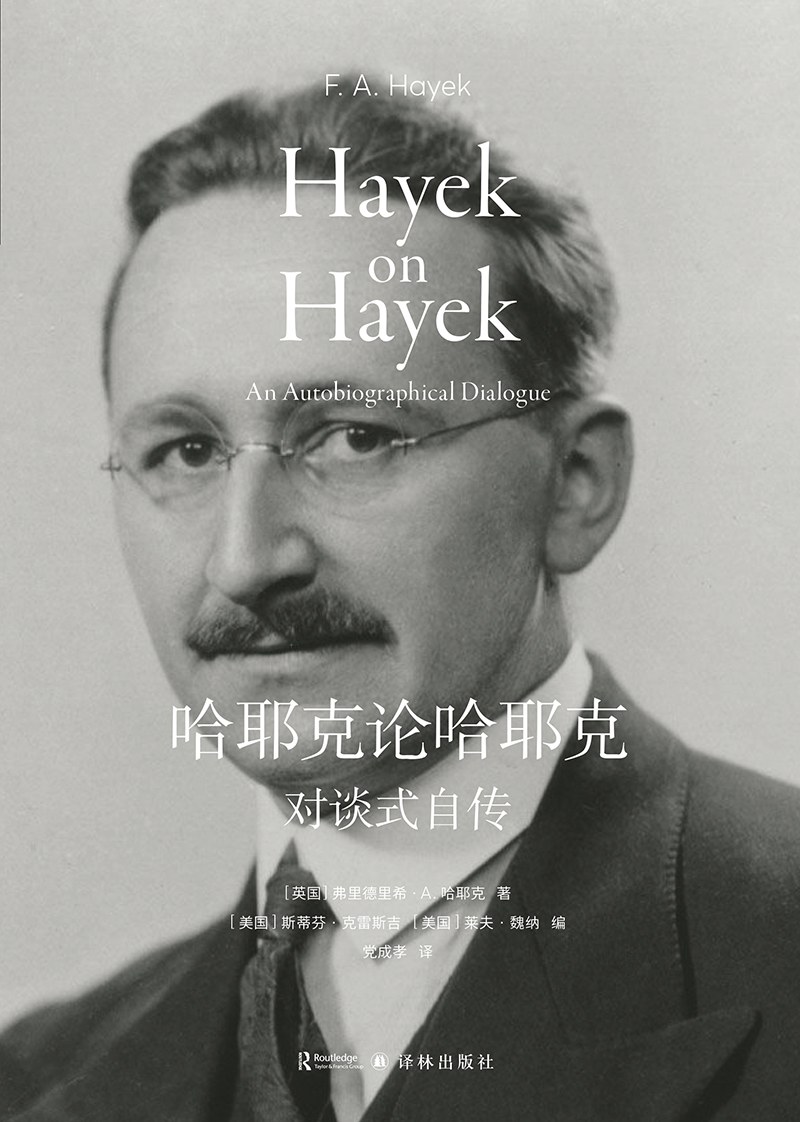
《哈耶克论哈耶克:对谈式自传》,[英]弗里德里希·A. 哈耶克著,[美]斯蒂芬·克雷斯吉、[美]莱夫·魏纳编,党成孝译,译林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288页,69.00元
一
1974年,当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哈耶克时,颁奖词对他在“货币理论和经济波动方面的开创性工作”的称赞只有寥寥数语,相反,更多肯定则指向三十年代以后他“对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之间相互关系的洞察性分析”。因出版《通往奴役之路》而在经济学界名誉扫地的哈耶克就此重回公众视野。这是战后故事转折的一个预示: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3年的彻底崩溃,以及一个同时面临通胀和失业的欧美世界,都使凯恩斯主义的药方信誉扫地。而哈耶克对完全市场作为自由社会必要基础的辩护则在即将到来的、席卷全球的改革时代重新受到肯定。故此,连其支持者后来也乐于承认,“哈耶克的最终胜利是由文化和政治变革而非理论论证的说服力所推动的”(17页)。这造就了哈耶克的预言者身份,并将他框定在了二十世纪理论与现实缠绕的图景中:他所观照和提出的问题与这一世纪前半叶政治与社会体系的运行相关,而对问题性质的哈耶克式认识则要延宕到战后、在一系列政经实践失败后才成为欧美世界的共识。
然而,倘就其主张与现实的交错而将哈耶克完全归于二十世纪,则不仅对他所倚赖的智识和趣味传统熟视无睹,而且必定要对其后期作品向大的思想传统回归的尝试加以忽略。个人经历的影响,使哈耶克的研习倾向以及研究视野,理所当然地站在二十世纪专业化倾向的对立面上。他的维也纳岁月中,那种“不必局限在自己学科之内”(72页)的修习方式,“伴之以超乎寻常的智识刺激”(74页),读之恰如阅读马克斯·韦伯近半个世纪前经历的海德堡岁月。这是十九世纪洪堡的柏林大学模式在二十世纪的余晖,背后是作为知识聚集地、其蓬勃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一路持续至二十世纪的维也纳。另一方面,维也纳时光中对他有重要影响的老师们,身上多带着十九世纪的知识风格和品味。以哈耶克的经济学启蒙老师卡尔·门格尔为例,他对竞争性市场中价格作为主观评价过程的无意识结果的阐释,完全是在同十九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的观念对立下做出的。林林总总的经历决定性地造就了哈耶克对前一世纪的偏爱,他钦慕阿克顿勋爵,讽刺凯恩斯对十九世纪经济史的漠视和无知,并曾自诩在心理学理论上,他“是一个来自十九世纪的幽灵”(21页)。这样的哈耶克不可避免地带着十九世纪的观念遗存来审视二十世纪。
更重要的是,哈耶克并不意图面向未来做出任何论断或预言。促使他在四十年代从研究货币和资本理论转向研究理性滥用问题的动机,是对当时整体状况的回溯性追问:“启蒙运动在十八世纪所允诺的、伦理学与物质层面在十九世纪的进步,怎么会在二十世纪导致了如此野蛮的冲突?”(21页)故此,对二十世纪政经实践的评述与介入尽管是哈耶克最为人所知的部分,却是他观念构成的起点。从《科学的反革命》开始,一项按迹循踪式的工作即在有意识地沿着两条线索展开。一方面,他将造成二十世纪政治灾难的建构理性的起源,指向十九世纪法国“科学主义”的代表圣西门和孔德等人,而后更是上溯到现代思想开端的笛卡尔以及卢梭那里。另一方面,哈耶克取道托克维尔和阿克顿勋爵,将与之对应的自发秩序传统一路追溯到苏格兰启蒙运动(参见《致命的自负》第一、第五章及补论)。如《哈耶克论哈耶克》一书编者所提及的:“哈耶克通过亚当·斯密、大卫·休谟和亚当·弗格森把观点的起源上溯至伯纳德·曼德维尔那里。”(31页)这个分野被进一步描绘为“英国的思想”(《通往奴役之路》第一章)与大陆思想(“德国的思想”以及“法国启蒙运动传统”)的对立。他曾借用桑巴特的表述,将其形容为“英国商业文明”和“德国英雄文化”的思想内核间的冲突(《通往奴役之路》第十二章)。而在其观念划线中,霍布斯和密尔几乎被他驱赶到了大陆阵营,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则与一众英伦思想家并列,成为其观念盟友。由此,现代思想从源流上被一分为二,一道哈耶克式的思想史的观念铁幕就此被构筑。
二
这道铁幕是如何展开的?
哈耶克以“个人自由”,即免于干涉的或消极自由为锚点,视其为文明进步的基本动力。他的现代思想史观念轴线,就围绕着对个人自由的申张与压制划开来。体现于二十世纪两大政治实践中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普遍军队化,是个体自由在十八世纪以后的进展所造就的,同时构成其反噬的极端形态。根本上说,以工业技术的进步为表征,个体自由导致的个人活力解放造就了物质境况的改变,使人产生了对理性控制和改善命运的无限信心。因此,“自由主义的衰退,正是它的成功所造成的”(《通往奴役之路》第一章)。
哈耶克觉察到,削弱个人自由的二十世纪实践有着共同的德国起源,它以对理性的肯定为标志,体现为人为制度重构的雄心:“人类有意的设计会按照预先构想的模式来改造社会。这种状况所激发的社会野心和政治野心,受到当时德国流行的哲学倾向的有力支持。”(《自由秩序原理》第十六章)其典型是十九世纪德国实践中,以公共行政的法制化和规范化为目标的“法治国家”(Rechtsstaat)构想将法律执行视为行政权唯一的正当职能,与管理科学相配合,催生了对行政活动进行司法监督的专设机构,即行政法院的产生。后者自成为行政机构的一部分起,就在法律实证主义的影响下,日渐沦为纯粹授权性程序的空洞形式,从而使政府意志的贯彻愈发不受限制,最终表现为对个体的压制。
而如果说德国提供了建构理性的实践样式,那么法兰西思想则为此负有观念和理论层面的责任。孔德提出以理性能够证实其结果的道德规则来替代“启示的伦理学”,构成理性滥用所产生的“科学主义”的直接结果。再向前,“在十七和十八世纪的一些法国思想家中间,出现了若干重要的发展,它们结合在一起,开始向扩展秩序的中心价值和各项制度提出了有效的挑战”(《致命的自负》第四章)。这其中又以卢梭的“人民主权”观念为代表。“人民主权”赋予多数人统治以无限正当性以及不可限制的权力,就此使制度脱离了保护个人自由的范畴,成为共同体意志的表达和护卫:“卢梭让人们忘记了,行为规则必然是限制性的,它们的产物是秩序。”(同前)解除限制的“人民的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所实现的是集体或政治意义上的自由,而个体得到的只有义务。
这种对集体无限自由的主张被哈耶克视作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传统影响下“高卢自由”的表现,它根本上动摇了伴随私有财产权的出现而得到保护的个人自由。后者肇始于雅典与罗马的制度精神,在现代则体现在英国的实践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表述中,构成“盎格鲁自由”的内核。这是贡斯当古代人和现代人自由区别的重述:悲剧性的法国大革命的实质是时代措置式的对古代人自由,也即政治自由的追求。只是在哈耶克看来,这种政治自由的源头并非在雅典与罗马共和制中,而在其制度与法律始终着眼群体性目标的斯巴达。于是,自十八世纪“高卢自由”兴起而后的脉络,“基本上是法国式的政治自由的观念实际上渐渐地取代了英国的个人自由理想”(《自由秩序原理》第十一章)。
在另一观念线索上,随着私有财产权的建立得到确认的个人自由观念往往“把自发性和没有强制看作是自己的精髓”,故而“赞成有机的、缓慢的和半意识的生长”(《自由秩序原理》第四章)。自发和建构的矛盾,在现代表现为组织的自然演化和契约论之间的差异,后者在“自然状态”的假设之下以人为契约将个体捏合为国家,也预设了共同体意志及其表达的优先性。而另一传统下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则把对共同体优先的否定表达为对个体激情的接纳,他们关心的是“人性中最普遍的原动力——爱己(self-love),是如何通过本是以追求自己的利益为目的的个人努力而被导向促进公共利益上面去”(同前)。在复杂的社会交往脉络中,自利的个体行动与群体层面非意图结果间的参差,往往是秩序演化的应有之义。就此而言,即便申述个人自由的思想家也并不完全在“盎格鲁自由”之列。英伦的功利主义者如约翰·密尔以是否影响他人作为“群己权界”的划定,必然滑向国家权力的普遍介入;以后果论证道德也将导致法律体系及其制度的完全重构。其对自发秩序的破坏最终将反过来不可避免地损害作为土壤的个人自由。
三
无可否认的是,尽管对二十世纪政经实践的反思只是这道观念铁幕的构成性起点,但它却作为一种源头性的经验浸润了哈耶克回溯性思考的方方面面。无论战争中的伦敦岁月,还是战后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基于这种反思而对人之限度和个人自由脆弱性的觉察与警醒,使哈耶克试图在异时异地同一切形式的相反实践斗争。对理性突破限度的肯定,必然会破坏理性得以滋长的自由环境,因此从思想史角度尝试将个人自由脉络与启蒙的理性主义传统完全撇清,就成为捍卫前者的重要奠基性工作。
不过,目睹极端实践产生的忧惧基调成为护卫个人自由的压倒性动机,这一定程度上使哈耶克忽视了被他放置于观念铁幕另一端的、归为建构理性之下的诸多理论和概念之间的差异性。他并未试图论述“高卢自由”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一条严密的反对个人自由的逻辑线索,反而将道德功利主义、“人民主权”观念以及契约论甚或绝对主义不加区别地放置在一起,似乎忽略了即使以个人自由为参照,它们各自对哈耶克固守之物的背离并非等距。而当他仅以为国家的广泛介入留有可能契机而批判功利主义时,我们似乎看到哈耶克自己在捍卫个人自由方面表现出的绝对化倾向。这种倾向体现为一种“国家主义”批判的泛化:他甚至将集体主义追溯到国家理由学说,宣称“国家理由(raison d'état)是集体主义道德最明确的表述,它的唯一界限就是利害权宜”(《通往奴役之路》第十章)。
反过来,将“盎格鲁传统”下个人自由的线索以私有财产权之由回溯到雅典和罗马,以便拉长这场斗争的历史时间线,似乎也颇颠覆惯常理解。芬利曾将希腊人的经济模式视作嵌入式经济,以为其追求的并非经济利益最大化,相反,经济追求附属于在城邦公共领域对政治和社会地位的追求。因此,希腊世界的私有财产权是否如同哈耶克所言“助长了私人目标多样化的秩序”(《致命的自负》第二章)是存疑的。如同汉娜·阿伦特看到的,古典世界的私有财产权意在使人能够从必然性中得到解放,从而投入公共生活,故而私有财产是作为公民身份的奠基而存在的,它所护卫的是政治而非个人自由。这与哈耶克意义上的私有财产在目的上几乎有着云泥之别。
另一方面而言,哈耶克的论证似乎在诸多面向上都与被他归为建构理性阵营的观念存在某种亲缘性。例如,尽管强调个人自由的天然正当性,认为“在事先确定自由之效果将有益于人的前提下赞同的自由不是自由”(同前),但他对个人自由的辩护却时常陷入他所批评的功利主义论证中。特别是当他在辉格史学的进步观念下考证自由的变迁史时,几乎难以避免从对文明的推进这一视角阐述个人自由的正当性。此外,哈耶克常以有机体来拟喻存在自发演化机制的社会,但同时又决然拒绝承认民族或民族国家作为有机体的抽象凝结而存在的正当性,后一种观念为不少被他归为建构理性的十九世纪有机论者所持有。他唯着眼于讨论作为演化后果的风俗、习惯及其所带来的微弱的民族特性,而将超出这个界限的存在一并视为人为建构的结果而加以刻意回避,也就由此在国家问题上显得与他所批评的观念界限不明。“政府实施的强制,应非人格化,并受制于抽象的一般原则”,就此,“如果‘统治’就意味着,强制贯彻不考虑特殊情况之条件下而被制定出来、对一切同样的情况都适用的普遍规则,在这种意义上公民可以被统治”(《自由秩序原理》第十章)。哈耶克对公共权力边界的描述,与卢梭的“人民主权”背后的“普遍意志”如何以法律形式运转的描述似乎并无本质差异。
诸多颇令人生疑的部分,或许只有在对哈耶克生平的重新关照下才能得到恰当的解释。他在自传性对谈以及论辩中反复提示的是“危险”及其可能的后果。的确,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政治灾难以及战后长久的分裂现实,都促使他站在一个更为节制与个人化的自由立场上,从而难以诉诸任何抽象的总体性原则;而同时对这种立场的捍卫在现实的驱赶之下,又显得颇为急促与武断。对“危险”的意识始终构成他的基本底色,也或许是这道观念铁幕如此构筑的源由。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