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两种不同的观念体系推动引导着西方文明
拉斐尔·桑蒂(Raphael Sanzio)是个乡下男孩,后来继承父亲的衣钵成了一名画家。每个人都能看出他身上特有的那种天资卓越的艺术才能——借用与他共事的画家瓦萨里(Vasari)后来的话说,他这方面的才能就像神灵一样,世间罕有。十六岁那年,受父亲鼓励,拉斐尔离开那个发达的家乡小镇——意大利的乌尔比诺,和翁布里亚艺术大师彼得罗·佩鲁吉诺(Pietro Perugino)一起工作。后来,他又搬到美第奇家族统治的城市佛罗伦萨。
在那里,拉斐尔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场学术和艺术的盛宴。他认真研究米开朗琪罗和莱奥纳尔多·达·芬奇两位前辈的作品。根据瓦萨里的描述,这两位艺术家让拉斐尔产生了“更加强烈的钻研欲望”,并由此将自己的技法提升到近乎两位前辈的高水准。然而,1508年,拉斐尔的艺术生涯发生了重大转折。当时,他的乌尔比诺老乡、建筑家布拉曼特(Bramante)来信,邀请他到罗马为教皇服务。
1508年,罗马是当时整个西欧心驰神往的城市。这座辉煌的城市之前是一个古老帝国的首都,如今成了当代艺术的最高殿堂。教皇尤利乌斯二世(Pope Julius Ⅱ)五年前登上了圣彼得宝座,决定按照心中的宏伟愿景重建这个城市,他想在自己这块领地上复活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经典风格。他委托建筑家布拉曼特设计新的圣彼得大教堂,这个大教堂要比任何一座基督教堂都更加宏伟气派,光芒四射。
不过,在尤利乌斯教皇的训谕之下,布拉曼特还主持了一系列其他的艺术项目。1508年的罗马吸引了大量投资,也满足了人们对宏伟艺术作品的狂热想象。对于拉斐尔这样的天才来说,这意味着一个又一个施展才华的绝佳机会。
布拉曼特和教皇网罗意大利最伟大的艺术家。拉斐尔抵达这座“不朽之城”时,米开朗琪罗刚刚竖起脚手架,准备在西斯廷礼拜堂的穹顶上创作一系列壁画。
这个忧郁的佛罗伦萨大胡子艺术家刚刚三十四岁,年富力强,正处于创造的巅峰时期。当米开朗琪罗全身心地创作教皇陵墓里四十个真人大小的雕像时,教皇中断了这个项目,让他去绘制教堂穹顶壁画。那时米开朗琪罗还有些愤怒,但他没有想到他即将创作出最伟大的杰作;他也没有意识到,布拉曼特介绍的这个身材单薄的乌尔比诺年轻人将开创西方文明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正如他自己创作的西斯廷礼拜堂穹顶画一样。
除了这个脾气暴躁的佛罗伦萨人,为尤利乌斯教皇效力的艺术家还有卢卡·西尼奥雷利(Luca Signorelli),拉斐尔的老师佩鲁吉诺,神秘莫测的威尼斯人洛伦佐·洛托(Lorenzo Lotto),以及那个性格古怪、因为让人反感的性嗜好而得绰号“鸡奸者”的伊尔·索多玛(Il Sodoma)。不过,与这些喜怒无常甚至有点狂暴的艺术家不同,拉斐尔性情温和,特别容易共事。他早年在乌尔比诺乡间的生活教会他如何与人交朋友,如何影响身边的人。在与米开朗琪罗就西斯廷礼拜堂的穹顶壁画进行激烈谈判之后,教皇很乐意和一个风度翩翩、个性迷人的人打交道。
可是应该把这个年轻人安排到哪儿呢?尤利乌斯教皇想到了梵蒂冈宫殿的罗马教宗公寓。他讨厌这些东西。里面引人注目的镀金装饰和陈旧而毫无生机的壁画,除了让他想起前任——恶名昭彰的亚历山大·波吉亚(Alexander Borgia)教皇及其道德败坏的孩子恺撒(Cesare)和卢克蕾齐娅(Lucrezia)之外,别无用处。尤利乌斯已经让索多玛、洛托和其他艺术家开始重新装饰第一层和第二层的重要房间。不过,他对拉斐尔还有别的安排。
他想到的是宫殿的第三层,那里有超过五百平方英尺的墙面需要装饰。这个楼层有高拱穹顶和一套几何图案组成的马赛克图案,剩下的就只有一些穹顶壁画作为装饰了,他想把这些壁画替换掉。于是,在1508年冬天的某个时刻,教皇、拉斐尔和布拉曼特徘徊在这座宫殿里,身边是大批艺术家及其助手,他们在辛勤劳作,手里拿着画笔和抹子。站在寒冷的空气中,他们可以看到自己口中呼出的白气。他们的声音在空旷的大厅中回荡。
尤利乌斯教皇也许会指着这些空白的墙壁,自豪地说:“此处将会是我们的私人图书馆,请给我们一个与这一意图吻合的设计方案吧。”
说实在的,那时拉斐尔的壁画创作经验并不算丰富,无法构想出一个综合的艺术方案填满如此大的空间。但尤利乌斯懂得如何驾驭人,他了解艺术家。他感到,如果让这个靠个人魅力而非平淡的圣母和圣子像出名的乡下小伙放开手脚去装饰罗马教宗的图书馆——尤利乌斯教皇精神生活的核心部分,将会产生一件杰作。
事实证明,教皇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从西斯廷礼拜堂的墙壁上看到这件杰作。就像米开朗琪罗的穹顶壁画那样,拉斐尔的签署厅(Stanza della Segnatura)壁画就是他在艺术技巧和理解力上的巨大成就。用瓦萨里的话说就是,“拉斐尔这幅作品中展现的卓越天才,清晰地表明他决心成为与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不分伯仲、无可争议的文艺复兴绘画大师”。
我们知道,拉斐尔的签署厅壁画的完整艺术计划——寓言式地展现哲学、神学、法律和艺术,并不是拉斐尔本人草拟的,更可能出自教皇的图书馆管理员之手,当然也离不开人文主义者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的大力相助。但不管如何,拉斐尔借助自己在生动描绘戏剧性场景上的天赋完成了这件了不起的作品,壁画的核心部分处处体现着这种天赋。《雅典学院》是拉斐尔在其艺术生涯的鼎盛期创作的鸿篇巨制,它总结了古代世界对西方文明的重要贡献,而那个时代贡献最为卓越、影响最为深远或许也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两个人,正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拉斐尔《雅典学院》
这幅壁画填满签署厅的整面墙壁。它以比真人更大的尺寸,用建筑方面的安排表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无与伦比的光辉,其他古希腊哲学家围绕在他们身边。
柏拉图站在稍微靠左的位置,他的手指向天空,指向一个超现实的世界。他旁边站着他伟大的老师苏格拉底,下面坐着数学家毕达哥拉斯。与柏拉图并肩而立的是他最亲密的门徒——他的外甥斯珀西波斯(Speusippus)和色诺克拉底(Xenocrates)。此外还有一些古代思想家,他们都强调直觉、情感和思辨哲学的重要性。这些人包括柏拉图的前辈阿那克西曼德及其对手色诺芬和伊壁鸠鲁主义的奠基人伊壁鸠鲁。学者们在上面发现了普罗提诺,他是新柏拉图主义之父。此外还有阿拉伯哲学家阿维洛伊(Averroës)和一名异教徒修女希帕蒂娅。坐在他们脚边的是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而上面画的其实是米开朗琪罗。在这些人的头顶矗立着艺术和预言之神——阿波罗的雕像。
柏拉图的对面,也就是他的右边,是一个活力四射的大胡子人物——亚里士多德。这幅亚里士多德半身像出自拉斐尔本人,准确逼真,栩栩如生。亚里士多德旁边是古希腊时期科学和理性思想的一些代表人物。有数学史家欧德莫斯(Eudemus),植物学之父、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此外还有深受亚里士多德影响的古代亚历山大学园中的科学家们:天文学家托勒密、几何学家欧几里得。这两个人物的肖像是拉斐尔的良师益友布拉曼特的手笔。对此,瓦萨里说:“描绘得如此生动逼真,看上去仿佛是活着的。”此外,还有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有些人认为实际上画的是达·芬奇,拉斐尔快完成这件作品时,达·芬奇来到了罗马),犬儒学派的第欧根尼(拿着他那著名的乞钵),以及其他一些难以辨认的人物。拉斐尔在这些人的头顶上放了守护神雅典娜的一座雕像。众所周知,她是理性和智慧之神。
拉斐尔的画作用视觉形式呈现了皮科和文艺复兴继承自罗马政治家、思想家西塞罗的一个观念: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作为西方理性的两大滥觞,是同等重要的智者,他们的思想涵盖所有知识领域。这个历史观点不仅贯穿文艺复兴,还渗透到迄今为止数个世纪的西方教育中。传统教科书说到“古希腊人的智慧”时,实际上指的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智慧。此外,在那些频繁提及“古典心灵”和“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权威学者那里,这两个说法仿佛是可以相互替换的。
现在我们可以深入考察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雅典学院》这幅壁画不仅总结了古代哲学和现代思想的先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精神遗产,也刻画了西方文化在其开端处的那种双重性格。
一方是理念论者柏拉图,他成了西方理念论和宗教思想的精神指引。拉斐尔在柏拉图的手上放了一本《蒂迈欧篇》(Timaeus),这本著名的对话录在过去千百年来激励了无数神学家、神秘主义者和超自然的信徒。
另一方是亚里士多德,这位崇尚科学和常识的哲学家用手指着大地,与柏拉图用手指天的形象形成鲜明对照。在亚里士多德的手上,拉斐尔放了一部《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用这部旷世名著改写了天主教会对人类道德的理解,西塞罗则相信它是回答自由生活和自由社会如何可能的最佳指南。即使经历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仍然对现代人理解政治、道德和社会有决定性的影响,正如他仍被尊为现代科学之父。
神秘主义与常识,宗教与科学,理念论与政治学——两种对照鲜明但都有深远影响的世界观在《雅典学院》中得到了极其生动的隐喻性呈现。那些相互匹敌的世界观实际上塑造了我们的世界,从其诞生的古希腊时代到21世纪的今天,它们为争取对于西方文明之灵魂的主导权而展开了长达两千多年的斗争。
由此看来,西方伟大的思想家、神学家、科学家、艺术家、作家甚至政治学家不约而同地发现,自己要么属于柏拉图阵营,要么属于亚里士多德阵营。这两种不同的观念体系及其代表的通往智慧的两种道路之间的对垒和竞争,贯穿了两千四百多年的历史长河。在历史的某些关键点上,不少思想家试图将这两种思想整合到一个统一的体系中。但是每一次,那些古老的对抗都会重新出现。交锋世代不息。
一条道路由柏拉图开创,用艺术家和宗教神秘主义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它发现了思辨和沉思的境界所拥有的强大力量,寻求人类梦想和欲望的释放。
亚里士多德则相反,他用一双冷静的科学眼睛观察现实世界,揭示出逻辑和分析的力量是人类获得自由的有效工具。“事实是我们的起点。”他这么说,而且是当真的。
几个世纪过去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念从彼此冲突的两个方向推动和引导着西方文明。
这场斗争深刻地塑造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传统文化,同时对古罗马基督教的勃兴起了推波助澜作用。以中世纪为例,这场斗争不仅塑造了圣奥古斯丁和圣托马斯·阿奎那相互对立的世界观,还对当时其他伟大人物的著作有着渗透性影响——从彼得·阿伯拉尔(Peter Abelard)、阿伯特·苏歇(Abbot Suger)到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首次文化接触有决定性影响。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的碰撞在沙特尔主教堂和巴黎圣母院的石头上仍然清晰可见。它首次催生了关于民族国家的观念,中世纪的罗马教宗几乎因此覆灭。
这两个古代天才持续不断的斗争实际上激发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政治、艺术和科学等领域的新思考,启发了达·芬奇、马基雅维利、马丁·路德和莎士比亚等伟大人物。这种碰撞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画家,托马斯·莫尔爵士会写出著名的《乌托邦》,而马基雅维利会写出《君主论》,以及为什么宗教战争的暴力冲突客观上有助于近代科学革命的产生。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两派之间的战火直到近代仍燃烧不息,深刻影响了以下人物的观点:伽利略、约翰·洛克、艾萨克·牛顿、路易十四、亚当·斯密、托马斯·杰斐逊和让-雅克·卢梭。它在浪漫主义时代持续发酵,在卡尔·马克思、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和弗里德里希·尼采等人的思想中闪耀光辉。它甚至为现代科学的发展和20世纪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埋下了伏笔。此外,它还决定了我们如何思考人类本性以及全球变暖。
英国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曾经说过,每个人要么生来是柏拉图主义者,要么生来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事实上,不管是柏拉图主义者还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就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拉斐尔《雅典学院》中的人,要么站在柏拉图一边,要么站在亚里士多德一边,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最后,正是这两种不同世界观之间的持久张力使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包括它之前的文明和与它相当的文明——迥然有别。它也告诉我们,为什么西方文化具有如此绵延不绝的生命力,为什么西方文明总是不时地在地球上其他文明面前呈现出一种令人困惑的“两面怪兽”形象。此外,它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某些年代西方人那么有同情心,那么富有远见和创造力,而在另外一些历史时期又表现出强悍、冷静和专制色彩——甚至可能同时表现出这两个方面。
受这两种世界观影响的科学技术挽救过数百万人的生命,当然也曾在轻轻摁下一个按钮时杀死过成百上千万人。受它们影响的神学观念催生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品,同时将无助的受害者送上了火刑柱。受它们影响的意识形态创造了世界上最自由和最有活力的社会体制,同时催生了人类历史上最残忍野蛮的暴政。
为什么会这样,上述大多数现象——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可以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永恒斗争中得到解释。
现代读者身上一般都有互联网时代的深刻印记。他们对层出不穷的新鮮事物早已习以为常。对他们来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似乎只是两个模糊、遥远的人物。在政治正确的时代,他们成了典型的“已故白人男性”,是奴隶制和压迫女性的辩护者。
本书要展示的正是那个活在我们身上也活在我们周围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的影响力简直无与伦比,不仅反映在每个具体的活动中,也反映在每一项抽象的制度设计中,包括我们的大学教育体系、实验室制度,我们的政府机关以及互联网。他们甚至帮助我们最终把人类送上了月球,探索人类内心最深处的秘密。与一些现代性的误解相反,他们的影响实际上有助于我们废除西方乃至全世界的奴隶制度,赋予女性平等权利。
本文经出版方授权摘自《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西方哲学文化的源与流》一书,原章节名为《开场白:柏拉图学园》,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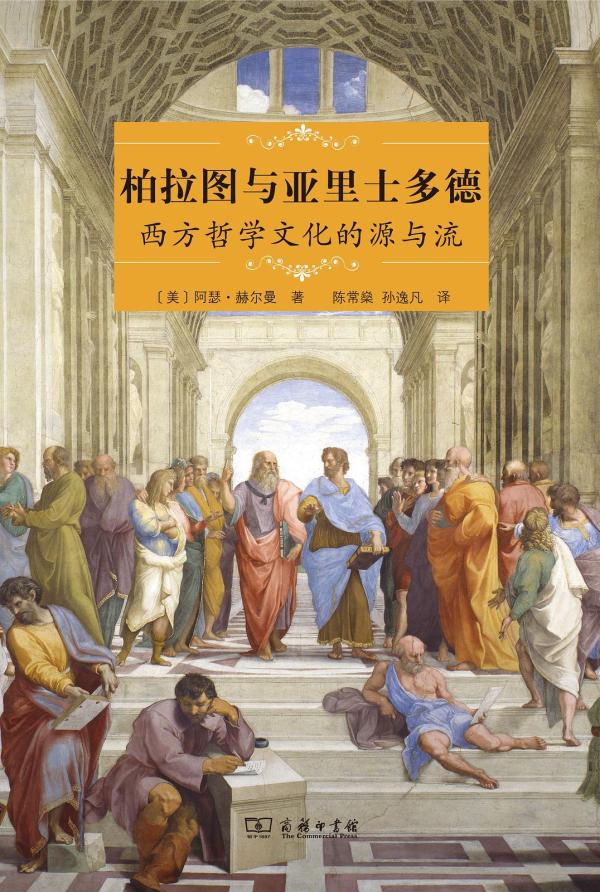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西方哲学文化的源与流》,【美】阿瑟·赫尔曼/著 陈常燊、孙逸凡/译,商务印书馆,2024年4月版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