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战争、法律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1914年7月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变革开始阶段的结束。与18世纪中叶以来的其他大规模战争一样,它的蔓延无法预测,破坏(有时甚至摧毁)了政治秩序,加速了多变的思想的传播。在这一过程中,与过去的许多战争一样,它也促进了新宪法的传播,只是方式截然不同,规模也史无前例。
出现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与漫长的19世纪60年代相比,这次甚至有更多国家参战,世界上的主要帝国都被拖入战争。因此,这场战争中最为有名的杀戮场,蜿蜒穿过法国、卢森堡、比利时的西线战场,只是整个战争地理范围的一部分。以英国、法国、俄国等为一方,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等为另一方的战争,将风暴带进了各国的殖民地和卫星国。实际上,这意味着整个非洲(除了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中东、加拿大、中东欧大部分地区,以及亚洲和澳大拉西亚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受到了影响。各帝国对其他大陆的干涉进一步放大了这场战争的范围和影响。日本于1914年参战,因而战争状态必然蔓延到中国;而美国于1917年参战,也令它的正式与非正式的殖民地——菲律宾、古巴、夏威夷、中美洲大部分地区——卷入其中。甚至在此之前,这场战争就已波及南美洲和大洋洲,智利沿海和马尔维纳斯群岛发生了大战,新西兰则占领了德属萨摩亚。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队新近抵达法国战场的英国士兵正行进在山脊上。
正如拿破仑战争中发生的那样,越来越多的跨大陆冲突迫使主要参战国立刻以比以往更激进的方式招募本土兵员,并从本土中心地带之外获取人力。拿破仑招募的外籍士兵绝大多数来自欧洲;而在一战中,法国则从更远的地方攫取人力。1914年后,法国从其海外殖民地征募了超过50万兵力。英国也扩大了征兵范围。1914—1918年,仅印度就贡献了140万士兵和近50万劳工。其中许多人在印度次大陆家乡之外服役,这改变了战争的特性与文化,其方式仍有待探索和有想象力的研究。从15世纪末以来,各种各样的欧洲人不断通过海路来到印度半岛,在那里战斗。而一战见证了大量南亚士兵和契约仆役前往欧洲大陆,参加战斗和战场工作,这在世界历史上是首次。
一战中还有其他一些标志性的变化。与漫长的19世纪60年代发生的许多战争一样,这场战争中的科技变革导致了死亡率的大跳跃。只是这一次涉及的不仅仅是速射步枪、蒸汽机、电报。1914年之后,作战涉及坦克、潜艇、飞机、机枪、毒气,以及用于协调部队行动的电话和双向电台。加上与战争相关的疾病、饥荒、事故和对平民的屠杀,这些因素可能造成了至少4000万人死亡,还有数百万人伤残,痛失亲友,被迫背井离乡。
英国小说家、政治活动家、未来学家H. G. 威尔斯身材魁梧,绝顶聪明,作品多产,出版作品的速度甚至超过了他勾搭女性的速度。他最初曾支持对德作战的正义性。但是,和平还没有正式到来,威尔斯就承认“旧制度的许多部分”此时“已经灭亡”,因此需要“重建”。他认为,至关重要的是要设计出“让人们在世界大战之后(可能)理解整个人类”的方法。对他和当时其他许多知识分子和政治家来说,这种抚平战争创伤的重建工作和重新评价工作中,一个必要的部分就是建立一个国际联盟,这是一个新的专业机构,将监视、监督全球事务,从而预测、控制、遏止未来的武装冲突。
1918年5月,威尔斯发表了急切而有影响力的论文集《第四年:世界和平的预期》(In the Fourth Year: Anticipations of a World Peace)。他在书中的一节里专门讨论了为这个未来的国际联盟起草宪章的难题。作为可能努力达成的一个范例,也为了吸引美国(由于战争,这个国家变得比以前强大得多)的读者,威尔斯援引了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的成就,“讲英语的智者真正深思熟虑的创造”。今天,这一评论的文化沙文主义气息可能令我们吃惊,但威尔斯的其他设想和语言也值得注意。
这场世界大战的高死亡率、对经济的极端破坏,加上一场瘟疫的爆发(所谓“西班牙流感”,在1918—1920年导致5000万人丧生),带来的不仅仅是悲痛和长时间的阴郁。在各个国家,它还造成了一种有证据证明的迷失感、一种挥之不去的信念,正如威尔斯所说,“旧制度的许多部分”已经消亡,或者变得多余。但是,他关于国际联盟的提议说明,战后的这种忧虑和被迫与过去断绝关系的感觉,并没有延伸到宪法起草上。相反,1919年初,一名身在中国的评论家说:“宪法的起草永无止境。”他还补充了意味深长的评论:“在建立共和国方面,现在有很多活动。”
一百多年前,法国对伊比利亚半岛的军事入侵加速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帝国的瓦解,从而为多个配备实验性成文宪法的南美国家的兴起铺平了道路。类似的大规模战争的模式加速了历史悠久的君主制帝国的消亡,推动1914年之后出现的以共和制为主的国家和宪法取而代之,但这种变化的规模更大,而且发生在不同的大陆。一战之后的这个阶段,君主制更加难以(但仍然不是不可能)与雄心勃勃的成文宪法舒适地并存。
1914年,奥斯曼帝国站在德国一边参战,希望重申在中东和巴尔干半岛的地位。而在战争中成为失败的一方,不仅终结了这个帝国,也终结了苏丹的世袭统治。回望1908年夏季,流亡的康有为已经看到,拥入伊斯坦布尔的群众庆祝奥斯曼帝国宪法的恢复。到1924年,在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又一位出身职业军人的立法者的领导下,这部宪法让位于一部全新的宪法。新宪法的第一条直截了当:“这个土耳其国家是一个共和国。”
霍亨索伦王朝和德意志帝国的1871年宪法,以及哈布斯堡王朝和奥匈帝国的1867年宪法,都在军事失败的捶打中被粉碎了。实力被严重削弱的德国于1919年、国土大为缩小的奥地利于1920年都采用了新的、明确的国家宪法,这两部宪法各是为了建立一个共和国而制定的。奥地利的一些原帝国行省制定的宪法也是如此。例如,捷克斯洛伐克于1918年末宣布独立,到1920年已实施了共和制宪法。
甚至英国,表面上是主要战胜国之一,也是幸存下来的君主制国家,但也被这场战争大大削弱,这也再次影响了新宪法的传播和新共和国的出现。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起就不时兴起。但是,正是因为伦敦被世界范围的战争需求所困扰,所以1916年在都柏林发生的、初期笨拙的小规模爱尔兰民族主义起义才得以升级成来势凶猛、不可阻挡的革命。到1922年,除了北部的六个郡,爱尔兰其他地方都成功脱离了明显不再存在的联合王国。新的爱尔兰自由邦成立,有了一部成文宪法;不过,1937年的又一部爱尔兰宪法才明确宣布这个独立国家是一个共和国。
两年前(1935年),威斯敏斯特议会通过了《印度政府法案》。制定这部法案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安抚印度民族主义者,遏制他们的反抗—这种反抗由于战争的爆发而明显加剧。大英帝国的这部法案没能令任何人满意,很快就被各种事件淹没了。不过,该法案的通过表明,即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安然无恙地存活下来的欧洲帝国,此后也持续承受着压力。《印度政府法案》并不完美,带有帝国主义的偏见,语言明显很节制,但它也是反映战后宪政设计的丰富性、重要性的案例之一。这部法案将延续下去,构成1949—1950年印度独立宪法中三分之二的内容,该宪法是后殖民时代世界上存续最久的宪法,也是为一个共和国而制定的。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摧毁了另一个历史悠久的君主制帝国——俄国,这给后来的宪法造成了与众不同的影响。罗曼诺夫王朝在1905年失败的革命中幸存,并且避开了次年的制宪尝试。1914年之后,情况不同了。无论是传统形式上的俄罗斯帝国,还是罗曼诺夫皇室,都无法承受多次战争失利的冲击,以及这些战争对业已运行不畅的经济的破坏。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1905年革命期间发表了一本关于宪政体系的小册子。1917年,搭乘一列闷罐车,他从流亡地瑞士回到俄国。正如列宁援引卡尔·马克思的比喻所做的贴切评论所言,战争“推动了历史,以火车头般的速度前进”。当年2月,俄国发生了又一次革命。3月,圣彼得堡守军加入罢工的工人,迫使尼古拉二世逊位。到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这个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以暴力夺取了政权。
最初,沙皇俄国的崩溃使一些原省区急切地抓住机会实现自治,并将其体现在成文法律中。以此方式,西亚和东欧之间的多民族地区格鲁吉亚首先宣布成为共和国,随后于1921年2月颁布了一部宪法。这部宪法给议会制度和宗教自由等成熟的改革措施留出了空间,也规定了更有革新性的举措。格鲁吉亚妇女现在至少在纸面上得到了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这部宪法还迎合了劳工组织的要求,将罢工定为神圣的权利,并以法律限制工作时间。该宪法承诺,新的格鲁吉亚将“没有阶级差别”,这一承诺甚至被弱势的儿童可领受国家补贴的服装的措施所加强。
上述举措表明,一战后的成文宪法展现出纷乱、激进的社会性风格,这种情况也不只是出现在欧洲和亚洲国家。战争结束之前的1917年,通过一系列革命而取得政权的墨西哥政治家就起草了这一时代最为引人注目、最为持久的宪法之一。过去墨西哥宪法序言的一个特征,1812年《加的斯宪法》的遗迹——“以上帝的名义”这一陈规——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1917年起草的宪法赋予了墨西哥政府分配国家大片地产的权利,也赋予了政府帮助小农场主和农民的义务。
强调向社会和社会主义的转变,自然也是1918年7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根本法的特征,这部法律以“被剥削劳动人民的权利宣言”开始。一战和二战之间的整个时期,甚至到1945年之后,这一文本都是西方左翼激进分子和改革者以及西方之外的一些反殖民活动者的参照物之一。《魏玛宪法》中也明显有意转向社会。这部宪法是1918—1919年德国革命的产物,这场革命源于战争引发的贫困以及俄国革命。自始至终,《魏玛宪法》的关注点都是“社会进步”。正如战后的格鲁吉亚宪法,它也赋予女性与男性相同的政治权利,还规定了国家对教育的控制、完备的社会保险体系以及“工人与雇主在平等地位上”的合作。战后一些东欧宪法也表现出了向社会坚定转变的趋势,例如1921年的波兰“三月宪法”宣布,“劳动是共和国财富的根基”。
这些有激进风格和社会主义风格的战后宪法,许多都没能繁荣发展,甚至没有存续下去。例如,由犹太律师、学者、自由主义政治家胡戈·普罗伊斯起草的德国《魏玛宪法》虽然存在种种缺陷,但也称得上是一份精心写成的有影响力的文件。尽管如此,它仍无法阻止阿道夫·希特勒夺权,其寿终正寝也在意料之中。
然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些和其他一些失败,并没有阻止制宪活动向社会转变的趋势;这些令人失望的现象,以及欧洲、亚洲、南美洲新独裁政权的增多,并没有导致人们对成文宪法方案的希望彻底破灭,也没有使人们长期远离这些方案。的确,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最雄心勃勃的文件之一是一位大人物的杰作:约瑟夫·斯大林于1936年12月主导颁布的苏联宪法。
费边社会主义者比阿特丽斯·韦伯在当时写道,这部宪法有创造“世界上最包容、最平等的民主制度”的潜力,现在看来,这一判断似乎近于天真。可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在不同国家都能发现这种乐观的态度,其中一部分是出于对苏联宪法非凡而动人的起草方式的反应。斯大林本人当然密切参与起草。不过在1936年下半年,苏联各地的4000多万男女公民也兴奋地参加了特别会议和讨论,撰写关于这部宪法草案的意见书。在这里,在批准宪法(从18世纪末起越来越普及的政治技术)的过程中,群众的参与程度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
……
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它的规模增强了成文宪法的推动力,扩大了成文宪法的范围。一方面,有些帝国主义国家在1914年之后被迫从欧洲之外抽调人力,这有助于那些要求将权利延伸到有色人种的反殖民活动家的活动,并证明了这些活动的合理性。1915年,一名黑人记者就加勒比海东部英国统治的格林纳达的征兵行动写道:“作为有色人种,我们将为更多的东西而战斗,那是一些对我们自身无价的东西……我们将通过战斗证明,我们不再仅仅是臣属,而是公民。”出于同样的原因,女性在这场全球战争中被正式动用和征召的程度(不过只是在世界上的某些地区)也巩固和扩展了一个论点:她们现在应该以书面法律的形式,被纳入完全的积极公民身份的范围。
这种关于战争工具的主张有时候会遭到抵制,理由是它们贬损了1914年之前思想与阵营已经发生的变化。的确,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者鼓动的工会与福利改革已经在不同国家和大陆兴起。女权主义运动和反殖民行动主义也是如此。然而,1914年后的战争导致的压力、冲击、要求是史无前例的,这些因素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普及、深化、推动了对现有政治制度的各种批评。空前规模的战争冲突,对作战人员和战争劳工更大、更多样化的需求,也可能集中以及缓和那些有影响力的行动者(他们以前以种族、收入、阶级、宗教、性别为由为排斥制度辩护)的思想。
1914年之后,妇女参与战争(正如殖民地居民参与同样的战事一样)的规模,关键是妇女参战的官方地位,为一些政治领导人提供了可以接受的方式,让他们做出退让,并走向有效变革。伍德罗·威尔逊在第一届总统任期(1913—1917年)内对女性普选权十分冷淡。可是,到了1918年9月——美国参战后17个月——他的言辞和立场都有显著改变,至少在关于妇女的问题上是如此。他坚定地告诉美国参议院:“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与女性结成了伙伴。”他接着说道,因此,现在只承认女性是“牺牲、受苦、辛劳的伙伴,而不是特权和权利上的伙伴”,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尽管1918年后的许多宪法都失败了,而且出现了新的一拨独裁领导者,但对于将国家、政府形式与各种权利写入有感染力的单一文件这一更广泛计划,人们并没有长期、普遍的幻灭感。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令全球的国家与民族支离破碎,加速了西欧残存的各海洋帝国的崩溃时,宪法的制定只会以更快的速度向前推进。1945年这场战争正式结束后,世界随后迎来了新民族国家建立的一次新高潮,先是在亚洲,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则转向非洲。这也导致政治宪法的又一次大爆发。
这远不是故事的结局。
在其他地方也发生了不同种类的战争。反复出现的跨大陆战争(这是从18世纪到20世纪中期这段时期的特点)可能已经停止,至少暂时停止了,但内战仍在不断增加。据估计,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年起,在世界的某些角落,每一刻平均有20场内战正在进行,特别是中东、非洲、中亚的部分地区。
在不断发生的内战推动下,宪法起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到1991年,世界上现存的167部单文件宪法中,只有大约20部有40年以上的历史,说明从1950年起,新文本的制定、旧文本的失败或更替都非常迅速。从那之后,宪法的变迁和制定只会变得更快。
(本文选摘自《战争、法律与现代世界的形成》,[英]琳达·科利著,姚军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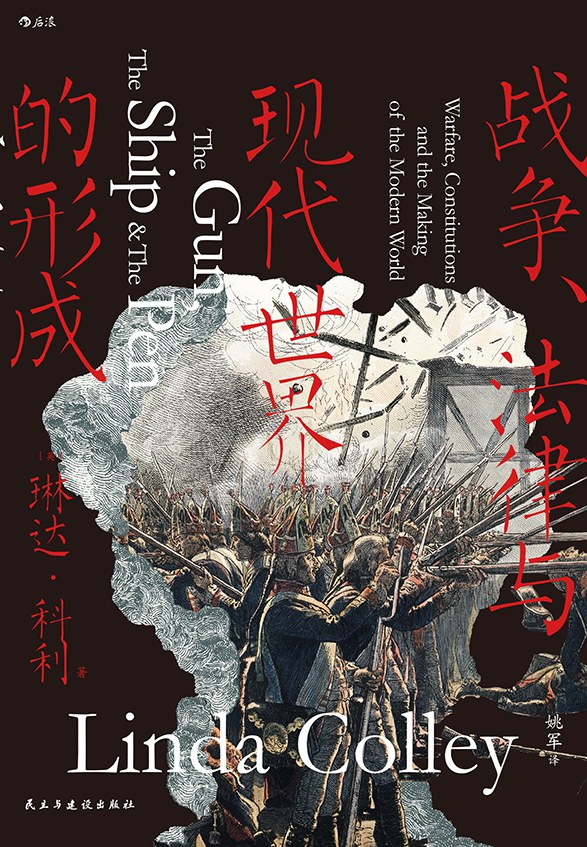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