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他被称为秘鲁的纳达尔,拍摄的肖像动人心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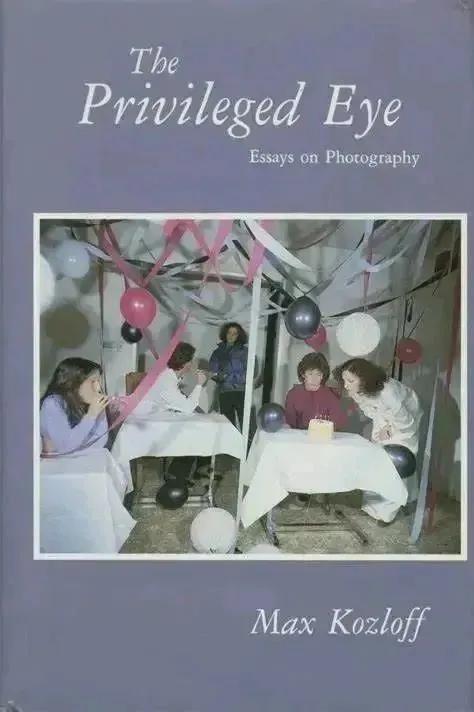
马克斯·科兹洛夫,《特权之眼》,英文版封面
马克斯·科兹洛夫(Max Kozloff),1933年生于芝加哥,纽约大学艺术史博士,曾执教于耶鲁大学、芝加哥艺术学院等机构。科兹洛夫从事艺术史研究和现代艺术评论,尤重于摄影。其人著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Cubism/Futurism,1973)、《特权之眼》(The Privileged Eye,1987)、《纽约:摄影之都》(New York:Capital of Photography,2002)、《面孔的剧场:1900年以来的肖像摄影》(The Theatre of the Face:Portrait Photography Since 1900,2007)等作,评论文章见于VOGUE、《光圈》(Aperture)、《美国艺术》(American Art)、《欧洲摄影》(European Photography)等刊。
科兹洛夫曾任《国家》(The Nation)艺术编辑和《艺术论坛》(Artforum)执行主编。七十年代,他与萨考斯基一道倡导新彩色摄影,自己亦开始彩色负片创作,作品在纽约、巴黎、伦敦、苏黎世等地展出。他于1968年获古根海姆奖,1990年获国际摄影中心终身成就奖。
《特权之眼》收录了科兹洛夫撰写的19篇文章,分为四个部分。前三部分探讨了20世纪摄影中的街头传统、肖像与政治,最后一部分反思了摄影理论和摄影史中的若干重要议题。对于科兹洛夫而言,摄影的独特基于媒介信息的有限性,观者因为置身经验之外而被引向真实与虚构之间“愉悦的矛盾”,也因此成为解读的特权者。在这种媒介认知之上,科兹洛夫的写作寻找个人美学与社会图景之间的平衡,略显老派,但坚实、深刻。
库斯科的昌比
文 | 马克斯·克兹洛夫
译 | 刘其远
马丁·昌比(Martin Chambi)是一位秘鲁摄影师,大致于1920年代至1950年代早期活跃于库斯科。1979年,他在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展览,其中显露的那种交心而摄人的感性与新奥尔良的E·J·贝洛克(E.J.Bellocq)和阿肯色州希伯斯普林斯的迈克·迪斯法默(Mike Disfarmer)近同。昌比在一个更加模糊的共同体中工作,他的职业生涯更长,性格更好探寻。与其他人一样,他是当地的商业肖像摄影师。与那些摄影师一样,他注意到了保守的行业规则并且超越了它们。在每种情况下,昌比感知的多样性和敏锐性使得他所拍摄的古老主题充满生气。在这里,人们过时的衣服和举止成为明显的证据,表明束缚他们人性的风俗并不比我们的更奇异。
以昌比拍摄的加德亚婚礼照片为例。没有什么能比一张旧的婚礼照片更让后来者了解业余庆典的生硬和维多利亚式情感的矫揉造作了。凝视这库斯科的景象,人们几乎无可避免地闻到霉味。新娘的花束看起来已经有点枯萎,而那个脸色苍白、戴着高顶礼帽和手套、穿着燕尾服和细条纹裤子的新郎看起来就像一个忧心忡忡的殡仪人员。在新婚夫妇身后的亲友中,女孩们抓着婚纱裙摆,有人伸长脖子想进入照片。但这张照片令人不安地富有生气,在年轻男女聚集的自然光之外,周围环境笼罩在惊人的昏暗中。昌比只使用环境光,无论是出于原则,还是因为通常没有其他选择,他执着于事实,但创造了一场梦幻般的婚礼,使之被虚空环绕。

在库斯科,人们是如何修眉毛,或者设计审判庭的呢?列举这些以及其他无尽的生活安排,还不足以被称为社会史。这些是从过去中无尽滋生的模糊和琐碎的事实,只能通过某种偶然的机会才能被部分地获取:一段文本,一张专辑,或一沓重见天日的照片。1960年代,来自新墨西哥州的摄影师埃德·兰尼(Ed Ranney)前往库斯科拍摄印加遗迹和高原风景。在随后的一次访问中,他与一位名叫维克多·昌比(Victor Chambi)的摄影师交上了朋友,后者的父亲在一代人之前就是镇上的肖像画家了。马丁·昌比曾经是当地的名人,库斯科的纳达尔(Nadar,19世纪法国画家、摄影师——译者注)(一样广受欢迎,但他更加谦虚),他仍然被邻居们记得,但在秘鲁以外几乎不为人知。这位更年轻的昌比决定整理和重建老昌比的档案。
这件事发生在1975年。两年后,在旨在推动科学探索的组织“地球观测”(Earthwatch)的支持下,由兰尼领导的十名北美人来到库斯科,在昌比工作室的14000张底片中清洁、整理和冲印了一批照片(大多为5x7英寸和8x10英寸的玻璃底片)。由兰尼制作的这些图像证明,它们所恢复的不仅仅是关于过往习俗的视觉记忆。我们能够得到清晰的、不进行判断的记录,应该感到十分高兴,比如阿里纳利兄弟(Giuseppe,Leopoldo and Rumualdo Alinari)的佛罗伦萨或詹姆斯·范·德尔·泽(James Van Der Zee)的哈莱姆的照片、然而,昌比不仅尊重他所呈现的现实,同时也塑造了它。他剖析了其中的张力。至少从直觉上讲,他是一位当代史家,而不仅仅是记录者。

典型的秘鲁形象是一幅山景,其间散布着美洲骆驼,还有穿着破旧衣服和披肩的“原住民”。他们戴着独特的无边帽或软呢帽,在市场上忙碌着。当然,还有残破不堪的印加要塞和神奇的殖民时期教堂。这些观光的刻板印象得到数以千计的同类的支持,直到现在依旧稳固,但是昌比对秘鲁截然不同的审视可能会改变它们。
昌比的照片中包含印加帝国的过去,西班牙文化的影响,以及当代印第安人的生活,但是没有美洲骆驼。它们在他的作品中占比巨大,更多地是因为他对自己周围环境的敏锐意识,而不是对市场的迎合。他是最早真正对马丘比丘[由海拉姆·宾厄姆(Hiram Bingham)在1911年发现]进行拍摄的摄影师之一。我们还有他工作室中的照片,这些照片首次描绘了偏远山地社区的习俗和服饰。它实际上非常罕见,因为对象据说不愿意被摄影师拍摄,除非这位摄影师会说凯楚亚语,并和他们同出一族。因此,这次摄影活动不只是出于民族志的好奇心。在他们的居留地之外,这些山民的面孔中透着一种特定的自豪感,仿佛受到一位旅行者的鼓舞,这位旅行者与他们曾有相似的社会地位和出身。
事实上,昌比1891年出生于秘鲁普诺省(Puno)的科阿萨(Coaza),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因为极为幸运,他从一位在一家英国金矿公司工作的摄影师那里学到了基本的行业知识。经过在阿雷基帕(Arequipa)的进一步培训,他最终在库斯科安顿下来,作为往昔伟大印加帝国的首都,这里的商业前景和文化历史强烈地吸引着他。在此地和别处漫游了几年之后,他投身于1920年代本土意识 (indigenisia) 在秘鲁的兴起,略晚于墨西哥,进展也相对缓慢。毫无疑问,昌比充满怀旧心绪地纪念即将消失的文明,就像柯蒂斯(Edward S. Curtis)和弗洛曼(Adam Clark Vroman)在我们的西南部所做的那样。超过九成的秘鲁居民是印第安人。他们没有面临灭绝的风险。但山区居民对自己的遗产缺乏理解,而他们的文化身份在权力结构和沿海社会中几乎没有积极意义。

这种自我贬低的形象有充分的原因。仅仅在皮萨罗征服秘鲁一个世纪后,该国七分之六的印第安人口已经被消灭。由于法律权利和人权被剥夺,印第安人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都一直被忽视、被荒废和剥削。独裁者奥古斯托·莱吉亚(Augusto Leguia, 1919-30)强迫许多人成为契约劳工,建造从沿海深入内陆的道路。大庄园主雇佣他们,事实上将其作为没有工资的劳动力,同时又让他们勉强维持生计并因此无法上诉。直到1920年,新宪法才承认原住民社区的合法存在,稍后才勉强建立了一个尸位素餐的印第安事务部门。直到1930年,投票权才取消了拥有财产的要求,让一些小农场主只要能够读写西班牙语就能投票。这些变化并非旨在消除消除印第安人非人地位的耻辱。50年前的库斯科是一个典型的司法上腐败、经济上压迫、由混血人种统治的省级中心。
这个城镇也恰好孕育了民俗学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和激进分子。那里建立了一所艺术学院,还有秘鲁共产党。这个圈子中的许多人,也许是绝大多数人,是昌比的朋友和同龄人。其中昌比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何塞·乌里埃尔·加西亚(José Uriel Garcia)出版了一本名为《新印第安人》(El Nuevo Indio)的书,呼吁文化复兴。这方面的争论与异见政治之间的联系可以从1924年海亚·德·拉·托雷(Haya de la Torre)成立“美洲人民革命联盟”(Alianza Popular Revolucionario Americana,简称APRA)窥见一斑。海亚最初强调秘鲁的本土主义目标,这与他的反美情绪和土地国有化计划完全一致。但是为了增强党的力量,他不得不更多地吸引沿海无产阶级,而不是种植园工人和明显群龙无首的安第斯山村民。有理由认为昌比对APRA的目标抱有同情。
马克思主义者何塞·卡洛斯·马里亚泰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在《秘鲁现实的七篇解释性论文》(Seven Interpretive Essays on the Peruvian Reality)中对庄园制度发表了尖锐的抨击,他的读者肯定限于少数受过教育的激进分子。相比之下,为昌比的作品付钱的大多数人出身资产阶级,他们乐意出于家庭或市镇的动机拥有这些作品。昌比身处于那样的社会,在工作中并跨越了分歧,他描绘了社会分层,向上流动的希望以及它与“下层阶级”的关系。

一张庄园法院的合影不仅展示了其中的工作人员,还有吹笛子和打鼓的音乐家、小丑、高地居民、军队、一个宗教兄弟会,以及监工或主人和他的白人家庭,在这个惊人的人群中非常显眼。无论是什么场合将他们聚集在一起,这张照片都充当着类型和权力互动的制度混合体。像每张集体照片一样,这张照片因其对象“穿着制服”而受赞美。除此之外,这个画面非常密集,但又不拘礼节。
他将同样的编排运用到其他更加融洽的人群中,例如1930年在萨克赛华曼举行的国民警卫队出行(图30),这处印加城堡统治着库斯科。这些国家警察处于轻松、热烈的心情中。微笑面孔的浪潮似乎被吸入祖先砌筑的山口。摄影师能够让他们以如此新鲜的甜蜜和神气回应,表明他具有相当的魅力。(昌比擅长让人们露天摆姿势,倚靠着斜坡草地,或者找到小土丘坐下。)这个场景的积极特质也可能与事实有关,即军队为农民提供了极少数的途径来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他们所享有的特权源于新的塞罗(Cerro)政权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因而至少在此,国家和种族团结的说辞可以相容。
昌比研究了在城镇内部展示的、更为世俗的权威。库斯科的大地主们掌控着皮萨克和其他村庄的政治官员。通过这些联系,他们使一种近乎封建的体制保持活力,其中要求农民提供自由劳动和农产品,并在他们的城镇住宅中提供个人服务。大地主还掌控着农产品的销售,并支付远低于农民在社区中提出的定价。此外,通过一系列的供应商网络,印第安人被迫以高昂的价格从大地主那里购买商品。如果这些问题涉及扰人的骚乱,昌比所展示的那些欢乐的国民警卫可以将其镇压。以及,农民领袖碰巧经常遭遇致命事故。
昌比在明亮而自然的天光下拍摄了六个农民,他们在库斯科司法厅等待作证时缩在他们的披风下。这张照片揭示了他们的屈辱、困境和焦虑。花饰地毯上裸露而粗糙的脚趾等细节令人难忘。尽管距离只有一两码远,桌子旁的职员属于另一个世界。此刻,昌比自己可能是这个世界的一员,一名市政雇员。

他通常以更加中立的方式关注阶级对立。一名戴着白手套的警察拧着一个穿粗麻布衣服的小印第安男孩的耳朵,这个男人的神情像是炫耀收获的渔夫。(他完全可能是象征警察应该做的事情,就像昌比的其他作品中喝酒的人确保他们随身携带酒瓶一样。)至于蒙特斯家族(Montes)的王室新娘,她在自家门厅里摆姿势,这在库斯科可能看起来和巴黎的加尼耶歌剧院一样华贵。在她左边的阴影里坐着一个老佣人或女仆,非常卑微。这些并置不是偶然事件或不可避免的情况,而是一个具有对比思维的人所制造出来的。摄影师以同样直白的考虑,安排照片中某人处于上层而某人处于社会底层的陈述,而他的拍摄对象则以天真无邪的态度接受了这一切。
类似的接受也在19世纪的照片中出现,其中白人殖民者显眼地站在亚洲下属中间。这种天真的设置是殖民者和摄影师之间种族主义联盟的结果,人们感觉到相机是欧洲权力的强制延伸。
然而,昌比从其人类代价的角度审视了这种支配体系(每个人都有自己适当的属性)。他毫不含糊地表明了它生产受害者的事实。如果去掉刚才所述的两个画面中的卑躬屈膝者,它们就会从强烈的控诉变成仅仅是类型。
然而,正是通过类型化的作品——集体和个人肖像——昌比赚取了他的大部分收入。仅凭这种方式,他展示了一幅正在经历奇特转变的社会图景。方济各会的修道士与他们的英国赞助人布莱斯戴尔(Blysdale)先生几乎呈现出我刚提到的权力关系的反面。虽然布莱斯戴尔被放置在一个倒三角形的人物和回声回廊的交汇处,但更近的修道士并没有在气势上低他一等。他们面容严厉、姿态自信,似乎扎根在自己青翠的花园中。在许多昌比的照片中,天主教的虔诚真正绽放,例如在阿亚维里的节日俯视镜头,或者在葬礼礼堂中洒满鲜花的哀悼。这些照片中,丘里格拉式[Churrigueresque, 一种巴洛克建筑风格,得名于西班牙建筑师何塞·贝尼托·丘里格拉(Jose, Benito Churriguera),以装饰繁复夸张闻名。——译者注]的纷呈形成了光与暗的视觉游戏。我认为这只能由一个浸染了西班牙文化气质的人创作,他对空间的感知像西班牙教堂内部一样复杂。

然而,他对第一个翻过山脉的摩托车手和第一位飞行员的到来记录得相当简单。他们用现代技术穿越难以想象的距离来到这个地方,这个昌比居住的荒郊野外。然而,相机并没有像纪念昌比把它带入山间的远行一样,记下文明向“另一个地方”的探索。它所展示的恰恰相反。二十世纪最终抵达了“我们”……在此,无论修道士在镜头外是否真的像在镜头前那样心无杂念,或者摩托车手是否比他看起来更有本领,没有人知道。然而,昌比的作品清楚地表明,在他所在的地方,古老仪式与当代行为共存。虽然这些行为被视为当代西方的风俗,但它们既没有得到顺畅的实践,也并非完全自然。
人们感觉到,库斯科的资产阶级半陷入了一场角色尚未学习充分的虚假表演之中。(加德亚婚礼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例如,身体和商务西装彼此不融洽的相处,以及不对劲的剪裁。
在衣领以上,混血商店主往往和他周围地位低下的劳动力难以区分,在衣领下,他穿着他的身份。一些漂亮的混血女子粉饰了自己的脸部,使它们在昌比的照片中看起来几乎像戴着白色面具。从外部文化中涌入这里的一些商品虽然只有些许风格的暗示,但仍然吸引和威胁着这些城镇居民。
如果在海岸地区看到这样的姿态,它们会显得略显过时和尴尬,但是在家乡,它们巩固了所需的等级制度。在混血人之下是“Cholos”,那些不再无地可种,却仍在城里做佣人的印第安人。再往下一层是村民、牧羊人和佃农。如果一个混血人用科楚亚语对一个Cholo人说话,这意味着贬低他。昌比未分类的图像档案中交织着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冲击,还有外来与本土社会关系的交织。
当他们沉浸在彻底的模仿中时,他的拍摄对象只暴露了所受的那些原始的、未经消化的影响。想象一个化装舞会,在这里每个人都打扮成斗牛士、吉普赛人、侍者和小丑,还有一具骷髅和一个无关紧要的水手。这是一片凌乱彩带中闪耀的狂欢派对。在可能与之接近的时间点,有人也拍摄另一个在路易斯维尔的化装舞会,古怪的是,它是按照类似的方式构建的。同样缩小了的布景房间和隐藏的观众席让滑稽的人物们显得局促不安。与别处相比,北美场景的标志性图像更难识别,除了一些欢呼、牛仔、陷入绝境的孩子和富豪之外少有参考。即便如此,秘鲁人在所有这些俗丽的东西面前显得更加困惑。从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出这些造作的肯塔基人背离的规范。相比之下,昌比的被摄者们似乎无法传达他们的幻想。他们似乎没有对日常礼仪达成任何共识,这让他们的一次性奢侈行为难以凸显。其中一个狂欢者的图像在底片上被划掉了,整个华丽的画面笼罩着某种微妙的沮丧感。正是这一点使得它如此迷人。
在库斯科的化装舞会上,人们最不可能穿的服装之一是印第安人的服装,这种服装对我们来说有异域情调,但在他们眼里则有些贬低本土文化的味道。昌比最令人印象深刻、甚至令人敬畏的照片之一展示了来自帕鲁罗的一个七英尺高的印第安人。他在空无一物的摄影棚中矗立着。包裹着他巨大身躯的粗糙面料,被撕裂、修补和再次撕裂,遍布着许多破洞,其中挂缀着布条,就像羊驼毛的细丝。所有人一看便知,这样的破布说明他在城里的生活远不如乡下舒适。与此同时,它们无可辩驳地更加真实,因为它们根本不是“服装”,而是他的个人存在所造就的沧桑、蓬松的皮肤。
1948年,欧文·佩恩(Irving Penn)来到库斯科,租了一个像昌比一样的摄影棚,在朴素的背景前拍摄了村民。从中产生了广为人知的照片,标志着历史性的时刻,将第三世界国家无助而不设防的穷人的图像运用于时尚的视觉设计中渐成潮流。由于他只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潮流,佩恩不能被指责为道德堕落。他创造出比昌比更加时髦的照片,但他从未能够引发并捕捉到帕鲁罗印第安人的狂热而顽强的姿态。在佩恩访问两年后,库斯科被一场巨大的地震摧毁了。地震摧毁了许多当代建筑,大部分殖民时期的教堂也都倒塌。老首都庞大的印加城墙仍然完好无损。据报道,昌比因他的家乡被摧毁而感到绝望,他的作品逐渐失去了灵气。他于1973年去世。
文章
Max Kozloff, The Priviledged Eye, 1987.
作者
马克斯·科兹洛夫(Max Kozloff),1933年生于芝加哥,纽约大学艺术史博士,曾执教于耶鲁大学、芝加哥艺术学院等机构。科兹洛夫从事艺术史研究和现代艺术评论,尤重于摄影。
译者
刘其远,耶鲁大学东亚研究硕士生,本科毕业于南开大学,业余从事摄影、写作和翻译。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