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何祥迪评《八十七年》|美国宪法与国家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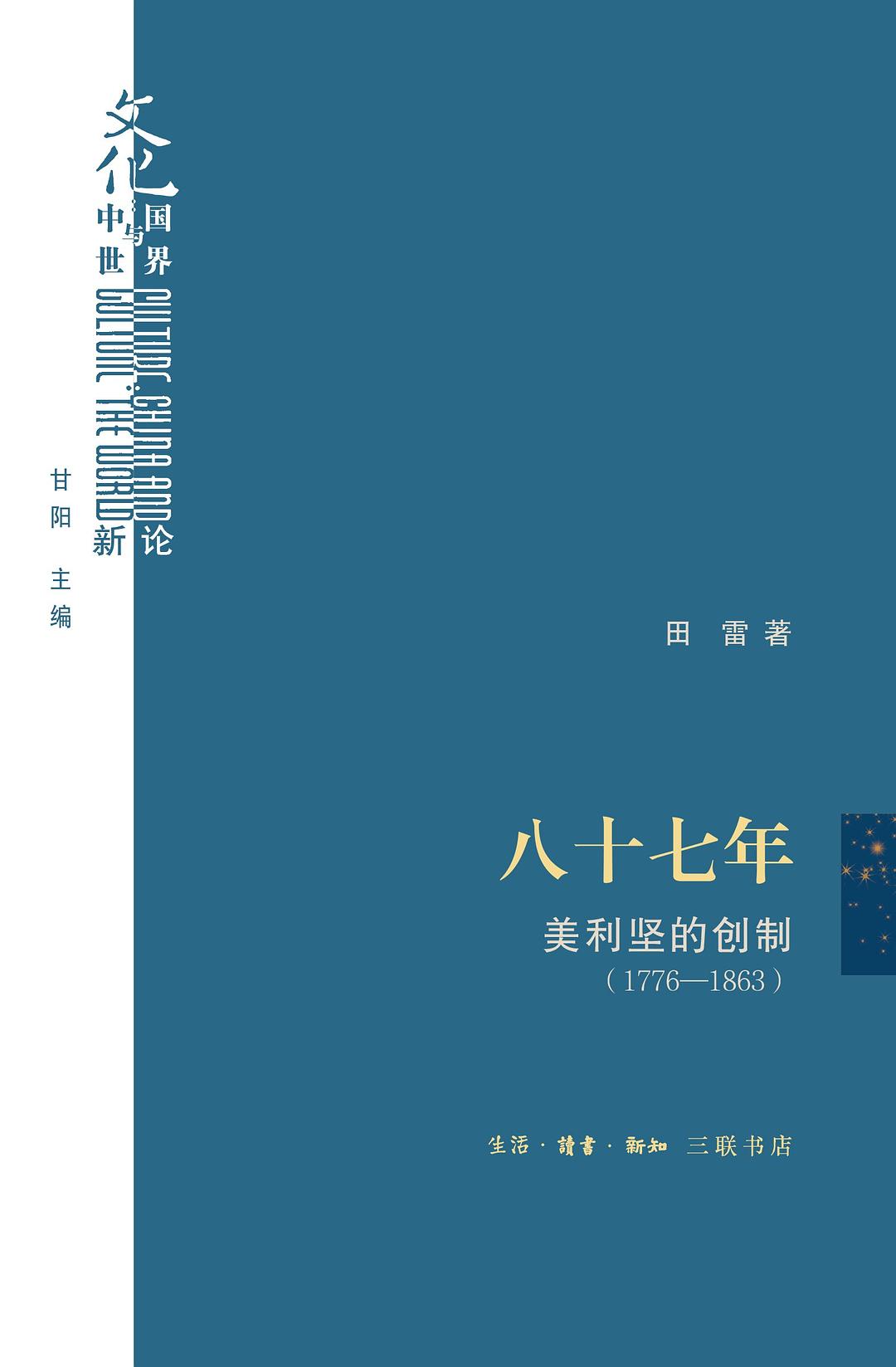
《八十七年:美利坚的创制(1776-1863)》,田雷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4月出版,240页,60.00元
《八十七年》是田雷十年来美国宪法研究的小结。本书是从已经发表的四篇文章进一步扩充和深化而成的,包括《宪法穿越时间》(《中外法学》2015年第二期)、《“构建一个由人管理人的政府”》(《清华法学》2019年第六期)、《第二代宪法问题》(《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六期)和《释宪者林肯》(《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三期)。不过,就本书的框架而论,与其说是四篇文章构成,不如说这四篇文章是一个整体的分段显现,这个整体就是勾勒从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1776)到林肯发表《葛底斯堡演说》(1863)这八十七年间的美国早期宪法史。“八十七年”这个概念的提出意味着田雷将宪法、宪政与国家统一的“三位一体”视为美国宪法的基本目的。
田雷沉潜美国宪法研究二十多年,既深谙美国学界的种种研究方法和立场,又有新时代中国法学-政治学者的自觉意识和慧眼。他借用中国春秋学的“三世说”(通三统)将美国早期宪法史分为三个发展且统一的阶段:第一代建国者立法和建国,第二代“共和国之子”(真正的第一代美国人)继承和守法,第三代重建者变法与重建。这种划分具有两点突破:其一,它既不像主流学界那样将宪法史缩短到1787至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确立司法审查),又不像阿克曼(在美苏争霸结束后)那样拉长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罗斯福新政,而是从美国“合众为一”的角度将早期宪法史限定在八十七年;其二,“三世说”超越了“建国-重建”的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既解决后人为何要遵循前人制定的宪法这个难题,也解决了后世进行宪法修订和改革的合理性的难题,最大的贡献在于将第二代美国人提高到跟前后两代美国人同等重要的地位。
作为美国宪法史研究著作,本书并不是以人们津津乐道的宪法、三权分立、宪法修订、司法审查、最高法院判例等纯粹法律问题为主线,而是将宪法的制定和发展嵌入到具体的政治史当中,解释宪法如何塑造共同体和塑造怎样的共同体,以及政治家如何运用他们的政治才干维持不变宪法与变化政治之间的动态平衡。因此,本书并不是狭义的“宪法史”研究,而是广义的“宪(宪法和宪制)-政(政治家和政治共同体)-史(发展与变革)”研究。在论述方面,田雷非常清楚西方学者常用的二元对立方法,例如宪法作为个体或各州或每代人同意和约定与作为祖先法或先定承诺的对立,宪法解释的原旨主义与能动主义的对立。但他力图使用矛盾统一的辩证法全面而发展地解释每代美国人自身思想和行为的正反特征,例如第一代人以实质上的违法手段建立形式上的宪法,第二代人在形式上的“守法”却实质上深化了分裂主义,第三代人又以形式上的违法手段来维护实质上的宪法,杰斐逊并不是杰斐逊主义者,林肯不是林肯主义者等。
第一章试图通过解决“后人为什么要遵守前人所制定的宪法”这个普遍难题来解决“后来的美国人为什么会遵守第一代美国人所制定的宪法”这个具体难题。这个普遍难题实际上是要求解决宪法优越性的问题,因为如果宪法不具有(更大)优越性就不能要求后人遵守它,毕竟在宪法或宪政尚未出现的数千年间,人们同样可以建立共同体,甚至可以建立更持久的制度以及同样繁荣和强大的共同体。田雷从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角度,批判自由主义的契约论和功利主义的权宜论,他认为宪法是先定承诺和祖宗成法(33-35页),人作为共同体成员而不是作为独立个体而存在,共同体在时间上和文化上是连绵不断和生生不息的(48页),宪法通过后人的认同、继承和热爱(而不是仅仅是简单多数的同意)“才找到了它的伦理基础或文化资本”(52页)。
田雷的论证基于历史实践的“人性论”和遵守宪法的“效果”,它不同于宗教创世论和自由主义契约论的“前历史和前社会”假设,也不同于相信“明天会更好”(69页)的进化论观点。可以看出,他的最大敌人是契约论者,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他把“开端”置于历史和时间之中,而契约论者将“开端”置于历史和时间之前。虽然历史实践论可以从事实层面驳斥“契约论”,却难以从逻辑层面驳斥它,因为契约论者显然可以说,宪法的正当性的先在“来源”不能通过事后“结果”来证明。此外,历史实践论还会面临这个严重后果的指控,即通过不正当手段建立起来的美国宪法如何具有正当性(138页)?须知,对于英国来说北美十三州的革命就是造反,连美国人也不得不承认“费城制宪”本身也是不合法的。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用“祖宗不足法”来证明革命的正当性,他这一代人又怎能制定“祖宗成法”呢?
历史实践论想要彻底驳斥自由主义至少还需要提供两个证明,其一,证明美国宪法本身内化了超历史和超社会的伦理,而这种伦理可以通过比较历史和同时期其他政制得到发现,因为在一个普遍实施君主制和现代自由民主理论刚萌芽(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的时代,美国人奇迹般地放弃了君主制和民主制而选择共和制,但这种奇迹乃是基于他们对君主制、共和制和民主制深思熟虑和谨慎选择的结果;其二,证明基于同意的“契约论”只是解释宪法产生的“一种可能性方案”,但它本身并不构成宪法伦理的来源,因为哪怕大多数人、全部人在事实上能够达成同意,也不能确保宪法是正确和善的,“同意”并不是“真理和善”的必要或充分条件。我并不清楚田雷是否自觉地意识到这个逻辑关系,但本书第二章却可以视为围绕这两点展开的论证。
第二章以麦迪逊如何“生育”和“抚养”美国宪法来描述第一代美国人的立法问题。田雷特别擅长同情地理解麦迪逊的困境和矛盾:在制宪上,宪法作为原则与妥协的产物既是麦迪逊的失败也是他的成功(93页);在释宪上,麦迪逊弱化自己的意图来强化已确立的解释原则(104页);在执法上,麦迪逊起初反对后来却同意建立国家银行(108-111页)。如此一来这一章就完成了上述两个必需的论证。一方面,麦迪逊在历史比较中得出人性恶的结论(89页),并由此设计出分权、限制权力和划定政府权限的制度(86页)。对政治权力的限制最大程度上避免了权力被滥用导致最大邪恶的可能性,对权力的保护则最大程度地提高了公民免遭邪恶的可能性,这就是宪法内化的最基本的伦理,也是美国宪政在当时最先进的理念和实践。另一方面,“宪法的正当性来自人民自己的同意”,但这种“同意”不是指所有人民的直接“同意”,而是指宪法代表了“人民的声音”(106页)。即使执法过程当中出现“违宪”行为,如果这种行为不是出于私心,而是为了且实现了公共利益,并得到国家和地方的默认,那么它同样代表“公意”(109页)。宪法所说的“人民”并不是事实上的人民(因为当时的“人民”显然不包括妇女、黑人、奴隶等),而是一种修辞,即“人民”是一种在卢梭的意义上代表公意的声音。仅从第一代人的私生活和他们对待奴隶制的态度和做法,都可以知道第一代人并不是圣人,但是他们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建立了宪政,当然,宪政也只是内化了最基本的伦理,还远远谈不上“善政”(145页)。
立法“意图”是必然存在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司法解释中把握“意图”的边界。田雷借助麦迪逊弱化自己的“意图”来弱化“原旨主义”和强化(麦迪逊的)“文本主义”(比较141页),这个做法本身同样是承认和寻求麦迪逊的“意图”。不过,田雷还发现麦迪逊本人的“原旨”却是“最能动的活宪法”(111页),如此他又反过来弱化了“文本主义”和强化了(麦迪逊的)“原旨主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破天荒地指出理解麦迪逊的最大的理论自觉是不读《联邦党人文集》(114页)。毫无疑问,这是极为细腻和精彩的辩证解读,它提醒我们时刻要注意到在不变的宪法和可变的政治生活之间存在张力,但只有在宪法规范之内解决政治问题才表明宪法是“活的”,而极端的原旨主义和本本主义都是宪法已“死”的表现。这是作者随后解读第二代人守法和第三代人变法的核心。
第三章讨论第二代美国人继承和守护宪政的问题。田雷注意到第二代人在宪法研究和政治研究中被冷落和“污名化”的现象(124页),并指出其实第二代人才是真正的美国人(127页)。第二代人在急剧的社会变化中继承和守护了先辈们的宪法(135页),开创了美国的守法文化(144页),并确保了宪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149页)。尽管宪法本身存在着后世所谓的“原罪”(145页),但是不应该用后世的道德去苛责第一、第二代人。可以说,多亏了第二代人的“守法和无为”,美国宪政传统才得以巩固和延续,因为没有他们“守法”,宪法不过是一纸空文,没有他们的“无为”,宪法也早已不是原先那套宪法。
田雷提醒我们注意到一个被忽略却至关重要的问题,就维护宪法权威、稳定性和连续性而言,那些只能守法的法官对宪法解释权和审查权的贡献,远不如那些本可以废除宪法却自觉守护宪法的政治家来得更大。不过,如果仅仅是为了守护宪法而守护宪法,那么第二代人的重要性无论如何也比不上作为立法者的第一代人;但是如果通过守护宪法达到了早期立法者想要实现却未能实现的目的,那第二代至少可以与立法者比肩了。宪法的目的是什么?在田雷看来,除了建立法治和宪政之外,更应该包括“建成一个主权统一不可分割的国家”(151页)。
虽然第二代人出现了两股极端的政治力量——有趣的是作者称之为“离心派”与“向心派”而不是通常所说的“民主党”与“格辉党”——但是这种观念和实践上的政治撕裂,并不是第二代人的污点,而是革命不彻底遗留的历史问题(154页)。难能可贵的是,这两派仍然“在既定宪法框架内进行着他们的斗争和挣扎”(166页)。在解释这两派的法理基础方面,虽然田雷没有做出他的个人判断,但是显然他会依据宪法的目的,批判离心派的“合约论”(宪法是代表人民的主权州的契约,157页),赞同向心派的“国家法律说”(宪法代表所有人民主权的国家法律,163页)。
第三章对第二代人的深度挖掘,可谓名副其实的“填补历史空白”(133页)。然而,正因为其开创性,这章的精彩程度稍逊于第二章和第四章。例如韦伯斯特偏向于用“统一”和“自由”来解释共同体最低和最高目的(118页),但田雷为了纠正现代激进自由主义之偏,更偏向于从“统一”和“延续”,而不是从“限制权力和保护个人权利”来解释1787年宪法的目的(150页,注51)。如果他能够将这个目的界定为美国宪法或宪政的最低目标,并进一步论证“如此不同”的人统一在一起,最终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一种来自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乃至林肯(192页)的政治哲学观——那他的论述可能会变得更加令人信服,尽管什么是更好的生活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因为,从历史上事实来看,宪法和宪政并不是人类共同体实现“统一”和“延续”(永续是不可能的)的必要条件,也许只有对美国人而言才是如此。
第四章探究第三代人如何重建美国,尤其是林肯如何实现宪法的“合众为一”的目标。田雷再次挑战主流的美国宪法史研究不重视林肯,甚至把林肯视为负面形象的做派(176页),致力于从错综复杂的政治背景、林肯言行的矛盾统一来理解林肯对美国宪法和宪政的贡献(177页)。在田雷看来,林肯的联邦观、民主观和法治观尽管看起来是错误的,甚至林肯的行为是违法的,但是林肯的目标和实践却重建了而不是破坏了宪法权威和国家统一。林肯在职演说中从结构、历史、实践、地缘四个层面否定州主权和州单方面退出联邦的权利(190-193页),他故意扭曲联邦与宪法的关系(196页),是为了实现国家“定于一”的宪法目标(197页)。或许唯一可以论证各州从来没有主权的依据是:各州原本就是英国的殖民地,而革命是为了摆脱英国统治,革命成功后,主权只有一个并且属于联邦。但是作为第三代的林肯显然已经无法接受这个“美国革命是造反”的论证,因为这个论证既可以用来批判各州的“退出就是造反”,又可以用来支撑各州(就像当年的美国十三州那样)“造反有理”的口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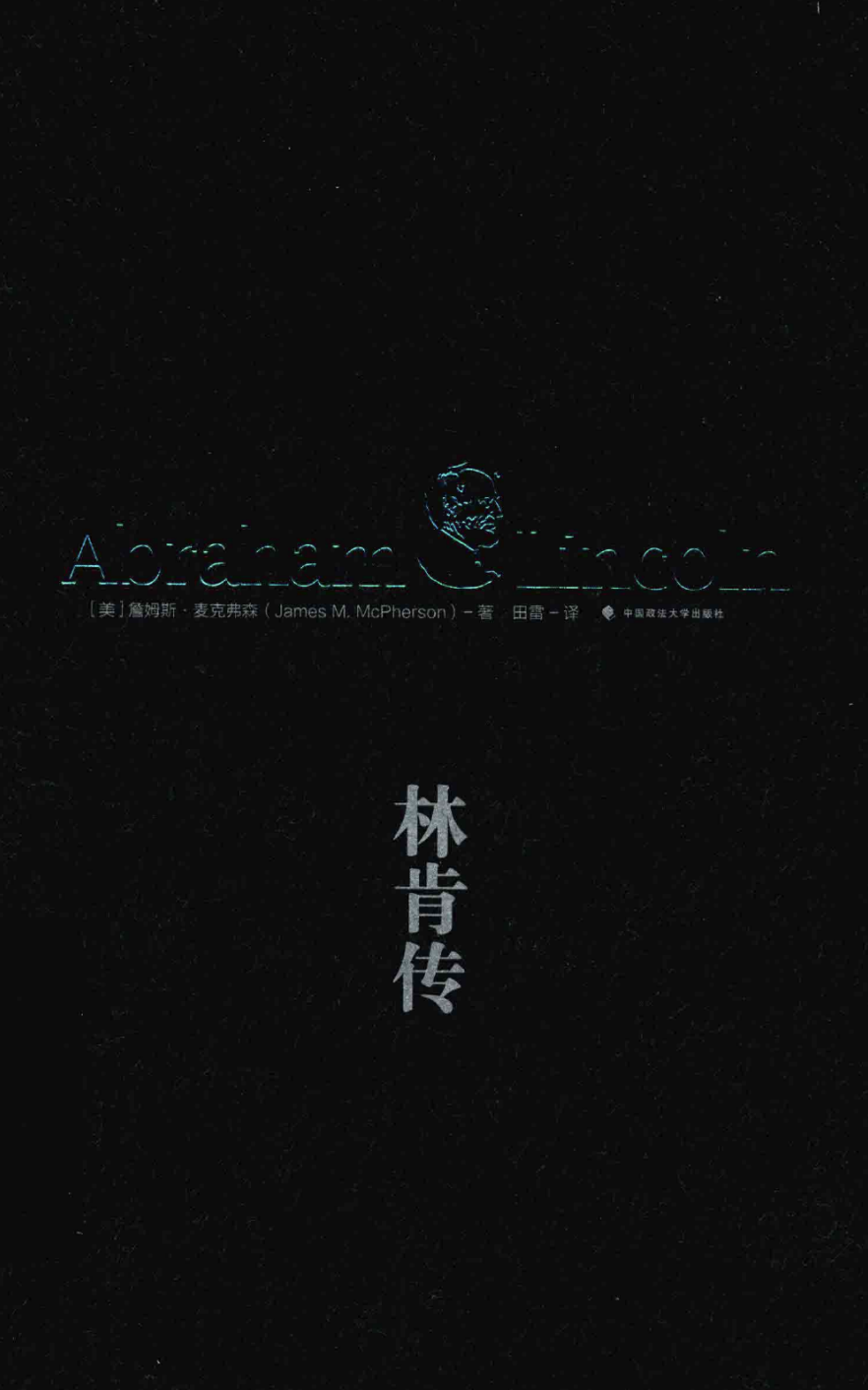
田雷译、詹姆斯·麦克弗森著《林肯传》
林肯反对君主制和民主制,支持“受宪法限制”的多数人民主(203页);他提出了强政府会作恶(侵犯州权)与弱政府无法阻止恶(国家分裂)的矛盾,为了避免更大的恶而要求强化政府权力(207页)。最矛盾的问题是,林肯一方面要求所有人守法,又承认恶法存在,同时还要求恶法也要遵守(209页),另一方面却认为用违法手段来维持法律和实现法律目的是合法的(210页)。田雷通过区分形式与实质、手段与目的、个别与整体来解释林肯的矛盾,这展示出林肯“平衡和审慎”的才干,也显示出一位法学研究者的融通性和灵活性理解。
《八十七年》打破了人们对自由和民主的迷思,让我们看到原来从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到林肯都反对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也打破了人们认为只要有宪法就有宪政和共同体的迷思,让我们看到正是一代代的美国人自主选择在宪法范围内行事,才造就了美国的宪政传统和统一;还打破了人们总是试图通过思辨的方式来寻求宪法正当性的假设,让我们看到宪法的正当性来自历史实践显现出来的内在伦理。另一个可能超出一般宪法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三代美国人都自愿遵守宪法?虽然田雷没有细究这个问题,但是他在全书末尾给出了暗示:“林肯已逝,林肯不朽。”古希腊政治史家修昔底德曾经指出,人性总是受利益、荣誉和恐惧所支配,并时刻想着突破法律和道德。这三代美国人毫无疑问都是利益追求者,他们当然也是最有能力突破法律的人,但却把追求不朽的荣誉当作自己的最大利益,并把维护宪法及其目标视为获得这种最大利益的手段。他们深知只有这样做才能获得“不朽”,也明白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则会立即众叛亲离、身败名裂。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既是宪政文化的塑造者,也是宪政文化的产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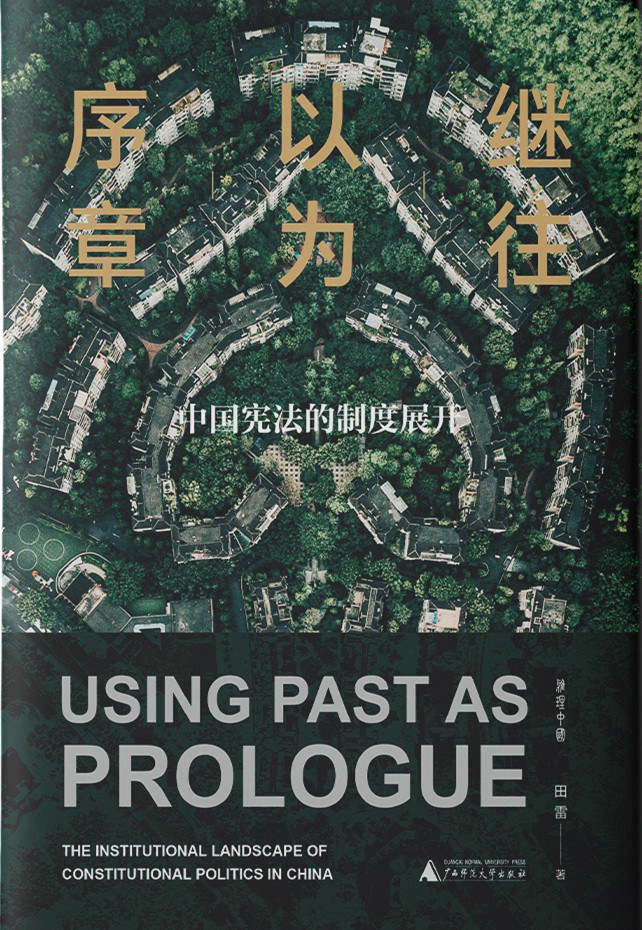
田雷著《继往以为序章》
田雷以中国学者的立场进入美国宪法领域,又带着对美国宪法研究的认识重新理解中国宪法史。本书的写作结束后,他立即转入对我国现行“八二宪法”的研究,同样秉承着类似的思路:开端仍然在历史之中,而且具有统治地位。八二宪法的修订强调并蕴含着连续性和稳定性,宪法修订恰恰是“活”宪法的表征等。实践的和辩证的宪法研究,不会像自由主义那样通过假设的“同意”来证明宪法的正当性,更不会像历史虚无主义那样否定存在任何跨时代的规范和价值,而是透过人民在历史当中的实践来检验宪法内化的伦理。可以说《八十七年》这本书体现出作者既有做中国特色法学研究的自觉和自信,也是以“两个结合”理论为指导做中国特色法学研究的践行者。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