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公元1016年:宰相官名这么怪?藏着制约相权的玄机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16年,大宋大中祥符九年,大辽开泰五年。
这是大中祥符这个年号的最后一年了。宋真宗从降天书折腾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九个年头了,明年,真宗皇帝就要改元,年号改成“天禧”。
一般来说,皇帝不会平白无故的换年号。因为年号一改,全国从上到下的文书都得跟着改,还得专门派人通知周边的各类政权,听着都很麻烦。所以,改年号多少得有个理由。
那这次改年号是为啥呢?简单说,这一年,天书降神、东封西祀这些神神叨叨的活动,已经走到了尽头,皇帝也好,大臣也好,都觉得,不能再搞下去了。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一场突如其来的蝗灾,突然席卷全国。蝗灾区域非常大,今天的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江苏、安徽这七个省的范围都遭了灾。这就给当时热热闹闹的各种迷信活动出了个难题:折腾了八九年的祭祀活动,各路神仙受了那么多香火,总得保护大宋朝啊。那现在那么多的虫子,那么大的灾难,总得有个解释吧?

蝗虫是只管吃,不管解释的,但是各地官员得解释啊。所以他们在向上汇报的时候,就只好胡编乱造,比如:虫子确实有,但是他们好乖哦,都不往田里飞;就是飞到田里,也不啃庄稼;它们都抱着草,活活饿死自己。总之吧,就是因为皇帝陛下道德高尚,在漫天神佛的庇护下,蝗灾确实有,但是,没有危害。
有一天,真宗皇帝就真的在朝堂上,拿出了一些死蝗虫给大家看。这啥意思?很明显,皇帝是想拿出点证据证明,这些蝗虫确实仁义,宁可自己死,也不吃庄稼。
马上就有大臣捧场说:哇塞,这么神奇!咱们得组织百官,搞个仪式,给皇帝道喜啊。这个时候宰相王旦站出来了:别别别,这么大的灾情,还道什么喜?!王旦是死活不同意。
过了几天之后,君臣们正在上朝,正商量事儿呢,忽然间,一大群蝗虫从大殿前遮天蔽日、密密麻麻地飞过。你看,天下偏偏就有那么多不识相、不听话、不愿死的蝗虫,飞到皇帝面前来示威。
你都可以想象,当时大殿里面的那个尴尬的气氛。真宗皇帝,扭头看看了宰相王旦,说,哎,如果前两天我听了那些人的话,真搞了什么百官道贺的仪式,今天蝗虫这么一来,还不被天下人笑死?
如果我们当时在场的话,估计都能听得到所有人内心里的那声叹息:办了那么多仪式,烧了那么多香火,造了那么多道观,老天爷是一点面子也没给啊。折腾了九年的一场大梦,终于要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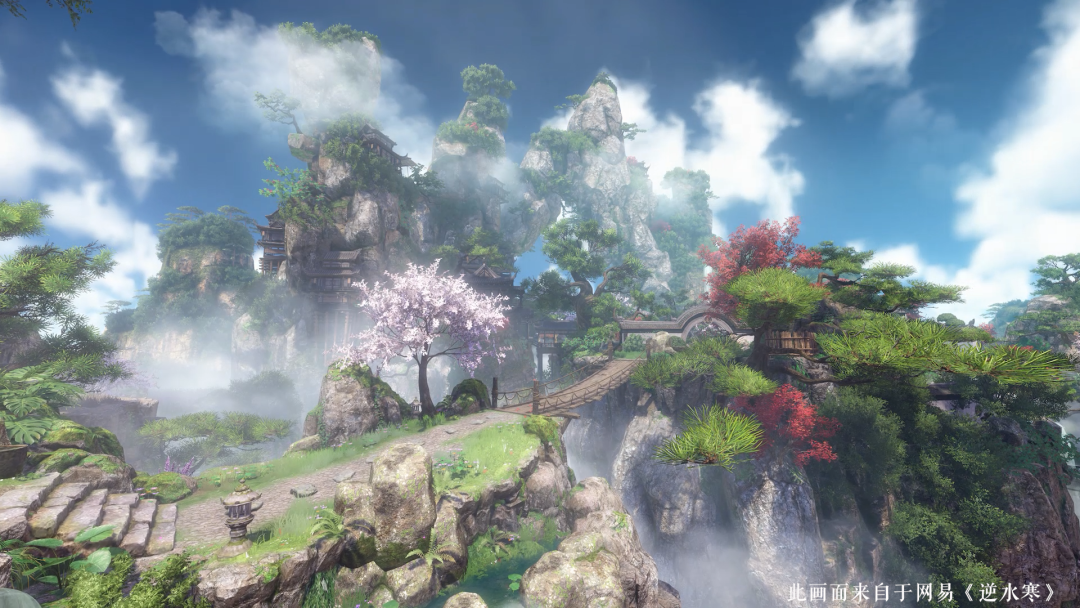
你看看,这场轰轰烈烈的天书降神东封西祀,刚开始,热情高涨起来的时候,所有人都会被裹挟进去,反面事实即使有,也没人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狂热的降温、硬梆梆的反面事实一个接一个地摆在面前,刚开始的支持者,比如王旦,开始保留意见了;被裹挟进去的人,开始寻找退路了。每个人静悄悄地往后撤了一步,而最狂热的发动者和支持者,比如真宗和王钦若他们,就被很尴尬地留在当场。
随着王旦态度的转变,大中祥符时代,就要落幕了。而且王旦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明年他就要去世了。
《文明之旅》节目,专门用一期节目讲过宰相吕端,也专门讲过宰相李沆,现在又要送别宰相王旦了。王旦是不间断地做了12年宰相,这在北宋历史上是独一份,所以,和前面那两位比起来,王旦还要更重要一些。关于王旦这个人,我们等到明年再讲。这一讲,为了便于理解王旦,我们要先跳出来,讲讲宋代的宰相和皇帝之间的关系。
这个话题也很大,从哪儿说起呢?就从宋代宰相的官名说起吧。
还是以王旦为例,这一年的二月份,朝廷就下达过一份褒奖他的文件,开头就列了王旦的一大串官名,我念给你听听:“开府仪同三司、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玉清昭应宫使、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
你听听,9个部分、48个字,看起来啰里吧嗦的,但是请注意,里面每个字都有特别的意义,都是长期演化琢磨出来的。其中有的是“官”,有的是“职”,有的是“爵”,有的是“勋”,有的是“散官”,有的是“差遣”,名堂多了。如果要拆开来细细讲的话,够写一本书了。
我们这一期节目,只讲其中最重要的那个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是北宋前期,宰相的正式官名。你看,多奇怪的名字。刚开始读史书的人,会觉得莫名其妙,一个官名而已嘛,搞得这么复杂、这么拗口干什么呢?
那“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个奇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名字的演化过程,又透露了中国古代政治的哪些秘密呢?
好,那就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一起穿越回公元1016年,大宋大中祥符九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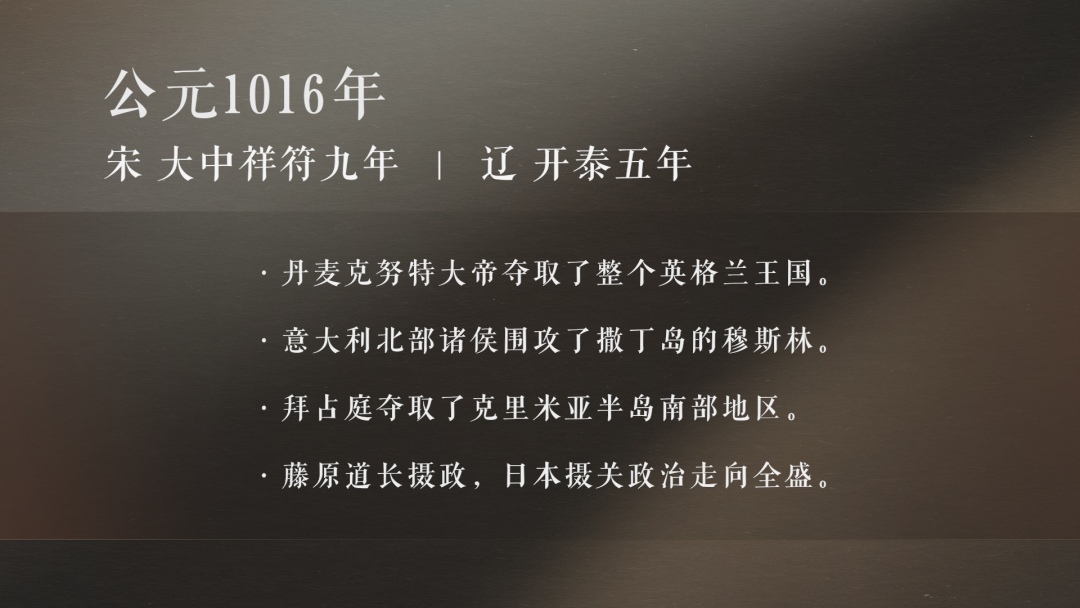
宰相的怪称号
我们经常讲“宰相”如何如何。其实,中国历史上所有担任宰相的人,他们的官名里都没有“宰相”这两个字。
历朝历代,有叫相国、相邦的,有叫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的,有叫司徒、司马、司空的,有叫尚书令、尚书仆射、中书令、侍中的,唯独没有叫“宰相”的。
你要是看历史书,只有辽朝的官制里有个“宰相”,但那其实也是从契丹语翻译过来的,人家本来也不叫宰相。
但是从正史到民间戏剧,再到文人之间的书信往还,宰相的名号一直在用的。举个例子:晚清的时候,有一副很著名的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地上荒”。下联,司农,指的是当时的户部尚书,管钱的翁同龢。翁同龢是江苏常熟人嘛,但是天下的粮食收成并不好,所以,地名中的“熟”和现实中的“荒”相对,很巧。上联呢,宰相合肥指的是谁啊?是李鸿章。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但是天下瘦啊,所以,“肥”和“瘦”,这又是巧对。
那么李鸿章真是宰相吗?他虽然官儿当到很大,又是直隶总督又是北洋大臣,但是他其实从来没有在中央出任过什么要职,只是头衔里面有个“文华殿大学士”,官阶正一品,他之所以被叫作“李中堂”,又被恭维为“宰相”,都是从这个职位来论的。但我们知道,明清两代,从朱元璋开始,那种既有议政权,又有监督权的真宰相,是没有的,所以李鸿章就是个假宰相。
那你可能有个疑问,宰相这个称号怎么这么乱哄哄的呢?
今天我们就试试,能不能通过解剖宋代宰相的称号,帮你把这个乱哄哄的问题捋一捋,让你不用记住太多的细节,但是能对中国古代宰相的演化规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在中国所有朝代的宰相称号中,唐朝和宋朝是最乱的。其中用得比较长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这个词,连在一起读,不知所云。但是拆开了,也就是三个部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下面我们一个个地简单解释一下。
第一个字最好解释,“同”,就是你还不是,但是就算你是吧。
类似的用法,科举考试里,有一个词,叫“赐同进士出身”,什么意思?就是你虽然没有考得很好,虽然你不是进士,但是,哎,朝廷宽大为怀,就算你是个进士吧。
这个用法,和古时候管小妾叫“如夫人”是类似的。不是夫人,但是,哎,也就算吧。晚清的时候,不是有一个有趣的对联吗?上联叫“替如夫人洗脚”,下联叫“赐同进士出身”。就是开这两种人玩笑的。
所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你先不用管后面那一大堆是什么意思,开头第一个字是“同”,这意味着:你还不是,但是暂且算你是。开头就是一个打压。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部分:“中书门下”。这是唐代政府里的两个部门,中书省和门下省,这两个部门的首脑,在唐代都是宰相。
再来看第三个部分:“平章事”,是什么意思呢?“平”,就是辨别,“章”,就是彰显,“事”,就是国家大事,“平章事”,就是一起商量处理国家大事。
好了,现在我们把八个字连起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个意思就好懂了,就是说,你这个人啊,皇帝指定你“暂时拥有跟中书省门下省长官相同的商量处理国家大事的权力”。
听出来了吧?你虽然不是个宰相,但是暂时就算你是啊。你虽然没有宰相的地位啊、荣誉啊什么的,但是你也有掺和进来处理国事的权力啊。那你可能会说,这怎么越听越像是一个临时性的安排?是的,它一开始就是个临时性的安排。
我们来大致捋一下这个演化过程:
话说在唐太宗时期,有个宰相叫李靖,也就是神话传说里哪吒的爸爸、“托塔李天王”的原型。在真实历史里面,他是唐代初年的名将,当了宰相之后,他也很自觉,怕功高震主,就假托生病,说我这个宰相不当了行不行?唐太宗心里当然明白是怎么回事,说,行行行,宰相不当可以,但是待遇啊、荣誉啊什么的都照旧,而且嘱咐李靖,你要是将来病稍微好一点了,就隔三差五地,到门下省、中书省去商量处理国家大事,这就叫“平章政事”。你不是宰相了,但是仍然可以管宰相的事。

这是后三个字“平章事”的来历。那前一个“同”字,又是怎么来的呢?
还是在唐朝,唐高宗年间,皇帝想让一些官员参加宰相会议,处理国家大事,但这些人级别不够啊。直接升官吗?那不行,这些人升官的资历还不够,怎么办?好办。那就加个头衔嘛。刚开始,这个头衔的还比较乱,渐渐地就统一在“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了。从这个时候开始,制度明确规定,加了这个头衔的人,也是宰相,跟中书令、侍中那些正牌宰相,在权力上没有差别。
那你可能会问了,那原来的正牌宰相头衔,后来去哪了呢?
这就问到要害了。在唐代的情况是这样的:公元755年,不是爆发了安史之乱吗?顺便插一句嘴,了解中国历史,很多年代记不住,没事,但是安史之乱爆发的这个755年,真心希望你能记住。因为这是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我们现在讲的宋朝的很多问题,都要追溯到755年的安史之乱,才能看得清楚。

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唐朝中央当然要集中一切资源来平乱,当时朝廷是既缺钱,也缺兵,但是有一样东西相对富余,随时都能有,那就是官位。给你一个节度使,给他一个大元帅,甚至有将领出征的时候,先领一大摞没填名字的委任状,你手下有人立了功,你就把他名字填上。所以,当时官爵贬值很厉害,据说一个“大将军”的委任状,只能换一顿酒钱。
那你可想而知了,一般的军功,都这么赏,那真正的特大军功怎么办?只能把尊贵的宰相官衔,比如中书令、侍中这样的官衔拿出来做赏赐。比如,平定安史之乱的两个大功臣,郭子仪、李光弼,朝廷就在同一天晋升郭子仪做中书令,李光弼做侍中,这可都是宰相的职务啊。
但是,一来,这些人要在前线统兵,不可能真在中央当宰相,二来,朝廷对他们也很戒备,不会真的让他们做宰相。所以,“中书令”、“侍中”这两个正牌宰相官衔,慢慢地变得有名无实,最后成了荣誉头衔。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个靠加头衔确认的宰相,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唯一的真宰相。
你看看,历史就这么曲里拐弯地走到了这里。一个非常别扭的官名,成了宰相的正式名称,而且从唐朝中期一直用到了北宋后期,大概用了300年。
那你说,这是一个偶然呢?还是背后有什么必然的规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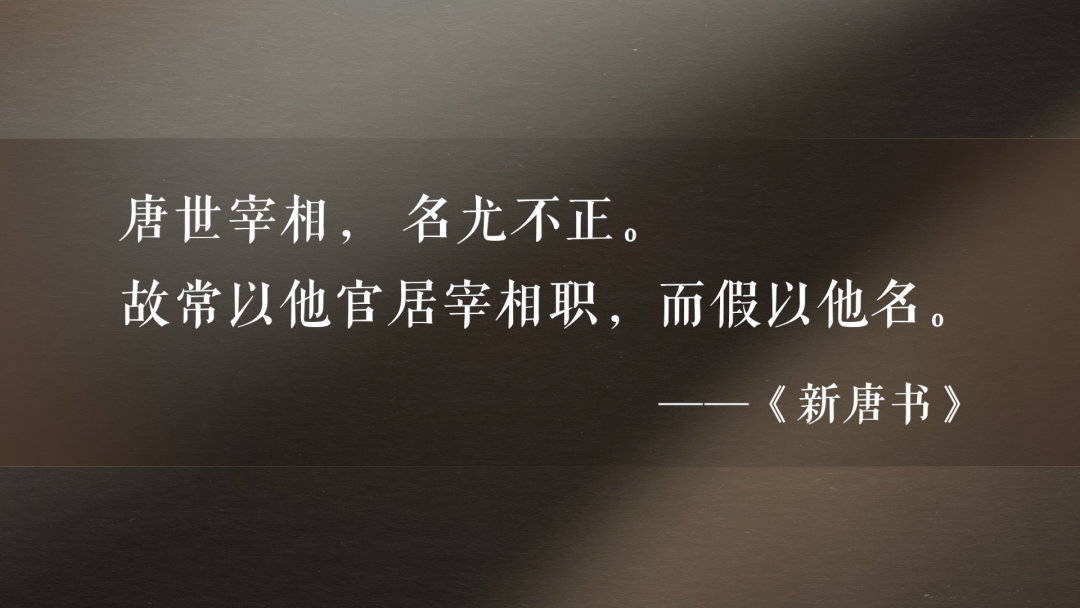
君臣一局棋
前面是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八个字拆成了三个部分来理解。我们不妨来个借题发挥,就从这个三个部分着眼,来看看中国古代官制演化的几个内在机理。
先来看第一个字,“同”。啥意思?你现在还不是,但就算你是了。这其实是一个普遍运用的方法,就是破格任用那些暂时还不够资格的人。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先举个例子,你感受一下:当年刘邦用陈平,陈平是个临时投奔到刘邦阵营里的人,刘邦马上就让他当自己的随从,而且负责监察军中的所有将领。那大家当然都不服,这个人既没有功劳,也没看出有什么本事,连底细都不清楚,他凭什么监督我们呢?哎,大家越是不服,刘邦越是用陈平。
你想想看为什么?熊逸老师在得到讲《资治通鉴》的时候分析这个故事,他说,你想想刘邦当时的那个班底,干的是造反的事业,做的是杀头的买卖,作为大哥,他得讲兄弟之情。但是军队又不能没有纪律,怎么办?自己跟兄弟翻脸吗?不行啊,得借外人之手。找一个年轻的、资历浅的、外来的、看起来机灵点儿的人,破格提拔一下,让他手握大权,压所有人一头。这人就是陈平啊。陈平就是刘邦好不容易遇到的年轻的、外来的、资格浅的机灵鬼儿啊。
那你可以推想两种情况。
一种是,陈平的勉强能镇得住场面。但凭什么能镇得住啊?肯定是因为他全力依靠刘邦,早请示晚汇报嘛。他自己没有资历,只能借用刘邦的权威。所以,这样的人,就算把活干成了,对刘邦也毫无威胁。
那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陈平搞砸了,镇不住这帮老兄弟,甚至还把这帮人惹翻了。那刘邦也好办,请老兄弟们喝顿大酒,然后双拳一抱,说一声:“兄弟们,对不住了,这都是陈平瞒着我干的。来呀,把陈平拖出去杀了。大家消消气。”这事就结束了。
我们通常会觉得,一个岗位上的人,资格到了,授予他相应的权力,天经地义。资格分两种,一种是熬年头带来的,一种是攒功劳带来的,所谓“论资排辈”或者“论功行赏”嘛。但无论是哪一种资格,只要他是靠自己的资格获得了某种权力,资格和权力就合一了。
但是,孟德斯鸠有一句名言:“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如果一个人权力的来源,是他自己的资格,那他的领导对他的支配能力就变小了。一般公司里的老油条或者是销冠,很难管,就是这个原因。
而刚才那个故事里,刘邦任用陈平,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在一个职务的任命上,他把“资格”和“权力”分开,提拔资格不够的人来掌权,那这个人的权力只有一个来源,就是提拔他的人。他就只能成为提拔他的人的工具人。
我这么说,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黑暗权谋的色彩。但在真实的历史上,如果臣子全都是资格和权力合一的人,皇帝想干的事儿真就推不动。所以,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首先,资格够的人,能力未必够。比如东晋南朝的时候,重要的职位都被门阀士族把持,这些人又不愿意干活。当时有一个词嘛,叫“望白署空”,就是这些宰相对送来的文书,完全不看内容,就在预先留下的空白的地方签字盖章。那朝政怎么办?爱咋办咋办。你要是皇帝,是不是得急死?但是没办法啊,这些门阀士族,你又请不走,那你只好提拔一些资格不够,但是愿意干活的人,实际掌握权力。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资格够的人,跟你不是一条心。比如唐玄宗的时候,有一个宰相叫宋璟,跟姚崇齐名,一代名相啊。宋璟哪儿都好,就是不愿意皇帝开疆拓土,所以他当宰相,就压抑军功。比如当时有个将军出征草原,把突厥可汗的头带回长安,这在当年可算是不世之功啊。但宋璟根本不睬他,到第二年,才勉强给这个人升了个低等级的郎将。
那你说,皇帝怎么办?宋璟声望非常高,他的原则也不能说不对。皇帝要想开疆拓土,唯一的办法,就是破格提拔一堆有军功的人。不断地往宰相班子里掺沙子,这样的人多了,皇帝的主张才好推行啊。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资格够的人,是不是好用,不知道。那就大批量地用不够资格的人,不行没关系,再换下来嘛。武则天用人,就是这个风格。有人数过,武则天前后任命了78人次的宰相,平均一年换四五个,远超前代。一个低级官员,一句话说对了,武则天就能让他当宰相,一件事办错了,该撤撤,该办办,武则天眼都不眨,反正你本来就不够资格嘛。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这个“同”字,妙用无穷。在中国政治制度的历史上,这是一个通行的规律:想要压抑相权或压制元老的时候,皇帝经常会用资格不够的人来担任权力很大的角色。比如明朝用大学士来替代宰相,而清代,又用军机大臣来替代大学士。
接着来看第二个词,“中书门下”。这是一个复合词,原来指的是唐代的两个中央机构,中书省和门下省。从这个词里,你可以看出来政治制度演化的第二个逻辑了,那就是“分拆”。
我们熟悉的分拆,是职能上的分拆,比如,有的管司法,有的管民事,有的管军事,有的管财政。这种分拆我们好理解。但是,从唐代开始的“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这么设置的分拆,就有点令人费解了。
表面上看,中书省是负责制定政策、拟定诏书的。尚书省是负责执行的。而这个门下省呢,奇怪,负责封驳诏书,什么意思?就是门下省的官员觉得,这个诏书下得不合适,那就驳回去,诏书作废。哎?这是为啥?这是为了制衡皇帝吗?
不是,是为了把一个人的思考过程分拆成三个段落。
你想嘛,如果你是一个有着完整权力的宰相,你做一件事,也要分成这三个阶段。遇到一个难题,先想想怎么办,这就相当于中书省的拟定诏书的过程。办法想出来了,再反思一下,妥不妥当?有没有什么漏洞?这就相当于门下省驳回诏书的功能。思前想后,觉得没有什么破绽了,那就放手去干,这就是尚书省的执行的功能。
你看,原来的分权制衡,是把众多事务分拆,然后让不同的人负责。而唐朝搞的这个分拆,是把一个人的思考过程分拆,让三个人才能拼成一个人。这种分拆方式,就更高级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种分拆方式解决了一个重大的问题:皇帝如果对一件事情不了解,但是又不愿意大权旁落,又想管这件事,行不行?
原来的事务分拆,比如,司法事务,授权给了一个大臣,遇到具体的案子,皇帝要想干涉,那就必须懂法律,懂这个案子,否则你怎么跟司法专业人员抬杠呢?这就给皇帝介入事务,设置了门槛。
而唐朝的这种分拆方式,就高明了。皇帝不用懂。
我举个现代社会的例子,你就明白了:一个公司领导,不懂某个具体的业务,那是不是就不能领导这个业务了呢?不会啊。他可以先问战略部门,这个业务应该怎么开展啊?研发什么产品?怎么销售啊?你们拿一套方案呗?这就相当于中书省。然后他可以在公司内部成立一个方案审核部门,也可以到外面去聘请咨询公司,可以面对面,也可以背靠背,对这套方案提意见,评估可行性。这就相当于门下省。等意见统一了,然后再交给具体业务部门执行。这就相当于尚书省。从始至终,领导不用懂这个业务。不同部门之间,有的只管该不该,不问难不难;有的只管对不对,不问行不行;有的只管低头拉车,不用抬头看路。
其实,中书和门下两省,他们并不真的是,我先拟诏书,然后发给你,你看完了,不合适再驳回来,我改完了再发给你看。这样搞的话,效率就太低了。最后一定是,干脆,咱们两个部门合署办公得了,关于这个事,我中书省想怎么办,我告诉你,你觉得不合适,咱俩现场商量,意见一致了,我再去写诏书。
对,这么合署办公,后来就出现了所谓的“政事堂”,大家虽然角色有差别,但有事一起商量。于是,原来的宰相角色,就从一个人,变成了集体领导。
比如说,唐太宗李世民手下,就有两个很有名的宰相,房玄龄和杜如晦。他们合起来,号称“房谋杜断”。其实,从这个词,你就可以推断出两个人的官职了。房玄龄善于谋划,所以是中书省的领导,出各种主意。杜如晦善于决断,你出主意,我听着,我就判断说,行还是不行。所以,他是门下省的领导。你看,两个宰相各自发挥特长,配合得很好。
王旦这个宰相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说完了“同”和“中书门下”,我们接着来看第三个词:“平章事”。这其实也是中国古代制度设计的一个逻辑,简单说,就是用临时的差遣来代替正式的官职。平章事嘛,就是派你来干这个事,可没说一定让你来当这个官。
历史学者张宏杰老师有一个洞察,中国历史上很多地方官的官名,往往都是动词,什么“刺史”、“巡抚”。为什么呀?因为一开始,他们都不是常设的地方行政官员,他们都是临时被朝廷派来办一个事的,久而久之才成了地方官。
再比如,清代有所谓的军机大臣。其实他们的正式名称不叫“军机大臣”,而叫什么“军机处行走”、“军机处学习行走”、“军机大臣上行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等等。你看,这个官职,核心还是动词,刚开始都是临时差遣,都是以本来的身份去干个别的事儿。直到清代末期的光绪年间,才有直接任命成“军机大臣”的例子。
可以再举个例子,一个县的县官,你肯定听说过,有叫“县令”的,有叫“知县”的,那他们之间有区别吗?有。县令,这是从秦汉开始的一县之长的正式称呼。但是到了唐代安史之乱之后,地方上很动荡,于是就出现了一种临时性的差遣,有的叫“权知某县令”,有的叫“知某县事”。意思就是,你的本职工作,不是这里,但是临时派你去管一下某个县。
那你说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很多啊。首先,便于处理各种新的挑战。就像我们今天的公司里面,有一个新的业务,很重要,怎么办?各个部门抽调得力干将,组成一个临时机构,先干着。干出名堂,再决定要不要成为正式的部门。这样更灵活嘛。
还有一点,就是官员的本职和实际工作分拆开来,就导致他们能上能下。就拿寇准举例子,1006年他罢相,知陕州。一个宰相,怎么能降级降那么多呢?从中央大员,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小地方官,这个落差怎么受得了?但其实呢,严格地说,寇准并没有被贬官,他的本职,一直是正三品的刑部尚书。只不过原来被差遣去当“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宰相,现在换了个差遣,去“知陕州”而已。不是地方官哦,你的本职还是刑部尚书哦。你看,这么处理,大家面子上都不难看。
好了,我们刚才是借“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个官名,借题发挥,讲了中国古代制度演化的三个逻辑:第一,用不够资格的人暂时替代够资格的人;第二,用分拆后的多个角色来替代一个完整角色;第三,用临时差遣替代正式官职。
你听下来,会不会有一个感觉?奇怪,为什么朝廷行政,不是用正式制度,光明正大地推行政策,而是非要搞出一套,曲线救国、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非正式制度呢?
确实,这又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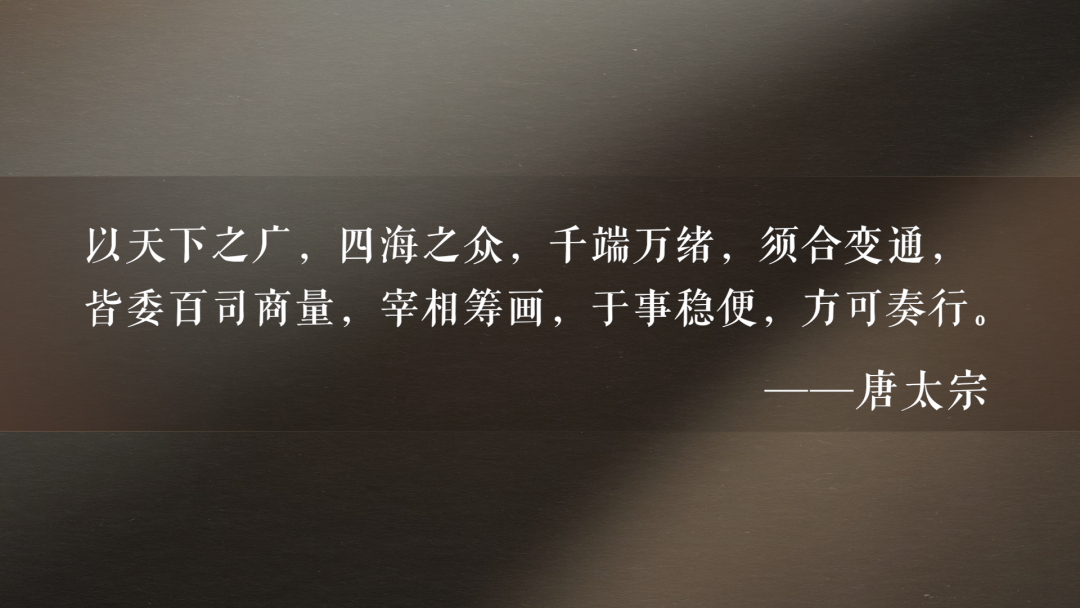
“非正式制度”
今天我们讲的是中国宰相制度演变的一个小侧面。
过去读书,经常看到一个说法,说中国政治制度演化,就是皇权持续强化,皇权不断打击、剥夺宰相权力的过程。
对,这好像也符合事实。从汉代还有一个名义上的丞相,到唐宋宰相制度的分权制衡、集体领导,到了明朝,宰相干脆被废掉,到了清朝,只剩下了跪着记录皇帝意见的军机大臣。这不就是皇权剥夺相权吗?
但是你抽身出来一想:不对啊。中国自从有了皇帝制度,皇帝就是大权独揽的,这从来没有疑问。宰相是什么?是皇帝请来干活的职业经理人啊,是皇帝授权,他才有权力的人。皇帝先是授权给他,然后再处心积虑地剥夺他的权力,这是何苦呢?这就相当于一个公司的董事会花重金请来了一个总经理,然后又想方设法削弱这个总经理的权力,那你图啥呢?

所以,问题不在于皇权和相权之间有什么争斗。而是什么样的宰相制度,既不威胁皇权,又能有很高的行政能力?皇帝和宰相,不是要分一个高低胜败,这事早就定了。他们是要在各种可能性中艰难地寻找一种平衡:让整个制度设计,既能保证秩序安全,又能兼有行政效率。这才是一个真问题。
从我们前面的分析,你能看得出来,让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共存,正式和非正式之间,有模糊地带,有弹性空间,就是一个有效的办法。
中国从古代开始,就是这么巨大的一个政治共同体。没有一套漂亮的正式制度,不行。但是如果只有一套漂亮的正式制度,也是没有办法运转的。在正式制度的末端,必须要有各种变通的、临时的、模糊的非正式制度,整个国家的治理,才会有弹性。
举个例子,唐代的三省六部制,设计得可漂亮了。跟长安城一样,设计得四方四正的,特别有秩序感,甚至是美感:上面一个皇帝,然后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下面是六部,六个部里面整齐划一地,每个部有四个司。比如,吏部,四个司:吏、勋、封、考;户部也是四个司:户、度、金、仓。每个部都这样,画出表格来,漂亮得很。
但是你想,那么复杂的行政事务,怎么可能这么整齐划一,严丝合缝地把职能分配到四个司呢?所以,在正式制度下面,一定是暗流涌动,实事求是地搞出了大量的非正式制度。
费孝通先生有一本《乡土重建》,这里面就提出来一个有趣的概念,叫“双轨政治”。自上而下的正式制度,是一条轨道。到了民间,大量的非正式的民间规则,是另一条轨道。中国政治是同时运行在这两条轨道上的。
这书里面举了一个例子,比如朝廷收税。县官制定出税收指标,每家每户每块地要交多少,那都是有数的。但问题是,皇权不下县啊,县以下,政府就没有“腿”了。数字是有,但是怎么收上来呢?
县里面的官差,只能把命令传递到保长这一级。保长是个苦差事,都是老百姓轮流干,他没有任何权力。保长只能跑去和各个村、各个家族的族长商量,县里让交这么这么多。如果族长觉得不合理,那就不交。
县里能有什么办法呢?最多也就是把这个保长抓起来,打屁股。朝廷的王法,厉害到头也就这样了。
下面的族长,也不能任由自己人被打屁股啊,所以,他们会出面,从各种公开的、私下的渠道和官府谈判,直到达成协议。然后县里把数字改一改,底下把粮食交一交,挨了板子的保长放回家。这事才算完。
王亚南先生的这本名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里面也提到,中国古代收税,叫做“原则上不让步,实施上不坚持”。什么意思呢?“原则上不让步”就是说,有一整套正式制度和数字指标,不能变的,一变就不好交代。但是实际上呢?根据具体情况再具体执行。实施上是不能坚持的。最后各方面过得去就行了。
带着这个视角,你再去看唐宋的宰相制度,再去看那个古里古怪的名字,“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会多一点“理解之同情”啦。
话说,南宋的时候,有人称颂宋太祖赵匡胤,说我们太祖牛啊,当皇帝之后,把五代时候的乱七八糟的制度都改掉了,所以,才能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
但是大儒朱熹听到这番话,就不认同。他说,不然啊,我们太祖只是把太过分的制度去掉,剩下的法令条目能留还是留。只要是个做事的人,能抓大放小,这才是英雄手段。你看后来那个王安石,大逻辑搞不懂,天天计较细节,结果变法就搞得一塌糊涂嘛。
朱熹说得真好啊。1000年前,他居然就把这个词儿说出来了:“做事的人”。
一个真想做事的人,就是这样:尊重正式制度,同时也尊重现实条件,不瞎动乱改,在现实基础上,根据需要,创生出一条条的权宜之计,蜿蜒曲折地、坚定地向前推动自己的目标,最终,虽然看起来有点乱哄哄的,有点不知所云,就像我们今天讲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个官名一样,但其实,他已经走出来了一条细如发丝的黄金中道。
这才是“做事的人”。
好,这就是1016年我们的话题。下一年,咱们专门讲宰相王旦。公元1017年,再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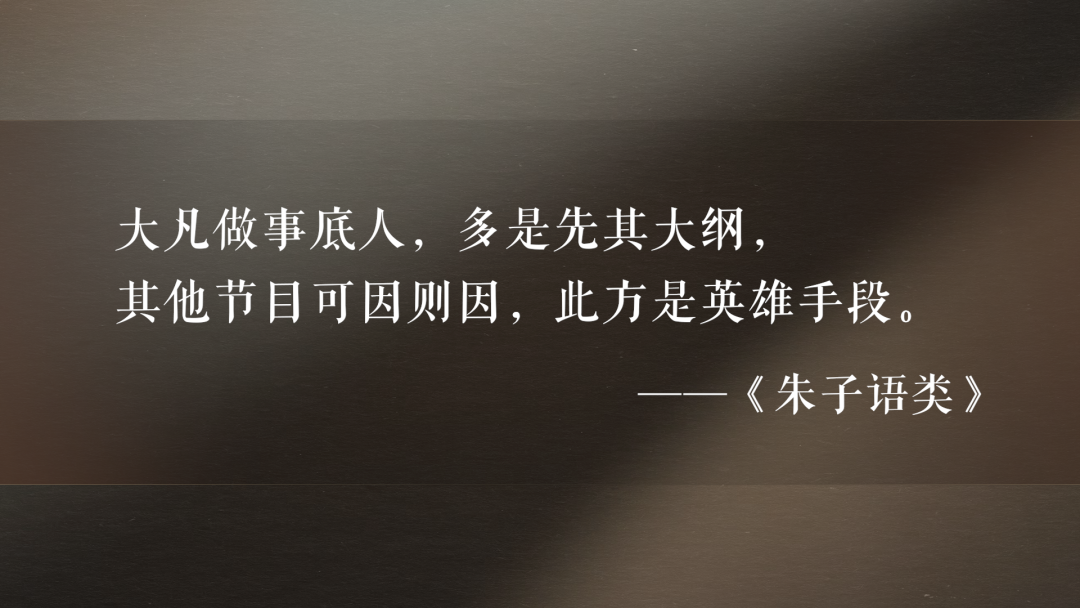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