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鲍勃·迪伦:歌唱的奥德赛,时代的灵魂交响
青年副刊为《复旦青年》学术思想中心出品:共分为思纬、读书、天下、艺林、同文、诗艺、灯下、专栏八个栏目,与你探讨历史、时事、艺术等话题。
诗
艺
有人说,诗歌是一个时代最后的秘密,是诗意照进现实的时刻。诗的世界,是“折叠”的广博,精致凝练在表,深刻隽永在里,言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意是“千呼万唤始出来”。
“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得主。他从喧嚣巨变的六十年代走来,被官方评为“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开创了新的诗意表达”,他是民谣艺术家,也是诗人——鲍勃·迪伦。作为逝去时代的歌唱者,迪伦是自由的、诗意的,像一颗滚石。他在歌唱中热泪盈眶,而歌声在风中飘荡。”
复旦青年记者 李欣桐 主笔
复旦青年记者 李欣桐 朱新颜 编辑
初探世界:民谣与时代

▲鲍勃·迪伦正在阅读一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报纸的头版写着大字“宣战”/图源:让-多米尼克·布里埃:《鲍勃·迪伦:诗人之歌》
今年是鲍勃·迪伦的83周岁诞辰。1962年,21岁的鲍勃·迪伦从他的故乡,美国北部的明尼苏达州离开,只身前往纽约追求他的民谣音乐梦想。20世纪60年代初,那时的鲍勃·迪伦还保留着自己的原名,罗伯特·齐默曼,一个乡下穷小子,狂热地迷恋着那时当红的民谣歌手伍迪·格思里(Woody Guthrie)的曲子。
“伍迪的歌曲对我就有那么大的影响,我吃些什么,怎样穿衣,我想认识什么人,我不想认识什么人,我每走一步都受到它的影响。”来到纽约后,迪伦仿效自己喜欢的英国诗人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的名字,将自己的艺名改为鲍勃·迪伦。在伍迪的病榻前,鲍勃·迪伦为他唱了一首歌,这也是迪伦生命中第一首属于自己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歌曲。
I'm out here a thousand miles from my home
只身在此我远离家乡一千里
Walkin' a road other men have gone down
走在一条别人都走过的路上
I'm seein' your world of people and things
我看见了你世界中的人与事
Your paupers and peasants and princes and kings
你的穷人与农人,王子与国王
Hey, hey, Woody Guthrie, I wrote you a song
嗨嗨,伍迪·格思里,我为你写了一首歌
'Bout a funny ol' world that's a-comin' along
关于前行中的可笑的苍老世界
Seems sick an' it's hungry, it's tired an' it's torn
它似乎病了饿了,累了也破了
It looks like it's a-dyin' an' it's hardly been born
看起来它已经要死了却才出生
Hey, Woody Guthrie, but I know that you know
嗨,伍迪·格思里,但我知道你知道
All the things that I'm a-sayin' an' a-many times more
所有我说的事,而且多过它好几倍
I'm a-singin' you the song, but I can't sing enough
我为你唱首歌,但是我总是唱不够
'Cause there's not many men that have done the things that you've done
因为没有多少人做过你做过的事
——节选自《献给伍迪的歌(Song to Woody)》
与此同时,在鲍勃·迪伦的年轻时代,世界正经历着巨变。二战结束,旧世界已然离去,新世界却还未来临。风云变幻的政治、发展的城市、嬉皮士、垮掉的一代……太多隐藏在城市里来去的故事,太多属于人们的情绪与声音,那些被看见的和不被看见的。
作为音乐狂热者,迪伦素有听收音机的习惯。但那个年代收音机里播放着的流行音乐,都是如“牛奶和糖”一般的单调主题,似乎所有歌手都在歌颂着爱情,但却缺少了能够体现这个时代双重性格的歌曲。在自传《编年史》中,迪伦曾这样说到,“《在路上》(On the Road)、《嚎叫》(Howl)和《汽油》(Gasoline)代表的街头意识形态标志着一种新型的人的存在,它们不在这里,但你能期望什么?每分钟45转的唱片做不了这些。”
年轻的迪伦期待着自己的音乐能够做些什么。他开始写自己在新闻里、在街头看见的世界;他也让过去的事进入他的歌曲——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加尔维斯顿的洪水等等已然完结的事件。民谣对迪伦来说是探索世界的图画。他将眼里的世界都写进他的歌曲里,这其中有他眼中,一整个向前的时代之缩影。
The line it is drawn
界限已经划定
The curse it is cast
诅咒已经施加
The slow one now
现在跑得慢的人
Will later be fast
不久就将健步如飞
As the present now
因为这现在
Will later be past
马上就会变成过去
The order is
当下的秩序
Rapidly fadin'
正在快速地消亡
And the first one now
现在是第一的
Will later be last
马上就会落到最后
For 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
因为这时代 时代它不停在变呐
——节选自《时代在改变(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
歌唱的诗:战后的吟游诗人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致辞中,鲍勃·迪伦曾提到过对自己影响最为深刻的三本书,其中一本便是古希腊盲诗人荷马的史诗《奥德赛》。在《奥德赛》中,诗人呼唤缪斯女神,请求给予自己歌唱的能力,“在我之中歌唱吧,缪斯,借我之口来讲述故事。”(“Sing in me, oh Muse, and through me tell the story.”)当我们回归诗歌的本质属性,我们会发现诗的本源是歌曲。从古希腊的歌唱传统,到中世纪的吟游诗人,诗歌总是被吟唱着。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垮掉一代”文学创始人如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同样坚持着诗歌是要被听见而非被阅读,其必要元素一定包含了音乐性。而作为音乐家的鲍勃·迪伦,将自己的诗歌融入进自己的音乐里。他的诗意表达与敏锐洞察使得他的歌曲与同时代的流行音乐相区分开来。
美国桂冠诗人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曾评价鲍勃·迪伦为“战后的铁器时代诗人”,但或许此处称迪伦为“吟游诗人”更为合适。低沉的声音,简单的吉他和弦,悠扬的口琴,寥落的键盘音,这是鲍勃·迪伦从诗歌吟唱传统走来的,作为当代吟游诗人的形象。
鲍勃·迪伦并不总是写社会与政治,与其说他是一个尖锐的批判者,不如说他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他将看见的写进歌里,再将它们唱出来。在《奥德赛》中,奥德修斯进入冥府拜访阿喀琉斯后得到一个结论,即死者世界的荣耀与不朽远不如安宁与长寿的生命。对鲍勃·迪伦来说,歌曲也是如此。歌曲是活着的,在生者的国度里,歌曲注定被歌唱而非被阅读。

▲《自由不羁的鲍勃·迪伦(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专辑封面/图源:网络
在鲍勃·迪伦的歌词中,诗歌的痕迹无处不在。一个优秀的诗人,必然是掌握了诗歌本质的韵律、意象与思想,并将它们以一种属于自己的创新性的方式表达出来。在六十年代早期的专辑《自由不羁的鲍勃·迪伦(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中,创作于古巴导弹危机前夕的《暴雨将至(A Hard Rain's A-Gonna Fall)》无疑是将歌曲与诗完美融合的成功之作。借鉴了一首英国中世纪童谣的对话体形式,全曲以两个句式相仿的问句,以及与上文问句分别对应的不同的回答而穿插贯彻始终,并形成了韵律整齐的段落分隔:
Oh, where have you been, my blue-eyed son?
噢 你都到过哪里 我的蓝眼小子
And where have you been, my darling young one?
你到过哪里 我亲爱的年轻朋友
……
Oh, what did you see, my blue-eyed son?
噢 你见识过什么呢 我的蓝眼小子
And what did you see, my darling young one?
你见识过什么呢 我亲爱的年轻朋友
……
And what did you hear, my blue-eyed son?
你听到过什么呢 我的蓝眼小子
And what did you hear, my darling young one?
你听到过什么呢 我亲爱的年轻朋友
……
Oh, what did you meet, my blue-eyed son?
噢 你遇到过什么人呢 我的蓝眼小子
And who did you meet, my darling young one?
你遇见过什么人呢 我亲爱的年轻朋友
……
And what'll you do now, my blue-eyed son?
现在你会做些什么呢 我的蓝眼小子
And what'll you do now, my darling young one?
现在你会做些什么呢 我亲爱的年轻朋友
其中,对于“蓝眼小子”与“年轻朋友”的问句从“been”到“see”,从“hear”到“meet”,最后汇聚成“do now”,形成了递进式结构,从感官感知到实际的行为,不仅使歌曲结构变得精巧完整,同时也让歌曲中想要表达的事物变得立体,而一切的一切融入进这场暴雨的声音里——“It's a hard rain's a-gonna fall(一场暴雨铺天盖地将至)”。同时整齐的韵脚也使得歌词在歌曲这一形式中朗朗上口,在吟唱中变得完整。
每个段落都描绘了不同的场景,它们宏大,神秘,在歌声中蒙上了一层忧伤的气息。他用文字渲染出一个近似末日的世界,一场暴雨即将来临前的世界。这些神秘的意象组合在一起,诡异地闪烁着兰波式的象征主义色彩,引诱听者进入那个压迫的、诡谲的暴雨前夕。
And what'll you do now, my blue-eyed son?
现在你会做些什么呢 我的蓝眼小子
And what'll you do now, my darling young one?
现在你会做些什么呢 我亲爱的年轻朋友
I'm a-goin' back out 'fore the rain starts a-fallin'
我会在暴雨降临之前离开此地
I'll walk to the depths of the deepest dark forest
我会走进最黑暗的森林深处
Where the people are many and their hands are all empty
那儿人头攒动 但他们两手空空
Where the pellets of poison are flooding their waters,
那儿沾满毒药的子弹涌进他们的水域
Where the home in the valley meets the damp dirty prison
那儿山谷中的家碰上潮湿肮脏的监狱
And the executioner's face is always well hidden
刽子手的脸总能被好好藏起
Where hunger is ugly, where the souls are forgotten
那儿饥饿令人憎恶 灵魂尽遭遗忘
Where black is the color, where none is the number
那儿黑色只是一种颜色 “没有”只是一个数字
And I'll tell it and speak it and think it and breathe it
我会辨别它 说起它 想起它 吐纳其间
And reflect from the mountain so all souls can see it
从山上反射出的倒影 所有的灵魂都能一望而知
Then I'll stand on the ocean until I start sinkin'
然后我会站立在海水面上直到我开始下沉
But I'll know my song well before I start singin'
但我非常了解我的歌 在我还没唱出它之前
And it's a hard, it's a hard, it's a hard, and it's a hard
然后一场暴雨啊 暴雨啊 暴雨啊 暴雨啊
It's a hard rain's a-gonna fall
一场暴雨铺天盖地将至
——节选自《暴雨将至(A Hard Rain's A-Gonna Fall)》

▲《尽数带回家(Bringing It All Back Home)》专辑封面/图源:网络
鲍勃·迪伦歌曲中诗意表达的发展在1965年发布的专辑《尽数带回家(Bringing It All Back Home)》达到顶峰。在这张专辑里,鲍勃·迪伦开始玩味语词的形式,并试图在自由的诗句连结中创作出强有力的句子与旋律。
就歌词而言,其中最著名的歌曲《铃鼓手先生(Mr. Tambourine Man)》由多个迷幻与飘渺的意象堆叠出兰波式的象征主义隐喻与通感,一种以幻觉和自由交织组成的歌曲。歌曲灵感源自于1964年2月,迪伦和几个朋友在公路旅行途中的新奥尔良看到的狂欢节景象,而这首歌则更多描写了狂欢迷醉之后的迷惘与寂寞。
而在形式上,迪伦效仿了惠特曼的“自由诗行”,并列举出意象与人物,构建出了一个整体场景,并以同样的句式或短语开启一段诗行,这一点已在前文所提到的《暴雨将至(A Hard Rain's A-Gonna Fall)》中有所体现。在本歌中,迪伦不断重复着的同样是这首歌的高潮部分,“Hey! Mr. Tambourine Man, play a song for me(嘿!铃鼓先生,为我奏一曲)/I'm not sleepy and there is no place I'm going to(我尚未入眠,且无处可归)/Hey! Mr. Tambourine Man, play a song for me(嘿!铃鼓先生,为我奏一曲)/In the jingle jangle morning I'll come followin' you(在这铿锵作响的早晨让我与你同去)”。
Hey! Mr. Tambourine Man, play a song for me
嘿!铃鼓先生,为我奏一曲
I'm not sleepy and there is no place I'm going to
我尚未入眠,且无处可归
Hey! Mr. Tambourine Man, play a song for me
嘿!铃鼓先生,为我奏一曲
In the jingle jangle morning I'll come followin' you
在这铿锵作响的早晨让我与你同去
Then take me disappearin' through the smoke rings of my mind
然后带我消失罢,穿过我意识中的烟圈
Down the foggy ruins of time, far past the frozen leaves
沉入时光深处雾气氤氲的废墟,远远越过冻僵的寒叶
The haunted, frightened trees, out to the windy beach
穿出阴森悚栗的林木,来到多风的沙滩
Far from the twisted reach of crazy sorrow
与狂乱伤悲的扭曲界域,遥遥隔开
Yes, to dance beneath the diamond sky with one hand waving free
是的,在钻石的天空下起舞,一只手自由的挥舞
Silhouetted by the sea, circled by the circus sands
侧影反衬着海水,四周是圆场的黄沙
With all memory and fate driven deep beneath the waves
带着一切记忆与命运,一齐潜入翻涌的波涛之下
Let me forget about today until tomorrow
且让我忘记今日直到明天来临
——节选自《铃鼓手先生(Mr. Tambourine Man)》
迪伦用对话的谣曲形式,唱出了其埋藏在隐喻中的哲思。“让我忘记今日直到明日来临”,自由的旅程是否只是一场梦境?最终我们还是带着一切记忆与命运,沉入原点,在虚无中寻找的自由是握不住的黄沙,也许自由不存在,我们所做的也只有注视着此刻的世界,在这铿锵作响的早晨与铃鼓手先生一同离去。
形式上的突破在本专辑其他歌曲中亦有体现。在受到垮掉派影响明显的歌曲《地下乡愁蓝调(Subterranean Homesick Blues)》中,迪伦将自己一贯采用的长句诗体改成短促而极押韵的短句形式,如“Keep a clean nose(要安分守己)/Watch the plain clothes(当心便衣)/You don’t need a weatherman(你不需要气象员)/To know which way the wind blows(就知道吹的是什么风)”以及“But losers, cheaters(然而衰人和骗子)/Six-time users(有六次经历的瘾君子)/Hang around the theaters(都在剧院周围游荡)”等语句,在一连串连珠炮式的念唱中,语言的质地变得轻盈而诙谐,同时又暗含了讽刺意味。在音乐上,这首歌混合了民谣风格与电吉他,是迪伦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民谣摇滚”。
而在歌曲《伊甸园之门(Gates of Eden)》中,迪伦有意识地通过典故、改写、戏拟的方式把自己的创作同文学经典和诗歌传统联系在一起。这是一首神秘而费解的歌。伊甸园之门这一意象,屡见于犹太教经文中。在歌曲里存在着大量宗教与传统文学意象,并被迪伦加上了新的流行色彩,如“牛仔天使(cowboy angel)”“阿拉丁和他的神灯(Aladdin and his lamp)”“乌托邦的隐修僧(Utopian hermit monks)”“金牛犊(Golden Calf)”“黑色圣母(black madonna)”等。
这一连串史诗般的意象与圣经风格的隐喻,最终引出的是一句同样隐喻式的悲叹——“And there are no truths outside the Gates of Eden.(而伊甸园之门外面没有真理)”。这首歌的歌名在后来被莫里斯·迪克斯坦引用在展示美国六十年代文化史的书籍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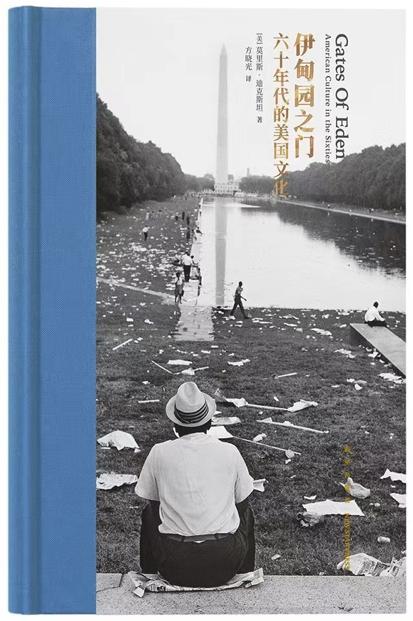
▲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书籍封面/图源:网络
自由钟声:答案在风中飘
In the city's melted furnace, unexpectedly we watched
在城市的熔炉中,我们藏起脸
With faces hidden while the walls were tightening
意外地望见墙壁在加固
As the echo of the wedding bells before the blowin' rain
随着婚礼的钟声的回音在雨吹打之前
Dissolved into the bells of the lightning
消融在闪电的钟声里
Tolling for the rebel, tolling for the rake
为反叛者而鸣钟,为浪荡子而鸣钟
Tolling for the luckless, the abandoned an' forsaked
为不幸的人、被遗弃的和被抛弃的人而鸣钟
Tolling for the outcast, burnin' constantly at stake
为被驱逐的、在危险中持久烧灼的人而鸣钟
An' we gazed upon the chimes of freedom flashing
我们凝视着自由的钟乐在闪耀
——节选自《自由的钟乐(Chimes of Freedom)》
这首歌出自鲍勃·迪伦在1964年发行的专辑《鲍勃·迪伦的另一面(Another Side of Bob Dylan)》,其所歌颂的主题“自由”成为上世纪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反抗歌曲代表作之一。而“自由”这一关键词同样也贯穿着迪伦的一生。比起流行歌手,他的活法更像一个自由不羁的诗人。迪伦并不在意将他捧上神坛的人们期望他写些什么、唱些什么,他不在乎昨日的世界与今日的世界要求他去歌唱那些风起云涌的政治与社会事件,而从来只做他自己:
“我确实从来都只是我自己——一个民谣音乐家,用噙着泪水的眼睛注视灰色的迷雾,写一些在朦胧光亮中漂浮的歌谣。现在我的名声已在我面前炸开,正笼罩在我头上。我不是一个表演奇迹的传教士。”
因此,他会勇敢地追求歌里的革新,一如他曾经在绵腻的流行情歌市场里开辟出属于自己的民谣史诗道路。在1966年5月17日,当他奏响那首由电吉他伴奏的《瘦人叙事曲(Ballad of a Thin Man)》时,观众们都感到不解与愤怒,认为他是民谣音乐的背叛者,而“把自己埋葬在一座震耳欲聋的电声坟墓里”。其中有一名观众甚至对台上演奏的迪伦咬牙切齿地怒吼:“犹大!”而迪伦那时只是转向身后已经开始演奏《像一颗滚石(Like a Rolling Stone)》的乐手,让他们“再大声些”。
此后的迪伦正式转向摇滚音乐,这不仅推动了美国音乐从民谣时代进入摇滚时代,同时也将他的诗歌才华融入到摇滚歌词的创作中。这使得摇滚乐通过他的作品变成犹如众多富含隐晦问题和模糊暗示的浪漫诗歌,让“摇滚”升华为一种公认的艺术形式,将词曲作者的角色提升至高等文化模式中的核心创作人地位。原本仅注重身体化、本能化、感官化的摇滚音乐,在迪伦的诠释下获得了诗性的维度。
我从来都只是一个站在自己的角度看世界的独行者。这就是我。我或许曾经让某些人明白,不可能也可以成为可能。如果我有什么想要与别人分享的,那就是这一点:不可能也可以成为可能。一切皆有可能。我只想说这一句。别的都没什么可说的。我的歌词里有些什么?有勇敢。没别的。我始终只是个民谣歌手而已,在歌唱的时候热泪盈眶,歌声在闪光的雾气间浮动。
——鲍勃·迪伦
迪伦的自由同样也体现在他的诗句里。他的歌里没有非黑即白的说教定义,也从来不给人答案。2020年,在全球都被蒙上疫情的阴霾时,年届79岁的鲍勃·迪伦发行了一首长达16分钟的单曲《最坏的谋杀(Murder Most Foul)》,以讲述肯尼迪遇刺为基调,用丰富的隐喻和引用向人们铺陈出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景观。《乱世佳人》、披头士、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狼人杰克、恶魔岛上的鸟人等等意象像梦境一样在听者的意识中漂移。
这是旧时代的挽歌——在西方世界似乎将要消失的时刻,对于西方世界的流行文化进行了近乎狂热的总结。这同样也可以被理解为迪伦对于如今的世界的抚慰——回望从前,也有一个时代如今日一样令我们惶然无措,但我们最终都会继续向前走。

▲鲍勃·迪伦的经典演出造型/图源:网络
在自传《编年史》中,迪伦如此感叹着:“无论我到哪里,我都是一个20世纪60年代的游吟诗人,一个摇滚民谣的遗迹,一个从逝去时代过来的词语匠人,一个从无人知晓的地方来的虚构的国家首脑。我处在被文化遗忘的无底深渊之中。你们为它命名。我无法撼动它。”他不说寓言,只是吟唱着他的诗句,他和那个时代里每一个人一样迷惘,他不是先知,也非救世主,只是一个满怀激情,歌唱着,歌唱着的诗人。而答案,在风中飘荡着。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一个人要走多少路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才能称得上真正的人
How many seas must a white dove sail
一只白鸽要飞越多少片海
Before she sleeps in the sand
才能安歇在沙滩上
Yes, and how many times must the cannonballs fly
炮弹要飞多少次
Before they're forever banned
才能将其永远禁止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朋友,答案在风中飘荡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答案在风中飘荡
——《在风中飘荡(Blowin' in the Wind)》
微信编辑丨李欣桐
审核丨张志强
原标题:《鲍勃·迪伦:歌唱的奥德赛,时代的灵魂交响》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