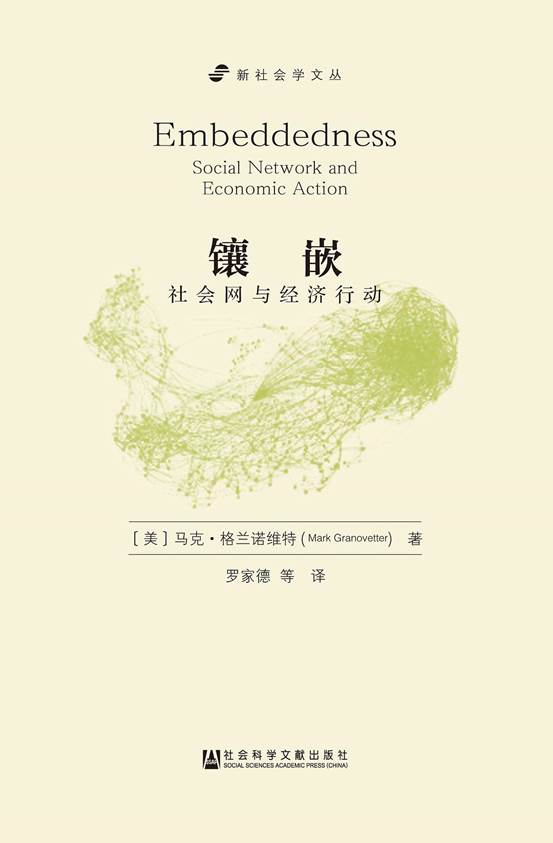特别喜欢陈奕迅的《十年》,娓娓道来,一次情感经历,或者一段人生旅程。“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
林夕曾说,他写人生的词全给了Eason(陈奕迅),大概是觉得Eason能以最恰当的方式演绎了林夕笔下的人生百味。十年很长,十年也很短。一些故事注定要发生,而另一些事情注定要结束。生活原本就如路边平常得不能在平常的杂草,顽强地在城市的坚硬丛林里生长,无需绚烂。不如坐在窗边,喝着一杯祁红,或者老家的金山时雨,静静听歌,品味着波澜不惊的人生。
身后是书架,上面挤满了书。这些书大多是读过的,还有一部分实在来不及,只能翻翻,总想着某一天能够去认真读读,但终归是一瞬间的念想而已。有些书大概在书架上就是起到装饰的作用,虽然也都是精品;而另一些书则反复翻阅,如多年的老友时常见面,聊天南海北的新鲜事。Eason唱的是《十年》,而我听着仿佛是二十年。二十年是我开始走上经济学家道路的时间。二十年以前,如歌中所唱,对身后的这些书籍,我不认识,这些书籍也不属于我,我和它们都陪在一个陌生人的左右。而二十年以后,我和这些书籍是真正的朋友,时时刻刻都可以问候。读书随缘,有些书籍注定是你的缘分,你会反复和它对话,感受着来自它的问候。而有些书籍注定无缘,只能静静呆在书架上,尴尬地彼此相对。
我并不是学经济学出身,也没有接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偶然的兴致考上了浙江大学经济系的研究生,开始攻读经济学专业的学位。好在自己有企业工作的丰富阅历,倒也方便选择研究方向。理解企业成了入门的第一课。可能是工作经历形成了刻板印象,使得自己在选择书籍的时候很是挑剔,一般的写企业方面的书在我看来都有点纸上谈兵,似乎和自己所见的企业根本不在一个世界。直到某一天,在浙大图书馆翻到了罗纳德·H.科斯的《企业、市场与法律》,这其实是科斯的一本论文集。我只关心企业问题,自然就重点看了其中的一篇《企业的性质》,第一印象是,这篇论文很奇怪,提出了一个怪问题:企业为什么存在?对呀,自己在企业成天呆着,可是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或者说从来没意识到还能有这个问题。这个提问第一次激发了我寻求学术答案的兴趣。科斯的回答是,因为交易成本。现实的社会中存在各种交易成本,这些成本被早期的经济学家所忽略,但这些成本非常重要。假如不考虑这些成本,根本不需要企业,因为任何物品都可以通过市场来组织生产。比如说一件衣服,可以分解成纽扣、布料、设计等环节,我可以向市场分别购买这些中间材料,然后自己组装,也可以直接向某个服装企业购买做好的衣服成品。哪个更方便?假如没有交易成本,两者是等价的。所以我根本不需要向服装企业购买成品,自己可以不费任何力气就组装好一件衣服。问题在于,现实的世界里交易成本普遍存在。我自己制作衣服的成本实在太高,远不如向服装厂购买成品衣服来得划算。服装厂制作衣服的交易成本很低,也就有了存在的理由。
由科斯的书推广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何我呆在企业里经常无所事事?我所在的企业是当地最好的一家国企,也是当时唯一一家活得还算滋润的国企。可即便如此,厂子里的人仍然经常愉悦地玩耍,人浮于事的现象非常普遍,厂内很多事情都要讲关系、讲背景,能力当然重要,但只是决定一个人发展空间的一个普通因素,甚至都不是重要因素。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直到我从图书馆借来了
《短缺经济学》一书,这是
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撰写的关于计划经济的著作。在这本书里,科尔奈解释了为何计划经济普遍存在短缺现象?原因在于预算软约束问题。由于政企一家,企业没有硬约束,就会导致官僚主义、人浮于事等现象,从而导致企业激励失灵,供给不足。科尔奈的这个观点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迈克尔·布若威的看法在一些层面上是相呼应的。
布若威在其
《生产的政治》一书中指出,计划经济下通过形成国家层面的官僚体系来统一配置资源,从而国企只不过是这官僚体系下的一个具体环节而已。科尔奈和布若威等人关于国企的分析其实也可以用科斯的理论来解释,即计划经济体制交易成本太高,所以导致了普遍的短缺和低效率。
经常听到国内一些学者批评科斯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对产权的过度关注。但这其实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误读。在读硕士的最后一年,我只身来到北京,当了几个月的北漂,在国家图书馆度过了非常愉悦的一段时光。国图藏书丰富,我特意借阅了
奥利弗·E.威廉姆森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威廉姆森的写作比较晦涩,所幸自己还是啃下来了。这部著作大概能在引用率方面排到前列。与其说是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不如说是分析市场经济制度更妥当。威廉姆森是科斯思想的真正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其核心思想是,社会中存在多种多样的组织(治理机制),包括市场、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介于市场与政府之间的某种形态,这些组织各有各的交易成本,组织的边界取决于交易成本的相对大小。也就是说,按照威廉姆森的观点,资源配置是采取市场多一点,还是政府多一点,完全取决于各自的相对交易成本大小。这就意味着某个特定经济体在某个特定的阶段并不必然遵循所谓的小政府教条。因为道理很简单,类似我们这种转型社会,市场机制还没有完全发育好,欠发达的市场可能交易成本较高,此时反而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更多地参与资源配置。实际上,后来
科斯和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一书中,也没有把产权改革放在核心位置,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认可渐进改革的路径。
对早期中国改革开放影响很大的,大概就是科斯和威廉姆森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而这也导致该学派频繁被批评。科尔奈可以说是哺育了整整一代早期改革开放时期活跃的经济学家。不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开始显现,其中最重要的是不平等问题。也正是这一背景,
阿马蒂亚·森的著作开始备受关注。彼时我已经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留在经济学院西方经济学教研室任教。最早接触森的著作是他的
《以自由看待发展》和《贫困与饥荒》。森被称作经济学家的良心,始终关心人类发展难题。通过对印度和孟加拉等地进行实地研究,森发现贫困的根源在于穷人缺乏必要的权利,也就是说穷人面临着选择的约束和分配机制上的劣势。这一发现几乎颠覆了人们通常对贫困的认知。因为在常人看来,贫困当然是缺钱或缺少物质,或者缺乏教育,或者是缺少人力资本,或者因为懒惰等等。但森认为这些都是表面因素,真正的因素在于穷人的权利是不完整的。有效地反贫困需要首先需要解决穷人的权利缺失问题。比如解决农村的留守儿童问题并非仅仅着眼于改善农村教育状况,而是赋予留守儿童完整的接受教育的权利,这就意味着农村劳动力流动需要伴随着相关儿童教育的城镇化问题。森的思想对于解决当前的不平等可能非常重要。
说到城镇化,就不得不想起农村。我自己出生在安徽南部县城绩溪的一个小山村,小山村的变迁实际上就是整个中国的变迁缩影。小的时候经常吃不饱穿不暖,改革开放以后生活才慢慢好起来。村里的人开始外出打工,成为城镇化过程中流动的劳动人口中的一份子。现在村子富裕了很多,但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人情味淡了。以前读
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就觉得是写自己家乡的。可能同是江南,社会结构有一定程度的同质性。《江村经济》这部著作深刻描绘了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家族、村落、权威、生产、贸易、亲缘等种种特征。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乡土社会的基本结构并非亲缘关系,也并非一个个的村落空间,而是个体,以及个体为轴心所形成了社会网络,后来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把这个网络概括为“差序格局”。这个差序格局是说,传统乡土社会其实是个人按照亲疏关系形成一个圈圈,构成关系层级,这个关系层级也就是个体眼中的人际网络,个体总是按照这个差序格局来决定自己的行为。比如家和村之间,家优先;村和乡之间,乡优先。如此类推。这可以看作是传统乡土社会独特的介于个体和社会之间的某种结构。这一结构和流动性差的社会是匹配的。而一旦劳动力开始流动,个体卷入市场机制的洪流,差序格局就被打破,而新的社会网络结构还没有形成,这就导致转型过程当中的惶恐和无助。人情冷暖,可能不过是社会重构的一个个片段而已。
费孝通先生的早期研究也可以看作是后来经济社会学的先期成果之一。
马克·格兰诺维特在
《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一书中,讲述了这样一种情形,在一个社会中,经济行为是嵌入在一组社会网络当中的,从而看似个体的经济行动实际上可能是某些社会结构所决定。不过和纯粹的社会决定论不同,格兰诺维特显然试图将个体行为和社会属性有机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把这本书中所描述的画面想象成一张渔网,网上镶嵌着一条条鱼,看似渔网决定了鱼的命运,实则鱼也在决定着自己的命运。有些鱼奋力挣脱了,从而恢复了自由。而另一些鱼则无力挣脱,只能被渔网束缚。在格兰诺维特的镶嵌理论当中,个体在社会网中互动,既受制于社会网本身,也在努力施展自身的能力。这种理论试图打破过去单纯的个体主义分析范式和社会决定论范式,并重新诠释社会中组织的性质。和新制度学派不同,格兰诺维特更重视个体与社会的互动以及社会结构对组织的影响。这本书其实是作者的论文集,反复品味,受益良多。想想看,改革开放初始,仅仅让劳动力流动起来,许多人便如鱼得水,社会的进步有时候就这么简单。
经济也嵌入在政治结构当中。政治结构其实就是一组规则。一个社会为何需要规则?以及规则是如何产生与演变的?我当时非常好奇,通过阅读
詹姆斯·M.布坎南的《民主财政论》以及
布坎南与戈登·塔洛克合著的《同意的计算》等著作,慢慢理解了规则的意义。在布坎南看来,社会中的规则可以分为基本规则和具体规则,基本规则涉及所有社会成员的利益,而具体规则涉及部分人的利益。给定这个条件,基本规则的形成就需要所有社会成员的一致同意,而具体规则仅仅需要不同形式的多数表决机制。布坎南特别重视一致同意标准,把该标准视为正义标准,等同于
罗尔斯《正义论》里阐述的正义原则。而布坎南的分析起点恰恰是从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演变而来的“不确定之幕”。布坎南把一致同意原则引入到公共财政领域,赋予了公共财政的政治属性,从而公共财政作为一种规则需要经过一致同意或者多数表决机制。在这种情况下,规则的选择和规则之下的选择(具体规则的选择)就被区分开来,从而类似法治社会这种基本规则范畴既是所有社会成员行为规范所需,也是所有社会成员一致同意的结果,进而也就获得了正义层面的正当理由。一个有趣的关注点是,一致同意原则下伴随着不参与的权利,也就是说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都构成规则形成和演变的有效机制。
说到政治,就不得不提及
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钱穆先生并非经济学家,当然不会去对中国传统政治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但他是一个杰出的史学家,从史学视角剖析了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治制度,饶有趣味。这本书实际上是一个讲稿汇编,称不上体系化,也谈不上理论逻辑的完整性,但对一些核心问题给出了简明扼要的回答,且非常有见地。印象较深的是,该书强调传统的政治制度有得有失,这和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契合度有关,如果契合度较好,则会呈现出繁荣;如果契合度较差,则会体现为王朝衰败。这个解释非常接近
道格拉斯·C﹒诺斯所强调的制度适应性观点,在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以及
《理解经济变迁过程》等著作中,诺斯强调制度的适应性效率,即在诺斯看来,很多时候制度无所谓好坏,而在于和当时的情景是否契合。有些从现在看似坏的制度可能在当时特定的情形下是有适应性效率的。钱穆显然也是这么认为。传统政治体系中的结构和制衡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明显的差别,而这差别恰恰反映了一种类似的适应性调整。于是钱穆推演到,即便一种好的制度引入进来,如果不能和本地的传统做很好的结合,也是不能发挥作用的。钱穆在书中具体讨论了汉唐宋明清五代政治制度的具体得失,时至今日,读来仍振聋发聩。
如果说对制度的集中关注是出于改革开放的特定成长环境,那么在思考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逐步开始关注社会心理。一个关键的原因是,转型时期一个好的制度设计可能并不能得到好的落实,理论上看似可实施的制度可能是有重大缺陷的,而这个缺陷就在于没有充分考虑人的心理。心理多重要?制度的演变或者设计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赖理性的假定。而假如理性非常有限,或者说甚至出现了非理性,就可能会导致情绪主导的社会行为,这对于我们这代人都是有记忆的。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心理因素的意义完全是被动地应对心理学家的挑战。
丹尼尔·卡尼曼 、保罗·斯洛维奇、阿莫斯·特沃斯基编的论文集《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启发式和偏差》,记录了心理学家对人的认知的研究。简而言之,人在决策和判断时并非像理性经济人那样,而是依赖启发式和框架,反映出人的认知局限。这些认知局限会体现在很多具体方面,心理学家通过心理学实验来论证和揭示这些局限。经济学家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无论是哪种情形,本质上都是应对心理学家的挑战。
科林·凯莫勒的《行为博弈》把经济学家的应对性研究记述了下来。在这本著作中,凯莫勒承认,一种基于认知科学和经济学交叉研究的新的经济学理论成长起来了,这就是最新的行为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家通过大量实验室实验和实地实验研究发现,人的经济行为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自利性和社会性两个方面,这个社会性被称作“社会偏好”,比如利他、互惠和公平等。社会偏好的揭示等于承认了人除了理智的另一面,那就是情感。由此,经济学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围绕这个新的理论所形成的新的政策设计理念——助推——也日益成为现代社会公共政策设计的重要依据。在我们不断转型的未来,也将看到各种助推政策,这是经济学可以带给社会的福祉。
别说二十年,就是三十年、四十年,或者更为久远,我们还是朋友,还可以时时问候。书已经成为生命的一部分。想想以前苦读的岁月,
商务印书馆的“蓝皮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白皮书”和“黑皮书”、上海三联书店的“绿皮书”和“黄皮书”,这几套书几乎涵盖了大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版的最重要的本土经济学著作和译著,一代又一代经济学人几乎都或多或少翻阅着这些书籍成长。我很难说这些书籍给中国社会变革带来的确切影响,但作为正在经历伟大变革的普通人,无论如何,都希望远方触手可及着一些美好的梦想。我不能改变什么,但我可以在阅读时光中静静地认识自己。
(作者周业安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