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对一项工作来说,重要的是谁来做以及如何做,而不是做什么
【编者按】
奥地利神经与精神病学教授维克多·弗兰克尔以创立“意义疗法”闻名于世,对心理学界影响深远,被称为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之后的维也纳第三心理治疗学派。纳粹时期,他们全家陆续进了集中营,其父母、妻子、哥哥全部死于毒气室内,只有他和妹妹幸存。在痛苦中,他开始追寻生命的意义。他曾对友人说:“发生那么多事、那么多磨难,一定有其意义。”于是在这种极端艰难的环境中,他将目光转向意义,写下了名著《我们活着的理由》和《活出生命的意义》。
他认为,当今社会面临一种“存在的真空”状态,人们普遍患有一种“心灵性神经症”。针对这种状况,他提出了意义治疗和存在主义分析。在本书中,他将哲学与治疗交织在一起,讨论了生命、死亡、工作、痛苦和爱情的意义,分析了焦虑症、强迫症、忧郁症、精神分裂症背后的深层心理。
本文摘自《我们活着的理由:弗兰克尔论生命的意义》[奥]维克多·弗兰克尔 著,王琳琳 译,岳麓书社·浦睿文化2024年4月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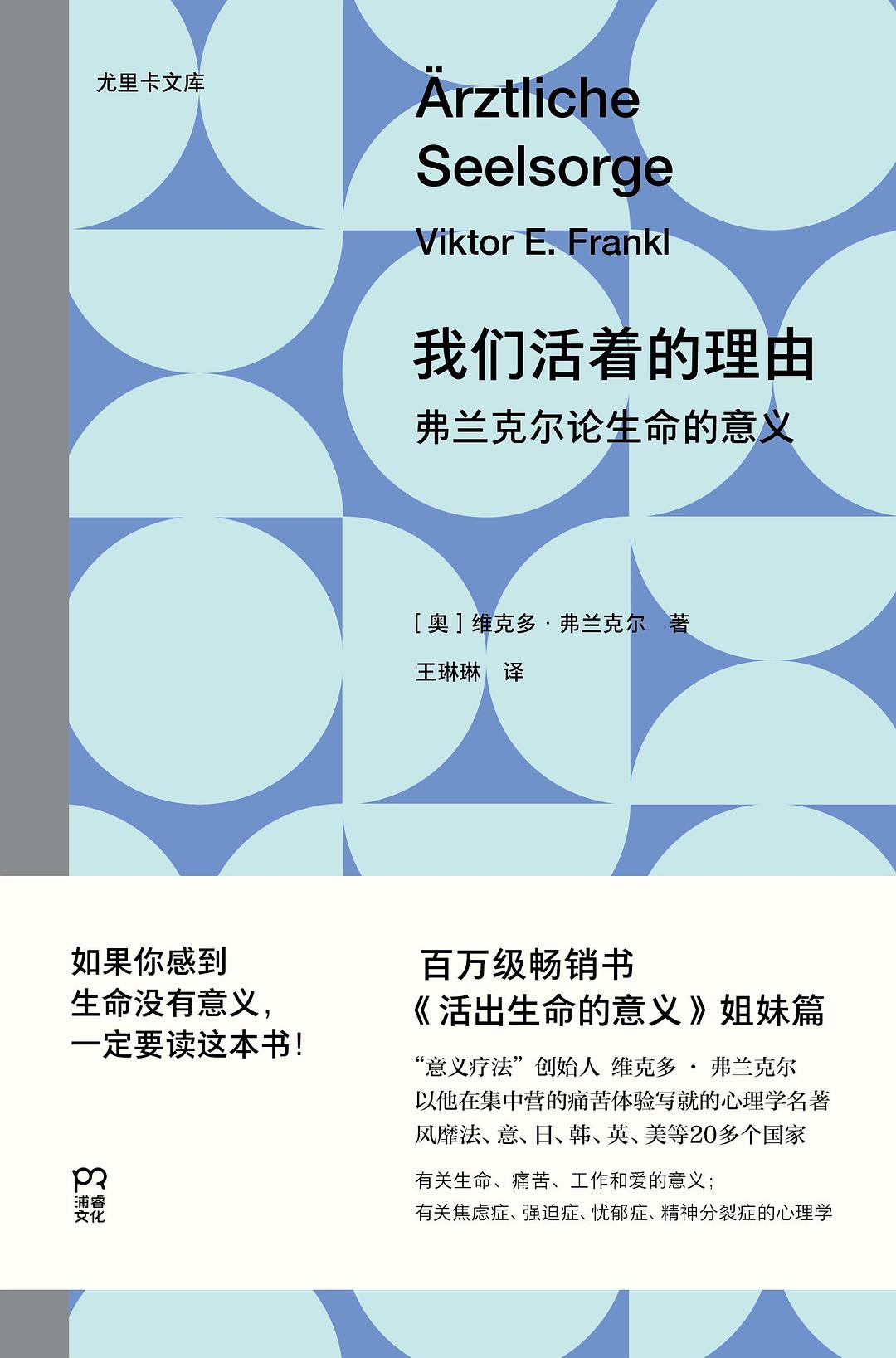
《我们活着的理由:弗兰克尔论生命的意义》书封
工作的意义
前面我们说过,生命的意义不需要被拷问,只需要被回答,通过对生命负责来回答。其答案并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行动给出的。此外,它必须与具体境况和人格相对应,并将这种具体性内化于自身。正确答案将是一个具有实际行动的答案,它作为人类责任的具体空间存在于日常生活的具体性中。
在这个空间里,每一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我们说过,意识的独特性和唯一性非常重要。我们已经知晓,存在主义分析努力朝着责任意识的方向发展的原因,但与此同时,责任意识又首先在具体的个人任务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使命”。如果没有看到存在的独特意义,人就必定会在遭遇困境时松弛倦怠。他就像一个被浓雾困住的登山者,在没有目标的情况下,危及生命的倦怠威胁着他。但当浓雾逐渐散去,避难所在远处若隐若现时,他就会突然感到神清气爽,精力充沛。登山者都熟知“攀登峭壁”时典型的疲劳体验,人往往不知道自己是否走错了路线,也许会陷入错误的岩石地带;直到突然看到通往山顶的路,他知道自己离山顶不远了,手臂就会仿佛又重新充满了力量。
创造性价值及其实现是生命任务的重点,其具体实现领域通常会与职业工作相契合。工作是可以代表个人在团体中的独特性,并让人从中获得意义和价值的领域。然而,这种意义和价值是附加在成绩(为集体做出的成绩)之上的,而不是特定的职业本身。并非只有某种职业才能为一个人提供获得满足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任何职业能让人快乐。如果有人——尤其是那些神经症患者——声称自己换个职业就会获得满足,那么这种说法要么是对职业意义的误解,要么就是自欺欺人。如果无法从工作中获得满足感,那是人自己的错,跟工作无关。职业本身无法使你变得不可替代;它只能给你提供机会。
一位患者抱怨自己的生活毫无意义,因此也根本不想恢复健康;她觉得如果有一份让自己感到满足的工作,例如,如果她是一名医生或护士,或者是一名获得某种科学发现的化学家,那么一切就会变得美好了。此处,重要的是要让这位患者清楚,起决定作用的绝不是一个人所从事的职业,而是她的工作方式;它与具体从事哪种工作无关,而在于构成存在独特性的人格是否在工作中发挥作用,从而使生活变得有意义。
医生这一职业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呢?是什么给他的行为赋予了意义呢?他是按照艺术规则行事,在必要时给这个或那个患者注射或开药吗?单纯的艺术规则中是不包括医学艺术的。医生的工作只是为医生的人格提供了一个通过人格实现职业成就的永久机会。医生只有超越纯粹的职业规则限制,才能开始真正的人格化的、自我满足的工作。让上面的病人如此羡慕的护士工作又是怎样的呢?做护士要煮注射器、端便盆、搬运病人——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工作,但这些工作本身并不能满足人们的内心需求;当护士超出规定义务,开始人格化的工作,如她用自己特有的方式照护重病患者时,她的职业才真正开始赋予生命意义。只要人们正确地理解自己的职业,它就会赋予每个人这样的机会。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无可替代性、独特性和唯一性,对一项工作来说,重要的是谁来做以及如何做,而不是做什么。除此之外,我们需要告诉那些认为在工作中无法获得满足的人,他们最终可以在他们的职业生涯和私人生活中展现他们的独特性和唯一性,正是这些赋予存在意义。例如,作为爱的付出者和被爱的人,作为妻子和母亲,在所有这些关系中,她对于她的丈夫和孩子来说都是无可替代的。
人在工作中可以实现创造性价值并获得独特的自我满足,然而,人与工作之间的自然关系却由于工作环境的原因被强烈扭曲。很多人抱怨,自己每天为老板工作8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必须在流水线上不断重复同样的动作,或者长时间操纵一台机器,总之,他们表现得越是非人性化,越规范,就越显得忠诚可信,越受欢迎。工作仅仅被理解为一种达到目的、赚钱以维持生计的必要手段。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生活仅存在于可以自由支配的业余时间中。然而我们要知道,有些人的工作会使他们非常疲倦,所以他们下班后就在床上倒头大睡,根本无法做自己想做的事;他们只能将业余时间变为休整的时间;这些时间里他们什么都不能做,只能睡觉。在空闲时间中,即使雇主本人也并不总是“自由”的;他也无法逃脱所谓的工作关系的扭曲。在日常生活中,为了赚钱和生计而忘记生活本身的人比比皆是。赚钱已经变成了一种生存目的。一个有钱人可以用他的钱达到很多目的,但他的生活却失去了理由。在这样的人身上,不断赚钱完全掩盖了他的真正生活;除了赚钱,他什么都不知道,他不懂艺术,也不运动,连他玩的游戏也以某种方式与金钱关联在一起,比如赌博游戏,其最终目的还是赢钱。
失业神经症
当工作完全停止,也就是在失业的情况下,工作的意义才会清晰地显现。根据对失业者的心理观察,我们提出了失业神经症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症状的焦点不是抑郁症,而是麻木冷漠。失业者对外界事物变得越来越不感兴趣,缺乏主动性。这种麻木冷漠并非没有危险,它会使这些人无法抓住可能向他们伸出的援助之手。失业者将他的空虚视为一种内在的空虚,一种意识上的空虚。他觉得自己没用,因为他无事可做。因为没有工作,他认为自己的生活没有意义。如同生物学中存在所谓的空白增殖(Vakatwucherungen)一样,心理学中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失业因此成为神经症发展的温床。精神上的闲散会导致“持续的”周日神经症。
麻木冷漠是失业神经症的主要症状,它不仅是心理空虚的表现;在我们看来,每一种神经症症状也都会伴有某种身体表现,很多情况下是营养不良。就像一般的神经症症状一样,有时它也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尤其对于已经患有神经症,只是由于失业而加剧或复发的患者,可以说,失业的事实作为物质进入神经症,作为内容被吸收到神经症中,并受到了“神经症化处理”。在这些情况下,失业是神经症患者为生活中(不仅仅是在职业生涯中)的所有失败开脱的一种受欢迎的方式。失业充当了替罪羊,为“拙劣”的生活背负了所有责任。一个人自己的错误被描述为失业的注定后果。“是的,如果我没有失业,那么一切都会不一样,一切都会很美好。”——然后他们就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事可做,神经质类型的人往往会这样竭力宣称。失业让失业者的生活变成了权宜之计,并诱使他们沉迷于一种临时的生存模式。他们认为别人不应向他们提出任何要求。他们也不向自己提出任何要求。失业的命运似乎免除了他对他人和自己的责任,也免除了他对生活的责任。人生所有的失败都可以归咎于这种命运。显然,认为鞋子里只有一处挤脚,在某种程度上是好事。如果将一切都归咎于某个因素,而这一因素又是一个看似命定的事实,那么这样做的好处是,似乎什么都没有被放弃,你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想象摆脱这一因素后一切就会好起来。
就像所有的神经症症状一样,失业神经症也有结果、表达和途径;我们期望,从最终和决定性的角度来看,它就像任何其他神经症一样被证明是一种存在模式、一种精神立场、一种存在的决定。失业神经症根本不是神经症患者所描绘的注定的命运。失业者不必陷入失业神经症无法自拔。即使失业,人“也可以有另外的活法”,他也能以某种方式决定他是否受制于社会命运的力量。很多例子证明,这种性格并不是由失业决定和塑造的。除了上述的神经症类型之外,还有另一种类型的失业者。他们和失业神经症患者一样,处于困窘不利的经济条件下,不过他们并没有为失业神经症所困扰,他们既不冷漠也不沮丧,有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愉悦。这是什么原因呢?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人往往还有其他形式的工作。例如,这些人可能是某个组织的志愿者、大众教育机构的名誉工作人员、青年俱乐部的无薪雇员;他们经常听讲座和好的音乐,他们广泛地阅读,并与好友交流讨论阅读的内容。他们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组织他们多余的空闲时间,这给他们的意识和生活带来了丰富的内容。像神经症失业者一样,他们的肚子也经常咕咕叫,然而,他们肯定自己的生活,一点儿都不绝望。他们已经明白如何让自己得到满足,并从中获取意义。他们已经意识到人生活的意义并非来自工作,失业的人也不必被迫过毫无意义的生活。对他们来说,生活的意义不再与拥有一份职业工作画等号。真正造成神经症失业者麻木冷漠,最终导致失业神经症的,是认为职业工作是生活的唯一意义的错误观点。错误地将职业和生活等同,必然会让失业者感到自己毫无用处。
所有这些都表明,人们对失业的心理反应根本没那么重要,人的精神自由还有巨大的空间。在我们尝试对失业神经症进行存在主义分析的背景下,很明显,不同的人会以不同的方式塑造相同的失业状况,或者更准确地说,一部分人将他们的心理和性格交给社会命运塑造,而没有神经症的人则反过来塑造社会命运。因此,每个失业的人可以自己决定成为内心坚定乐观的失业者还是冷漠麻木的失业者。
失业神经症并不是失业的直接后果。我们有时甚至看到,失业反而是神经症的后果。不难理解,神经症会对患者的社会命运和经济状况产生影响。在同等条件下,一个保持乐观坚定的失业者会获得比那些冷漠麻木的失业者更好的竞争机会,在申请工作时更容易有好的结果。而失业神经症的反作用不仅是社会性的,而且是性命攸关的。因为精神生活通过其任务特征获得的结构会影响到生物层面。此外,内在结构的突然丧失通常伴随着空虚体验以及器官衰退的现象。精神病学上有典型的心理—生理衰退现象,如人在退休后迅速衰老。动物也有类似的情况,如训练有素的马戏团动物的平均寿命比动物园里同龄的“没有工作”的动物更长。
之所以存在进行心理治疗干预的可能性,其原因在于,失业神经症与失业本身没有根本关联。如果有人对这种解决方式表示不屑,他们可以参考当下失业青年中流行的说法:“我们不要钱,我们要充实的生活。”很明显,狭义的非意义疗法,即所谓的“深度心理”治疗,在这些情况下是没有希望的。相反,这里所指出的道路只存在于存在主义分析之中,它要求失业者直面社会命运,保持内心自由,它唤起患者的责任意识,使他们可以赋予艰难的生活以内容并从中获得意义。
正如我们所见,失业和职业工作都可能被滥用为达到神经症目的的手段。为达到神经症的目的而工作与为达到有意义生活的目的而工作,二者必须区分开来。因为人的尊严禁止他将自己降格成为一种手段、一种单纯劳动过程的手段、一种生产资料。工作能力不是一切,它既不是让生活充满意义的充分理由,也不是必要的理由。一个人可以在有工作的同时过着毫无意义的生活。也可以在没有工作的同时赋予生活意义。一个人主要在特定领域寻求生活的意义,而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生命,这无可厚非。问题是,这种自我限制是否建立在客观的基础之上,或者就神经症而言,是不是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没有必要为了享受而放弃工作,也没有必要为了工作而放弃享受。这种神经症患者的情况正好契合了爱丽丝·吕特肯(Alice Lyttken)的一本名叫《我不来吃晚饭》的医生小说中的一句话:“如果没了爱情,工作就会成为替代品,如果没了工作,爱情就会成为鸦片。”
周日神经症
大量的职业工作并不等同于意义丰富的创造性生活;然而,神经症患者有时会试图通过完全沉浸于工作来逃离生活。一旦忙碌的工作在一定的时间段中暂停下来,存在层面上的内容空虚和意义贫乏就会显现。这个时间段就是——周日!我们经常见到,一些人在周日不得不抛弃手头的工作,他们的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绝望,与此同时,他们自己也被抛弃了,他们没有约会,没有人邀请他们看电影。他们手中没有“爱情”的“鸦片”,或者暂时没有了忙碌——那种可以掩饰内心空虚的忙碌,只有工作狂才需要这样的忙碌。在星期天,当平常的工作节奏放缓时,大城市的日常生活中意义的贫乏就会渐渐显露。我们会有这样一种印象,仿佛那些在生活中没有目标的人总在以最高的速度飞奔,仿佛这样他们就可以对无目的性视而不见。他们试图逃离自己,但无济于事,因为在周日,当平时的忙碌停止时,存在的无目标、无意义、空虚就又会在他们身上显现。
为了克服这种感觉,他们逃进了舞厅。那里有嘈杂的音乐,这让他们省去了勉为其难的“舞厅对话”。他们还省去了思考,全神贯注地投入舞蹈之中。此外,“周日神经症患者”还会逃离到另一项周末活动,也就是体育运动的“庇护所”之中。在那里他们仿佛可以关注地球上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哪个足球俱乐部赢了比赛。两个11人的队伍踢球,成千上万的人观看。在拳击运动中,只有两个人是活跃的,但是他们的竞争非常激烈,这可以满足不活跃的偷窥观众的施虐欲。我所说的这些不是反对健康的体育运动,只是批判性地询问,体育运动有哪些内在价值。让我们以登山者的运动理念为例,登山首先需要积极参与,被动地观看在这里是行不通的。这里比拼的是真正的能力,与身体素质密切相关,例如,在某些危及生命的情况下,登山者不得不落到最后;在心理关系中,“素质”再次被推至前台,无论登山者有什么心理弱点,比如焦虑或恐高,他都必须学着克服。应该指出的是,登山者不是(出于自己的意志)“寻找”危险,而是如欧文·施特劳斯所指出的,“尝试”危险。竞争在很多运动中往往导致对记录的追逐,在登山运动中却被转化为“挑战自我”的一种高质量形式。攀爬团队的体验最终代表了另一个积极的、社会性的时刻。
即使对记录的病态追逐也证实了人类的特点,因为这些记录也是展示人类追求其唯一性和独特性的形式。这同样适用于其他的大众心理学现象,例如流行时尚:人们不惜一切代价想从时尚中获得独特性;在这里,唯一性和独特性仅限于最外在的东西。
不仅是运动,艺术也会在神经症层面被滥用。虽然真正的艺术或艺术生活丰富了人的内心,并将他们引向最本己的可能性,但在神经症层面被滥用的“艺术”只会使人偏离自我。它更多的只是一种令人迷醉和眩晕的情况。例如,一个想要逃离存在的真空的人可能会去看一本扣人心弦的犯罪小说。他最终会在紧张中寻求解决方案——那些摆脱乏味的消极欲望被叔本华误认为是唯一可能的欲望。前面已经提到,我们并不是为了摆脱乏味、紧张、斗争而去体验消极欲望;实际上,我们并不是为了不断获得新的感觉而进行生命斗争,生命的斗争更多是带有意向性的,并在其中获得一些意义。
对于寻求刺激的人来说,最大的轰动事件莫过于死亡,不管是在“艺术”还是在现实中。市侩的报纸读者想要在早餐桌前读到不幸和死亡。然而大量的不幸和死亡报道也不能使他满足,匿名的大众对他来说太过于抽象,所以,这个人同时可能会产生去电影院看一场匪徒电影的需求。就像其他成瘾者一样:追逐耸人听闻的事件成瘾的人需要紧张刺激,而紧张刺激又会产生新的、更强烈的对刺激的渴望,从而导致刺激剂量的不断增加。这其实形成了一种对比的效果,好像死的总是别人。这种类型的人想要逃离的是对他来说最为灰暗的事实,即他自己也终有一死的事实,这让他无法承受存在的真空。必死无疑意味着一种基于愧疚的恐惧。死亡是生命的结束,它只能让那些没有填满自己生命的人感到恐惧。只有这些人无法正视死亡。他并没有意识到生命有限,也没有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自我,而是逃到了一种赦免的妄想之中,就像那些被判死刑的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开始相信自己还有可能被赦免。这种类型的人逃到了一种认为自己什么都不会发生,死亡和灾难只会降临到别人头上的妄想之中。
神经症患者往往会逃到小说世界中,逃到他们心中“主人公”的世界里。追逐纪录的运动员至少还想要在自己的功劳簿上休息一下,但这种类型的小说读者只想要别人满足自己的需求,即使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然而,在生活中,从来不会有任何形式的功劳簿可以休息,也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情;生命一再地向我们提出新的问题,让我们永远无法安宁。只有自我麻醉,才能让我们对那些永恒的刺痛不再敏感,生活以此不断向我们提出新的要求,并拷问我们的良知。谁停下来了,谁就会被超越;谁自我满足了,谁就会失去自己。所以我们不应满足于我们创造或者体验过的一切;每一个时刻都需要新的行动,都会产生新的体验的可能。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