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公元1014年:杨家将传说到底有几分真?
楔子
您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14年,大宋的大中祥符七年,大辽的开泰三年。
日子过得可真快啊,大中祥符这个年号一共用了9年,这都7年过去了。“大中祥符”,一看到这个年号,又是“祥瑞”又是“神符”的,就容易想起那个年头的那些神神叨叨的事儿。就在这一年,玉清昭应宫终于落成了;就在这一年,真宗皇帝去亳州祭祀老子也终于成行了。全国上下还是那个接着奏乐接着舞的氛围。
如果抛开这些祭祀活动不谈,今年大宋朝堂上最重要的事情,应该是一个人事上的变化。
上一期,我们在讲1013年的时候,说到朝廷提拔了两个枢密使,就是管军事事务的首长,王钦若和陈尧叟。但是,这两个人位子都没有坐热,今年就又被罢了官。
罢官的原因,说起来也是一地鸡毛。
枢密使所在的枢密院,不是管军事事务的吗?话说有边疆的武将立了一些功劳,就报到了枢密院,那怎么论功行赏呢?这就出现了意见分歧。王钦若和陈尧叟,就是刚被提拔的这两位,文官出身的人,说这种小功劳意思意思就行了。但这个时候枢密院还有一个副长官,叫马知节,武人出身,他说,别介啊,国家多少年不打仗了,边关没有立功的人了。这次可以赏得重一点,对其他武将也是个激励嘛。这个意见就统一不了,事情就拖下来了。
时间拖久了,马知节就不干了,当着真宗皇帝的面,和王钦若大吵一架。马知节这种大大咧咧的武人对王钦若这种机灵鬼儿,本来就各种看不上,这次也是借题发挥,陈芝麻烂谷子地揭了王钦若很多短。王钦若可能也是心虚,说行行行,不就是奖赏一些武将吗?给他们都破格升官行了吧?
没想到,王钦若这下又把真宗皇帝给惹了。为啥?因为你破格提拔武将,不向皇帝汇报,自己就做主了,没走程序嘛。真宗就跟宰相说了,王钦若他这是要干嘛呀?开始,不给人提拔,现在又擅自破格提拔。哟,原来朝廷用人,都是你们说了算呗!我身边的人要是都这样的话,我这个皇帝把手绑起来,啥也别管得了。你听听,这不仅是批评啊,这是话中带气了啊。
皇帝生气,还不止这一点,回头再一看那个跟王钦若吵架的马知节:你也不是什么好人,大事小事,动不动就吵。你就说你,朝廷里的官你是不是都骂遍了?真是宽以待己,严以律人啊。走,你们都给我走人,走了我这儿清净。
就这样,枢密院这会儿正副职加起来就这么三个领导,现在全部被撤了。那换上来的是谁呢?老熟人,寇准。不过这次寇准回开封没多长时间,也就十个月吧,很快又被撵出去了。关于寇准在这个阶段的沉浮,我们下一期再说。
我自己看到这段史料的时候,心里是有一声叹息的:这位真宗皇帝,确实是有点力不从心了。他继位已经17年了,用来用去,就是这几个大臣,他有很多不满意,但是也没办法:有的是处出了真感情,比如王旦;有的是用出了依赖性,比如王钦若、丁谓;有的是自己不喜欢,但是朝野声望挺高,不用还不行,比如寇准。
你就想一个现在的公司嘛,如果重要岗位老换新人、年轻人上来干,那通常是比较有活力的时候;如果中层干部很多年就是那几个人转来转去,高层对他们也谈不上多满意,但是好歹业务熟悉,也有些老感情在,就这么着吧,这时候的公司通常就进入了活力衰退的阶段。
再来看看真宗用的这一拨大臣,其实也是在日渐凋零啊。宰相王旦的生命,还剩下三年时间,他在1017年去世;刚才说到的马知节,还剩五年时间,他在1019年去世;这个阶段还有一个宰相向敏中,1020年去世,还有六年时间。后面这几年,真宗皇帝要一个个地送别他朝中的这些老臣。
回到这一年,1014年,真宗还送别了一个人,这个人比我们刚才讲到的所有人都有名,甚至比真宗皇帝本人还要有名。谁啊?杨六郎杨延昭,杨家将中杨老令公最有名的那个儿子,这一年也去世了。享年57岁。
杨六郎杨延昭原本叫杨延朗。你要是看过我们1009年的那期节目,就会知道真宗皇帝为他们老赵家发明了一个祖宗,叫赵玄朗,又是神仙,又是皇帝的祖宗,来头这么大,所以这“朗”字就要避讳了,杨延朗只好改叫“杨延昭”。
杨延昭是死在自己的岗位上的,当时是高阳关的副司令。高阳关在哪里?就是当时宋辽对峙的前线。民间说的杨六郎镇守三关,也就在这一带。现在虽然双方不打仗了,但高阳关毕竟还是大宋在军事上最重要的区域。有杨六郎这样的名将在,还是让人安心。所以杨六郎这一走,将星陨落,对当地的震动很大。史书上记载,杨延昭出殡的时候,皇帝派身边的宦官来料理丧事,而过来送殡的河北人,远远地望着他的棺材,纷纷掉眼泪。
那这期节目,咱们就聊聊杨六郎和杨家将。我们把重点放在一个有趣的问题上:真实历史中的杨六郎和杨家将,和传说中的杨六郎和杨家将有什么不同?又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呢?
好,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一起穿越回101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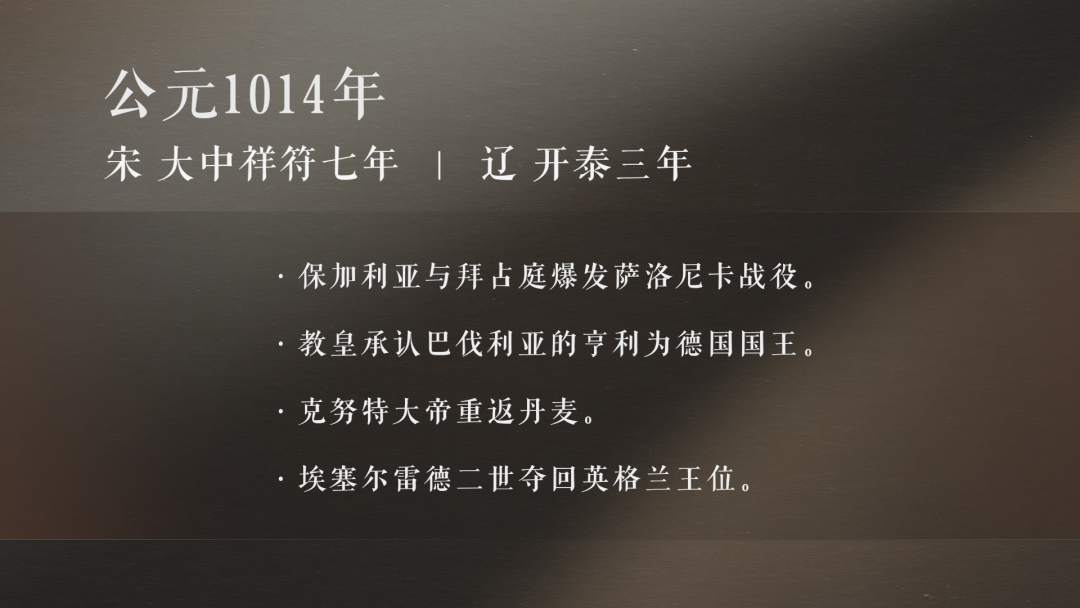
两种“杨家将”
我们来简单说一下正史中记载的杨家将。大概是三代人的事。
第一代,杨业,也就是杨老令公,原来是北汉的名将,号称“杨无敌”,后来投降了宋朝,是山西北部的雁门关一带的守将,屡立战功。后来在陈家谷之战中被辽兵俘虏,绝食三天而死。那这个“杨无敌”的称号是不是名实相符呢?北大历史系党宝海老师提供了一个侧面的证据:在《辽史》里面,很多个辽朝大将的传记里都提到了这件事,“俘虏杨业,这里面可有我哈!”。这说明啥?说明在当时的大辽,能俘虏杨业是一件值得夸耀的大功劳。那你说杨业厉害不厉害?

第二代,就是杨业的儿子杨延昭,民间传说管他叫杨六郎。他先是跟着父亲杨业在山西守关,然后调到河北。他在河北的这一段,正好是宋辽之间的博弈最精彩的一段。打仗的时候,有他;订立澶渊之盟的时候,有他;和平之后镇守边关的人,还有他。
第三代,是杨文广。杨延昭的儿子,毕竟是名将之后,还算被朝廷重用,在西北和西南都打过仗。但和他的祖父、父亲相比,没有什么突出的战功。
统计一下,在《宋史》里面,关于杨家将的介绍,也就2500字吧。这就是正史里面关于杨家将全部的资料。就这么点儿。
传说和史料对得上的,有那么一件事,我们1004年那一期还提到过,就是把杨六郎把井水泼到城墙上,冬天冷嘛,等冰凝固之后,辽兵就爬不上城墙了。这件事小时候听评书,印象很深,这事还真见于史料记载。
至于其他的,得老实说,基本上都是编的。
有一类传说,情节完全是虚构。比如说比如说金沙滩一战,杨家第二代,从大郎到八郎精忠报国,大郎射死辽主,自己被刺杀;二郎战死;三郎马踏如泥;四郎、五郎下落不明;七郎搬兵求救,被潘仁美射死,八郎落入番邦招了驸马,只剩下了杨六郎杨延昭护住老父亲……其实,这场大战根本没发生过。还有,评书里说得特别悲壮,催人泪下的杨老令公杨老英雄碰死在李陵碑上,对不住,也是编的。

还有一类虚构,人物,历史上是真有,但是在传说里关系是错乱的。比如,寇准和杨家将,在真实历史中其实没什么交集,但是在民间传说中,寇准那可是杨家在朝廷里的大靠山;再比如,潘美,在杨家将传说里叫“潘仁美”,是害死杨七郎和杨业的元凶。但在真实历史上,他的确跟杨业的死脱不了干系。但也就是个领导责任,肯定不是有意加害。
还有一类虚构,人物算是有个原型的影子,但和史料相差甚远。比如,杨业的夫人佘老太君,就是一百岁还能挂帅上阵那位老太太,有人说是西北武将世家折家的女儿,嫁给了杨业。但是说实话,宋代正史、野史上,都没有这个记载。这个说法出得非常晚。可信度非常低。

最后,民间传说里好多特别有名的人物,完全是子虚乌有。比如,杨宗保、穆桂英两口子。在传说中,他们是杨延昭的儿子儿媳,杨文广的父母。其实,这是横空插入的一代人,完全不存在。所以,什么穆桂英比武招亲,什么杨门女将,什么十二寡妇征西,什么八姐九妹,什么烧火丫头杨排风,所有这些人物,都是后来民间文学的创造了。如果你喜欢看京剧的话,那些著名的杨家将剧目,什么《金沙滩》《李陵碑》《清官册》《辕门斩子》《穆桂英挂帅》《状元媒》《四郎探母》,也都是虚构,不是真实历史。这些故事,在宋代的时候都还没影儿,到了元代杂剧里面,才开始陆续出现,最后在明代进入了杨家将演义小说,印成了书。
写到正史里的杨家将,虽然是白纸黑字,其实读过的人并不多。但民间的杨家将,我们从小就听评书、看京剧,就算是年轻的朋友,也不会完全没听过杨家将,电子游戏还有杨家将主题呢。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民间的杨家将,会这么添油加醋地编故事?为什么大家不按正史里记的事实来说?为什么编出来的故事,能多出那么多人、那么多的事?
这期节目,借着杨家将这个线索,来聊聊一个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有点陌生的话题——口语文化。
什么是口语文化?想象一下,如果这个世界上完全没有文字,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只能口口相传,那人类的文化面貌会是什么样?
你可能会觉得,那文化传播和留存就非常困难了。即使有,可能也只是非常短小零碎的一些片段。没有文字的帮助,大量的信息不可能被精确地记录,也不可能被远距离和长时间地传播啊。就像今天的很多人,没带电脑,没有PPT,连开会发言都不会讲。
但是不好意思,这个印象是错的。
口语时代,不仅有文化传播,而且规模非常大,传播力非常强。比如各个民族的史诗。世界文化史上有所谓的“五大史诗”一说,就是巴比伦史诗《吉尔加美什》、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篇幅都巨大。
其中,最著名的两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规模已经很大了,分别都有1万多行。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更长,2.4万多节,《摩诃婆罗多》更大,10万多节。但是所有这些加起来都不如我们藏族的《格萨尔王传》长,格萨尔王传现在整理出来的,就有100多万行。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长。中国还有另外两部超大型的史诗,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也是动不动就十几二十万行。
你可能觉得不可思议,这么长的诗,记得住,还能够几天几夜地这么一口气唱,真的可能吗?怎么做到的呢?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见过的解释,有这么几种。
第一种解释是:他们不是死记硬背的,都是有套路的。你看起来是那么大一篇,其实,里面有很多预制件,很多套话、程式、场景、主题,都是反复重复着用的。所以,有人用一个词来形容这种史诗的创作过程,叫“编织”。对,其实就是那么些套路,通过一通眼花缭乱的穿插、组合、拼装之后,变化就多起来了,编多长都不是事儿,记起来也没有那么难。在上个世纪,这是西方研究荷马史的一个重大理论突破,还有一个名词,叫“帕里-诺德理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这在我们听中国评书长大的人来说,这个理论特别好理解。评书听多了之后,你就明白,其实就那么些套路。
比如说,刘兰芳讲的评书《杨家将》,讲到杨宗保第一次见穆桂英,是这么说的:
宗保一看眼前女将:全身披挂,脑后插着雉鸡翎,凤凰裙双遮马面,牛皮靴牢踏在镫,只长得桃花粉面、眉清目秀、齿白唇红,眼神炯炯中透出杀气,胯下桃红战马,马脖子上挂着十三个银铃,“哗㘄㘄”直响,清脆动听,手中一口绣绒大刀,刀上拴着红缨,飞鱼袋盛镇天弓,走兽壶装穿云箭;斜挎百宝囊,不知还装有何物。
这一段要不要背?当然要,这叫贯口。但是背熟很多段这样的贯口之后,再去描写一位女将,不管是哪部书,也不管是谁,肯定是张口就来。这就是所谓的套话编织。
所以你看,中国的传统评书演员,很多都不识字啊。比如评书大师单田芳的父亲、伯父、叔父,都是当时的评书名家,但是都不识字。他的几个师姐,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是怎么样?不耽误一辈子会讲好多部大书,这背后靠的就是这种隐秘的技术,用套路编织故事和套话编织修辞的技术。
这是一种解释。其实还有一种解释,我觉得就更加深入了。就是口语文化时代的人,和我们这些文字文化下长大的人,其实大不一样。他们的很多能力,比如大段背诵的能力,我们是没有的。
这个地方我要说一个感慨。我们这代人是从文字文化过渡到电子文化的一代人,现在我们的记诵能力,已经差得很远很远了。我小时候,就见过一些老教授,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就真能说,到我的书架上第几排第几行什么书第几页,那里有答案。所以,钱钟书先生所谓“照相机”式的记忆力,不是什么传奇,那代人中的高手真就有这样的能力。在用上智能手机之前,谁身边没有几个张嘴就能背出几十上百个电话号码的人呢?
就在我们现在说的宋代,李清照和他的丈夫赵明诚,吃完饭之后就开始煮上茶,两口子玩游戏:你说哪件事在哪本书哪一卷第几页第几行,说对了的人就先喝茶。玩得不亦乐乎的时候,两个人经常举杯大笑,把茶都泼在衣服上。不是有那么一句诗吗?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这个典故听起来不过是两口子的闺房之乐,但是你跳出来一看:太惊人了,这是何等可怕的、碾压式的背诵能力啊。
那你想,这还是文字文化下的人,在没有文字的时代呢,人更依赖记忆力。在远古的时代,有些人具备可怕的记诵能力,有啥不可想象的呢?
我这不是在神化古人哈。这是对人类潜能的赞叹。只要有需要,在长期的训练下,人的某一项能力经常可以达到惊人的程度。
比如我曾经在霍布斯鲍姆这本《革命的年代》里看到一段话。他说,工业革命之前,欧洲人普遍非常矮,招来当兵的男人也就是1.5米左右的身高。营养不良嘛。但是千万不要小看这些人的体能,法国大革命中的那些军人,骨瘦如柴、发育不良,但是可以全部武装,每天负重行军50公里,连续一周,而且是家常便饭。这种体能,今天可能要特种兵才能做到。
别看我们今天营养好,人高马大,但是我们脱离体力劳动太久了,这种体能,对我们来说就是神话。同样道理啊,我们距离需要大段大段背诵的时代也太久了,所以,远古时代人的背诵能力,对我们来说,也是神话。充分理解人的可塑性、人的巨大潜能,可以打消我们这代人的傲慢。
这说了半天,其实只解释了一件事:不识字的评书艺人,为什么能进行那么长的口头创作,能把那么一点点的关于杨家将的事实,变成那么长的虚构故事。
那下面就还要解释一个事,这些口头文学的创作,为什么要胡编乱造,为什么会不在意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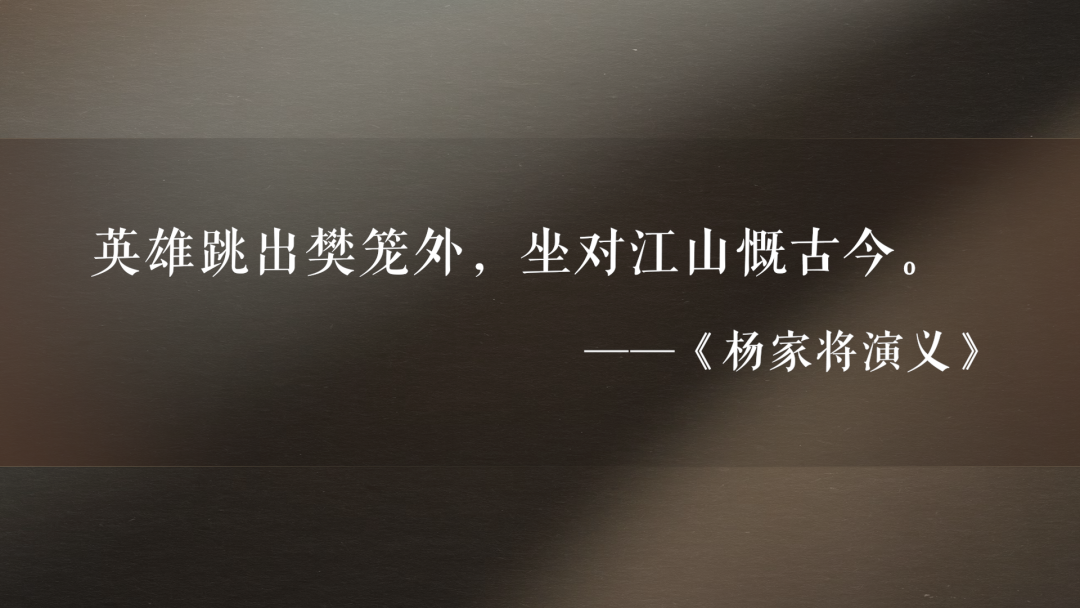
上口语的近处和文字的远方
为什么口语文化中的人,会倾向于胡编乱造?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问错了。不是他们在有意造假,而是口语文化下的人的真假观和我们不一样。
多年前,我看过一本讲藏区的书。作者当时在藏区的黄河上漂流,有一次在一户藏民家里喝茶,主人就讲起一件刚刚发生的事:一个黄河考察队的船刚刚在周围的一个湖上沉没,说这船在湖上飞速行驶,湖底的山涧把那条船像鱼一样从中间剖开,船像箭一样沉了下去,讲得充满了细节,是绘声绘色。但是没过几个小时,作者就遇到了那只考察队,他们的船原来只是被一个桥墩撞翻了,有惊无险,没有任何伤亡。作者就感慨,这么近的距离,这么短的时间,一个消息就能变形到这个程度,可见口语文化的想象力。那户藏民的主人肯定不是有意说谎,这就是口语文化的传统,一件事在每个人嘴里过一遍的时候,都要叠加自己的想象。

你要是观察孩子,他们其实就是这样。孩子有时候并不是撒谎,也并不是好骗,只是在他们的世界里,真实和虚构的边界没有那么清晰而已。有一次,我在节目里说起圣诞老人,我看有用户评论说,“哎呀,刚觉得你说得挺好,就把孩子叫过来看。结果正好听到你说圣诞老人不存在。罗振宇啊,你怎么把圣诞老人出卖了呢?”
这位朋友你放心,早就有研究发现,孩子对圣诞老人是真实是虚构,其实心里是非常有数的。我就观察我家的俩娃,她们小时候在一起玩,经常就说,我们假装这样吧,我们假装那样吧。对,孩子就是活在假装和真实不太分的世界里,乐此不疲。如果你告诉他们圣诞老人是假的,他们的感受并不是受骗了,而是你们大人为什么要强行把真实和虚构分开?这种撕裂感,把他们搞得很懵而已。
口语文化这种真实和虚构不分的状态,到了文字文化的时代,就要变化了:杂乱的、混沌的思绪,落实成了白纸黑字;白纸黑字再统一成了各种定本,于是真假、是非就判然分别开了。
我们这代人,打小读书识字、上学明理,整个心智模式都是被文字文化塑造出来的。文字文化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让人的世界里有了“确定性”这个东西。说白了,文字文化的世界里,有越来越多的标准答案。
想想我们的成长过程吧:最开始,我们只是会说话,就是口语文化里的人。只要生理正常的孩子,没有不会说话的。这个学习过程虽然很复杂,但是好像并没有多艰难。我说话只要周围的人听得懂就行,没有什么绝对的是非对错。但是一旦进学校开始学习文字,我们就一步进入了文字文化的世界,一大堆难题就扑面而来了。因为文字是有各种标准答案的。字形、笔顺、读音,哪个不对都不行,是非、真假,就变成了大问题。
而且你发现没有,这个是非真假的标准,不是以我身边的人校准的,是由远方的,我根本不认识的人定的。
举个例子,有一期《文明之旅》的节目,我说秦始皇的“阿房宫”,我读成了“fáng”,很多用户在评论区纠正,说应该念“páng”。其实,我这么读,不是自己信口开河,是认真查过《新华字典》的。但跟我较真的用户,说的也有道理,语文课本里是这么标的。但不管怎样,我们各自依据的这个标准,不是身边的人,而是远方的、我们根本不认识的人,那些教育部门的人、编教材的专家、编词典的权威。有时候,标准还会变动,那没办法,我们也得跟着变。
类似的字还有很多。一骑红尘妃子笑,现在要读qí;说客,现在要读shuō;确凿,现在要读záo。我小时候辛辛苦苦学的、胆战心惊怕写错的读音知识,现在都不对了。那没办法,只能按现在正确的,也就是远方的人给我制定的标准来。
生活在文字文化里的人就是这样:我们的生活,是由一系列的标准、是非、规则、定本、答案来决定的。而这些标准、是非、规则、定本和答案,又是由远方的、我不认识的人来制定的。我们对此见怪不怪,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但是,你现在可以想象一下,我生活在一个还没有文字的社会,我的世界什么样?
作为一个口语文化中的人,我可能从生到死也没怎么离开过我的家乡,我和熟人一起生活在“附近”。我的整个世界就在此地,我所有的成败利钝、吉凶祸福,也都在周边,我的一举一动,都是做给附近的人看的。远方的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更别提,由远方的、不认识的人来给我制订是非标准,这就更奇怪了。
你看,这就是口语文化和文字文化根本性的不同。借用米兰·昆德拉的那本小说的名字,文字文化中的人,是“生活在别处”,而口语文明中的人,是“生活在附近”。
理解了这种远处和近处的差别,我们再接着追问:为什么口语文化中的人,会不在意事实?
其中一个答案是:他们在意的是眼前人,是身边事。他们不会在意时间和空间上都很遥远的文字里的历史。
想象一个场景好了: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一天晚上村子里来了一个盲人吟游诗人,据说名字叫荷马,村长请他在这里住上一个月,每天晚上给大家讲唱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故事。那我期待的是什么?是当天晚上的精彩啊,是他的临场发挥和添油加醋啊,最好有些情节,别的村子里的人都没有听过才好。

可是再过几百年,希腊出现了文字,有人把《荷马史诗》记下来了,这就麻烦了:出现了定本。村里再来什么吟游诗人,不管他讲什么,大家脑子里都有一根弦:他说得对吗?跟定本上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是不是他没本事、记错了啊?这个念头一起来,那个活泼泼的,每天都在生长的,每讲一遍都不太一样的《荷马史诗》还在吗?不,《荷马史诗》就死了啊。
杨家将故事的流传,也是一样的道理。一个说书先生,民间艺人,他在意的是什么?是自己说的和历史记载是不是一样吗?不会啊。他又不认识字。他又不发表论文。他的作品又不需要对五湖四海和千秋万代负责。他需要负责的,需要在意的,就是今天这个书场:有没有座儿,能挣多少钱,能讲多少场,今天听的人喜不喜欢,能不能给他扬名,明天来的人是不是更多?你看,他只是生活在附近。
就像我刚才把杨老令公的儿子,从大郎数到八郎,可能有的人就要给我挑错了,落入番邦招为驸马的,明明是杨四郎啊,你怎么说成八郎了?没错,京剧里有《四郎探母》,说的就是落入番邦的杨四郎。但在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里,比武招亲娶了辽国三公主的,却是八郎杨延顺。你看,这恰恰说明了口语文化的特点,就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过去我们提到口语文化,总是觉得弱点很明显,不靠谱,话从口出,随风飘散,它只能照顾到眼前的人,既管不了远方,也传不到远方。今天这期节目,我想提醒你换个视角,口语文化,这种“生活在附近”,有没有什么被我们忽略的好处和强项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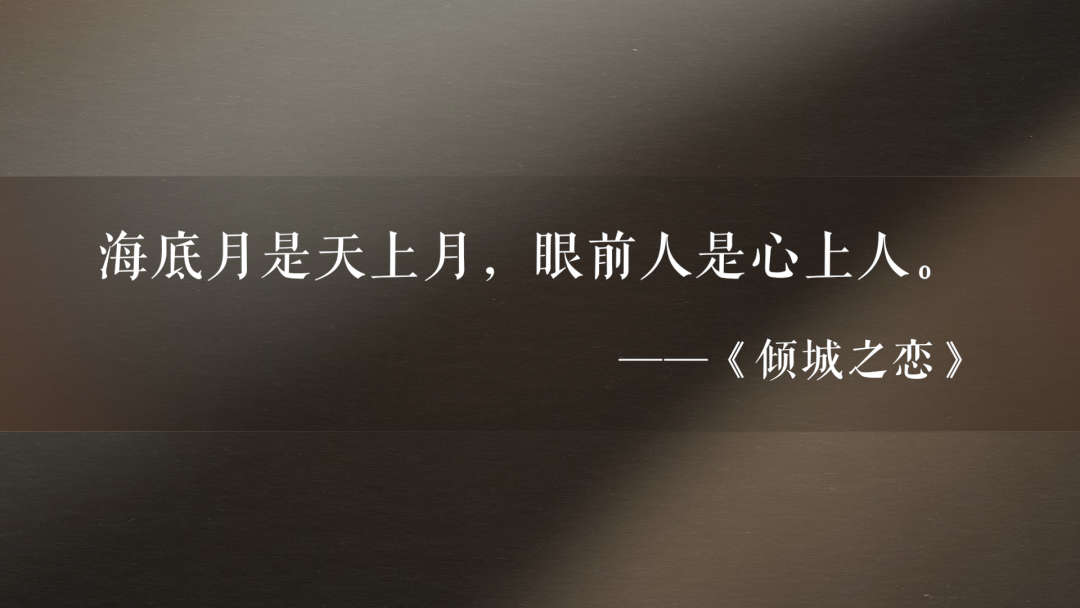
即兴现场与游戏精神
口语文化的好处,最简单的,就是给即兴发挥,也就是人类蓬勃的创造力留出空间。文字文化,白纸黑字印在那里,就动不了了,但口语文化不一样。
举个例子:话说晚清的时候有一个著名说书人,何云飞。在苏州的评话界,水浒传讲得最好的就是他。他师父能力不太行,讲一次水浒,最多只能讲二十七天。但他有个外号,叫做“何一年”,因为他一部水浒,一年都讲不完,而且真的这辈子都没把水浒全套讲完过。有个传闻,说他有一次在苏州的书场,讲水浒传的“石秀跳楼劫法场”,讲到石秀的左腿刚跨出窗户,有个客人突然叫,“你今天能不能让石秀跳下酒楼去!”何云飞问为啥,客人说他明天到上海去有事,要五天才能回来,这个关子错过了就听不着了。何云飞笑了,说你去吧,包你第六天来听,他仍旧在,没跳下去。嘿,结果在第六天,何云飞就是等着他回来了,才让这石秀跳下去。
所以你看,评书艺人不是在有意造假,他是随时关照自己的客人,那才是他的衣食父母。讲的时间是长是短?即兴发挥是多是少?那要看现场客人的反应。这是一个在场者共享的游戏。如果那天我在何云飞的书场里,我就倒要看看,你怎么一个石秀跳楼能跳上五天,我知道你在等那个客人,我愿意成全你这个善意,我也愿意看你显自己的能耐,我也愿意参与和见证到这段佳话里来。这才是口语文化里的人的心态。
我从旧书市场上淘到过一套上个世纪80年代出版的扬州评话《武松》,王少堂先生讲的。原来,扬州评话里面,讲武松,叫“武十回”,只能讲二十天,但是王少堂这辈子,不断地抻长,一直抻长到能讲七十五天。原来《水浒传》里的这段故事也就8万多字,但是这次王少堂讲,光录音稿就有一百一十万字,出版的这个版本,删节了很多,还有八十多万字,相当《水浒》原书十倍。这就是王少堂老先生的本事啊。
而且,这个本子,因为王少堂知道是要整理文字用的,很多本事都没用上。比如,王少堂有一次讲武松打虎,说到武松骑在老虎背上举起拳头准备打,中间穿插了许多噱头,讲了一个星期,武松的拳头还没有打下来。这种段子,想必是即兴发挥,在这次整理的版本中肯定就看不到了。一旦写成定本,要考虑的维度就太多了。评书现场的那些鲜活的创作,就只能忍痛舍弃。

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有一本书不得不看,郭宝昌先生写的《了不起的游戏》,讲京剧艺术的。这个书名起得特别好,不要觉得京剧是表演,是台上人演给台下人的戏,不,京剧是剧场里所有人都参与的一场游戏。
就拿“叫好”这事来说吧。听交响乐、看芭蕾舞,都不带叫好的,演出再精彩,中途鼓掌都不礼貌。芭蕾舞演员一举腿,你喊,好腿!那估计保安就要请你出去了。但是京剧就不一样,观众叫好,不是干扰,那是一场成功演出的一部分。

比如,我一个戏迷去听《四郎探母》,我是为了看那个情节吗?那根本不重要。我是参与今天这场游戏的人啊,我水平高的话,我当然知道我要听什么看什么。比如四郎探母,整出戏,也我就是要听那句“叫小番”的噶调是不是唱得上去。你唱上去了,我恰到好处正好在那个点儿上喊了一句好,哎,你也是行家,我也是行家,那才叫双赢。
京剧历史上有这么个事,北京的名角谭富英到天津唱这出《四郎探母》,本来他嗓子特别亮,唱“叫小番”不在话下,但是这次见了鬼了,就是唱不上去,第一次没唱上去,第二次,还是没唱上去。奇怪的是,票价一直涨,第三场涨到了一张票三块三。你想,那个时代,三块三大洋一张票,那是多贵啊。天津人说了,“三块三,我就要听你这叫小番”。结果呢,第三次还是没唱上去。据说谭富英再也不敢去天津演出。
那你说,买三块三票的人觉得亏了吗?按今天的话来说,产品交付不到位,演砸了,肯定亏了啊。但是京剧观众不会这么想。还是那个道理:这是剧场里所有人的游戏。天津人花三块三,来了这个剧场,他要参与的就是这段佳话,不管谭富英唱没唱得上去,他是赞叹,还是失望,他都是这个传奇故事的见证人。这才是他要的。
今天我们是从杨家将的故事说起。我试图给你看两种文化模式:
一种是我们熟悉的书面文化、文字文化。在这个世界里,确定性非常强,人类可以踩着前人的确定的脚印不断地往上走,不断地发起大规模的合作。每个人都可以和远方的人连接,用远方的标准、规则来校准当下的自己。
另一种呢,是我们已经有点隔膜的口语文化。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是那么鲜活,那么热火朝天。每个人都生活在附近。他们一手接过别人的传说,加进自己的想象和理解,然后再传给别人。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应对眼前的挑战,也达成和周边世界的共识。他们这样创造着自己的英雄,然后把英雄当做镜子,在里面看见自己的样子。
那么,哪种文化好呢?这就要说到历史上的一个名场面了。
话说王阳明的晚年,聚众讲学。很多学生听了课之后,就想用笔记下来。王阳明赶紧拦着,说,别记录。我给你们讲课,有点像医生用药,那都是因病施治啊,根据病人的情况不同,用药也不同。如果医生遇到什么病,都是同一副药,那不就是杀人吗?我现在给你们讲课,就是希望你们能有所改变,如果你记下来,变成了文字,将来流传出去,不管什么人,都按照这一套去做,这不是误人误己吗?这不是罪过了吗?
但是,王阳明还是没有拦住。他想守住的活泼的、临场的、有对象感的口语文化,最终还是被记录了下来,变成了有定本的、不再变化的文字文化。这就是著名的《传习录》。你看,不记录下来吧,这么宝贵的东西就随风而散了;记录下来吧,每一句话都是对在场的的人说的,听在不在场的人的耳朵里,多少都会发生曲解。
从这个故事里,你可以品出口语文化和文字文化各自的优劣,以及王阳明当年在面对选择时候的两难啊。
我们在公元1014年,借着杨延昭去世的这个话头,讲杨家将在口语和文字两种文化中的不同流传,是想拨开帘幕,让你看到口语文化的一角。口语文化,是不是和我们过去理解的不太一样?它不是低级的、临时的、易碎的。它其实是活泼的、率真的、有生命力的。
讲到这里,我自己也是心念一动:《文明之旅》这个节目的追求吗?把那些看起来已经落伍的、过时的、成为陈迹的文化,再翻出来,不是为了凭吊古人,更不是为了让身在现代文明中的人有优越感,而是让我们看到人类文明的多种样式和无限可能。凡是人类历史出现过的东西,就永远不会再消失了。它们是祖先倒好放在那里的一杯美酒,它们是跳跃在永恒时光里的一丛火焰,它们是在人类未来命运里必然会再次发芽的一枚种子。
看到它们的价值,然后随时准备享用。
咱们1015年,再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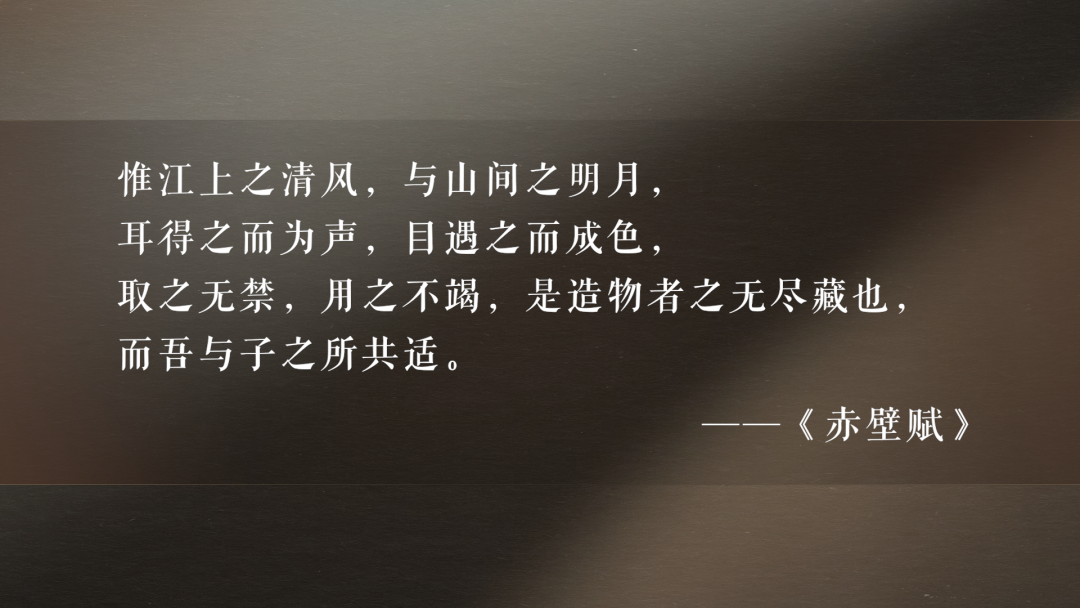
参考文献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宋)赵明诚撰:《宋本金石录》,中华书局,1991年。
(元)脱脱等撰:《辽史》,中华书局,1974年。
(明)王守仁撰:《传习录》,中华书局,2021年。
刘兰芳:《杨家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
陈小林:《杨家将故事考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
纪德君:《民间说唱与古代小说交叉互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
郭宝昌、陶庆梅:《了不起的游戏:京剧究竟好在哪儿》,三联书店,2021年。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中信出版社,2014年。
周良:《历史及传记演员口述》,古吴轩出版社,2011年。
连阔如:《江湖丛谈》,中华书局,2011年。
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王少堂:《武松:扬州评话水浒》,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年。
蔡连卫:《杨家将故事在南宋民间的接受与传播》,《明清小说研究》2022年第2期。
蔡连卫:《从史书看杨家将事迹在南宋的传播》,《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石麟:《杨家将故事的流变及其文化积淀》,《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1期。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