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卡夫卡逝世百年|在不确定的时空中寻找存在的意义
清晨,街道干净而空旷,我走向火车站。我把手表与塔楼的时钟比对了一下,发现时间比想象的晚了很多,我必须抓紧了。这一惊讶的发现让我感到不安,对于这座城市我还不是很熟悉,幸好附近有个警察,我向他跑去,气喘吁吁地问路。他微笑着说:“你想从我这里知道路怎么走吗?”“是的”,我说,“因为我自己找不到路”, “放弃吧,放弃吧,”他说,然后猛一转身,就像那些想要独自大笑的人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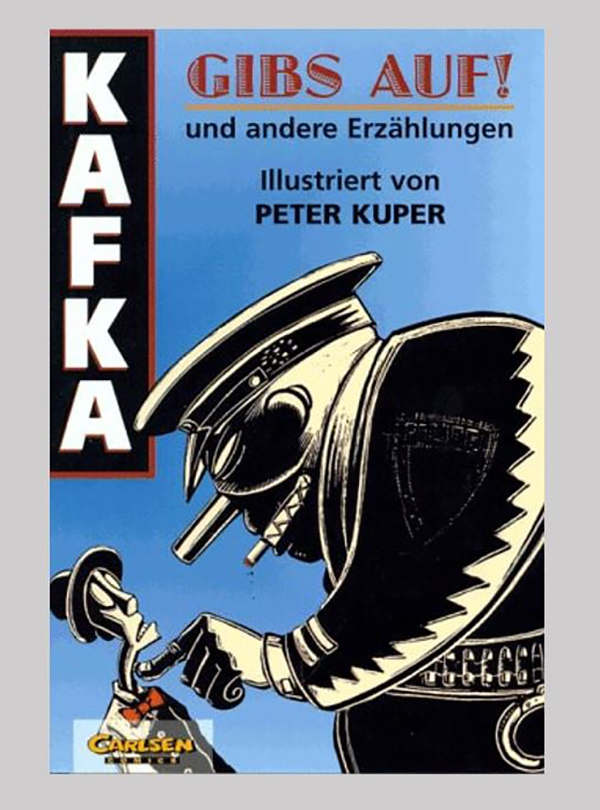
《放弃吧》(Gibs auf)书封
《放弃吧》(Gibs auf)是卡夫卡写于 1922 年底的一篇寓言式短篇小说,距离他1924年6月3日离世只有一年半的时间。1917年,34岁的卡夫卡确诊肺结核,这在当时是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席卷欧洲,卡夫卡也未能幸免,之后身体每况愈下。在卡夫卡的手稿中,这篇短文的标题是 “一则评论”。他自知时日无多,在寻找生命意义的旅途中,慌不择路。依旧是卡夫卡式朴素苍白的叙述,清醒而暧昧,在不确定的时空中,提问者只能自我救赎或是选择放弃。
变形
一天早晨,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Gregor)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害虫”(Ungeziefer)。
格里高尔是现代社会中典型的“社畜”。他并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工作完全吞噬了他。但是,家庭的重担迫使他履行自己的职业职责。他长年累月在外奔波,急于出人头地,又担心出错而备受煎熬。如果不是作为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他会立刻辞职,向专横的上司讨个说法。
起初,他认为这种角色的逆转只是暂时的,变身甲虫依然想着努力工作,之后却不得不接受残酷的现实。最先抛弃他的是职场,虽然在过去五年间,他兢兢业业做出了很多成绩,甚至没有请过一天病假。然后是家人的疏离,因为他不能再给家人带来任何好处,反而成为令人厌弃的负担。此外,还有来自陌生人的嘲笑、轻视与羞辱。一个被工作异化的人变成了“害虫”,失去了所有的社会价值,最终孤独地死去,并被当作垃圾处理掉。
在卡夫卡逝世百年后的今天,这种迷失自我的恐惧,依然笼罩着每一个普通人。一场大病、一个意外事故、一纸裁员通知书,都有可能使现代人陷入格里高尔的困境。人们害怕失去个人价值,害怕失去社会身份。软弱是人类的普遍现象。阅读卡夫卡,总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它在诉说着人们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
“如果你站在我的面前,看着我,对于我内心的痛苦,你知道什么;对于你的痛苦,我又知道什么?” (卡夫卡,《书信——致奥斯卡·波拉克(Oskar Pollak)》)
《变形记》(Die Verwandlung)是卡夫卡在 1912 年创作的一篇小说,具有强烈的自传色彩。1908至1922年,卡夫卡在位于布拉格的波希米亚王国工人意外保险机构工作。他把自己的工作界定为 “养家糊口的职业”,荒唐而轻松。此外,他还遵从家族的期望,照顾父母的奢侈品批发生意,作为合伙人在妹夫的石棉工厂承担职责。这些工作给他带来强烈的压迫感。
卡夫卡想要成为一名作家,但是他的父亲希望他成为一个符合社会价值规范的人。卡夫卡最大的痛苦在于无法满足父亲的期望,成为一名商人,实现家族社会阶层的跃升。他想要全身心地投入写作,又无法凭借作品养活自己和家人。卡夫卡在父母家的一个空房间里写作。终其一生,他很少离开布拉格:上午办公,下午睡觉,晚上写作。
对工作的回避,是卡夫卡创作的主题之一。在《关于罪恶、苦难、希望和真正道路的思考》(Betrachtungen über Sünde, Leid, Hoffnung und den wahren Weg)中,卡夫卡写道:世间尽是信使,他们奔波于各地,呼喊着已经变得毫无意义的信息。他们想要结束这可悲的生活,但是由于职业誓言的约束,他们不敢这么做。
《变形记》是一个复杂的隐喻。所谓的“害虫”,是功利主义社会中的无用之人,在既定的社会价值体系中不再具有任何价值。在卡夫卡的语言世界中,动物是弱小的、可怜的生物,是被统治的和被忽视的。“害虫”并不必然是有害的、令人厌恶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害虫”。
卡夫卡的叙事冷静而客观,穷尽细节的描写,赋予荒诞一种不言自明的日常。他试图将自己从职业和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他也深知,有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除非人生来就不受其约束。
“然后他又回到工作中去,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这是我们在大量老故事中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尽管它可能从未出现在任何故事中。(卡夫卡,《关于罪恶、苦难、希望和真正道路的思考》)
审判
又是一天的早晨。银行职员约瑟夫·K(Josef K.)在自己的公寓里突然被逮捕。一定是有人诬告,因为,他没干什么坏事。
约瑟夫·K有点沮丧,但是很快发现这次逮捕并不会影响他的工作和生活。他试图找出自己被指控的原因,思考如何为自己辩护,但是徒劳无功。他在法庭的世界里越陷越深,没有人能让法庭相信他是无辜的。直到故事的结尾,约瑟夫·K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起诉,不知道法庭是否真的作出了判决。最终,他接受了无形的审判。在31岁生日前的晚上,他被两个行刑者带走,在采石场被刺中心脏。“像条狗一样!”这是约瑟夫·K的最后一句话。
从1914年夏天到1915年1月,卡夫卡一直在创作长篇小说《审判》(Der Prozess)。在此期间,他的生活发生了三个变化:一是与未婚妻的婚约被解除;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三是卡夫卡第一次离开父母,独立生活在自己租住的房间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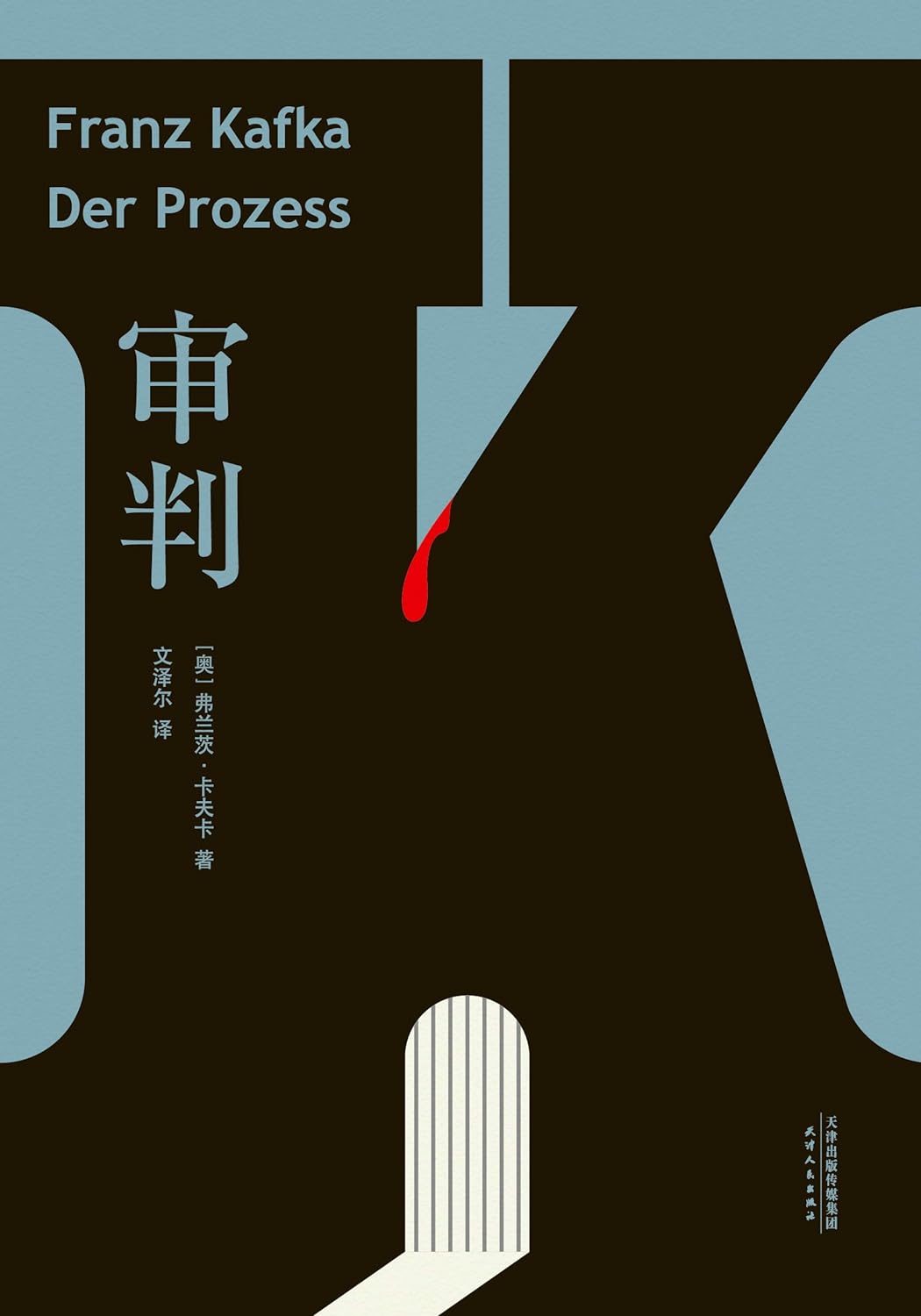
《审判》书封
卡夫卡白天在保险机构做公务员,是受人尊敬的“卡夫卡博士”。意外保险机构充斥着断肢、残臂、恐惧和冷漠,当然,也有希望。在职场或战场受到伤害的人,或许可以从保险公司得到金钱补偿或是再就业的机会,但是无法得到认同。作为官僚主义机器的一部分,卡夫卡不得不对他者的人生做出判决。1915 年初,卡夫卡中断了这部小说的创作,《审判》也因此成为一部未完成的作品。
自始至终,《审判》的叙述充满了冷静而严肃的事实。整个事件看似很糟糕,但是细节不失风趣和幽默。“当谎言成为世界的秩序”,无论往何处看,都是黑暗。
在预审阶段,约瑟夫·K试图通过一场慷慨激昂的演讲来获得法官和听众的支持。演讲内容直指法庭的荒谬、逮捕的不公、体制的腐败、官僚的蛮横傲慢以及看守的残暴。一些人给他鼓掌,为的是引诱他继续讲下去。最终,约瑟夫·K迷失在冗长的自我描述中,听众的注意力也很快转移到在角落里亲热尖叫的一对男女身上。听众看似分成左派和右派,实则是同类。没有人关心事实的真相。
“对某一事物的正确理解,与对同一事物的误解并非完全对立。”(卡夫卡,《审判》)
面对社会规范和价值体系,选择沉沦还是逃离,是贯穿卡夫卡创作的一个主题。作为社会化的人,我们无可避免地生活在这样或那样的社会评价机制中,被动地接受价值体系对个体的规范和审判。只要身处社会结构和工作关系中,就会像卡夫卡一样感到痛苦。在小说《审判》中,法官、律师、检察官、听差、办事员、宪兵、看守和行刑人都是价值体系的维护者,画家的存在是美化制度,教师教化个体,使其接受规范。
卡夫卡在作品中描述了现代人不得不面对的各种威胁:孤立无援、极权暴力、无名邪恶势力的摆布、无望与绝望以及毫无意义的努力。叔本华从自我的消解及其融入生命的普遍原则中看到了一种慰藉,也激发了卡夫卡对人心“坚不可摧”的反思:
“如果没有对内心的坚不可摧怀有恒久的信念,人就无法生活下去。坚不可摧和信念可以长久地处于隐藏状态,其中一种表达方式,是对人格化上帝的信仰。” (卡夫卡,《关于罪恶、苦难、希望和真正道路的思考》)
即使个体的人格随着死亡而终结,但是意志作为生命的基本原则依然存在。卡夫卡看到了那个时代刚刚发端的现象,而这些现象如今正主宰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审判》是卡夫卡对自由意志的探索。 “逻辑是不可动摇的,但它并不能抗拒一个想活下去的人。”(卡夫卡,《审判》)判断事物的基础应是个体的自由意志,而不是他人的意愿或社会价值。卡夫卡主张自我积极寻找身份,但是更高的权威却否认了这一点。在此,权力不仅仅是制度意义上的权力,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引力场。
“一个人怎么可能有罪呢。在这里,我们都是人,彼此相似。” (卡夫卡,《审判》)
巴勒斯坦
移民巴勒斯坦,是卡夫卡未能实现的梦想。
今天的加沙,是人间的炼狱。但是,一百年前的巴勒斯坦,对于卡夫卡来说,还是遥远的东方乐园。卡夫卡先后有四个女朋友,与每一任女友交往时,都会谈到巴勒斯坦这个话题。他始终没有勇气走入婚姻,也没能去往巴勒斯坦。
身份认同是卡夫卡的困境。在他出生时,布拉格还是奥匈帝国治下波希米亚王国的一部分,多民族混居,工业发达,文化繁荣,各种政治和社会思潮交织共存。世纪之交,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日益活跃,彼此间的社会冲突也不断增多。在给捷克女友米莱娜(Milena Jesenská)的一封信中,卡夫卡写道:“我从未在德国人中间生活过,德语是我的母语,因此对我来说很自然,但是捷克语更温暖。” (卡夫卡,《致米莱娜的情书》)
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没有任何与民族国家自我认知相关的内容。确切地说,卡夫卡既不是捷克人,也不是德国人。他是布拉格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卡夫卡都是在布拉格度过的。十九岁时,他这样描述自己与故乡的关系:“布拉格不会放手。这个小母亲有爪子”(卡夫卡,《书信——致奥斯卡·波拉克》)。1918年一战结束,布拉格成为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首都。奥匈帝国解体之后,布拉格民众的反德和反犹情绪愈演愈烈。犹太人被贴上“害虫 ”的标签,如同《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
卡夫卡注意到了这一点,开始思考具体的移民计划。他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他的三个妹妹后来均死于纳粹大屠杀。
奥匈帝国是近代犹太复国主义的发源地。1896年,犹太裔记者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出版《犹太国》一书,指出欧洲的“犹太人问题”不是社会问题或宗教问题,而是民族问题,呼吁建立犹太人的自治国家。布拉格作家马克斯·布罗德(Max Brod)是卡夫卡的挚友,也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拥护者。1939年德国军队占领布拉格,布罗德逃往巴勒斯坦,最后定居在特拉维夫。
对于犹太文化,卡夫卡的态度是矛盾的。他出身于被同化的犹太中产家庭,一方面觉得自己与犹太教有联系,对东方犹太文化抱有同情;另一方面,他又受到现代世俗化的影响,无法纵身投入一种信仰:
“我的生活,并没有像克尔凯郭尔那样,受到已经下沉的基督教义的引导,也不像犹太复国主义者那样,想要抓住飞走的犹太祈祷披肩的最后一角。”(卡夫卡,《第四本八开本笔记》,1918年2月25日)
解读卡夫卡,来自犹太文化的影响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许多学者强调,卡夫卡的作品深深植根于犹太教和犹太文化。但是,“犹太”一词从未出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卡夫卡的传记作家莱纳·斯塔赫(Reiner Stach)指出,卡夫卡的审美理想旨在解决以下问题:哪些部分是个人的,哪些部分是犹太人的,哪些部分是“人类的”(Reiner Stach, Kafka - The Years of Insigh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485)。对于任何明显带有犹太色彩的内容,作家卡夫卡都讳莫如深。
为了移民巴勒斯坦,卡夫卡一度深入学习希伯来语,直到 1923 年健康状况恶化。寓言式小说《放弃吧》似乎包含着这样的想法:对他而言,巴勒斯坦已遥不可及。
“不一定要飞到太阳的中央,而是爬到地球上一个纯净的地方,那里有时会有阳光照耀,你可以让自己暖和一点。”(卡夫卡,《致父亲的信》)
卡夫卡应该被归入犹太文学史还是德语文学史?确切地说,卡夫卡的作品超越了宗教,超越了民族。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可以如此深刻地抵达每一个心灵。
重生
无论是面对写作、婚姻,还是在摆脱父权、移民巴勒斯坦的问题上,卡夫卡常常陷于踌躇,缺乏行动力。他几次订婚,之后又解除婚约;包括《审判》在内的多部小说处于未完成的状态。卡夫卡对这种失败感感到懊恼。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他看来,不是由于惰性、恶意或笨拙,而是缺乏立足之地、空气和信念。
“目的虽有,却无路可循;我们称之为路的,无非是彷徨。”(卡夫卡,《关于罪恶、苦难、希望和真正道路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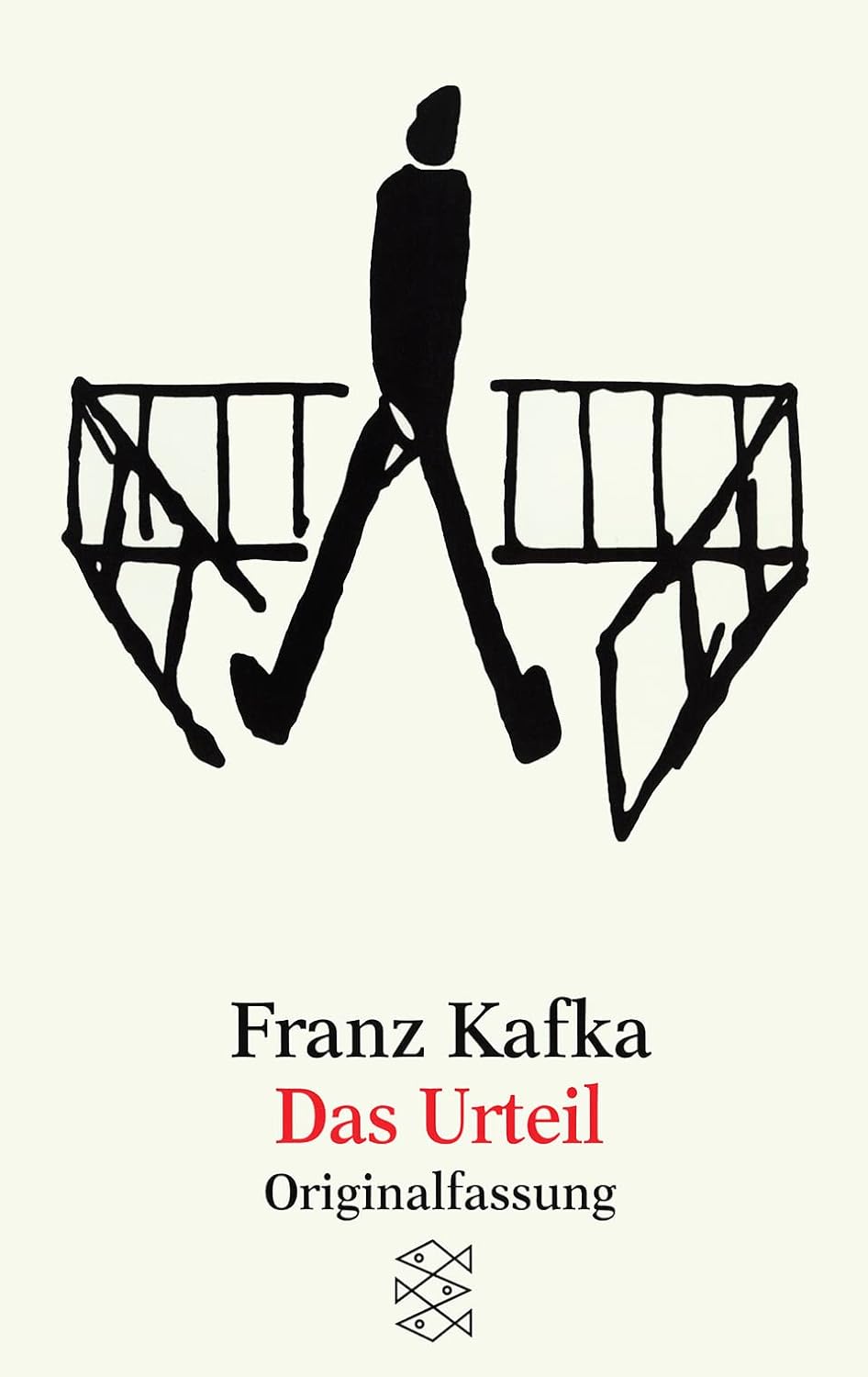
《判决》书封
在小说《判决》(Das Urteil)中,主人公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决绝。1912年9月22日晚至23日凌晨,卡夫卡用八个小时创作了这篇小说。他这样描述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故事从我的身体里诞生,就像一次真正的生产,沾满了污秽和粘液。”(卡夫卡,《日记》,1913年2月11日)
格奥尔格(Georg)是商人的儿子,事业成功,已经订婚并即将结婚。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时,两人发生了争执。格奥尔格的婚姻计划和事业成功改变了家庭的权力结构。父亲指责格奥尔格篡夺了经营管理权,选择了一个庸俗的未婚妻,判处他溺水而死。格奥尔格快步跑到河边,悬空吊在桥栏杆上,低声喊道:“但是亲爱的父母,我一直爱着你们。”说完,就让自己落下水去。
与父亲之间充满冲突的关系也是卡夫卡创作的主题之一。他想要得到父亲的认可,想要解放自己,想要自由。小说的结尾蕴含着致命的失败,也隐含了对父权审判的逃避。父亲的粗暴判决,让人联想到《审判》中无名力量的操控,梦魇般的情境,令人困惑,充满威胁。从某种意义上说,跳河意味着重生,对于游泳健将卡夫卡而言,尤为如此。是终结,也是开端。
1924年,卡夫卡去世后被埋葬在布拉格的犹太公墓,与父母共享一块细长的墓碑。至死,他也没有摆脱父亲。
“一本书必须是一把刀斧,能够劈开我们内心冰封的海洋。”(卡夫卡,《书信——致奥斯卡·波拉克》)
卡夫卡为我们举起了一面镜子。你在其中是否认出了自己?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