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读|“近密”的陈与义研究与陈与义的“近密”诗学
在南北宋之交的诗坛上,最耀眼的诗人当属陈与义。五六百首的存诗从数量上看也许算不得多,但却有着高度精熟的样貌和通贯始终的诗学追求。严羽《沧浪诗话·诗体》特别提出“陈简斋体”(陈与义号简斋),并将其与杨万里“诚斋体”并列,推举为南宋诗歌中最具个性特色的两家。后人也高度认可陈与义在宋诗发展流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宋末元初方回在对江西诗派作总结时提出著名的“一祖三宗”说——“古今诗人当以老杜、山谷、后山、简斋四家为一祖三宗”(《瀛奎律髓》卷二十六《清明》诗评),对陈与义的诗歌史地位给予了高度肯定。
陈与义在两宋诗坛上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学界既有的陈与义研究却似乎未能达到与其重要性相匹配的程度。尽管文学史对陈与义诗歌的核心特色、总体地位已有基本的判定,但少有更进一步的邃密深细的探讨。这或许是因为陈与义诗歌研究并不容易,鞭辟入里的分析必须以精细深入的诗歌解读为基础,而陈与义诗歌的精细解读又面临两个难点。第一个难点来自宋室南渡的时代动荡和避乱南奔的颠沛经历,陈与义最具分量的作品正是创作于这样的背景之下。若不能对其创作的历史事实和具体语境有所了解,很难走近其诗心。另一个难点来自于陈与义与江西诗学之间的复杂关系。江西诗学形塑了陈与义诗歌表达中许多关键的思维方式和语言形式,即便陈与义并非江西诗派中最难懂的诗人,对他的诗歌的解读仍然需要以深厚学养为基础。在这样的语境下,美国俄勒冈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王宇根教授的新著《万里江湖憔悴身——陈与义南奔避乱诗研究》(周睿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版)充分展现出直面陈与义的勇气,并在诗歌解读与诗学阐释方面取得了重要创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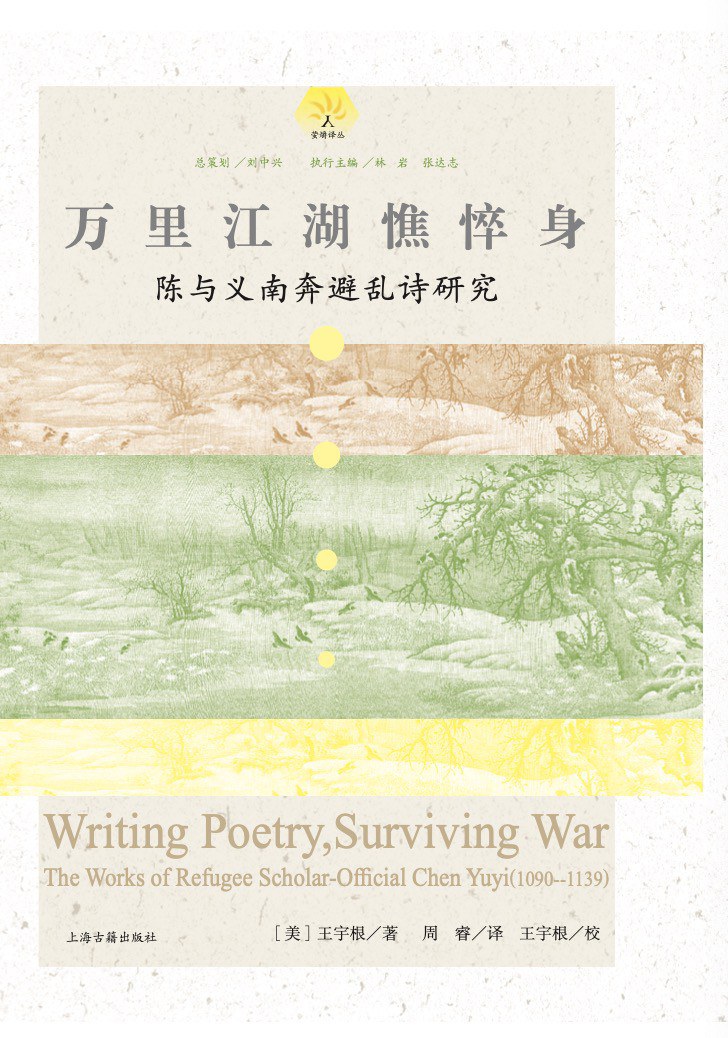
《万里江湖憔悴身》英文版出版于2020年(New York: Cambria Press),原标题为Writing Poetry, Surviving War: The Works of Refugee Scholar-official Chen Yuyi (1090-1139)。在此之前,北美汉学界已有两篇研究陈与义的博士学位论文,分别是印第安纳大学何瞻博士(James M. Hargett)于1982年完成的The Poetry of Chen Yu-yi, 1090-1139,斯坦福大学麦大伟博士(David R. McCraw)于1986年完成的The Poetry of Chen Yuyi (1090-1139)。两篇博士论文对陈与义的生平创作、诗歌技巧与历史地位作出了整体性的考察。《万里江湖憔悴身》则进一步聚焦于陈与义南奔避乱时期的诗歌写作,并尝试把握陈与义诗风演变的独特轨迹、揭示陈与义诗学特质的内在筋骨。
尽管该著以陈与义的南奔避乱诗为主要研究对象,但讨论的范围并未局限于南奔避乱时期的作品。作者将陈与义的毕生创作视为一个整体,在历史的坐标系中锚准南奔避乱的位置和意义。全书共分三部分展开。第一部分“早期作品”包含三章,分别为《客居》《年华》《贬谪》,是对南奔之前的考察。第二部分“行旅途中”包含第四至七章,分别为《前路漫漫》《山与水》《面对面》《诗到此间成》,讨论陈与义南奔途中的作品,是书中的重点。第三部分“劫后余波”包含第八章《破茧成蝶》、第九章《茕茕独立》和尾声,考察南奔结束以后陈与义诗风转变的余音。三个部分的组合,既梳理出陈与义起伏跌宕的生平,又展现了对陈与义诗歌的艺术剖析,更贯穿着对陈与义诗风变革的思考。
在笔者看来,“近密诗学”(The Poetics of Intimacy)是书中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虽然作者没有给予它一个非常醒目的位置,但它不仅是作者对陈与义诗歌特色及成就的精彩提炼,而且契合了全书的研究方法和写作方式,即:以诗歌解读为扎实根基、以诗学阐释为内在脉络,将陈与义放在宏观格局之下作微观而近密的审察。
近密的比较:学习杜甫与成为“自己”
陈与义学习杜甫,这是文学史公认的事实。不过这一事实内部仍有许多关节尚未得到细致的分疏。一个尤为关键的问题是:为何陈与义并没有成为另一个“杜甫”,而是造就了属于自己的“陈简斋体”呢?这正是贯穿于全书的核心问题之一,作者对此给出了细致的讨论和有力的回答。
一方面,该著通过大量作品分析印证了陈与义对杜诗内在精神与外在形态的积极效仿,将陈与义定位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标志着北宋文人对杜甫集体迷思的一个高潮点”(第7页),对陈与义效仿杜甫的具体表现作出了较前人更具为细致全面的梳理。
作者以靖康之变为界,对比陈与义在此前后学习杜甫的不同侧重。前靖康时代的借鉴多为“技术性的化用”,主要是词义、技法、意象等层面的学习,“往往开门见山又直截了当”,甚至不乏对杜甫观点的调侃与颠覆、尝试超越杜诗技法的冲动(第169页)。后靖康时代的借鉴则源自精神上的认同,在频繁借用杜诗的内容与主题以外,陈与义还会化用“杜诗思想情感的整体建构”,或代入“杜甫其诗其人的特定身份”(第170页)。前者如《发商水道中》的“草草檀公策,茫茫杜老诗”,这是将杜诗的“整套情感联想”编织到自己诗作的主题结构脉络中。后者也被作者概括为“角色扮演”(第9页),在面对国破家亡、天涯沦落的惨况时,陈与义强烈感受到与杜甫的重合,进而以与杜甫相同的姿态发出沉重的感喟。如《次舞阳》末四句“忧世力不逮,有泪盈衣襟。嵯峨西北云,想像折寸心”,不但在字面上化用杜甫《西阁曝日》的“忧世心力弱”和《冬至》“心折此时无一寸”,更在姿态上化用《秋兴八首》中的“每依北斗望京华”,从而与杜甫的身影叠加,仿佛一同凝望、流泪、心碎。这些基于诗歌的切近分析,有着极为清晰分明的肌理,从细节上推进了陈与义学杜的考察探究。
另一方面,该著始终关注陈与义有别于杜甫的一面。在作者看来,即便有着“但恨平生意,轻了少陵诗”这样经典的情感觉醒(《正月十二日自房州城遇虏至,奔入南山,十五日抵回谷张家》),但这种觉醒并未把陈与义变成另一个杜甫。作者通过对陈与义南奔诗歌的历史考察,细致描述了陈与义代入杜甫的“角色扮演”是如何逐渐冲淡搁浅、中道而止的。
在第一部分对早期诗歌的讨论中,作者已敏锐指出陈与义诗歌中鲜明的理性色彩。陈诗“在思致的呈现和叙述上”具有“井然有序和务真求实”的特点(第113页),追求“周密观察和细致描述的精确性”(第121页)。作者在第二部分的探讨中也不时强调,这些诗学倾向在南奔避乱时期不但始终存在,而且在南奔避乱后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如第四章在分析陈与义与杜甫的同题之作《北征》时指出,不同于杜甫为家国危亡、生灵涂炭迸发出的沉痛悲叹,陈与义侧重于旅途山水物象的书写,展现出相对平稳的叙事风格,体现出对现实世界制约的清醒认识和接受。第六章则围绕《登岳阳楼》展开了详尽分析,认为尽管这被认为是陈与义师法杜甫的经典作品之一,但与杜甫相比,陈与义的想象与表达仍然更受物质环境的局囿和现实情境的制约。
相关论断不仅建立在对陈诗的详细解读基础上,而且建立在对诗歌史发展脉络的宏观把握的基础上。作者不忘指出,陈与义之所以没能成为“杜甫”,背后有着时代的因素。将杜、陈二人放入唐宋诗的大背景之下,更能理解这种差异的产生。正如作者所言:“陈没能完全化身为杜甫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他是在一个非常不同的思想和技术语境下写作的,其时代对诗歌在技法和文化上都有非常不同的预期。”(第211页)对此作者有着极为透彻的理解。他的上一本专著《万卷:黄庭坚和北宋晚期诗学中的阅读与写作》对印刷技术影响下的唐宋诗学差异有着独到的观察和精辟的论述。因此作者能够敏锐揭示陈、杜的区别——陈与义比杜甫更关注“思理的细密”和“与物质世界的契合”(第10页),促使他更愿意从眼前的风景中寻求意义,以限知视角去观察和理解周遭的世界。
总之,在对陈与义与杜甫的近密对比中,作者充分考察了陈、杜二人在观察世界和诗歌写作等方面的异同,为读者描述了陈与义“破茧成蝶”的精彩历程:通过努力成为“杜甫”,陈与义成功地重新发现自我,最终成为了“自己”(第9页)。
近密诗学的提出:自然与诗人
自然与诗人的关系,是该著探讨陈与义诗歌的另一条重要脉络。这条脉络与上一条脉络是交织并行的关系。作者多次表达,对自然与诗人关系的不同理解,是陈与义与杜甫渐行渐远的关键原因:“简斋诗与子美诗之间的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尤为表现在诗中所隐含的诗人与世界的关系上。”(第240页)
自然与诗人的关系是中国传统诗学中的经典问题。不同时代的诗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尽相同,带来了诗歌中不同的表现倾向。在宋代以前,发挥核心作用的是“比兴”诗学,由此积累起来的基本表达方式是:自然唤起诗人的情感,诗人在对自然书写中投射自己的情感,“高度主体性的诗人本体”构筑了诗歌中自然世界的秩序。而作者尝试证明,陈与义对自然与诗人的关系有着不一样的理解。
首先,作者指出,陈与义诗中的自然是具有独立性的存在。“自然风光的内在逻辑并不是诗人自身伦理世界的直接投射”,诗人作为“天地万象和乾坤变化的见证者”,与自然保持冷静客观的距离,因而“专注于对自然景物的观察和描述,而不试图去影响或改变它们”(第186页)。书中反复提及,陈与义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和观察更加务实理性、也更具物质基础。这在诗歌中体现为对限制视角的使用,对个人感受体验的精确表现。在第五章中,作者对陈与义《观江涨》与杜甫《巴西驿亭观江涨呈窦使君二首·其一》这两首同题材的作品进行了比较。杜诗中的“孤亭凌喷薄,万井逼舂容”等不但体现出超越实景的视点,而且投射着诗人内心情感的动荡。而陈诗中的“叠浪并翻孤日去,两津横卷半天流”等则框定了诗人与景物的位置关系,因而体现出“物质现象的内在连贯性和秩序”(第228页)
其次,在尊重自然之物质性的基础上,陈与义得以与自然展开更为亲密的互动交流。作者特别关注陈与义与自然之间的“亲密”关系,导论中即指出“靖康之难后陈与义的频繁亲近自然……是成就其诗艺精妙的主要原因”(第9页)。第四章亦称自然是诗人争取内心平静的可靠“盟友”(第182页)。在陈与义看来,自然不但是独立的,而且是可亲的。以这样的认识为基础,陈与义倾向于近距离地感知观察自然景物的细微变化。作者将陈诗这一特色概括为“近密诗学”(The Poetics of Intimacy)。第四章中的“近密诗学”一节,着重谈论了陈与义与自然景物近距离感知交流的近密模式(intimate mode)。这种近密互动模式体现为诗人对自然风景的深入穿行和悉心感知。作者举出了《山路晓行》等例子,“篮舆拂露枝,乱点惊仆童。微泉不知处,玉佩鸣深丛”,从行旅者的角度出发,书写行走在山水中的视觉、听觉等即时感知,展现出沉浸接触自然山水的亲密体验。“诗人不是山水风景的单纯观察者和追随者,而是其深情探索者,主动融入并与其间的柔声细语及细枝末节积极互动。”(第196-197页)
通过以上考察,该著提炼出陈与义对自然与诗人之关系的独特理解,并勾勒出由此带来的诗风演变趋向。在经历南奔避乱以前的陈与义,尽管酝酿着一些新的变化,但总体上仍是以相对传统的表达方式为主的。不过随着南奔避乱的到来,自然这一物质世界在陈与义的诗歌中越来越占据主导的地位,不但获得了鲜活、具象、精确的描述,而且成为诗人“自我和身份建构的核心‘元件’”(第5页)。当漫长的南奔结束,一切尘埃落定之际,陈与义“一生襟抱与山开”(《雨中再赋海山楼》)的表述再次总结了自然对自己的意义,“他的敞胸开怀并没有指向某个具体的人,而是指向其所视所见的自然山水”(第320页)。通过对自然与诗人关系的考察,作者尝试证明,陈与义不仅是“源自中古魏晋时期的山水诗的漫长演变的‘终点’”,而且是下一代中兴诗人如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的“先驱前贤”(第6页)。
这一观点对于理解宋代诗歌中的自然观及自然书写具有重要价值。前辈学者多关注到,对大自然亲密感的增强是宋诗的一大特色,表现为人格化自然意象的增多、拟人手法的频繁使用等。诗人往往秉持对自然的尊重态度,积极与自然展开互动和对话。其中苏轼与杨万里被视为最具代表性的诗人,得到了不少探讨。而该著对陈与义的分析则让我们认识到,在苏轼与杨万里之间还应当加上陈与义这一重要环节。陈与义对自然的主动融入、与山水风景中的细节进行亲密互动,以及在此基础上达成的诗歌成就,在宋诗自然书写的发展脉络中无疑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
近密的写法与读法
从写法上看,《万里江湖憔悴身》以陈与义诗学成就的达成作为叙述的内在脉络,而以陈与义各阶段代表性诗歌的解读作为外在的肌理。正如作者自己的表述:“从最基本的层面上说,本书是对简斋诗的细读和通论,重点集中于其避乱金兵侵扰五年半羁旅中的诗作。”(第21页)作者沿着生平时序与诗人经历来设置章节,对陈与义诗歌作精细的文本解读,以“现场直播”的方式铺展开诗意的原始语境。这一写法本质上映射着作者的研究方法,因而这一写法本身也具有关注和讨论的价值。
该著对诗歌的深细解读令人印象极为深刻。这种细读的功力首先有着北美汉学的直接影响。北美汉学擅长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在将古代诗歌翻译成英文的过程中,对主语、谓语、宾语、时态、单复数等各类语法形态的落实,迫使作者不得不深入诗歌的内部,力求精准把握每一个字词的意义。王宇根教授毕业于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系统接受了北美汉学的学术训练。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专著《万卷:黄庭坚和北宋晚期诗学中的阅读与写作》已充分展示了文本细读的扎实工夫。在数年积淀之后,《万里江湖憔悴身》对陈与义诗歌的解读显得越发圆融。
与此同时,《万里江湖憔悴身》所展现出来细读功力还有另一条源流,即来自中国的学术训练。王宇根教授有着颇为独特的学术背景,在就读于哈佛大学以前,他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获得了硕士学位。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他的文本细读中时时体现出中国学者解读古典诗歌的细腻熨帖。古典诗学中知人论世的经典批评方式在书中得到了妥当恰切的运用。对宋室南渡的时代背景和陈与义南奔逃难经历的真切呈现,是对陈与义诗歌特色及诗歌成就进行准确提炼的重要保障。这也使得这部著作成功回避了许多海外汉学论著中容易出现的过度阐释的缺点。诚然,在对诗歌展开精细解读的过程中,偶尔一两处的误读或许难以避免,但这些细节的偏差并不影响书中的核心意旨。毋宁说这些细小的误读中印证着“诗无达诂”的阐释可能性,展现着作者为贴近诗心而作出的不懈努力。
与诗歌细读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贯穿在诗歌细读中的思考主线。诗歌细读在内容上构成了该著的主要组成部分,但该著绝不只是诗歌解读的连缀。无论是以南奔诗为中心所形成的三大部分的结构,还是各个章节精心设置的标题,都指向了统一的方向,也在事实上成功揭示了陈与义诗歌的独特成就。关于这一层,本文前两部分已作出了揭明。诗歌细读与思考主线的结合,使该著成为近年陈与义研究中一部有突破意义的力作。
《万里江湖憔悴身》的写法也关联着读者的读法。不过该书在翻译前后的读者群体是存在差别的。该著英文版的读者应当含括了海外汉学研究者以及对中国文学与文化抱持兴趣的非专业读者。考虑到海外学术写作的常态及海外读者的接受能力,围绕陈与义的南奔经历展开、梳理他在这一过程中的心路历程与诗风变迁,确实是一种更为理想的写作方式。而当该著翻译为中文时,读者群发生了改变。中文版首先面对的读者将会是专业的研究者。在当前的学术环境中,专业研究者早已习惯于阅读观点鲜明、框架清晰的专门性研究论著,因而在初逢《万里江湖憔悴身》时,或许会存在一些不适应。从追求效率的角度,我们有理由埋怨作者没有对观点作一览无余的展示,任由许多精彩的见解淹没在叙述的细节中,让读者在提炼观点和梳理脉络时煞费苦心。然而换一个角度来看,该著在诗歌细读中所展现出来的从容舒缓的叙述节奏、叩动人心的情感温度,却又有些令人羡慕。书中没有对诗人作冰冷的解剖,而是尽可能还原了这位诗歌名家在遭遇艰难困苦时的挣扎与蜕变,并且保留了读者在邂逅这些精彩诗作时所能感受到的内心悸动。
因此,在阅读这本书时,我们不妨像作者解读陈与义那样,采用一种“近密”的读法,放慢节奏,穿行于字里行间。也许我们会进入一种“角色扮演”的情境,不自觉地采用与陈与义相同的姿态,行走于自然山水间,在对风景的近密体验中获得心灵的慰藉。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