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一个人的无国界漂流:她在世界隐秘的角落,与创伤对话|镜相
镜相栏目首发独家非虚构作品,如需转载,请至“湃客工坊”微信后台联系。
作者 | 胡卉
编辑 | 吴筱慧
编者按:
从大学开始,孟晨就想要找到与广阔世界深入发生联系的通道,并在这个通道里发挥她的独特价值。她开始在多个国家奔走、倾听,记录世界角落不为人知的目睹和感受,她去尼泊尔参与小山村建立项目,在澳大利亚北部港口帮船长“造船”,在乌干达与战争幸存者交谈……“一个人的无国界漂流”系列分上下两篇呈现,通过孟晨人生中大部分重要阶段的选择,讲述了一个普通女孩探索自己,在全球化的时代机遇下认真和世界建立关系的故事,本篇为下篇。(查看上篇可点击此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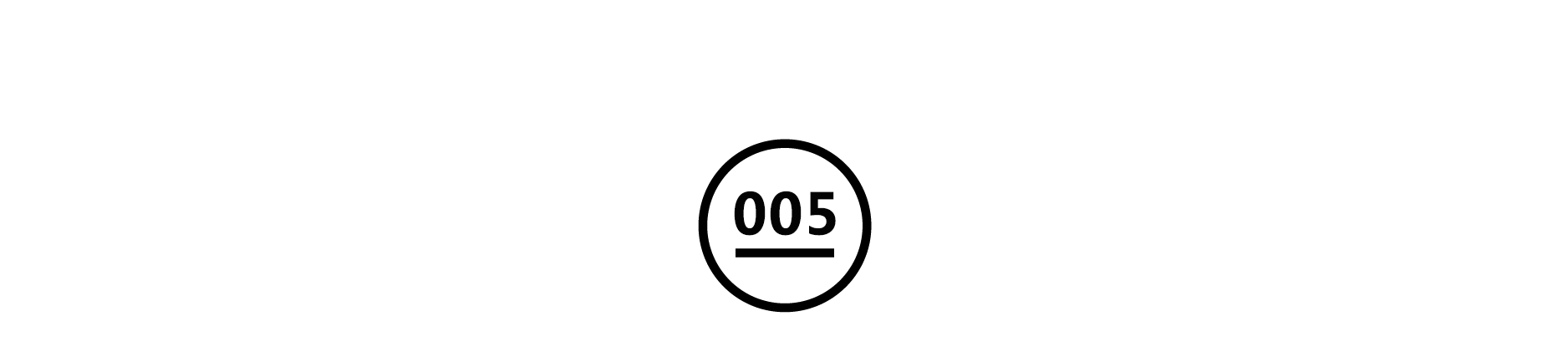
在路上反而没什么可怕的
几个月后,孟晨了解到大学里有一个合作项目,工作单位是乌干达国家和平与记忆记录中心。从照片上看,那是一栋修建在枯草和泥地上的两层简易楼房,和当地最常见的茅草屋相比,这栋砖瓦结构的土黄色楼房肯定算得上地标建筑。
工作内容和乌干达内战有关。1986年,打游击战的穆萨韦尼夺取政权,北方的阿乔利人兵败,逃回老家后想要卷土重来,给北方带来了巨大灾难。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反政府武装部队起义不断,其中一支叛军“圣灵抵抗军”为了补充兵力,突袭北方村庄和学校,绑架了几万名孩子,屠杀了其父母。男孩被训练成杀人机器,女孩被训练成性奴。不服从者被送到人体交易市场,补充军费,或者直接交换成枪支。这支叛军不断壮大,成为非洲历史上破坏力最大的超级恐怖组织,乌干达、苏丹、刚果等非洲十几个国家深受其害。
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支军队的主力就是孩子。孟晨看到网上流传的非洲儿童兵的照片,表情冷漠,杀人如麻,那些稚嫩的小脸比他们身上挂着的重机枪更加可怕。
内战结束后,直到如今,北部村庄还有一万多个孩子失踪。从战场上幸存下来的孩子,或者在战场上长大成人的孩子,返回家乡时遭到了强烈的抵制。他们被视作可怕的杀人犯,灵魂受了污染的人,而不是当初离家时那个手无寸铁的孩子了。然而,从战场上活下来的人认为自己当初是被迫的,人们根本不知道的是,一个孩子被掳走后经历的一切是多么骇人听闻。现在,除了回到家乡,他们无处可去。
到底是驱逐,还是接纳,孟晨的工作指向这个分岔口。她想,她此行要做的依然是一个看见彼此、加深理解的工作,也就是说,至少先了解那一代孩子经历了什么。
在纽约,对接她的人说:“恭喜你,晨,这一趟去乌干达,你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们没有人可以给你提供经验,也不知道那里的工作会怎么展开。作为唯一的申请者,你是一枝独秀,没有同伴。”孟晨自嘲地想,如果这人懂中文,大概会用中国人审慎不安又兵来将挡的语调说:“请自求多福吧。”
出发之前,孟晨下载了一个查看世界各地安全指数的国际版SOS软件,它预报乌干达恩德培机场近期将有一场恐怖袭击。但这像天气预报一样,是讲究概率的。但不可掉以轻心的是传染病。乌干达目前流行的传染病有艾滋病、埃博拉病毒、黄热病、疟疾、甲肝、乙肝、流脑,以及霍乱。在墨尔本受过医学训练的她,对这些病毒的危险性都有认识。纽约的医生给她注射了八种疫苗,不安地交代说,这两三个月千万要戒除性事。孟晨猛摇头:“没有,从来没有。”这一点她不担心,她害怕的是疟疾。她想起诗人穆旦随远征军翻越胡康河谷时,因为疟疾差点死掉。纽约也没有疟疾疫苗,她只能带点儿救急的口服液。
在路上反而没什么可怕的了。
工作单位驻地是乌干达北部一个叫Kitgum的村庄,在斯瓦西里语中,那是应许之地、祝福之地的意思。村庄空气湿热,尘土飞扬,盛大的棕榈树林中间,散落着原始社会气质的尖顶茅草屋,没有门板,往里张望,黑乎乎的,还没有通电。几只锅搁在黑色的泥地上,散发出水煮香蕉的气味。妇女们裸着粗壮的胳膊,一只手扶着头顶的一筐绿香蕉,缄默沉稳地在路上走。孩子们光脚跑着,为了争夺一个矿泉水瓶,凶狠的劲儿简直像小小的猛兽。后来孟晨才知道,那矿泉水瓶是他们制作玩具的材料,瓶盖是小汽车完美的车轮。

在乌干达 受访者供图
一个拥有一栋砖瓦平房的知识分子家庭接纳了孟晨入住,为她免费提供一间单独的小房间,有单人床、蚊帐和热水瓶。主客同吃,每天是油炸绿香蕉和水煮土豆泥,过两周有一顿改善型的食物:猪肉、番茄和土豆,做法类似河南的烩菜,出锅装在一个义乌制造的大碗里。当她聊起对疟疾的隐忧,女主人轻松地笑着说,这里没有谁没有得过疟疾。“放心吧,打摆子和拉肚子,死不了人的。”果然没过多久,孟晨得了疟疾,乌干达人的轻松态度似乎比行李箱里的口服液更有安慰作用,那几天,日行两万步去做口述的她允许自己躺平。她会点开荔枝电台,回到母语的怀抱,用中文给浙江的朋友们讲述她的乌干达故事。
这家的丈夫是个导演,拍摄了非洲最早一批女性主义题材的电影,比如,大独裁者阿明统治时期的女囚,奔赴韩国留学的乌干达女性。1995年,他作为乌干达代表,到北京参加了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他身上有着非洲知识阶层的共性:举止友善,英文流利,留学北美,对中国兴趣浓厚。导演的客厅里每天播放CCTV国际频道。
有时候,孟晨也跟他聊起工作的进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孟晨身处的环境安全舒适。她在这里遇见了重庆工程队。他们在升级乌干达的道路系统,像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一样,铺设沥青双车道,实现人车分流,安装太阳能路灯。这群异乡人三四年没有回国,但普遍不想融入当地,平时只在工程队的板房周围活动,吃重庆火锅,不碰什么炸香蕉。当他们不得不出门时,一定随身携带AK-47步枪。
白天,孟晨在乌干达北部的几个村庄跑来跑去,寻找战争的幸存者,与他们交谈,用录音录像的方式记录。晚上,她做大量的整理工作,也琢磨呈现的形式。她既是记者,摄像,速记员,又是策展人。她看见个体的遭遇和痛苦,恐怖组织的邪恶和机制,看见一个人为了拒绝灵魂堕落的命运,需要冒多大的危险,以及,一个人要有怎样的勇气、决心和运气,才能保留住身上好的人性。她盼望最终她的成果,能在乌干达国家和平与记忆记录中心展出,同时作为一份特别的礼物,留赠给乌干达人。事实上,她后来也是这么做的。

乌干达 视觉中国 图
孟晨拜访的第一个人,是阿乔利部落的酋长毕肖普。酋长也有一座砖木结构的平房,有石灰的墙壁和防水的屋檐。这座房子既是他的家,也是他创办的“失踪者文化中心”的办公室。房子的墙壁上贴满了失踪孩子的名字和照片。酋长知道杭州,说他喝过一位中国人赠送的龙井,他“很喜欢看绿茶的叶子一片片地漂浮在水上”。
他带孟晨参观了家里,指着满墙的照片和细字说:“这些都是失踪孩子的姓名、出生日期和他们父母的名字。”
孟晨深受震动:“怎么一对父母的名字下面对应那么多孩子呀?”
“没错,这些家庭的十来个孩子都被抓走了。”
“至今没有下落吗?”
“是的。”酋长说,“失踪的大部分都没有回来,生死未卜。很多小孩被卖到阿拉伯国家的器官黑市换取枪支。你有机会去这些父母家里看看,他们很绝望,很消沉,每天喝得烂醉。”
毕肖普酋长就是被“圣灵抵抗军”掳走的孩子,在丛林和兵营接受过儿童兵的训练。那一年他14岁。战争爆发,叛军每一天天一黑就来扫荡村子,穿家入户地抓孩子。他的父亲没有武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被带走。
时隔八年,我读到孟晨这些不为人知的口述记录,在这些繁多的资料中有毕肖普酋长的,也有其他人的:
“我(毕肖普)和叛军在一起待了六个月,目睹和经历了种种……后来我得了一种叫麦地那龙线虫的恶疾,无法行走,只能靠双手爬行。我没有用了,被丢弃在丛林里。那里非常偏僻,植物遮天蔽日,只有鸟兽,一个人也没有。生死关头,一只同样残疾的狗救了我。它被捕兽陷阱夹断了腿,走路一瘸一拐的。是它找来蜂蜜和虫子喂养我。在那些日子里,我反而获得了久违的安全和平静。我听见了内心的声音,好像神在对我说:‘你的日子打开了。’(Your days are opening.)我向着家的方向继续爬,爬了好久好久,日子都模糊不清了。非常偶然的,我遇到了我的姐姐。原来在我失踪的日子里,她一直在坚持找我。”
“亲爱的晨,我(凯蒂)想告诉你的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9岁那年,1995年,八月十五,晚上八点,叛军来到我家的茅草屋,敲门,敲门。我们拒绝开门,他们就踢门。门一下子开了,他们冲进来,留下我的姐姐们在屋里,强迫我跟他们出去。他们查看我的隐私部位有没有毛发。我那么小,什么都没有。但他们还是想强暴我。他们的首领让我跟随去丛林。我的哥哥也被一同抓去做士兵。就是在那个晚上,他们把我的叔叔锁在一个房子里,逼我和哥哥点火。我们这么做了,我叔叔被烧死了。我们在丛林里待了三年。我被强暴,但没有怀孕。很幸运的是有一天,叛军误闯了政府军埋伏的丛林,他们四下逃窜,这给了我逃跑的机会。”
“……有时候,逃跑很难。因为逃跑会招来报复。他们会因为你逃跑而回到你父母家,杀光你村子里的人,所以她们牺牲了自己。”

生命最终都会有意义
面对有创伤的人,仅仅倾听和记录是不够的,孟晨渴望用正确的方法去修补那些荒败的心灵地貌。束手旁观,无法切实有效地行动,这让她心生挫败感。她对自己缺乏心理医生或精神科医生的专业知识耿耿于怀。她寻找接受教育的机会,了解到纽约有大学设有心理咨询专业创伤方向,相关授课老师有过集体创伤的经历,对此深入思考和研究过。比如,一位教授是美国创伤协会的创办者之一,二战期间,他的家庭遭受了纳粹屠杀。孟晨认为专业设置符合期待,不仅有系统的理论知识,还有很多创伤案例的实践课程,涉及艺术、戏剧、游戏、美育等操作性较强的疗愈方法。
她顺利入读这所学校,继续求学。
一如既往,她首先从同学身上见识他们的勇猛精进。尹智慧是一个韩国女学生,五十多岁,说话时双目熠熠,看得出年轻时一定很漂亮。她是一个非常先锋的民主运动斗士和女性主义者。这是孟晨的评价。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纽约滴水成冰,孟晨和尹智慧踩着新鲜的大雪去另一个街区的电影院看《黎明之前》,影片内容是韩国光州事件引发的学生运动。屏幕上出现的学校正是尹智慧当初在读的,她也身在其中,和同学们一起手挽手挡催泪弹。从首尔大学毕业后,她开始了另一种人生,嫁给三星集团的高管,养育孩子,过着典型的上流社会的生活。然而婚姻内部的景观经不起细看,特别是传统力量中蛮横的一面令她倍感压抑。她反感丈夫朝夕相处的母亲用审查的眼光看待她,批评她,她身在伦理排序的低位,忍耐了二十多年。五十岁那年,她决心送自己一份生日礼物,离开那个家,带着未成年的儿子一同出来求学。智力和行动力是生命力的表现,求知和远行让她觉得重焕生机。
课堂说来也不太一样。孟晨看到,似乎少有这么一个专业,不是务实地面向未来求职,而是务虚地面向过去,和个体的生命经验息息相关。教授们也奇怪,自己选择了创伤研究的方向,在里面走完了几乎一生,却不理解学生们“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条狭窄的路”。一个打扮完全西式的男生,表示自己是柬埔寨裔美国人,他的妈妈是红色高棉大屠杀的幸存者。美国同学面面相觑,没听过这段历史。孟晨想起在北京时,随摄制组拍摄了一个幸存的华人在柬埔寨劳改营接受强制劳动的经历。她记得法国学者拉古特的统计数据,1975-1978年,在柬埔寨的43万华人死了21.5万。之后,孟晨在纽约遇到另一个华人,李。李的父母70年代在柬埔寨开店,听到种族灭绝的风声,全家八口人朝大海的方向逃命,接近海边时,红色高棉巡逻队拦住了他们。李的父母拿出携带的所有钱财和物品,想换条生路。军人一一清点,说:“这些只够买一个人的命。”父母让兄弟姐妹六人抽签,最后李成了唯一活下来的人。后来,李作为难民进入美国的大学,他总觉得是八个人在一起上学。
开学不久,孟晨路过纽约炮台公园时,遇到由无国界医生举办的一个展览。展览的入口,人们领取一张仿真的阿富汗身份证,盖上一个寻求庇护的章。由人带领着,体验阿富汗难民之旅:选好只能带走的三样东西,坐上难民跨境逃难的简陋小船,抓住边境线上的铁丝网,钻进挤满一家子索马里难民的帐篷。不知为什么,此时此地,孟晨一下子想起了幼年在杭州看无国界医生题材的TVB电视剧的心情,她心潮澎湃,感到内心对崇高的需要和追求的迫切心。那种不知如何命名的静谧激情,并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相反,她认为,从理性上讲,正因为她长大了,受了专业的教育,去了那么多地方,她可以让无国界医生的梦想超越幼稚的空想,拥有变成现实的可能。

无国界医生的展览 受访者供图
第二年夏天,孟晨通过申请,参加了哈佛大学医学院在意大利小城奥尔维耶托举办的全球难民心理创伤训练班。奥尔维耶托是一座建造在火山凝灰岩山顶之上的小城,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它高居于悬崖峭壁,城墙由一块完整的大石头天然形成,没有受到工业革命的影响,也完好地躲避了“二战”,至今和人类文明保持着警惕的距离。城里没有超市、快餐店和摩天大楼,汽车不允许进入,一律停在城外的大型停车场。
师生们住在一个修道院里,看着很像西西里电影里的建筑,三个像三胞胎一样难以分辨的修女老太太照顾起居。上课是在一个圆形的古堡,穹顶很高,画满了壁画,一般安排上午老师讲课,下午学生做案例分享。第一天,有个尼日利亚的心理医生讲述的是2013年,两百多个正在参加期末考试的尼日利亚女孩被一个名叫“读书即罪恶”的恐怖组织集体绑架。因为政府能力较弱,救援不成,女孩们被关押了940天,遭受虐待和强暴,很多人死亡。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女孩被营救出来,但因为那段可怕的经历,她们出现了严重的精神问题。政府提供了一家小型疗养院给她们,这位医生就来自那家疗养院。几年过去了,他感到工作依然棘手,充满挑战,于是来这里寻求同行们的建议。
孟晨是班里年龄最小,资历最浅的,其他医生都有过长期的人道主义救援和公共卫生服务的经验,大家谈论的内容苦难深重;但另一方面,孟晨觉得自己与世界上最优秀的同行前辈朝夕相处,非常地幸福。
她与加拿大医生马克建立了长久的友谊。马克是个中年男人,体型庞大,风趣幽默,身边总是跟着一条爱吃松鼠的狗,这是一条跟他去过日本地震、海地地震和叙利亚战争现场的救援犬。听说孟晨的理想职业是和他一样,做无国界医生,马克告诉她,他的代价是没办法承担家庭责任,以致妻子离开,两个女儿不理他。
在意大利分别时,孟晨让马克录一段给女儿的视频,如果他失联了,她会发邮件给她们。马克同意了。他微笑着说:“你们都是好女孩!希望你们不要嫁给消防队员和人道主义工作者,嫁给朋克,嫁个嬉皮士吧!……生命有时候是哀伤的,但这些最终都会有意义的。”
一年后,孟晨在纽约收到马克从叙利亚寄来的明信片,他用英文和叙利亚文写道:“圣诞快乐!这一年我经历了很多的起起伏伏,我慢慢意识到我有亲密的朋友,伟大的父亲,很好的家人,这些都是我生命里的爱和祝福。这一年我仍然不乏很多的挑战,孩子们仍然不愿和我讲话,这不是她们的错,我只希望时间能抑制她们心里的伤口。叙利亚人教会了我太多,我不能相信没有他们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叙利亚的现状也超过了人的理解,请为他们祈祷。这儿的孩子们和母亲们承受了太多太多。圣诞快乐!谢谢你,愿爱与和平与你同在。”
有好几年的时间,孟晨说,她没有意识到她的生活有多奇妙。因为别人遇见像马克这样一些人的几率很低,她却在持续地遇见。她走的是一条完整的上坡路,遇见的是精神气质相投的人们。这些人不会轻易把目光从一个同类身上移开,而是会彼此加持。相反,她也看见很多人发生了断裂,被连根拔起,被移植到本不属于他的土壤,走的看似是一条主流的道路,其实是真正的孤军作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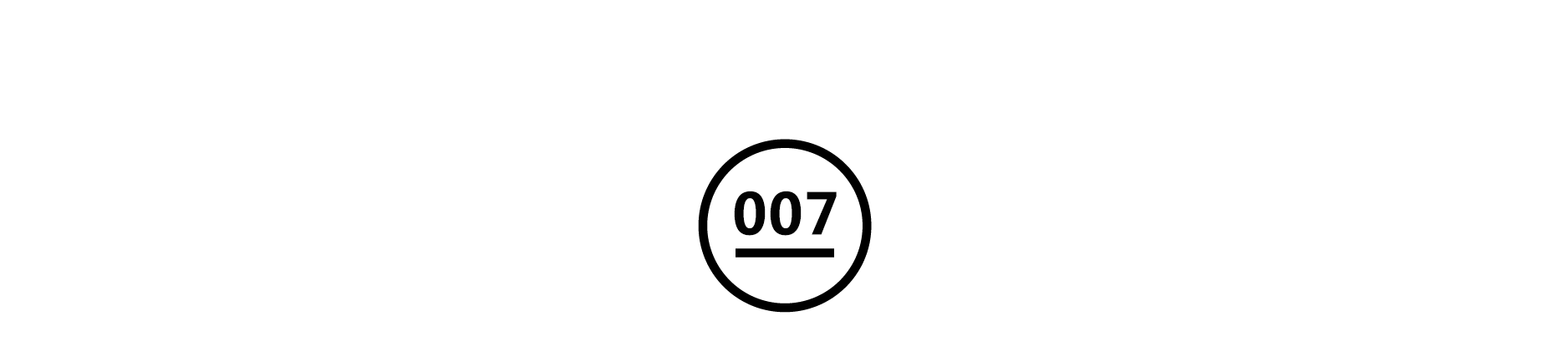
没有时间变老
28岁的那个夏天,孟晨去柬埔寨金边的政府部门做翻译。她发现公务员的文书写得完全不通,这才意识到他们是红色高棉之后的第一代大学生,受教育质量很差——此前,政权试图毁灭城市和文化,赶尽杀绝了上一代知识分子。周末她会骑一小时摩托车去甘丹省的贫民窟,给那里的孩子们做手工书和玩具。她学会了睡吊床,吃油炸昆虫、老鼠和蝙蝠,随身携带手电筒,因为金边随时会停电。

柬埔寨金边 视觉中国 图
后来,她辞掉翻译工作,去茶椒省的村子里做红色高棉幸存者的口述记录。那里有一个像集中营一样的屠宰场,埋葬了一千多人。受访者只能讲高棉语,雇来翻译的大学生英语不好,交流困难,孟晨感到自己常常在泥沼里打转,只能多做一些采集和保存的工作。她看见有的人否认,有的人闭口不言,有的人视而不见,有的人叫卖自己的历史以求当下的一条生路。
可能她是第一个来到这个村子的外国人,学生们见到她格外兴奋,要和她合照。合照地址选在村口一座高高的白塔前。她当时没留意,后来放大照片一看,身后的白塔里面,四层全是码得整整齐齐的骷髅头,那是特殊时期的被害者。学生们似乎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只把这沉默的白塔当作一个地标建筑。平时,这里是一个老年活动中心,人们在塔下跳舞。她想起金边屠杀博物馆门口的一位地摊画家,白塔中的骷髅都是他的同代人,他幸存下来,在博物馆门口叫卖自己手绘的黑白明信片。他指着明信片介绍说,这是他遭受刑讯逼供的场景,这是鞭打,这是强制劳动。他希望人们买一张,因为他是特别少见的幸存者。画画能救命,正是因为会画领袖像,他活了下来。
有一天,孟晨在《华盛顿日报》看到一篇文章,作者是国际医疗队(International Medical Corps)的一位心理学家,他在约旦北部边境沙漠的扎塔里难民营给叙利亚人做心理援助。孟晨查看了他的脸书和工作机构,把他名字与工作邮箱组合的几种可能排序罗列出来,抄送了几份邮件。约旦心理学家回复她,介绍了负责招聘的同事。面试通过后,孟晨接受对方安排的安全培训,需要通过一场笔试。题量很大,但很实用。比如,遇到炸弹,你该怎么办?
2019年5月20日,飞机落地约旦首都安曼。咨询机构提供了住处,室友是同事,一个在伊拉克分部工作的叙利亚女孩。她来约旦办签证,偶遇一个中国人特别兴奋,亲自下厨做了全素食的阿拉伯方便面给孟晨接风。吃饭时,她告诉孟晨,她出生于叙利亚一个中产家庭,拿了教育学硕士后,在学校教书,日子殷实安稳。2011年内战爆发,她全家和市民们一起步行穿越北部边境抵达伊拉克,伊拉克的难民营就是他们唯一的去处。谁都以为仗打不了多久,盼望回家,但是家没有了,战争还没有结束。在难民营,一个伊拉克小伙子对她穷追不舍,她现在正在恋爱。

约旦安曼 视觉中国 图
每天上午,孟晨搭两个小时的大巴到沙漠里,和同事们聚在一起喝上午茶,聊天,中午开始工作,平均每天接待四个来访的病人,三点多下班,搭大巴回安曼。办公室是铁皮活动板建造的组合房,像难民营的简易房一样,外墙上画了颜色鲜艳的阿拉伯风格的绘画。叙利亚难民最受关注,以至于阿富汗难民常常撒谎说自己是叙利亚人。
的确,不少国际慈善组织入驻了这里,硬件投入多,初级教育比约旦本地做得更好。但难民营归根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难民不能接受高等教育,也没有平等的就业机会,看不到人生向好的可能,只能悬浮在异乡等待,为了活着而活着。孟晨工作的心理咨询机构和别处也很不一样,做干预,给建议,要非常小心阿拉伯人的观念、习俗和宗教文化。尽管工作时间不算长,但她每天都在应对极端处境中的人。作为一个女性,她接待更多的也是女性。十三四岁的少女们来向她咨询,该怎样面对她们智力障碍的孩子。一位母亲说,这天早上,她的儿子杀了她的女儿。
回国后,孟晨在杭州一所大学做心理咨询的工作。之后,她辞职,去了一家专门收治青少年的精神病医院。再后来,她辞去医生职位,跑了重庆、怀化、大理、青岛、贵州、瑞丽、楚雄、桂林的中小学给学生们和老师们上短期的公益课程。晚上,她通过视频或电话接受一至两位患者的咨询,这给了她经济独立的保障。适逢疫情管控,她每一次出行必须按规定提交申请和核酸检测,但她不想因为怕麻烦而停在原地。从她发来的照片看,飞机、火车、地铁上往往只有她一个乘客。疫情解封后,她先去上海看望朋友,然后递交了去柏林的乌克兰难民营做志愿者的申请。
刚过完33岁生日,孟晨收到无国界医生组织香港办事处发来的邮件,祝贺她通过申请。她将去香港接受训练,半年后,派驻非洲或中东执行援助任务。
从去年冬天开始,她经过了历时四个月的笔试、分组面试和单独面试,“做梦一样的车轮战”。年少时觉得遥不可及的大梦,等到真正实现的时候,一切都显得自然,轻松,像讲讲日常的玩笑话。主持最后一面的印度尼西亚大姐问孟晨怎么找到组织的,她几乎没有见过大陆来的申请。她和孟晨聊起共同拥有的非洲经历,吃到想吐的炸绿香蕉啦,只有一个孔眼的旱厕啦,等等,最后印尼大姐收拢笑容,抒情地说,上一次,她在南苏丹出任务,看见医生助手、大厨和清洁工,每一个苏丹人从早到晚都在拼命工作。因为他们非常渴望改变族群的处境,改变孩子们的命运。印尼大姐说:“我有好多崩溃的时刻,但从来没有想过放弃这份工作。永远有不同的患者,不同的病症,我甚至觉得过去十年我没有时间变老,一直三十岁。”孟晨明白她在表达什么。
我很久没有见到孟晨了。她依然很忙,见很多的人,做很多的口述记录。听说她在等待出国的这段时间,去了洛阳和西安给乡村教师做工作坊,给舰艇上的海警做心理访谈,去了江西的寄宿学校、广东的小洲村、西藏的中小学,给孩子们做心理评估,同时参与中小学心智素养活动手册和安徽省小学生心理教材的编写。最新的近况是来自抚顺。她幽默地说,抚顺到处都是殡葬行业的广告,她坐的这辆公交车上贴着巨幅的福山公墓广告,好像这趟车是直接送她去人生的终点站。她还说,在东北做记录不需要自我介绍,你往那儿一坐,人家就唠起来了。坐在她身边的老奶奶说,抚顺人祖上多是山东的,闯关东呀,她做小女孩的时候,跟父母一步一步硬生生走千里,留在原地就要饿死。哪儿落地,在哪儿打生存战,不挑,她什么活儿都做。
孟晨听着,脑子里想着她的祖父。祖父也是山东枣庄人,只是没有随大流北上,饿的时候部队来了,他就跟着往南走,一路走到浙江。孟晨想想她的父亲,她自己,所谓物种起源,落地生根,天翻地覆的局面都只是一念的行动,此后独木成林,自然而然。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孟晨为化名)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