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郑振铎诞辰一百廿年︱吴真:1940年,见郑振铎一面有多难
1937年“八·一三”事变,上海沦陷,知识分子纷纷避难大后方,少数困处上海“孤岛”的文化人之中,时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长的郑振铎可算大名人。已在自由区的朋友,屡屡来信催劝郑振铎尽早西行,然而郑振铎却执意留居上海,秘密为国家搜求古籍。1940年1月至1942年12月,“近代以来最大的一次购藏文献行动”在郑振铎的带领下展开了。郑振铎和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长徐森玉等人,结成“文献保存同志会”,在日军爪牙密布的上海,秘密收购近五万册在日寇入侵之后流散沦亡的古籍善本,避免了中国文献落入敌手,流出海外。
郑振铎在抗战中所做的事情,只有少数三五人知道,当时外界对于郑振铎此举有过不少猜测;由于行动“万分机密、万分谨慎”,郑振铎亦无法向朋友表明心志。抗战胜利后,郑振铎才在《大公报》上连载的《求书是录》之中袒露心迹:“在足足的八年间,我为什么老留居在上海,不走向自由区去呢?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然而我不能走。许多朋友们都走了,许多人都劝我走,我心里也想走。而想走不止一次,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前四年,我耗心力于罗致、访求文献,后四年——‘一·二八’以后——我尽力于保全、整理那些已经得到的文献。”
老朋友叶圣陶直到1981年才大致了解郑振铎留守上海的原委:“现在看了这部集子里的《求书日录》才知道他为抢救文化遗产,阻止珍本外流,简直拼上了性命。当时在内地的许多朋友都为他的安全担心,甚至责怪他舍不得离开上海,哪知他在这个艰难的时期,站到自己认为应该站的岗位上,正在做这样一桩默默无闻而意义极其重大的工作。” (叶圣陶:《〈西谛书话〉序》)

2018年,恰逢郑振铎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及不幸遇难六十周年,各地在纪念郑振铎之时,这一段抢救文献的历史,自是屡被提及的不朽功绩。然而隔着近八十年的时光,今人很难真切地体会到 “孤岛”苦守所面对的危险与诱惑,就更难理解郑振铎的孤立无助与耿介自持。前段时间恰巧读到一本日本学者在侵华战争期间的日记——《苏州日记》(东京弘文堂书房1943年版,孙来庆翻译的中译本2014年由古吴轩出版社出版),作者高仓正三记录生命最后三年(1939-1941年)在苏州、上海等地的经历。由于是私人日记,文中述及郑振铎的相关细节颇为详实可信。有意思的是,郑振铎的日记或传记却无一字提及此人。两种文献互文对读,孤岛时期郑振铎的“困守”更显出不一样的意义。

“我特别想得到郑振铎先生的有关俗文学资料”
苏州沦陷的第二年,1939年9月27日,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的助教高仓正三抵达苏州。高仓正三是京都大学著名学者仓石武四郎的高徒,毕业后留在仓石身边担任研究助手。此前日本派出留学生大多到北京留学,学习和研究北京话的官话系统,高仓的老师——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就曾在北京留学两年之久。1939年,吉川幸次郎主持着京都研究所的《元曲选》读书会,经常遇到一些百思不得其义的方言语汇;仓石武四郎则正着手修订博士论文《段懋堂的音韵学》,急需段玉裁等一批清代江南学者的音训治学文献。在这两位学者的推动之下,各地方言的研究,尤其是中国江南文化的代表语言——吴语的文献搜集,就成为战时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的一个研究目标。被赋予厚望的助教高仓正三顺利获得外务省“在中国特别研究员”资格,派驻苏州搜集江南文献,学习吴语文化(钱婉约:《吴语研究的开拓者:高仓正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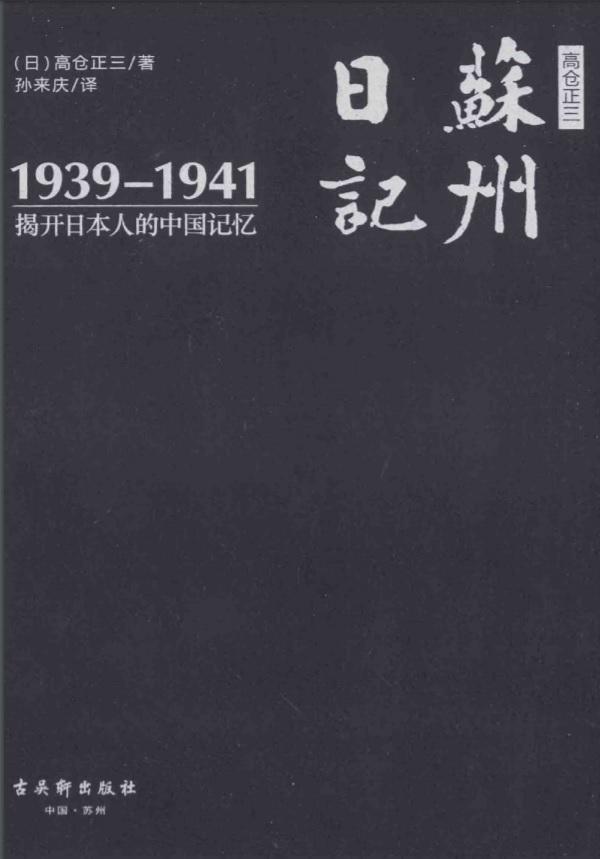
高仓正三早在京都求学时期就仰慕郑振铎,他把《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1937年秋郑振铎编撰的私人藏书目录)《佛曲叙录》(《小说月报》1928年第十七卷号外)等郑氏论俗文学的论著看得滚瓜烂熟,到了苏州之后,就拿着这两个郑氏目录,按图索骥,四处搜求戏曲弹词本子。“下午去觉民书店购买了几种弹词,三本《玉连环》的钞本看来特别有情趣。由于它是三本一套的,故还不太明白与郑振铎藏本的关系。”高仓正三知道郑振铎还留在上海,他在日记中多次表达结识郑振铎的迫切希望——“我特别想得到郑振铎先生的有关俗文学资料”,“想必在上海,特别是郑先生那儿有数目可观的资料”。
1939年10月13日,高仓正三拿着导师吉川幸次郎、仓石武四郎的介绍信,到上海的中国书店,“拜托与陈乃乾氏会面之事”,次日在中国书店见到陈乃乾,“从他那里打听到了不少东西”。这位陈乃乾(1896—1971)在上海文化界人脉颇广,主持编辑出版《古今杂剧》《清名家词》等十几部古籍善本,又曾在上海最大的旧书店——中国书店担任总经理。陈乃乾与日本学界联系颇为密切,东京的长泽规矩也、田中庆太郎,京都的吉川幸次郎、仓石武四郎,均与他保持鸿雁往来。1939年10月23日,高仓致信吉川幸次郎说:“前些天,冒着大水在上海只会见了陈乃乾氏,而您特意给我介绍的另几位先生只有等下次的机会再去拜访了。我想下次一定由我事先与陈先生和中国书店联系好,万无一失地和他们见面。”11月14日,又汇报说:“陈乃乾先生住天潼路慎馀里26号(请把此也转告给仓石先生)。”1940年1月20日记,“陈乃乾来函,主要告诉我他已从天潼路迁居到了法租界白泉部路渔阳里26号”。
可惜的是,陈乃乾与日本学者的这些往来,均不见于2018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的《陈乃乾日记》。该书收录陈乃乾上起1922年下至1966年的日记,陈先生在“文革”时期饱受折磨和非难,有可能保存日记时,故意抽去这些部分内容。从高仓正三的《苏州日记》来看,陈乃乾对这位日本后辈十分照顾,帮他在上海买书邮寄到苏州,高仓到上海六次,陈乃乾有三次请他吃饭。

陈乃乾也是郑振铎在“孤岛”时期过往最为密切的友人,1938年郑振铎为国家购得国宝古籍《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便是陈乃乾从中牵线的。郑振铎1943年的《蛰居日记》,几乎隔三两天就能见到陈乃乾的名字。既然陈乃乾与郑振铎熟识,高仓正三想当然地认为,很快就能见到偶像了,他在1939年11月14日信中跟吉川老师说:“这次要事先请陈乃乾和中国书店联系妥帖后再去,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无缘对面不相识
陈乃乾大概打了包票,一定能将高仓正三介绍给郑振铎。所以1940年1月27日,高仓正三兴冲冲地坐火车到上海,直奔中国书店,“陈乃乾赶来了,稍微寒暄几句,约好明天下午四时再见而告别。看来没希望见到郑振铎了”。不死心的高仓第二天中午又到中国书店,购买了十五元九角整的图书,又到附近的开明书店买书,回到中国书店等,但一直等到下午五点,还没见到陈乃乾。1月29日,高仓又到郑振铎常去的来青阁书店买书,兜到四马路,各个书店都看了看。当天回到苏州,他给哥哥克己写信抱怨说:“但一到上海,就使我悲观起来。首先是虽已拜托了陈乃乾给我联系见见郑振铎的面,但郑却避而不见。”
据郑振铎战后发表的《求书日录》,1940年的1月4日,郑振铎从朋友来电得知,“梅机关”计划搜捕的文化界救亡协会负责人十四人名单之中有他的名字,不得不离家躲藏。1月8日,又有日本宪兵到静安寺路庙弄的郑宅去搜查,结果无所获,当时郑振铎不在寓所。在这样紧张的危境之中,离家别居的郑振铎更加小心行事,怎么可能答应陈乃乾去见一个不知来历的日本年轻人呢?而且高仓正三到上海也不是纯粹的拜见偶像,他每次都要到特务机关去报到,1月29日,“借了小轿车去了特务机关”。
高仓正三到上海寻访郑振铎的这个时间,恰好是以郑振铎为中心的“文献保存同志会”秘密搜购文献的起步时刻。1940年1月19日,郑振铎与张元济、张寿镛合议,“自今以后,江南文献,决不听任其流落他去。有好书,有值得保存之书,我们必为国家保留之”(《求书日录》)。之后连续五天,郑振铎每天到中国书店、来青阁“阅肆”,1月26日下午,“至中国书店,无一书可取,又至他肆,也没有什么新到的东西”。高仓正三到上海那三天,郑振铎正在跟潘博山协商购入苏州刘氏藏书一事,无暇阅肆。高仓1月29日下午离开上海,郑振铎1月30日又到中国书店,买了一部明代《遵生八笺》。
早一天,或者晚一天,高仓正三都能碰上郑振铎,可是两人就这么“完美错过”了。
纵使高仓正三在中国书店撞见郑振铎,也有可能“脸盲”认不出来,因为郑振铎压根就不想被人认出来。
有一天,我坐在中国书店,一个日本人和伙计们在闲谈,说要见见我和潘博山先生。这人是“清水”,管文化工作的。一个伙计偷偷的问我道要见他么,我连忙摇摇头。一面站起来,在书架上乱翻着,装着一个购书的人。(郑振铎:《暮影笼罩了一切》)
这个专程到中国书店“偶遇”郑振铎的日本人,就是日本大使馆一等书记官——清水董三。此人精通汉语,日本重要人物与汪精卫会见,均由其担任翻译,他也是1939年8月成立的特务组织“梅机关”的头目,1941年之后兼任汪伪文物保管委员会研究部副部长。清水董三对中国小说颇有研究,1930年代,上海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在书店内不定期举办“文艺漫谈会”,清水董三亦名列出席者名单,内山在1955年撰文回忆道:“清水董三毕业于同文书院,也是同文书院的教授,是一个谈起《金瓶梅》一个晚上不睡觉也说不尽兴的主儿。”(内山完造:《内山书店与文艺漫谈会》,《我的朋友鲁迅》,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年)郑振铎正是洁本《金瓶梅》的出版者以及研究的先行者,于公于私,清水董三都想结识郑振铎,却在中国书店的咫尺之间,擦肩而过。这不得不让人感叹某些神奇的缘份,更要感叹郑振铎高明的“易容术”。
郑振铎从1923年担任《小说月报》主编之后,名声高涨,再加上具有辨识度的长相,早在1930年代就是公认的文坛美男子。吴梅的学生、著名学者卢冀野曾在《十日杂志》上发表《郑振铎先生》,赞美这位“现代型的美男子”:“乌黑的头发,高高的鼻子,架上一付不大不小的眼镜……微笑老是挂在路边,露出糯米似的一排牙齿。”唯恐读者不能想见郑振铎的美貌,文章还附上传主的高清大头照。

类似这样的郑振铎美男照,在1930年代的报纸期刊中还能找到其它的三五张。照片上的郑振铎,西装革履,高大威猛。然而抗战时期,郑振铎“换一身中装,有时还穿着从来不穿的马褂,眼镜的黑边也换了白边”(《求书日录》)。也许是这样的旧式文人样子,与之前的西式文人样子相差过大,以至于特务头子清水董三,在中国书店与郑振铎“对面不相识”。另据陈福康先生《郑振铎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7年),清水董三还曾托一个落水的朋友,企图以数额巨大的支票收买郑振铎,被郑先生大骂而走。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之后,郑振铎任教的暨南大学停办,为了抢救的文献及个人的安全,他不得不再次离家蛰居,易姓改名,“在外面住了近四年的时候”(《求书日录》)。汪伪政府企图拉郑振铎“落水”,他们摸透了郑振铎的生活规律,派出一个熟悉郑振铎长相的特务到上海执行绑架任务。以下是1943年重庆《中外春秋》第一卷第三期的一则报道《郑振铎在四马路赛跑》:
宁方敌伪慕郑振铎之名,亟思绑为什么文化工作的主委,特派樊逆仲云到沪寻觅。樊逆过去与郑相识,素知郑振铎有书癖,常常在四马路一带旧书铺,购买遗弃的孤本与珍本。一天晚上,樊逆在旗盘街转弯的弄堂口,遇见郑正在出神地翻阅旧书,樊连连拍其背脊,郑仍不理,樊又拍了几下,郑才微转其首,刮目相看,知是樊逆仲云,不作一声,立即拔步狂奔,樊逆亦不与语,只是跟踪追赶,像在四马路举行远距离赛跑似的。郑氏终于逸去,樊逆大呼懊丧不止。

中国书店上演“沙家浜”
正如汪伪特务所掌握的,抗战时期唯一可以邂逅郑振铎的地方,就是中国书店、开明书店、来青阁等旧书店。其中“偶遇指数”最高的地点,则非中国书店莫属。
1925年,金颂清在收得原“古书流通处”的存书后,在上海西藏路大庆里开设了一家名为“中国书店”的旧书店,专门经销古旧图书。因经营得法,中国书店很快成为上海书餮聚集的中心,“凡谈书林掌故的,总要谈到该书店,因该店专售古本线装书”(郑逸梅:《金祖同与中国书店》)。陈乃乾在1925年曾出任中国书店的经理,翌年离开。1937年以后,中国书店延请海上著名的旧书从业者——郭石麒驻店主持店务。黄裳在《记郭石麒》一文中回忆,“在上海买书十年,相熟的书店不少,其中颇有几位各有特点的书友……首先记起的是郭石麒”;“虽然他也靠贩书博得蝇头微利、养家糊口,却是循循有如读书人的人”,“他经营过中国书店,在旧书业中很有地位,他的鉴别能力高,同业中有拿不准的版本问题总是请教他”。
郭石麒与郑振铎私交甚笃,郑曾在明刊《乐府先春》题跋中写道:“石麒为书友中忠厚长者,从不欺人,书业中人无不恃为顾问。劫中余闭户索居,绝人世庆吊往来。惟结习未除,偶三数日辄至古书肆中闲坐,尤以中国、来青二处踪迹为密。”清水董三肯定也是事先掌握了这一个规律,才到中国书店去打听郑振铎的下落。在那次中国书店历险之后,郑振铎就吩咐中国书店的伙计们:“以后要有人问起我或问我地址的,一概回答不知道,或长久没有来了一类的话。为了慎重,又到汉口路各肆嘱咐过。我很感谢他们,在这悠久的八年里,他们没有替我泄露过一句话,虽然不时的有人去问他们。”(郑振铎:《暮影笼罩了一切》)

中国书店在上海“孤岛”时期曾是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哨站,少东家金祖同在1931年赴日本留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金祖同在七月下旬跟随郭沫若回国。郭沫若在中国书店住了数天,八月下旬与夏衍等创办了《救亡日报》,借了中国书店一间偏屋作为编辑部。叶灵凤赞道:“年轻的金祖同,在当时日本人横行的租界环境下,敢于借出他的书店余地供《救亡日报》使用,实在是很勇敢的行动。”(《金祖同与中国书店》)
由于这样的抗日背景,中国书店曾遭受日方的搜查,郑振铎在1945年底发表的《暮影笼罩了一切》记道:“有一天到了中国书店,那乱糟糟的情形依样如旧。但伙计们告诉我:日本人来过了,要搜查《救亡日报》的人,但一无所得。《救亡日报》的若干合订本放在阴暗的后房里,所以他们没有觉察到。” 中国书店屡遭日军搜查,却可以一再化险为夷。从《苏州日记》所见,“孤岛”时期,暗地抗日的中国书店,明里与日本人的生意往来还不少。
高仓正三1939年9月25日第一次到上海,第二天就到中国书店买书,并委托该店为他搜罗小说弹词等书籍,定期将书籍邮寄到苏州给他——“我请中国书店先替我把《王国维遗书》买下,并请他们在方便时给我寄来”。高仓在上海大量购书,太重拿不动,也会请中国书店帮他寄回苏州。这些业务往来采用的是民国旧书业普遍的赊账方式,一年之中的“三节”(春节、端午、中秋)统一结账。1941年1月,病榻上的高仓正三收到中国书店寄来的催款单,“这是合理的请求,我曾写信给渡边(注:渡边幸三,“满铁”上海支所主管,京都大学东洋史的毕业生)请他帮我还债,但看来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了。” 2月10日,“好不容易请渡边在阴历年后先替我垫付了给中国书店的四十九元的借款”。
中国书店还有一项为外埠客人订购书籍并邮购的业务,吉川幸次郎早在高仓正三到中国之前,即在上海亚东图书馆、中国书店等处邮购了一批书,寄放在满铁上海支所的渡边幸三处,高仓到上海之后,“马上请他通过中国书店给您邮去”(1939年11月14日致吉川信)。吉川幸次郎因在准备元杂剧的博士论文,需要郑振铎的《西谛目录》一书,高仓正三1939年12月19日信中说:“请允许我通过上海的中国书店给您邮去以略表薄意。”
高仓正三每次到上海,都会到中国书店去与陈乃乾、罗振常(罗振玉之弟,上海蟫隐庐书店老板)、小竹文夫(同文书院研究员)、渡边幸三等朋友会合。有时上海的朋友要通过高仓转送书物到京都大学,也会留在中国书店托给他。1940年5月15日,章太炎弟子潘承弼(景郑)到中国书店,把一本章太炎的《春秋左传读》留给高仓正三,委托他寄回京都的吉川老师。1931年2月,吉川幸次郎到南京、苏州等地,曾拜访黄侃、吴梅、张元济,并结识了潘景郑。黄侃病故之后,吉川幸次郎于1935年11月2日致信潘景郑悼念黄侃(《与潘景郑书》,《制言》第五期,1935年)。上海沦陷时期,潘景郑与其兄潘博山一直留守上海,并与郑振铎多有往还。潘景郑晚年自述:“沪上奇书,时有一二散在飞凫人手,余每遇及,必为先生居间购求,以是过从较密。”(潘景郑:《郑振铎先生遗札跋》)。高仓正三先后六次到中国书店,通过中国书店联系上潘景郑、陈乃乾等郑振铎的好友,却始终与郑振铎“缘悭一面”。

1942年停业之前,中国书店不仅是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哨站、日本人买书的首选地,还是伪北平的书商到上海搜书的聚散地和中转站。
几乎每一家北平书肆都有人南下收书。在那个时候,他们有纵横如意、垄断南方书市之概。他们往往以中国书店为集中的地点。一包包的邮件,堆得像小山阜似的。我每次到了那里,总是紧蹙着双眉,很不高兴。他们说某人得到某书了,我连忙去追踪某人,却答道,已经寄平了,或已经打了包了。寄平的,十之八九不能追得回来,打了包的,有时还可以逼着他们拆包寻找。但以如此方法,得到的书实在寥寥可数,且也不胜其烦。(《求书日录》)
在中国书店,郑振铎痛心地看到北平的旧书店大肆搜购江南文献,辇载北去。这些“平贾”的背后,是伪“满洲国”、敌伪华北交通公司,汉奸梁鸿志、陈群等人,以及美国哈佛燕京学社。1938、1939的两年之间,江南沦陷区的古籍大多流落到美国人、日本人和汉奸手上,郑振铎忧心如捣地感叹:“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郑振铎:《〈劫中得书记〉序》)他联合了张元济、张寿镛等学者向重庆国民政府上书陈情,要求政府尽快拨款遏止古籍北流。
1940年1月,获得重庆政府资金支持的郑振铎,开始以中国书店为据点,“阻挡平贾们不将江南藏书北运”。1月25日记:“下午,赴中国书店等处,见平贾辈来者不少,殆皆以此间为‘淘金窟’也。今后‘好书’当不致再落入他们手中。”郑振铎与中国书店掌柜郭石麒谈妥合作细节,委以收购江南藏书家成批藏书的重任。在之后的近二十个月之中,凡有江南旧家售出古籍,中国书店第一时间告知郑振铎,并代为评估旧家藏书的售价。比如1940年3月底购进“铁琴铜剑楼”所藏元明刊本廿种,“系由中国书店估价,而与瞿凤起君直接商妥”(《上海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一号工作报告书》)。同时中国书店也介绍杭州、苏州、嘉兴等地的江南故家藏书,收取一定的佣金。1940年3月,中国书店经手的杭州胡氏七百八十种古籍,共价六千元,按照旧书业行规,中介佣金一般是售价的一成,但中国书店仅收四百元,郑振铎写给张寿镛信中说:“如此批书佣金仅为四百元,倒还在情理中。”(1940年3月15日信)
上海大藏书家张葱玉传出适园藏书待售消息后,同时有两家书商在竞争中介权:一是孙伯渊(即1938年将《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以九千元售与郑振铎的苏州书商),二是中国书店的郭石麒。郑振铎1940年5月15日致张寿镛信中提到:“盖孙贾利心过重,平空加价不少。中国则甚为稳健公平也。除取若干佣金外,决不会妄行加价也。”郭石麒的公道,在上海旧书界是有口皆碑的,黄裳就说,“从他手里买书,从来不必还价。也不必担心本子的完缺、版刻的迟早,这些他都是当面交代清楚,完全可以信赖的”(黄裳:《记郭石麒》)。
不妨想像一下当年“淘金窟”中国书店的情景:人来人往的店铺内,有前来淘书的北平书商,有前来购书的高仓正三们,有前来打听郑振铎下落的日本密探,还有乔装打扮的郑振铎,与北平书商比赛着谁捷足先登获得珍贵古籍。掌柜郭石麒犹如《沙家浜》春来茶馆的阿庆嫂,“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日本人的生意他做,伪北平同行的生意他也做,至于郑振铎介绍过来的重庆政府的生意,他更是下力气地做。
不知身是敌的敌人
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二人1928至1931年留学北京之时,郑振铎还在上海,现存三人的日记及著述中,均找不到三人相识的记载。不过仓石、吉川二氏的学长,著名的文献学者长泽规矩也,与郑振铎相知颇久。长泽1962年在《日本经济新闻》发表的回忆文章称,战前郑振铎与他书信往来频繁。陈乃乾与长泽也是多年好友,1930年,陈乃乾特地将世间罕见的清康熙陶瓷活字版《周易说略》冲晒成书影照片,邮寄给长泽。“七·七事变”之前,中国的学者大多与日本同行保持互通信息与互访的关系,因此高仓正三想当然地认为,可以凭借吉川、仓石的老关系,再加上陈乃乾的推荐,见到郑振铎。他乐观地向吉川幸次郎请缨:“如果在郑先生那里有什么急于了解、调查的以作为参考的话,请来信教示。”同时他又抱怨在上海的日本同行完全不跟郑振铎等留守上海的文化名人建立联系:“东亚同文书院的各位也没有去与上海的这些人打交道,使我多少感到遗憾。他们未必就是关紧大门不让人进、不好商量的人。”(1939年11月14日致吉川幸次郎信)
这句话显示出高仓正三的政治无知。他提到的“东亚同文书院”即日本东亚同文会于1901年设立的“书院”,1938年后蜕变为与“满铁”调查部并称的日本情报机关。东亚同文书院在上海组织情报搜集与文化间谍活动,也负责向特务机关“59号”提供不合作的知识分子名单。东亚同文书院当然不是没有打算拉拢郑振铎,主管该书院的清水董三就曾到中国书店去找郑振铎。

天真的高仓正三还以为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势之下,中日学者仍可以保持战前的亲密合作。事实上,“七·七事变”之后,文献保存同志会各成员与日本学界的关系皆降到冰点。张元济与长泽规矩也在战前联系密切,张氏一方现存共有十八封信,1938年5月4日张元济致长泽第十九封信,也是最后一封信,开头第一句便是,“时事至此,无可告语,故久未通讯”(《张元济全集》第十卷)。
与陈乃乾、潘景郑不同,郑振铎刻意避免接触日本人,因为他知道两国交战,势不能念以往旧情。1941年之前,郑振铎是“抗敌救亡协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上海全面沦陷后,他化名“陈思训”,以“文具商”的身份,蛰居于上海高邮路一小楼内。他在开明书店遇到东京大学教授盐谷温的女婿,“嘱肆伙不声言,乃得不交一语而去”(《蛰居日记》,1943年6月23日)。

高仓正三似乎从未考虑过中国学者“避而不见”的原因, 1941年2月10日,躺在病床上的高仓还跟友人抱怨错过了结识闻一多的良机:“原先在武汉大学任教的闻一多,现任武昌武汉政府民政厅的主任秘书,而且在去年我们去武汉时就在了。当时因不知此情,为错过了那次见面的机会而感到惋惜。”
细读《苏州日记》就会感受到,在高仓正三“天真”的语调之下,透出历史的森森寒意——侵略者完全不把自己视作被侵略者的敌人,而且明明是侵略者,却完全没有意识到在当时局势下,哪怕是主观上出于学术意图的结识与见面,也会给被侵略者带来压迫。
高仓正三到中国的任务之一是搜求文献,恰恰在这方面他就是郑振铎及其“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对手。高仓正三与郑振铎始终没有见过面,双方在两批藏书上曾经有过的争夺,今天看来,就好似京剧《三岔口》,一场黑暗中的打斗。
民国名士刘公鲁,继承其父刘世珩的“玉海堂”藏书,又自己搜罗戏曲珍本,聚为“暖红室”藏书。他晚年定居苏州大太平巷,1937年底日寇侵略苏州时遇难,藏书陆续散出。高仓正三抵达苏州即留意刘公鲁藏书的去向,1939年12月18日,他拜访日军驻苏州的辻部队的长官,约定一起到刘家去查看藏书。第二天,“辻部队长夜里来电告诉我:书在三天前已在北平卖完,现别无它法”。高仓当天写给京都的吉川幸次郎报告此事,抱怨晚了一步,没能获得刘家藏书。其实,这批书早就秘密卖给了苏州古书商人孙伯渊,被运到上海。论留意刘家藏书,郑振铎要晚于高仓正三,但是他从潘博山(潘景郑的哥哥)那里得到准确的书讯:“(孙)本来经营字画古董,气魄颇大,故能独力将公鲁书拿下。恐怕又要待价而沽了。”(郑振铎1940年1月4日日记)1940年整个1月份,郑振铎都在为收购刘公鲁藏书而奔走,甚至还请动了七十多岁的张元济一起去孙伯渊处看书。高仓正三到中国书店去找郑振铎的时候,一定想不到,他的偶像正在为重庆政府收购一个月前他错过的那批珍籍。
另一场争夺则围绕着民国规模最大的私人藏书楼——嘉业堂。1940年2月1日,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的所长狩野直喜,向高仓正三下达命令,要求他参与上海满铁支所的嘉业堂调查班。伪满铁大连图书馆已经觊觎嘉业堂藏书长达两年之久,大连的满铁总部派出田中老人到上海洽谈收购事,高仓正三2月1日到上海参加这次碰头会,正准备启程到南浔,日方军部背景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突然发难,不许满铁插手。日方两个机构陷入对峙局面,高仓于2月13日记曰:“渡边寄来了延期去南浔调查的通知,对此,我茫然不知所措。”
高仓正三所代表的日方机构停下脚步,给了郑振铎“后来居上”的机会,4月2日,郑振铎致张寿镛信中说,“嘉业堂书甚可危”。他通过各种渠道接近嘉业堂主人刘承幹,经过一年反复磋商谈判,文献保存同志会最终以二十五万元秘密购下一千二百余种嘉业堂藏书。

1941年3月13日,高仓正三病逝于苏州盘门新桥巷的苏州医院,享年二十八岁。这一天,他慕名已久却又无缘得见的学术偶像郑振铎,刚刚整理完嘉业堂藏书的待购书目:“一年以来,瘁心力于此事,他事几皆不加闻问。殆亦可告无罪矣。”(郑振铎1941年3月13日致张寿镛信)
高仓正三与郑振铎,未能相见于中国书店,亦未曾相见于争夺刘公鲁或嘉业堂藏书的场合。从日本学人的角度来看,高仓正三对偶像的“求之而不得”,正是这个年轻人孤身一人到异国求学“天涯孤独”(吉川幸次郎:《苏州日记·跋》)的一个象征。然而如果我们站在今天的“全知视角”,以“后见”观之,不禁要为郑振铎与高仓正三的每一次擦肩而过,捏一把汗。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