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夜读丨县城里,我的单身小姨
周一,我和小姨匆忙见了一面。她独自在上海奔走一整天,采买一日三餐和生活用品,帮生病的大姐——我的大姨,打理接下来一个月的治疗事宜。
这个季节的上海昼夜温差大,我们见面已是夜深。小姨穿着一件驼色风衣,在夜色中更显消瘦。回到酒店后她难掩疲惫,但聊起大姐好转的病情,又眉飞色舞起来。她对即将尝试的新疗法充满信心,尽管明天才同医生商量细节。
小姨调侃自己的年龄已经禁不起这样折腾,但在我看来,小姨长得漂亮,打扮讲究,性格开朗大方,也喜欢小孩子,经常带我们买好吃的、好玩的。
小姨是农村出身,在本地的大学毕业后,回到老家的县城,进入体制内工作。这在家乡人眼里,是相当体面的身份。但20多岁时,小姨没有结婚生子,甚至没有谈恋爱,这在县城是一种叛逆。我们那儿的大多数女性,过了30岁,似乎就失去了婚恋的选择权,只要完成“任务”,嫁给谁都足以告慰祖辈。相当多的女性,过了所谓“适婚年龄”就没得选,只能“向下兼容”。
我小的时候,很多亲戚都操心过小姨的终身大事,她频繁被家人、同事安排相亲,但都以失败告终。和她相亲的男性,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有的离异带娃,有的刚见面就希望她将来辞职在家带孩子。“压力很大,相亲失败的话亲友可能会在背地说闲话。”她告诉我。
比起相亲,小姨更喜欢周末出去爬爬山、练练瑜伽,哪怕只是呆在家里看书休息,而不是和那些不喜欢的异性谈那些无聊的话题。
我曾问小姨,为什么不拒绝相亲呢?“熟人社会,不去的话就欠下人情了。”她露出无奈的表情。
有人说她眼光高,谁也看不上;不喜欢县城那一套职场规则,工作始终不温不火地做着……这些县城职业女性面临的境况,小姨一个都没逃过。有的女性选择离开家乡,去更大的城市生活。但在父亲离世后,从小就是乖乖女的小姨更希望留在家乡,方便照顾亲人。
随着时间的流逝,周围人的声音慢慢弱下来。小姨已经三十过半,已经对婚恋话题脱敏。她成为大家口中的“大龄剩女”,家人不再催婚,相亲频率也大大降低。但即便如此,关于她的流言蜚语从未停过——只不过大家会在她面前有意避开结婚这类话题,仿佛这会使她的自尊心受伤。
在家里,和她同龄的很多青年人都外出打拼,多年后也步入结婚生子的轨道。逢年过节,小姨会帮他们带娃,也常和他们打成一片。有几次过年,她因为单位值班没能回老家,立马有人揣测她是因为没结婚才不敢回家。在老家,有关小姨的话题几乎只与婚恋有关。
而在我眼中,小姨始终是美丽和独立的象征。一直单身,也并不意味着她不愿意步入婚姻殿堂。在那个被婚姻焦虑包围的环境中,她坚持阅读、运动,保持着对爱情的期待。比起初次见面就谈婚论嫁,她更希望两个人慢慢恋爱、静静生活,因为她始终认为:“结婚是白头偕老的大事。”
去年底,小姨的姐姐在讲台上突发脑出血,所幸抢救及时,但仍有半身瘫痪和丧失语言能力的风险。整个春节,一家人都在为大姐的病情劳碌,四处求访名医。小姨承担起大很多照料病人的活:一遍一遍地同大姐说话,即使很多时候得不到回应;帮助她活动身体,进行漫长的康复训练。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每天奔波在单位与医院的两点一线中。
经过初期的治疗,大姐的病情好转,家人决定送她到上海的医院。在姐夫和大哥都因工作无法抽身时,小姨再次承担起护送病人的责任。到上海的第二天,她事无巨细打点好所有事务,又匆匆回去上班,等到下一个假期再来探望。
她相信这次治疗能够让大姐康复如初,重新回归讲台、回归家庭。突发的事故也让人们暂时忘却了这个“大龄”未婚女性,更多是把她视为离家近的“满女”(湖南话中意为最小的女儿),肩负着照顾长姐的责任。
或许在我们那样的县城里,会有越来越多与小姨相同处境的女性,她们用一种温吞的方式抗争着。她们有文化,经济和人格独立;她们对恋爱和婚姻不愿将就,不愿屈从身边人的焦虑情绪;她们在自己的轨道里用力生活,大多数时候只展示坚韧的一面;她们留有先辈的牺牲精神,在家族中挑起责任……但我相信,未来她们将不再局限于“县城体制内”的标签,而是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的:不必行色匆匆,不必光芒四射,不必成为别人,只需做自己。
我和小姨的谈话结束在第二天清晨。看望病人过后,她送我到地铁站。医院旁的人行道有些狭窄,她却丝毫不感到局促,从容地大步向前走着。
行道树新长出的叶片间漏出阳光,小姨对我说:“下次要来体验一下烟雨江南,你带路。”“好,一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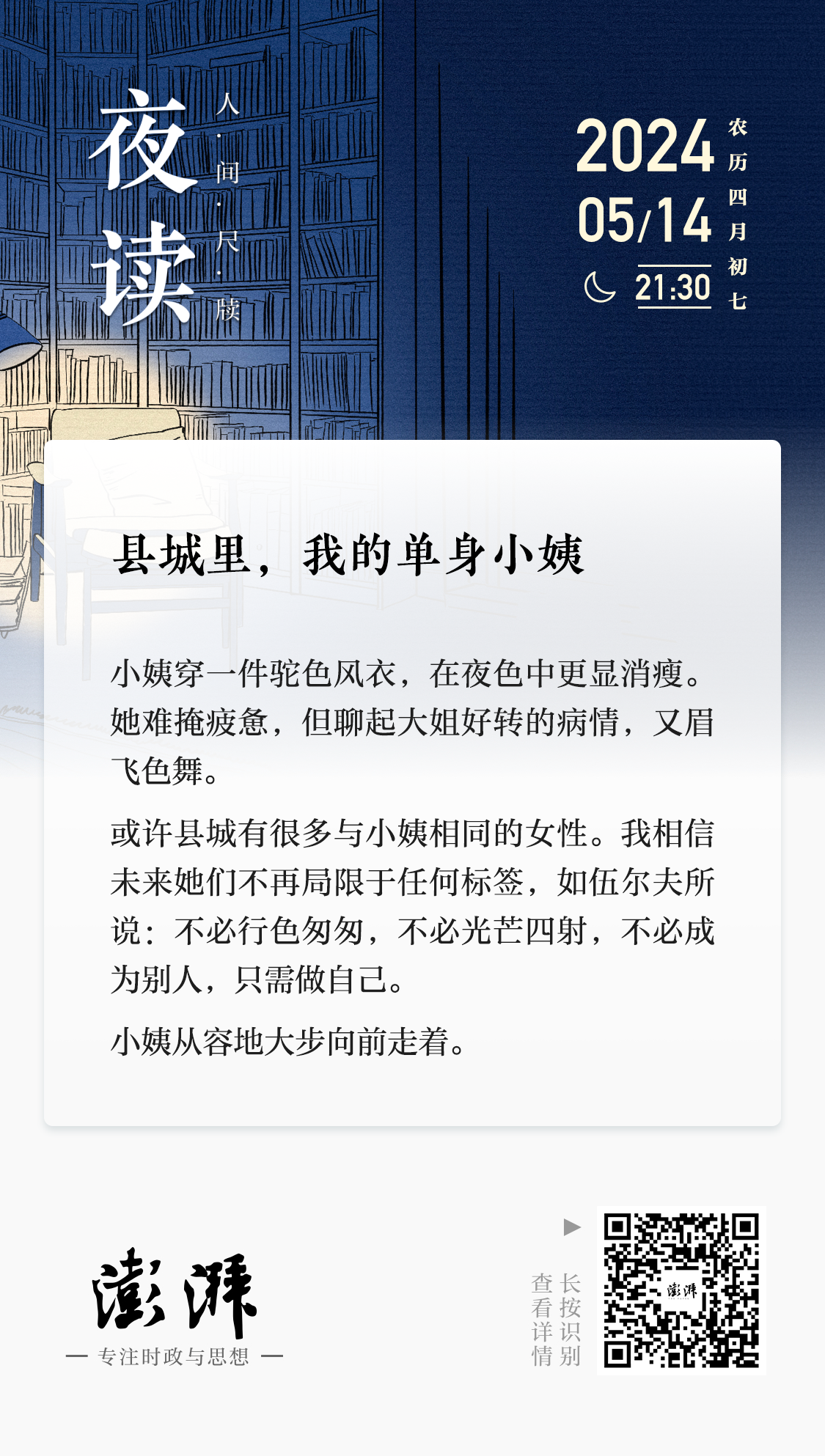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