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普通人的自然|东亚鸟保推手:从东方白鹳开始的跨国合作
2023年最后一个工作日,我收到了湿地保护界朋友的消息,告诉我今年有30多只东方白鹳在后海湾(深圳湾)上空被观测到,还有三只东方白鹳在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停留,叫我快来看看它们。

鸟类保护学家陈承彦。
其中一只东方白鹳背的追踪器显示,这三只鸟一路向南,历时47天,从黑龙江洪河保护区飞到了香港米埔。

2023年底、2024年初于香港米埔拍摄到的3只东方白鹳。图片除特殊标注外均来源于受访者
东方白鹳为冬候鸟,夏天主要在中国东北、内蒙古、俄罗斯毗邻中国的地区以及日本、朝鲜等地繁殖,冬天迁徙到华东、华南区域,主要集中在江西鄱阳湖、江苏扬州等地。很少成群飞往香港。而它们这次来的路线,与我去年合著出版的一本东方白鹳自然科普绘本《向南飞 向北飞》里描绘的路线“不谋而合”。这让我有些激动。

《向南飞 向北飞》绘本里东方白鹳兄妹飞到香港深圳交界的后海湾。王婷 图
这本绘本的灵感,源自上世纪的一则观鸟新闻:1990-1991年冬季,香港曾有121只东方白鹳在米埔停留过冬,景象令人惊叹。此后再无如此规模的东方白鹳群体来到香港或后海湾(深圳湾),只有零星几只‘’迷鸟‘’。
为什么当时这么多东方白鹳出现在香港?这121只东方白鹳是哪里来的?为什么后来东方白鹳又不常来了?带着这些迷思,我为绘本创作了一条半虚构的故事线。
更让我激动的是,几天后,我见到了1991年这则观鸟新闻的亲身经历者: 陈承彦(Simba Chan)。
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首位华人志愿者
一个午后, 我在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游客中心门口见到陈承彦。他面色古铜,身穿休闲衣,背着双肩包,头系一条日式头巾,胸前挂了一副望远镜。他似乎充满着年轻活力,冲我们笑,眼中透着孩童般的好奇和纯真。
陈承彦是米埔自然保护区1987年成立时的首位教育培训主任,也是一位鸟类保护学家。他曾在亚洲多个国际鸟类保护机构任职,目前担任日本鸟类研究协会嘱托研究员,专注保护迁徙鸟类和国际合作。

陈承彦带我们去了1990/91年发现东方白鹳的水沟。王婷 图
回忆起与米埔保护区的结缘,陈承彦深感自豪。20世纪70、80年代初,香港从事野生动物保护的圈子中,几乎都是来自欧美的外国人。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许多大学甚至还没有相关专业。陈承彦因为从小热爱野生动物,选了最接近的生物学专业。1980年,还在读大学的他,得知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兴奋地直接跑去敲开了他们的办公室大门,询问他们在香港准备开展哪些项目,并自荐要提供帮助。由此,陈承彦成为第一位加入WWF-HK义务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香港本地华人,参与了大量的前期科研和鸟类环志工作。

1992年7月8日,陈承彦在俄罗斯阿穆尔州兴安斯基保护区,协助一个日本和俄罗斯的鹤类研究组捕捉白枕鹤作卫星追踪
鸟类环志(Bird Ringing)是通过标记个体,研究鸟类生活史、种群动态趋势——特别是鸟类迁徙规律的一种简便方法。最早的系统性运用是在1899年,丹麦的中学教师和业余鸟类学家汉斯·莫特森(Hans C. C. Mortensen)为捕捉到的鸟戴上写有地址和编号的特制铝环。其他人发现戴有这些铝环的个体后,会写信告知汉斯具体时间地点。汉斯则将这些信息在报纸上发布,以鼓励更多人效仿参与。到了1930年左右,几乎所有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都有了自己的鸟类环志中心。汉斯的环志模式至今仍在全球使用。
陈承彦指着米埔保护区里的一座绿色铁皮房子说,这就是他们最早从事环志工作的地方。林栖鸟类的环志,需要清晨5点之前,在树上布置好网;对于水鸟,则需在半夜时分在基围塘上设置更大的鸟网。工作人员会定期检查网,将鸟儿从网上解救下来,然后带到这个房子里,为它们佩戴环志并进行标记,最后放飞回大自然。

米埔里早年进行鸟类环志工作的场所。王婷 图
虽然环志工作辛苦,但陈承彦每次都兴奋不已。因为,有些鸟类如半蹼鹬,因为稀有很难被观察到,进行环志时才有机会近距离观察。环志工作还可以与前瞻性的研究结合。陈承彦还记得,1989-1990年与香港大学合作进行环志工作时,就做了野鸟禽流感的监测,比病理学家在1996年开始关注禽流感的全球肆虐早了六年多。
1987年米埔自然保护区的教育中心成立,陈承彦正式加入了WWF香港分会,除了参与一线鸟类保护工作,他还作为米埔第一任培训主任,定期为内地的湿地保护管理人员提供培训。米埔自然保护区因为靠近城市,面积小,陆地化进程快,很早便参考英国皇家鸟类保护协会,制定了主动栖息地管理模式。

1987年秋天,米埔环志的半蹼鹬。
追寻东方白鹳之谜
谈起1990年代第一次发现东方白鹳的记忆,陈承彦仍历历在目。
他回忆道:“那是1990年11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有一位工人激动地跑来告诉我,米埔出现了一大群东方白鹳。起初我还以为他搞错了。我说,那可能是苍鹭吧?也许因为光线,你觉得它们看起来很白?然后,我和工人一起出去看,结果让我们大吃一惊。在米埔渔护处入口前的水沟里,竟然站着40多只东方白鹳!我立刻联系了香港的鸟类观察者,大家都认为,它们可能是短暂停留。然而,这群东方白鹳一直在香港米埔越冬,直到1991年3月才离开,我们总共观测到121只。”

1990年冬季在米埔16/17塘的东方白鹳。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大群东方白鹳来到香港?这个问题萦绕在陈承彦心头。他表示,1990年代东方白鹳已知总数在2000~3000左右,121的数字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为了追溯源头,陈承彦写信给许多国内已知的东方白鹳栖息地,如鄱阳湖、东洞庭湖和盐城等地,以确认它们是否从某个保护区“逃逸”而来。那是在电子邮件普及之前,一封封纸质的信构建起了香港与内地各个保护地的联系。
遗憾的是,最终大家未能找到哪里有大量东方白鹳“出逃”。陈承彦猜测,1990年代初中国大陆没有兴起观鸟热,在很多地方,可能当地居民知道存在东方白鹳,但没有专业的保护人员做记录。
尽管未能找到源头,陈承彦却得以有机会对停留在米埔的东方白鹳进行了长期观测记录,包括:它们在米埔栖息在哪里,吃些什么;全球的东方白鹳有多少,在哪里繁殖和越冬?他关于东方白鹳冬季状况的文章,发表在香港观鸟协会1990年的年报中,为他的人生带来了重大的转变。

1992年7月4日,参会人员从哈巴洛夫斯克出发的大合照。
陈承彦的文章引起了国际鹤类基金会现副主席吉姆·哈里斯(Jim Harris)的注意,他邀请陈承彦在1992年在黑龙江/阿穆尔河国际鹤类鹳类大会上做汇报。会议在俄罗斯阿穆尔河上的一艘大船上举行,汇集了来自俄罗斯、中国、日本、韩国和美国等地的鹳类研究专家,讨论东北亚地区鹤类和鹳类的保护事宜。
陈承彦除了完成自己的汇报外,还发现会议的中文翻译不准确。他多次纠正,以避免给从中国来的专家们带来不准确的信息。因为精通英语、中文、日语和俄语,陈承彦在会议上“出了名”。大家对这么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感到惊讶,他不仅具备专业的鸟类保护知识,还对鸟类保护事业如此热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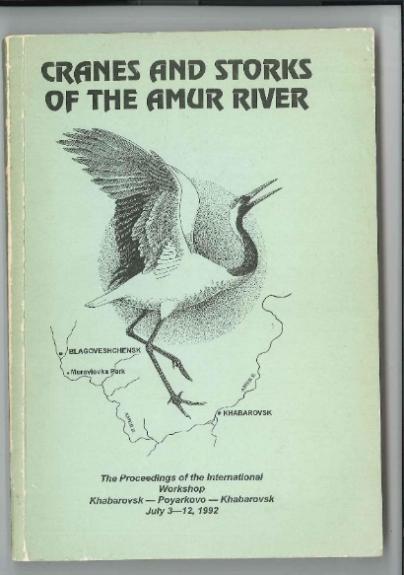
1992年国际鹤类鹳类大会的会议论文集。
亚洲鸟类保护国际合作网络的崛起
虽然鸟类保护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的欧洲,英国的皇家鸟类保护协会(Royal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Birds)1899年成立,但国际上广泛关注到鸟类保护,是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环保热潮开始的。那个年代《寂静的春天》一书出版,引起人们对DDT和环保的关注。1961年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成立,1971年拉姆萨尔湿地公约的制定,1963年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通过等,让人们开始关注鸟类的数量减少和栖息地的破坏。
20世纪90年代,是整个亚洲地区鸟类保育和研究起飞的年代。日本的鸟会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探索保护的问题,日本野鸟会和国际鹤类基金会最早开始合作,对候鸟(例如鹤类)进行研究保护,也尝试联系亚洲各国。随着1990年代亚洲各国的逐渐开放,亚洲建立了各级的鸟类保护组织,并逐步加入国际鸟类保护合作网络,1996年建立了MWCC(迁徙水鸟保护委员会)和鹤类,鴴鹬,雁鸭三个东亚区的网络【即现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伙伴关系协定(EAAFP)的前身】。

2001年6月5日,陈承彦在东京举行的亚洲鸟类红皮书出版仪式上致辞
陈承彦1995年赴日加入日本野鸟会工作。所参与的第一个大的项目是编写亚洲鸟类红皮书。以往两部红皮书(非洲和美洲)都是由国际鸟盟的前身国际鸟类保护委员会(ICBP)编写,但亚洲红皮书的编写工作,日本野鸟会和国际鸟盟认为,应该鼓励亚洲各国的鸟类学者和保育工作者主动带头执笔,不再全由外人包办,借此提高各国对保育工作的重视。亚洲各国都成立以本地学者为主的编写小组,不再“被代表”。于是,陈承彦与北京师范大学著名鸟类生态学家郑光美教授沟通,1996年7月底在呼和浩特召开了亚洲鸟类红皮书的中国大陆编委会议。
红皮书类似现在的保护红色名录文件。当时的编写者主要考虑以下三点。第一,先要收集信息,确定在亚洲地区有什么鸟类是受到绝种威胁的。第二,尽量找到这些鸟类的资料,因为物种共有两三百种,工作量繁重,从1996年开始,他们几个人写了5年。第三,他们觉得,红皮书不只是一个文献,还应落实到保护行动上。于是,编委们与保护迁徙野生动物物种公约(CMS,又名:波恩公约)合作,找了勺嘴鹬、黑脸琵鹭、中华凤头燕鸥这三种迁徙性的水鸟,编写了一个国际行动计划。

1998年8月陈承彦在剑桥国际鸟盟总部编写亚洲鸟类红皮书
黑脸琵鹭因扁平如汤匙状的长嘴,与中国乐器琵琶极为相似而得名。它繁殖于中国辽宁省、朝鲜半岛北部等地区,越冬南迁,在中国一般为冬候鸟,越冬于广东、福建、海南、香港、台湾岛、澎湖列岛等地的内陆湖泊、河口、芦苇沼泽等地带。它曾是中国沿海地区常见水鸟之一。后因战乱、猎捕、沿海地区人口激增和污染等,导致栖息地锐减。1989年,简立理 (Peter Kenerley) 在香港观鸟会鸟报上公布仅记录到288只黑脸琵鹭。人们第一次意识到,这种鸟类在东亚地区的生存现状不妙。

黑脸琵鹭 图: Ian Davies
1994年8月,德国罗森海姆Rosenheim 举行的国际鸟盟评议会ICBP第21届国际大会,欧美和亚洲的学者首度提出加强国际合作、共同保育黑脸琵鹭的倡议。1995年,由台湾著名鸟类学者刘小如老师牵头,陈承彦参与撰写的第一本黑脸琵鹭国际保护行动计划出版;这是多个东亚国家和地区共同商定的保育行动纲领。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陈承彦与两岸三地的鸟类学者共同召开保护黑脸琵鹭的会议,由香港观鸟会统筹,开始寻找黑脸琵鹭在北朝鲜以外的繁殖地。

1995年1月17日曾文溪口黑脸琵鹭行动计划编辑团实地考察
此后,在中国内地、中国台湾地区、朝鲜、韩国、越南和菲律宾,大家共同执行了多项黑脸琵鹭保育措施。不仅建立了保护区,还开展了近28年的全球普查,每年隆冬1月的两天,来自东亚地区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名志愿者,齐聚沿海湿地,寻找黑脸琵鹭的踪迹。这项调查活动汇集了诸多数据,包括来自中国大陆7个省份和1个直辖市、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还有东亚的日本和韩国,以及东南亚的菲律宾,泰国等,基本可涵盖这种鸟类的整个种群数量。黑脸琵鹭的数量也从1988年的288只,增加到 2024年的6988只,脱离极度濒危级别。

1997年6月,陈承彦、郑光美教授、刘小如、林超英、市田则孝和Nguyen Cu.在东京参加保护黑脸琵鹭的会议时合影
打破偏见,在世界自由飞翔
陈承彦是中国早期走出去的鸟类保护学家的典范,对待科学研究,他们严谨、专业、不畏艰难。在全球话语体系中,他为中国的鸟类保护事业赢得了卓越声誉。
对于工作,他们专注并具备高度的职业道德。采访当天陈承彦感冒了,喉咙不适,但他仍坚持一口气完成了采访,没喝一口水。
陈承彦的生活轨迹,像鸟儿一样自由。他这些年来活跃于国际各个保护网络,参与了中国韭山列岛凤头燕鸥的野外监测与恢复招引计划,以及广东黄胸鹀的保护与教育等工作。最近他在积极推进迁飞陆鸟的保护工作。
他坦言,自己不喜欢坐办公室。尽管其他人认为,从事保护工作要奔波很辛苦。但这种不确定性,是陈承彦最喜欢的。他说:“一个人如果总在一个地方从事一种工作,慢慢会形成一种成见,认为世界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了。其实不尽然。”

2014年7月30日,浙江韭山列岛野外调研计划结束前一天,陈承彦在帐幕住所前
采访末尾,我们谈及,为何1991年后再无成群的东方白鹳来香港米埔越冬,而这几年东方白鹳又频繁光临时,陈承彦说,根据1991年发现东方白鹳时的观察,他当时觉得,东方白鹳之后不会经常来,因为后海湾没有适合的生境。至于这几年增多,他认为,不能只说是这些年保护的成果,也表明自然界里有太多人类还不了解的事物和变化。这提醒人们需要广泛学习和交流,纠正认知偏见。
从陈承彦身上,能看到鸟类保护者在科学家标签下的一种浪漫主义特质。保护迁飞的鸟类,给了他们一个构建理想世界的机会。在这个世界,国家、民族、政见、利益之间的冲突都显得微不足道。对大自然的爱好,是共同的语言。
(作者王婷系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后,从事湿地景观与环境人类学研究)

个人能为环境做什么?普通人如何在自然中自处?
“普通人的自然”(A New Normal for Nature)专栏将记录普通人与自然相遇的故事。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