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乔治·卡兰德谈朝鲜半岛的狩猎与环境史

乔治·卡兰德(章静绘)
乔治·卡兰德(George Kallander),2006年博士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现任美国雪城大学历史系教授,雪城大学东亚项目主任。他的研究重点是前现代和早期现代的朝鲜半岛,著有《异己的救赎:东学异端与早期现代的朝鲜》(2013)、《〈丙子录〉与丙子之役》(2020),他还是“剑桥朝鲜史”项目的共同编者,并撰写了其中一章。2023年卡兰德教授出版了专著《朝鲜和东北亚的人类-动物关系及狩猎活动》(Human-Animal Relations and the Hunt in Korea and Northeast Asia),以狩猎活动为核心议题探讨了前现代东北亚和朝鲜半岛人与动物、人与环境,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近期,《上海书评》专访了卡兰德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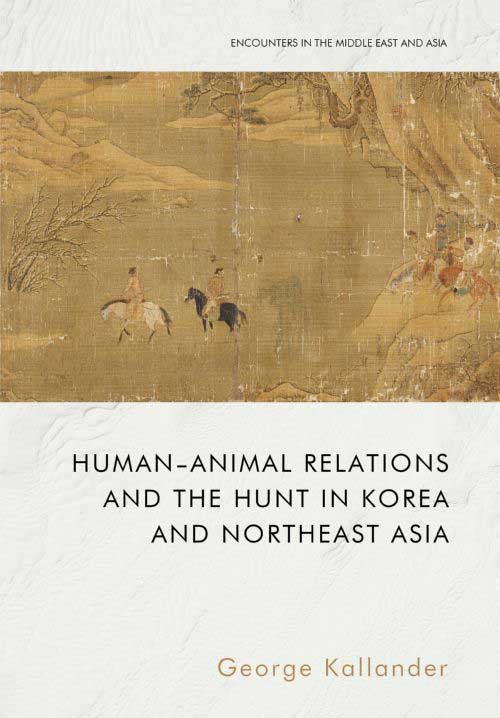
George Kallander: Human-Animal Relations and the Hunt in Korea and Northeast Asia,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23
您目前为止出版的三本书在时间和主题跨度上都比较大,从朝鲜末期追溯回高丽末期,在主题上第一本书《异己的救赎:东学异端与早期现代的朝鲜》(Salvation through Dissent: Tonghak Heterodoxy and Early Modern Kore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3),将激起甲午战争的朝鲜东学党起义放置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国际变局之下朝鲜政治、宗教思想、区域社会等方面的综合变迁中加以分析,尤其以东学党思想回应了朝鲜半岛新的国家认同的出现。第二本书《〈丙子录〉与丙子之役》(The Diary of 1636: The Second Manchu Invasion of Kore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0)第一次将罗万甲的《丙子录》翻译成英文,对其详细介绍和评注,向西方学界展示了十七世纪初满清入侵朝鲜这一重要事件。您的第三本书《朝鲜和东北亚的人类-动物关系及狩猎活动》(Human-Animal Relations and the Hunt in Korea and Northeast Asia)则将目光投向了高丽末到朝鲜初期,是什么问题意识或学术兴趣串联起您的研究轨迹?
乔治·卡兰德:从表面上看,这三本书似乎并无关联,所处理的历史时段和具体问题都大相径庭。但是,将三者联系在一起的是研究视野和主题。我着迷于东亚历史上的重要时刻,以及朝鲜半岛如何应对国际问题,或者说朝鲜半岛与日本、中国,以及与其他或跨越北方边界、或跟随西方人或西方文化(例如天主教)而来的外部力量之间如何进行互动。我的第一本书讲的是十九世纪朝鲜的“东学”信仰,研究朝鲜看待和对待自己,以及与他人互动方式的重大结构性转变。东学党从朝鲜半岛东南部的一个小宗教团体发展成全国性宗教和引发中日战争的叛乱,从中让我们看到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汉城权力基础之外的人们如何对周围世界的变化、社会的崩溃、西方人的到来、邻国清朝的衰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崛起做出反应。
我的第二本书也在宏观层面上讲述了东北亚历史的重大灾难性事件。与十九世纪末一样,朝鲜人也需要对十七世纪初地缘政治的种种宏观变化做出反应,包括明朝的衰落、满清的兴起,以及不再对朝鲜和中国构成威胁的德川幕府的和平崛起。因此,这本书同样是关于朝鲜半岛与邻国的复杂关系,以及这些地缘政治变化在朝鲜人之间释放的内部动力。正如我的第一本书所探讨的那样,朝鲜对外部世界的反应并不统一。一些朝鲜人支持明朝,另一些人明白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意识到应该与明朝断绝关系,转而支持清朝。这本书也包括很多翻译,其主体就是对《丙子录》的翻译。对原始材料的翻译十分重要,能向不熟悉朝鲜社会或不能阅读文言文的读者介绍直接来自那个时代的声音。
最新的这部著作也处理了我感兴趣的宏观层面的权力转移,讲述宋朝的衰落、蒙古帝国的兴衰,以及高丽人和朝鲜人如何应对这些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化。当然,欧亚大陆和全球在这几个世纪中都经历了重大变化。不过,在阅读有关蒙古和朝鲜的相关原始资料时,我想通过研究一个让我着迷的议题——狩猎——来扭转一般叙事。我注意到这一时期的狩猎活动比之前甚至之后都更加显著。狩猎是透视政治合法性、身份认同、经济和生活方式的重要视角。当我开始用狩猎这一视角来构建叙事时,动物自然而然地出现在史料中,所以我也将动物囊括进研究中。随着阅读材料和研究工作的深入,我越发意识到故事远不止于此。因此,本书也是一部环境史,讲述了动物和人类如何在山区、森林和平原上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既是真实的也是想象的),以及动物如何塑造人类社会。众所周知,动物在史学中通常被忽视。但是,一旦我们在史料中寻找它们,它们又无处不在。它们只是被忽视了,被认为不值得进行历史研究。所以在本书中,我开始将自己对狩猎、动物和环境的兴趣与十三世纪到十六世纪朝鲜和东北亚的宏观和微观变化交织在一起。
总的来说,我的三部著作考察了朝鲜半岛对东北亚、欧亚大陆和全球地缘政治变化的多重反应。与之前的两本书一样,我的新书也为读者提供了大量原始资料的翻译。这些译文穿插在各章中。我使用的最令人兴奋的资料之一是十五世纪一份关于驯鹰的手稿。这份手稿的技术性很强,我不得不学习很多驯鹰的术语来进行解读,但像这样的原始材料为前现代人类与动物的互动提供了绝佳案例。这份手稿在德川时代也流传到日本,正如朝鲜半岛上经过训练的猎鹰、猎犬等也流入日本一样。
此外,“暴力”是联结这三本书的另一主题。作为一种学术视角,暴力可以帮助阐明我们熟知的历史事件的各个方面,可以展现相关人群的本质以及社会如何变化和演变的更深层次的故事。我的第二本书通过人与人之间互动的视角来研究暴力。我的第三本书则扩展到人对动物的暴力。这种暴力虽然对动物有害,但也塑造了人群中特定的身份认同、政治文化、经济等等。这一视角可以应用于历史上任何社会,甚至是现代社会。对于前现代时期的朝鲜而言,政府会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控制暴力,例如颁布禁止携带武器的法律、对身体暴力或谋杀施以惩罚,但同时政府也对本国人民使用大量暴力以压制异议,比如对那些反对国王的人处以极刑或政治处罚。但是,当人们对动物施加暴力时呢?人们可以自由地杀死动物而不受任何报复吗?对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施加暴力的界限在哪里?这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是内部安全问题?这是国际事务问题,还是别的什么?人们对动物施加的暴力和对他人施加的暴力之间有一条微妙的界限。最后,我的著作讨论了前现代社会如何协商这些界限。有时人们试图规范暴力,但有时又出于经济、政治、宗教或安全需要而容忍暴力。与所有事情一样,这些都没有单一的答案。
狩猎,尤其是国家的“讲武”之仪和由王室、贵族、军人等参与的小型狩猎活动,是朝鲜史和东北亚史的研究中都十分少见的议题。您为何选择狩猎,尤其是王室狩猎这个主题?又为何认为高丽末期到朝鲜早期(即十三世纪末到十六世纪初)这一时间段尤为重要?
乔治·卡兰德:我认为狩猎在东亚历史上没有被讨论太多的部分原因是,它是一种看似不重要的“消遣”。狩猎和耕种是人类与环境接触的最基本的方式。农业因其对社会的经济贡献而在学术上引起了更多兴趣,但狩猎却被忽视了。这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偏见,因为今天我们更多地将其视作一项运动。但在十三到十六世纪,狩猎并不是一项运动,而是构成政治文化、军事安全、经济需求和宗教仪式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过史料记录最多的仍是贵族和王室成员的狩猎。然而,包括奴隶在内的社会各阶层都在狩猎。讨论这一时期的狩猎活动很重要,因为这代表了他们生活方式的另一个方面。
在世界范围内,王公贵族的狩猎活动一直是权力和声望的表现。狩猎影响了朝鲜半岛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例如,动物被写入税法。它们被奉献给中央政府,用以满足宗教仪式和军事需求。我在书中还讨论了为获取毛皮、食物和声望的狩猎如何成为塑造男性理想、或权威和合法性表达的一部分。王室的狩猎远征可以给来自边境的外国政要留下深刻印象,或者可以帮助那些展现出狩猎技能的贵族精英和士兵赢得蒙古皇帝的好感。特别是十三世纪到十六世纪初——这是欧亚历史上一个动荡的时刻,蒙古人崛起、衰落和崩溃,并在他们接触的社会中留下遗产。这一时期,狩猎作为一种表达权力和合法性的方式变得更加重要。研究这几个世纪的朝鲜,可以证明一个“边缘”国家如何与更强大的邻国接触,并应对不断变化的地区和全球变化趋势。
您提到,本书希望从王室的狩猎活动出发,探讨前现代朝鲜和东北亚地区的人与动物的关系。那么,您是如何看待前现代时期东北亚地区,尤其是朝鲜半岛的动物和人类社会的关系?或者更进一步来说,动物在塑造人类社会生活时具有怎样的作用或是能动性?我想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为什么研究人与动物的关系,这能为我们理解朝鲜史或者东北亚史提供怎样的新视角?
乔治·卡兰德:能动性(Agency)是一个非常迷人的概念。动物确实具有能动性。它们不是被动服从人类主观意志的附属品。反之,它们积极应对环境变化、气候波动和栖息地变化,尤其是那些由人类引发的变化。人类对野生动物的需要远远超出它们对人类的需要。我在书中讨论了很多例子。例如,动物不会主动向人类捕猎者投降;动物的能动性激发了其与人类的接触——人们冒险进入山区、森林和平原,在动物活跃的地方狩猎,或者偶然与它们相遇。无论是出于狩猎需要还是偶然相遇,在人类反复遇到野兽的地方产生了关于动物和环境的特定类型的人类叙事。领袖人物冒着生命危险打猎,因为这可以为他们带来声望。貂或鹿的故事刺激朝鲜半岛内外的许多人冒着失去生命、肢体受损和丧失地位的危险进入山区。政府则制定详细的律令来控制人们对野生动物的获取。一些律令适用于平民,他们获得的猎物应当献给国家;一些律令限制人们进入军队的狩猎场地;还有一些律令试图对王室进入狩猎场和获取动物加以管控,以限制国王及王室成员的权力。这些控制都以保障国家安全和宗教仪式的名义进行。透过人类-动物关系这一视角研究历史,可以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已有充分研究的历史事件和时间段开辟新的理解方式。尤其是,将这一视角应用于前现代社会,有助于理解我们一直在努力应对所处环境这一重要事实。这不仅是一个当代才应关注的议题。
本书希望探讨的另一个主题是人与环境的关系。十三世纪末到十六世纪初的朝鲜半岛,在气候上经历了从中世纪气候异常期到小冰期的变迁,又因战乱、朝代更迭、疾病等原因经历了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您认为朝鲜半岛的狩猎活动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动物、土地资源如何与这一时期的环境与人口变迁产生联系?
乔治·卡兰德:对动物的研究就是对环境的研究。虽然本书的各个章节也讨论了被驯养的动物,但重点仍是野生动物和那些被王室精英、平民和其他人猎杀的动物。与之相关的一大原因是人口和气候的变化。十三至十六世纪,人口增长给环境带来压力,而这一时期又是东北亚政治发生巨变的时期。从十四世纪中叶开始,气候模式开始发生变化。气温下降,河流结冰的频率更高,这刺激了人与人之间更多地发生互动。北方的女真部落和来自南部的朝鲜人在这一地区狩猎鹿和貂。在朝鲜中央政府看来,这威胁到政治稳定,构成安全威胁。此外,随着气温的变化,北方人群的食物危机尤为加剧,因此人们更多地转向打猎,以此弥补食物数量的不足,或将其作为实现贸易的经济手段。十五世纪,朝鲜王廷减少了狩猎场的数量,其中许多土地开放耕种,或供附近村民公用。此外,有许多狩猎场集中在汉城附近的京畿地区。这在当时看来是方便和合理的:前往狩猎场并控制那里的资源变得更加容易,国王和王室成员可以减少旅行,在宫外花费更少的时间。但这也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过度狩猎和气候变冷的影响也减少了京畿地区的动物数量,影响了人与动物的关系,给国家带来麻烦。正如书中所示,动物也被写入税法。野生动物被猎杀、诱捕,有些被加工并上呈给中央政府,以满足宗教仪式、军事和经济方面的需求。但随着气候变冷,在山中接触这些动物变得更加困难。朝鲜中央政府却很难意识到这些变化,反而是向地方要求更多的动物制品,直到为时已晚。这也使得当地官员迫使平民和奴隶进入更危险的地方狩猎和诱捕动物。过度狩猎也因此成为一个问题。此外,动物也可以是卫生系统的一部分。特别是对于贵族来说,某些种类的野兽被加工、晒干、磨碎,并与其他成分混合成中药或乡药。这还是一个疾病增多的时代。对疾病的忧虑随之增加,需要更多的动物制品(尤其是鹿)用于制药。我试图梳理出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故事。动物与朝鲜和东北亚社会的许多方面息息相关。因此,朝鲜半岛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研究案例,展示出前现代社会如何努力应对环境、土地资源、动物管理等议题,以及这些议题对地区、国家、村庄甚至个人的意义。
您在书中花费大量篇幅阐述了狩猎如何塑造朝鲜半岛人与人的关系,尤其是朝鲜国王与推崇理学的官员之间的关系。那么,不同立场的人群如何赋予王室狩猎复杂、动态的政治文化含义?
乔治·卡兰德: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也是我首先对这个话题产生兴趣的原因:我阅读了大量国王、王室成员和官员之间对狩猎意义和重要性的详细争论,这些争论尤其涉及国王在狩猎中扮演的角色。官员们利用狩猎来支持或反对某些政府政策,有时以此限制国王的行动,从而遏制后者的权力。很明显,狩猎活动的移动性非常强,它需要人们冒险进入狩猎地,有时需要花费好多天。这项活动也十分血腥。这些事实与我们对朝鲜王室和贵族文化的传统理解相冲突。主流史学和大众理解认为,朝鲜国王和贵族通过书本获取知识。他们遵循程朱理学的观念,对国王进行约束,并要求学者们在室内空间开展研究、学习和娱乐。但正如我希望在书中表明的,事实远非如此(尤其在十六世纪以前)。国王会打猎,军事将领和儒学领袖也会打猎,有时还会伴随国王左右。但也有少数官员强烈反对这些活动。对于国王来说,狩猎是其家族成员(其中一些成员有军事背景,比如朝鲜王朝的开国君主李成桂)传承下来的一项重要传统,以此展示他们的军事技能及对环境、人民和动物的控制。其他贵族将狩猎看作获得王廷或元朝皇帝青睐的一种手段。其他一些狩猎形式(包括驯鹰)则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朝鲜从上至下的文化中,尤其在我所研究的这个时期。这一时期,通过科举考试和书本学习来显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仅止于此。其他一些更需要体力的活动,例如狩猎和拥有辅助打猎的动物(如猎犬、猎鹰),也可以展现一个人的能力并助其获得利益。
一些士大夫对狩猎提出抗议,另一些则积极参加狩猎或驯鹰,还有更多选择在口头上支持国王的狩猎活动。武将们也狩猎。而在和蒙古关系良好时,演示驯鹰技术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少数顽固的儒学家感觉自己被排挤在这些机遇之外(有时这种排挤是故意为之),所以他们自然地试图控制人们对动物的接触,尤其是狩猎,并限制国王的这些活动。无论国王做什么,其他精英群体都试图模仿。这也正是所有人类社会的本质——我们倾向于模仿等级在我们之上的那些人的行为,而这在高丽晚期到朝鲜初期尤甚。朝鲜半岛的人们意识并参与到这些国际变化中。
十六世纪初以后,也就是朝鲜中宗朝开始,王室和贵族的狩猎活动在史料中逐渐消失。那么,王权是否找到其他的方式进行自我表达和强化?与之相关联的一个问题是,十六世纪初以后,整个国家对于动物、植物等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开发又出现怎样的变化,产生怎样的影响?
乔治·卡兰德:我确信在十六世纪初以后,朝鲜国家在继续处理人与动物的关系时变得更为官僚化了。朝鲜王朝的重农政策和人口增长政策给环境和动物种群带来了巨大压力。这会对朝鲜国家和东北亚产生什么影响呢?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国家开始更多地转向驯养动物,以弥补野生动物的短缺,后者对于国家运行所需的制品、药物和祭祀食品而言必不可少。壬辰战争以及丁卯、丙子胡乱也给朝鲜当地的动物造成创伤。此外,更值得研究的是明朝和日本军队在朝鲜当地的大规模冲突对人与动物的关系造成了何种影响。我更感兴趣的还有清朝出兵朝鲜并与之结盟这一调整如何改变朝鲜人(尤其是精英阶层)看待动物的方式。这一时期与元明之际人与动物的关系有什么不同或吻合的地方吗?我想这些问题都还有很大研究空间。
讨论十三至十六世纪高丽/朝鲜的狩猎活动和人与动物的关系,对于理解现代的朝鲜半岛与东北亚是否有所启发?
乔治·卡兰德:人与动物的关系是帮助我们审视重要历史时刻和历史趋势的新视角。其他研究者也可以采用这种理论视角,将其用于考察现代朝鲜半岛或其他任何地区。事实上,对人与动物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考察他们如何相互影响并塑造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等种种议题,都可以放在现代进行。这一时期有更多不同来源和类型的材料被保存、流传下来,因此我们可以接触到多得多的资料。我也期待对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的研究。不过,要充分研究这一课题,学者需要利用多样化的资料,包括韩文、日本、英文、其他西文资料,以及气候研究等科学数据。话虽如此,本书也确实有助于理解现代时期。我们可以把关于前现代朝鲜和东北亚的这一研究成果和现代社会的发展进行对比,以此帮助我们理解关于动物的想法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或保持不变)的,以及动物如何在现代参与塑造特定的身份认同。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