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曲柄睿:汉武时代的大侠
汉武帝以后,因为政治风气的巨大变动,游侠一类的人物越来越和高层政治疏离。战国时曾经左右天下局面的游士和侠客,现在只能退回地方乡里,在基层社会中扮演要害角色。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奇怪,而是早有端倪。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都不大,君主和庶人之间的沟通也相对容易。异乡游士或本土侠客想要出名或跻身朝堂,虽有难度,却并非不可实现。当汉朝真正完成天下一统,也就是汉武帝之后,郡国并行制已经名存实亡,人才流动的范围和人才的数量,都是战国乃至汉初不能比拟的。
楚汉之际,刘邦每天要接见很多毛遂自荐的人,他顾不上来,一次接见七个人。试想,天下纷争之际,行路有多艰难;抵达刘邦军营还能通上名姓,有多艰难;与刘邦相识,又被他认可,委以官职,又有多艰难。刘邦时代,做这些事尚且如此艰难,更何况汉武帝时,涌入长安的人才数量远多于刘邦时代,汉武帝时的官僚制度又远较高祖时发达,得见人君难于上青天。在这样的时代,一个人能够被皇帝赏识且重用的机会又有多少呢!
进一步讲,汉武帝时代,很多侠客都只有地方的影响,没有全国性的影响。比如《史记·游侠列传》记载的汉景帝时济南瞯氏、陈国的周庸,其后还有代郡白氏、梁国韩无辟、阳翟薛兄、陕地的韩孺等等,这些人都是在居住地出名,而后名声传播至长安的。在一郡之内或者一国之内出名,其情况与战国时在一个诸侯国内出名近似。从这个角度说,汉武帝以后,侠客依然存在,他们的数量和战国乃至汉初没有太大区别。只不过一方面,汉朝此时已经实际上完成一统,对于一郡乃至一诸侯国内的侠客活动,除非严重干扰统治,否则朝廷并不过问。这些工作,通通由刺史或郡守负责。另一方面,后人审视汉代历史时会注意到,汉初侠客们还很活跃,汉武帝以后就没那么活跃了。这并不是侠的数量减少了。问题的关键在于,汉初的情况更接近战国,汉武帝以后是一统的王朝。这样说来,侠客施展拳脚的历史舞台变得更大,他们自己光芒辐射的范围就相对变小了。
人还是那些人,只是因为他所处的平台发生改变,于是就不像之前那样显得引人瞩目了。
汉武帝时最有名的大侠是郭解。他是大相士许负的外孙。前面提到,许负给周亚夫看过相,预言都很准确。郭解的父亲就任侠,游离在法律之外,被官府抓住处死了。郭解这人有两下子,《史记·游侠列传》说他:
为人短小精悍,不饮酒。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以躯借交报仇,藏命作奸剽攻,休乃铸钱掘冢,固不可胜数。适有天幸,窘急常得脱,若遇赦。及解年长,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为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阴贼著于心,卒发于睚眦如故云。
郭解的为人,概括起来就四个字:心狠手辣。年轻时极度自律,不饮酒,敢杀人,行事果决,从不含糊。年纪大了点,看起来更文明了一点,儒雅了一点,不过背地里还是奉行睚眦必报那一套价值观。他越是狠辣,追随者就越多。他越看起来无害,别人就越信服他。人虽然穿上了黼黻文章,用礼乐揖让规范行为,口出圣贤之言,不入鲍鱼之肆,内心潜藏着的底色,却还都是大自然优胜劣汰的逻辑。
郭解势力极大,大到他不能控制。如果他有不喜欢的人,那人自然会被人杀掉,郭解可能动了杀心,可能没有。但是他周围的人为了让他顺心,就会替他除掉冒犯他的人。因为这个原因,他在乡里很有威信,官府里也都是朋友。他的名声远播全国,甚至洛阳有人结仇难解,最后请郭解来说和才化解。
解执恭敬,不敢乘车入其县廷。之旁郡国,为人请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厌其意,然后乃敢尝酒食。诸公以故严重之,争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夜半过门常十余车,请得解客舍养之。
越是这样,郭解反而越显得恭谨了。不过要注意,富贵从来相通。郭解在乡里如此有威势,他的钱从哪里来呢?他如何豢养宾客呢?可知,郭解一定极有产业。积累财富最迅速的办法,一定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司马迁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按照这个至理名言,郭解必定有着庞大而秘密的产业经营。而人们都知道,当财富积累到相当程度时,财富自己就有着巨大的繁衍力量。郭解可以不再做挖坟掘墓和动手杀人的勾当,也可以理解为自然有人替他做就是了。郭解这样的侠客,和战国时期的侠客有一点不同。那就是他兼具侠客与豪强的双重身份。先侠客而后豪强,故而有了政治和社会上的势力。
汉朝对付地方侠客豪强的办法非常简单,一个是用酷吏在当地杀掉;另一个就是将他们迁徙到长安地区,在中央的权力下管理起来。这两个办法都很直接。对于郭解这种看起来没有什么污点的人,只能适用第二个办法。郭解要被迁徙到长安了,大将军卫青向皇帝求情,说郭解家贫,不应该迁徙。汉武帝是何等见识,他马上回应,郭解能让将军替他求情,他家不贫。
郭解到了长安,就得适应关中的政治气候。天子近畿,很小的事都会上升到很高的高度。郭解到了关中,很快找到了和自己气味相投的人,在当地又建立起了自己的圈子。还是老样子,有人替他报仇,杀了人。过去在地方,和官府招呼一声,也就罢了。这次不同往日。郭解指使人行凶,惊动了朝堂。当时还是御史大夫的公孙弘说:“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这话说得不差,普通人稍不如意,就能有人替他杀人,长此以往,政权的权威何在?汉朝对侠客的残酷镇压,本质就是要扫除豪强在地下社会中扮演仲裁者角色的能力,将所有的社会信任收归国有。
当然了,王朝的政策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就会存在千差万别的折扣,毕竟豪强和地方政权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豪强一定程度上也是地方政权千挑万选筛出来的。他们双方达成了共识,缔结了共谋。基层政权未必不会打击豪强,不过他们可能更多地借助一批豪强打击另一批豪强。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汉武帝时有王温舒,年少时也是杀人掘冢之辈,后来进入捕盗序列,步步升迁,一直到担任广平都尉。他选了郡中十几个敢杀伐的小吏作爪牙,让他们出去罗织罪名,搜捕罪犯,“快其意所欲得”,干了很多坏事,也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这批爪牙自然也留了很多把柄在王温舒手里。王温舒纵容他们,从不处罚,不过要是他们有事得罪了王温舒,王温舒转身就将他们除掉,易如反掌。后来王温舒做了中尉,负责京师地面治安,他又把这一套发扬光大:
督盗贼,素习关中俗,知豪恶吏,豪恶吏尽复为用,为方略。吏苛察,盗贼恶少年投缿购告言奸,置伯格长以牧司奸盗贼。温舒为人讇,善事有势者;即无势者,视之如奴。有势家,虽有奸如山,弗犯;无势者,贵戚必侵辱。舞文巧诋下户之猾,以焄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奸猾穷治,大抵尽靡烂狱中,行论无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于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势者为游声誉,称治。治数岁,其吏多以权富。
这一套办法可谓是驱虎吞狼,培养一批豪强打击另一批豪强而已。
还有些地方官,有朝一日做不成官了,转身就能成为豪强。比如宁成,本来是内史,汉武帝时犯法,遭受髡钳之刑。受过刑的人就不能做官了。宁成心思活动,不做官就不做官,他给自己伪造了身份证明,出函谷关回山东老家,他的主张是“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有这种心劲儿的人,干什么都能成。他回家借钱买地千顷,雇人耕种,役使数千家,致产数千金。宁成摇身一变,又成了大侠,反过来还能“持吏短长”,在地方上比郡守还有影响力。如此看来,豪强与地方官本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共同体。
讲到这里,还得再将汉代商人的情况交代一下,借以说明他们与豪强之间的联系。
司马迁独具只眼,在《史记》中设立《货殖列传》,用以交代战国秦汉的主要经济区以及立足于此上的商人活动。什么是国家大治的终极状态?《老子》说那便是:“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司马迁觉得这个标准太高了,难以理解,于是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司马迁是实用主义者,他认为治理得好的国家,应该是老百姓的物质欲望和精神追求同时得到满足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不是被管理出来的,而是通过因循、引导、教诲、整齐实现的,最差的办法就是管理。
司马迁的意见非常特立独行,和商鞅变法以来国家统治重视限制民众不同,他提倡利用经济活动引导民众。对于经济活动的不同态度,是区分法家和黄老的一条标志。黄老根源于齐地,当地通鱼盐之利,经济生活异常发达。人们热衷于商业活动,不鄙视商人。法家虽然和黄老有某些共通之处,但是更多强调国家的管控,对商人的态度非常严苛,将之视作社会蛀虫之一,是变乱分子,人君一定要予以警惕的。
作为黄老信徒的司马迁,将他的理论放在经济活动中来说明人们因循天时,自发趋利,努力生产,全心致富的过程。看吧:“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所谓治理,就是将民众顺应天时而自发行之的生产活动,给予保护与认可。王朝必须认识到财富的重要意义,那可是让普通人惊心动魄,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又全心全意的魔法。整个社会都围绕着财富组成并运动着,金钱的规律就是人性的规律,财富的秘密就是国家的秘密: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不要不服气,有钱人才有资格讲礼仪,穷人只能谋生存。君子有钱便能践行自己的价值观,小人有钱呢,也能谋得好的生活。人有钱了,自然就学会仁义了。司马迁反复提到“势”,无论是前面讲汲黯、郑庄,还是后面讲酷吏王温舒,“势”就是凝聚人、团结人的那种力量。这力量从何而来?官员自然以官身为势,普通人呢,则以钱财为势。即使贵为王侯,也担心没钱,何况普通人了。故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实在是人性所致。
如果不相信财富对于政治和学术的力量,那就看下面的例子。越王勾践,用计然之策,生发财富,国人繁殖,得以破吴报仇。范蠡用计然之策,泛舟江湖,殖产兴业,成为巨富陶朱公。孔子的弟子子贡,善于在曹、鲁之间经商,他“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孔子的大名得以传播,与子贡关系巨大。再看孔子另一个弟子原宪,他真诚地践行夫子之道,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匿于穷巷,不厌糟糠,的确称得上儒家信徒的表率。不过,孔子如果天天和这样的学生混在一起,恐怕早晚饿死。
财富是政治和学术的生命滋养,鄙视和回避财富的人,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标明自己某些意见的人,并没有站在黄老的历史眼光下思考历史的关节。
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时,魏国有个白圭,通过黄老变化的视角观察物资的盛衰,能做到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故而往往获得稀缺物资。他观察的对象是星象,恐怕也包括国家政治动向。白圭不是凡人,他自己吃很粗糙的饮食,没有过多的爱好,穿着朴素,和自己的奴仆一道生活,可是他追逐时机的迅猛,如同猛兽鸷禽一般毫不犹豫。他自己总结自己的成功:
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治大国若烹小鲜,治产业则若行兵法。和平年代,商场是最接近战场的地方。故而侠客的气质和思维方式在商场中最为必要。经营活动中,智慧让人能够随机应变,勇气则使人能够当机立断,仁义让人做到有所取舍,刚强则让人能够坚持原则。这些道理和治国治军一模一样,白圭就是财界的宰相,商界的王师。
汉代商人的财富巨量积累,形成了极大威势,他们在地方上就是豪强,豢养宾客。比如宛地的孔氏,他们经营的产业是冶铁。于是“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孔氏已经有游士的做派了。
齐地民俗,鄙视奴婢,可叫刀间的人反其道行之。他收留了大量难以控制的刺儿头奴婢,他们聪明决断,擅长追逐鱼盐商贾之利,以至于“连车骑,交守相”。汉朝商人地位卑微,很难和守相交结,现在只是几个豪奴,居然可以与守相抗礼,不能不让人惊叹财富的力量。
更精彩的故事是下面这两个人。一个是宣曲任氏,他曾经在秦朝管理粮仓。秦朝败亡,豪杰们都到仓库里搜罗金玉珠宝,只有他将粮食窖藏储存起来。等到楚汉相争之际,战争造成粮食短缺,连种子都没有了,粮价翔贵,这时候,任氏将所藏的粟米拿出来,积累了第一桶金。
另一个是无盐氏。吴楚七国之乱时,长安列侯封君都要替朝廷效力,置办装备得准备大量的资金。本家钱不足,便向钱庄一类的机构借贷。这样的机构,汉代叫做“子钱家”,意思是以钱生钱,不断增殖。“子钱家”考虑,这些列侯的封邑都在关东,仗打胜还罢了,要是失败,他们自己的封邑都没有了,用什么还钱啊。故而“子钱家”纷纷躲闪,没人给列侯们提供借款。这个时候,无盐氏拿出千金给列侯作本金,约定十倍偿还。不到三个月,吴楚七国之乱平定,列侯们凯旋归来,无盐氏的千金变成万金,一下子跃升为关中首屈一指的大商人了。
这些例子说明什么?财富的运动,是伴随着时机的转变而调整方向的。顺应天时,无非获得常规性利益;最大的暴富时机,来自于对国运的判断。换言之,商人对经济规律和政治形势的感知和把控,决定了他们经济地位的高下。而经济地位的高下,又决定了他们政治地位的高下。由富而贵的追求,是人人所欲的。不妨用司马迁的话做一小结: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坑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
富贵使人长久,贫贱灭人志气。商贾与侠客的合流,是汉代以后的特色。战国时代,侠客依附政治权力而获得支持的情况,在汉朝一统的局面下难以为继了。故而只有不断地追逐财富,不断地积蓄财富,才能让侠客们争取到更大的势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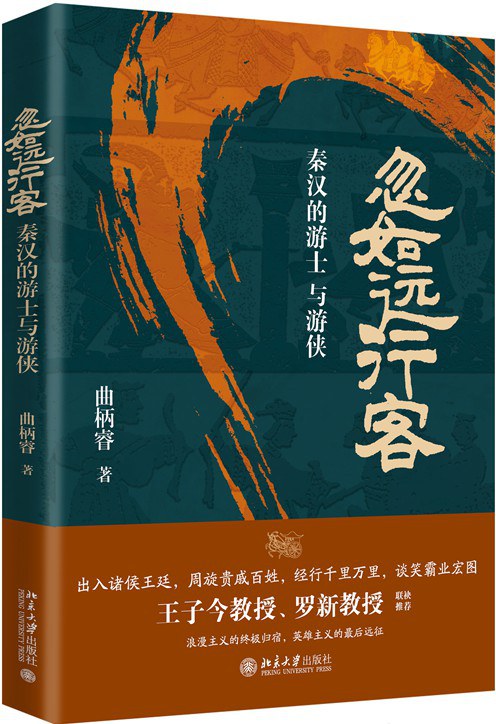
(本文摘自曲柄睿著《忽如远行客:秦汉的游士与游侠》,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3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