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仇鹿鸣:读经已死,经典教育万岁
写下这个略有耸动的标题,并非是有意要哗众取宠,与这个题目多少有关而可引为谈资的至少有两个话头,一个是胡适1930年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以“儒教的历史”为题发表的演讲时曾说:“儒教已死,儒教万岁,我现在也可以是儒教徒了”。胡适的意思大约可以做以下理解,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规范着人们日常秩序的儒教随着原有帝国体制与社会结构的崩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已走向死亡,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对象的儒教则恰恰因此获得了新的生命,整理国故之业,方兴未艾(参读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困境》,收入《现代儒学论》)。另一位则是美国学者施坚雅(G.W.Skinner)在1960年代推动美国中国学研究范式的转变过程中曾向新一代的学者发出呼吁:“汉学已死,中国研究万岁”!施坚雅此处作为论敌抉出的汉学(Sinology)指的是传统汉学,其治学特色以语言、文字、考据为基础,大抵重知识而轻解释(参读姚大力:《西方中国研究的“边疆范式”:一篇书目式述评》,收入《读史的智慧》)。
毋庸讳言,汉学这门学问的产生本来就带有鲜明的西方中心论及殖民主义的色彩,与汉学并称的印度学、突厥学、藏学等学科,大抵都以研究与西方文明异质的、已经死亡(至少丧失活力的、停滞的)的古典文明为宗旨,因此往往倾向于将这些文明理解为僵化停滞、均质同一的实体,而以社会科学家自居的施坚雅所提倡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则强调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展开对于中国的研究,重视观察中国内部焕发的活力与持续性的变化,强调中国各区域间的不平衡与文化差异,试图基于综合性的、长时段的视角来考察中国历史的变迁,并建立更有效的解释框架。
胡适与施坚雅发言的时机恰好都处于时代风气与学术思潮的转折点上,胡适承续五四以来的科学主义精神,所欲分梳的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儒教与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儒学之间的不同,施坚雅所极力推动的学术范式的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展示的是古典学问与现代学术之间的分野。直至今天,这对我们理解何谓经典、如何在现代学术体系下审视经典、乃至于如何理解以大学教育为核心的现代学术训练的意义与目标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近代以来,随着反传统的浪潮日趋激烈,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如何理解“打倒孔家店”之说多有歧见,但除了个别之外,大多数学者都基于清末以来国难日深的历史现实,主张以西为师,热情拥抱西方的科学主义,即使在最传统古代文史研究,也往往热衷于从乾嘉学术中发掘出科学主义的基因。大体可以认为,大多学者间的分歧只在于在多大程度上打倒孔家店、是否要全盘西化,至于“打倒”与“西化”这两个取向本身,虽然亦间有质疑者,然所论多并不为时所许,当下甚受推重的国学大师钱穆等人,在民国时,却是学界的旁支异数而已。钱穆曾落选由胡适派学人主导的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而同时与胡适政见相左的郭沫若则顺利当选,尽管郭沫若宗奉马克思主义,与胡适等政见分歧,但郭沫若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历史也是西方科学方法的一种,与钱穆固守国故的藩篱不同。胡适所欲分梳儒教与儒学的不同,便基于此背景,其言语之中已将儒教视为已经死亡的过去,正因如此,儒学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

毫无疑问,二十世纪的前八十年,无疑是儒学地位急剧下降的时代,这一风潮在文革中达于鼎盛。在二十世纪,孔子被拉下了神坛,先是失去了先圣的光环,后来连先师的资格也保不住,在文革中更因政治牵累成为要横扫批臭的对象。而有第二次启蒙之称的1980年代的社会文化思潮,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五四科学主义精神的复归,带不来四个现代化的传统学术自是只能避居旁席,拥抱西方、走向世界的梦想便是此种思潮的典型表现。直至1990年代以后,随着所谓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现的文化变局,学者一方面已不再像80年代一样在站在舞台中央,对于公众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转而退居象牙塔中,另一方面与之对应的是中国转向内在,某种程度的文化保守主义开始成为中国思想界的重要一翼,当然这种变化也与近二十年来国力见长,民族自信力的恢复相辅相成。因此,我们首先要在20世纪已来的中国思想变迁的脉络下来审视最近几年广被媒体炒作、追捧的国学热及读经运动。
无疑民族主义情怀是现代民族国家得以成立的重要共同心理基础,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在近代史上曾遭逢过屈辱的国家而言,所谓国学之争确实很难只作为一个纯粹的学术话题而被讨论。事实上,近代史任何一次所谓的国故整理都不是纯粹的学术事业,甚至国学这一概念的出现,也是西学冲击下的产物,因而谈及国学,不免容易陷入多少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中西优长之争中去。在承认了这一前提之后,笔者接下来想要讨论的是,在大学教育中我们应该来用何种态度来讲授国学、以及作为国学成立基础的中国古代经典。
首先要承认的是,中国现代的大学体制、学科分类乃至课程设置方式都是移植自西方而来。因此,这一前提是我们展开讨论的基础,笔者以为现代学术体制下的大学教育与传统的读经式的教育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在于,当下大学所培养应该是具有科学素养及理性批判意识的现代知识人。所谓国学经典只是整个课程体系中的一个部分,而且这种教育应该是建筑于精密学术研究基础之上的对于经典研究式的、分析式的探讨,而不是接受式的、信仰式的习得,这与传统读经教育强调将经典内化为指导自身行动的道德律令,并由内圣而致外王的路径有着本质性的区别。中国的传统学问(特别是儒教经典)带有强烈的经世色彩,这一方面固然养成了中国知识分子达者兼济天下人文主义情怀,但一方面也使得中国学术往往与现实政治纠葛不清,以“仕”作为“学”的目标,便使天下英雄尽入此彀中。等而下之者,更是有“术”而无“学”,打着“帝王师”、“哲人王”的旗号汲汲于功名利禄之图。
反思当下国学复兴的热潮,我们一方面固然要为传统文化研究重新得到关注而感到欣喜,但更加要对隐藏在其背后的某些非学术的内容、某种民粹主义的情绪抱有深刻的警惕,笔者个人绝无法同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以所谓“通三统”为名,将传统儒家学说与现代意识形态相结合,杂糅包装成某种政治权力合法性来源的述论,现代学术的基本特质便是其不依附于特定权力与意识形态的独立性,胡适早已说过儒教已死,我们不必再让已死的幽灵飘扬在中国学术的上空。现代大学本质上应该是一个摆脱意识形态束缚的学术中立机构,基于此点,其所教授的必须是儒学而非是儒教,民间可以搞各种读经班,可以穿汉服,但在大学之中,教师在讲授需秉持价值中立的原则,毋以个人好恶为褒贬。

这种经典教育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古代强调读书需先识字的治经方式有共通之处,所谓的精读自然要从最基本的疏通文义、典章故实入手,而不是搬弄一些二手的概念、分析与研究给学生。因此,古人的经疏史注在当下依然构成了我们进行经典教育与研究最重要的文献基础。以此入手,训练学生点读、理解中国经典的基本能力,进而培养其对于中国文化的同情之了解,在这方面很多学者已有共识,毋庸赘述。但笔者所欲申论的则是另外一面,即除了基本的文献训读能力,基于现代学术的要求,经典教育还必须提供给学生什么。笔者以为最重要的便是对批判性思考能力的训练,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古典学问与现代学术的不同取向。我们教学生读四书五经,并不是要将学生培养成一个儒家道德的信徒,若因此提升学生的道德水准,只能算是附带的成绩。经典教育在培养学生阅读古籍的能力,加深其对古典的亲近感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教学的过程中需训练学生独立的思考能力与科学的批判精神。
学生须对古代经典有所了解,这是作为一个中国现代知识人所必须具有的素养,但经典教育的目的并不是要教育学生信而好古,而是要在学习研读经典文本的同时,习得现代学术的批判精神与思辨能力。20世纪中国学术从信古、疑古到释古的演变过程无疑彰显着学术研究从古典走向现代变迁,而经典教育课程的规划亦要体现现代学术的研究水准。以中国经典的一般情况而论,这主要需在讲授中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介绍经典文本复杂的多次结集形成过程,介绍历代经师出于各种政治、文化目的对于经典的诠释与曲解及古代政治与学术的复杂互动关系,介绍现代学术的前沿研究(特别是对于先秦典籍而言,最近五十年出土简帛对于先秦学术史的改写是必须传递给学生的重要讯息)。
总而言之,我们经典教育的目标并不是要向学生传递一个中国文化悠久、灿烂、连续的完美图像,而是展现中国经典本身所具有复杂的历史面貌,须让学生了解中国历史书写中层累造成的特征(如三皇五帝神话的建构与发明),经典文本流传形成的复杂性及其背后政治、文化动力(如尚书古文的公案),经典地位的变迁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如孟子升格运动)。通过这种建筑于精读基础上的文献批判,学生一方面可以加深对于古代经典的了解,另一方面也在对文本制作形成的分析中,学习如何批判性地理解历史记载、通过对相关经典研究论著的研读建立起对学术史的基本了解、初步学会收集资料、开展学术研究的方法。
复旦大学自十余年前便提出建设研究型的大学口号,这一目标自然不是靠研究生数量的增长所能达成的,培养本科生的学术能力才是其中的根本所在。因此,所谓经典教育课程与以往课程的最大不同之处,便是要从注重知识传授转为注重学术能力的培养。而笔者私见以为经典教育课程最核心的两点一个是扎实性,强调对于原典文本及第一手文献的接触与阅读,不作耳食浮泛之言,奠定展开学术研究所必须的文献学根基。第二则是前沿性,注意将经典研究论著及国际学术前沿的动态介绍给学生,侧重于对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在此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分析思辨能力,进而了解学术史的演进过程,培养从事学术工作的兴趣与能力。若能初步做到这些,庶几近于在现代学术体制下展开经典教育的目标所在。
(本文摘自《读闲书》,仇鹿鸣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9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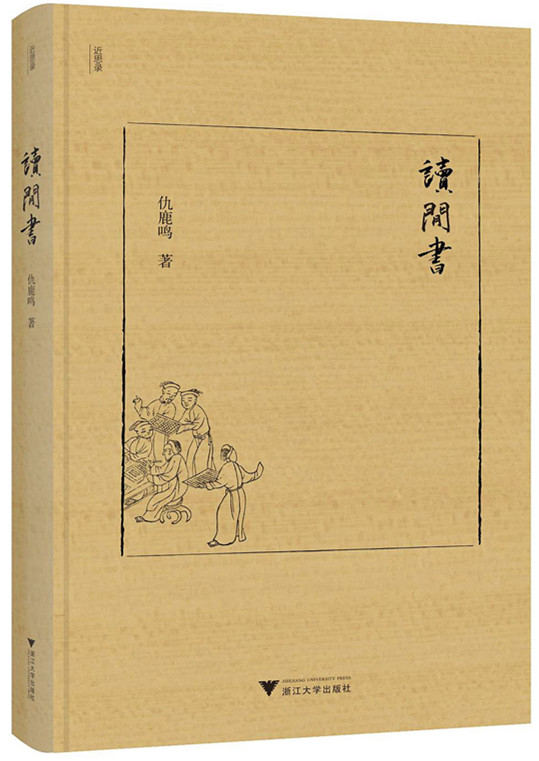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