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1
巴塔耶:精神分析与“恶”的解构
巴塔耶不仅是精神分析理论的阅读者,更是精神分析临床实践的体验者和超越者。他与精神分析之间的联姻不仅仅通过他第一任妻子西尔维亚·巴塔耶和拉康的关系达成;经由他自身的虚构写作,他在拉康提出“圣状”[1]概念的几十年之前——法国精神病学界仍是弗洛伊德的时代——就创造了前-拉康意义的文学增补,使自身获得在文学界命名的主权性。我在阅读和翻译《文学与恶》的过程中回溯性地看到,阉割(la castration)[2]作为一道卡夫卡意义上的“法门”,隔绝出无意识领域和意识领域、童年的王国和成人的活动世界。萨德和萨德式的倒错幻想在这本书中被搬上舞台,而在无意识的机制中,这不过是儿童多态情欲[3]的夸张隐现。
国家图书馆的借阅记录[4]便可佐证他作为弗洛伊德阅读者的身份,早在1920年,他就看了《精神分析入门》。1927年,他阅读了《图腾与禁忌》:在这本书中,弗洛伊德提出的假设是,在神经症那里被压抑的机制(乱伦的欲望,或者是对“正确”生殖活动的无视)在“原始人”那里则是光天化日发生的,而巴塔耶讨论的对禁忌的僭越无疑是在回归这种原始性或动物性;而弗洛伊德对“神圣”“禁忌”等概念的双重性挖掘在巴塔耶那里也可以瞥见[5]。巴塔耶很有可能也看过《群众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这篇文章中提及的“无意识”[6]这一术语,“意识自我的审查和排除机制”帮助他构思了《法西斯主义的心理学结构》(1933)的写作。

巴塔耶
除此之外,弗洛伊德关于性欲、驱力和梦的学说等对于巴塔耶来说并不陌生。巴塔耶曾待过的超现实主义团体Contre-Attaque里,弗洛伊德的影子也随处可见:“教皇”布勒东作为曾经受训的年轻精神科住院医生,一直潜心研究弗洛伊德,他也见过弗洛伊德本人。比起临床的诊断目的,他更在意自动主义(automatisme)在文字联想和写作上的运用。然而,无论弗洛伊德的影响能不能被准确追踪,都无法遮蔽巴塔耶原创性的光芒。在《天空之蓝》中,我们可以看到无意识最重要的素材——梦境的显化:关于一场革命的墙画被他描述为庞贝的死尸,闹事者像被掩埋了一样悬置在房间中。这一场景的描写无疑是在影射欲望的压抑(refoulement),尤其是当我们联想到弗洛伊德关于詹森《格拉迪瓦》的评述,即浮雕和压抑机制的美学类比(analogie):浮雕上的少女格拉迪瓦在主角汉诺德的幻想中被庞贝城倾斜下的火山灰掩埋;而汉诺德童年时期的欲望则也像这样遭到掩埋。
巴塔耶体验精神分析临床的经历也值得展开来讲。在巴塔耶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Joseph-Aristide已经感染了梅毒,接近失明、四肢瘫痪。在《眼睛的故事》中,他写道:“我的神经性梅毒的父亲在怀上我的时候就已经失明了,在我出生后不久,他就因恶疾而被禁锢在扶手椅上。”[7]1915年,他早已失智的父亲去世。巴塔耶曾确信他父亲乱伦式地抚摸过它,甚至强迫过他进行性行为,但这段历史并未得到确凿的证实。或许在巴塔耶的眼中看来,对父亲的感情总是混杂着这种淫秽的爱恨交织。如果说,这些个人史并不足以让我们推断出“父之名”的脱落(forclusion du Nom-du-Père),因为这样显得有些仓促和冒进,但这一历史的难以过活(invivable)确实足以让一个人进入精神分析——不止是谈论他的痛苦遭遇,更是谈论他的享乐。
1925年,巴塔耶通过朋友认识了曾在圣-安娜工作过的精神病医生Adrien Borel。有意思的是,Borel的名字与巴塔耶光顾的“妓院”和他生活的“烂摊子”(这两个词在法语里都是bordel)只差了一个字母d,而这个字母的发音正是dé,在法语中表示去除、剥除的前缀。也正是Borel在这一年给他展示了最著名的被凌迟的犯人照片。之后,在《内在体验》(1943)中,他描述了受酷刑折磨之人传递给观看者的共融(communion)式狂喜(extase):“头发竖起,面目狰狞,面容憔悴,血迹斑斑,像妖女一样美丽”[8]。在最后一本书《爱神之泪》(1961)中,他也重新展现了这些相片和对这一享乐的沉迷:“我从未停止对这种痛苦形象的痴迷,既心醉神迷又难以忍受”[9]。通过精神分析,巴塔耶串联起来了他这一痴迷的连续性,他联想到自己沉浸在患梅毒和性无能的父亲的痛苦和死亡中的快感[10]。从这一意义上而言,Borel的介入促成了巴塔耶写作的开始,又扣上了他写作的结尾。
1926年夏天到1927年,他与Adrien Borel正式进入简短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精神分析。在和Madeleine Chapsal的访谈中,他这样总结他的这段体验:
我做过一段时间的精神分析,可能不是很正统,因为只持续了一年。虽然时间有点短,但最终它让我从一个完全病态的人变成了一个相对可以生存的人[…]我写的第一本书是在分析之后才能写出来的,是的,从精神分析中走出来之后。我想我可以说,只有当我以这种方式获得解放时,我才能够写作。[11]
从“难以过活”到“可以生存”(viable),并不是说物理现实中的创伤被清算干净,而是说,在心理现实中,驱力以另一种方式激活。它不再只憧憬自己实在的机能性死亡,而是把死亡以符号的方式演绎在虚构之中,把死亡视为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赌注,引入他者,自此生与死的二元悖论得以在矛盾中延续。Borel的治疗方式并非是弗洛伊德派那样,找到创伤的源头并给予解释,而是和巴塔耶交流如何以其他的方式配置享乐——这种交流甚至是非-语词的,直击感官的。在这个意义上,Borel的操作是前-拉康式的:其治疗的目的不是为了让症状消失,而是为了让症状有潜能地成为创造的线索,让主体找到一个位置,站稳在世界中。
这些精神分析的理论和体验材料,都将成为巴塔耶创作的养料。因此,在当下,我们重新引入这一角度再去看《文学与恶》,更是在塑造一种把他的生命历程纳入虚构中的解构式阅读。雅克·德里达在其1975—1976的研讨班《生死》(La vie la mort)中提出这样解构弗洛伊德《超越快乐原则》的方式:他把biographique(传记性的)一词拆分成bio-graphique[12](生命-图示)。而因为死亡又混杂在生命中,因此又可以写作bio-thanato-graphique(生命-死亡-图示)。他认为,弗洛伊德的自传(autobiographie)和书写场景如影随形。弗洛伊德对其外孙Ernest著名的Fort/Da场景(也就是线圈游戏)的描述嵌套了他对自身死于重病的恐惧和对他者(hétéro)——女儿之死的哀悼,其实也是他自身哀悼、谋杀式和嫉妒式的认同(identification)网络[13]:“(历史)的遗产和嫉妒不仅构建了Fort/Da,而且将Fort/Da构建为自我-生命-死亡-他异图示的书写场景”。精神分析的理论作品、弗洛伊德的生死传记和精神分析史上死亡驱力概念的演变就这样通过“类比”(analogie),几重嵌套在了一起。
书写场景是否是遮蔽死亡之焦虑的面具呢?当我们借助德里达的这一思路,从巴塔耶的自我-生命-死亡-他异图示出发,便可以揭开他书写场景的种种嵌套、穿越《文学与恶》的幻象。但我们不妨从证明这一解读巴塔耶角度的必要性开始。《眼睛的故事》的书写场景中,巴塔耶戴上了Lord Auch的面具,而他的父亲形象被掩盖得只剩下了失明了的、只剩眼白的眼睛,沦为放荡者的玩具。巴塔耶的传记作者Michel Surya写道:“在面具下,只有眼睛是可见的。但在面具下,一张盲人的脸还能看到什么呢?除了两只死了的眼睛荒诞地出现在为它们开的缝隙里,什么也看不见。巴塔耶为自己的名字和父亲的面孔戴上了假名的面具,从中可见的只是死物。在这种情况下,面具产生了一种悖论的效果,即遮盖了活物,而裸露了死物”[14]。而我想补充的是,巴塔耶用虚构的活人名字置换了死人,并不代表他彻底遗弃了死物。他异性死物的不可名状推动了虚构的生产,并一直存在于他的自我-生命-死亡-他异书写图示当中,使得碎片式的写作可以成为一种未达成死亡状态、没有上帝律法而弥散扩张的生命。
现在,我们可以正当地提出《文学与恶》书写中的三重类比关系,观看巴塔耶如何把死亡、动物性和恶蒙上面纱展露其赤裸,如何把自我-他者-生死置换成文学史上永远鲜活的人物和人性:(1)巴塔耶自身的Éros和Thanatos与文学人物的情欲生死类比。(2)童年和原始社会心理的类比。(3)无意识之恶、意识之善(bien)与耗费之恶、劳作之善的类比。当然,这三重类比并非毫无交集的并行关系,而是环套镶嵌在《文学之恶》的书写场景中。
首先,巴塔耶在书写,巴塔耶在书写卡夫卡、波德莱尔、萨德……的书写。如果说,卡夫卡的父亲“代表着权威,他只关心有效行动的价值”,且我们已知巴塔耶真实的生父(le père réel)的一些信息,那么巴塔耶认为的符号性父亲(le père symbolique)是什么呢?行动的世界、介入的世界、功用性的世界。巴塔耶在《卡夫卡》这一章中,选择了共产主义立场来扮演这一符号性父亲,因为“它是典型的行动,它是改变世界的行动”,这一行动显然需要主体负担起责任。面对父亲,卡夫卡“让自己仍然是那个不负责任的孩童”,而巴塔耶在和杜拉斯的访谈中,则承认:“我缺乏那些觉得要对世界负责的人所有的使命感。从某种程度上说,在政治上,我要求拥有作为疯子的免责权……我不是那么疯,但从任何意义上讲,我都不会对这个世界负责。”[15]怎么能要求一个如此焦虑,离完全的疯癫就差一步之遥的人负责呢?然而,当巴塔耶选择为《文学与恶》中一系列文章署名,而非像其他虚构作品中一样戴着笔名的面具出场时,便悖论性地选择承担责任,承担作家的责任。如果说行动让文学处于从属地位,抗争的出路便是拥有以自我赐死为代价的主权性:不为有用、效率、目的而写作,也不为规范化的责任感而写作,相反,是为反道德而写作,为耗费写作,为无目的的恶而写作。
因此,在评述波德莱尔时,巴塔耶也认为,“在他身上占据上风的是拒绝工作,从而拒绝满足;他维持在他之上的义务的超越性,只是为了强调拒绝的价值,以及更有力地体验到不满的生活的焦虑吸引力”。这一取向便是在对未来的关注(与有用性和道德并置)和当下(与消耗和感官享受并置)的关注之间做的选择。主体在做选择时,总会获得和失去一些东西。选择工作,意味着可以累积生存的需要,满足生命的存续,但同时必须要承担“成人”关注未来之首要性的责任;而拒绝承担责任,就如同巴塔耶在他生命中想拥有像疯子的免责权一样,得经受无法满足的持续性焦虑,走向存续的反面——毁灭性的死亡驱力。但把死亡置于主权式的选择之中,便可以取消生命在等待死亡的过程中所等待的利益,因此得以摆脱诗歌、文学对作家的外在要求,遵从内心的私密要求。上帝或各种意义的“父亲”的死允许了巴塔耶不期待“父”所许诺的效用性利益,使他成为自身的主权者,成为自身唯一的责任人。必须经由这样的否定性操作,接受死亡的内嵌,“死刑判决”[16]的立刻到来,死亡在当下享乐时的悬置,巴塔耶才能悖论性地完成书写文学之恶的责任。
从这一意义出发,巴塔耶、威廉·布莱克和詹姆斯·乔伊斯在“无名老爹”(Nobodaddy)这一新造词上汇合了。这一词由无名之辈(nobody)和爹地(daddy)组合而成。而Nobodaddy取自布莱克阅读的圣经中一个人物的名字变形:Abaddon,在希伯来语中指的是毁灭。通过倒置和变形,这个词又可以变成Nobadad。因此,Nobodaddy在布莱克的语境中,代表着不受经典意义上的上帝眷顾的,杂乱无章、幽暗模糊、具有毁灭性力量的原型形象,同时,又是看不见、摸不着,躲在云里享受原乐的嫉妒之父。巴塔耶借用布莱克的这一词时,涉及到的形象更像是上帝所代表的律法消失后的“无头人”(acéphale)。上帝死后,更糟糕的是欲望的消失,主体以前欲望着上帝的欲望,善引导着欲望,而后,主体要去欲望超出上帝欲望之外的东西,便要承担巨大的焦虑,因为上帝不再为任何想要摆脱外在要求的欲望负责。巴塔耶和他评论的这些文学人物进行这样主权式跨越时,不会有任何律法为它们的行动背书,不再有僭越这一欲望存在的合理性。在悲剧性的死亡之上,又叠加了一层喜剧性的欢笑,仿佛孩童在没有父母的房间玩耍时面对破坏性烂摊子的无用(inutile)欢笑。“无名老爹”代表的正是这种荒唐的不司其职,上帝的抛弃。在《文学与恶》中,巴塔耶引用了“幻视者”布莱克的这首诗歌来表达这样“不合时宜的自由”:
当克洛普施托克向英格兰发起挑战时,
威廉·布莱克骄傲地站立起来;
因为那上面的无名老爹,
放屁、打嗝、咳嗽;
然后,他大声地咒骂,震动了大地,
疾呼英国人布莱克。
布莱克在兰贝斯的白杨树下,
正在解手。
然后他从位置上站起来
自转三次,转了三圈。
看到这一幕,月亮面色绯红,
星星扔下酒杯,撒腿就跑[17]……
巴塔耶的世界便是这样无父无头的世界,更是一个没有父法兜底的自由世界。这样的自由永远有着悖论性,它携带着摸不着边界的恐慌,因为主体僭越上帝的欲望后,便要承担无章法世界的到来,类似末世论的恐惧。正如詹姆斯·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写道:“至于这些是罪恶还是美德,无名老爹会在末日降临时告诉我们”。这意味着由“父”承担的价值判断的失灵。这三个人对这一词的使用并非偶然,亚历山大·科耶夫写道:“所有的神秘主义都在这个词里:Nobodaddy”。[18] 毫无疑问,这里对应着拉康所说的“父之名的脱落”(forclusion du Nom-du-Père)——这一概念指的是,没有一块地方,可以使得主体能在其中找到象征性的定位,来回答和命名“父”的显现。因此,“父”在无意义的实在界回归,以妄想、幻觉等的形式出现。
这样的法外之地在现实中的对应物无疑是童年和原始社会。在《图腾与禁忌》中,弗洛伊德试图勾勒起这样的联系:无意识机制和社会文明组织形式之间的联系,以及野蛮人、原始人的心理和人类心理发展阶段的联系。简单来说,他提出了个人与集体进程之间的类比,将主体的驱力与文明的发展相提并论。他假设这些活在所有机制和组织之外的前-原始人展现了文明发展的第一阶段,即所有的性驱力都毫无约束、不以繁殖为目标的阶段。与之平行的,是儿童性驱力的倒错特征——只追求部分性的快乐满足。弗洛伊德为他的立论过程插入了父姓“图腾”来解释:即便在原始人那里也遵守着乱伦禁忌。而巴塔耶则彻底来到“父姓”之前的时代,也就是他在描述《呼啸山庄》所说的“童年的王国”。他着重描写这一被成人的算计所禁止的世界,也就是神圣的领域。在巴塔耶的笔下,它是天真、无邪和对当下享受的关注,是走向善的对立面,“童年的‘冲动活动’类似于神圣的迷醉,它完全处在当下。在儿童教育中,对当下瞬间的偏爱定义了普遍的恶。”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共同违犯了这个世界的理性规则,回归童年时共谋的日子和野性的冲动,拥有律法之外的野性幸福,因此他们最终要接受彼此的献祭。这种主权式选择始终和巴塔耶成为“文学家”的选择是同构的。
热内作为生性顽劣的少年犯,不也一直固着在童年的王国里吗?不也演绎了“成为作家”(devenir-écrivain)“从无到有”的过程吗?首先,我们将建立热内的生性顽劣与巴塔耶的关键概念“耗费”的关系。回到《超越快乐原则》的线圈游戏场景中,观察者弗洛伊德作为“父”在场,他先入为主地认为,小孩子玩线轴应该是把线轴当车一样拖来拖去,而他却拽着线绳把线轴扔了出去。也就是说,精神分析之父认为,小孩子玩汽车、火车才是真正的游戏,而非摔东西、扔玩具。然而,事实上,孩子会毫不留情地在大人眼皮底下摔坏他们的玩具,他们会把玩具赠送给公园里刚认识的玩伴,他们会要求得到和哥哥或妹妹一样的玩具,并在得到它的当下立刻把它扔到储物柜深处。这便是儿童的玩乐——它像夸富宴(potlatch)一样,具有奢侈、赠送和浪费的性质[19],是资本主义规则难以想象的场面。而孩子这样做,是为了对抗大他者这一大人世界的符号秩序。在公园中当着其他家长的面因为抗议父母而大叫,为了就是“失去”(perdre),失去“父”强调的秩序,失去效率,同时让大他者也失去脸面。孩童正是在这一肆意玩闹的空间中获得主权性。热内和他笔下的人物便是这样的“野孩子”。在他眼里为了利益而偷盗,满足生活的需求,这样的恶就成为了积累而非耗费,而因谋杀而被判死刑,则走向了耗费的最高程度:自我毁灭。巴塔耶这样评论:
热内只能在恶中成为主权者,主权本身也许就是恶,这一恶因为受到惩罚而更加确定是恶。但偷盗远没有杀人能得到的声望多,坐牢和送上断头台相比也是如此。罪的真正主权是属于那些被处决的杀人犯的。热内努力用想象力和看似武断的方式赞颂王权,在监狱里,他不顾关禁闭的惩罚,大声喊叫:“我在铁骑上高贵地生活……,我进入他人的生活就像一位西班牙的最高贵族进入塞维利亚大教堂一样”,他的虚张声势脆弱但又意味深远。如果处处都充满死亡,如果罪犯造成了死亡又等待着接受死亡,他的忧伤便会让位给他认为是完满的主权性。
对律法和禁忌的僭越让无名之辈(nobody)一跃成为王室后代,拥有贵族的荣耀,过街老鼠成为目光的焦点,如同“名流”一样以盛名存世。这样的“成名”以自身的死亡为代价,它蔑视了生命存在的有限性,因为它像安提戈涅的行动一样,打破了成文“父法”的界限,通过埋葬兄弟的举动,在尚未死去的时候就被父法的世界除名,来到神圣律法的地域。毁灭自身的存续,但在此基础上,犯罪主角的非人性让她发出刺眼的光芒,使她独异的主体性能够被创造出来,并延续下去,这便是热内给少年犯戴上璀璨皇冠的真正意味。如同巴塔耶评价的那样,这种存在之美是“是由对延续的漠视、甚至是由死亡的诱惑所造就的”。可以补充的是,对延续的漠视其实是对人法时间局限的漠视,而通过耗费之恶、毁灭之恶,热内和巴塔耶完成了主体被抛在没有符号秩序的荒漠之后,无中生有的创造。正如拉康在《研讨班七:精神分析的伦理学》中所说:“毁灭的意志。重新开始的意志。他异之物的意志,只要一切都可以在能指的功能基础上提出质疑。[……]在这一点上弗洛伊德思想的要求其实是合理的,因为它要求相关的东西被表述为破坏驱力,正因为它怀疑所有的存在之物。但它也是一种从无到有的意志,一种重新开始的意志。”[20]不要忘记,拉康正是从本书的主人公之一萨德那里学来的毁灭冲动——真正的犯罪不仅是杀死身体,更是对自然交换秩序的毁坏。巴塔耶和莫里斯·布朗肖则看到,在巴士底监狱中,萨德把一切存在者的局限性、所有的创造物都驱逐出去,达到了彻底的毁灭。宇宙的孤寂和想象的浩瀚存在于四壁空无一物的牢房中,感官的满足无法通过肉身实现,于是欲望无尽的创造、萨德式的理性思辨都得以自由滋长。
当我们回顾《文学与恶》中那些“成为作家”的道路时,会发现在“文学何为?”这一问题上,巴塔耶的立场和萨特的介入式写作分道扬镳。在这本书中,巴塔耶提到萨特谴责这样的消费社会,而期待以苏联为范式的生产社会。巴塔耶承认耗费本就该被谴责,然后呢?他追求丑闻式的写作,及其能传递的交流:一旦这样的恶喷射向读者,读者立刻就沾染了神圣之物(即不可触碰的禁忌之物)的肮脏。无论他的反应如何,都证明了这一传染方式的命定性,即人们无处可逃。布朗肖评价巴塔耶《爱华妲夫人》的这句话很好地总结了这点:“这本书正是以这种方式抓住了我们,因为它不可能让我们毫发无损,这是一本真正丑闻性的书,如果丑闻的本质就是人们无法抵御它,而且人们越是抵御丑闻,就越会将自己暴露在丑闻中”[21]。
我们最终会来到普鲁斯特,以及他通过书写承载起的东西——同巴塔耶做的一样,不是别的,正是死亡本身。书写欲望(Vouloir-Écrire)和书写之间的关系正如(死亡)驱力与(写作)活动的关系一样不言自明。罗兰·巴特这样评论马塞尔的“成为作家”之路:“对于普鲁斯特而言,写作也意味着死亡可以用于某事,书写书写的欲望(écrire le Vouloir-Écrire)说明了这点,即可以利用死亡,即书写欲望和书写可以用来拯救、征服死亡;不是他自己的死亡,即便他在与之抗争,而是那些他曾爱过之人的死亡,通过写作、通过使他们永存、通过将他们从非-记忆中树立起来,他为他们做见证”[22]。正是由死亡的黑暗造就出的对比,生之幸福才令人渴望,因此,巴塔耶说普鲁斯特比萨德更加狡猾,“他让恶习保留了其令人憎恨的色彩,和德性的谴责”。保留恶的可谴责性,我们也偷偷为自己保留了幸福的可被欲求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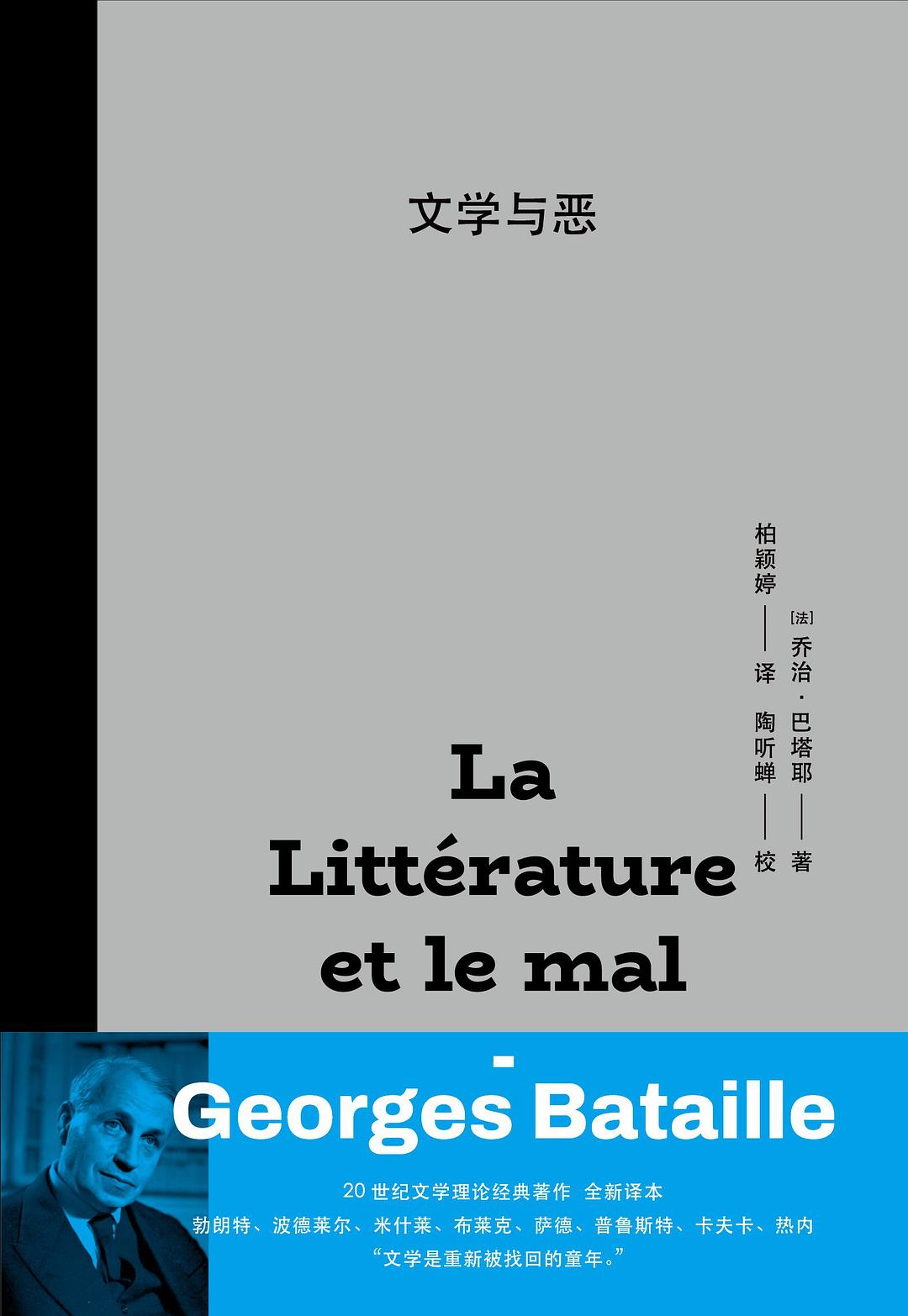
《文学与恶》;[法] 乔治·巴塔耶;译者:柏颖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
注释:
[1] 圣状(sinthome)是症状(symptôme)的一种古老的书写方式,拉康在1975—1976年的研讨班上使用这一术语来指写作对于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特殊作用。弗洛伊德曾认为症状也是一种痊愈的尝试(tentative de guérison),而在拉康派精神分析看来,这一概念现在用来指主体用来站稳脚跟、串联三界(想象界、符号界、实在界)的特殊方式,或是指主体与语言的特殊关系。
[2] 在拉康看来,阉割指的是儿童放弃与母亲的融合状态,从想象性关系过渡到符号性关系(学会语词化他者的缺席、进入社会联系)的过程。
[3] 当谈及儿童性欲时,弗洛伊德认为儿童因其探索身体时驱力的局部性,具有多样态性倒错的倾向。
[4] Georges Bataille, Œuvres Complètes, tome XII, Paris, Gallimard, 1988, p.554 et 565.
[5] 罗杰·凯洛瓦在《人与神圣》(L’homme et le sacré)中也几次提到人面对神圣之物时的矛盾情感:神圣之物既是有益的又是邪恶的,既会激发欲望又会激发恐惧。
[6] Georges Bataille, Œuvres Complètes, tome I, Paris, Gallimard, 1970, p.344.
[7] Georges Bataille, Histoire de l’œil, Œuvres Complètes, tome I, op.cit., p.75. 巴塔耶把“怀孕”这一词赋予给父亲,而并不在意父亲的实际生理功能。
[8] Georges Bataille, L’Expérience intérieure, Œuvres complètes, tome V, Paris, Gallimard, 1973, p. 139.
[9] Georges Bataille, Les Larmes d’Eros, Œuvres Complètes, tome X, Paris, Gallimard, 1987, p. 627.
[10] Michel Bousseyroux, « La psychanalyse de Georges Bataille », dans L’inconscio letterario, n°6, dicembre 2018, p. 324.
[11] « Entretien avec Madeleine Chapsal », parue le 23 mars 1961 dans L’Express, n°510, p.35. 笔者按:巴塔耶在精神分析结束的后一年1928年,用笔名Lord Auch写了《眼睛的故事》。
[12] Bio(s)这一前缀源自古希腊语 βίος,表示生命。而graphique源于γραφικός,表示书写的动作。
[13] Jacques Derrida, La vie la mort. Séminaire (1975-1976), édition établie par Pascale-Anne Brault et Peggy Kamuf,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2019, p.139. « Et le legs et la jalousie ne construisent pas seulement le fort/da mais le fort/da comme scène d'écriture auto-bio-thanato-étéro-graphique ».
[14] Michel Surya, Georges Bataille. La mort à l’œuvre, Paris, Gallimard, 1992/2012, p.113.
[15] Georges Bataille, « entretien avec Marguerite Duras », France-observateur du 12 décembre 1957.
[16] 《死刑判决》为莫里斯·布朗肖的书名,法语标题L’arrêt de mort又可以被译为“死亡的暂停”。
[17] « Poèmes mélangés », dans William Blake, Poetry and Prose, p.103.
[18] Cité par Michel Surya, Georges Bataille. La mort à l’œuvre, op.cit., p.350.
[19] Marcel Mauss, « Essai sur le don. Forme et raison de l’échange dans les sociétés archaïques », dans Sociologie et anthropologie, Paris, PUF, 1950, p. 239.
[20] Jacques Lacan, Le Séminaire. Livre VII, L’éthique de la psychanalyse, Paris, Seuil, 1986, p.152.
[21] Maurice Blanchot, Le livre à venir, Paris, Folio essais, 1986, p.262.
[22] Roland Barthes, La preparation du roma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8-1979 et 1979-1980),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2015, p.37.

- 致命三秒,真相待解
- 外交部回应中方有关联合演训
- 王毅谈中俄务实合作成果和目标

- 雷军回应SU7车祸:很多问题此刻还没办法回答,承诺无论发生什么小米都不会回避
- 美股开盘:道指跌0.38%,标普500指数跌0.38%,纳指跌0.46%

- 太阳系行星中,有一颗星在傍晚被称为长庚星,清晨被称为?
- 量子力学中,描述粒子动量与位置不能同时精确测定的原理

- 15又见庞麦郎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