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普鲁斯特:仿佛贡布雷不过是一道窄梯联结起来的两层楼,仿佛那里时间永远是晚上七点
追忆逝水年华(第一卷):斯万家那边
[法] 马塞尔·普鲁斯特 著 陈太乙 译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01
在未来寻回消逝的时间
文/陈太乙
2019年底,读书共和国的郭重兴社长与木马文化社长陈蕙慧女士邀我重译《追忆逝水年华》,并慨然允诺十年。从此,我不再是普鲁斯特世界的局外人。
太难、太长、太绕、不知所云,再也不能拿这些借口来逃避这套传说,而且动作要快,因为,人生真的太短,十年转眼已过了五分之一。然而,即使如此,似乎已过了好久,仿佛还很遥远。终点会安然在那一端等我吗?回首先前的五个十年,惊觉如此匆匆,恍惚自己做了什么,记住了什么…… 普鲁斯特神启一般地告诉我:答案得往未来去追寻。
我尽可能地将前一段翻译人生装进行囊:塞荷的“泛”思想铺就一个包罗万象的宇宙、比斯万稍长的波德莱尔为第二帝国的巴黎涂上现代色彩、与叙事者年纪相近的阿兰呈现某种博学者的样貌,以古典哲思迎对工业革命带来的进步、尤瑟纳尔的文字气场和重建两千年前时空的功力、甚至不漏掉欧赫贝的奇幻想像、三境边界里的失重感,当然,也绝不忘记悉心照顾亲爱的马塞尔至他离开我们那天的塞莱斯特。出发,首先航向充满参考书籍、影音广播、讲座展览、手稿文献,比《追忆》本身更深更广的资料汪洋。Jean-Yves Tadié的两大册普鲁斯特传记和Annick Bouillaguet主编的普鲁斯特辞典常驻案头,Antoine Compagnon在法兰西公学院讲授的相关课程我听了一遍又一遍。《斯万家那边》自1913年初版至今已超过一个世纪,在网路资源丰沛,共享观念发达的时代翻译这套书,非常幸福。
一个世纪后的读者,应当也是幸福的。经过百年来的发展,精神分析已成显学、社会趋向多元与包容、艺术表达更富创意、更摆脱框架,正到了品味普鲁斯特的最佳时刻。因此诞生这项经典重译的计划。感激多位前辈开垦这片土地,如今,我们希望它成为容易亲近的乐园,就像贡布雷的教堂,随时可进去默祷片刻,每个星期日固定去望弥撒;彩绘玻璃雕刻壁画织毯诉说故事,是美的启蒙,文化的传承;守护镇民的日常生活,亦为游子指引家乡的方向;时光在这里流淌,心灵在这里休憩,“若是外面天色灰暗,教堂里必然明媚灿烂”。

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
然而,如何捉摸短句隐晦不明的意味,处理那些迂回的长句?要安置逗点之间、破折号之间或括弧里的项目,扣紧相隔甚远的关系子句及其先行词,用流畅到位的中文表现且不违背原意,不简化细节(因为所有逻辑都在细节里!)同时令读者乐意细细咀嚼;如何扭转众人对普鲁斯特叨叨碎念的既定印象,进而认识他的幽默、轻盈、灵巧…… 挑战何其多。很幸运地,出版社时时倾听我的需求,不吝人力物力,给予温暖的支援;我不乏为我解惑的师友,还有挑灯夜读,一面记下每个卡关段落并陪我找出解法的秘密读者,以及,最重要的,一位心思缜密,极其专业,灵魂比我更贴近普鲁斯特的编辑。我想,我们一起为中文读者找到了契合内心独白的阅读节奏。
我以1987年的七星文库版及1988年的Folio版为文本依据,翻译大约一年半,修稿不只六个月。每一次修稿,每一次重读,小范围大范围地重读;每一次重读皆修改,每一次修改皆多一次更贯通原意,更贴近原文,领略更多文学之美,作家之神妙的机会。那亦是激发自己,说服自己尚未枯竭的机会。于是稍懂普鲁斯特为何改稿不停,至死方休:那是与自己的对话,为自己打气,藏着活下去的动力。重读,修改,昨日死,今日生,预约一个理想中的,未来的自己,为她准备后续的旅程。
谨愿此版翻译能令华文读者感受只有透过文字才能体会的真与美。

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陈太乙 译)书籍设计内外封
深度阅读
《斯万家那边》(选读)
[法] 马塞尔·普鲁斯特 著
陈太乙 译
就像这样,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当夜半清醒,再度回想起贡布雷时,我再见到的总也唯有这样一片亮光,在朦胧幽暗当中清楚浮现,宛如火焰弹的火光,或是电子探照灯的光束,照亮了屋子,区隔出其他仍深陷漆黑之处:在相当宽广的底层,小沙龙、餐厅、那条阴暗小径的开端,将从那儿走来的斯万是无意间使我烦忧的始作俑者,还有衣帽间,我慢慢走至尽头,从那里踏上楼梯第一阶,那么残酷地非得爬上它不可。那道楼梯独力构成这座不规则金字塔极为狭窄的锥台,而塔的顶端即是我的卧房和小走廊及玻璃门,妈妈便从那里进来。一言以蔽之,总是在同一时间见到那亮光,从周围可能有的一切隔离而出,孤立于漆黑之上的,是我更衣就寝时分那场大戏绝对必要的场景(就像那印在去外省巡演的老戏码剧本上的首行提示),仿佛贡布雷不过是一道窄梯联结起来的两层楼,仿佛那里时间永远是晚上七点。说实话,若有人问起,我本可回答他:贡布雷还包含其他事物,也存在其他时刻。但由于日后我记起的一切都将仅只源于自主的记忆,属于智性的记忆,而且由于这记忆提供的讯息完全不含那段过去,我本来绝不会出现去细想其余这个贡布雷的念头。这一切对我而言其实皆已逝去。
永远逝去了吗?有此可能。
这一切当中有许多偶然,而第二种偶然,我们自身的逝去,通常不允许我们长久期望第一项偶然带来的好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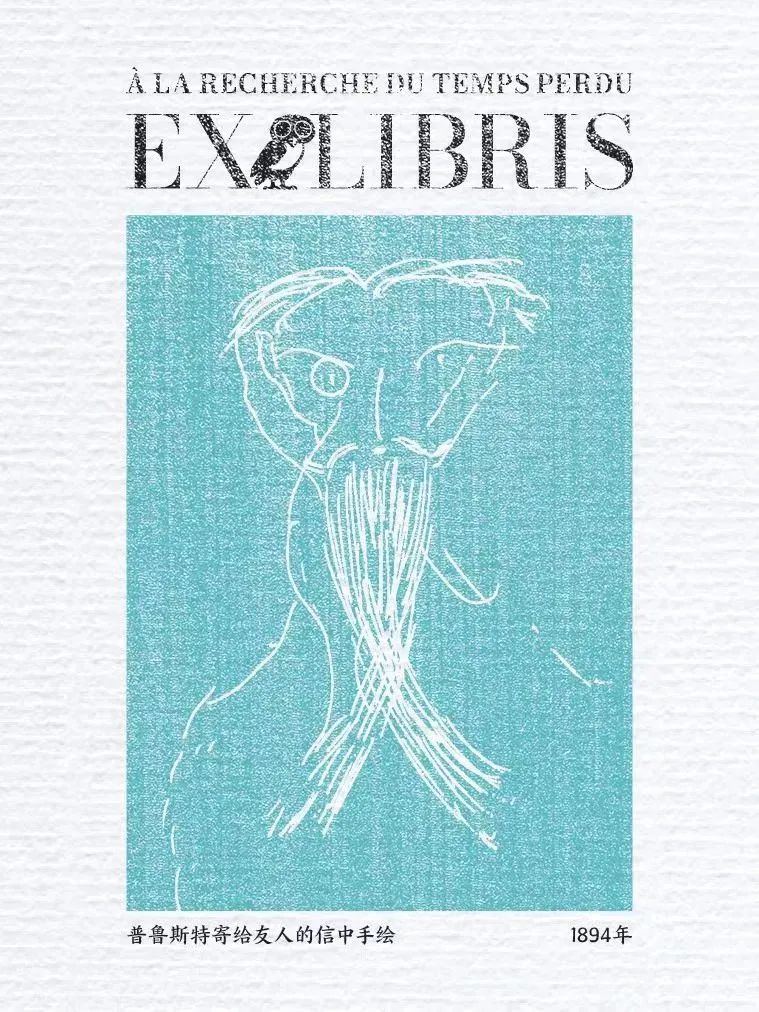
《斯万家那边》藏书票(仅首印赠送)
我觉得凯尔特人的信仰十分有道理:他们相信我们失去的那些人的灵魂,都被禁锢在某个较低等的生物当中,困在一头动物,一株植物,一样无法灵动的东西里,对我们而言,的确已然消逝。直到有一天,对许多人来说永远不会到来的一天,我们刚好经过那棵树,或拥有困住他们的那样东西。于是他们骚动起来,呼唤我们,一旦我们认出他们,魔咒就被破除。被我们拯救的灵魂克服了死亡,回来与我们一起生活。
我们的过去也是如此。试图追忆过去是枉费心机,穷尽智性必徒劳无功。过去隐身在其领域和范围之外,寄寓于某项我们意想不到的实质物体(于这项实质物体带给我们的感受)。这项物体我们能否在死前遇见,或根本遇不见,但凭偶然决定。
早在许多年前,关于贡布雷,凡不属于我就寝前那场大戏和那情节的一切,对我皆已不复存在。某个冬日,回到家时,母亲看我很冷,即使有违我的习惯,仍提议让我喝一点茶。我起初拒绝了,但不知为什么又改变了主意。她派人找来一块叫做小玛德莲的那种胖胖短短的蛋糕,那似乎是用圣雅各伯大扇贝的贝壳当模子压出了条纹。没过多久,没多做想,饱受镇日的阴郁湿冷及对明日的悲观折磨,我举起茶匙,将一小块用茶汤浸软的玛德莲送进嘴里。就在那口混合着蛋糕碎块的茶汤触及上颚那瞬间,我全身一阵轻颤,全神贯注于出现在我身上的非比寻常现象。一股美妙快感全面袭来,让我与世隔绝,我对其成因却毫无头绪。这股感受瞬间使我生命中的潮起潮落变得无所谓,使灾厄无害,使生之短暂化为虚幻,一如恋爱的效用,使我全身充盈一份珍贵的精华:或者应该说,这精华并不在我身上,我即是那精华。我不再自觉平庸,无关紧要,不是个终将一死的凡人。如此强大、充沛的喜悦究竟从何而来?我觉得它与茶和蛋糕的滋味有关,但又远远超乎其上,性质应该不同。从何而来?意味着什么?可从何处领略?我又喝了一口,觉得比起第一口毫无增色,第三口给我的感觉又比第二口还更少些。我该就此打住了,茶汤的效力似乎在逐渐消退。我追寻的真相显然不在于它,而在于我。茶唤醒了真相,却不认识它,只能模糊地依样重现我不知如何诠释的那份相同体悟,而且力道越来越弱。而我希望至少能够,等过了一会儿之后,再次要求它出现,完好无缺,随我所欲,得以明确厘清定案。我放下茶杯,回过神来。真相要靠神智去寻找。但怎么找?严重的不确定感;当神智这个追寻者即为那该去寻找的阴暗国度,而在那里,毕生累积的知识派不上任何用场,他总有力不从心之感。追寻?何止如此,堪称创造。他面对的那事物尚不存在,且唯有他能实现,然后引入他的灵光之中。

电影《追忆逝水年华》(2010)剧照
我重新问起自己,这种陌生状态可能是什么?它并未带来任何合乎逻辑的证据,但那明显的喜悦至福之感、那真实之感当前,其他一切尽数烟消云散。我试着想让那感受重现。思绪将我拉回咽下第一匙茶汤时。我要求神智更努力,将散逸流失的感受再次带回。然后,为了不让任何事物破坏神智即将试图重新捕捉它的冲劲,我除却所有障碍,所有奇怪的念头,掩上耳朵,不让注意力受隔壁房间传来的噪音侵扰。但是,我感觉到神智逐渐疲乏,配合不上,于是反过来强迫它实行我原先拒绝的散漫放松,去想其他事情,在极端的最后一搏之前恢复元气。然后,再一次,我清空心神,重新呈上那依然鲜明的第一口茶汤的滋味,感觉到内在有种什么在轻颤,在移动,想往上蹿,像是从极深之处拔锚而起的东西。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它缓缓上升。我感觉得到阻力,听得见这段路程沿途的骚乱。
的确,如此在我心底搏跳着的应当是意象,视觉记忆,它连接到这股滋味后企图继续跟随,一路追踪到我身上。但那挣扎跳动的记忆太遥远、太模糊了,若说我勉强瞥见难以捉摸的杂色漩涡搅混出的中性光泽,却无法辨识其形体,无法宛如请求唯一可能胜任的译者那样,请求它为我翻译出滋味,它那亦步亦趋的同伴,所见证之事;无法请求它告诉我,那究竟关乎哪种特殊状况,是过去哪个时代的事。
是否终能浮升至我意识清楚的表层?这份回忆,旧逝的那一刻,被一模一样的一个时刻从心底深处撩拨,触动,翻掀,那么远地吸引过来?我不知道。现在我什么也感觉不到,它停止了,也许又下沉了;谁知道它会不会再从它那漆黑深夜中升起?至少十次,我不断重新开始朝它探询。每一次,带我们绕过所有困难的任务、所有重要工作的软弱不坚总是劝我放弃,要我继续喝茶,只要想着今日的烦恼,想着明日的渴望,想着那些让人能毫无负担地反复思索的事。
突然间,那回忆浮现在我脑海。这股滋味是在贡布雷的那个星期天早晨(因为在星期天那天,去望弥撒之前我不出门),当我去雷欧妮姨妈的房间向她道早安时,她请我吃的那一小块玛德莲蛋糕,她先放进了她的红茶或椴花茶里沾湿一下。在尝到味道之前,见到小玛德莲蛋糕并未令我想起任何事。或许是因为在那次经验之后,即使没吃,我也常在糕点铺的托盘上见到它,它的形象已脱离贡布雷那段岁月,连结到其他较近期的时光;或许因为,这些弃置于记忆之外如此之久的回忆,没有任何残存,一切都已分崩离析;举凡形体——也包括那贝壳状小糕点,在那朴素又虔诚的褶纹之下,显得那么丰腴诱人——皆遭废除,或者,沉睡不醒,失去扩张的力量,难以连结意识。但是,当生灵死去后,事物毁坏后,一段旧日过往留不下任何东西,唯有更微弱却也更猛烈,更不具象,更持久,更忠实的气味与滋味得以长久留存,如同幽魂,徘徊所有残骸废墟之上,回想、等待、期望,在它们难以捉摸的微小粒子上,不屈不挠地,扛起辽阔无边的回忆宫殿。

电影《追忆逝水年华》(2010)剧照
一认出姨妈给我的那浸过椴花茶的玛德莲滋味(虽然彼时我还不知道这段回忆为何令我如此快乐,而且迟至许久之后才发现其原因),她房间所在的那幢路旁灰色老房子立即如同剧场布景般浮现,就搭在面对花园的小楼后方,小楼原是为了我父母而在房子尾端加盖的(在此之前,我脑海中曾再见到的唯有那个截面);随之而来的还有大宅,城镇,午餐前他们送我过去的那座广场,从早到晚无论晴雨我都会去买东西的那些街道,若是天气风和日丽我就会走的那几条路。这好比日本人那套游戏:他们在一个盛满水的瓷碗里浸入原本看不出是什么的小纸团,纸团一旦碰水就舒展开来,逐渐成形,染上颜色,各有不同形貌,或变成清晰可辨的花朵,房子,人物,一如所有正在我们家院子和斯万先生家的庭园里绽放的那些花,还有维冯纳河的睡莲,以及小村里朴实的人们和他们的小住屋和教堂和贡布雷全镇及其周遭区域,全都有了形状与实体,连城带着花园,这一切全从我的茶杯涌现而出。
(本文原题为《挑战普鲁斯特也是一种人生动力,<追忆逝水年华>推出个人独译新译本》,作者:陈太乙, 新媒体编辑:郑周明,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文学报)
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Marcel Proust)是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意识流文学的先驱与大师,也是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普鲁斯特出生于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自幼体质孱弱、生性敏感、富于幻想,这对他文学禀赋早熟起了促进作用。中学时开始写诗,为报纸写专栏文章。后入巴黎大学和巴黎政治学院钻研修辞和哲学,对柏格森直觉主义的潜意识理论进行研究,尝试将其运用到小说创作中,可以说柏格森、弗洛伊德成了他一生文艺创作的导师。1984年6月,法国《读书》杂志公布了由法国、西班牙、联邦德国、英国、意大利王国报刊据读者评选欧洲十名"最伟大作家",所排名次,普鲁斯特名列第六。
原标题:《普鲁斯特:仿佛贡布雷不过是一道窄梯联结起来的两层楼,仿佛那里时间永远是晚上七点|纯粹新书》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