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陈子昂,自我深处的孤独
开元、天宝时期唐诗的繁荣,是与生活年代稍早的一批诗人致力于探索诗风转变的各种途径密切相关的。其中首先在实践与理论两方面倡导新诗风的,是陈子昂。
陈子昂性格旷放倔傲,仕途又遭挫折,因此他的诗大都慷慨苍凉,具有一种唐初诗歌中不多见而与汉魏西晋诗歌有较多联系的苍劲之风。
他的组诗《感遇》三十八首,诗旨与形式上承阮籍《咏怀》诗,又参以左思诗的骨力和手法,主要抒写对时事及个人境遇的感慨,虽有一些篇章由于过分注重玄学式的理念而显得诗味不足,但大都慷慨苍凉。如第三首:
苍苍丁零塞,今古缅荒途。
亭堠何摧兀,暴骨无全躯。
黄沙漠南起,白日隐西隅。
汉甲三十万,曾以事匈奴。
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孤!
以苍茫无垠的塞上荒原为背景,将由汉及唐的数百年战争史纳入诗境,通过暴露于荒野的不完整的尸骨、大漠里如屏障般漫天而起的黄沙等极富感情色彩的、惊心动魄的意象,对残酷的战争进行了严肃的反思。
又如第二十九首,写垂拱三年丁亥(687)武则天为袭击吐蕃而下令唐军进攻羌人,致将士毫无意义地奔走于危岩冰雪之间,风格与曹操的《苦寒行》颇为相似。
其中“严冬岚阴劲,穷岫泄云生。昏曀无昼夜,羽檄复相惊。攀跼竞万仞,崩危走九冥。籍籍峰壑里,哀哀冰雪行”数句,用战士行军的艰苦侧面描绘战争的严酷,使自然的山石、风云、冰雪都带有一重压抑人心的基调,从而把作者对“丁亥岁云暮,西山事甲兵”的忧虑与不满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达了出来。
但从唐诗发展的历史来看,陈子昂诗歌更具有独特性的一面,是其中表现出的对自我的关注及其随之而来的孤独感。如《感遇》第二首: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
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
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
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
此诗以香草兰、若(杜若)为喻,写它们“幽独”地生于“空林”,春、夏间茂盛、美丽,但时光迅速流逝,终至凋谢,任何希望(“芳意”)都无法实现;由此来抒发其在冷漠的环境中的孤独和绝望,渗透着深重的失落感和高度的自傲。
感情内涵甚为丰富。而在此类诗中最突出的则是其千古绝唱《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除了广阔的天地,诗中没有任何多余的背景或道具,所有的,只是一个孤独的自我。
这一自我置身于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场景中,眼前与心中所呈现的,是时空的无尽、历史的悠远,以及个人生命的短促,这怎能不使人悲从中来,为自己一腔的抱负与热血洒一掬痛切之泪!
值得注意的是,陈子昂所描绘的这一在中世文学拓展期具有士大夫通性意味的自我及其孤独感,其创意很可能受到阮籍《咏怀诗》第四十六首“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等诗语的启发,因为阮籍在登高而望时也只看到旷野和失群的鸟兽,却看不到人类;
但陈氏在表现方式上突破了阮诗的通体五言,而采用五六言交替并且句式相对拗口的形制,以反常规的诗歌形式,呈现不同寻常的诗歌境界,从而凸现文学中的个人形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创举。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陈子昂又是一位力图改变、扭转唐初诗风的文学理论家;其理论要旨见于《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东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解君云:“张茂先、何敬祖,东方生与其比肩。”仆亦以为知言也。故感叹雅制,作《修竹诗》一篇,当有知音,以传示之。
序中十分引人瞩目的,是其“文章道弊五百年矣”的感叹和对齐梁诗“彩丽竞繁,兴寄都绝”的不满。而从序中看,陈子昂提倡的,是“汉魏风骨”和“正始之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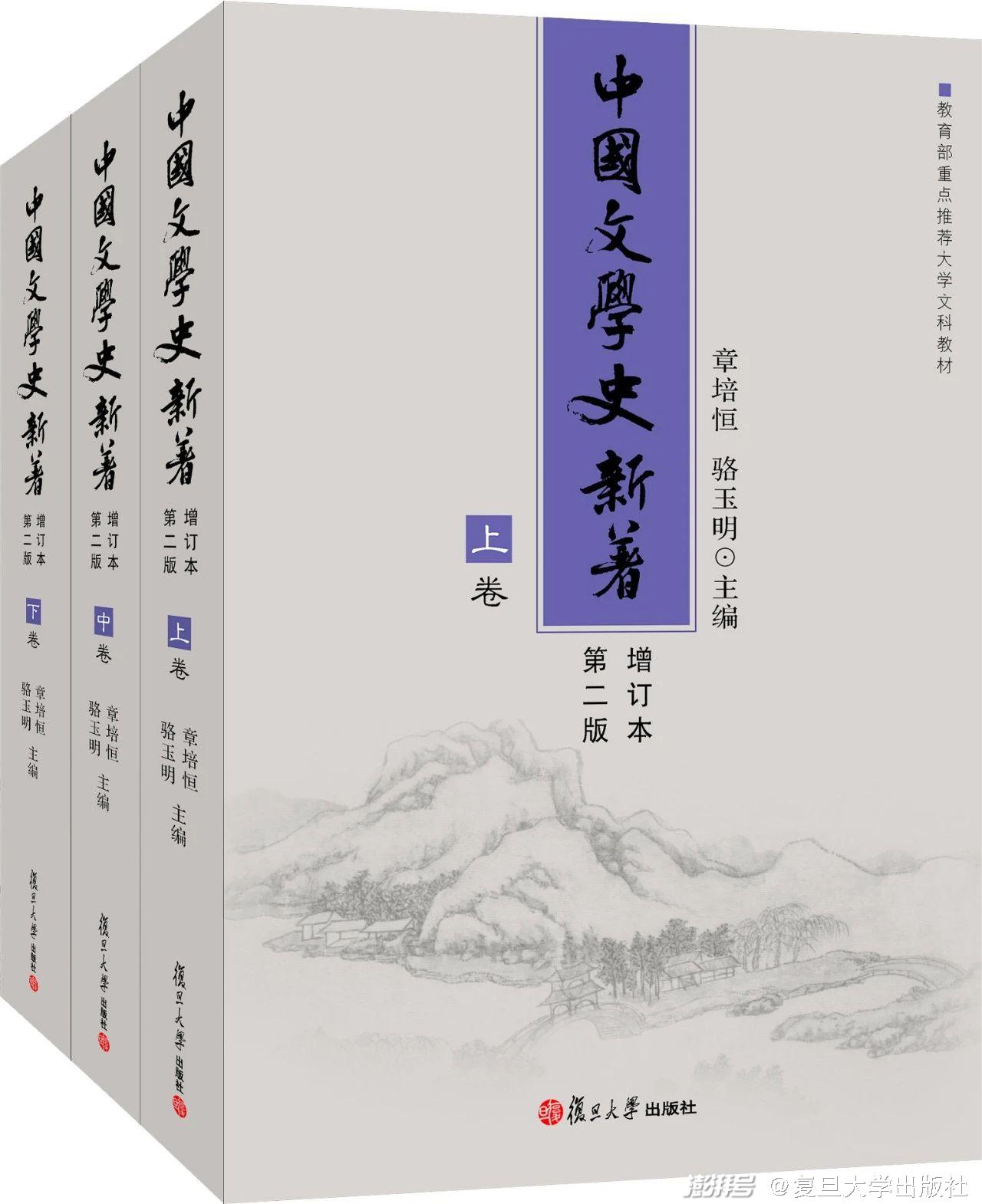
《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第二版 章培恒 骆玉明 主编
两者作为诗歌风貌,在陈子昂的诗中有明显的表露,再结合序中所说东方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等语,可以体会陈氏的宗旨是希望唐诗的发展回到以建安、正始文学为代表的比较注重内质的道路上去。
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将“彩丽”与“风骨”相对立,将齐梁与汉魏、正始之风相割裂,则不免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这中间另有一问题可以讨论,即陈子昂的这篇序中所言及的“兴寄”、“风雅”究竟是指什么?这就需要来读一读他于作序同时“感叹雅制”而作的《修竹诗》:
龙种生南岳,孤翠郁亭亭。
峰岭上崇崒,烟雨下微冥。
夜闻鼯鼠叫,昼聒泉壑声。
春风正淡荡,白露已清泠。
哀响激金奏,密色滋玉英。
岁寒霜雪苦,含彩独青青。
岂不厌凝冽,羞比春木荣。
春木有荣歇,此节无凋零。
始愿与金石,终古保坚贞。
不意伶伦子,吹之学凤鸣。
遂偶云和瑟,张乐奏天庭。
妙曲方千变,箫韶亦九成。
信蒙雕斫美,常愿事仙灵。
驱驰翠虬驾,伊郁紫鸾笙。
结交嬴台女,吟弄升天行。
携手登白日,远游戏赤城。
低昂玄鹤舞,断续采云生。
永随众仙去,三山游玉京。
诗将修竹称为“龙种”,当其为“伶伦子”所取而制成箫后,对于不能保持“终古保坚贞”的初衷并不感到特别遗憾,反而有“信蒙雕斫美,常愿事仙灵”、“永随众仙去,三山游玉京”的庆幸与表白,对于“张乐奏天庭”、“结交嬴台女”等等亦感到无上光荣而颇加渲染。
如果说这样的诗有“兴寄”,则其“兴寄”所在必是作者本人对于身列朝班的得意,带有极强的功利色彩;如果说这样的诗“风雅”,则这种“风雅”也并没有超出齐梁以还文人感谢圣恩之作中常见的那种丽辞堆砌的套路(这种堆砌从文学史上看可以追溯到汉赋)。
因此,在肯定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确为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时,如认为其所云的“兴寄”也有崇高的内涵,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其实真正能代表陈氏一生文学成就的,还是像《登幽州台歌》那样充分表现了自我及个人孤独感的诗,以及像“怀挟万古情,忧虞百年集”(《秋园卧疾呈晖上人》)这般凝聚了时空、历史和个人深刻感受与沉郁感情的诗句,而不是《修竹诗》一类的作品。
*本段内容选自《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第二版第七章第一节,有删减。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