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透过《罪与罚》这道棱镜,文豪如何走出人生低谷
传记作家约瑟夫·弗兰克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撰写的系列传记现在被公认为是传记作品在二十世纪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在以各种语言撰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中,这也许是最佳作品。
在努力撰写这部传记的漫长过程中,弗兰克还根据他对西方思想的敏锐见解撰写了一些文章、书评和随笔,阐述当西方思想透过俄罗斯棱镜反映出来时如何改观变形以及如何被赋予新的意义和内涵。多年来,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这种相互影响深深吸引了弗兰克,同时也为这些论文提供了焦点。

近期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贝贝特引进出版的《透过俄罗斯棱镜:文学与文化随笔》一书,汇集了弗兰克撰写的二十篇文章,它们涉及孕育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些伟大小说的文化以及二十世纪初期俄国形式主义者的批评理论,后者的观念至今仍然塑造着我们对俄罗斯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看法。本书的内容包括对雅各布森和巴赫金的著作的评价,也包括对一些与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理论和思想发展有关的著作的评价。这些文章汇集在一起展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某种富有力量的批评才智,它们涉及的问题因弗兰克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产生,但是,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极大地超越了这位小说家个人所处的时代和地域。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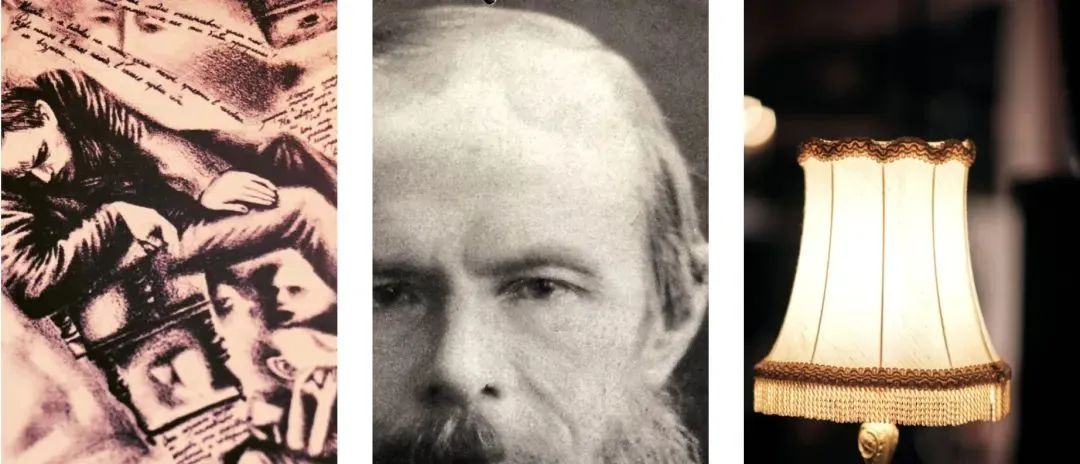
《罪与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人们或许可以感觉到,他的天赋在这部小说中以最纯粹、最清晰的形式表现出来。流放西伯利亚(一八五○至一八六○年,其间在苦役营里度过了四年)归来五年后,他开始创作这部小说,那时他与哥哥米哈伊尔在六十年代初期共同编辑出版的两份文学时事评论杂志中的第二份刚刚倒闭不久。这部小说的创作正值一个个人极度痛苦的时期,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私生活突然遭遇灭顶之灾,他正竭尽全力寻找一个新的立足点进行重建。他患有肺结核的第一任妻子——曾经被他称为“红装骑士”,某些性格特征在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马尔梅拉多娃身上表现出来——在长期病危、历尽令人心碎的病痛折磨之后于一八六四年四月病故。几个月后,与他合作默契共创事业的哥哥米哈伊尔突然去世。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哥哥去世后就像古代的奴隶一样拼命工作竭力维持他们的《时世》杂志的运转,但事实证明他的努力是徒劳的,而且使他背上了巨额债务。
由于在圣彼得堡被债主逼债,他希望去欧洲旅行得到一些清静。以前在欧洲小住曾经使他的癫痫症状有所缓解,他还期待与年轻作家阿波利纳里娅·苏斯洛娃重聚。他对苏斯洛娃依旧怀有强烈的感情,一直与她保持通信,仍未放弃使她回心转意的希望。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八六五年春天忙于为这次旅行四处筹集必要的资金,并且设法从为帮助贫困知识分子和大学生而设立的文学基金会(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八六三至一八六五年间担任该组织管理委员会的秘书)弄到了一笔贷款。他还与几家期刊接触,提出了创作一部新小说的想法。

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写给《祖国纪事》杂志主编安·亚·克拉耶夫斯基的一封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描述了新小说的构思:“我的小说题为《醉鬼》,与当前的酗酒问题有关。它不仅涉及这个问题,而且表现它衍生的所有问题,尤其是描写酗酒成风的情况下家庭以及儿童教育等一系列问题。”他还说,小说至少有三百页篇幅,可能更长;他要求预付三千卢布稿费,对于他这种地位的作家来说,这比通常的标准低得多。尽管由于急需放弃了作家的自尊心,他的要求仍然遭到拒绝。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求助于一个名叫Ф.Т.斯捷洛夫斯基的冷酷无情的出版商,后者向他支付他要求的稿费,作为交换,他允许后者出版他的三卷本作品集;另外,陀思妥耶夫斯基保证在一八六六年十一月一日以前向斯捷洛夫斯基提供一部新作,至少是一部中篇小说。如果作者没有履约,斯捷洛夫斯基就获得陀思妥耶夫斯基未来所有作品的出版权,为期九年,不必支付任何报酬。
我们无法确定《醉鬼》的创作计划是否比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封信中的寥寥数语有所进展;他敷衍的语气使人相信,他可能顶多只是草草记下了一些初步想法。此外,这些话表明他在构思一部典型的社会问题小说,可是,在其文学生涯的这个阶段,他对写作这种小说几乎没有什么兴趣。不过,这样谈论这部小说也许只是为了加强它可能产生的新闻时事效应对一位持怀疑态度的编辑的吸引力,也许还因为克拉耶夫斯基曾在二十年前发表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创作的此类作品,例如《穷人》和《诚实的小偷》,这些作品以深刻感人的同情笔触描写了无法自拔的醉鬼。然而,学术界一致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为《醉鬼》积累的所有素材最后都被用在《罪与罚》中与马尔梅拉多夫一家有关的辅助情节上。
与斯捷洛夫斯基签订的合同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够在把大部分稿费分配给债主、继子帕沙和已故哥哥的一大家子人之后出国旅行。途中他在威斯巴登短暂停留,希望在那里通过赌博充实一下钱包,不料很快就把所剩不多的钱输光了。因为无力支付旅馆的账单,为了等待使他可以重新踏上旅程的钱汇来,他在这个德国温泉疗养地足足滞留了两个月。从他写给不久以前来到威斯巴登看望他后刚刚离开的阿波利纳里娅·苏斯洛娃的一封信中摘录出来的下面这一段内容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集中反映了他的心情:
我的情况糟糕透顶;不可能比这更糟糕了。此外,肯定还有另一些我尚未得知的不幸和坏消息。……我在这里住着仍然没有饭吃,这已经是我第三天以早晚的茶点充饥了——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我其实并不想吃饭!最糟糕的是他们对我处处设限,晚上有时不给我蜡烛,[尤其是]在先前的蜡烛快燃尽时,就连最短的蜡烛头也不给。不过,我每天下午三点离开旅馆,直到六点才回来,以免别人觉得我根本没有吃饭。(弗兰克、戈尔茨坦编选,麦克安德鲁英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选》新泽西州不伦瑞克,1987,第21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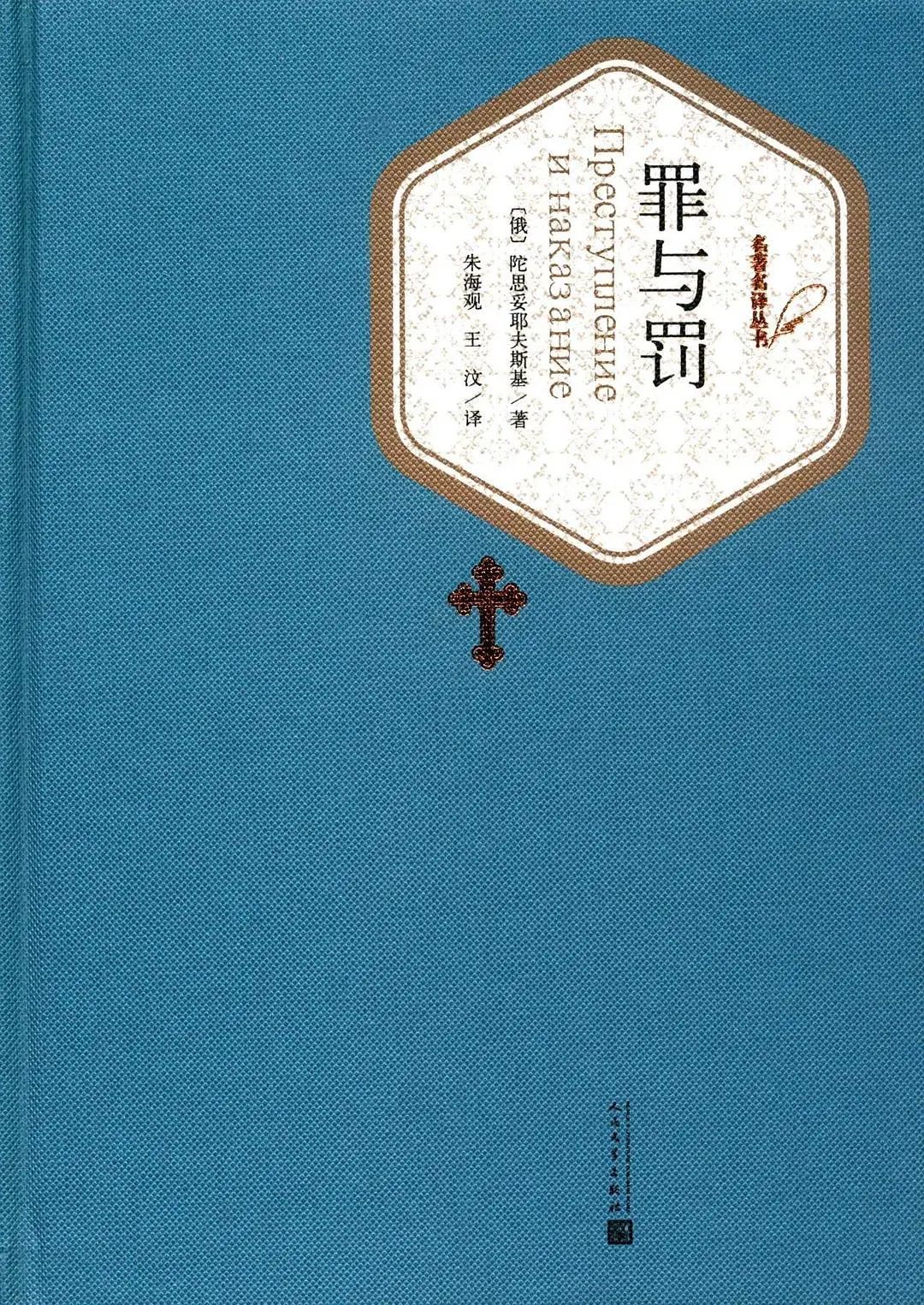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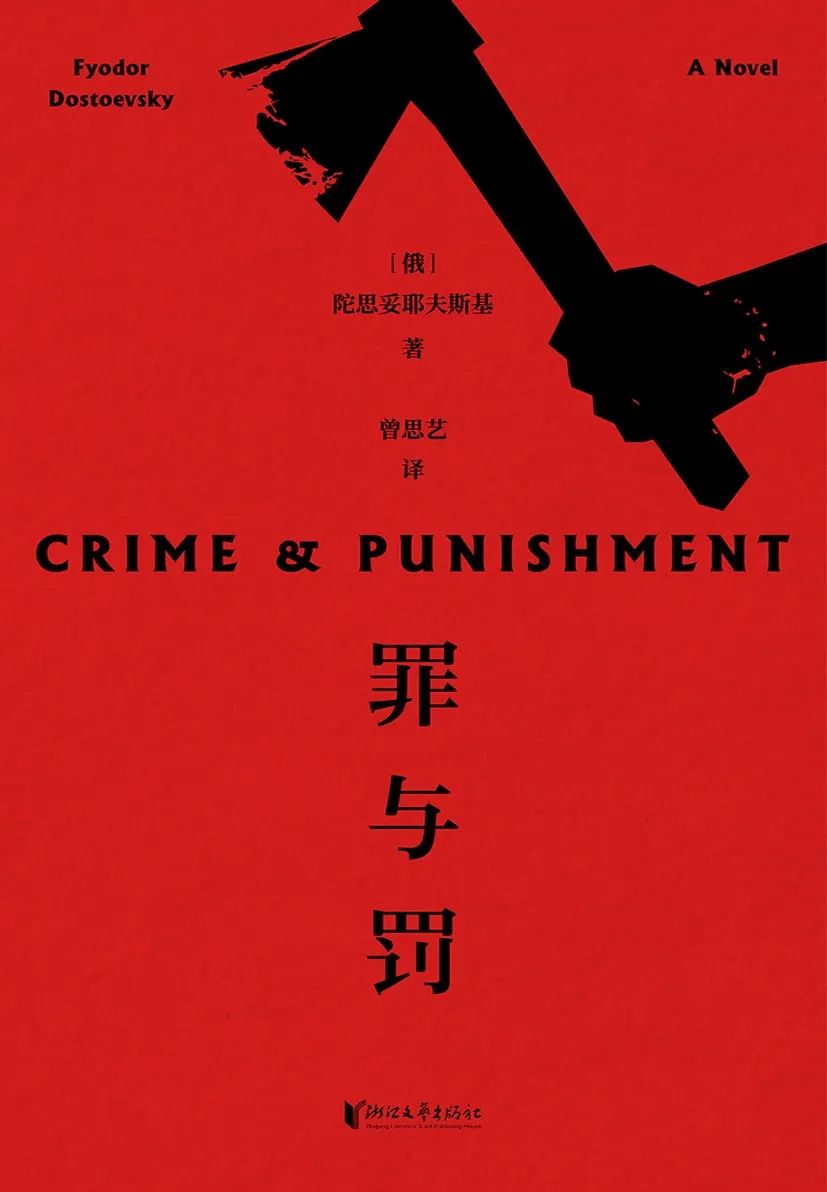
《罪与罚》不同版本中文版书影
正是在个人受到羞辱因而内心极度愤怒的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次看到他想把一个故事最终写成小说的打算——当时他肯定能够感觉到某个拉斯柯尔尼科夫对一切社会不公的仇恨在自己心中奔涌。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一封信请求朋友亚·彼·米柳科夫向杂志推荐他的一篇小说并且争取弄到一笔预付的稿费。他没有具体谈到小说的内容,只是向米柳科夫保证:“人们将会关注它,谈论它……我们当中还没有人写过这种类型的东西;我保证它有独创性,对了,我还保证它有抓住读者的力量。”可是,彼得堡的杂志都不感兴趣,结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给老对手米哈伊尔·卡特科夫写信。卡特科夫是近来转向保守的《俄国导报》杂志具有影响力的编辑,他也是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出版商,不过,在这个特定时刻幸运的是,那两位作家最近都没有向他提供新作,于是,他接受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计划创作的小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私人文件中找到的小说家这封信的草稿让我们看到了他这部新作最初的基本构思。
他把这篇小说称为“一起罪案的心理报告”,犯罪的是“一个被大学开除的年轻人,出身于小市民阶层,生活在极度贫困中”。他受到“周围环境中流行的‘不成熟’的离奇思想”的影响,“决定”通过杀死一个靠典当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一举摆脱自己令人厌恶的处境”。
[她]愚蠢而且病态,贪得无厌……凶狠邪恶,吞噬别人的生命,虐待妹妹,把妹妹当成佣人使唤。“她一无是处。”“她为什么应当活着?”“她对什么人有哪怕一点点好处吗?”这些问题使年轻人迷惑。为了使住在外省的母亲生活幸福,为了把受雇于一户地主人家做侍伴的妹妹从这家主人淫荡的勾引——这种勾引使她有失去贞操的危险——中解救出来,为了完成自己的学业、出国深造,以后终生做一个正直的人,坚定不移地履行“对人类的人道义务”,他决定杀死她。即使人们真的能把对一个耳聋、愚蠢、邪恶、病态的老太婆——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在世上并且可能在一个月之内自然死亡——采取这种行为称为犯罪,他所履行的“对人类的人道义务”最终也会“抵偿”他的罪行。
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说明了他打算如何安排故事情节。杀人之后一个月过去了,“没有人怀疑他,也不可能有人怀疑他”,但是,“犯罪的整个心理过程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逐渐展开,杀人凶手面对着无法解决的问题,突如其来的种种意想不到的情感折磨着他的心灵。天堂的真理、人间的法律产生了作用,结果,他最终不得不投案自首”。驱使他这样做的是“与人类疏离的孤独感”,他在犯罪之后切身体验到的这种感觉一直折磨着他。最后,“罪犯决定承受苦难为自己赎罪”。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说,报纸最近刊登的与受过教育的年轻一代的各种犯罪行为有关的报道使他确信“我的主题一点也不离奇古怪”,他还列举了两起大学生在冷静思考并精心计划之后所实施的谋杀为例。(《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选》,第221—223页)
2

很有可能最初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密切关注的报刊上的此类报道激发了他的想象力,使他产生了创作一篇可以迅速完成并且能够畅销的小说的想法。但是,如果他是这样捕捉到最新的轰动一时的素材的话,那是因为他长期专注于犯罪与良心这个问题,而且还因为,由于六十年代一代俄国激进分子试图在更加“理性的”基础上建立新的道德规范,这种问题已经成为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苦役营服苦役那几年使他直接接触到人类经验的一个令人恐惧的广阔领域,他朦胧地感觉到可能存在着一个可怕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的行为完全不是由善恶标准控制的。例如,他在苦役营回忆录《死屋手记》中写道,在几乎都是杀人犯的农民囚犯身上,没有任何明显的“内心痛苦”的迹象,这让他感到非常震惊。但他同时注意到,“几乎所有囚犯都在睡梦中胡言乱语”,他们的梦话通常都与他们残暴的过去有关。也没有任何农民囚犯拒绝接受评判他们的道德规范;在复活节礼拜仪式上,他们全都下跪祈求基督的宽恕。
真正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可怕的根本不是哪个农民囚犯,而是一个聪明、英俊、受过良好教育的上流社会成员。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这个名叫帕维尔·阿里斯托夫的囚犯是个“典型的最令人憎恶的人,他证明一个人可以沉沦堕落直至坠入万丈深渊,可以毫不费力、毫无悔恨地泯灭自己的一切道德情感”。阿里斯托夫是个奸细和告密者,他被送进苦役营是因为诬告各色人等策划反政府的阴谋,然后用帮助秘密警察诱捕他人所骗取的赏金花天酒地。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当道德规范土崩瓦解或者遭到破坏时,这种堕落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在苦役营的所见所闻还使他相信,这种堕落发生在受过教育的精英当中的可能性比发生在民众当中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当斯维德里盖洛夫这个人物——他完全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另一个玩世不恭的自我——第一次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为《罪与罚》所作的笔记中时,给他起的名字是:阿里斯托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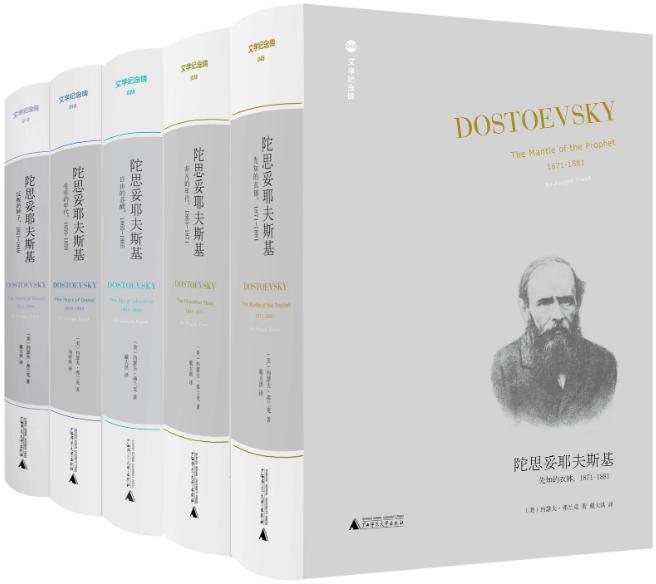
约瑟夫·弗兰克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
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中还提到另一类受过教育的人,但他并没有把这一类人与同营的任何其他囚犯相提并论;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认为这是通过想象反映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情况,他默默地对自己年轻时的革命热情进行了反思。(我们应当记得,这种热情的产物包括煽动一场血流成河的农民革命的计划。)这一类人与农民罪犯截然不同,后者可以犯下野蛮的杀人罪,却“从不……反省自己所犯的罪行……甚至认为自己做得有理”。另一类犯罪者是“受过教育的有良知、有觉悟、有感情的人。在受到任何惩罚之前,内心的痛苦早就足以将其折磨至死。他因自己的罪行而产生的自责比最苛刻的法律还要严厉无情得多”。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即将交给卡特科夫发表的小说的主人公的人物原型。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犯罪主题和良心问题深深吸引肯定是由这些直接印象和思考造成的,加之他热衷于阅读莎士比亚、席勒、普希金、雨果和狄更斯等作家的作品,他们的作品一次又一次有力地体现了这一类问题。但是,由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动荡变幻,他的注意力特别集中。激进分子迫切要求发动革命并且坚信一场革命将在不久的未来爆发,他们同时忙于重塑构成道德规范的整体观念。受到杰里米·边沁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功利主义学说——卡尔·马克思认为这种学说是中产阶级为资本家的自私自利进行的辩护——的影响,俄国激进派最重要的思想家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公开表示,“理性利己主义”比基督教信仰所宣扬的传统良心观念更为可取。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因此,人们喜欢一切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自我牺牲的概念是有害的无稽之谈;不过,人们通过运用理性将认识到,他们的最大利益在于使他们的个人利益与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达成一致。由于激进分子天真地相信理性思考的力量可以控制主宰人类精神的一切潜在冲动,所以,在从西伯利亚归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他们这些思想是最愚蠢、最危险的幻想。因此,他在六十年代初期创作的主要作品(《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死屋手记》《冬天记录的夏天印象》《地下室手记》)全都试图揭露这种功利主义信条的局限性和危害性。
实际上,如果寻找某种一般的模式来概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历经流放的磨难后所创作的作品的特征的话,我们可以认为这些作品是一种辩证混合物:他把他在观察和自我审视的受难岁月所领悟的东西应用于归来之后所面对的激进知识分子的理论。在西伯利亚时期积累的印象——当然包括他对自己的过去的反思分析——显然包含在他后期的所有作品中。但是,他从来没有仅仅为了呈现这些印象本身而描述它们(即使是在以新闻特写的形式写成的《死屋手记》中);他的作品总是以激进知识分子哲学信条的道德含义为目标。这两种因素的结合以及它们之间的张力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兼具显著的人性深度和哲学思想的高度。他估计了激进意识形态对人性必然包含的真实成分——在西伯利亚,这些真实成分的存在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可能产生的影响。他采取的做法是,富有想象力地预测这些激进理论的具体行为后果并以他在早期作品中已经显示出来的那种无与伦比的心理描写天赋戏剧性地表现它们。
(《透过俄罗斯棱镜:文学与文化随笔》约瑟夫·弗兰克/著,戴大洪/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贝贝特 2024年2月版)
新媒体编辑:傅小平
配图:历史资料

原标题:《透过《罪与罚》这道棱镜,文豪如何走出人生低谷丨夜读·倾听》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