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探访溯源“二本学生”的人生,从芜杂中寻找一种清晰视野
近期,学者黄灯的新作《去家访》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用黄灯自己的话说,《去家访》是她走下讲台、走进学生家庭实地考察和亲历的家访笔记,四年前出版的《我的二本学生》则是一本立足讲台视角、建立在从教经验之上的教学札记。这两本书从某种程度而言,让“二本学生”有了更完整的表达。书评人张捷铭在通读《我的二本学生》后表示,黄灯并不尝试给予解决问题的方式,她所做的是提出问题,并通过引发社会的探讨延长/延展对这一问题的聚焦——她向社会之河抛去一枚石子,期望能够泛起层层的涟漪。

文 / 张捷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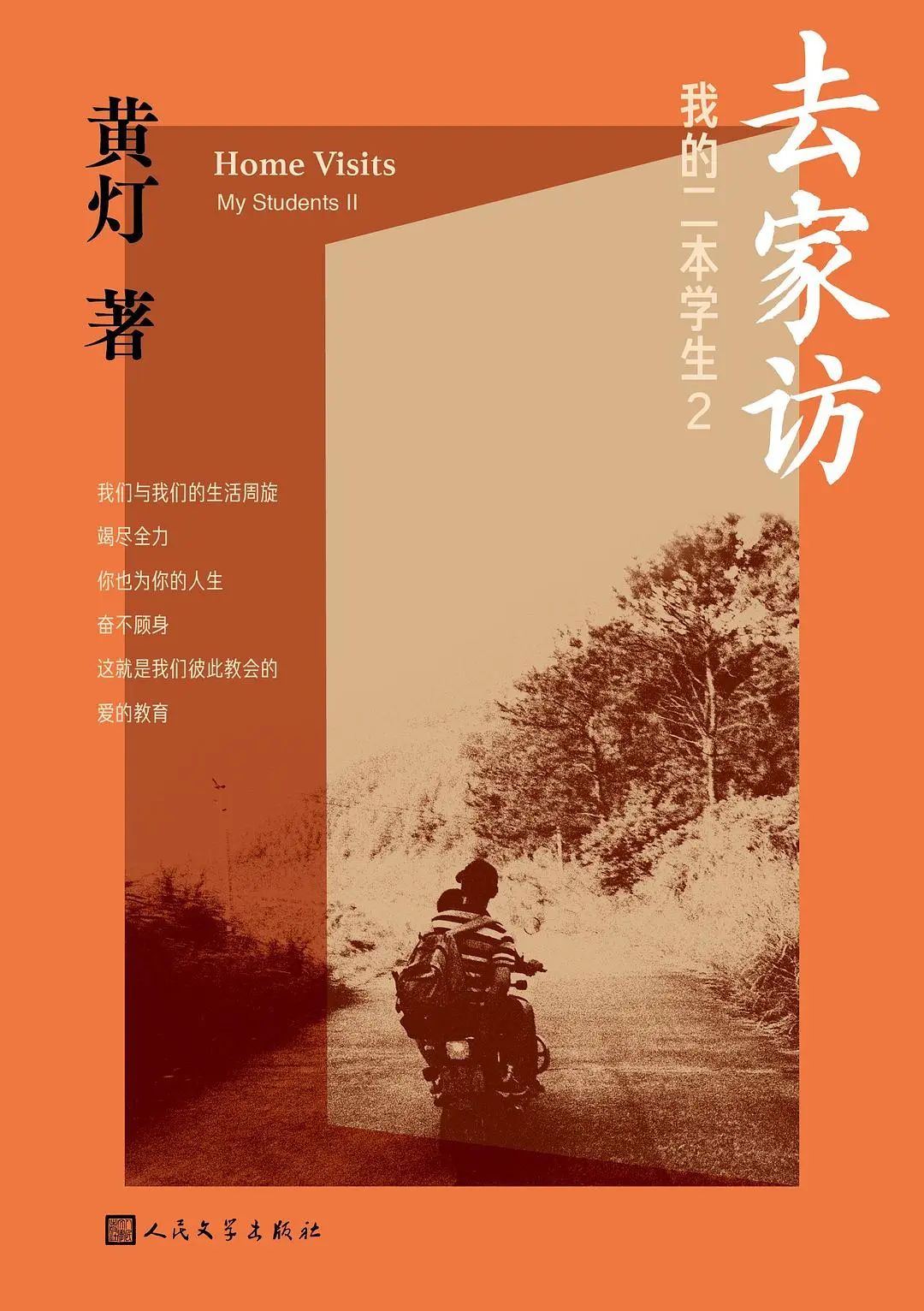
《我的二本学生》《去家访》
学者黄灯创作的《我的二本学生》,被归为中国当代的“纪实小说”;时下大热的非虚构写作更是将其迅速拉拢到自己的阵营。正如书名所明示,作者聚焦于中国最普通二本院校学生的命运,借此希望社会能够“看见他们,看见更多的年轻人”。之所以将“二本学生”作为书写对象,不仅仅是因为黄灯曾是二本学生的切身经历,以及她作为二本院校教师的缘故;更是因为:在黄灯看来,二本院校的学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中国最为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其命运“勾画出中国年轻群体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他们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
也正是因为作者亮明了自我身份及“在场”经验,加上“纪实”或者说“非虚构”的叙述方式,使得写作本身似乎带有某种天然的合法性和自洽性。但当文本进入到读者的阅读实践中,许多质疑的声音随之而来:作家是否能够为二本学生这一群体代言?这一群体的内在差异性在代言的过程中是否会有所遮蔽?甚至这一书写行为本身,是否有“歧视”或“消费”二本学生之嫌?若作者是真切关注着自己的书写对象,那么,她在发现这一问题之后是否提出了有效可行的解决方案?如果没有,那么其写作之意何在?由此扩展到“非虚构写作”,它有别于社会学、新闻学著作且能够使得自我确立的地方是什么?
囿于这些质疑的沼泽之中,并执着于如何一一反驳是琐细而无止尽的;再而,“非虚构”概念本身无法自明的特点也让我们很难在绝对意义上找到对其明确的界定(这反倒会成为一种框定)。相较之下,我们不妨关照于作者是如何选择及书写的,揣摩其创作心态,探究她是在什么样的知识框架与叙事逻辑下做出了对二本学生的认识,以此更好地理解她的创作用意及背后的人文关怀。

黄灯在去家访路上
黄灯在《个人困扰如何对接公共经验》一文中说道:“有一次在北京开会,别人说你真会选IP,我当时听了好生气,我从来没有IP的概念,感觉他们也太小看那种主动的写作者了,这种轻薄的语调,习惯性地策划设定为写作的动力,完全忽视掉了那种来自内驱力触动写作的不同质地。”换言之,黄灯对于社会公共经验的关注是基于其个人的困扰,而这些困扰她的问题及对象是身边和她有情感交集的一群人。只不过她身边的这群人恰好是现今社会所定义的“底层”或“失败者”,他们不受到重视,甚至被歧视——他们的个人遭际就像《十三邀》纪录片中一位学生所写的那样:“我们这群‘工业废水’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如此看来,我们将不难发现:黄灯的写作并不是在“歧视”或“消费”二本学生,而是在披露社会中所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重视,且期望能够做出改变。其内心强烈的沉痛感渗入毛细管中,扰乱了叙述的节奏和语调。文本可能存在的“过于抒情”并不是滥情,而是她对于这种不公平低声连绵的控诉——作者自然希望通过克制的、较为理性的表述进行书写,但重新构思与书写的过程让这位亲历者的在场经验再次唤醒,某些情绪不受控地流溢在理性的缝隙之中,而“过于抒情”的部分正是其具体表现。
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曾言,“人们总是比社会科学家以及外部观察者所认为的要更为自由。人们应该总被预想为有能力思考和行动。”然而,底层的思想、声音和行动在“秩序森严的社会制度和被‘再现的重负’压垮的审美体系中”(金理语)被压抑和隐匿。我们无法看见、听见底层,而当我们试图去这么做的时候,又有可能受到诸如启蒙的思想预设而“重层”模糊视线,并因此遭来谴责;更进一步地说,即便我们能够满怀着信心寻找到某一看似可行的路径并为之努力,到头来也有可能遇到残酷的事实:真正的“底层”,在重重压迫下,根本不可能具有独立的意识和言说的平台和语境,他们处在“失语”的、无法言说的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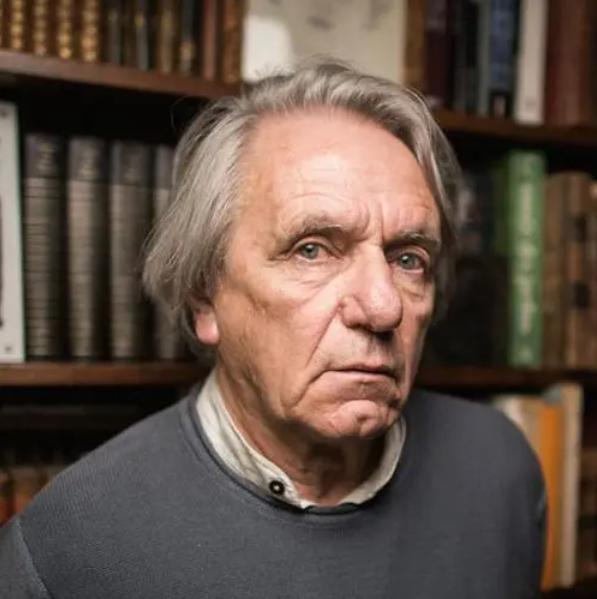
雅克·朗西埃
人们总是比社会科学家以及外部观察者所认为的要更为自由。人们应该总被预想为有能力思考和行动。
“失语”和无法言说,是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其不能承受之重——这些“底层”或“失败者”没有能够与社会的不公进行直面对抗的资本。但在黄灯这里,他们并不沉默。这不是说黄灯能够给予她的二本学生们对抗的实效力量,而是说她与这一群体之间的关系让他们愿意袒露心扉,直面自我。相较于深度报道、社会调查、纪录片跟踪拍摄等,《我的二本学生》中研究者和受访者之间的关系之建立并不是出于某种实际目的。我们并不否认深度报道等作品也蕴含着创作者对社会的关切及人道主义关怀,但黄灯和她的学生们之间的关系显得更为丰富。前者是围绕某一问题才与受访者接触,这一创作完成之后可能就不再联系。而黄灯和学生们的基本关系是师生关系,她无法预测谁会考上广东F学院并成为她的学生,首先受访者在身份上就存在着不确定性;其次,她更不知道学生们的个体遭遇是什么样的,并在了解后会写出《我的二本学生》;再而,书中“刘婉丽”、“徐则良”、“李沐光”等等名字不只是受访者,更多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以学生的身份出现。换言之,《我的二本学生》写作、出版与否,并不影响黄灯在书中所提及的与学生们的情谊往来。也正是因为这份真诚,才让学生/受访者愿意和黄灯沟通(书面形式/口头形式、课堂内/外),在此过程中不只是黄灯对他们能够了解并有机会写出作品让社会“看见他们”,更为重要的是她也在引导着学生们“看见自我”。

黄灯谈二本学生
那么,当社会“看见他们”,二本学生这一群体“看见自我”以后,是否就会得到预期的改变?出版商自图书营销的角度,将话题延伸到二本院校学生的出路、逆袭的可能性,并落脚于“‘哪怕二本院校的学生,仍然可以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给读者以希望和向上的力量。”事实上,黄灯在她的个人公众号上也曾写下“经验唤醒立场,文字抵挡现实”,表达过类似的乌托邦式期许。但在她接受采访时说过的一段话,饶有意味:
以前我总觉得一个人,一个写作者,他有足够的关注度、足够勇敢,表达有足够的感染力,他就可以去做一些事情,但是现在我发现,不见得。如果有些东西没有根本改变的话,文字是非常无力的。(黄灯,冯卉:《非虚构是从现实中自然而然成长出来的》,《文艺报》2022年06月06日)
是什么具体原因让黄灯在思想上发生这一改变,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一改变本身对于其创作的考察是极其关键的。2021年第八批深圳重点文学作品的扶持项目,黄灯的《家访记——二本及职业院校学生的出路考察》(亦即《去家访》)位列其中,这或可视为《我的二本学生》的“续编”——黄灯在《我的二本学生》中对学生的毕业走向已经有所涉及,《去家访》将会是对这一话题的进一步延伸和深入。对于大学生的出路考察(尤其是在疫情及其后的背景下)也是社会学的热点话题,程猛的 《“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当代农家子弟成长叙事研究》(2018)和郑雅君的《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2023)等都对此有较为深入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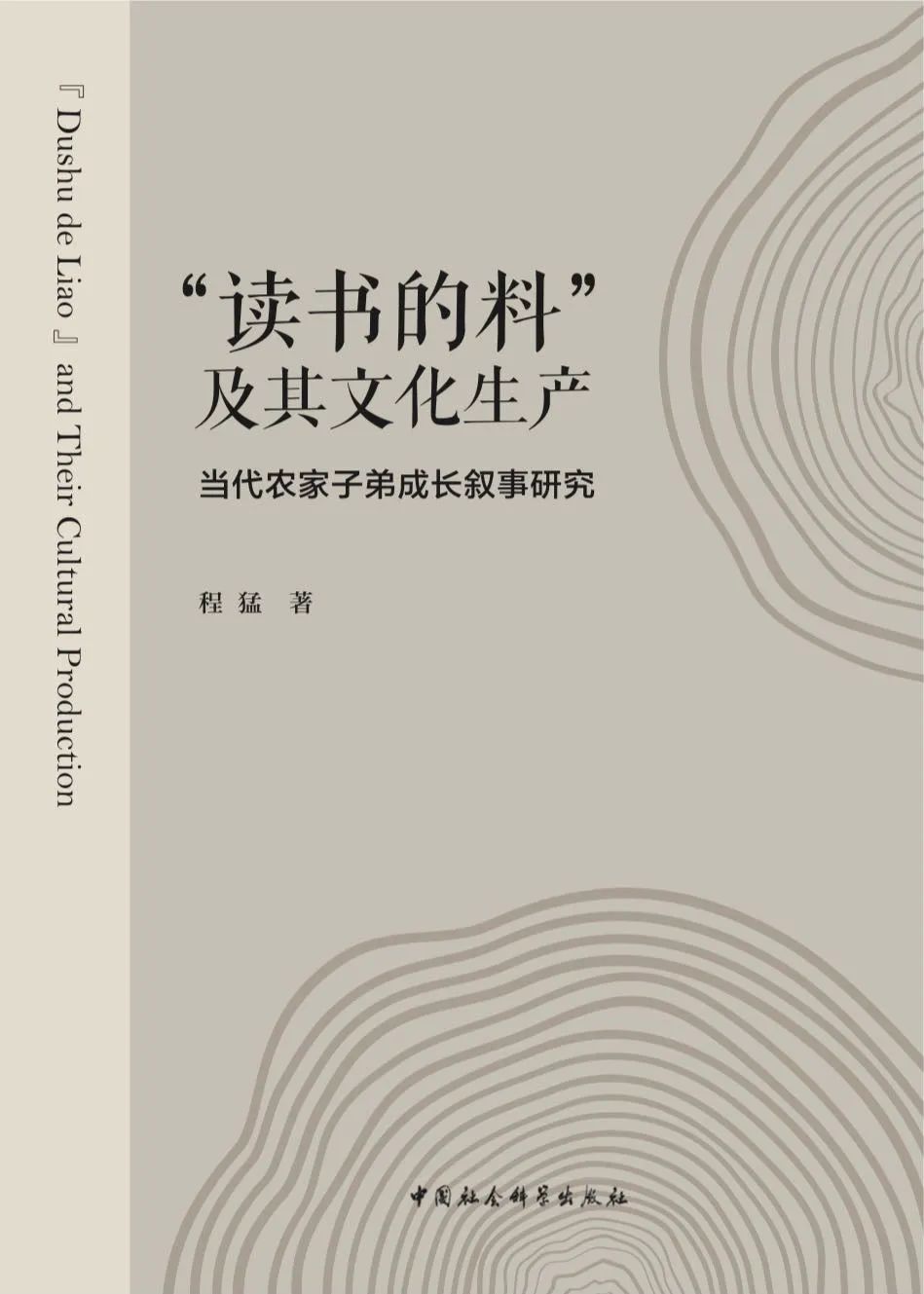

在社会学学者看来,这些处于逆境的学子需要突破文化障碍,熟悉场域规则,并结合自身处境进行自反性分析;同时呼吁构建一个完善的公共社会体系,使得阶层流动更为频繁而不至于固化;而在黄灯这里,问题化的处理被有意的耽搁。作者并不是淡化或者回避横躺在面前的现实问题,借用她对“非虚构写作”的认识:在黄灯看来,非虚构写作本质上就是一种“问题写作”,它“直接处理全球化视野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很多难题和症结”,而非虚构本身的出现就是为了呼应这一社会存在的需求。即是说,黄灯的写作同样指向问题的内核,但她并不尝试给予解决问题的方式,她所做的是提出问题,并通过引发社会的探讨延长/延展对这一问题的聚焦——她向社会之河抛去一枚石子,期望能够泛起层层的涟漪。
在涟漪效应的回荡中,人们不止关注到作为问题的二本院校学生群体,更关注到作为个体存在的这一群体的每个人,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对黄灯来说,每一个个体不是样本,而是活生生的、有身份的学生;她与这些学生有深厚的情感连结,从而在通往理性的道路上羁绊重重。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黄灯不是以研究者的身份理性地分析并提出解决的可能性方案,而是更多呈现内心的复杂和纠结。对那些找到稳定工作的学生感到庆幸,对那些执着于内心梦想却处处碰壁暂无着落的学生心存担忧,作为施教者的黄灯常常身处于两难境遇:
现实对年轻人的训诫、淘洗,多年工具化的教育管理、就业至上的信条,是晚秋面临的现实处境;她身处其中,不过及时调整姿态,更快地加以适应,以另一种更为彻底的工具化方式,找到对付的途径。对现实的顺受和看透,是她面对时代、命运时不纠结的秘密。从个体角度而言,这是一个突围者的胜利,但从教育效果而言,却也掏空了年轻人身上更为重要的青春特质。
当文字难以抵挡现实之时,是否就要任其摆布?对学生个体命运的焦虑和无奈以及深感文字无力的感叹,并不必然导向消极主义的肆虐和吞噬,黄灯在此次思想的阵痛后,恰有可能迎来涅槃重生式的新机。
新媒体编辑:傅小平
配图:出版资料

原标题:《探访溯源“二本学生”的人生,从芜杂中寻找一种清晰视野》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