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梅俊杰:从经济史看文化的作用——经济活动“镶嵌”于文化中?
周正男:梅教授在近著《李斯特与赶超发展》和《重商主义与赶超发展》中多次强调,经济发展不能单靠经济因素而取得成功。想请你谈谈非经济因素的作用。
梅俊杰:在人类生活中,经济是综合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此外还有政法制度、地理环境、文化习俗、军事强力等其他多个子系统。这是不言而喻的常识,即使现代学科的分化使得经济学越来越专注于经济因素的研究,那也无法改变各子系统相互联系、经济发展受到非经济因素影响这一事实。从韦伯(Max Weber)关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到制度学派强调政治与法律制度安排的重要性,不难看到,需要把非经济因素纳入关于经济发展的思考中。

梅俊杰著《重商主义与赶超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周正男:请特别讨论一下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吧,因为文化的作用尽管无可否定,可一般又难以梳理清楚,是否就从你研究的经济史角度作一阐发?
梅俊杰:文化是个常用高频词,世人赋予它的含义却五花八门。我把文化理解为价值观念与行为习惯、宗教信仰与教育认知的综合体,它构成了人类知识相传、文明进步的广泛基础。可以说,文化决定着我们如何看待世界、如何安身立命,经济活动显然“镶嵌”于文化中,市场和制度不可能架设在真空里。经济学的历史学派就惯于把文化习俗、宗教思想、政法制度等诸多非经济因素引入经济讨论,比如,桑巴特(Werne Sombart)考察了奢侈、战争、宗教、精神、爱情、犹太人、记账方式对资本主义兴起的影响,韦伯关于新教伦理的命题更是广为人知。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哈耶克(F. A. Hayek)甚至说过,长远而言,是观念主宰着人类历史进程,世界的现状是由观念的转变和人类的意志塑造的。可见,我们不可避免地需要研究经济发展中的文化因素,毕竟同样的经济举措在不同文化中经常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其实我不大愿意谈论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因为文化庞杂多面、捉摸不定,任何一种看法都可能聚讼纷纭。以前,李光耀在讲到东亚经济奇迹时,一度论及“亚洲价值观”的重要性,后来却又承认新加坡的经济成就本质上依靠了英国留下的法治。你看,即使对待同一个经济发展现象,即使是同一个当事人,也会有不同的说法。如此看来,经济学家如果避而不谈文化,也可以理解。事实上,20世纪40、50年代关于经济发展的讨论中,文化论固然盛极一时,可及至60、70年代,有关解释已乏人问津,这种情况到80年代才有所改变。我的看法是,文化问题挥之不去却难以定量分析,随手可以举证但又总能提出反证,所以谈之也难。好在借助世界经济史的宏大视野和历史维度,相对来说还可以探讨一番并获得某种启发。
周正男:众所周知,欧洲是最早启动现代经济增长的地区,是否存在某些独特的文化因素使得欧洲率先发展起来?
梅俊杰:世上有一种叫“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观,这种史观在目睹近代以来欧洲文治武功的综合优势后,倾向于理想化那里的一切,包括其文化。这种观点当然有失偏颇,因为欧洲之前也曾不发达过,之后内部的发展水平也参差不一。为此,在判断欧洲是否拥有更利于现代经济发展的独特文化时,我们必须非常谨慎。不过,考察17-19世纪欧洲西北部的崛起时,只要跳出单纯经济主义的思维框框,还是可以发现某些有助于现代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确在占据主导地位。如果借用当今文化专家格龙多纳(Mariano Grondona)归纳的促进抑或阻碍经济发展的20个对照性文化因素的话,可以看到西北欧明显走在文化现代化的前头。
首先体现在价值观上。根据麦克劳斯基(Deirdre McCloskey)的研究,西北欧在17-18世纪率先经历了价值观的变迁,崇尚发财致富、逐利经营的风气先在荷兰再在英国盛行起来。要知道,古希腊古罗马看重的是闲暇而非劳作,即便重视财富也主要是看重它能带来闲暇自由。这种鄙视劳动的观念延续到中世纪,精英们相信,值得弄脏手去做的事情最多是打仗而不是打工。然而,荷兰和英国等地转而日益推重商业、革新、竞争、冒险,并且给予这些方面的成功人士以较高社会地位。这种时风之变容忍并鼓励优异者投身于生产经营和财富积累,从而推动经济发展踏上快车道。不难想象,一个依然重农抑商、耻于言利、安土重迁、因循守旧、封闭一统的地区决不可能像西北欧那样,开辟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型的道路。
周正男:文化价值观念的变迁固然重要,但西北欧近现代的崛起肯定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那么相对而言,文化的作用究竟有多大?
梅俊杰: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从来都认为经济发展是多因素合力推动的结果。专就荷兰和英国的领先发展而言,确实可以从文化以外的多维角度加以解读。经济史学家们相信,跨大西洋航线的开辟、欧洲经济重心的北移、先进生产要素的吸纳、社会市场导向的增强、自由经营群体的涌现、商品化农业的成长、交通运输的便利、重商主义的贯彻、海外利益的拓展、国家能力的提升、行政权力的受限、宗教宽容的享有等等,都无不重要。事实上,文化有个特点,它发挥作用往往是在与其他各因素的综合互动、相互作用中。即使在文化这个大筐子中,也还有思想观念、宗教信仰、知识教育、行为习惯、社会信任、家庭结构等众多非经济因素。
不过,这里可以明确指出一个推动欧洲经济与科技发展特别是推动英国工业化的文化因素,这就是由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知识精英所结成的“知识共同体”(亦称“书信共和国”)。欧洲的知识精英们利用17世纪起覆盖全欧的邮政系统,致力于交流并探讨最前沿的科学发现和研究成果,举凡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科技创新、民生改善的理念、方法、成就都得到了扩散与分享。英国1660年创立皇家学会便得益于此,而且,连英国的技工、匠人、厂商也都从中获益。因此,考亚马(Mark Koyama)等研究者认定,这一轮文化启蒙,就如国内外市场的扩大、限权而理性的政府、工匠和商人的充沛等其他因素,同样构成了英国工业革命的一个关键性前提条件。
周正男:以欧洲的历史传统而论,宗教确乃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动力,你认同韦伯有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结论吗?
梅俊杰:韦伯提出的命题人所乐道,不能不予以重视。韦伯依据在家乡德国新教徒比天主教徒更勤俭、更成功的观察,认定新教主要是加尔文教有关“上帝选民”、注定进入天国的教义会激励教徒勤奋劳作、乐意储蓄。他认为,就是这种新教影响下的“工作伦理”构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基础。从大面上看,新教覆盖的荷兰、英国、北欧、北美英语移民地确实创造了更令人瞩目的经济成效,与奉行天主教的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巴尔干、波兰及俄国等地的经济落后适成对照。韦伯命题看起来证据充分。
但是,也有学者如陶尼(R. H. Tawney)指出,所谓“资本主义精神”在新教出现前即已存在,如在中世纪晚期意大利的城邦国家、德国的独立城市、低地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原已相当活跃,足以说明资本主义精神在宗教改革前已经走在路上。与此同时,也明显存在不少反例。虽然16世纪以后的领先经济体均属新教国家,但恰如森哈斯(Dieter Senghaas)所见,天主教势力强大的比利时却是一个工业化早发国家,法国北部、西班牙的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意大利北部、上奥地利等,虽与本国其他地区同处天主教文化中,却照样取得了较快的经济发展。
这些事实表明,以后围绕韦伯命题也得出了若干不同的结论。不过,韦伯命题的价值在于,它让人更有意识地关注精神文化与经济活动之间的亲和共生关系,哪怕不容易精确测定其间的因果关系。当然,经济、社会、宗教、文化、历史个个都是超级复杂系统,所以我们一方面可以承认新教对经济发展相当程度上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还有其他因素在共同起作用。而且,纵然是归于新教的那些东西,实际上也不是新教所独有,无非是此时在新教身上正好明显可见或一起在产生作用。这样思考的意义是,还能让我们透过新教这个宗教外壳,去关注随后促进资本主义兴起或经济发展的某种更具普遍性的因素。
周正男:那么,你觉得在新教掩盖下,与某种教义相比,是否存在某种普遍性因素更直接地促成了资本主义?它的作用机制是怎样的?
梅俊杰:研究表明,所谓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及经济发展之间所发生的联系,更可能借助了文化教育这一机制。简言之,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强调信徒自己阅读圣经从而与上帝直接联系,这客观上提高了民众识字率和受教育水平。据考证,19世纪初期在普鲁士境内,新教徒占比即与入学率提高及男女识字率差距缩小存在正向关系,进而再与收入和工商就业,与工业技术的接受也呈正向关系。这样看来,与其说是新教的工作伦理在促进资本主义发展,莫如说是新教所导致的更高文化水平在起作用。事实上,犹太教徒就历来看重教育,重视人力资本投入,资本主义的兴起不是说曾得力于犹太人吗?
与此同时,新教也会经由政治机制而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宗教改革瓦解了传统教权的统治地位,引发了权力从宗教精英向世俗精英的转移,新教地区的主政者尤其不再通过教会获得其统治合法性,转而向议会这个新政治机构寻求支持。因此可见,在世俗权力上升、权力结构转型的近代,议会在欧洲范围内走上舞台。议会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旨在遏制君主的征税冲动、寻求安全的产权安排、增加基础设施的投入、提高权力行政的理性。此类变革助推了随后西北欧经济的加速发展,其集中发生在宗教改革之后谅非偶然。以荷兰为例,新教信仰的传播激发了荷兰针对西班牙的政治抗议和立国诉求,而政治革新又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当然,宗教文化如何造就经济发展,以及造就到什么程度,也不容易斩钉截铁地加以实证,这是文化讨论的一个特点。
周正男: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围绕儒家价值观在东亚经济奇迹中的角色,也曾发生过令人纠结的争论。
梅俊杰:有意思的是,探讨儒家与东亚经济快速发展的关系,一方面削弱了韦伯的命题,让人看到,并非只有西方社会的那个新教伦理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则继续让人看到了文化与经济之间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分析儒家价值观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相信东亚人重视教育、勤劳节俭、服从守纪之类文化特征塑造了适宜的劳动队伍,进而促进了经济发展,这的确是个有益的视角,有助于拓展人们对经济发展动因的理解。况且可见,归到儒家头上的那些正面因素相当程度上也与韦伯所谓新教的积极内涵颇相类似,这也有助于确证文化因素与经济发展的关联性。
然而,人们不免要问,东亚国家早就拥有那些儒学价值观及其他有利的文化特征,怎么之前就没有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更没有在近代自主地迎来经济发展的突破?再说,同文同族在分割为不同政治实体后,为何其经济绩效迥然有别?显然,尚不能把经济的发展与否简单归因于文化因素,还必须同时借助其他因素来寻求更全面的答案。就东亚经济体而言,战后的国际秩序、制度安排、社会改造等等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无论是内部的土地改革、开放的国际市场、欧美的产业转移,还是精英的观念转变、系统的学习先进、美日的雁型带动,一起形成了适当的条件,因而让那些儒学因素经由劳动投入的途径而产生正面效果。因此,文化犹如某种潜藏的资源,它需要得到恰当的开发才能呈现其价值,而恰当的开发也有赖于其他因素,这一点与欧洲经济发展史的经验如出一辙。
周正男:我注意到,你始终没有单一地强调文化,而是认为多因素在共同作用于经济发展。能否请再具体谈谈跟文化一起发挥作用的其他因素?
梅俊杰:影响经济发展的非经济因素太多了,无法一一论列,这里只能挑出地理和制度这两个因素来谈,它们传统上都与文化密切互动,如今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却一轻一重。先说地理因素,它不仅涉及地段、土质,还涉及气候、资源等等,在前工业时代尤其决定着一国的产业特点、市场规模、经济命运,且由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还会塑造风土人情、文化习俗、国家治理。然而,人类文明越是演进,无论是交通方式的改善、生产方式的改进,还是科技创新的应用、医药水平的提高,都越能把一国从地理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也是为什么在地理轮廓一成不变的情况下,世界的经济版图至少从地理大发现以来,却时不时地发生重大变化。如今已不难判断,在决定各国经济绩效的过程中,固态的山川风物已不再关键,动态的“事在人为”才是更具决定性的变量。
“事在人为”中,主政人物、政治决策自然重要,但更具长远塑造力的还是政法制度,涉及经济社会的基本组织方式和游戏规则,它们决定着采取或不采取某些行动有何成本与收益。世人日益认识到,资本、技术甚至政策、才智尚不足以确保持续繁荣和良治久安,制度这样的非经济因素更为根本,制度经济学派于是风头日健。在探求为何西方率先实现国家富强和科技突破这个问题时,人们看来在西方明显拥有而非西方相对缺乏的那些制度因素中找到了答案。大致而言,列国体系的多元竞存、贵族制度的根深蒂固、自治城市的自由经营、议会制下的利益代言、立宪制下的有限政府、基督教会的自成一体、古罗马法的重新发现、法治保障的产权安全、股份公司的应运而生、常年征战的倒逼效应,都被认为是西方总体领先的制度要素,也是欧洲内部发生国别差异的缘由所在。这里之所以特别提出制度,是因为文化往往经由制度而发挥作用,一如制度总是生长于特定的文化土壤上,并且由文化决定着它的质量和功效。总之,制度与文化彼此塑造、深度绑定,经常很难在经济发展中分离出制度的功效相对于文化的功效。
周正男:那么相对于其他因素尤其是政法制度、为政决策及主政人物等因素,文化因素具有何种特点呢?
梅俊杰:我想文化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它的变迁速度要大大慢于制度、政策、个人之类因素,文化的车轮是在千百年的时间刻度上演变的。由于各子系统变化速度不一,经常可见某种文化现象即使不再有效,却仍然存在并塑造着众人的思想和行为,并且与经济环境的需求明显脱节,由此而阻碍经济发展。特别是跨入近代后,技术、社会、经济的变化都日益提速,这意味着某些文化内容虽曾适应旧有经济条件,时过境迁之后却不再与新经济条件相匹配,致使相关国家或地区无法利用新的发展机会从而落伍下来。当然,我不赞成什么都简单笼统地用文化来说事,那样很可能既抓不住问题要害,又提不出有效对策。记得朱学勤说过“别在文化的脂肪上挠痒痒”、“原因的原因的原因不是原因”。这也提醒人们,相比于事物的远因,更应当关注近因,舍近求远容易事倍功半。
与其流于表面地相信文化决定论,还不如更具体地考察文化作用机制。例如,不少人“一刀切”地认定,对伊斯兰教的信奉造成了中东的经济停滞,可这种一概而论缺乏逻辑支撑并容易被证伪。须知,公元7-10世纪也曾有过“伊斯兰的黄金时代”,其时中东的财富、文化、技术等多在西欧之上。据研究,中东地区以后的落伍成因在于,伊斯兰法规定,任何合伙人死亡时,合伙制即告解除;合伙制固然可以重组,但死者的任一继承人均可要求停业清盘。在不需要经营规模的时代,这一安排尚不足为虑,可越到近现代它越会限制社会资源的调动和企业家的志向。这让人看到,某种文化规定如何循由某种机制而从正面走向负面。不过,纵然如此也仍要看到,上述案例中,也不是单一的文化因素就阻碍了近现代经济发展。中东地区教权的独大、对世俗教育的束缚,终究与西方宗教改革后的趋势相背离,二者经济上的大分流由此也就不难索解。
周正男:那文化因素是否很难改变呢,这会不会导向某种文化宿命论?
梅俊杰:导向文化宿命论倒也未必,但文化因素的确源远流长,而且在缺乏制度干预或刻意矫治的情况下的确存在自我强化的倾向。研究者注意到,即使在20世纪中叶,意大利南部的农村也存在严重的“不良家族主义”文化特征,人们强烈追逐家族的短期物质利益,那里缺乏公共产品,缺乏社会组织,缺乏参政热情,缺乏陌生人间的信任,这些与意大利的北部形成了鲜明对照。进一步研究表明,相关的文化差异一直可上溯至千年以前的中世纪,与当时天主教会严禁堂表兄妹婚姻的禁令有关。在教会影响强大的北部,禁令得到落实,跨家族合作关系遂得到加强,而在南部情况正好相反。日积月累之下,便形成了个体主义还是家族主义、公民社会是发达还是萎缩、政治参与是积极还是消极等等差别。
这些差别对经济甚至政治的发展影响甚大。据格雷夫(Avner Greif)分析,在经济发展早期,当贸易总量较小的时候,家族主义的文化在营建贸易网络时比起个体主义的文化更有优势,因为人们更可借助家族网络展开贸易,还能有效防止贸易中的舞弊现象。然而,随着跨地区贸易机会的涌现,家族主义文化便不敷使用,个体主义文化的超家族合作及相应的非亲缘制度安排便日益展现其竞争优势。在更大范围内,中国与欧洲的对比也能给予某种佐证。欧洲近代的股份公司制度、银行金融制度,以及这些跨家族制度与社会信任之间的互相促进,还有它们为开辟现代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都不容易见存于家族主义强盛的国家。因此,拉长历史镜头可见,文化上初始的失之毫厘确可长远地谬以千里。
周正男:上述分析中提及了信任问题,当代的经济学就经常在强调信任这一文化性因素。
梅俊杰:是的,上面的例子充分说明,超越血缘的、陌生人之间的信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对现代经济甚至政治发展至为重要。实证研究显示,富有国家的人际比贫穷国家的人际有着更高的信任度。一个极端的例子涉及撒哈拉以南非洲,那里在15-19世纪经历了大规模的人口被掳、长距离贩运为奴的“奴隶贸易”。除了所造成的人口与经济灾难外,此等暴行还留下了深远的社会和心理创伤。据研究,在受奴隶贸易冲击的地区及族群中,至今人们对亲友、邻居、同族裔人、当地政府依然缺乏信任,从而影响到经济发展,非洲内外的比较及非洲内部的比较也证实了这一点。
不过仍要说明,信任与否尽管可以溯源到文化宗教的教化、历史经验的塑造,但一定也与法律制度、政治安排大有关系,它们始终是彼此交织、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当然,上述各方面的变迁节奏未必合拍,就文化而言,一旦成型,它会比曾经造就它的政法制度、历史环境具有更持久的影响力。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性别不平等问题。农耕社会中犁地等耕作方式的形成让男性获得了超过女性的优势地位,这种影响哪怕到了工业社会甚至信息社会也仍难以消除。有趣的是,研究还发现,当代国家中,前现代的犁耕主导社会比起纺织主导社会,在统计上就呈现更大的性别不平等。
周正男: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的提升,科技创新愈发关键,在此背景下,教育的作用愈发重要,这也使得文化的作用上升了吧?
梅俊杰:基本上是这样。第一次工业革命(约1750-1830年)主要是回应了市场需求,那基本上是能工巧匠在技艺上心灵手巧的产物,比如,作为当时主导产业的纺织业不过是把之前已知的生产方式系统性机械化、大规模工厂化罢了。与此相比,第二次工业革命(约1860-1914年)则主要由科学发明拉动,科学的介入使得技术变革不断加速,引发了交通、电力、化学等领域的日新月异,决定性地自我制造着市场需求,大举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既然科学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直接推动力,教育的普及包括科学实验的系统开展显然发挥了巨大作用。德国能引领第二次工业革命,与普鲁士19世纪上半叶实施的一系列教育改革是有因果关系的,更高的教育程度造就了善于借鉴英国、进而本土创新的科技队伍。这样看,只要把教育也归入文化这个大篮子中,那么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只会越来越大。
顺便要指出,上面讲到德国对英国科技的借鉴,其实,在引进外部先进的技术和制度时,首先就有一个对他我发展程度之高下、发展路径之优劣的文化性判断。近代日本努力“脱亚入欧”与近代中国坚持“中体西用”,背后就反映了二者在文化判断上的重大差别,此种文化判断等于是一种根本性的世界观。而要改变世界观又谈何容易,正如要改变族群的自恋心理、走出传统的舒适区决非易事。以此观之,英国领先的工业文明与现代发展能够迅速传播到欧洲大陆、北美大陆及澳洲等白人自治领,不单由于地理上近水楼台之便,更有文化上亲缘相通之利。与文化体系相异的地区相比,同属欧洲基督教文化圈的后发追随者首先就省却了必须改变“祖宗家法”的那些心理障碍。对于这方面凭空多出来的文化顾虑,我们作为西方文化的圈外人至今都有切身的体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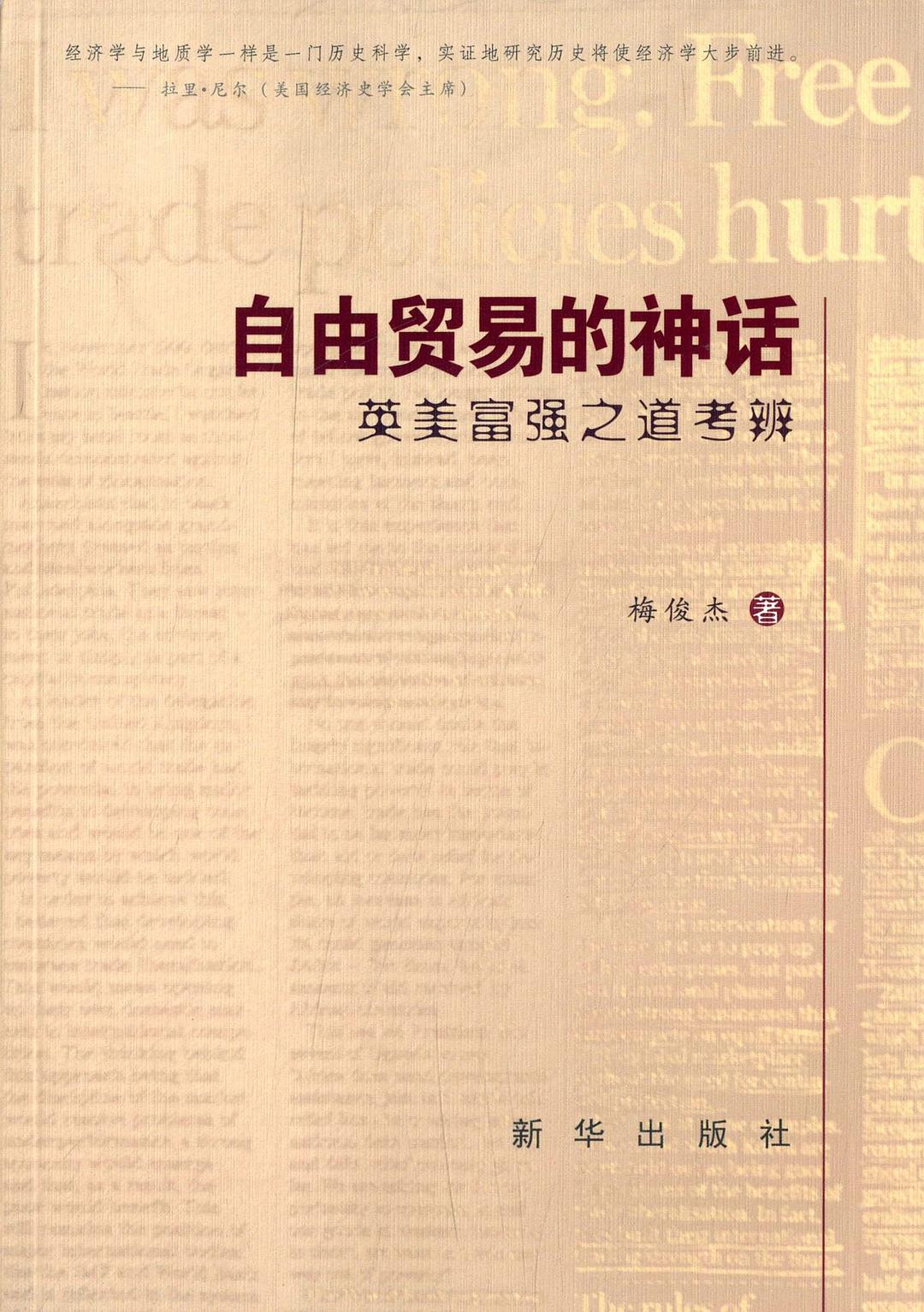
梅俊杰著《自由贸易的神话》,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
周正男:这里正好提到了落后国家的赶超问题,就后发赶超国家而言,它们除了在文化上调整世界观之外,还应该做些什么?
梅俊杰:还是先应老生常谈,经济发展必然意味着多因素互动,可是,各种因素不可能是等值的,某些或某个因素难免会比其他因素更加关键。拙著《自由贸易的神话》在解释英美的崛起时,就特别强调了借助关税手段保护幼稚产业的重要性,同样,在解释近现代落后国家的赶超时,我更多地聚焦于重商主义。即便如此,任何单因素解释不管有多大的学术合理性,终究都是不全面的,都不应该排斥其他解释。极而言之,大家都是“盲人摸象、各摸一块”,对文化因素的聚焦也应该作如是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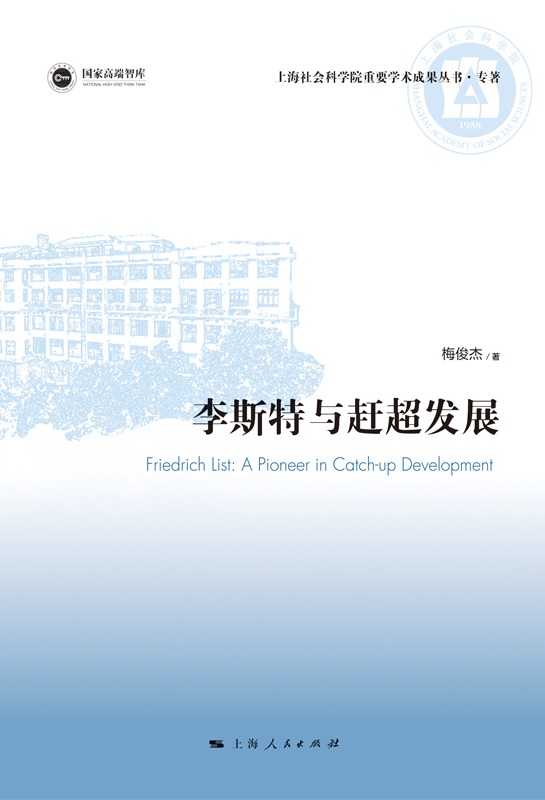
梅俊杰著《李斯特与赶超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版。
至于后发国家在赶超发展中应当采用何种战略、重视哪些因素,我还是借助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学说加以说明。通常所谓“赶超”至少应该分为“赶”和“超”两个阶段。在前面这个追赶阶段,落后国理应采用以产业保护为核心的防御性发展模式,而不是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一体化发展模式,后一种发展模式只有在具备必要竞争力后方可实施。对赶超道路作出阶段细分并采取不同方略,实乃理所当然。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就主张:“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至于赶超发展中应当重视哪些因素,按我对李斯特学说的梳理,就包括从人到物、从制度到经济共五方面16个因素。具体不必细述,可参见拙著《李斯特与赶超发展》。
总言之,在回顾历史综合考察了文化等非经济因素的角色后,我还是相信,经过几百年来正反两方面的实践以及对相关经验教训的总结,经济发展与赶超成功关键何在已无疑义。从自由经营到法治保障,从改善国内交通等基础设施到吸引国外先进的生产要素,从保护和培育幼稚产业到效仿先进并参与合作,从开展高质量经济活动到争取不完全竞争优势,行动方案其实都是清楚明白的,难点只在于如何克服障碍、落实推行。套用托尔斯泰的话说,成功的国家赶超都是相同的,不成功的赶超却各有各的障碍。为此,与其再去费力寻找成功经验,莫如仔细辨识障碍何在,每鼓起勇气多克服一个障碍,就多增加一分成功的可能。这一点该没有疑问吧?
参考文献:
Avner Greif, “Cultural Belief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A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Collectivist and Individualist Socie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2, No. 5, 1994.
Deirdre N. McCloskey, Bourgeois Dignity: Why Economics Can’t Explain the Modern Worl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Deirdre N. McCloskey, Bourgeois Equality: How Ideas, Not Capital or Institutions, Enriched the Worl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Joel Mokyr, The Gift of Athena: Historical Origins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Mark Koyama, and Jared Rubin, How the World Became Rich: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Economic Growth, Polity Press, 2022.
Nathan Nunn, and Leonard Wantchekon, “The Slave Trade and the Origins of Mistrust in Afric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1, No. 7, 2011.
R. H. Tawney,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Routledge, 1998.
Sascha O. Becker, and Ludger Woessmann, “Luther and the Girls: Religious Denomination and the Female Education Gap in Nineteenth-century Prussia”,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0, No. 4,2008.
Timur Kuran, The Long Divergence: How Islamic Law Held Back the Middle Eas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戴维·兰德斯:《国富国穷》,门洪华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迪特·森哈斯:《欧洲发展的历史经验》,梅俊杰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马克斯·韦伯:《经济通史》,姚曾廙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奇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梅俊杰:《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
梅俊杰:《李斯特与赶超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梅俊杰:《重商主义与国家赶超:世界经济史上的经验和教训》,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维译,新华出版社2020年版。
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侯小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维尔纳·桑巴特:《犹太人与资本主义》,安佳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