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默音《尾随者》:八个中短篇故事,吹皱一池春水
近期,作家默音睽违十年的中短篇小说集《尾随者》,由中信出版集团·春潮Nov+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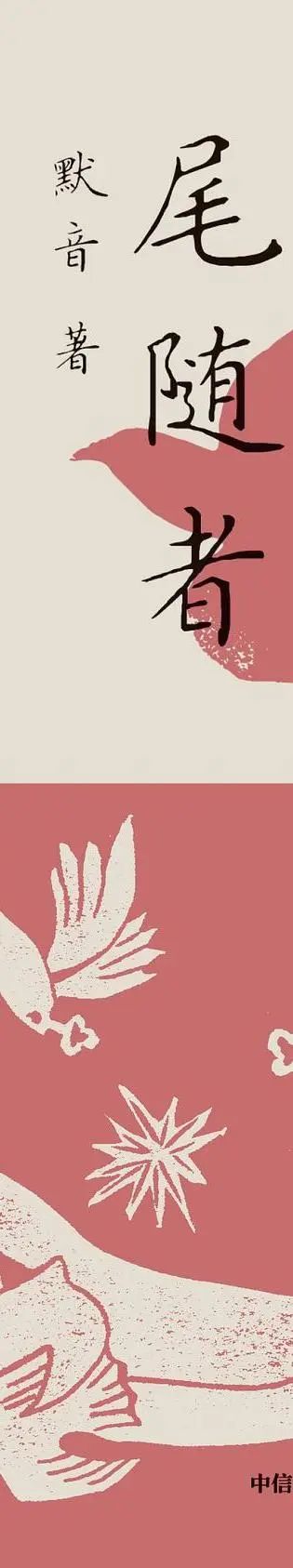
小说集包括《镰仓雨日》《酒狂》《暗香》等八篇小说。离婚后独居日本画插画为生的中年女性、工作之余只爱看书与喝酒的孤僻男子、不断与陌生经验相遇的返沪知青后代、剽窃别人的经历生产爆款的公众号写手……这些人有各自的问题需要面对,而原生家庭与早年生活留下的烙印,也一并影响着今日个体的抉择与行动。
集子以“尾随”为关键词,透过对个人记忆和家庭记忆的追溯,让萦绕不散的一切显现,也让读者在他者的经验里看见自我。
吹皱一池春水
文/夏丽柠
默音曾跟我说,她有一本小说集待出版。没想到,一等就是两年。
《尾随者》终于出版了,收录了八个中短篇小说,创作时间跨度很长,从2012年到2020年的都有。默音在《后记》中写道:“其间写的中短篇不止这些,有几篇我觉得差些意思,未做收录,所以算是精选集。”
“差些意思”,就得从默音的创作态度说开去。与默音相识多年,初识,她还在出版社当编辑,业余做日文翻译、写小说。后来,嫌工作过份消耗创作时间,遂转做自由职业者。
默音是那种勤奋,但“不苛求”的作者。“不苛求”,是指她显少公开说有何种创作计划,或者频繁发表写作思考,而是秉承一种与她笔名颇为相衬的写作态度:默默地发声(写作),船到桥头自然直,灵感到了,也就写出来了。

默音拍摄
日常里,她在社交平台上分享最多的是,去拍了什么鸟,爬了哪座山,吃了啥味的米线、面条,最近尝了哪些酒,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又做了手冲咖啡。每到此时,我就想:您是不是该动笔写小说了?
与小说家的形象比起来,默音更像生活家。她的小说里充满了烟火气。笔下人物有活生生的身边人的神韵,令读者既熟悉又陌生。那陌生的部分里藏着隐匿的自我,体现的就是默音的创作初衷: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春水之下,是生活的暗涌。可那些看似与我们无关的人,承受着不为人知的爱与痛,我们真的能够做到视而不见吗?默音的小说,我们提供了思考的空间。
中短篇小说不易写,受篇幅所限,无法像长篇小说那样波澜壮阔几十年,只能聚焦于某个场景,或者某个时间段,有点像电影拍摄里的小景别,反映的是导演的主观想法,简单说,就是强调导演想让观众看什么。
自艾丽丝·门罗以短篇小说成就勇夺诺贝尔文学奖后,读者中又掀起了一股“短篇小说热”。读者发现,短篇小说的弹性,无疑对“小景别”进行了突破。做为文学作品,故事之后隐藏着无限想象空间,尤其是以家庭做为写作根源的作品,更似将读者投入了生活的深海,想见与不想见,即在眼前。

本书开篇的《镰仓雨日》,就是将生活的隐秘刨开给读者看。想起热播的悬疑剧《隐秘的角落》,家庭的“丑闻”不是应该藏在角落里吗?但那是对外人而言。对于家庭内部成员来说,没有丑闻,只有难以接受的现实。
小说里的姐妹李纯和李星,年幼时分别被分配给了离异的父母。当成年人大喊“不许离婚,吾宁死”时,孩子们是没有发言权的。所有人都需要成长,离异家庭的孩子也不例外。可多年以后,当李纯发现母亲带着比她小十多岁的外遇对象来镰仓旅行时,自己也正在与插画老师佐野开展不伦之恋。望着母亲,李纯在“第三者”的痛苦之下又平添了“血脉”的宿命感。没人有愿意选择见不得光的爱情,最不想像母亲一样生活,却终究与她走上了同一条路。这种拼命想挣脱原生家庭的撕裂感,让李纯显得格外孤独。偌大的世界,无论走到哪里,我们始终被困在原生家庭里,逃也逃不掉。
同样的情绪,我们也在《附加值》中远赴日本寻找自己少年时离家出走的爸爸的男主人公,以及《最后一只巧克力麦芬》中的陆南身上都感受得到。是枝裕和的电影《奇迹》中的兄弟俩一心要撮合离异的父母和好,听说在新干线上两辆火车交汇处喊出心愿,就能产生奇迹。但在最后关头,哥哥航一没有喊,他解释说:“可能,比起家人,我还是选择了世界吧。”是啊,我们必须卸下原生家庭的重负,才能勇敢地拥抱世界。这个道理,我们都懂,可谁又能做到?只有小朋友才会如此勇敢地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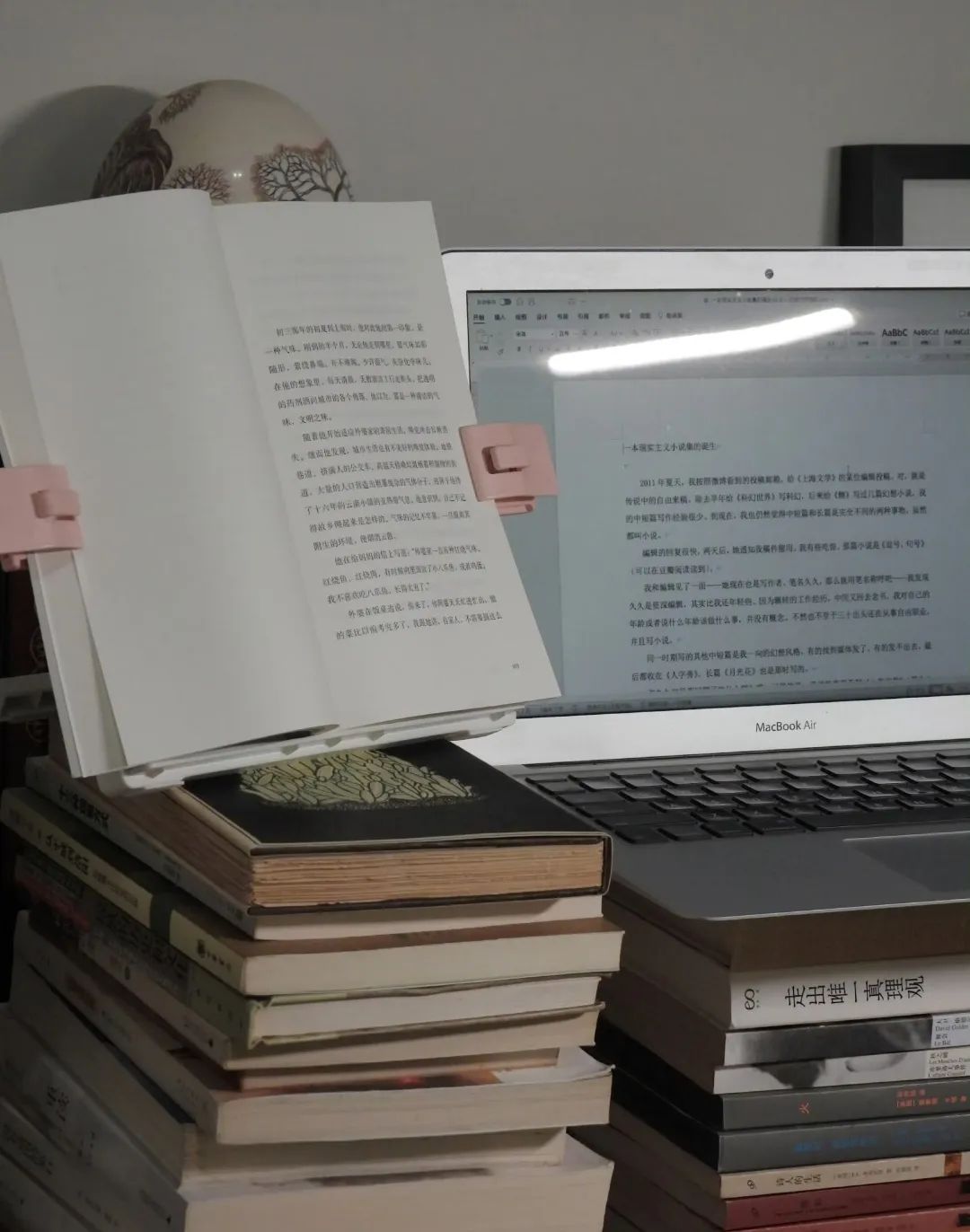
《最后一只巧克力麦芬》,是默音长篇小说《星在深渊中》的番外,失语症患者、咖啡师杨其星和咖啡馆老板陆南仍在其中。新加入者是一个年轻的女孩,街道清扫工。女孩在家乡被冤枉撞了人,独自跑到城市中,母亲仍在老家照顾被撞的人。女孩孤独地生活着,甚至与树说话,却在每日与杨其星有距离的社交中,感受到了失语者的温暖。正如女孩在小说结尾说,“好的坏的总是在一起的。”选择记住什么,接受什么,是我们的权利,也是人生智慧。
默音有个公众号“默音吃酒去”,显然,她深谙此道。倘若留意,她小说里的酒人酒语,颇有一句惊醒梦中人的意境。《镰仓雨日》里的漫画家感叹去小酒馆的频率:“唉,真难受啊。哪怕一个月能去一次,活着也有点滋味。”《暗香》里家里开酒厂的戴浩说,“能喝到一起,就能说到一起。”默音对生活的细致观察,成就了她对世界的理解,继而融入小说,形成了主人公的价值观。
纵观全书,默音的笔触细腻动人,写进了读者心里,又给足了边界感。生活犹如一池春水,有风波动,无风淡然,我们心里都有藏得最深的痛,可坐在阳光下,春天仍是春天,池水还是池水,这本小说集里,大概就写了这样的故事。
作品选读

《尾随者》
默音 / 著
中信出版集团·春潮Nov+2024年2月版
意识到时,公交车上只有我一个人。
不,准确说来并非如此。售票员和司机仍在车上。
属于过去时代的两节式公交车,车厢连接处是如同手风琴风箱的橡胶褶皱,每当车辆转弯,便像手风琴演奏时一般折成扇形,发出的只有嘎吱声,没有音乐。
司机在左前端的驾驶座,售票员在右侧的中门旁边,我坐在“风箱”背靠背的四只座位之一,背对司机,斜对着售票员。随着车辆行进,我身下的座位不时大幅度地摆动。售票员的座椅高出一截,头顶亮着灯,她像是舞台上的演员,又像是审讯台后的犯人。她挂在胸前用来收钱找零的帆布包很旧了,看着像是老一辈传下来的,背带两侧张着毛絮。制服白衬衫是新的,闪着白光。
售票员垂着眼,像睡着了,又像是死了。
我忽然有些紧张,这趟深夜的公交车会不会在接下来的站牌不停,摇晃着把我带向深夜不可测的某地?以及,我身后的驾驶座,果真坐着司机吗?会不会车上根本只剩下我和闭目合眼的女售票员?
一旦开始放任想象,车厢中部微暗的空间变得难以忍受。我感觉到脉动加快,口腔干涩,泛起咸味。

等我讲完公交车的梦,江云水没有立即做出回应。和以往一样,我坐在她的办公桌对面,视线一转便能看到对着窗户的书架上的相框。框内的照片上,比现在年轻、笑容也比现在放得开的江云水蹲在一个四五岁模样的男孩身边,揽着男孩的肩。
我问过她,男孩是不是她的儿子,她说不是。所以那是某个患者,还是什么亲戚?我知道她不回答涉及其他患者的问题,便放弃追问。
“你最近仍然感到自己被人跟踪吗?”江云水问了个和我的梦无关的问题。
“昨天还遇到过。我在罗森买东西,有个人隔着货架,盯着我看。”
“后来呢?”
“后来我就去结账了。出门的时候往那边看了一眼,已经没人了。”
“那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
“没注意。戴棒球帽,很瘦。好像男女都有可能。”我停顿一下,“你是不是一直觉得是我的幻觉?被害妄想。”
江云水温和地说:“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咖啡馆,当时你说斜后方桌子坐的人是跟踪狂——那张桌子没人。我并不是说你遇到的情况都是你臆想出来的,不过,也许有些时候是。”
“也许有些时候,确实有人在跟踪我。”
“李茗,那你觉得是什么人在跟踪你?你的公众号粉丝吗?”
她总是连名带姓地叫我,让我想起教过我的一些老师。尽管我离开学校有十八年了。
我说我当然没有头绪,继而问她,有没有看过我上一条推送,关于带孩子走一小段四国遍路。
推送的本质是某品牌儿童跑鞋的广告,拿了三万推广费。客户提出让松果穿他们的跑鞋出镜,被我拒绝了。我的公众号向来是随笔加插画,从不放照片。
我对他们表示,孩子出镜后患无穷。对方说不拍脸,我坚决不松口。
最后达成的协议是用两幅插画承载品牌方的热望。一幅是我和儿子松果手牵手的背影,我戴着遍路者标志性的斗笠。另一幅是松果盘腿坐在树下休息、我站在他旁边俯瞰的视角,画面呈现的是他有两个旋的圆脑袋,一片樱花瓣沾在发旋旁。画笔的好处是不用摆拍,场景天成。不,应该说,可根据实际需求生成。
江云水还没和我聊过松果,她有她的步调。算上今天是第三次见面,除了讲述被跟踪的事,我也提到失眠的问题,指望她给我开点特效药。她说她没有处方权,她是心理治疗师,不是精神科医生。收钱不办事,指的就是她这种吧。
我忍不住提醒她,昨天那条推送也是十万加的阅读。
“江老师,你不太了解粉丝这个群体的生态。有的人看看文章就算了;有的人爱打赏,用行动表示支持;还有人热衷于抢沙发留言,后台私信那更是聊什么的都有,好在主要由助理帮我回复;然后就是渴望在现实中和公众号作者交流的……”
我忽然说不下去了,嗓子像被猫爪挠过。我端起杯子喝水,太着急,差点呛到。江云水看我的眼神带着冷漠的好奇,像一只没学过抓老鼠的猫面对啮齿类。
直到咨询时间用完,她都没给出任何建设性的意见,只在告别时对我说,如果再做记忆鲜明的梦,请及时从微信写给她或者语音。

离开江云水位于建国西路的工作室兼住家,我沿着梧桐毛絮飞舞的马路走了一段,为了躲避毛絮的攻击,躲进一家咖啡馆买了杯牛奶咖啡。不大的咖啡馆室内整体呈白色,牛奶咖啡装在比iPhone SE更迷你的玻璃杯里,二十五元。我想起和某位咖啡培训师聊天时听来的,花式咖啡的成本占比最大的不是咖啡而是牛奶。十七年前我打工的那家台湾人开的红茶馆,一杯柠檬红茶也是这个价。如果仅以此作为观察样本,感觉近二十年来物价没什么变化。这当然是错觉,看看房价就知道了。我认为培训师说错了,咖啡的成本,不管是花式还是黑咖啡,最多的部分在房租。
江云水是否知道她的居所是本城最昂贵的地段之一呢?如果她有一天厌倦了心理医生的工作,只需要卖掉房子,就能在随便哪个二三线城市度过不为稻粱谋的后半生。
作为高中毕业后来到这个城市试图闯出一片天地的人,我自问混得不算差,错就错在没及时买房。对比房价,不管是以前的工资还是后来的自由职业收入,我的所得简直像个玩笑。从去年夏天起,靠公众号一个月有小十万进账,这才看见些微的曙光。
照这个节奏,明年就能凑够首付。
喝完咖啡,九号线转八号线,花了一个多小时,回到我在同济大学斜对面的家。来上海这么些年,生活区域从浦东到浦西的西南角,再移到东北角,近几年总在大学周边打转。
我喜欢大学。出于缺什么补什么的心理。十九岁离开老家,一路下来,换工作像翻书,也算是在社会各个层面摸爬滚打过。本质上我是个社恐的人,尽管为了生计不得不和各色人等打交道。大学在我眼里是最好的地方,远离外面的营营役役。草坪上、走道上、食堂里,年轻男女们在闲聊或辩论,有些在温书,有些专注于手机,并用耳机将自己与他人隔绝。他们即便在群体中也维持着个人的形态,尚未被打磨。
以前杰森嘲笑过我对校园的看法,说我把自身内面的幻想投射到大学,再从大学汲取虚假的安慰。
他还说,就像粉丝对偶像,只不过你的目标不是个人。
人类学专业的人,就喜欢给事物贴标签、做总结。我没有反驳他,是因为我崇拜他。
至少在当时。
从地铁出来不想回家,我直接进了校园。离晚饭还早,随便晃晃也不错。
地铁上看到的一幕附着在大脑皮层,不肯掉落。
高中生模样的女孩坐着玩手机,双肩包反背在胸前。有一年很热的韩国牌子,人造革质地缀满金属钉,假充朋克,实则浮华。旁边的女人像是女孩的母亲,握着指甲钳耐心地在女孩肩膀附近剪啊剪,帮她修掉包带上的线头。女孩全程头也不抬。
江云水在上次面谈时说,如果你愿意,我们聊一聊你的父母。
我拒绝道,我离家早,我是自己长成现在这样的,不要和我谈原生家庭那一套。
校门口的甬道上伫立着毛泽东像,永远昂扬的神气。老家的高中也有这么一尊,做工和尺寸逊色许多。我从雕像台座旁走过,摸出从去江云水那里就设成免打扰的手机。能够三个小时不碰手机,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但逃离带来的放松总是短暂,只要重新看一眼屏幕就够让人焦虑的。密密麻麻的未读消息和未接来电,红色的圆点和数字。我先点开某个甲方,合作过一次的玩具公司,那边说,想让他们的火车模型在我近期的推送“出镜”。当然,是以插画的形式。
我说,松果喜欢火车!不过家里没地方放轨道啊,我要想一想。
未接来电有助理小夏打来的,三次。我回拨过去,她却没接。现在的小姑娘都不太靠谱。
新媒体编辑:傅小平
配图:摄图网

原标题:《默音《尾随者》:八个中短篇故事,吹皱一池春水》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