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干春松谈儒学与中国现代社会

干春松(章静绘)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干春松多年致力于儒家思想和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他最近出版的新书《儒学与中国社会十五讲》,侧重对儒学与社会之间互动的独特认识,拓展儒家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今该如何理解儒学对于当下社会与个体生活的作用,在接受《上海书评》记者专访时,干春松认为: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儒学的主要功能是为整个社会建构和政治秩序提供价值基础。而现代学科建立倾向于概念化的问题推进方式,于是儒学跟社会的关联就会被遮蔽。他对儒学的最大关切,则是儒学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发挥作用,或者退一步讲,还能不能发挥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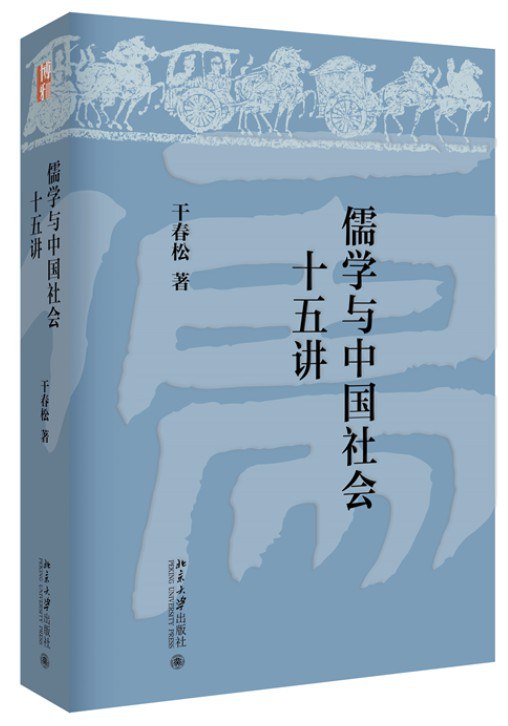
《儒学与中国社会十五讲》,干春松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10月版,415页,98.00元
我觉得书名很有意思,之前您的《儒学小史》是历时性的著作,而这本书是把儒学放到社会的横截面中来考察。这种写法您是出于什么考虑?
干春松:我对儒学的最大关切,是儒学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发挥作用,或者退一步讲,还能不能发挥作用。这体现在我最近出版的一些著作中,比如《公天下与家天下:儒家的社会理想》以及《理想的国度:中国近代思想中的国家观念》。而《儒学与中国社会十五讲》是我在北大开设的同名课程的讲课记录,从课程名称就可以看出是与我的一贯关心有直接联系。
大多的儒学史作品,主要是以人物和概念为线索来梳理儒家义理的发展史,但是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儒学主要功能是为整个社会建构和政治秩序提供价值基础。这也是其他思想传统的共同特点,正如司马谈所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诸子之争的核心在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建立社会秩序,诸子百家其实都关心这些。儒学之所以在诸子百家里显示出更大的影响力,就是它的思想所涉及的面比其他各家要多一些。方方面面,诸如身、家、国、天下都“管”。
现代儒学之所以比较倾向于采用“哲学化”的言说方式,是因为现代学科建立倾向于概念化的问题推进方式,于是儒学跟社会的关联就会被遮蔽,如此,许多在传统社会中被反复讨论的经典问题,就难以在现有的学科分类中得到展开。这并不是说学科化以后,学者不关心儒学对社会的影响,比方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里面的论题很多涉及儒学遭受现代挑战的反应,所关心的就是儒学和中国社会的关系,关注新旧转型过程中,儒学形态所遇到的挑战。潘光旦也有《儒家的社会思想》等讨论儒家与中国人的伦常和人际秩序的作品。但很显然,费孝通先生的作品更多地属于社会学的学科领域,他们的作品并不为搞哲学化儒学的人所关注,这种学科的隔阂,毫无疑问,严重地影响了人们对儒学的整全化的了解。我认为,如果不去讨论儒学和传统社会的关系,对儒学的了解就只有一部分;或者说只了解了观念的部分,没有了解观念的目标、观念对建构社会秩序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对儒学的认识肯定是片面的。
促使我从儒学与社会的问题意识展开研究的缘由还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原因,我开始研究儒学时,刚好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翻译进来,他有一个说法:儒学只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影响,但已经失去了影响现代中国的可能。这种判断的影响很大。但是我对这个说法有质疑,因为我们从小生活的那些场景告诉我,我们对祖宗的追念,或家里叔叔、伯伯、姑姑、舅舅之间的关系的处理,父母在过年的时候叮嘱的一套拜访亲戚的原则,还有清明节上坟等等,在我们生活中依然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这些东西背后有很大的部分受儒家观念的影响。如果生活在南方,尤其是浙江、福建和广东一带的人,应该不太同意列文森的观点,因为他们一直从礼俗的经验中感受到敬天法祖的观念。
这是现实的经验性给我的刺激,还有一些当时对我而言有点遥远的讨论,比如儒学与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关系。《儒学与中国社会》十五讲里有关于经济的内容,就是对这个问题刺激的回应,这促使我去考虑,儒家对未来中国的经济建构、社会建构、法制建构会不会产生关系?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导致我的研究倾向与当时很多儒学研究者不一样。二十多年过去了,儒学研究所形成的学科壁垒,依然有待进一步突破。
您第一讲就是谈儒家的自我定位和社会角色,您认为儒家在现代社会的困境就是自我定位,您特别认同徐复观讲的双重主体,能不能具体讲一下您对双重主体的理解,这和我们一般所理解的现在的知识分子有什么不同?
干春松:这个问题比较具有争议性。近代以来,人们有一种刻板的印象,即儒家是皇权的帮凶。所以,新儒家在讨论传统儒学的时候,比较强调儒学以德抗位的一面。但也不可否认在大一统国家建立之后,儒家要发挥作用,就只有被政权吸纳这样一条路。徐复观先生对儒家的社会身份有比较独特的看法,他看到上述两种倾向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儒生身上有奇特的结合,一方面儒家强调仁政、民本等基本价值,这是儒家参与政治和社会的最基本的原则,并以民本和正统等学说来制约权力。另一方面,儒生要发挥作用,又很难摆脱秦汉之后的政治格局,成为权力结构中的辅佐者,只能跟皇权结合。即使孔子和孟子等先秦儒家有更强的独立性,可以选择符合自己理念的统治者,但他们也无法撼动基本的社会等级。孔子有自己的理念,比如“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但是他为什么要周游列国?为什么孟子要去游说梁惠王、滕文公等人?因为他们自己没有统治的区域,属于士阶层,必须要与政权结合,才能把自己的理想发挥出来。他们试图让这些统治者接受自己的理念,就需要妥协和合作,如果不妥协,他们的设想完全没有发挥的空间,只能退而著书,记录自己的政治理念,以待圣君。不过,儒家与单纯迎合统治者想法的那些士人有差别,苏秦、张仪这样的纵横家,主要是策略的提供者。你今天要打谁,怎么能打赢他?至于打赢的手段是否仁义,这个不是他们要考虑的。但是儒家不同,在考虑胜负的前提下,还得符合仁义礼智这些原则。在春秋战国这样的混乱时代,要符合仁义原则,事情往往就做不成。
社会急需出效果,但是儒家的方案又是慢工出细活。所以徐复观的双重主体论,点出了儒家的矛盾之处,我觉得定位特别准。你不能把儒生看成是投靠权力的政治投机分子,政治投机分子是纵横家。董仲舒也是有原则的,董仲舒在天人三策被汉武帝接受以后,他的学生眭孟就劝汉代皇帝禅让,这就是他的理念,最终招致杀身之祸。他算是为自己的理念而牺牲的,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一部分儒生,无论在什么样的政治环境下,都坚持自己的原则,并不迎合权力。如此,儒家的命运就决定了,它的困境就在这里。一方面它是有理念的,但另一方面又必须有一个政治的场域。但是在寻求政治场域的时候,儒生跟政权的妥协是必须要做的。一旦有所妥协,儒生的独立性就很难保持。
儒学越往后发展,它的独立性越弱。但也有一些新的特点,比如宋代儒生,存在着一定的政治空间。比如王安石所推行的变革,虽然失败了,但是其政治意愿得到部分伸张。到了明代,要像王阳明那样保持独立性,就会被政治体系所排斥,空间越来越小。所以钱穆有一个很明确的说法,到了明清以后,中国的专制体制越来越严酷,儒生的独立性越来越弱。这也导致近代的人一提到儒生,就想到他们妥协的一面。
这种困境,其实在全球范围内的知识分子都有所体现,我们现在讨论知识分子的时候,一般会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任何知识分子和政府的合作都会被视为是抛弃原则的一种妥协。但事实上,如果知识分子完全不与政府组织合作的话,发挥作用的空间就会被压缩。如果按照突出其批判性特征来定义知识分子,他就只能成为一个游离于社会的批判者。一旦要在社会结构中发挥作用,肯定有一些与现有的制度、价值观、法律法规协调的地方,这种协调有可能会跟他的政治理念发生冲突。所以传统儒家的双重主体性在现代知识分子身上依然存在,这也使社会对知识分子的评价会产生多样化。
宗法、家族与孝道是儒学很重要的社会基础之一,但在现代社会原子主义、个人主义的趋向越来越明显,两者的矛盾越来越大,您怎么看这个矛盾?
干春松: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像阎云翔通过调查,发现中国社会日益趋向个体化。对此,我们都会有类似的感觉。社会越往前发展,非宗族化的生活方式将会越来越普遍,生育意愿的降低,核心家庭的形态,对传统的家族化体系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城市化得到空前的推进,某种程度上说,造成了对传统儒家基本观念的巨大挑战。我也关注到个体化的社会,甚至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儒家宗法观念的冲击超乎想象。比方说,越来越多的代孕现象,以及随着生育技术的进步,当人们可以通过细胞复制,通过人工的方式来生育的时候,那些亲情、伦理的基础就都不存在了。所以我认为一定要关注这些可能对儒学造成致命冲击的问题,当我们讨论“家”和孝作为儒家的基本特征的时候,这些特征所需要的土壤在未来是否存在,儒学将如何面对一个原子化的社会,这是个重要的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我有另外一个思考的维度,以免牺牲当下的功能来为未来埋单。我想先把最困难的问题放一下。我现在关心的是,即使中国社会向原子化或个体化的转型不可避免,但在这个过程中,儒学还能不能有所作为?中国现在城乡二元结构很明显。在乡村社会里,人们依然是依靠家庭养老,多子多福的社会基础依然存在。在城市已经日渐个体化,而乡村还在家庭化运行的当下,中国还需要提倡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还需要提倡孝道和亲情。
理论难题的冲击性太强了,我只能先绕着走。在独生子女的时代到来的时候,这些独生子女的父母将如何度过他们的晚年,这些问题很现实。我认为在这个时代,不要过早地去分析原子化的时代儒学该如何,反而应该关注孝道观念依然还有残留的中国人这一代,如何健康平安地度过晚年。听上去好像是一个非理论性的讨论,因为那个理论问题实在是太大了,对儒学几乎是颠覆性的,这意味着儒学建立在血缘和宗族的基础上的格局被颠覆以后,儒学还能不能存在。也正因为如此,我的理论很难做到彻底,那样太“绝情”了。
儒家讲爱有差等,“三纲五常”最初也是将权利与义务结合起来的,但在古代社会很早就转化为上下级关系乃至维护皇权之下的等级制,在现代社会,我们是不是要抛弃三纲五常而代之以新的权利义务关系?
干春松:对,但是这个问题其实贺麟他们就开始处理了。对平等的理念我们该如何处理,比方说组织结构里的上下级关系,或者说家庭结构里的父子关系。父亲和孩子是平等的,领导和员工在基本权利上也是平等的。但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在所有的结构里都是平等的,是否在一个工作场景或教育场景上,接受上下尊卑的关系。
我觉得如何处理基本人权的平等与人在社会组织、权力结构中的关系,是特别现实的问题。在西方社会其实也有很多讨论,就是平等和自由的关系。我们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自由和平等是互相促进的,但很多政治学者也指出,平等是自由的敌人。自由意味着人和人在程序平等的情况下进行竞争,竞争的结果必然是有输有赢,造成一个结果上的不平等。可能是财富的不平等,或者是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甚至还有先赋性的不平等。我觉得我们对儒家的讨论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没有区分权利平等和社会格局中人和人之间的差距。甚至把中国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都归咎到儒家提倡爱有差等,认为儒家认可了不平等。其实我们会发现,在儒家的制度理念中,对平等和差异的复杂性有充分的体现。既有类似天赋人权的理念:比如说,认为人除了为父母所生以外,还有人为天生的理念,这种理念也是所有人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的制度观念的基础。但儒家同时又认为人为父母所生,那你一出生,就处于一个社会结构里的不同,儒家认为你要接受这种不同。所以我认为现在社会批儒的时候,是把所有的问题搅和在一起。贺麟先生在《五伦观念的新检讨》里已经在开始区分权利平等和由于各种原因所产生的实际存在的不平等该怎么理解的问题。
儒家有天下观,很多建构是建立在天下意识之下展开的。而现在民族国家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形态,儒家在具体的实践层面上来说,与民族国家的冲突很大,您怎么看?
干春松:刚才我们说到平等的问题,儒家认为从终极的意义上,最后的结果是人和人之间的充分平等。因为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天下的秩序就根本没法理解。这点,我跟葛兆光老师他们有一些区别。葛兆光老师批评部分学者谈论天下观念,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否定,是要怀念曾经有过中心边缘的帝国秩序。如果我们面对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把国与国之间能力的、实力的差别合理化,事实上是把强国对弱国的优势地位合理化,这一点,天下观念的提出有其意义,即使历史上并没有存在过,但理念的价值一样重要。现在重新提出天下观念,是在反思民族国家体系所导致的不平等后果。因为民族国家体系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国家利益至上,会合理化强国对弱国的剥夺。我反复引用杨度的那句话,即认为民族国家体系是“对内文明,对外野蛮”。这一点也是有许多历史事实可以作为证据的。
为什么中国人对这个问题特别敏感,是因为中国接受民族国家体系时,是积贫积弱,这固然是由于专制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拒绝变革的原因,但国家的落后并不能成为殖民合理性的根据。我们一直处于民族国家秩序中比较边缘、比较弱的地位,当然会质疑这样的秩序。天下观念恰好是要批评民族国家体系把国家实力的不平等合理化。很多人也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这个目标五百年也可能实现不了。我认为,即使我们暂时不能实现国与国之间完全平等的局面,但依然可以提倡以国与国的平等价值为基础的天下理论,来批评、反省现有的秩序体系。不能取消这个批评的维度。
您书中有两讲都是谈法律问题,古代社会有法律儒家化问题,而现代法律的基本原则又使儒家退出了公共生活,瓦解了儒家化制度的惩戒机制,那么儒家只能成为个人修养了?
干春松:我特别同意你这个说法,我以前写过一本书《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核心就是要讨论这个问题。儒家与社会结构的分离,尤其是与法律体系的分离,儒家就只能退入个体修养的私人领域。现在很多人喜欢去讨论君子人格,强调浩然之气,反而不去讨论儒家的底线伦理。我们认为道德是社会的高阶要求,法律是低阶的要求,但是促使社会顺利运行的是一些基本法律法规,儒家能否为现代中国的法制提供资源,这是我关注这些问题的出发点。就是儒家或所有的法律法则,与社会运行机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中国社会处于血缘社会向个体社会转变的过程中,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个体化社会。但我们现在的法律体系是移植过来的,是一个完全以个体权力为基础的法规体系。社会意识和法律规范之间的距离是中国社会普遍存在法律的权威性不足和大家守法意识欠缺的问题。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加强普法教育,但另一个是,我们现在很多法律的条文脱离了中国人的情感和价值取向,必然会导致法律效率的折损。
这些年出现的几起为母亲复仇(张扣扣、于欢)的案件,都引发了社会巨大的争论,就是上述矛盾的体现。
古代社会通过科举制度维持着一个庞大的乡绅社会,因此科举维系着儒家的文化价值和传统制度体系之间的平衡,失去这个平衡,儒家价值观的生存土壤逐渐流失,现在谈儒家的知识阶层,好像主要就只有你们高校教师了,儒家要在社会发挥作用,就很困难,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干春松:以往中国社会一个比较合理的地方,就是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互动很密切,读书做官、告老还乡。在现代教育体系下,教育主要是职业培养,农村中有知识、有能力的人都跑到城市,甚至学校也在向城市集中,进一步抽空了农村的有机体。但最近有一些好的苗头,比方说绍兴——我的老家,当地政府强调发挥乡贤的作用,鼓励城市里退休的教师、干部回乡生活。这些新乡贤跟儒家看起来搭不上边,但鼓励城市的精英阶层回乡,能满足叶落归根的心理需求,也能带动一些社会资源为家乡的发展作出贡献,效果比较好。我个人认为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传统社会结构的种借鉴,可以产生很正面的作用。在老家已经有这样的例子,知识阶层从城市回到乡村,利用农村的风景和自然条件,建立相关的研学培训基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可以把这些尝试看作是“新乡贤运动”。以前梁漱溟搞乡村建设事实上没有成功,现在如果以产业带动,或者以智力加入,可能是乡村建设一个很重要的方向。这样的一个方向跟儒学有什么关系呢?首先是,在社会角色的定位上,他们类似于现代版的乡绅。第二就是充分借助了乡土社会中的故土情结。这个春节我在泉州,当地政府说泉州的经济是一种“熟人经济”,即充分借助泉州人的乡土情感来提供投资机会,这个提法很有启发性,这里面也有许多儒家观念的印记。
整本书读下来,我感觉通过儒家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社会中现代性的很多问题,但是儒家似乎很难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当然并不是说一定要有解决方案。只是更多地表达一种无奈或失落的情绪,比如您讲儒家和道家,最后说我们就看看《论语》《庄子》吧,很无奈。
干春松:我的这种“畏难”情绪,你看得很准。关注社会问题的人对儒家命运的焦虑可能比只关心理论问题的人要严重。我认为没有一个理论建构可以一揽子解决儒学所面对的困境。我觉得自己现在还只是处于提出问题的时候,我以前做过天下理论、重回王道这些理论探索,但这些年,我也在告诉自己,现实中有那么多问题,可能更迫切。当然,可能也是我对自己的理论建构能力信心不足。中国社会还没有定型,在一个高速运行的社会里,你想去建构一套稳定的新儒家的解释体系,难度实在太大,这是一个现实的考虑。《儒学与中国社会十五讲》更多是反映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但终究,我还是期待建构一个新儒学的理论体系,迎接来自社会和理论各层对儒学的挑战,成为我的学术研究的总结。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