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3·21|随时随地能睡着的他们,学习、婚姻、工作都被拖累
有人因为睡不着困扰,有人却因“总是犯困”痛苦。
“瞌睡虫”“懒人”,是上海女孩罗梦(化名)从小学时代就被贴上的标签。小学,一天8节课,她至少3节课在打瞌睡;到了初中,瞌睡的时间延长到了半天。
因为爱打瞌睡,对学习这件事有心无力的她,高考时只考入了一所职校。念职校期间,瞌睡频率又高了一些,一天8小时,她有6个小时在打瞌睡。
小时候,她真的以为自己只是爱睡觉,但时间长了,细细想来,每次发困她都无法控制自己,拍巴掌、掐大腿……这一切动作都无济于事。
25岁那年,罗梦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被确诊为“发作性睡病”。这是一种慢性睡眠障碍,临床上以不可抗拒的短期睡眠发作为特点,往往伴有猝倒发作、睡眠瘫痪症、睡眠幻觉等其他症状。这一疾病已在全球多个地区被认定为罕见病,也于2023年9月被纳入到中国《第二批罕见病目录》中。

华山医院虹桥院区内的睡眠障碍诊疗中心张贴着发作性睡病的临床特点。本文图片均为 澎湃新闻记者 陈斯斯 摄
过去,人们很少意识到这种罕见病的存在,也对这类罕见病患者所面临的困境知之甚少。
“得了这种病,它并不致命,但却给我的生活、工作、婚姻、社交都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罗梦说,因为爱打瞌睡,她从小总是遭到周围同学的讥笑嘲讽、冷言相向,学习、实习、求职、成家、育儿……一路过来,艰难坎坷。
过去,她在20多家公司工作过,因为打瞌睡的习惯总是频繁失业,收入也一直徘徊在上海最低工资标准。疾病也给她带来了诸多的家庭矛盾,丈夫因此与她离婚。如今,41岁的她,独自与七旬的母亲照顾一个10岁的女儿,正在申请就业困难补贴,“对于未来,不敢想,也不能多想。”
2024年3月21日,第24个世界睡眠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采访多名发作性睡病患者、患者组织负责人,来讲述这类特殊的患者遇到的生活困境。同时,记者采访了复旦大学睡眠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华山医院神经内科教授于欢,其就如何解决患者在求职、诊疗、配药、出行风险等方面的难题,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华山医院虹桥院区内的睡眠障碍诊疗中心。 本文图片均为 澎湃新闻记者 陈斯斯 摄
患者罗梦:上学期间2/3以上的时间在睡觉,已换了20几份工作
“小时候,在学校常常是课上着上着就睡着了。”这是罗梦记忆中的童年。那时候,老师也看出了罗梦的不正常,告诉了家长,但当时的医学没有那么发达,从小学到初中,家人带她去了很多医院看,医生都说“一切正常”。
随着年龄渐长,罗梦感受到自己在课堂上打瞌睡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从一天3个小时,到6个小时,甚至到后来超过8个小时,“我本身很爱学习,但总会在白天打起瞌睡来,我自己也没办法控制自己,当时就会感觉眼皮子睁不开了,就想躺下睡会儿。”
考入职校后,罗梦坦言,上学期间2/3以上的时间在睡觉。临近毕业,她去一家公司实习,老板看她睡觉的时间比工作的时间还多,实习期一结束就把她劝退了。她也在社会上连续找了很多份工作,往往都是一过试用期就被辞退,有些老板会委婉地告诉她:“这份工作不大适合你”“工作上看来你没有很大的积极性”……
罗梦曾在20多家公司工作过,有些干了一个月就被辞退,大多只能干三个月到半年,收入也仅仅是上海最低工资标准。干的活中,有前台、库房管理员等等,均为轻量化工作。2006年前后,她曾入职一家餐饮公司做服务人员,做了一个月,坚持10点上班、零点下班的工作节奏,这一度引发她甲亢急性发作,那时医生看诊时告诉她,她有嗜睡症,不能过度劳累,不然病情会加重。
随后的几年就职经历中,她的病情越发严重,不仅仅是嗜睡,还发生了猝倒,在公司摔倒过好几次,“和同事说说笑笑,就能突然摔倒在地,起不来了。”为此,她从2007年起,选择暂时脱离工作环境,回归家庭。
2010年,25岁的罗梦去华山医院求诊,那时,神经内科教授于欢刚从国外进修回来,帮她做了一次全面的诊断,这才找到真正的病因——发作性睡病。
而家庭生活也并没有她想得那么如意。失业带来的负面情绪、生活中的琐碎矛盾,外出带娃时打瞌睡带来的各种风险,成为她与丈夫中的矛盾点。最终他们选择离婚,由她独自抚养女儿。
如今,41岁的她还处于失业状态,正在申请就业困难补贴。由于时常担忧外出时打瞌睡、一觉不起,多年来,家人常陪同她一起出门。“我妈妈如今70多岁了,从小帮我一起带我女儿,现在等于她又养了一个我,不知道她可以陪伴我多久,未来的路我该怎么办?”
患者鹏鹏:尝试洗冷水澡9年无法解决瞌睡难题,妻子不理解而离婚
33岁的鹏鹏(化名)与罗梦有着相似的遭遇。
读书时期,因为总是在课堂上睡觉,鹏鹏被周围人打上“懒人”标签。
从小学、初中到大学,鹏鹏从未意识到这是个病,甚至一度以为是蛇伤带来的后遗症,“在我12岁时,那会儿住在江西,有天夜里停电,我半夜起来摸黑去上厕所,被毒蛇咬伤。那时候缺乏治疗条件,我扛了一个晚上才去治疗,医生告诉我蛇毒会破坏神经,我也一度以为我爱打瞌睡就是这个蛇伤引起的了。”
鹏鹏大学毕业后,只找过一份工作,随后就自己创业。平日里的他,甚至会一个礼拜不出门,一天在家睡觉18个小时,都觉得不够。结婚以来,他经常被妻子指责“没有上进心”,最终因各种原因,妻子选择了与他离婚。
“别人说羡慕我,能睡真好,但不知道我无法控制自己睡不睡。我也被家里人说懒惰成性、上进心不强,起初我以为是我意志力不强,初中到大学我就坚持了9年,冬天用冷水澡洗澡,我以为这能锻炼我的意志力,但最终发觉一点效果都没有。”鹏鹏回忆,他也多次去过当地县人民医院检查,拍过脑部CT,但医生没有检查出他有什么毛病。
确诊“发作性睡病”是一个巧合。那一次,鹏鹏在家里刷手机,正好刷到了一个短视频。视频中提到,一名女孩在确诊发作性睡病的第二年,开始接触摩托车,在一个公益机构的帮助下,这名患者化身“追梦骑士”,骑摩托车从西安出发,历经77天、8000多公里,她在这趟旅程中尝试着对抗病魔,希望可以找到抗睡病的钥匙,创造一种“内驱力”。
这个故事启发了鹏鹏,他意识到自己和这名女孩有着一样的症状。于是,他辗转找到了这家公益机构,咨询到上海医院可以看这种病,随后就找到了华山医院神经内科于欢教授,经各项检查包括睡眠监测,最终他被判定患有这种罕见病。
患者叶子:经历精神折磨,上路开车风险并存
在25岁发作性睡病患者叶子(化名)看来,除了就业难、工作难外,这个疾病还给她带来了巨大的精神折磨。
“它不影响我健康,也不影响我寿命,但直接拖慢了我的人生进度。”叶子将自己比作一台时常断电的显卡处理器,“每次断电,就只能不断重启,所有的数据都需要重新跑起来。”
毕业3年,工作过1年零2个月,叶子已经找过5份工作,最短的仅仅持续了10多天就离职了,有老板在辞退她时,曾直言:“为什么你总有那么多的觉要睡?”而那时的她,被问得哑口无言,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患病。
“现在我还会时常做噩梦,想起开会时突然自己睡过去了,而老板就坐在一旁盯着自己;或是工作没做完,就直接睡过去了,剩下的工作只能由同事赶工帮自己去完成。”叶子说,过去多年来,紧张、焦虑、害怕,时常伴随自己,而她最大的精神折磨还在于,作为一名设计师的她,常常分不清梦境与现实,后来她知道,那种感觉在医学上被称之为“睡眠幻觉”。
发作性睡病患者,还时常面临开车时的风险。叶子经历过,开车时突然打瞌睡,那时候她感觉到车子歪歪扭扭地在路上开,不断压线,马上就要撞上绿化带,吓出了一身冷汗,只能立马靠边停。
这样的经历鹏鹏也有过:开车打瞌睡,车速降了下来,车道还发生了偏移,自己想要强装镇定往前开,但困意袭来、难以自控,“那时候的眼皮子会变得特别沉重,我试过滴风油精,扇自己嘴巴,但没一点帮助,最好的办法还是立即选一个合适的位子停车,但车子如果开上了高速,不能立马停车,就完全不敢相信会发生什么。”
发作性睡病患者组织、觉主家发作性睡病关爱中心负责人暴敏东坦言,她还遇到过一名患者,职业是一名公交车司机,因开车时打瞌睡导致发生了车祸,并因此被判刑,随后,他的家也散了。很久之后,他才确诊了自己患有发作性睡病。
专家:患者确诊前的过程是漫长的,还存在配药难买药难
作为治疗睡眠障碍的专家,华山医院神经内科教授于欢接触过很多发作性睡病患者,“这些年来,很明显可以感受到,这类疾病的患者越来越多,一下午30个门诊病人中,其中10个是发作性睡病患者,各个年龄层都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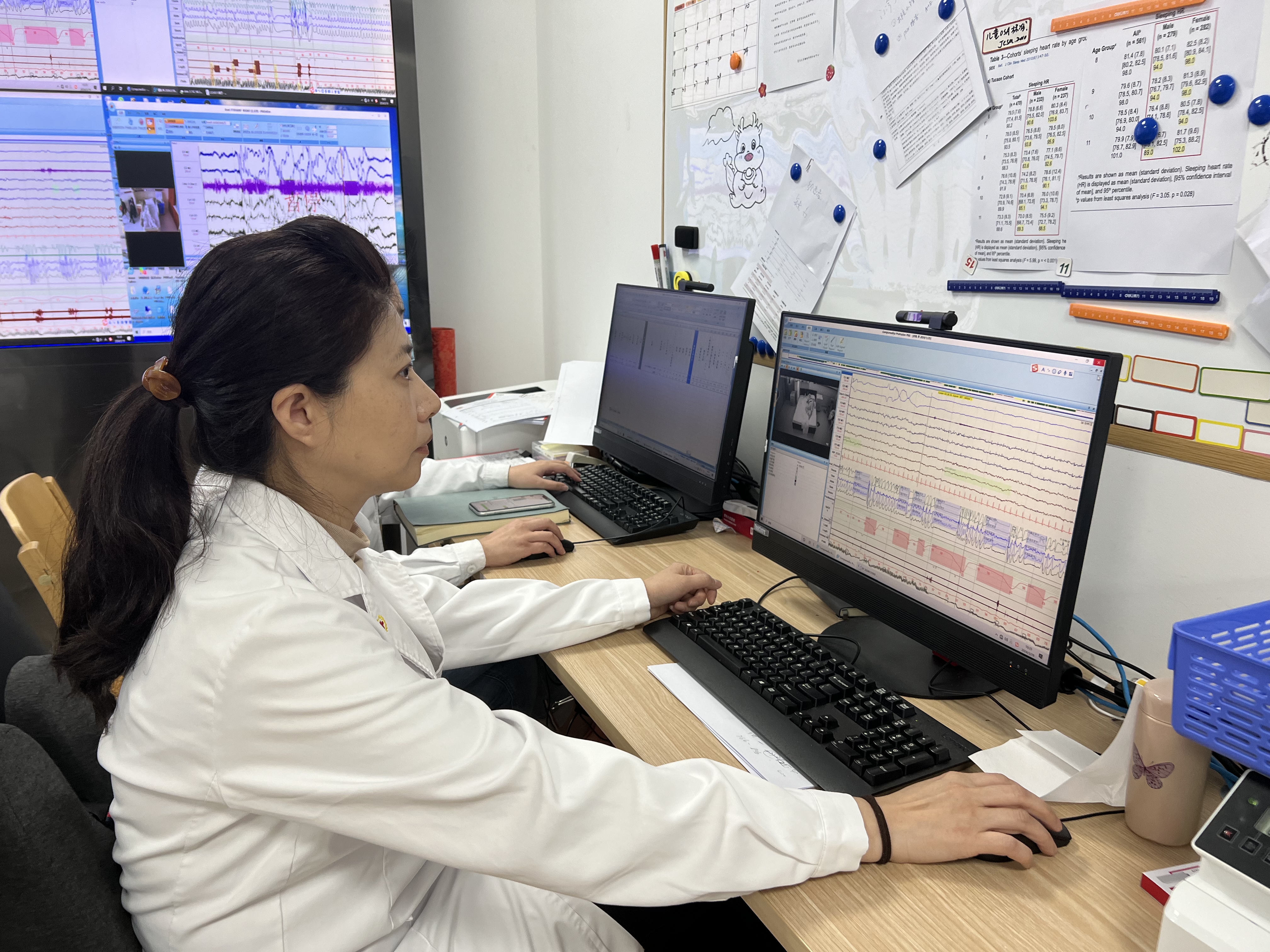
于欢教授正在查看患者的睡眠监测情况。
尽管是一种罕见病,但于欢表示,这种病诊断并不难,难就难在病人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病,不会来看。“一般来说,这种病的确诊主要是通过做多导睡眠监测,再做一个遗传基因检测,另外再结合影像学检查,来排除颅内可能发生的器质性病变等,就可以明确诊断,个别人群可能还需要进行脑脊液检测等。”
诊断容易,但患者确诊前的过程往往是漫长的。“我遇到很多患者,起初从小就有嗜睡的毛病,但很多人不知道这是个病,直到10年、20年甚至更久之后,才来看诊。而国内的睡眠障碍诊断中心的数量其实也并不多,在很多的基层医院,医生如果没有接触过或听过这类病,也很难第一时间识别出来。”于欢说。
发作性睡病患者药物治疗的可及性,也是于欢关注到的。“在治疗发作性睡病的药物中,莫达菲尼、替洛利生等新药已经上市了,但目前多数医院药房没有备药,患者难以获得。而作为非一线治疗药物的‘专注达’,是目前临床开的是较多的,一个月花费700多元,用药负担也相对小一些。”
在于欢接触过的发作性睡病患者中,往往普遍经历过家庭生活的不幸福、个人前途不明朗等,“社会对他们的关爱不足、对疾病的认识不足,导致他们的生活工作都是不幸的。”于欢坦言,原本就业、工作就很困难的发作性睡病患者,他们还需要经历配药难带来的困难。“当前在临床上,他们可以使用的药物属于国家一类管制精神药物,这类药物的开具有严格的标准,多数医院只能一次开3天的用量,最多也只能开15天的用量,很多病人每1-2周跑来医院配一次药都很正常,请假配药也会给他们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困扰。”
于欢也意识到了睡病带来的开车风险。她希望,中国能针对公共交通从业人员普及睡眠检测,“荷兰、法国等多个国家都有相关法规。拿荷兰来说,他们的公共交通从业人员只有做过睡眠检测,排查睡眠方面的疾病,才可以领取驾照。而我国虽然还没有开展起来,但已经迈出了探索性的步伐。就在2023年下半年,民航体检中心与我们合作,明确要对航空从业人员开展睡眠监测,一般1-2天在院监测即可完成。这项工作如能普及,将从源头上减少睡病患者的出行风险,也能及早发现并干预这项疾病。”
同时,为了提高这种疾病的认知,帮助社会做好疾病的早发现、早治疗,于欢还建议将睡眠疾病筛查纳入融入中小学生体检以及职业体检补查中,“就像学生群体查视力一样,如果睡眠疾病筛查能被纳入学生体检,那就可以帮助这一群体及早发现和识别,及早采取药物等干预措施;同样地,如果可以将睡眠疾病筛查纳入到职业上岗前的体检工作中,那么也有助于让社会更了解这一群体的存在,给予更多的关爱和理解。”
于欢表示,睡眠障碍疾病总共有七八十种,发作性睡病仅仅是其中一种。“睡眠疾病不是看一次就好,需要长期随访和管理。很多人需要长期服药,控制病情,无论对本地还是外地患者而言,配药一直是个大难题,这也就意味着对这些群体的疾病管理变得很难。”
于欢呼吁,针对治疗睡病的药物,今后能给予患者在配药方面更多便利,避免患者来回跑、频繁请假就医的麻烦。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