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高明士︱永怀东洋史学泰斗池田温先生
2023年12月11日,恩师池田温先生在东京去世,享年92岁,诚是学界重大损失。先生系出名门,为尊翁池田醇一(1893-1974)长子,而池田醇一亦是池田菊苗(1864- 1936)长子。菊苗先生为日本“味之素”(AJI-NO-MOTO味精)的发明人,被日本专利局评选为日本十大杰出发明家之一。菊苗先生夫人煮的昆布汤,意想不到会带来逾一世纪的味觉革命。菊苗先生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化学科,经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现为筑波大学)助教授、东京帝国大学助教授,然后留德两年,再回到东京帝国大学化学科升任正教授,获理学博士学位,为帝国学士院会员,退休后是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

池田菊苗先生
池田醇一先生,号古日,取自《万叶集》。中学就读东京数所学校,其兴趣偏向艺术,曾向名家学习西洋画,尤其是油画,也独自摹绘日本古画。1924年至1931年间,其父菊苗在德国时,曾代处理“味之素株式会社关系”事务。1938年,在《書菀》发表《蘭亭叙の由來》《虞世南小傳》二文。1940年、1943年曾至中国华北、东北和朝鲜旅行。1954年,因喜爱明末清初著名书画家恽南田绘画,于自宅成立“南田会”,并与同好研读恽南田的画跋。1955年,与友人共译《瓯香馆画跋》(又名《南田画跋》),于《三彩》连载。其对奈良博物馆的正仓院所藏国宝亦有独好,即使晚年病后仍去观赏“正仓院展”(1972年)。
池田先生的岳父仓石武四郎先生(1897-1975),是新潟县高田市人。武四郎先生的父亲仓石昌吉是著名思想家,亦是福泽谕吉的学生。仓石武四郎先生堪称出自名门,先后就读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京都帝国大学大学院,然后就任京都帝国大学讲师、助教授,接着被日本文部省派往北京留学。留学回国后,继续在京都帝国大学任职,并兼任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今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前身)研究员。1939年,以《段懋堂の音學》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同年,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再转任东京大学教授。仓石武四郎创立了中国语学研究会、仓石中国语讲习会(日中学院前身),对清代考据学特别是小学、音韵的研究,甚感兴趣,在中国经学、文学等领域著作甚夥,其中《岩波中国語辞典》可谓脍炙人口。其儿女之名,都取自当时所读清儒著作的作者名之一字,例如师母仓石翚子女士之名用“翚”字,即取自清儒胡培翚(著有《仪礼正义》)。

仓石武四郎先生与次女仓石翚子女士
师母仓石翚子女士为仓石武四郎先生次女,曾任幼儿园教师,善折纸手艺。

池田温恩师和翚子师母于甲午年(2014)元旦贺卡,左页为翚子师母折纸马。
以上池田恩师的家世背景,对恩师的治学似无直接影响,惟浅见以为影响仍然存在。其祖父菊苗先生发明“味之素”,来自夫人煮昆布汤一事,说明必须具备敏锐的观察能力才有可能发现,恩师的研究精神即具有其祖父之特点。尊翁池田醇一兴趣在绘画、书法,恩师的大著之一《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大藏出版,1990)的“解说”,提到识语也采录若干书画之跋,并参考早期《書菀》出版西域写经特集(六卷九号,1942;七卷二号,1943),其中刊载影印中村氏藏品之识语。此处之书画跋,或许受到尊翁研读恽南田画跋的启示;而在《書菀》找到识语材料一事,或许亦因尊翁曾在《書菀》发表文章,而引起池田先生对《書菀》的注意。恩师其实具有深厚的书画知识,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时,对展示的书画都能娓娓道来;多次受邀来台湾地区,也常赠给我奈良正仓院展册以及其他书画册。我起初不解其故,在思索尊翁特长之后,豁然省悟,恩师其实有尊翁之影子存在。
池田温先生在初中、高中求学时期,即对历史感兴趣。其后就学东京大学十一年(1950.4-1961.3,包括教养学部文科二类、文学部东洋史学科,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修士、博士课程,并曾当财团法人东洋文库研究生)期间,在教养学部,曾旁听三上次男先生主持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会”,研读的是《史记》;在文学部东洋史学科,曾修读西嶋定生先生的“演习”(相当于研究讨论),当时解读《通典‧食货田制》;也修读西嶋先生的“中国农业史”“中国经济史概说”课程。另外,又修读山本达郎主任教授的“演习”课程。山本先生在海外研究敦煌文书二年多刚回国,当时是以敦煌文献中的户籍类残卷作为教材,此文献系斯坦因所携回,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山本先生从微卷影印十数张发给学生,一字一句研读,由此理解敦煌所见北朝后期(即西魏大统十三年丁卯,547年)均田租调役制的实态。池田温先生即由此开始接触敦煌文书,进而深入敦煌学世界。
由此可知池田先生在东大就读时期所关注的课题,属于社会经济史、法制史领域。其文学部的毕业论文是《楊堅の出自》;进入大学院以后,以《唐代均田制の一考察——その施行の實態を中心として》作为修士论文,均在西嶋定生先生指导下完成,但亦受教自山本先生。修论的主旨,是从敦煌、吐鲁番户籍、手实类,证明七、八世纪之际,该地区的确有实施田地还受措施,只是其受田率偏低。1957年,兼作东洋文库研究生,从事斯坦因文献微卷制作工作。此后数年间,致力抄录官文书、寺院文书或写经识语等,日后出版专书均奠基于此。
池田先生于1961年11月就任东京大学文学部助手,至1964年4月出任北海道大学文学部助教授,长达七年,开始从事大学教师的教学及研究生涯。1969年夏秋之际,有机会参访伦敦大英博物馆、巴黎国立图书馆,实查若干敦煌文献,以及列宁格勒科学院东洋学研究所、东柏林科学院古代史考古学研究所,因为期限关系,对奥登堡所获敦煌写经断卷、普鲁士探险队发现的吐鲁番文书,只阅览籍帐类。至1971年4月,转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助教授,1976年4月荣升教授。
1970年代后半叶,东洋文库以山本达郎先生为中心,成立“内陆アジア出土古文献研究会”,不定期举行研究会;发行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史料集》)全五卷,池田先生参加编纂第一卷法制文献(1978、1980)、第三卷契约文书(1986、1987)。另一方面,由金冈照光、福井文雅两教授编集《講座敦煌》全九卷(大东出版社,1980-1992),池田先生主编第三卷《敦煌の社会》(1980)、第五卷《敦煌漢文文獻》(1992)。其后,先生出版《敦煌文書の世界》一书(名著刊行會,2003),内容包含第一部“序编”,分敦煌、敦煌遗文、敦煌文献、敦煌学与日本人;第二部“本编”,分敦煌的历史背景、敦煌的流通经济、契、敦煌汉文写本的价值;第三部“附编”,收录敦煌文学日本上代文学、敦煌‧吐鲁番研究的现况,实是研究敦煌学者必备的参考著作。土肥义和先生说:“日本敦煌学研究的进展,如果没有池田先生的业绩是不可能的”,这个说法并不过分。1983年,先生以巨著《中国古代籍帳研究 概観・録文》荣获日本学士院赏,享誉国际。
池田先生另一成就在于律令法制以及礼制研究。这一方面,主要受仁井田陞与西嶋定生两位先生的影响,远承东大前辈中田薰、石母田正等先生之学说。池田先生在文学部东洋史学科求学时,对法学完全陌生。就读大学院时,曾修读仁井田陞先生的“中国法制史”课程。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东洋文库在解读敦煌文书等,仁井田先生常出席,有机会当面请教。池田先生在东大当助手时,承蒙仁井田先生推荐为法制史学会会员,在学会报告时,亦获仁井田先生教示。池田先生在律令法制方面的成果,主要是提出“律令制”“律令法”的概念。从西晋《泰始令》至南宋、金末,甚至明初的明令,约一千年,是令与律并立时期;若由云梦秦简《语书》所见“灋(法)律令”用语看来,在中国使用“律令”一词超过二千年。因此从“国制”角度使用“律令制”,从“法”角度使用“律令法”,这在日本学界已被普遍采用,中国学界仍少见,但池田先生仍确信这个用法有它的“妥当性”。
池田先生每周一晚上在东大主持的“律令制研究会”,主要是研读《唐律疏议》,但研究成果则着重唐令。学界最受惠的成果,即由先生代表编集完成的《唐令拾遺補》(東京大学出版会,1997)。此书本系仁井田陞先生补订其大著《唐令拾遺》的宿愿,因病故未能如愿。池田先生受托,集合小口彦太、古濑奈津子、坂上康俊、高盐博、川村康等教授,共费十三年而完成这一伟业。所谓伟业,盖自江户时代前期起儒医松下见林就试图搜集唐令佚文,至明治时代以后有宫崎道三郎、中田薰继续推动,尤其中田氏已完成初步的稿本。在唐代的律令中,律大致保存至明清,但令已散佚,所以《唐令拾遺》《唐令拾遺補》的出版,不只对法制史研究作出重大贡献,对整个中国史乃至东亚史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日本律令继受自唐朝,律文大多散佚,而令文则大部保存,因此池田先生从事《唐令拾遺補》工作时,同时也进行唐日令的比较研究。1999年,宁波天一阁所藏明钞本《天圣令》残卷被发现后,先生亦据此继续唐日令的比较研究。至2007年,更集中检讨《仓库令》《医疾令》,从条文结构、字句等加以检讨,可知日本令基本上继承自唐令。
池田先生对礼制的研究,受教于西嶋定生先生讲读《礼仪志》《祭祀志》,其后关注《大唐开元礼》与唐令的关系。仁井田陞先生先前在《唐令拾遺》已指出《大唐开元礼·序例》三卷含有许多祠令(序例上)、卤簿令(序例中)、衣服令、祠令、仪制令、丧葬令、假宁令(序例下),以及礼部太常、光禄等式。池田先生继续仁井田先生未完成的志业,除讨论其版本及其流传外,并取《唐六典》《太平御览》两书、日本《养老令》与《大唐开元礼‧序例》,对照其内容与顺序,发现《序例》与前两书大多一致,而与《养老令》有较多出入。《唐令拾遺》原来条文排列顺序多参照《养老令》,《唐令拾遺補》对此问题已有所改进。
池田先生在2002年出版《東アジアの文化交流史》(吉川弘文館,2002),篇篇掷地有声,其中《裴世清と高表仁》一文,由井上光贞先生推荐发表在《日本歷史》杂志。池田先生早在教养学部学习时,即选修井上先生课程,并解读《日本書紀‧推古紀》,当时井上先生要求池田先生查阅有关隋使文林郎裴世清资历,该文的发表,堪称不负使命。其后受到日本古代史乃至东亚古代史诸位先生的启发,得以陆续撰写有关中、日、韩文化交流论文,正如此书诸篇所示(池田先生另有一篇《中國と日本の元號制》,不见于该书,而收在池田温、刘俊文编《日中文化交流史叢書》第2卷《法律制度》,大修館書店,1997,读者可参照)。
1973年9月,我以台湾大学历史学系讲师身份,获得美国哈佛燕京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资助,留职留薪到东京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研究。1974年4月,入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东洋史专攻,主任教官西嶋定生先生是我的指导教授。由于台大留职有期限规定,至1976年3月必须回国,因此我在完成修论后,立即回台湾大学继续任教。我的修论题目是《日本古代学校教育的兴衰与中国的关系——中国教育文化圈在东亚之形成的研究之一》(1986年出版增订一版,书名改为《日本古代学制与唐制的比较研究》)。在东大留学期间,指导我最多的老师,除西嶋先生外,就是池田温先生。
池田先生在东大的大学院开授“古文书”研究课程,并于每周一晚上组成律令研究会,成员包括教师及院生,一起研读《唐律疏议》等法制文献,同窗有金子修一、鹤间和幸等人。这是我初次接触敦煌、吐鲁番古文书,以及《唐律疏议》等法制文献。留学期间,到东洋文库抄录及影印敦煌文书有关教育方面资料,因此在1986年12月,我能够撰写《唐代敦煌的教育》一文,并发表在《汉学研究》4卷2期。1994年8月,参加在敦煌召开的“敦煌学国际学术会议”,并发表《敦煌官方的祭祀礼仪》一文。这些研究成果都受教于池田先生。至于律令法制方面,1994年,我在台湾组成跨校际的“唐律研读会”,迄今持续不断,亦源自先生主持律令研究会。
1976年3月,我将返回台湾大学任教,临别时,池田先生从书架赠予泛黄之《宁乐遗文》三册。其后先生有大作出刊亦常惠赐,甚至赐予不易取得之日本学界重要著作,如律令研究会(泷川政次郎代表)编《譯註日本律令》(全十一册)、井上光贞等校注《續日本紀》(全五册)等,对本人之学术研究,给予莫大鞭策与教示,永远感念。
1980年8月至1981年7月,我再度获得美国哈佛燕京社资助,赴日本、韩国进行研究一年。主要是考察两地现存的孔庙(文庙)官学及书院,同时要了解这些庙学史迹如何与现代社会生活结合。在日本的半年,我是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指导教授亦为池田温先生。我的研究室就在先生隔壁,每天看到先生孜孜不倦地进行研究工作,使我丝毫不敢松懈。特别是每日上午约十时,先生要我去他的研究室喝咖啡闲聊,这是我最感温馨的咖啡时间。听说东文研最晚下班的就是池田先生,其勤奋研究如此。在东文研的半年,我先透过先生的介绍,到东京汤岛圣堂拜访斯文会理事麓保孝教授,当时为防卫大学名誉教授,专研中国思想史。其后在麓教授的建议下,参访较具规模的足利市足利学校、冈山备前市闲谷学校,以及佐贺多久圣庙等。在韩国的半年,我是首尔大学国史学科研究教授,接受边太燮教授指导,考察首尔的成均馆,以及地方具有文化财性质的乡校与书院。这些史迹大多保存良好,收获甚多。我的“东亚教育圈”论即在日、韩考察完毕后臻于成熟,文献的记述可获得史迹充分的证明。1983年7月,拙稿《唐代东亚教育圈的形成》一书终于通过东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口试。口试前,池田先生还带我一起坐电车赴箱根,参加唐代史研究会的夏季合宿。当时我被安排与谷川道雄、东晋次两位教授同寝室。池田先生对我的关照,永难忘怀。
池田先生常莅临台湾,出席研讨会,发表鸿文。先生最早来台是1978年11月7日,作三天的私人访问。如台湾大学晚宴的照片所示,影响我最大的三位老师都在座,诚属难得,而今三位均已作古,所以照片极其珍贵。傅乐成先生事后说自己对池田先生的印象是“温文儒雅”,确实如此。

后排左一傅乐成教授、左二池田温教授、左三徐先尧教授,时为1978年11月8日。
1984年8月,台湾先成立“唐代研究学者联谊会”(简称“联谊会”)。至1989年12月,正式成立“中国唐代学会”(简称“唐代学会”)。其后常举办学术活动,池田温恩师与谷川道雄教授都鼎力支持,并被聘为荣誉会员。联谊会时期,池田先生来台两次,一为1986年12月27日,在国家图书馆演讲“天长节管见”,当日亦邀请京都大学谷川道雄教授演讲“隋唐政权的性质问题”;一为1988年1月末,在台湾大学举行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先生发表《采访使考》,同行的还有日野开三郎教授、谷川道雄教授。中国唐代学会成立以后,先生来台二次,一为1996年11月下旬,在政治大学举行第三届中国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先生发表《唐代<法例>小考》,同行的还有气贺泽保规教授、高桥继男教授;一为1997年11月下旬,先生在台演讲三场:第一场11月23日,由中国唐代学会主办,在师范大学综合大楼演讲“关于日本圣武天皇宸翰《杂集》”;第二场11月25日,由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主办,演讲“唐律令与日本律令”;第三场11月26日,由台湾大学文学院主办,演讲“敦煌、吐鲁番文书与日本正仓院文书”。

池田温先生在台湾大学文学院演讲。时为1997年11月26日。
池田先生来台湾除参加“唐代学会”活动外,也参加其他学术机构的活动。例如1980年8月,中研院举行第一届国际汉学会议,先生莅临发表《古代日本摄取中国典籍问题》。1983年4月,由财团法人太平洋文化基金会召开的中日韩文化关系研讨会,先生发表《东亚古代假宁制小考》。1986年12月,中研院举行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先生发表《唐朝实录与日本六国史》。2002年6月,台湾大学历史学系主办“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先生发表《东亚律令的交通规制一瞥》。

左起为胡平生、曹永和、池田温、高明士、谷川道雄、邱添生等教授,时为2002年6月22日。
2005年6月,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主办“传统东亚的家礼与国法”国际学术研讨会,先生发表《<文公家礼>管见》(此次他未亲自出席)。
以上这几场论文发表及演讲,充分展现恩师池田先生的学术专长:东亚文化交流中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学、律令法制,以及文献典籍研究。池田先生出版的专书,除上列诸书外,还有《唐研究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唐史論攷——氏族制と均田制》(汲古書院,2014)等。
我自1976年3月回国后,池田先生经常透过书信给予研究上的指导。例如1999年1月,由我主编《唐律与国家社会研究》(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一书,这是我们“唐律研读会”第一次出版研读成果。我将此书寄给池田先生,请他叱正。他收到书后,回信教示说:“你的序开头云‘中华法系的成立,无疑的是以唐律为蓝本。’但是敝生感觉中华法系源流悠远,李悝《法经》、《尚书吕刑》、《周官》秋官诸项,或若干金文可谓中法系之上古段阶,经过秦汉律、魏晋南北朝而发达进化,遂到达《唐律》。认为《唐律》是中华法系之典型,代表者即可,秦汉律等亦中华法系的不可阙构成要素。贵文表现稍过分评价唐律,是不是?”其实我的“序”,承上文接着说:“因为它是集古代以来诸法典、法理的大成,直到明、清时代,不过是在它的基础上作局部修正而已。”我这样说,基本上应该与池田先生的教示无冲突,但也让我继续思索其中源流的原委。最近从畏友高盐博教授大作获得启示,乃尝试对难读的《尚书》法理撰写如下小文《<尚书>的刑制规范及其影响——中华法系基础法理的祖型》(《荆楚法学》2021年第2期,总第2期,2021年11月),拙文亦可称为对恩师教示的报答。
2010年11月,我去东京明治大学文学部参加气贺保规教授主持的研讨会,池田恩师亦莅临指导,会中我们的合照,可说是最后一次在比较正式场合的照片。

作者和池田温恩师摄于明治大学,时为2010年11月27日。
2015年6 月,我和内人去东京方南町池田恩师府上拜访,恩师与师母精神不错,行动自如,遂取拙著《中国中古礼律综论——法文化的定型》(元照出版公司,2014.10)合照。

池田温恩师和师母摄于方南町自宅二楼,时为2015年6月10日。
2018年11月,再去方南町拜访时,恩师已由家人安排住在方南町的老人院,因此由师母接待。我曾表示想搜集有关恩师家人的资料,师母即赠予《池田醇一追悼文集》(1975)、仓石武四郎著《中国語五十年》(1973)、仓石武四郎著《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荣新江、朱玉麟辑注,2002)三册。当时先请师母在《池田醇一追悼文集》一书签名,去老人院时再请恩师签名(如照片所示)。由于师母玉体微恙,所以由其千金なおこ女士陪同前往。到老人院时,只见恩师坐轮椅,平时要卧床,言语有些困难,状况大不如往昔,拿笔签名已有些不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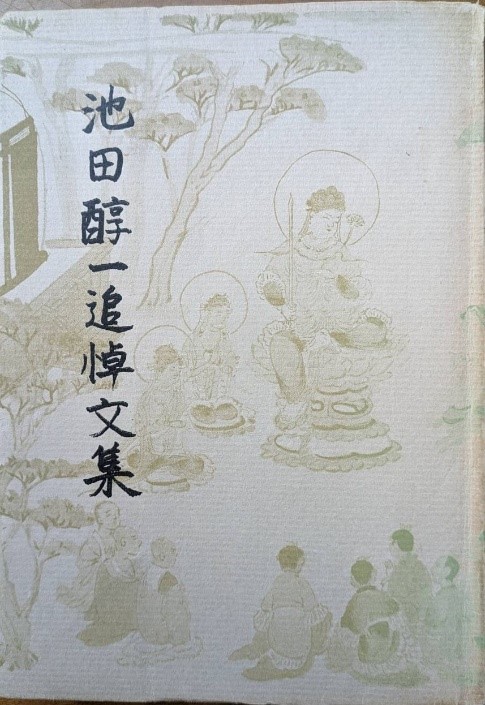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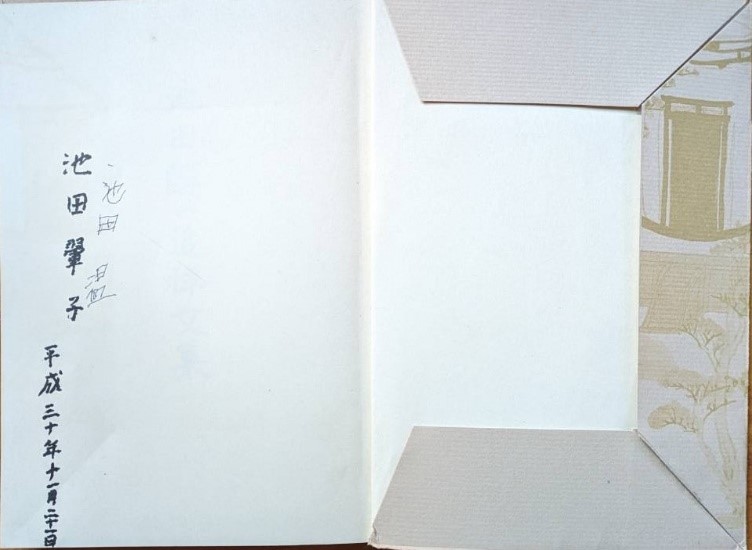
《池田醇一追悼文集》内页签名,落款为2018年11月2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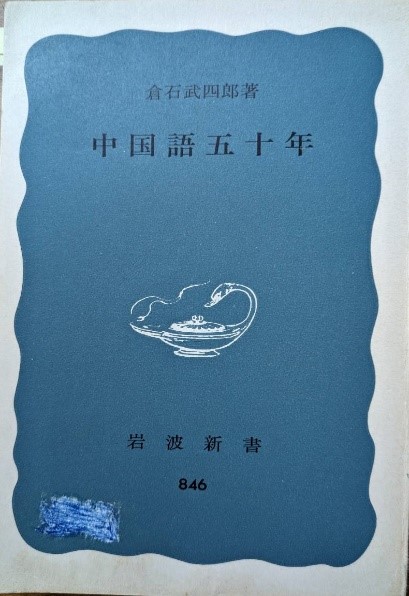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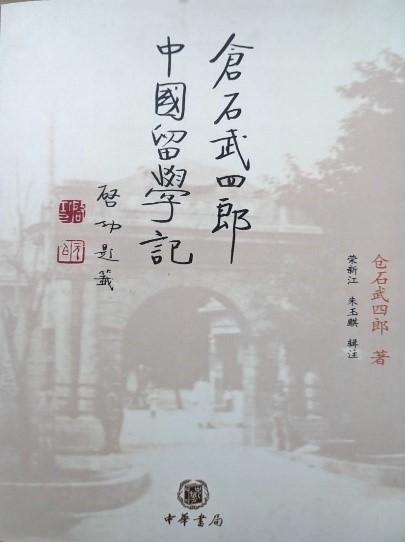
一代学人的凋萎,虽也是人生必走的路,但我们离去时,内心深感唏嘘不已。2023年12月15日在衫并区妙法寺举行告别式,灵堂前摆放一顶池田先生经常戴的圆形帽,显见家属别具用心,睹物思情,不觉柔肠寸断。
恩师为人谦虚诚恳,慈祥笃实,虽是沉厚寡言,言必深中肯綮。治学严谨,细心入微。学识渊博,精通数种外语,著作等身,累获殊勋。乐于助人,奖掖后进,不分畛域。
而今哲人其萎,典范长存。赞誉池田恩师为东洋史学泰斗、文化交流的播种者,实至名归。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