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李放春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理性”的历史与历史的“无理性”

《理性的反讽: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李放春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2024年3月即将出版
百余年来,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名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下简称“《新教》”)在西方学界可谓饱受争议,但也倍受推崇。在这部经典作品中,韦伯对早期现代西方出现的那种视营利赚钱为天职/职业(Beruf)的“资本主义精神”及其潜在的基督新教禁欲主义伦理渊源做了匠心独具的妙笔钩沉。它成为一个经典命题。
就韦伯个人而言,《新教》在其整个学术人生中无疑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韦伯遗孀玛丽安妮·韦伯(Marianne Weber)在为亡夫撰写的传记中曾提道,“这是严重的神经疾病迫使韦伯悲剧性地丧失了生命活力之后,让他这颗学术之星重新闪耀的第一部著述”,同时,这部论著“与他最根本的人格有不解之缘,并以难以确定的方式打上了他人格的烙印”([德]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简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264页)。而在晚近的另一部韦伯传记中,作者则认为:“这部作品中有关新教的诸多主题均可视作当时韦伯自身境遇的直接反映:他的孤独与绝望、无助感、渴望释放,竭力寻觅一种可以达成自我救赎的生活方式。”(Joachim Radkau, Max Weber: A Biography, Polity Press, 2009, p.200)可见,《新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术作品,而是深深烙上了韦伯个人的生命印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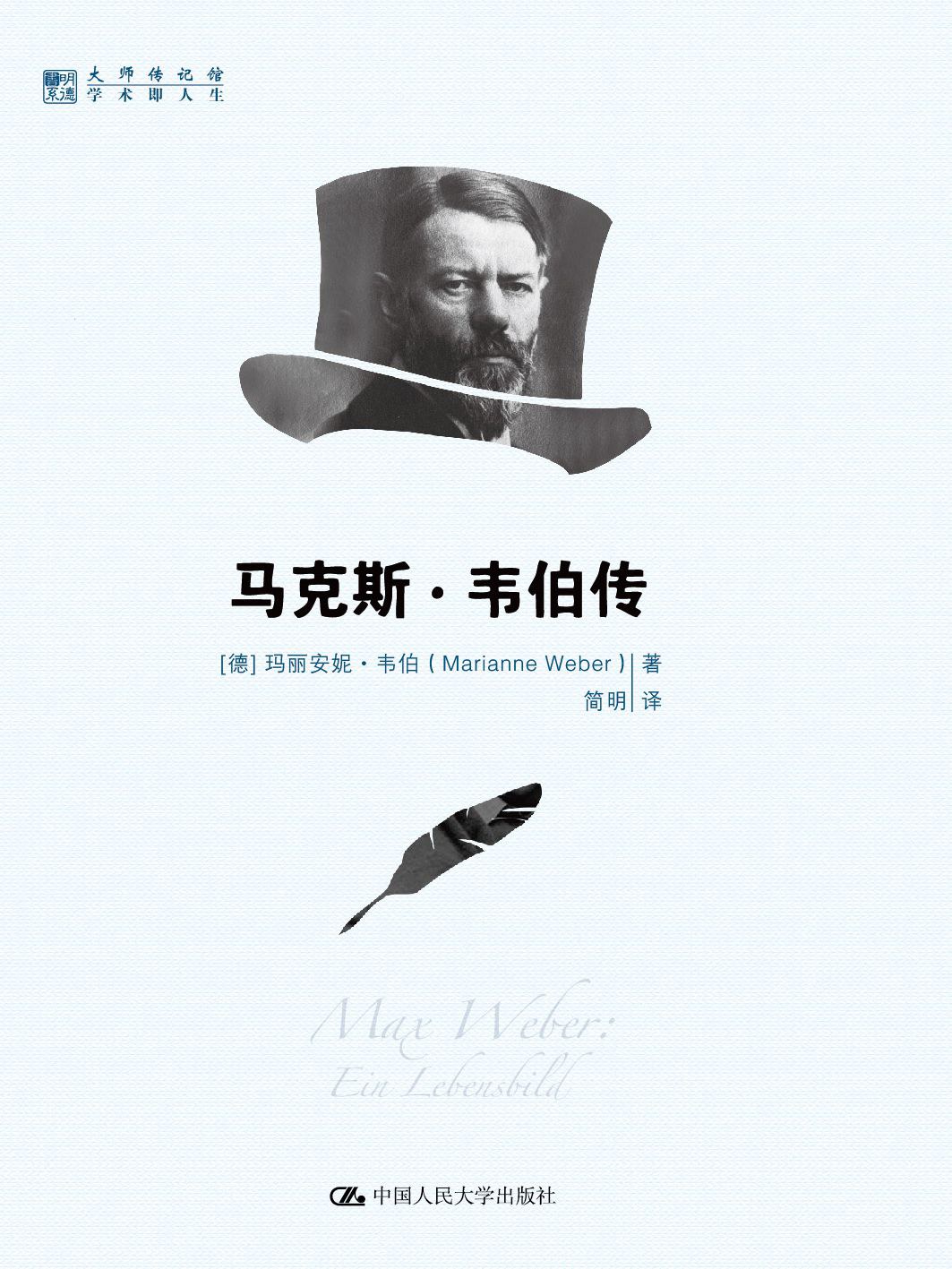
玛丽安妮·韦伯著《马克斯·韦伯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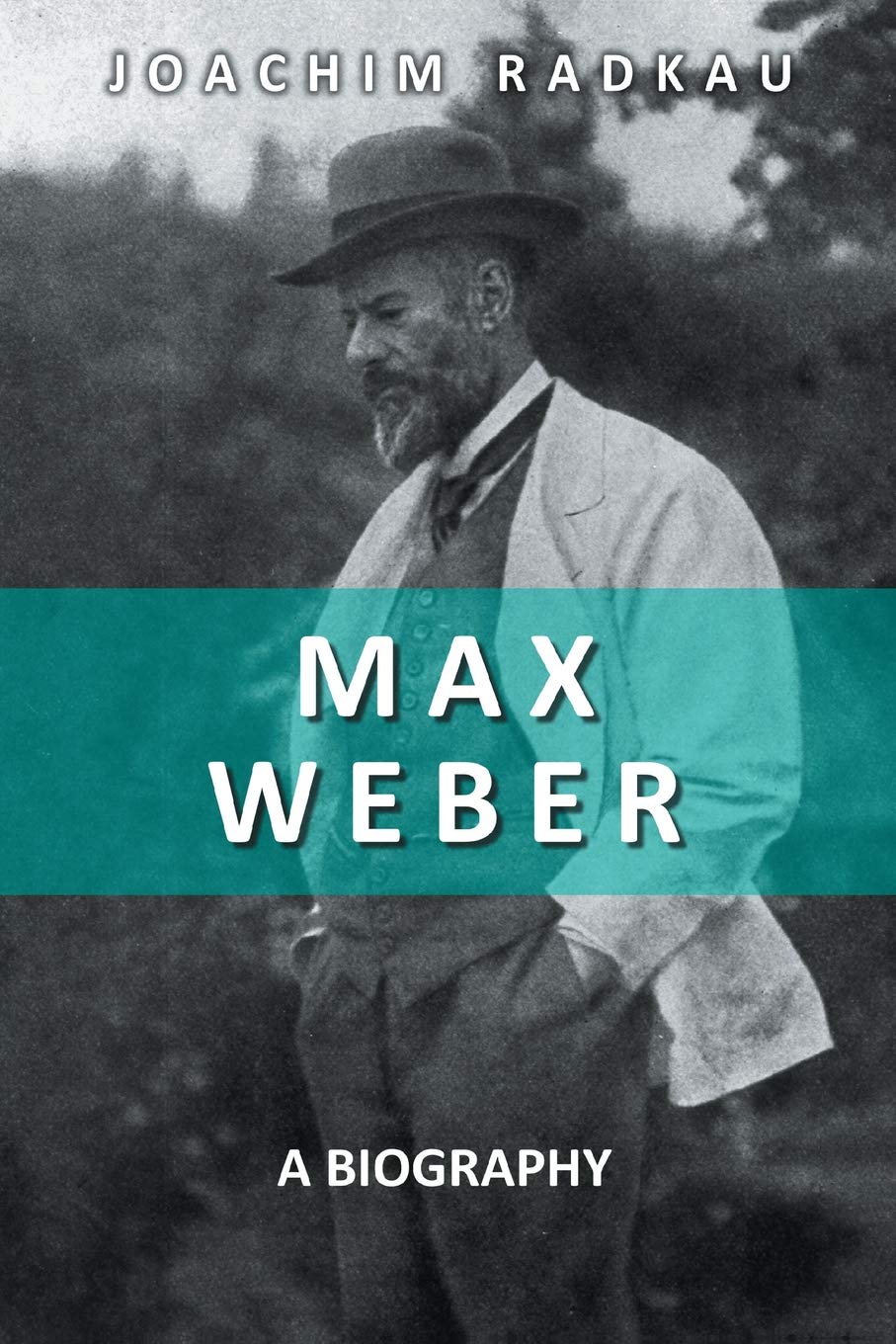
约阿希姆·拉德考著《马克斯·韦伯传》
就这部作品在韦伯著述中的地位而言,其重要性亦毋庸置疑。《新教》研究专家、英国历史学者格奥西(Peter Ghosh)认为,这部作品标志了韦伯智识生涯中的一次“断裂”,或者说一次创造性“突破”。它是韦伯关于西方现代性——所谓“现代文明”(Kultur)——之特点的首次阐发。格奥西甚至认为,《新教》提出的命题构成韦伯此后的学术工作(包括其比较宗教社会学系列研究以及《经济与社会》的写作)围绕的轴心所在。就此而论,后续的思想延展相比《新教》都只具有次级的地位(参阅Ghosh, Max Weber and The Protestant Ethic: Twin Histor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viii, 183-184)。韦伯本人也非常钟爱这部未竟的作品,晚年将它收入其《宗教社会学文集》第一卷并列为首篇。不惟如此,他还为准备《新教》的再版花很大精力作修订、补注等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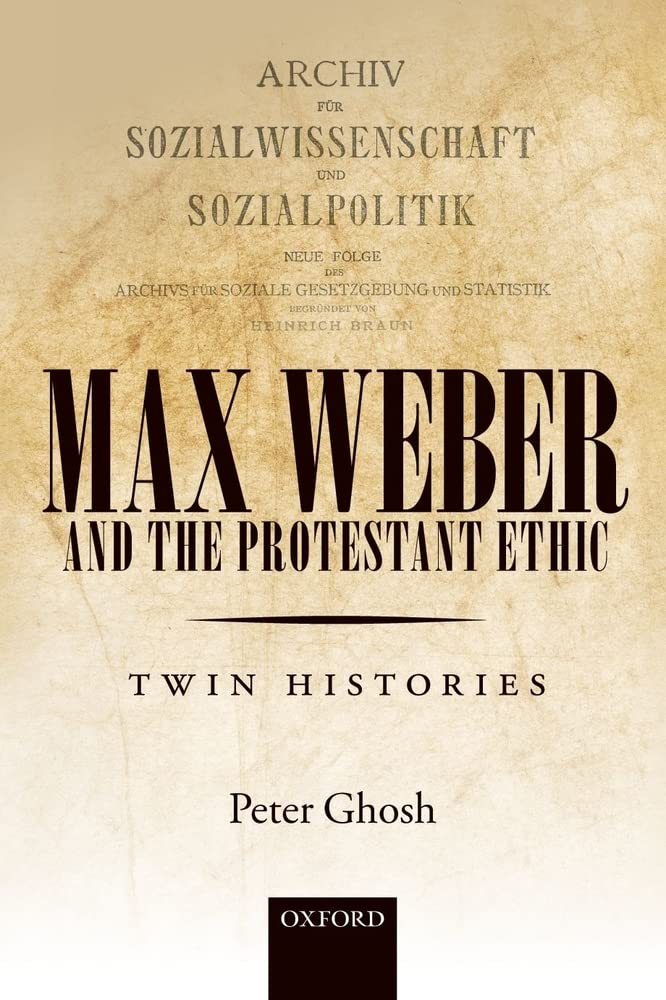
彼得·格奥西著《马克斯·韦伯与〈新教伦理〉:双重历史》
在韦伯身后,这部作品何以获得了如此受人瞩目的学术经典地位?《新教》的原创性在于独辟蹊径从十六、十七世纪“禁欲主义新教”(asketischen Protestantismus/ascetic Protestantism)塑造的生活伦理及其历史演变中梳理、辨识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文化“出身”。这项“精神”史的考察,揭示出看似极度悖反的历史谱系关联,其反直觉的论断深深震动了韦伯的同时代人。例如,在192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奥地利学者施庞(Othmar Spann)有感于韦伯命题的不可思议,形容它就像是“要从火热出发来解释冰冷”一样悖反(转引自Joshua Derman, Max Weber in Politics and Social 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89)。二战后,韦伯成为西方(首先是美国)社会科学界的热点人物,而经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翻译的《新教》也随之逐渐获得了经典地位。特别是对英美世界而言,这部由一位来自非英美世界的欧陆学者撰成的文化史杰作——或可称作是一部“精神”资本论——揭示出了现代西方文化的英美清教(韦伯所谓“禁欲主义新教”)渊源。因此,它受到英美世界的特别推崇就在情理之中了。至于二战后的联邦德国,《新教》则是在接受帕森斯式的现代化理论“再教育”过程中才重新“复兴”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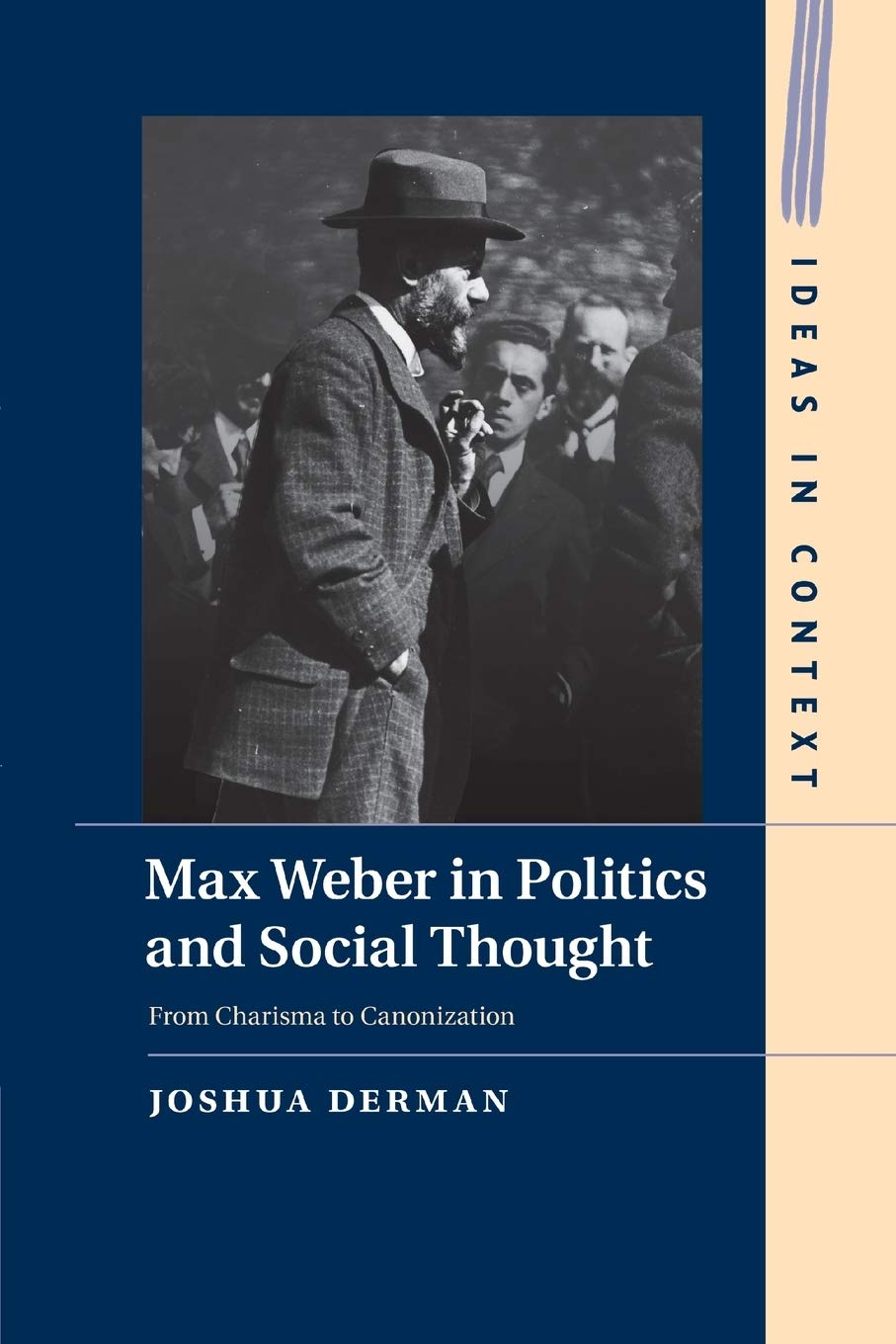
约书亚·德曼著《政治与社会思想中的韦伯:从超凡魅力到封为圣徒》
对中国读者而言,《新教》又有着别样的知识与政治意涵。上世纪八十年代,伴随着社会科学“补课”,帕森斯的《新教》英译本被引入大陆。特别是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的中译本(于晓等译,收入“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流传甚广。此后,《新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国内学界管窥“西方”文化堂奥的重要门径。同时,它在相当程度上也和现代化理论范式建立起密切关联。特别是韦伯在那篇著名序言中的发问——“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走上西方现今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呢?”(1987年版中译本,“导论”,15页)——不知曾深深震撼过多少中国学人的心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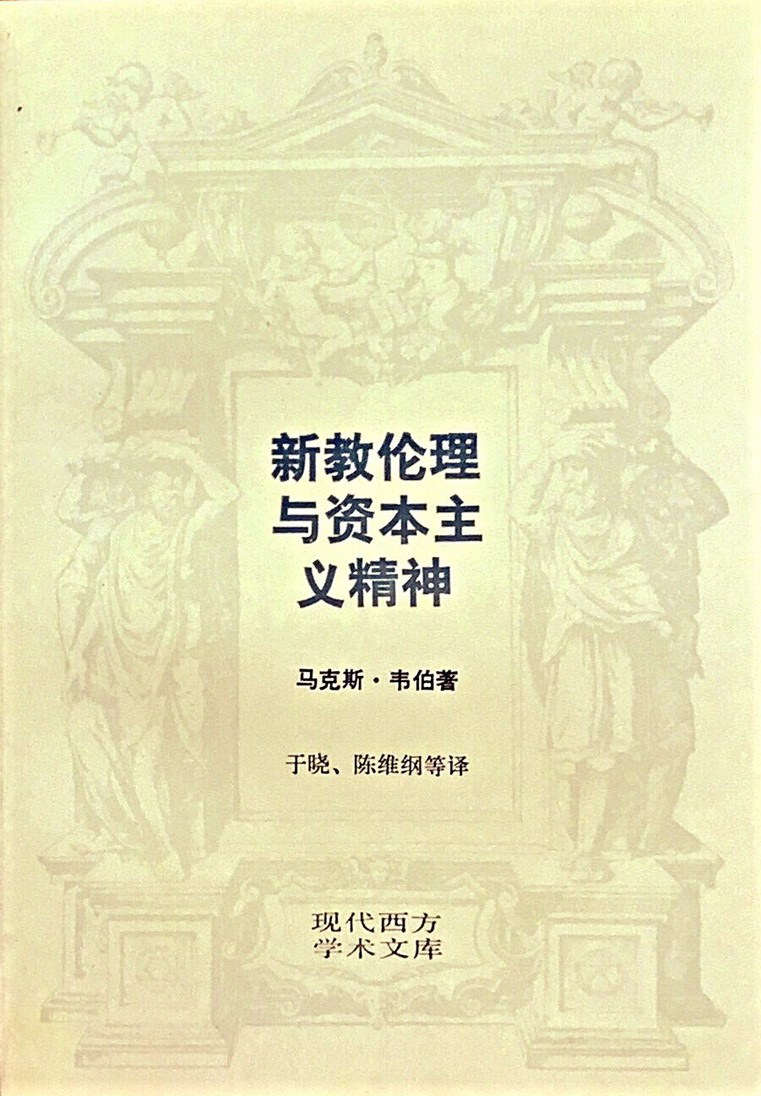
1987年出版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译本
然而,在《新教》的全球学术传播过程中,不免由于时空错位、文化隔膜而造成诸多的误读。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文化史考察高度凸显了基督教文化特别是“理性的”禁欲主义新教伦理在现代资本主义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到1920年《新教》收入其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再版中时,他为文集撰写的序言中则将研究题域进一步拓展为“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spezifisch gearteten „Rationalismus“ der okzidentalen Kultur)问题(Max Weber Gesamtausgabe, I/18, Tübingen: J. C. B. Mohr, 2016, S.116)。实际上,这个远为宏大的问题意识是1909年前后才开始发展出来的,而并不是韦伯1904年发表《新教》第一部分“问题”时的问题意识(参阅《韦伯传》,263-264页)。韦伯研究权威专家、德国社会学家施路赫特(Wolfgang Schluchter)将此称为韦伯思想的“第二次突破”(Schluchter, Rationalism, Religion, and Domination: A Weberian Perspective, translated by Neil Solom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44-48)。然而,帕森斯的《新教》英译本(在英方出版社安排下)将这篇序言以“作者序言”为题放置在《新教》正文前,导致了几代读者的误会。在汉语学界,从起初的“文化决定论”批判到近来的“文化帝国主义”指控,对《新教》的各种误读可谓比比皆是、层出不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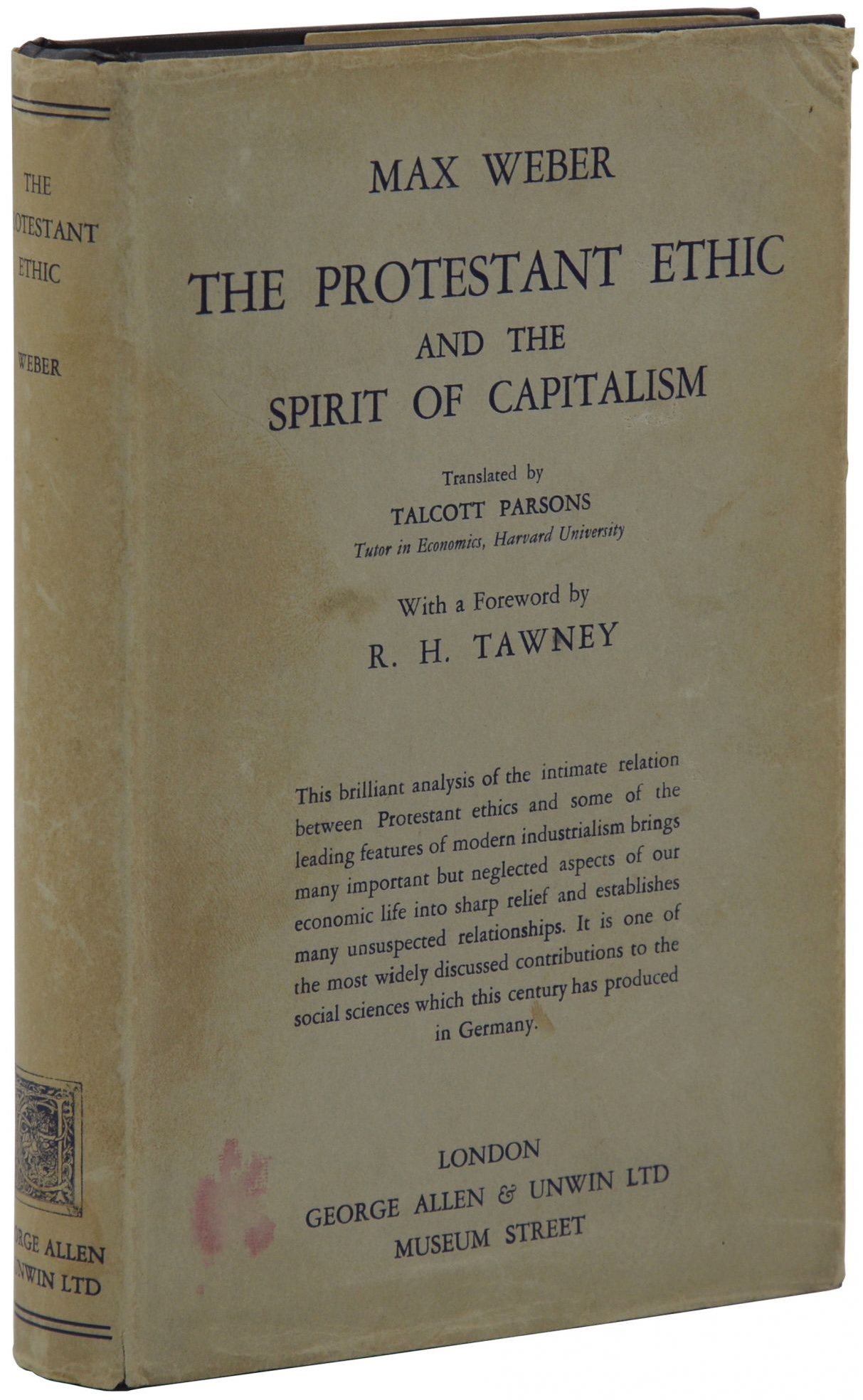
帕森斯1930年《新教》英译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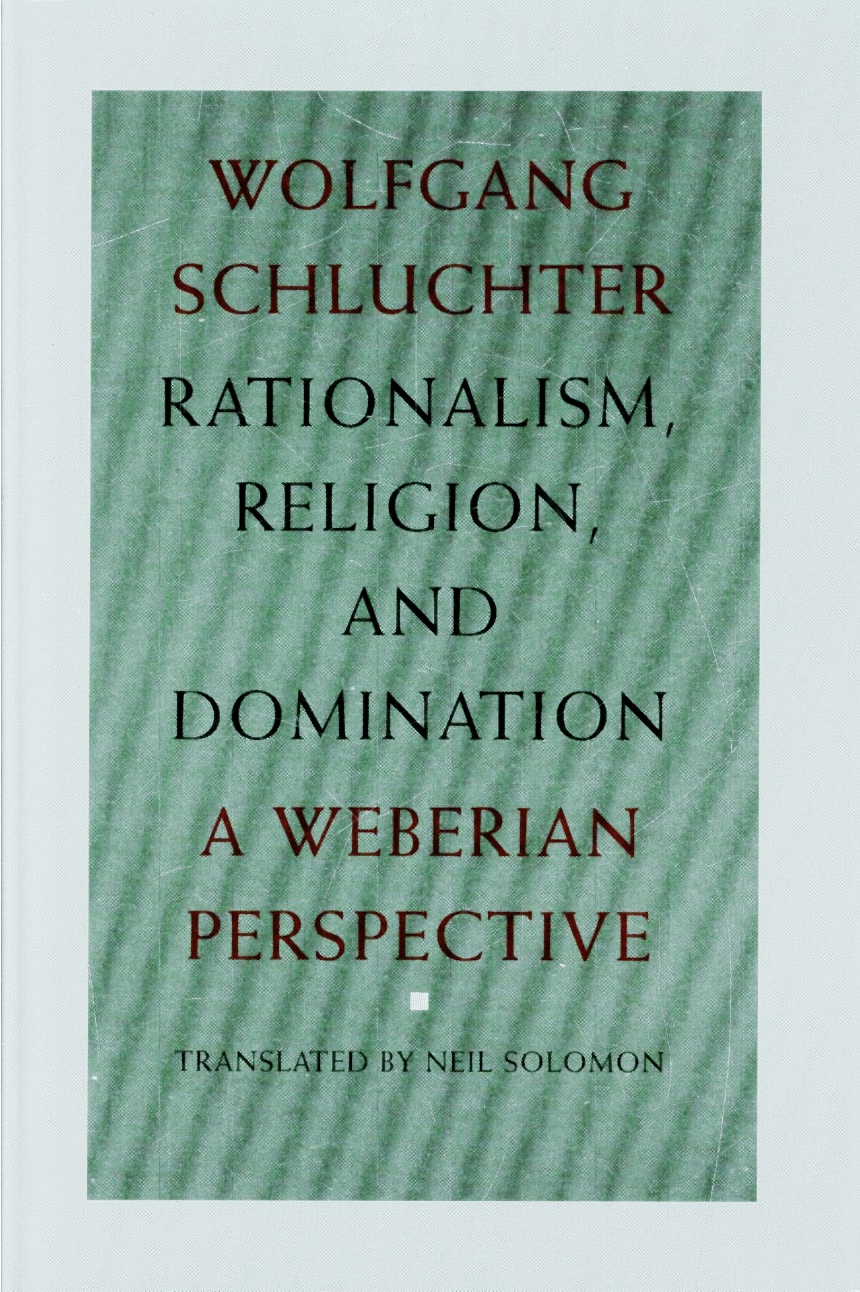
沃尔夫冈·施路赫特著《理性主义、宗教、支配:一个韦伯式视角》
实际上,此前已有不少学者关注到《新教》前、后两个版本的差异,并强调《新教》最初文本独立的研究价值。美国历史学者利伯森(Harry Liebersohn)指出,韦伯后来对《新教》的增订旨在使其契合于他关于世界诸宗教的比较研究这一更为宏阔的语境,然而却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其研究初衷(Liebersohn, Fate and Utopia in German Sociology, 1870–1923, MIT Press, 1988, p.226)。例如,韦伯在其分析中高度凸显了加尔文宗(及其他禁欲主义新教派别)与路德宗之间的差异。其中隐含的政治用意,可说是为正在崛起中的德意志民族与帝国提供一个从文化上反省自身弊病(路德宗的“传统主义”、俾斯麦式的政治威权主义)的历史借镜。借用德裔美国学者罗特(Guenther Roth)的说法,就是“要把盎格鲁-撒克逊的过去当作一面镜子来映照德国的现实”(罗特:《绪论》,载莱曼等编:《韦伯的新教伦理:由来、根据和背景》,阎克文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页)。这与1920年序言的立意可谓大相径庭。2001年,卡尔贝格(Stephen Kalberg)新译的《新教》英译本出版。为避免此前的误读,译者干脆将韦伯1920年文集序言作为附录放到最后(但中译本则又将序言重新调回到正文的前面)。2002年,贝埃(Peter Baehr)与韦尔斯(Gordon Wells)合作翻译的《新教》最初版本由企鹅出版社出版。两位译者专门就《新教》的1905年与1920年两个版本的差异做了长篇讨论(参阅Baehr and Wells, “Addendum on the 1905 and 1920 Versions of the Protestant Ethic,” in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2, pp.xxxiii-lxiii)。这个译本也将1920年绪论作为附录放到最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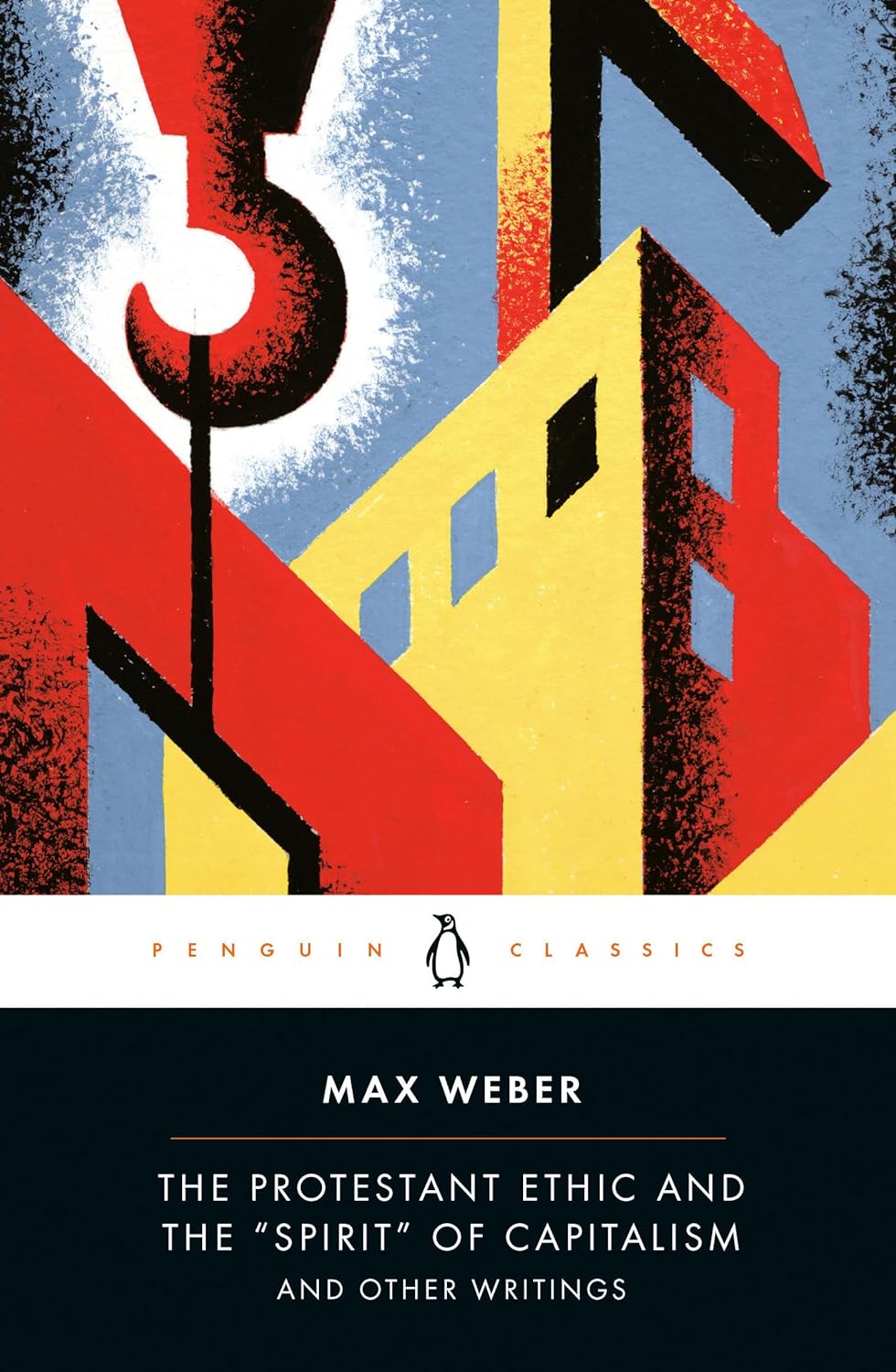
彼得·贝埃与戈登·韦尔斯合作翻译的《新教》最初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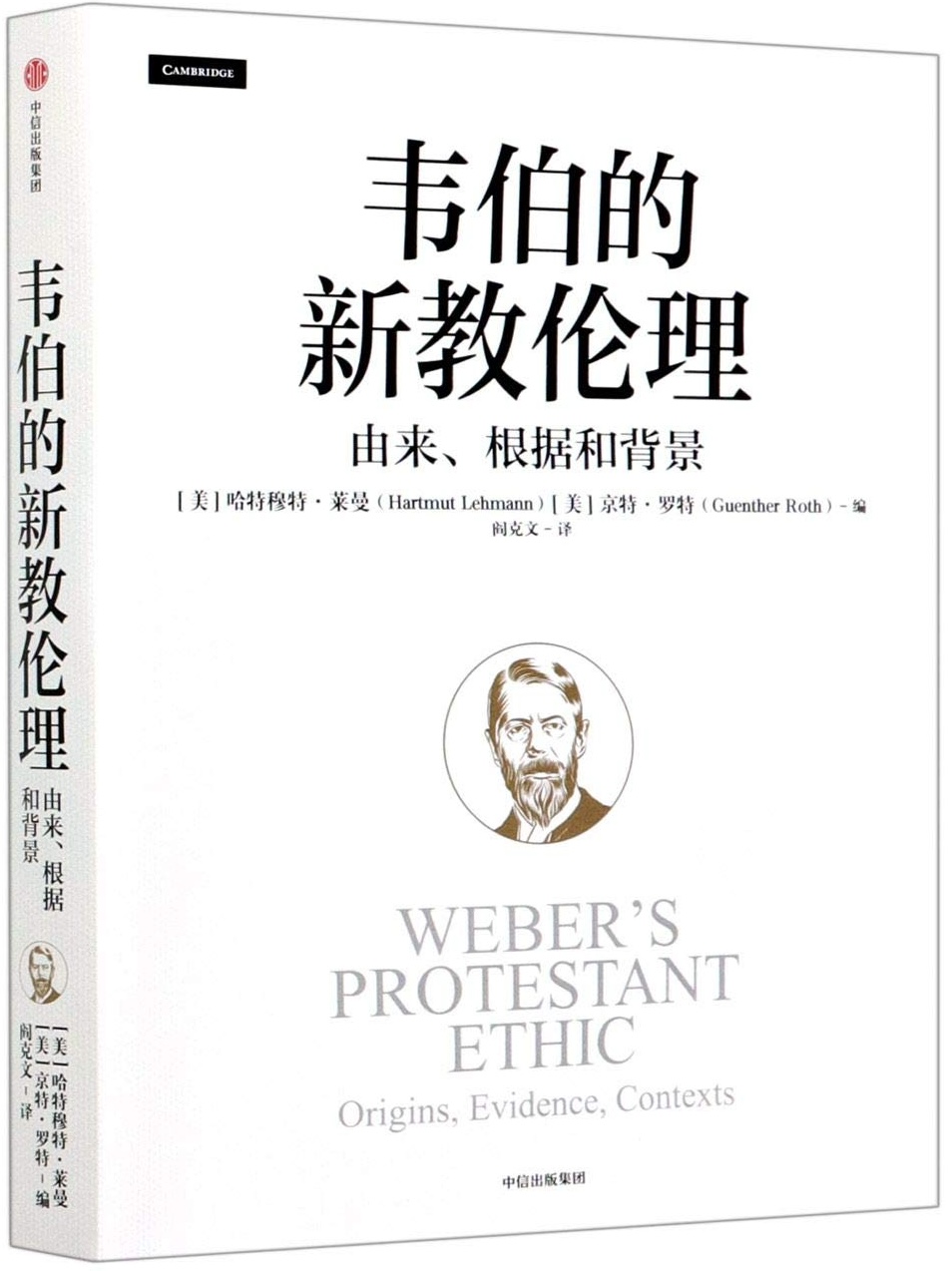
哈特穆特·莱曼和京特·罗特编《韦伯的新教伦理:由来、根据和背景》
1920年版序言的错置所引致的“跑偏”只是误读的一个原因。此外,还有很多其他常见的误会。例如,《新教》常被学界习惯性地视作一部社会学经典。这似乎也有其根据。毕竟,韦伯本人在生前将它收入了其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中。然而,事实上在《新教》的初版中完全没有出现过“社会学”这个字眼。就其最初的知识旨趣而言,韦伯的着眼点在于“资本主义精神”这一独特“历史个体”的文化意义及对其进行归因说明。从“禁欲主义新教”到“资本主义精神”,从巴克斯特的灵魂牧引到富兰克林的致富箴言——通过韦伯的妙笔钩沉而浮现出的这一文化史谱系,与其说是揭示了什么“普遍历史法则”(如“理性化”),毋宁说是具体而微地揭示了历史进程(如“理性化”)之内在的“无理性”。就此而言,与其说《新教》是一部“社会学”经典,倒不如说是一部“反社会学”经典更确切些。如果带着法则性社会科学的思维方式来阅读这部作品,则势必造成误读。如果对韦伯前期的“历史的文化科学”(historische Kulturwissenschaft)观点缺乏必要的了解,而直接带着他在后期发展出的“理解社会学”(verstehenden Soziologie)观点来阅读这部作品,也可能会产生相当程度的误读。
又如,《新教》常被视作一部“西方”(面向“非西方”)自我言说的经典。的确,对于任何阅读帕森斯译本的读者而言,首先跃入眼帘且印象深刻的就是韦伯在“序言”中围绕“西方”(Okzidents/the West)展开的“洋洋自得”的言说。然而,如前所述,韦伯最初写作《新教》时的经验立足点并不是作为整体的“西方”。在韦伯的基督教“西方”文明图景中,至少存在传统天主教世界(如意大利和波兰)、路德宗的德国以及盎格鲁-美利坚清教世界三个文化板块。即使在德国内部,也存在普鲁士的路德宗与西南德国的新教之间的差异,更不用提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巨大文化差异了。韦伯在《新教》中着力凸显的则是加尔文之后的英美清教文化对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独特历史贡献。论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意义,相较于“禁欲主义新教”,天主教、路德宗和诸如伊斯兰教、佛教、儒教等亚洲宗教一样都属于“传统主义”的范畴。就此而言,与其说《新教》建构了“西方”,倒不如说它解构了“西方”更确切些。这跟韦伯在1920年序言中的立意存在很大的反差。如果带着序言中浓墨重彩描绘的“西方”意象来阅读《新教》,则很容易“跑偏”、迷失。
因此,阅读这部经典,最好是先把“序言”放到一边,直接进入文本正文。这样,更有利于把握韦伯原初的问题意识。反过来,先对《新教》这项研究的理路及其方法论原则有了较好的了解后,再来读韦伯的文集序言,就能对他关于西方文明“特有的‘理性主义’”这个问题意识有更为准确的把握。实际上,这是在不同的研究规模尺度(scale)上提出的问题。在世界不同文明(“宗教”)之间展开社会学的比较研究时,“西方”才被视为一个“整体”,而淡化了其内部的差异或者说复杂性。它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历史个体”,尽管就其对于世界历史进程而言可能具有“普遍”意涵。相应地,韦伯所谓“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并不是说唯独在西方才产生了“理性主义”,才有“理性化”进程。恰恰相反,他在文集序言中明确提出:在世界各文化圈(Kulturkreisen/cultural circles)中,“理性化”会以极为不同的方式在众多不同的生活领域中出现(Max Weber Gesamtausgabe, I/18, S.116)。韦伯在序言中当是借用了民族学家格雷布纳(Fritz Graebner)提出的“文化圈”概念,可惜帕森斯将之误译为“文化的各个领域”(areas of culture),以至以讹传讹。实际上,韦伯关于“理性主义”“理性化”的知识立场是多元主义的,而不是一元主义的。如果我们先读《新教》就知道,韦伯的多元主义“理性”观在里头已经初步形成。他明确认为,人们“可以从根本不同的基本观点并在完全不同的方向上使生活理性化”(1987年版中译本,57页)。而在后期的比较宗教社会学研究中,韦伯进一步将这一基本原则运用到关于世界诸文明(“文化圈”)的认识。例如,他在关于中国文明的开创性研究中将儒教视为与清教截然不同的“理性主义”类型。应该说,这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先锋的,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当然,身为一个“欧洲文明之子”,韦伯主要关注的是现代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问题。

马克斯·韦伯全集第十八卷《新教》
无论是前期关于“资本主义精神”之独特性还是后期关于“西方理性主义”之独特性的探究,都和韦伯在与《新教》同时期发表的《社会科学认识与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这篇重要论文中阐述的社会(文化)科学方法论息息相关。因此,结合这篇方法论文献来阅读《新教》是一条重要门径。初步了解了韦伯关于“文化实在”“历史个体”“因果归责”“理念型”“价值自由(免于价值评判)”等一系列“历史的文化科学”方法论原理后,再来阅读《新教》,就能对韦伯如何在实质性经验研究中贯彻其科学方法有较好的把握了。
《新教》不仅出色贯彻了韦伯式文化科学方法,而且集中展示了韦伯式文明史(文化史)钩沉的匠心独运。“往昔如异邦”(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韦伯在行文中不厌其烦地反复提醒读者,《新教》所呈现的这段“精神”史是已经习惯于人本主义、幸福主义思维的现代人难于理解的。为此,他在开篇提出问题后特别提醒读者不要带着现代思维而把“工作精神”的觉醒理解成是为了追求现世幸福,也不能在“启蒙”的意义上来理解它(第一章)。与现代人耳熟能详的启蒙叙事截然不同,韦伯着意从宗教改革出发来勾勒西方现代文化的另样历史叙事。无论是十六世纪加尔文宗教义的极端非人性(第四章),还是十七世纪英格兰清教教牧实践对信众的巨大影响(第五章),抑或是十八世纪北美新英格兰人的“资本主义精神”(第二章),对现代西方人而言都是非常陌生的。直到全文篇末,韦伯再次重申:现代人如今已经很难理解昔日宗教观念对人们的生活之道、文化以及“国民性”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可以说,韦伯在整个研究中都非常着意保持历史的陌生化。
另一方面,对于现代人而言,历史以及身处历史中的人们又是可理解的。韦伯通过“理性(的)”(des „Rationalen“)这一概念的运用而建立起这一可理解性。只不过,他所谓的“理性”完全跳出了人本主义、启蒙主义的“理性”概念的框框。例如,他认为清教入世禁欲主义伦理具有“理性”性质,世俗的“资本主义精神”亦具有“理性”性质。但是,它们的历史生成与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本主义、十七世纪以来的人本理性主义无关。可以说,此“理性”实非彼“理性”。在1920年修订版中,韦伯曾特别就“理性”问题加写了一个注释:“如果说本篇文章还有一点真知灼见,但愿这点真知灼见能用来说明表面看似简单的‘理性的’这一概念的复杂性。”(1987年版中译本,156页)可以说,一方面韦伯的研究理路在策略上是“理性主义”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在研究中对“理性”“理性主义”以及“理性化”的具体处理则又是“历史主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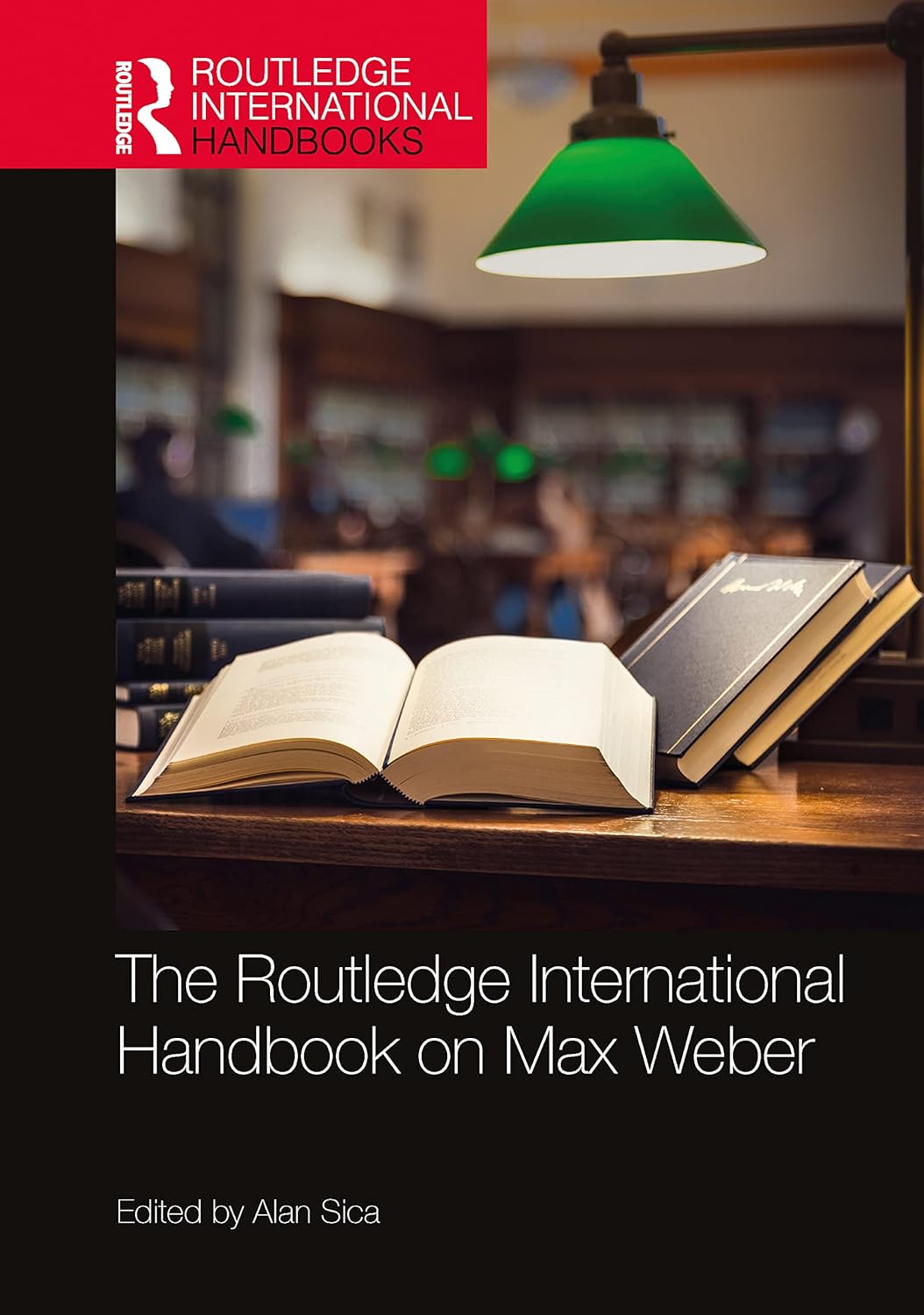
《劳特利奇马克斯·韦伯国际手册》
有论者指出,《新教》探讨的核心问题与其说是资本主义,不如说是理性主义。韦伯着重考察的并不是新教与资本主义的关联,而是禁欲主义新教与现代理性主义的关联(参阅Peter Ghosh,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in Alan Sica ed. The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Max Weber, Routledge, 2023, pp.148-149)。的确,韦伯在分析中经常将“禁欲的”与“理性的”联系起来乃至等同起来。从禁欲主义伦理到资本主义精神,贯穿了“理性主义”的线索。然而,仅仅看到这一点仍是不够的。因为,这样的现代性叙事很容易沦为有别于启蒙现代性叙事的另一种目的论(teleological)的“理性化”叙事。韦伯在研究中显然清楚地意识到这个潜在陷阱,并通过巧妙的历史钩沉避开了这个陷阱。在他的叙事中,固然“禁欲主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都是“理性”的,但新教禁欲主义“孕育”资本主义精神的历史过程则是“无理性”的。后者绝非前者的“目的”;毋宁说,它是个“意外”后果。而且,从宗教革新者们的原初动机(灵魂的救赎、天国的找寻)到其世俗的结果(财富的积累、资本主义“铁笼”),整个历史过程充满了极为悖论(paradoxical)、反讽的(ironic)意味。就此而言,《新教》绝不能说是一部“西方理性主义”在凯歌中前进的胜利史。韦伯夫人玛丽安妮在谈及这部作品背后的“思想家的人格”时曾评论道:“你可以感受到他深深地为‘激荡胸怀’的人类命运的历程所动。他尤其感到震撼的是,一种理念在尘世间的传播中不管在哪里最终都总会走向自己原来意义的反面,并因此而自我毁灭。”(《韦伯传》,266页)在一定意义上,韦伯勾勒的“精神”史在经验地展示“观念的力量”的同时也写意地呈现了“观念的悲剧”。身处技术与工具理性主导、享乐主义充斥的现代资本主义“铁笼”,他转头回望那早已被人们遗忘的早期 “资本主义精神”,并一路追溯其禁欲主义新教伦理起源。这是关于“理性”和“理性主义”的历史,也是充满反讽、“无理性”的历史。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