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世界首部!兰大名片!

两千年来盛大辉煌的丝路记忆
在悠扬的驼铃声中
在鸣沙山的风沙里
在月牙泉的水波里
也在莫高窟的飞天壁画里
如今 它还在
兰州大学郑炳林教授主编的《敦煌通史》里
《敦煌通史》是敦煌学界第一部关于敦煌两千年的通史
将作为兰州大学的“名片”、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招牌”
打响学界 打出世界

《敦煌通史》(七卷本)
“大河又东,右会敦薨之水,其水出焉耆之北,敦薨之山,在匈奴之西,乌孙之东。”2000多年前,张骞从长安出使西域,一路穿过河西走廊抵达敦薨之山,他将“敦薨”记为“敦煌”,连带这里的风土人情、山川形势送回中原,汉武帝得此先机下令征讨匈奴,占领河西地区,“列四郡,据两关”。从此,敦煌成为中华文明史上一颗璀璨神秘的明珠。
2023年8月,历时16年,由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教授主编的《敦煌通史》(七卷本)终于面世。这部丛书全面、完整、系统地重现了秦汉至明清时期敦煌及丝绸之路东段的历史变迁。2024年1月4日,《敦煌通史》入选“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贺信精神五周年重大成果”。
“敦,大也。煌,盛也”,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敦煌发生了什么?它为什么被称为“华戎交汇一都会”?中原与西域文化如何在这里碰撞交流?……近日,融媒体中心记者采访郑炳林教授及其团队成员,探索《敦煌通史》背后的故事。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尼雅遗址)
敦煌史研究并不完整
2007年,郑炳林在北京参加首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评审期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的林甘泉先生向他提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能否组织完成一部《敦煌通史》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选题。“虽然当时学界有部分叙述敦煌历史的小册子,但都不足以呈现敦煌完整的2000多年历史。为什么不做一部完整的书呢?”16年前的短暂交流,让郑炳林萌生了完成敦煌通史的想法,他也由此开启了长达16年的著书之旅。
敦煌区域的历史研究多依赖于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献,时间集中在唐宋时期,特别是晚唐五代宋初时期。因而百余年来,学界对吐蕃、晚唐张氏归义军、五代宋初曹氏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及周边地区历史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且成果颇丰。由于文献缺乏,两汉、魏晋北朝、隋及唐前期、西夏、元明清时期的敦煌历史研究处于相对薄弱的阶段。为了填补这段空白,2007年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启动《敦煌通史》编纂,2012年作为重点工作全面展开。
根据研究现状,郑炳林及其团队将敦煌历史划分为两汉、魏晋北朝、隋至唐前期、吐蕃占领时期、张氏归义军时期、曹氏归义军时期、西夏元明清七个阶段,分七卷撰写。“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项目,想要靠一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我们组成了10余人编撰团队,其中很多人如今都已成为独当一面的史学研究工作者。”
深耕汉简还原历史真相
“敦煌作为国际市场的地位形成于西汉,要想研究清楚两汉时期的敦煌历史,绕不开出土的24000枚敦煌汉简。”为此,郑炳林花费两年多时间认真研读汉简。
敦煌出土简牍数量众多,主要包括斯坦因等人在敦煌地区收集的汉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的马圈湾汉简和悬泉置汉简等,其中以悬泉置汉简数量最为庞大、内容最为丰富。小到风土特产,大到移民制度、对外贸易,汉简中的信息极大程度上填补了两汉敦煌历史的空白,为团队研究敦煌及其与西域的关系提供了一条新的道路。
然而所谓“道路”也是需要人“走”出来的。相较于难理解的古籍资料,汉简中的语句更加晦涩难懂,句读极难,甚至是一字一句,因而在本就无法识别许多文字的基础上,句读愈显困难。“我想,如果将研究唐代历史时读典籍的方法与读汉简相结合,也许能解决这一难题。”尽管读简十分艰难,但郑炳林还是竭尽所能地去解读并挖掘其背后的含义。他解释到,汉代文字数量较少,因而汉简中很多文字具有多重意思。例如,在汉简中“偷”一字并不作“偷窃”理解,而作“治病痊愈”理解,读音也不念“tōu”念“yù”。可见,在语句语义与现代汉语大相径庭的情况下,研究简牍对学者来说极具考验。

悬泉里程简(1974年从居延破城子出土的里程简和1990年敦煌悬泉出土河西驿道里程简,构成了汉代长安到河西敦煌的里程表,两处发现的原始里程简(又称“传置道里簿”),清晰地记载了汉代丝绸之路驿传设置和行进路线。)
在对汉简的研读中,郑炳林看到了“不一样”的敦煌历史。《汉书·西域传》中记载,傅介子杀楼兰王后,改楼兰国为鄯善国,汉朝派驻军三十多人,然而根据简牍显示,当时汉朝实际派驻屯田军近1500人。“可见早在汉代,敦煌便已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屯田军作为当时中央政府管理西域地区的重要兵力,也是构成敦煌居民的重要部分。此外,还有从山东、河南、河北南部、山西南部等中原地区迁徙而来的贫苦百姓,时至今日,敦煌仍有来自中原的美食变种,敦煌的糊锅正是由河南胡辣汤演变而来。人口迁徙将中原的风土人情带到敦煌,甚至传播至更远的西方,敦煌逐步成为文化交融之都。
简牍资料帮助郑炳林团队将研究汉代敦煌历史的视野从《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传世典籍拓展到更加微观、具体、真实的史学研究之中,是团队将研究从历史场景转向具体事件的一次积极有益的尝试。“以往的研究多从后世记载的资料入手,内容多比较宏大,这次写作借助汉简,让我们了解更多当时真实发生的小事,很有意义。”郑炳林说。

胡商遇盗图
跌宕起伏的两千年
“敦煌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中国西北史的缩影,也是中原王朝与西域的关系史。因为从西汉开始到唐代,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基地就是敦煌。”正如郑炳林在总序中所言,敦煌在中原王朝的边防地位,影响着中原王朝对敦煌的态度及政策取向,而这又反过来对敦煌历史走向产生直接影响。
自西汉开始,敦煌的玉门关、阳关就被视为中原与西域交界。纵观西汉设敦煌郡至今两千多年的历史,敦煌地区作为历代中原政权向西延伸势力和影响的前沿基地,见证了古代中国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
总体来说,敦煌的发展起伏变化主要存在于汉唐时期和西夏元明清时期。
汉、隋、唐俱属大一统王朝,也是敦煌社会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上升期。“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兴起,敦煌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尽管在国祚短暂的隋朝时期,敦煌依然得到较快发展”,团队成员陈光文副教授解释到。至唐朝统治敦煌的160多年间,敦煌凭借其交通枢纽位置,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一大都会。这一时期的敦煌,户口滋盛,文化繁荣,是其历史发展的鼎盛时期。
隋及唐前期,敦煌为安置来往于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商人设置专门的聚居地,即从化乡。这些商人的主体为粟特人,他们不仅直接参与商品的贩运与买卖,还担任管理敦煌市场的官吏,由此可见敦煌作为贸易市场的国际化功能。

敦煌文献P.2005 《沙州都督府图经》(中国现存最早的图经,就是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沙州都督府图经》。该图经纂写于盛唐时期,共667行,除了记载行政机关和区域外,还缕述沙州所辖敦煌县、寿昌县的河流、渠道、泉泽、堰坝、湖泊、山脉、驿站、州学、县学、医学、社稷坛、寺庙、古关隘、城堡、道路、祥瑞、歌谣等。)
西晋之后,北方进入疆土分裂、政权林立的十六国时期,敦煌先后被八个政权统治,直到吐蕃攻克沙州,敦煌开启吐蕃统治时代。五十多年后,沙州张议潮率众起义赶走吐蕃统治者归唐,唐朝遂设立一沙州治所的归义军,自此敦煌进入张氏归义军、金山国及曹氏归义军统治时期。敦煌在归义军政权的统治之下,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空前繁荣,敦煌大部分石窟壁画和藏经洞文书也是这一时期的文化结晶。
团队成员杜海副教授特别强调,尽管各种不同的民族曾聚集在敦煌,但其文化的核心依然是华夏文明。“根据文献记载,敦煌崇尚佛教,归义军时期佛教仪式上的模式化套语也体现出儒家的忠孝、仁义、民本等思想。”他认为,敦煌不同的历史时期之间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因而研究完整的敦煌历史有利于探索华夏文明对民族交流交融产生的深刻影响。
西夏元明清时期,陈光文提及,“敦煌对于元、明、清这样定鼎中原的大一统王朝而言,其军事、政治、交通地位虽有起伏,但总体呈日益下降趋势。”元朝时期,敦煌因其重要的边防作用和大规模屯田得到较快发展,然而由于明朝政府对西北边防政策渐趋保守,明朝时期西北边境和军事防线向东后撤至嘉峪关,关西地区成为蒙古族、藏族等民族的耕牧区域,而汉人数量几乎流失殆尽。这对敦煌的历史走向产生决定性影响,敦煌由边内重镇变为边外弃土,由当地蒙古头目管辖。
清朝建立后,中央政府积极开拓西域,开始在关西地区逐步设立行政建置,同时组织甘肃各地百姓向敦煌进行大规模移民。敦煌的重要地位再度凸显,成为经营西域的“口外之地”,逐渐恢复生机。但由于其属移民区域且僻居内陆,敦煌最终成为僻居西北的普通县城。
至此,两千年的敦煌古代历史划上了句号。

“驿使图”画像砖
以“小”见“大”,敦煌学研究不能只看敦煌
“我们的发展,中国的发展,要走国际道路,要与世界交流,研究敦煌的历史必定有借鉴作用”,谈及敦煌研究的重要性,郑炳林这样说。
作为华戎交汇之都,敦煌是古代中央政府经营西域的基地,更是中外文化交融、交流、交往的关键节点。
西汉时期,敦煌专门修建西域都护的军备物资存储仓库——居卢訾仓城,西域诸城邦的贡品皆经由敦煌进入中原,中原派遣至西域的官吏驻军也经由敦煌送往迎来,因而成就了敦煌“华戎所交一都会”的名号。
曹魏时期敦煌太守大力发展敦煌郡,并维护路上丝绸之路的通畅,隋代的敦煌也是通使西域的咽喉之地。“敦煌的发展牵动着整个西北历史的发展,研究敦煌历史不能仅局限于敦煌本身”。
郑炳林提到,学界曾有“小敦煌,大敦煌”的说法,“敦煌学的研究若拘泥于敦煌文献,那便只能做‘小’敦煌,研究者若将敦煌置于中国西北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之中,敦煌的史学研究价值便能以‘小’见‘大’。”
在郑炳林看来,当前敦煌学研究提倡的“东进西出”直接体现出敦煌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东进”是将敦煌历史与中原历史联系起来,敦煌是文化交融的集汇地,敦煌文献、壁画中随处可见中原文化的影响,若研究者不了解中原历史,则无法在研究过程中做到触类旁通。
“西出”是以敦煌为窗,观世界之像。古代敦煌承担着交流交往的重要职责,东来西往、形形色色的人曾汇聚于此,特别是西域诸国国王、贵人以及他们派遣的客使。根据《后汉书》记载,为迎送接待外客,敦煌郡设有较为完备的相关外事机构、官吏、译者等,同时确立了甄别外客身份、发文通知酒泉郡外客入关等相关规定。
研究历史上中央政府如何利用敦煌对外交往,能为我国如何更好地在世界舞台讲好中国故事提供思路。“2009年,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到兰州大学调研时曾叮嘱我要将敦煌学做强做大,为国争光。2019年,在敦煌研究院座谈会上,我又向总书记汇报了《敦煌通史》的编写情况。对于敦煌研究我们必须事先做好准备。”做前沿研究,随时做好建言献策的准备,这也是郑炳林撰写《敦煌通史》的初心。

人才培养与重大项目并驾齐驱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编撰的《敦煌通史》是敦煌学界第一部关于敦煌两千年的通史,七卷本由郑炳林及其学生历经十余年完成,背后离不开研究所对人才培养的重视和坚持。
研究所拥有从本科至博士后的完整人才培养体系,是《敦煌通史》完成的保障条件。郑炳林强调,“团队项目更有利于重大研究成果的产出,这对个人、团队和学校都是共赢的。”
当初与郑炳林一同撰写《敦煌通史》的学生,如今多已成为敦煌学研究中新一代的中流砥柱,李军任职于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担任院长,吴炯炯、陈继宏、杜海、陈光文都选择留在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工作,司豪强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司豪强回忆到,在他还是硕士研究生时便拜入郑炳林门下学习,在他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后,老师向他提出加入《敦煌通史》的撰写,这让司豪强感到受宠若惊。“郑老师总是给勤奋的学生更多机会,尽管我当时只是一个准博士生,但郑老师还是给了我这样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在撰写两汉卷期间,郑老师的知识储备常让团队感到震惊,他总能旁征博引地将我们想不到的史实带入具体的案例中去解决问题,这让我受益匪浅。”
杜海在读博期间加入《敦煌通史》撰写团队,他深受老师和团队成员的影响,“郑老师让我看到一个人怎样在自己热爱的领域多年保持激情和日复一日的坚持,撰写《敦煌通史》对我而言的收获是:蜕变。不论是学术眼界开阔,还是学术研究方法的提升,敦煌学已经成为研究团队成员们一生坚守的事业。”
面对学生的成长,郑炳林眼中也充满骄傲:“老师教学生不同于匠人教徒弟,老师若被学生超越,反而证明教育越成功。”未来,《敦煌通史》将作为兰州大学的“名片”、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招牌”打响学界,打出世界。

《敦煌通史》首发仪式
“《敦煌通史》的面世不仅为陆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深入开展奠定深厚基础,更为新时代敦煌学的繁荣发展增光添彩、添砖加瓦。”郑炳林希望,它不仅成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发展历程上的里程碑,也能帮助更多中国学者在开拓敦煌学研究新境界上迈出更加稳健的一步。
从早年重文献研究到如今补史、证史,敦煌学还在等待更多学者投身其中,古老的敦煌文化将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召唤中焕发新的生机,就像郑炳林所言,“这个过程也许会长一些,但一定会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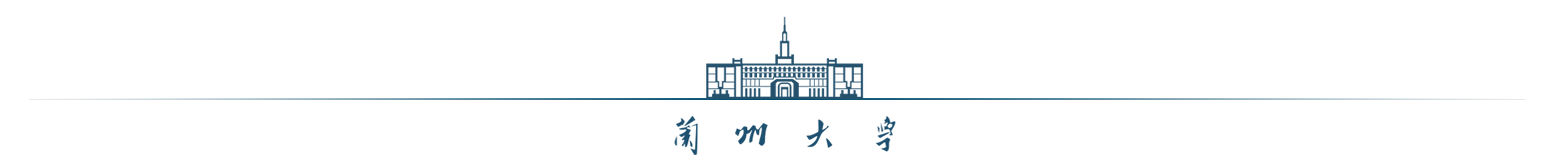
内容来源 |兰州大学新闻网
编辑 | 王文彬
责任编辑 | 彭倩
原文链接|世界首部!兰大名片!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