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吴越:一个文学编辑部里“静默的嘈杂”|新气集
文|李梓新
我和吴越、郭爽在2018年的一次线下分享,被收入吴越去年的新书《必须写下我们——被写作改变的人生》里。时隔五年,我邀请吴越来新气集播客聊聊,说说她在《收获》杂志是如何发掘新人,陪伴作者修改作品,以及见证他们的成长。

《必须写下我们》
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吴越说:“每一个小说都像要跳出来一样,它们在说话,很响亮。所以一个文学编辑部是静默当中的嘈杂。”
我们谈到《收获》杂志每期的青年作家专号以及其中的作品。吴越还分享了如何向《收获》杂志投稿的方式,以及他们选稿流程和标准。
本期嘉宾
吴越
作家,《收获》杂志编辑
以下为本期节目内容节选
从记者到虚构编辑
李梓新:这期我们来谈谈写作,我邀请了《收获》杂志的编辑吴越。
《收获》是中文文学创作者的殿堂。吴越原来是记者,然后转到《收获》杂志,既负责非虚构,也负责虚构的栏目。现在,你已经在这里工作九年,这个过程里也发掘了很多青年小说家,你还写下了那本作家访谈——《必须写下我们》。
我蛮好奇,非虚构和虚构在中文世界的文学范畴中是怎样呈现的?而且你是从非虚构写作者变成虚构作品的编辑,这个过程也特别有意思。
想先问你一个问题,在《收获》杂志,虚构的氛围会不会更浓?工作中,你们谈论虚构和非虚构,会分得这么清楚吗?
吴越:会。这是肯定的,首先题材不一样,考量的标准也不一样,甚至可以说是两个作者队伍,当中重叠的人不是很多。从量上面来说,我们杂志主要发表的还是小说。一本《收获》,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加在一起,每期肯定占2/3左右。其它的还有散文专栏,这个我们也算入非虚构吧,然后还有不定期出现的一些中长篇非虚构,所以非虚构的量没有占到一个绝对的大比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我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可能很大程度上会指向小说。
《收获》是一本文学期刊,所以在这里发表的非虚构作品应该是比较迥异于特稿概念的非虚构作品,它还是进入到了文学范畴的。举个例子,最近在《收获》非虚构榜占榜首的作品是《太阳透过玻璃》,写的是作者自己的父亲患了老年痴呆症后躺在临终病房里五年的时间。作者记录了这五年时光里父亲的状态,以及病房里面其他病床上的人的状态、护工的状态;还有伴随父亲全部机能的丧失,他们这个家族很多重要的事情。由于作者薛舒是个作家,她在下笔的时候,既能兼顾到这个话题涉及的各个议题,又能用文学的笔调和情感的抒发,把这些变成一个可读性很强的文本。这篇的特点可以看成是在《收获》上发表的非虚构的特质,它含有文学成分,但同时肯定是一个非虚构的题材。
李梓新:你作为记者进入《收获》工作,最开始,怎么上手去编辑小说或者遴选小说?
吴越:我们每一个人进入到《收获》工作的时候,除非是绝对的天才,不然都有一大堆心酸跟笑话可以讲。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因为你看过《收获》上发的作品,以及以前看的精品,比如格非、余华,现在就可能一篇都看不上,选不出来。还有一种情况相反,你可能会有特别有同理心,觉得这篇也有优点,那篇它也有亮点,都可以发展一下。这两种情况,都是没有状态的状态。
当我真正经过一些时间的磨合,进入状况后,就会体会到一个神秘的韵律,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来描述它。如果一定要说,第一个是文学的语言,不是指文采或者文笔,而是属于一个作品的节奏、腔调和选字,每一句读下去的感觉。第二个,我感觉会吸引我们的作品,对人的精神状态与时代之间产生交叠和共鸣能够表现得比较好。在文学的标准上面,既要有自我的东西,同时还要有和其它事物相互投射的自觉,如果一个写作者能有这样的一种意识,可能就会成为走得比较远的写作者。其它的标准我就不展开了,比如不写人家写过的,不要用小说来讲道理等等。
但同时,我们编辑部内部的气氛是在不断打破既有的一些判断的,我们会不断地发跟以往判断不一致的东西。举个例子,最近发了一篇中篇小说,是作家韩松落的作品。他开始写小说的时间应该不是很长,但是我觉得他是文坛的一个刺客。这篇作品的名字是《鱼缸与霞光》,写得很特别,到结尾的时候,出现了一点散文化的倾向,如果按照我们以往对小说的判断,这个地方就不能装进那个“小说的套子”里。但是,我们很希望这个作品能被更多人看到,就这样把它发出来了。发出来之后,《收获》2023年文学榜上的中篇小说类里,它被投票评为第一名。
我们既往的发表作品会形成一种标准,我们不发低于那个标准的东西,否则是对以往作家作品的不公正,但同时,我们也不断接受新作者的新表达,新的思想内容和新的观点,以及不断匹配这些观点的新结构。
大家觉得一个文学期刊的编辑部看上去好像是非常安静的,只有“沙沙”的那种声音。实际上,我个人感觉不是这样,我觉得我们编辑部内部每个人看的稿子、做的工作,还有相互之间的交谈,其实都充满了一种沉默的动态。每一期我在编稿子,都觉得每一个小说都好像要跳出来,它们在说话,很响亮,然后我们要不断低下去倾听那里面的声音。我经常觉得,我们做的工作虽然在静默当中,却是很嘈杂的,每个编辑必须要不断把耳朵和眼睛打开。
李梓新:讲得特别好。那么一篇文章最终可以登上《收获》杂志,这中间会牵涉多少位老师的讨论,最终才能够拍板?
吴越:以你为例好了,可能你最近想写一个题目,我们在认识之后,相互取得信任了,你可能就会跟我说,然后我们会进行一些讨论,我大致了知道你想写什么。如果你真的把稿子交给我,就是第一稿,我看完以后会跟你聊结构、表达等等的问题。从初稿到改动,这中间往来可能至少两三个来回,会有几个月时间。等到我把你的稿子交给我的同事和领导,而他们不会发出感叹说“吴越连这样的稿子都送来给我看”,如果到了这样的程度,那就可以进入二审,就是向我的副主编送稿子。等到主编也看到了你的稿子,提了一些意见,那就再看排期和篇幅,以及是不是有同类的比这篇更好的稿子?这些问题都回答了后,如果觉得这篇稿子确实是很难得,我们就会进入到另一个漫长周期,也就是校对。一般来说,一个新人,或者是一个在写作经验上还没有到达顶峰状态的写作者,从稿件和编辑发生关联到最后发表,三个月到半年已经是很快的速度,半年到一年是很正常的。
李梓新:我还想问,从非虚构作者或者记者的眼光,往往会相对看重这个内容跟社会的互动、在社会议题方面的意义和价值,而小说来讲,有时候它是谈一个人性上的东西,甚至与社会的关系是模糊的,这个会不会在一开始对你造成一些来说判断上的困难?你会在一开始仍然用一个记者的偏好来判断那些小说作品吗?
吴越:如果一个作品包含重大的社会性,我觉得我能比别人判断得更快,这是我作为记者的一个优势。与之同时存在的,必然是我对低仿现代小说的无感,或者说反感,比如文字方面的技巧很多,但其实没有表达什么内容的作品。这可能跟我没有长期做虚构作者有关。
李梓新:那会不会有作者提出疑问,觉得他们作品里的人物弧光或者蕴含的意思编辑是不是没看出来?
吴越:我会说,不会看不出来的,如果真看不出来,一定是写得还不够好,或者说你还在一个很小的频道里写。我们要把作品拿到一个发表的程度上看,其实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是我们对你写作的期许和鼓励;第二个是,作品发表后,大量的读者会读到它,这会对读者产生意义。有一些太过于像写作练习的东西,我认为它还不适合发表在一种大众文学期刊上,但它可能可以出在书里。比如你有一个短篇小说集,其中要有代表你自己风格和一些特别阶段特色的东西,有一些篇目是很值得收入的。但是,在期刊上发布,就需要一个更强大的理由,为什么要发表你?
作者、语言和创作的变化
李梓新:《收获》的青年作家专号也出了有小十年,你会接触到越来越新的年轻人,你有感觉到Ta们的文学技巧或者说对社会议题的表达上有什么变化吗?
吴越:2023年,我们的青年专号,当时请了两个青年评论家进行点评,一位是复旦大学的金理,还有一位是《文艺报》副主编,也是评论家,叫岳雯,她跟我年纪差不多。她很敏锐地指出了一点。她发现,我们的青年作者(87后90后00后)们创作的被收入到青年小说专号中的小说,不约而同出现了一种“幻想动物”的意象。比如白鲟、渡渡鸟、鲸,还有《夜游神》里的黑猫。这可以说是“公仔化”带来的安慰吗?还是我们的心灵都需要像龙猫一样的陪伴?或者说要寄托于一种远古动物、一种要消失的动物?这种趋势肯定不是作者们商量好的,也不是一种已经形成了的明确的写作风尚,但是可以看到大家不约而同出现了这种路径。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个人的解读是,意味着生活更加残酷了。我们很需要安慰,很需要幻想中的一种安慰性的东西来给我们实有的拥抱。最近一个世代,3-5年,我看到的写作者是写得越来越好了,现在要做一个好的写作者,难度真的越来越大。
李梓新:我看了你发给我的青年专号,我能看到的,首先是语言风格的多样化,像《白鲟》,这个故事设置在香港,背景又有曼彻斯特,开始了有一点国际化的感觉。这代年轻人的全球化痕迹本身就比较明显,他们把这些语言融合进中文里,在文本上带来了一个新的景观。另外一种趋势是相反的,也很有意思,是向本土化、方言化追寻。
吴越:我们前几年发表了一个长篇小说,是广东的一位作家林棹的《潮汐图》,她的写作用了很多古粤语词汇。发表之前,我们请她对一些词做了改造,为了让文本更易于理解。作品发布后,她一下子就受到了非常广泛的欢迎。对我来说,可能是有一点惊讶的,因为毕竟这个文本毕竟在接受上还是稍微有一点门槛的。
我还想说一下为什么我很喜欢《白鲟》这篇,这个小说里的每一个人其实都在抵抗一种叫乡愁的东西。我记得我写过一个很短小的评论,就是说乡愁这一古老的事物,我们甚至都已经在排斥它,不愿意面对它,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你无法面对一个明确的乡愁。但是作者却能够在小说当中微妙地撬动一下,我可以感受到,乡愁还是能微妙地撬动我们的命运。一个题外话,今年元旦之际,我真的带着孩子到了鄱阳湖,在鄱阳湖,我真的看见了江豚,当地人也跟我们说到了白鲟,还有很多已经消失的生物。我觉得我在小说之外,又被运送到了另一重空间里,关于地域的文化、上几代祖辈看到过的东西,它们的文化魅力竟然是那么的深,也许它现在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我们好像又真的会跟过去产生很多牵连。一个作者能够在很多个他想写的东西中去写这个很难表现的东西,这是一个小说的文心,这样的作者就能去共振和感受到更多更大的东西,就会越写越好。
创作者如何进入编辑部的视野
李梓新:小说确实是一个很精巧的装置,很不容易,你们平时一般会如何接触到新的作者呢?年轻的作者们会通过什么渠道和你们建立联系?
吴越:什么都有,自荐、他荐、我们自己去挖掘寻找。我们看很多其他期刊上发表的作品,看豆瓣,看新的中短篇,看各种文学奖项,等等这些都有。还有你联系了很多年的作者,可能最近突然进入到一个很不错的状态,你会跟Ta约一下,就问Ta在接下来的什么时候能不能写出那么一两篇?我们想看一下。总体来说每一年,这个年龄段能浮出水面的名字应该不会超过100个。
李梓新:如果是一个没有发表经验的素人,首先还是会感受到《收获》好像是一个这个高不可攀的平台,可能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
吴越:名家也会写出败笔,新人也有可能一跃而上,文坛这种事情太多了。我们不可能长了一张势力眼,给作者分等级。但是从更多经验接触上来说,素人可能在早期写作的时候会遇到每个写作者都会遇到的问题。比如说过度依赖自己的经验,或者去书写一些Ta认为很特别但是已经被写过很多次类似母题的东西。所以,我比较希望Ta是一个很成熟的文学阅读者,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素人写作。Ta已经看过很多,大概知道好的小说长什么样?怎么分章节,每个章节解决什么问题。这说起来就很多了,我觉得这些可能就是通过阅读可以自学到的一些东西。
李梓新:那技术上的一个问题,你们是有一个专门收投稿的信箱吗?大家会不会担心投到这个信箱你们不会看呢?
吴越:我自己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啊。我们有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我们上海市静安区巨鹿路675号《收获》文学杂志,纸质的稿子寄到这个地址。如果你是辛辛苦苦打印出来的,希望被退稿字后我们能把稿子再寄回给你,要写好“退稿请寄回,同意到付",我就会给你顺丰到付回去,这个周期是三个月左右。我们有六个实习编辑,每天做这件事。寄来的稿子会专门有人登记,等看完了之后,如果编辑觉得你还有发展空间,还想跟你说几句,就会给你手写回复,我看小红书上很多人都晒了。还有一条腿,是我们的官网,在这个官网上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来投稿,具体的网址和投稿办法在《收获》的新浪微博的头条置顶。
李梓新:像索南才让这样的作者,他在青海,你是怎么连接或发掘到他的呢?
吴越:2018年的时候,我和同事去了一次鲁迅文学院,做了一个简单的宣讲,当时有人对我们提出了一些比较尖锐的质询,其中有一个人就问“你们发不发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我当时对这个问题感到有点生气,我说,不存在民族作家,你写的东西其实是我们共同都关心的。后来我才知道,索南才让就是这个提问的人。
当时他就跟我说,他说有一个作品叫《巡山队》,问我能不能去宿舍来带给我看。我告诉他我们马上就要走了,让他给我发邮件。我记得我是漫不经心打开了邮箱,但我好像看了三行字,就坐直了,因为他的语言非常特别。后来我就跟他说,这个还有点简单,我问他还有没有其他的在写的作品,他又给我发过几个。大概是在看到《荒原上》这个中篇小说第一稿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厚重的,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这个作家应该是能获得鲁迅文学奖的那种作家,但是我没想到这么快。仅仅是几年之后,2022年,他就已经获得了“鲁奖”。
我跟索南有一次开玩笑说,这个故事我们自己都觉得妙趣横生,不可思议,因为这是一个菜鸟编辑和一个菜鸟作者的故事。他在跟我联系的时候,还是一个牧民,到2021年之前,他都是一个真正的牧民,赶着几百头牛羊。但是我跟他交流的时候,丝毫不觉得隔阂,因为他曾经在北京打工,中断了之后,又回去做牧民。我觉得上天特别酬勤,像他这样的作者被大家看到了,也取得了很让人满意的结果,这对很多人来说都是有鼓励作用的。你写得好,就是会被大家看到,会有很多人来帮你。让写得好的人被更多人看见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使命。
在这个时代如何成为作家?
李梓新:最近,大家一直在谈“文学的衰落”,在这么功利的时代,还有谁在坚持在写字?像你说的,一篇作品都要打磨一年,甚至一年以上,谁还在写?
吴越:我没有觉得写作或文学在衰落,我觉得就没有衰落过,因为时代中的人总是需要嘴替的,作家就是嘴替。一开始,作家是替自己说话,当足够强大的时候,就要替这个群体说话,或者要写Ta所了解到的只有Ta能说出来的故事。这样的人永远是会存在的。
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全民写作的时代,人人都是诗人,潮水退去之后,剩下的就是一个基本盘。只是说,我们的读者会不会减少?上次跟成都的宁不远做活动,有一个读者问:“今后都AI写作,对你们人肉写作的人有什么影响?”。宁不远说:“你其实想问我,如果我没有读者了,我还写不写?毫无疑问,我还是会写。”
问题就迎刃而解,无论是文学读者多还是少,作家其实是为自己写作的人,他们不会因为读者减少而停下来。当然,读者也真的不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就减少,因为人随着自己的成熟,会对历史、哲学、社会等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而要得到答案,文学肯定是参与其中的,这跟一个个体成熟的时间有关。
李梓新:作为中文世界中影响力这么大的一本杂志的编辑,对你来说,这种生活状态,甚至生命状态,你的感受是怎样的?
吴越:首先,非常私人的一个角度是我通过做编辑认识了很多好友。编辑和互相有信任感的作者之间像是旧年代的笔友,我们用小说来交流思想状况。
第二点,这个工作很符合我的性格,我既在一个现当代史真正的发展现场,但我又不是一个冲锋陷阵的人,因为我没有想要做一个作家。我也自我评估,我不具有一流作家的才能,但是我可能又比一般人稍微再多一点的文学的触觉,可以帮助到作家。并不是说我比作家更聪明,我就像一个陪跑的,运动员在一个特别特别疲惫的阶段,需要有志愿者出现在旁边,陪你跑一段。我觉得我挺愿意做这个工作的,它给我的满足感,不需要什么奖状或者肯定,光是工作本身就已经能带给我很多肯定了。
第三,我总有一种感觉,文学一直在发生变化,就算是古代世界里的文学,也并不是我们想得那么静态,其实也在随着学术考据和解读,发生着很多变动。在我眼里,文学就是一个思想性的东西,是特别先锋的,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我们群体中最聪明的那些人带给我们的分享。这个事情需要继我们这个社会当中很聪明的、很愿意付出的人把它继续做好。
李梓新:我们六年前的一次对话,也显示出一些端倪,我和你还有郭爽,三个人都是记者出身,然后我们都离开了媒体。说到文学,你现在是文学编辑,郭爽已经是出名的小说家,我现在在学习写作。在中文世界里,很多新闻工作者都往文学的方向游动,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吴越:六年前,我承接的作者当中有挺大一部分就是前媒体人,现在这个趋势更加明显了。从作者队伍来说,我觉得前媒体人进入到虚构一定是加分项,肯定是会给小说的写作带来新的东西。另外一方面,我自己也有进行一些练习,深知虚构之难,但我也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要进行虚构。因为有很多超越于真实的东西要寄托在一个自洽的世界里面,你想表达的东西,想说的话,想要记住的人,想一再回顾的事,可能已经没有别的方式可以叙述了,可能就剩下小说。
我记得之前有一次活动,有人说让我聊一下故事和小说到底区别在哪里?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这个问题。后来,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好的小说,它的内核肯定会是一个好的故事;但一个好的故事为什么有时候不一定是一个好的小说?很多时候,我碰到作者跟我说,他写的基本上全是真的,某件事情,他觉得非常离奇,但是为什么写成小说,我们读起来就不觉得离奇呢?那就是因为,小说不是故事,小说是对故事进行叙述的过程。它太好玩了,会让很多人想要试试看能不能玩好。但是我觉得做一个阅读者其实是最幸福的,有的时候你读得很好,然后去写,写完以后就会觉得很沮丧,觉得自己完全没有办法写好。那我觉得也ok,很多作家大量的时间也是在沮丧的。
这个就在于你有没有这方面的天赋,以及你能不能坚持去做。这些事情累积到一起,决定了你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作家。那你事先也要想好,我大概能成为一个怎样的作家?如果成为怎样的作家你都能接受的话,那你就去做。

「新气集ThinkAge」是由写作平台“三明治”创始人李梓新主播的个人播客。探索写作、教育游牧和家庭话题。
节目编辑:备备
片头原创配乐:李其乐
欢迎在以下平台收听
小宇宙app
苹果podcast
Spotify
喜马拉雅
网易云音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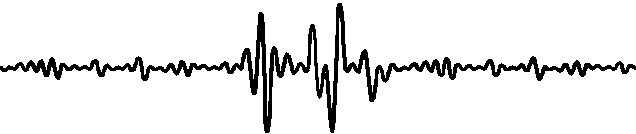
原标题:《吴越:一个文学编辑部里“静默的嘈杂”|新气集》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