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还原伍尔夫强健与探索的一面,她期待女性应独立坚定地面对社交
在大众视野里,弗吉尼亚·伍尔夫常常要么是一个脆弱女作家,要么是一个远离真实世界的唯美主义者。著有《T.S.艾略特传:不完美的一生》《夏洛蒂·勃朗特传》等作品的学者林德尔·戈登通过小说、日记和书信重构出这样一个伍尔夫:她是强健的步行爱好者、努力工作的职业作家,更是“不知疲倦的探索者”,探索“人类处境的千奇百怪”。林德尔·戈登想要呈现的并非常规的线性传记叙事,而是在真实性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详尽地追踪记忆和想象在伍尔夫一生中的持续流动。

[英] 林德尔·戈登 著|谢雅卿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近期,《弗吉尼亚·伍尔夫传:作家的一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在国际妇女节到来之际,通过阅读此书,回溯由伍尔夫曾实践的全新的重视无名者的历史观,今天带来的片段从她的友谊与社交观念谈起。
Virginia Woolf
在学徒生涯末期,弗吉尼亚·斯蒂芬(注:弗吉尼亚·斯蒂芬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婚前使用名字)把生活设计成了一场实验,她要在一个志趣相投的朋友圈里尽可能自由地生活。她慎重地选择生活环境、工作习惯、住所和伙伴,这也反映在她的创作方式中——落实于和谐、美好、顿悟的瞬间,决绝地忽略所有关于成功和幸福的陈旧安排,不论是传统婚姻还是被她称为“地下世界”的文学市场。《海浪》中的那位作家伯纳德告诉他的读者,他想要“把我的生命赠予你”。这是一个被创作出来的生命,就像他的五个个性鲜明的朋友一样,每个人的生命都由一个不起眼却反复出现的短句构成——“一个粘附在岩石上的帽贝”或“总是湿淋淋的泉水仙女”——它们赋予了每个独特的生命内在的连贯性。相比之下,常规传记中的固定套路,就像伯纳德所说的,只是“一种方便做法,一个谎言”,因为它没有看到藏在公共行动的舞台背后的断断续续的语句、隐隐约约的行为,而那些才是真实的人生所依附的东西。弗吉尼亚·斯蒂芬对传记的热情受到父亲的影响,但早在1909年她就写过讽刺传统传记的文章,因此,在独创性方面,她其实已经超越了父亲。

▲ 电影《时时刻刻》(2002)中的伍尔夫形象
她下定决心要成为作家,而对于她那一代的年轻女性来说,为了从事某种职业或投身一门艺术(她后来在她第一篇关于女性地位的檄文中解释过),她们不得不为自由冲锋陷阵。这不仅意味着与家族决裂,还要与社会普遍接受的女性形象和行为准则决裂。而这种决裂,她继续写道,是“极度痛苦的折磨,我认为,它超出了任何男人的想象”。
不论布鲁姆斯伯里对其他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对她而言,它代表着对海德公园门的一场反叛。她的各种回忆录、1903年的日记随笔和1904年至1905年的布鲁姆斯伯里日记,都有助于解释当时的处境为何让过去的家变得难以忍受,以及在两姐妹眼中,她们搬去布鲁姆斯伯里的举动使自己产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弗吉尼亚多次的评论清楚地表明,布鲁姆斯伯里的朋友们的重要性不在于他们的思想,而在于他们第一次为她营造的精神自由的氛围。后来,当她在想象中塑造朋友们的形象时,作为《海浪》的基本素材,他们将变得愈发重要,《海浪》这部小说探索了一个小圈子中的六位友人持续一生的关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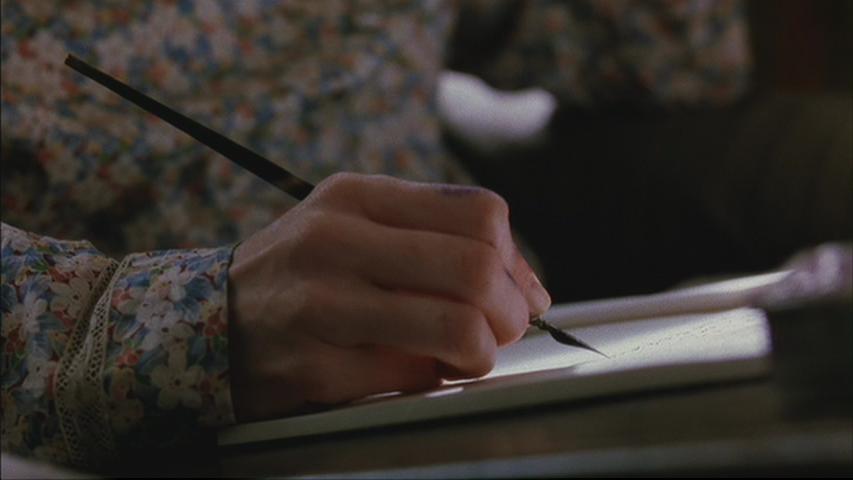
1904年10月标志着一段新生活的开始。二十二岁的弗吉尼亚·斯蒂芬再也不用隔着狭窄的街道,看着对面的老雷德格雷夫太太洗她的脖子了。她朝窗外望去,树木仿佛从戈登广场中心喷涌而出。更重要的是,她现在拥有了一间单独的工作室,那里有一张高高的书桌,每天早晨她都可以站在那里写作两个半小时。她声称,站着写作是为了和凡妮莎保持一致,因为凡妮莎常常抱怨要在画架前站好几个小时。不过,这个姿势或许很适合她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旺盛精力。午餐前,她喜欢“冲向”托登罕宫路,在旧家具店和牛津街的旧书店里闲逛。一切都改变了,在为“回忆录俱乐部”(Memoir Club)写的随笔《老布鲁姆斯伯里》(“Old Bloomsbury”)中,她写道:画画和写作是头等大事;他们在晚餐后喝咖啡,而不是在九点钟喝茶;他们扔掉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红色天鹅绒地毯和花样繁复的莫里斯墙纸,改用素色的涂料粉刷墙壁,用白色和绿色的印花布装饰她们房顶很高、干净清冷的房间。凡妮莎让祖姑母的印度披巾恢复生命,把它们铺在了桌椅上。映着雪白的墙壁,披巾的色彩呈现出原始的艳丽。沃茨给父母画的肖像画陈列于此,大厅里还挂着一整排卡梅伦太太给母亲拍的照片,对面是赫舍尔、洛厄尔、达尔文、丁尼生、勃朗宁和梅瑞狄思的照片。1907年,在凡妮莎结婚后,弗吉尼亚和阿德里安·斯蒂芬就搬去了菲茨罗伊广场,那里的建筑都有亚当风格的精美外观,有一种衰颓的典雅。在那里,很多十八世纪的房屋都被改建为出租房、办公室、疗养院和小工匠作坊。斯蒂芬姐弟是唯一拥有整栋房屋的居民,他们和厨师、女佣还有狗住在一起。

现在,两姐妹需要围绕工作来计划她们的一天,她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前只是出于一种结盟的需要——如今变成一块肥沃的土壤,无论对她们的艺术实验还是对新团体来说都是如此。她们给这个团体带来了家庭色彩——哥哥的朋友们从男性主导的剑桥大学出来,进入了由两位见解独到、意志坚定的女人主导的女性环境中。
弗吉尼亚似乎是追随者。当凡妮莎在1911年有了情人罗杰·弗莱时,弗吉尼亚也在格兰切斯特的河里与鲁伯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一起裸泳。那一年,弗吉尼亚在布伦斯维克广场(Brunswick Square)34号和几个单身男人(包括伦纳德·伍尔夫)住在一栋房子里。当乔治·达克沃斯反对这种不得体的行为时,凡妮莎代表妹妹冷静地反驳了他,她说育婴堂就在附近,非常方便。两姐妹穿着用印花棉布做成的非洲服装,把自己打扮成高更画里的样子,在1912年第二次后印象主义画展的庆功舞会上,她们绕着克罗斯比大厅飞奔。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放荡不羁的叛逆行为并没有完全吸引弗吉尼亚,她更关心的其实是精神自由而不是性自由。

▲ 弗吉尼亚·伍尔夫和伦纳德·伍尔夫
朱莉娅·斯蒂芬以她强大的人格魅力维持着女性的顺从。而她愚笨的替代者乔治却激起了两姐妹的反抗,因为他强迫她们进入婚姻市场。从乔治的角度来看,他只不过是在践行帕特尔家族的信条,即代代相传的女性美应该被售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弗吉尼亚记录了她的姨母弗吉尼亚·帕特尔如何让女儿受尽折磨,只为把她们嫁给贵族人士,与之相比,“中国女子的三寸金莲都不值一提”。弗吉尼亚还在书房学习的时候,就被姐姐穿着白色绸缎长裙的“壮观场面”吓呆了,她就像个未来的贵妇人,然而,在蓝色蝴蝶珐琅发饰的掩盖下,是她“对绘画和松节油的强烈渴望”。不久之后就轮到这位年轻的妹妹体验社交季了,她在羞怯的痛苦中被带上了铺着稻草的出租马车,去伦敦某座豪宅参加舞会,在那里,她不认识任何人,整晚也不跟别人说话,被人群挤到墙边。
邓肯·格兰特第一次见到弗吉尼亚是在她称之为“做希腊奴隶的那几年”,他说,当别人没有知会她就把她介绍给其他人时,她总会用极其不情愿的表情和几句精挑细选的套话来表达她的不满。有一次,乔治带她去和两位贵族遗孀吃饭,她滔滔不绝地谈论柏拉图,打断了她们的应酬。在她最滑稽的讽刺文之一《海德公园门22号》里,她回忆起这个糟糕的夜晚,两位贵妇人先是因她不合时宜地谈论柏拉图而大为恼火,后来又因为剧院里的法国演员放纵的哼叫声而勃然大怒。正当弗吉尼亚扮演着迷茫少女这一固定角色时,她无意中听到了乔治和卡那封伯爵夫人(前加拿大和爱尔兰副总督的夫人)在大理石柱后面偷偷接吻。

和凡妮莎一样,弗吉尼亚也在舞会上被忽视了,而且,她还断言自己一定也是个社交失败者,但她能较为超然地看待这件事。在日记“花园舞会”(“AGarden Dance”,1903年6月30日)里,她记录了一位健壮的女士如何面带微笑地欢迎她们,“她的微笑已经向另外五十个人展示过了,而且还将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中继续履行它的职责”。舞池很拥挤,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在房间中央跳华尔兹,他们看起来“就像在一盘粘稠的液体里挣扎的苍蝇”。她看着贵族小姐们从窗户里涌出来,仿佛一道由蕾丝花边和丝绸组成的瀑布,沿着花园的斜坡冲下去:她本可以把这个场景描绘成“一幅法国油画”,不过,等她回家后,却转而读起床头柜上的一本天文学著作来。既然她不论怎样都处在观察者的位置,她还是更喜欢从卧室窗户里隔着一段安全距离观看女王门的舞会,她敞开睡袍,散着额发,在她眼里,舞池就像“一个撒满谷粒的晒谷场,毛色亮丽的鸽子纷纷停落于此”。而当乐师们突然奏起华尔兹舞曲时,“房间仿佛立刻被大水淹没了。一瞬间的犹豫过后,第一对舞伴,紧接着另一对,跳进了河流中央,在漩涡里转个不停”。
……

▲ 瓦妮莎·贝尔为弗吉尼亚·伍尔夫画的没有面目的肖像
弗吉尼亚曾经表达过反抗,她不仅说出了她对社交失败和性骚扰的感受,还反抗了乔治强行扣在她们身上的女性“样板”。旺盛的生命力是多余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人看起来就像鸡蛋一样:圆润、光滑、毫无特点。贝雷斯福德(Beresford)在1903年为弗吉尼亚拍摄的照片广为流传,那上面她看起来毫无生气。而在拍摄于1901年的另一张照片上,弗吉尼亚身穿白色连衣裙,身旁主人似的乔治在盯着她看,她身材瘦弱、面无表情、身体僵硬。1903年夏天,在《关于社交成就的思考》这篇随笔里,弗吉尼亚·斯蒂芬为正常的女人下了一个定义。这个女人擅长的学问是一种社交技巧。她只在晚间生活:八点钟响起的晚餐钟声召唤出她的生命。她会说些什么呢?对弗吉尼亚而言,这是“终极的谜题”。这个人造生物躲避其他女人的目光:“如果我在旁边路过,她会一言不发,”她评论道,“她合拢花瓣,让它们紧紧包裹住自己。”1908年在佩鲁贾的时候,她曾观察过一位漂亮的英国姑娘,她的“商标”是她“始终如一”的单纯和好脾气。她想着维多利亚时代的母亲如何把这种性情传给自己的女儿,并为这样贫乏的自我观念感到悲哀:“老母亲并非天生就是吝啬鬼;人类是可以飞得很高的。”
弗吉尼亚·斯蒂芬的自由观既直接又实际:微薄的收入和一间自己的房间——解放思想所需要的金钱和隐私。E.M.福斯特笔下那位独立的女主人公玛格丽特·施莱格尔曾坦率地说,没有独立的收入就不可能有独立的思想。后来,弗吉尼亚声称,在维多利亚时代之前,女人根本没有独立身份,因为她们的收入被法律控制了,她们的隐私也被各类家庭需求侵吞了。
新媒体编辑:郑周明
配图:历史资料

原标题:《还原伍尔夫强健与探索的一面,她期待女性应独立坚定地面对社交|夜读·倾听》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