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不患无卤而柴难”:明清时期云南盐业社会如何保持生态平衡
一般认为,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会导致生态环境被剥削甚至破坏。不过,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的李陶红博士对这一断言有些犹豫。她在自己的新书《柴薪与盐:明清以来滇盐开发的生态人类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9月出版)中写道,“诸多关注自然资源开发与生态关系的研究均一味地关注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而忽略了人类为争取生存和发展、力图维护和谐生态环境所做出的努力,以致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考量过于平面化,缺少人的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多维互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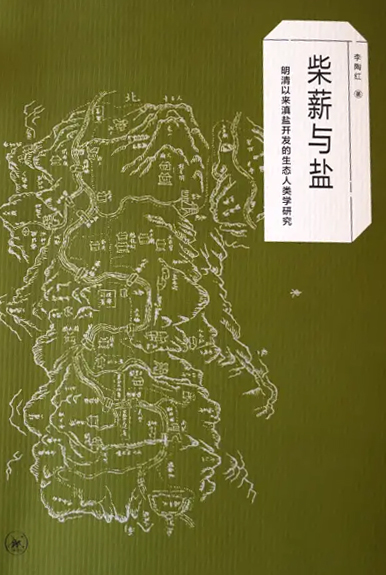
《柴薪与盐:明清以来滇盐开发的生态人类学研究》
李陶红对云南盐业社会的兴趣来自对故乡历史的好奇。她出生于云南楚雄州白盐井附近的一个村落——赤石岩,尽管家族已迁居他处,但她的父母仍常回去居住。据村里老人回忆,白盐井周边的村子历史上承担着制盐工序上的各种各样的工作,她家所在的村子主要是砍柴。因为熬制盐卤需要消耗大量柴薪。村民可以把柴或山区的其他物资背到盐井那边的集市上做交换。这是云南盐业社会“以卤代耕”的生计方式中的典型一环。
关于滇盐的研究,李陶红介绍说,尽管滇盐在某些时期可能进藏或流向东南亚,但总体而言,它的区域影响力相对有限。在边缘地区,这种局限性是合理的。与川盐或两淮盐相比,滇盐在学术共同体中的地位相对较弱,研究群体也相对较小。不过李陶红认为,滇盐的研究仍然具有丰富的潜力,尤其是在探讨云南地区社会中滇盐的意义时,仍有许多待发掘的问题。
目前李陶红专注于滇盐史的研究。她已出版三部关于云南盐业历史与文化的学术著作,分别是《咸的历程:明清以来云南石羊古镇城镇化研究》(2019),《以卤代耕:云南盐业社会的经济共生与文化交融》(2023年),以及《柴薪与盐:明清以来滇盐开发的生态人类学研究》(2023年)。澎湃新闻就云南盐业社会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的生态适应情况采访了李陶红。

现石羊古镇全貌。作者供图
澎湃新闻:从《咸的历程》到《柴薪与盐》,你一直关注着云南盐业社会的变迁。什么是盐业社会?为什么盐这种物资在云南这么重要?
李陶红:变迁是人类学的一个经典议题。我的变迁研究最初关注的是城镇化的过程(《咸的历程》),在这个议题的框架下,第二本书《以卤代耕》关注的是盐的经济共生形态和民族关系。《柴薪与盐》是我做滇盐研究的第三个专题,关注盐的生态议题,特别是柴薪和盐的生态关系。
“云南盐业社会”这个概念是基于我的研究,用我自己的语言来定义和分析云南的社会类型。我知道创造一个概念是很难的,也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但我还是想尝试一下。“云南盐业社会”是以卤水和柴薪为原料,以盐业生产运输交换为主要生计方式,形成了食盐交换和其他附属经济的经济形态。在这种云南盐业社会中,以盐为中心,形成了人群的聚集和分工的社会形态。同时,以盐为基础,也产生了盐业社会的文化形态。这是一个典型的社会类型,我用云南盐业社会这个概念来描述它,也是为了方便我的研究。当然,这个概念可能还有一些不足,也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进行补充和讨论。
云南盐业社会最基本的生计是“以卤代耕”,这让我们联想到农耕文明——费孝通先生说的乡土社会是以土地为根基的社会。而以卤代耕的盐业社会,是以卤水为原料、柴薪为生产资料的社会。在云南,比如我这本书关注的白盐井和黑盐井,盐的原料卤水都是从地下抽取的。卤水就是含有盐的水,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再用另一个重要的生产来源——柴薪——来加热、挥发等过程,制成我们使用的盐。
历史上有一句话,“滇之大,惟铜与盐”,意思是铜和盐是云南两种非常重要的物资。云南的地形主要是山区,所以它的田税收入很少,盐税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云南的地形主要是山区,平地或坝子只占不到10%。云南这样的地形地貌,决定了外盐很难进入,运输成本高。云南的盐主要供应云南区域。如果我们从盐的角度来看云南区域社会的历史,其中一个关键词就是国家化。滇盐的开发过程也是云南的国家化过程。因为盐是国家管控的战略物资,在这种边缘的产地,国家也最早介入了管理。这也影响了云南的政治文化的一体化。
澎湃新闻:关于中国盐业的研究汗牛充栋。在《柴薪与盐》这本书里面,你想回答的新问题是什么?
李陶红:我在做中国盐业社会的研究时发现,既有的研究多是从宏观历史的角度来表述的。特别是在盐业史的研究中,多强调制度和经济史的影响。在这样的历史叙述中,我们看不到人的存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近几年有一些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介入到盐业史的研究中来,我自己也在做一些创新和反思。
现在中国盐业社会的研究有一种转向,就是从宏观历史转向微观历史,从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转向社会史。盐业史的研究也受到了学科性的影响,它从盐政史的研究转向了盐业社会史的研究。
在这样的转向中,我也可以回应我为什么关注柴薪与盐这样的一个新问题,以及为什么我要关注生态的议题。因为在正统史学指导下的盐业史的研究中,这个问题可能是不被关注的。我们西南这边近几年一直在做环境史的研究,其实也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转换而产生的新的分支。
基于这种大的转向,既有的研究中多是以盐论盐的状态,而我的研究是通过柴薪来讨论盐的,这是一个视角的转换。就像我站在一个与盐相关的研究对象“柴薪”来看盐本身,就像我们从他者的视角,再回到本我的视角转换,应该是可以出一些新的东西的。根据这样的一个预设,我开始了一些相关的学习和文献的研读,就发现历史文献中有“不患无卤而柴难”的表述。从这样的一个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盐业社会中,生产资料卤水是不缺的,缺的是柴。
还有一些关于盐业生产过程中的柴薪消耗数据的表述。我看了相关的史料,比如我关注的白盐井,它的盐生产和柴薪消耗的比例是四斤柴薪可以生产一斤食盐。在清代康熙年间,白盐井的年产量是870万斤,平均每天产量是2.4万斤,根据这样的比例,它每天要消耗柴薪8万斤。通过具体的数据,我们可以感受到柴薪在原料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在“不患无卤而柴难”的情况下。
在具体的研究中,我想回应的新问题是:之前有一些关于盐业生产会带来环境破坏的相关表述,这在我的文献阅读和田野访谈中是一种非常低频的叙述方式,而我的研究可能会呈现盐业生产过程中的生态的复杂性。
在已有的一些研究中(比如一些盐业志的研究、楚雄州盐业志或大姚县盐业志等),都是比较简单地认为盐业开发必然导致环境破坏。但随着我阅读的文献越来越多,我发现盐业社会中既有对柴薪的需求,也有对柴薪的养护和照料,这体现了社会文化的能动性。
澎湃新闻:书里提到你在田野调查当中发现了与相关研究中不符合的情况。具体是哪些情况?
李陶红:我还在读民族学硕士时回到自己的老家做田野调查,发现我对自己的家乡其实一无所知。我记得小时候看着周围光秃秃的山,觉得我们这里的山怎么这么糟糕,还以为是因为产盐造成的。后来我去问了一些老人家,他们告诉我,这是因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炼钢铁和集体化时期砍伐了很多树。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和我原来的认识不一样,于是我就想继续深入研究这个问题,这个小小的问题引发了我后来的一系列思考。
我回到历史的现场,看了一些地方志和盐业志,发现了一些关于这里生态的生动描述,比如为了降低柴薪的成本,人们利用河流来运输柴薪。还有一些关于盐业制度的内容,比如清代的盐业志记载了一些自上而下的规定,省级的盐业部门还有白盐井和黑盐井的一些文件(比如封山育林碑等)里都有关于保护生态的法律法规和操作。我想这个时期的生态保护和理念是很值得探究的。
我认为产盐和生态保护这两者并不冲突。比如,盐业管理部门最重要的是要收盐税,要保证食盐的产量,而食盐的产量背后必须有柴薪的正常供给。所以他们也会为了柴薪的供给做很多努力。我们也可以看到官民之间其实有一种利益共同体,也是一种互动的状态。
澎湃新闻:你去田野的滇盐产区主要分布在云南哪里?盐井的自然环境是怎样的?
李陶红:云南的盐井可以分为三个区域:滇中、滇西和滇南。这三个区域的开发时间不同。滇中和滇西的开发比较早,有汉代以来的历史记录。滇南的开发比较晚,因为那里的盐是矿状的,需要“以矿制卤”,所以大规模开发是清代以后的事情。这是一个时间上的顺序。
我主要关注的是白盐井和黑盐井,这两个盐井都在滇中区域,现在的地理位置是楚雄州。历史上,白盐井是由盐课提举司直接管理的,也有属于盐业管辖的滇西范围。黑盐井现在叫黑井古镇,白盐井叫石羊古镇。这两个地方在1995年都被评为云南省首批历史文化名镇。这些产盐的地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在周围有山、中间有河这样的一种山水环绕的地形。我去过的白盐井、黑盐井、雒马井(现在的宝丰古镇)和诺邓,都是这样的地形。这些地方都是典型的山地盐井。黑盐井(现在的黑井古镇)在楚雄州的偏北部,交通不便。这让人很难想象,为什么这样的地方会有如此厚重的历史文化。

现黑井古镇全貌。作者供图
当盐的生产作为一种常规的、平衡的生计方式时,盐业的生产需要大量的柴薪消耗,就会带动周边更大范围的、以柴薪为生的群体。白盐井的周边有很多少数民族,比如彝族等,在这样的盐业社会里,通过提供柴薪和以卤代耕的方式促进了更大区域范围的物资交流和经济繁荣。在柴薪和盐比较平衡的时候,每个个体都可以在这样的生产过程中分到自己的一份收益。
当盐业生产的原材料供给出现了非常规的情况,就会带来生态的压力和反馈。如果这种压力在可控范围内,是适度的压力,我们也可以看到当地有一些比较超前的地方性的生态知识,还有当地的一些为了维护生态平衡的社会行为。
比如,从当地的山林保护来说,我在口述史的访谈中得知,当地人说他们以前煮盐时不会乱砍树,只会砍大树,留下小树让它们继续生长。整个山林也没有被破坏,不像现代是成片地砍伐。以前用人工的方式,他们会挑选合适的树,或者每隔五年才砍一次,还会修枝割叶。这些都是当地的一些习惯性的文化,非常难能可贵。
在当地人的文化信仰当中,也有一些对于山林保护的信念。我书里用了一个我喜欢的概念,叫做“有神社区”,意思是,你所在的空间里,如果你觉得你身边有神灵的存在,你就会对你的环境有一种敬畏之心,然后你就会按照你的道德和文化来处理你和环境的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再看盐业社会,也会发现,比如白盐井,它历史上有很多的宗教场所,有七寺八阁九座庵,还有儒释道和地方信仰,这些都是当地的宗教形式。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有神社区的构建中,就会有一个平衡的时期,对山林有比较有序的保护。
澎湃新闻:以柴薪为中心来研究,你看到了哪些从传统角度没有看到的一些互动?
李陶红:一个是人对山林的依附。盐业生产需要大量的柴薪,这就促进了更大区域的人群的互助。除了柴薪,还有其他的盐业生产资料,比如挑盐卤的竹箩、木桶、皮具等,这些都要从山林中获取。所以人对山林就形成了一种必然的依附关系。我们有句话叫“靠山吃山”,就是说人知道自己对山林的依赖,也会产生对山林的敬畏、“有神社区”的观念、适度开发的原则等等。在保护山林方面,就有有序的砍伐、植树造林、选择速生林的树种、封山育林等法律法规的制定等等。
还有一个方面是山林的所有权,比如民国时期的公有山和私有山的并存。以白盐井为例,白盐井的灶户(指煮盐的人),他们既要有卤权,也要有自己的山,保证自己的盐业生产资料。平时他们可以通过购买的方式获取柴薪,柴薪价高或供应不足时,他们可以砍自己私山的柴薪。白盐井还有一个类似行业协会的机构,管理着不同层次的公山,比如小片区的公山,大片区的公山,开发也有层次性。他们的山林所有权很复杂,但现在都归公有了,由国家保护。
山林的所有权可能还涉及土地的问题,比如农村的土地承包,每个农户都有自己的承包地和固定的山林,自己经营开发。所以你看,虽然我关注的是柴薪的问题,但是背后有很多复杂的利益关系,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结构。
澎湃新闻:跟柴薪直接相关的盐井生态问题有哪些?当时人们是如何应对和适应这些生态灾害的?
李陶红:我们现在去农村看到的炊烟,和白盐井、黑盐井的历史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因为那里不仅有民众的炊烟,还有灶户的炊烟,他们不停地生产食盐,整个盐井都被浓烟笼罩,当地的文献也有记载这个情况。白盐井和黑盐井因为产盐的缘故,柴火从早到晚都在燃烧,不会停下来。这样就导致了当地的气温比周围的要高。
还有火灾的问题。因为盐业生产需要持续的消耗柴薪,所以要有大量的柴薪作为储备。这样一来,就有了火灾的隐患。盐井每天都在煮盐,火也一直在燃烧,也有火灾的风险。
应对灾害我分两个部分来谈。第一个部分是火灾的问题。清代地图上的白盐井,河流是弯弯曲曲的,但现在白盐井的河流被打直了,因为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维护。当地老人告诉我,历史上这条河流叫香河,是九曲十八弯的,这样的状态有很重要的防火功能。因为河流弯曲,水流的面积和空间就比较富足,如果哪里发生火灾,就可以及时取水灭火,这是有生态的考量的。后来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为了增加人的居住面积,就对河流进行了一些处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和过去的风貌不一样了。
为了防火,人们会把大量的柴薪堆放在河边,这样就不容易着火。他们还会定期疏通河道,清理淤堵。还有当地有风水的说法,说盐井地是火旺的地方,所以他们自然会有一套防火的意识和信仰文化。在白盐井,你可以看到有火神庙。
第二个部分是水灾和泥石流的问题。白盐井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有过一次很大的洪水,大概90%的建筑都被冲走了。在盐业志里,白盐井和黑盐井历史上经常发生水灾。这些盐井都是在山旁边有河的地方,有时候发洪水。同时,砍伐柴薪和挖井硐取卤水都会造成水灾和泥石流的隐患。
我们现在如果去黑井古镇旅游,可以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遗迹,叫庆安堤,是一个防洪堤。当地人说这个是黑井“小长城”,说明他们在防范水灾和泥石流方面有人的技术能动性。还有一些措施,比如植树造林、填埋盐井。比如有泥石流的地方,少挖井硐;如果井硐的卤水太淡,食盐的产量低,就会关闭井硐。
澎湃新闻:尽管从官方到民间都想了很多办法,但从历史的进程来看,柴薪还是越来越贵,原因是什么?盐政当局和从业者怎么解决柴薪越来越贵的问题?
李陶红:这跟滇盐的特点有关,就是“苦于柴,苦于运,苦于税”。这三者都跟柴薪的价格有直接关系。苦于柴,是因为盐业的生产不是自由的,而是由盐业部门核定的,有一个固定的任务量。这样的话,食盐的生产就缺乏地方的逻辑,只能按照上级的要求去完成。
当食盐的产量被核定激增的时候,柴薪的供给圈就会越来越外扩,运输的成本就会增加,柴薪的价格就会上涨。
还有一个原因是云南的盐税比川盐和江淮一带的食盐要重得多。我看了一些相关文献,云南的盐税有时候会比川盐、淮盐等高出两三倍,甚至十几倍。盐税里面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薪本,最重要的就是砍伐和运输柴薪的成本。柴薪有一段时期可能占了整个成本的50%。
第三个原因是滇盐很难找到替代的燃料。不像川盐,它历史上可以用煤或者天然气来代替。
盐税重、薪本重,制盐成本高,当地的盐井负担不起,就会想办法应对。比如说,他们会借薪本。先借来用,然后慢慢还。或者他们会关闭生产不良的盐井,在下一轮食盐核定的时候试图减少任务量。或者他们会周旋于上层盐业管理部门,争取一些利益。还有一种情况是当地的食盐供不上,外地的盐商要进来,盐政当局就会让外地盐商先帮他们运柴,运到足够的柴,然后再让他们运盐——利用别人的运力。
他们也会从技术的层面做一些改良,比如说在晚期引进晒盐篷,比如黑盐井、白盐井,就会有晒盐篷,就是用动力的方式晾晒卤水,增加浓度,减少柴薪的消耗。在云南这边,其实可以晾晒的季节不多,晒盐的条件不优越,不划算。只有云南的澜沧江沿岸,因为是干热河谷,晒盐的效果比较好,在云南其他很多地方,晒盐只是一个补充。

石羊古镇晒盐篷。作者供图
澎湃新闻:民国时期张冲在灶户们的反对声中推行盐业改革,“移卤就煤”“合井并灶”,旨在解决燃料供给问题。上世纪50年代云南盐业开始公私合营,70年代改用真空制盐代替平板锅制盐。这些转变对当地生计和社会带来了什么变化?
李陶红:张冲的盐业改革是云南盐业改革的一个创举。他的具体做法是把元永井的卤水通过管道运到20公里外的一平浪煤矿,用煤代替柴薪熬盐。这是云南盐业转型的一个典型和表率。但是他的改革没有在别的地方推广开来,我认为是因为他的改革不可复制。
他的改革是一种社会改革,会产生很大的变动。灶户的卤水是世代传承的,有卤份才有开采权,卤水也是一种资本,可以买卖。张冲的移卤就煤是把原来分散的卤权重组了,把卤水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去产业化。这个变动非常大,是靠行政力量推动的。我们的历史文献和现在的评价都对张冲的“移卤就煤”给予了正面和一致的好评,因为他确实为云南盐业的转型做出了很多努力。
我们也可以把张冲的盐业改革放到当时的时代背景里看,他是在推动一种工业化的盐业生产,以取代传统的盐业生产方式。工业化意味着高效,“移卤就煤”就是用煤替换柴薪。煤的燃烧效率高,比如说用柴薪熬盐,可能要四份柴薪熬一份食盐,用煤可能不到两份煤就可以熬一份食盐。
随着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张冲改革和五十年代的公私合营,传统的盐业社会的生计方式就衰落了,一些社会角色也不在了。比如说由私转公的过程中,灶户群体就消失了。在历史文献里,这个群体是非常重要的,灶户也代表了一种地方精英、地方士绅或是沟通者的角色。在当时盐业社会里有很多的社会组织,灶户是社会组织里的一种重要力量,比如说有施水会,就是为沿途的拉柴火或贩盐的人提供饮用水。还有施棺会、掩骨会,就是给一些穷苦人家提供棺材的。灶户在社会的正常运转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盐业社会里的重要的利益方就是家族。白盐井就有四大家族甘、罗、布、张,以灶户为代表的家族所施行的地方教育、文化、经济等方面都是起到了主导者的作用。比如说有家族的学堂等教育形式。
简而言之,张冲的改革彻底转变了盐业的面貌,将其从几乎涵盖每个人的生计方式、社会和文化形态,转变为一个专业化产业。这一变化是深刻而剧烈的。在传统社会,凭借盐业维生的模式下,不同群体都能从盐业社会中获得收入。地方的口述史中提到,只要愿意努力工作,每个人都能通过盐业过上温饱生活,即使是从事小规模的贸易,哪怕售卖生活用水,也能赚取收入。然而,随着盐业的专业化转型,仅有一部分人继续从事该行业。例如,白盐井和黑盐井地区发展起旅游业,原有的盐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社会结构和经济形态因此而重塑。一些人转而投入到旅游业中。根据我的研究,例如诺邓、宝丰以及磨黑等多个盐井地区,都已经开始开展旅游业。正如我在第一本书中探讨的,盐业的历史可以概括为“因盐而兴,因盐而衰,又因盐而复兴”。旅游时代的到来,这一转型对当地社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重塑和变革。尽管是否每个人都能依靠旅游业谋生还是一个疑问,但至少部分人群已经开始参与其中。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得到了保障,为地区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
澎湃新闻:白盐井的关停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李陶红:那是上世纪90年代或者2000年左右的事。我那时候还是小学生,我们学校就在当时的石羊盐厂旁边。盐厂时不时地在生产,有很大的烟囱,像工业时代的标志。上课的时候,我看到我们户外的桌子上落的都是烟灰,印象很深刻。
澎湃新闻:既然当地有多种保护山林生态的手段,为何最终还是没能阻止柴薪危机的出现?
李陶红:保护山林不能阻止柴薪危机,需要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盐业生态的平衡最后被打破的原因之一是柴薪危机,但是它不是盐业衰落的根本原因。我们看到张冲的盐业改革和五十年代的公私合营,其实背后有一个盐业的大背景的转变,就是向工业化转型,提高效率,降低能耗。所以我们还要考虑盐业衰落背后的时代背景。
澎湃新闻:在你看来,我们现在能不能说,盐矿开采是当地大量消耗森林资源的重要原因?
李陶红:随着对相关研究的深入分析,我逐渐意识到,我们的判断并不能一概而论。在评估某一判断的准确性时,我们必须考虑到不同的时期:是在一个稳定平衡的时期,还是在非常规的时期。依据我所研究的历史文献,稳定时期主要指的是清代,明代的文献相对较少。清代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前期至中期,到了晚清以及民国时期,生态环境的紧张程度日益加剧,这一趋势逐渐显著。
总的来说,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综合考虑。例如,食盐的生产量、柴薪的可再生速度、农作物的人工培植,以及时代变迁等方面。特别是时代的变化带来的社会不稳定、人口迁移增加了对食盐的大量需求等问题都应被重视。若在一个常态的平衡状态中,既有资源的开发利用,又重视生态保护,形成一种精巧的平衡,我认为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不存在过多问题。然而,如果是以运动式的开发为主,那么就会破坏原有的社会基础设施,这无疑是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