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理查德·沃特默谈启蒙运动的终结

理查德·沃特默(章静绘)
理查德·沃特默(Richard Whatmore)是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现代史讲席(Chair of Modern History)教授、圣安德鲁斯大学思想史研究所主任、国际著名期刊《欧洲思想史》(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主编,曾任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思想史研究所主任。他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十七世纪末以来的欧洲政治思想和国际关系。他的新书《启蒙运动的结束:帝国、商业和危机》(The End of Enlightenment: Empire, Commerce, Crisis)于2023年12月由企鹅出版社出版,该书被认为是将“启蒙运动”这一历史概念“从循环论证(circular debates)中拯救出来”,回到相应的历史语境中分析的杰出作品。近期,《上海书评》专访了理查德·沃特默。
“启蒙运动”这一历史概念非常复杂,不同学派对它的理解很不同,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理查德·沃特默:我不确定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总结当代学术界或者一般争论中有关启蒙运动内涵的辩论。我最关心的是那种将启蒙运动与民主人权和包容相联系的倾向,即好像存在着一种让所有国家都可以发展出这些价值的简单路线。在《启蒙运动的结束》中,我要表达的一个观点是,如果我们把启蒙运动视为任何意图终结宗教战争的“策略”(strategy)的话,那么阻止内乱与建立信仰包容的路线有很多种,就会有很多种启蒙运动。比如对人口的控制,或者我们所谓的“独裁制度”(autocracy),如果它是意图阻止暴力发生的话,也可被视作一种启蒙的策略——这也是我对历史学者习惯于称为“开明专制”的定义。在《启蒙运动的结束》中,我最感兴趣的是那些所谓的“自由国家”(free states)和启蒙运动的关系,因为正是在这些国家,特别是英国和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当时的人相信启蒙运动已经结束了。所以,我的目标是以十八世纪人对这个术语的理解重新定义启蒙运动,也就是通过“历史化”(historicizing)的取径。
《启蒙运动的终结:帝国、商业和危机》这个书名直接反映了您关注的一个重要论点:十七世纪末欧洲兴起的商业帝国(以英国、法国为代表)导致了启蒙运动的失败。能具体说说吗?
理查德·沃特默:《启蒙运动的结束》一书从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写起,因为他相信启蒙运动在现实中存在过。他曾很开心地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由宗教激发的意识形态冲突已经过去的时代。后来他逐渐认为,宗教争端的起源——他称之为“迷信和狂热”(superstition and fanaticism)——在世俗的伪装下再次爆发。休谟将这归咎于商业帝国,但是他的观点需要被精确地解释。当然,历史上有过很多商业帝国。它们大多数兴起后又衰败了,古代的例子是迦太基,近代的例子是荷兰共和国。休谟对这些商业帝国没有特别的兴趣,因为他认为在十七世纪末世界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用他的话说,“商业成为国家的一个理性”(commerce became a reason of state;“国家理性”的翻译参考周保巍:《国家理由,还是国家理性——思想史脉络中的“reason of state”》,《学海》,2010年第5期——采访者注)。休谟认为,因为军事技术已经非常昂贵,陆军和海军规模如此庞大,为了保卫国家,所有的国家都必须从贸易中获取收入,用以支付潜在战争的费用。因此最终所有国家都在思考扩大商业的办法,这导致帝国化,因为领土更大,势力更强的国家想要控制小国的市场和财富,而过去大国与小国可以和平相处。商业兴起为“国家理性”对十八世纪两个贸易强国——英国与法国有特别的意义,这让两个国家陷入彼此冲突的困境。到了晚年,休谟相信,因为商业帝国的兴起,“迷信和狂热”已经从神学性的冲突转化为世俗性的冲突。凭借公共信贷(public credit),英法沉溺于战争与扩张。这两个国家通过向民众传播仇外形式的爱国主义维持自身。休谟还担心由他的朋友亚当·斯密定义的“重商主义”(mercantile system)在英国已经被创造出来了,腐败政客被商人和银行家贿赂,从而制定出符合商人和银行家利益而非民众利益的法律。这些情况让当时人认为启蒙运动结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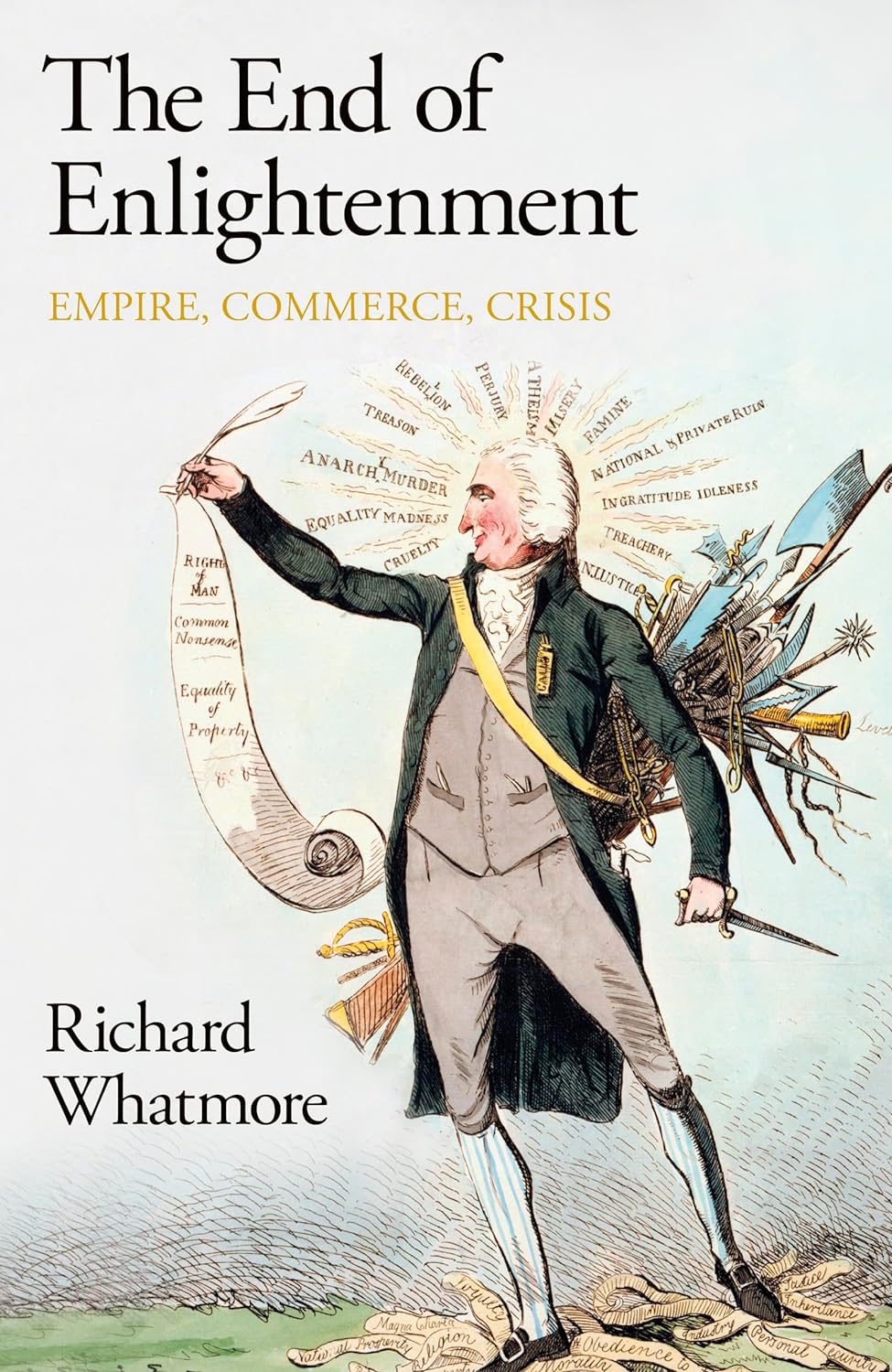
启蒙思想与帝国、商业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大国或者说帝国与启蒙运动能否结合?
理查德·沃特默:我们都需要记住,十八世纪发生的世界巨变,至今仍伴随着我们——究其原因,部分是缘于商业帝国的兴起。小国逐渐消失或者难以维持,被大国特别是商业帝国兼并。一些评论者会说,在十八世纪初,仅在欧洲就存在过几百个小国。到拿破仑战争结束的时候,国家的数量已经远不如前了。世界已经是大国的世界了,只有大国可以繁荣和存续。小国不是变成濒危物种就是已经消失了。这种情况在欧洲的自由国家,即自称共和国的国家特别明显。日内瓦、热那亚、威尼斯、荷兰共和国、瑞士邦联都是共和国,没有一个在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后还存在的。十八世纪成了帝国的时代。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你生活在大国的世界并且相信启蒙运动,那么找到一个让大国世界和启蒙运动结合的方法是必须的。我在《启蒙运动的结束》中提出的观点是,对大多数当时人来说将商业帝国与启蒙运动结合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商业帝国倾向于鼓励战争、公共暴力、仇外情绪等邪恶的事情。很多当时人一度以为自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在抑郁中离世。我不认为他们中有人认为帝国是一个建立或者维持启蒙运动的可靠办法,帝国只是他们生活在大国世界中的一个现实。在追逐市场的过程中,大国变得越来越大。如果和平与包容是值得捍卫的价值,这些就是为了实现启蒙运动必须应对的“真实情形”(straightforwardly the circumstances)。
长期以来启蒙运动被视为是理性克服迷信的进步时期,催生出了诸如自然权利学说、立宪政府等深刻影响全球现代历史的观念和制度。然而,在您的论述中,在十八世纪中后期,甚至在七年战争(1763年)结束之际,一些思想家认为他们的启蒙事业失败了。请问,为什么至今许多学者都没有注意到启蒙运动和国际和平的关系?似乎在启蒙运动的历史语境中,和平问题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议题?
理查德·沃特默:我不同意将十八世纪的“理性”(reason)这个术语作为建立包容与和平的进步性改革的同义词。虽然伊曼努尔·康德等人论证过追求和平的计划是“理性的”(rational),但是康德等人的行动是十八世纪末的故事。在十八世纪末之前,如果你将启蒙运动定义为任何可以阻止“迷信和狂热”爆发的策略,那么它不一定与立宪政府或者自然权利有联系。《启蒙运动的结束》的一个观点是,自由国家和启蒙运动的关系是复杂的。对当时人来说,共和主义很像是在再造激进新教主义的历史,因为两者都有生活在一种“同质性”(homogeneous)的文化之中,并且都以自由之名发起斗争。而激进新教主义的历史,在当时人看来是一段引起分裂和冲突的历史,将原本统一的教会分裂成彼此对立的两种阵营,并且在进一步分裂之前经历更多的暴力。法国革命时期,很多观察者相信法国朝新教的方向发展,这不是说法国的天主教徒改宗新教了,而是一种比喻,指法国将重现十七世纪新教徒先是建立一个教会然后内部分裂成不同教会的经历。法国共和主义有出现类似发展轨迹的迹象。这是自由国家和启蒙运动之间复杂关系的一个例子,可以提炼出的观点是对自由的欲望让人变得狂热。这也是大卫·休谟在1776年去世前的观点。
您的研究路径与以昆丁·斯金纳、约翰·波考克为代表的剑桥学派的思想史研究有什么异同?
理查德·沃特默:我想要成为一名思想史学者的想法最初是1980年代在剑桥大学听了昆丁·斯金纳的讲座后产生的。自那以后,我受到约翰·波考克作品的影响特别大,我第一次读他的《马基雅维利时刻》也是在1980年代。所以,我大概会这样形容我自己,一名剑桥思想史学派的“忠实成员”(a fully paid up member)——这也是恰当的形容。但是像所有的教会一样,剑桥学派的内涵很广,包含了关于思想如何变化以及如何与政治联系,这里有不同的、并且是经常有冲突的研究路径和假设。我在《什么是思想史》和《政治思想史简论》里专门写过剑桥学派不同分支的关系,特别是比较了斯金纳、波考克和伊斯特凡·洪特(Istvan Hont)的观点及影响。《启蒙运动的结束》受到了这些“大家”(luminaries)以及很多其他学者的影响。我最感兴趣的是“行动中的思想”(ideas in action)以及历史人物如何回应他们谋求改变或者改革的计划失败时的挫败感。像波考克,我对“支撑”政治行动的文化特别有兴趣;像洪特,我也感兴趣商业社会对传统文化时常造成的扰乱性影响。总的来说,我最感兴趣的还是“行动中的思想”。

约翰·波考克
《启蒙运动的终结》是否与斯金纳、波考克建立起来的古典共和主义传统有对话?如果有,启蒙运动的终结是否是古典共和主义在十八世纪衰退的一个结果?
理查德·沃特默: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当然,斯金纳和波考克没有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古典共和主义”(classical republicanism)或“公民人文主义”(civic humanism)在十八世纪末发生的变化。我之前认为因为法国大革命,这一传统消亡于欧洲——朱迪丝·施克莱(Judith Shklar)在1990年代初对我说过这个观点。现在我认为虽然共和主义到处碰壁,但在美国的特殊环境中得以繁荣,在欧洲则以一种支持建立帝国的意识形态存续,因为共和主义可以是非常仇外并且煽动狂热爱国情绪的。《启蒙运动的结束》认为这种共和主义的“变质”是共和主义者获得的教训,书里提到凯瑟琳·麦考莱(Catharine Macaulay,辉格党共和主义历史学家——采访者注)的例子,她在1760年代尊崇老皮特(William Pitt the Elder)扩张英帝国的战争。1760年代之后,古典共和主义者变成自由国家观念的“热情捍卫者”(patriotic defenders),特别在美国和法国。《启蒙运动的结束》部分讨论了这段故事,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共和主义意识形态危机。
《启蒙运动的终结》与您之前研究的关系是什么?您之前研究了法国、英国、日内瓦和爱尔兰的一些共和主义者,重农学派和帝国主义者,您也写过诸如休谟、卢梭等大思想家的论文,请问您之前的研究是如何帮助《启蒙运动的终结》的写作?如果对新书有一个定位的话,《启蒙运动的终结》主要考察的是大思想家还是怀有政治思想或理想的、名气没有那么大的人物呢?启蒙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是哪些人?
理查德·沃特默:在某种意义上《启蒙运动的结束》是我过去三十年研究十八世纪历史的累积,也是我第一次专注于研究英国而非法国或者日内瓦的历史人物,虽然书里有一章讨论的是雅克·皮埃尔·布里索(Jacques-Pierre Brissot)。在写书过程中,我与波考克讨论,他说《启蒙运动的结束》比《恐怖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最后一章对共和主义的解释“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这样说。《启蒙运动的结束》的主题范围广得多,对现有的历史学解释也提出了更多的质疑。但是我认为在观点上延续了我自己之前关于个别共和国与小国(如日内瓦)的研究,《反对战争和帝国》就是一个例子。《启蒙运动的结束》有专章讨论爱德华·吉本、谢尔本伯爵(1784年起成为兰斯当侯爵——采访者注)、埃德蒙·伯克、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托马斯·潘恩以及上面提到过的人物。但是其他重要的人物,例如卢梭、杜尔哥(Turgot)、伏尔泰、康德、普莱斯利、约翰·亚当斯或者奥拉达·艾奎亚诺(Olaudah Equiano,十八世纪著名的非洲裔英国作家——采访者注)也有足够的证据被包括进《启蒙运动的结束》的主题讨论里。《启蒙运动的结束》讨论了一些十八世纪最知名和最重要的人物,但是人物选择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任意的,因为“迷信和狂热”引发的问题再次爆发(1789年法国大革命引发的国际冲突——采访者注)并且影响了所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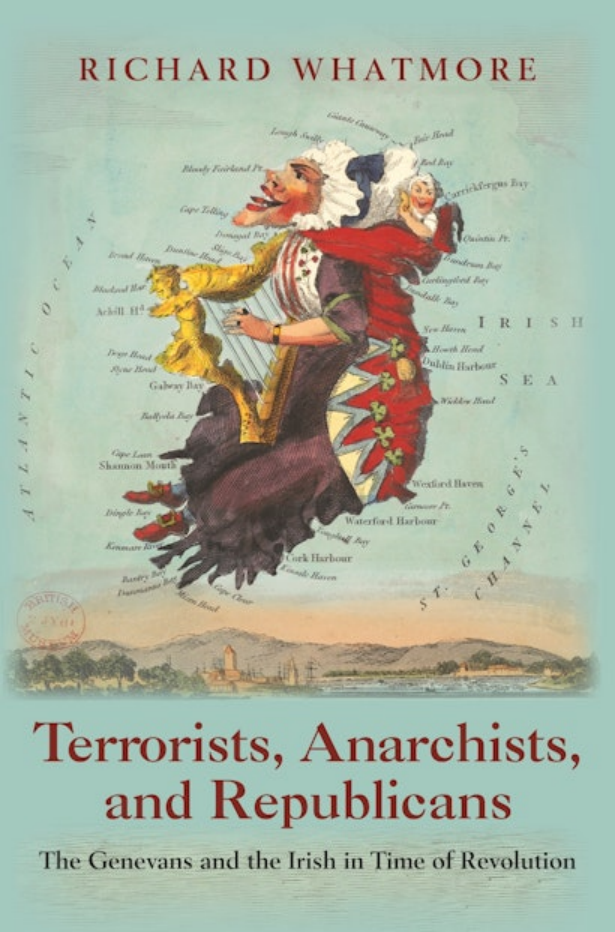
《恐怖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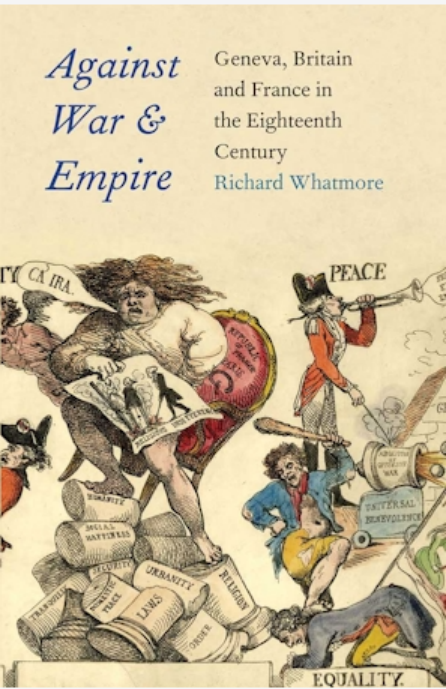
《反对战争和帝国》
《启蒙运动的终结》有明确的国别地域范围吗?或者说,在您看来,存在独立的苏格兰启蒙运动、英格兰启蒙运动、法国启蒙运动么?是不是启蒙运动自始至终都是一种跨国运动?
理查德·沃特默:如果你将启蒙运动定义为任何可以阻止宗教战争爆发的策略,那么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启蒙运动。这种逻辑的成立意味着从国家策略角度定义启蒙运动是不对的,也不存在某种特别的苏格兰启蒙运动或者法国启蒙运动。而且像“跨国的”(transnational)这样的词汇只有在下述两个条件同时成立时才有讨论的意义:“跨国的”事物有着国际性的影响力,并且处理的是连接内政与外交策略的问题。在十八世纪极少数人相信“永久和平计划”能够实现。随着时间过去,更多人确信在一个商业帝国和公共信用的世界里,一定要发展出能够实现和平与包容的新策略。世界已经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没有回到商业时代之前的可能,突然间“前商业时代”(a pre-commercial age)被重新定义为一个乌托邦。
启蒙运动在十八世纪仅仅是一场欧洲范围内的运动吗?抑或是大西洋两岸受到欧洲文明影响的运动?主张把大西洋内部及其周边的岛屿、国家和区域等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的路径对您的启蒙运动研究有影响吗?
理查德·沃特默:在我的定义里,不管在哪,只要你发现“迷信与狂热”就需要发展出一个建立和维持启蒙运动的策略。所以,启蒙运动过去是,现在依旧是一个非常全球性的现象。在任何地方建立启蒙运动,意味着你必须清楚自己所处的区域国家和国际语境,否则启蒙运动就会失败。但是启蒙运动的策略,我称之为应对“行动中的思想”,是关系到特定时间和地方的,这意味着“过度的概括是危险的”。因为《启蒙运动的结束》讨论的是个别历史人物提出过的策略,我比较少受到强调欧洲文明作为一个阐释类型或者大西洋世界作为一个阐释类型的影响。我的主题和“作者意图”引导我走向其他地方。
启蒙运动与欧洲文明是什么关系?
理查德·沃特默:我想要明确的是,由宗教带来的“迷信与狂热”问题转变为世俗化的形式从来都不只是一个欧洲现象。只是,因为商业帝国的兴起,在欧洲这一现象特别明显。但是启蒙运动的结束绝不意味着故事的结束,因为人们总是想要重建包容与和平,特别是正经历危机的人。因此启蒙运动的战斗没有结束。十九世纪的某些时段可能经历过启蒙运动的恢复,但是二十世纪的灾难让人们再次失去启蒙运动。可以进一步说,十八世纪末的世界和今天的世界“是可以直接比较的”(is a direct parallel),特别是在对政治意识形态失去信仰并且感到所有改革策略已经失败或者正在失败的意义上。
生活在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欧洲人认为他们所处的大陆对战争上瘾了。启蒙运动很难实现,因为在所有欧洲国家中“市民性质的与宗教性质的动乱”(civil and religious turbulence)似乎变成了一种常态。因此,他们很自然地将目光投向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更加和平的区域——包容与和平是这些地方的常态而非例外。十八世纪启蒙策略家着迷于中国,尤其是重农学派(the physiocratic)对中国的浓厚兴趣就是一例。事实上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危机时期,你会想看看别的地方,这种观察可能会激发能够建立和平与包容的策略。所以,认为启蒙运动的时代是欧洲中心的说法,是不对的。正相反,启蒙思想家认为欧洲的改革更难,因为在这里市民性质和宗教性质的暴力,其历史更久,得向世界上更加和平的地方去讨教、学习。
您书名中的“商业”一词是否指的是资本主义?在您看来,十八世纪的启蒙人物是否预见了商业帝国主义对和平的破坏?有没有人在预见这种破坏后继续思考用制度化的方法(立法)抵制商业帝国主义,并在您看来是值得今天国际秩序的决策者学习的?
理查德·沃特默:十八世纪有很多类型的商业社会,相对于“资本主义”我偏好“商业”这个术语,资本主义一词的内涵太宽泛了和模糊了。很多十八世纪的人,例如谢尔本伯爵和他的朋友理查德·普莱斯,相信商业帝国将引发全球战争。《启蒙运动的结束》解释了他们反对殖民和阻止帝国兴起的努力。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们充分意识到了问题,即贪求战争、利润和贸易的后果。对今天学习这些问题的人来说,我的建议是学习思想史,特别是“行动中的思想”失败的时刻。我认为重建启蒙运动的努力总是重复性的失败,而我们可以从十八世纪末的政治经济思想中学到很多。认为思想发展有文化属性的假设是错误的。我们的先辈有很多可以教给我们的。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