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重读国木田独步:明治知识人的内心苦斗
【编者按】
日本近代诗人、小说家国木田独步在不到四十年的生命中创作了几十篇短篇小说和大量诗歌。日本现代文学史对国木田独步文学的研究汗牛充栋,一般认为大自然与庶民是其作品的两大主题,他早期作品以自然观察、寄情自然的浪漫主义风格为主,后期开始关心庶民生活。不过,在过去近百年的研究史上,围绕国木田独步文学的争论就从未停止过。
《帝国风景的历史性与内在性:国木田独步文学研究》(刘凯著,四川大学出版社2020年9月版)将国木田独步放置在日本文学、中国文学和英美文学的多重关联中,并从媒体、话语、地理、翻译等跨学科角度,对其进行了重新解读。该书于2023年12月荣获第十届“孙平化日本学学术奖”三等奖,将于近期再版。澎湃新闻节选《帝国风景的历史性与内在性:国木田独步文学研究》(刘凯著,四川大学出版社2020年9月版)的绪论和第四章,以飨读者。文章略有删节,注释从略。标题为编者所加,本文经作者审定。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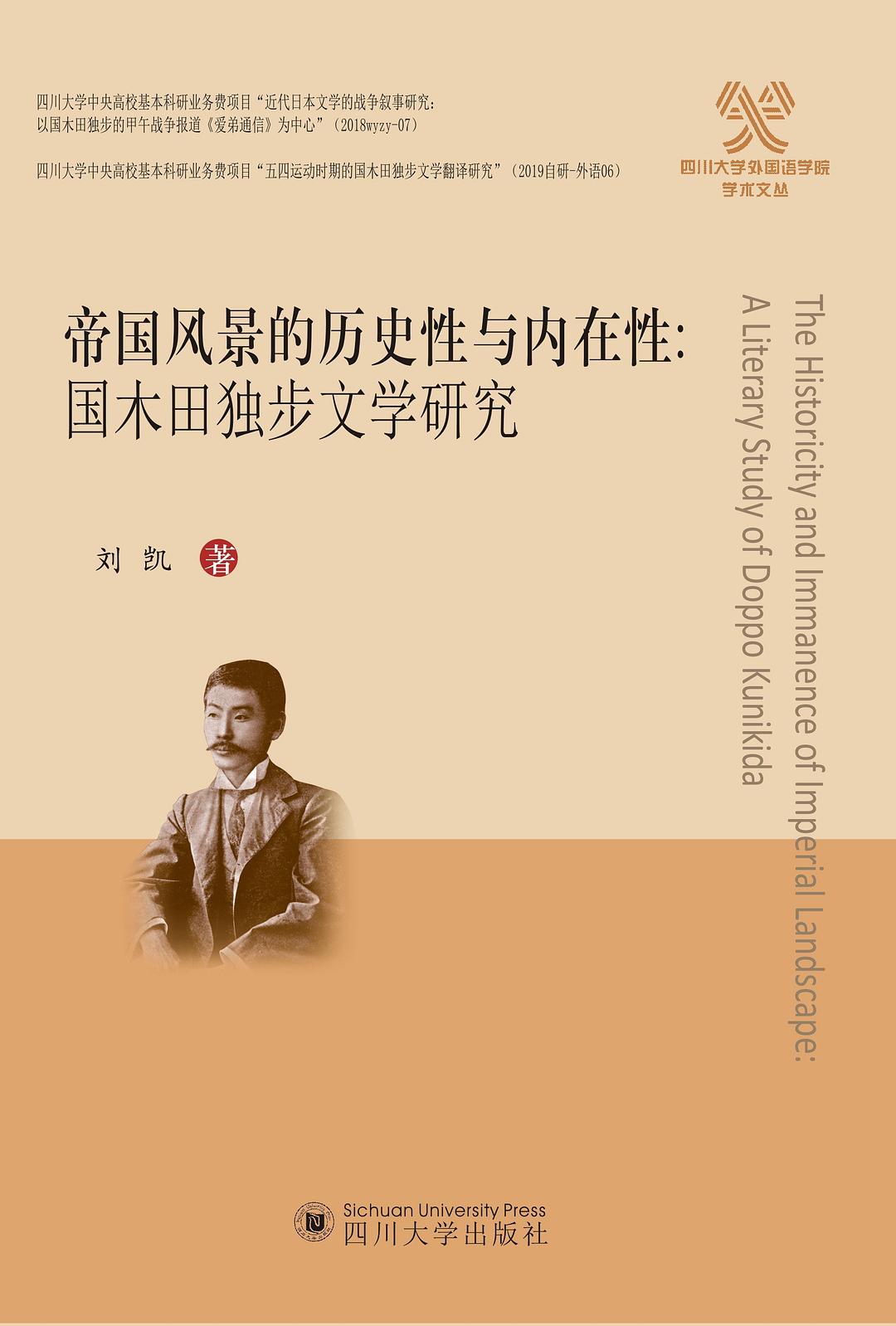
《帝国风景的历史性与内在性:国木田独步文学研究》书封
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国木田独步文学的定位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从宏观上看,国木田独步被描述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先驱,或者是从前期浪漫主义转换到后期自然主义的文学者,再或者是一个充满同情心的人道主义者。直至今日,几乎所有的日本现代文学史都如此叙述。从具体内容看,在过去近百年的研究史上,围绕国木田独步文学的争论就从未停止过。早在日俄战争刚刚结束时,他就被刚刚兴起的自然主义论者拉进了自己的阵营,尽管他本人对此百般否认;进入大正时代后,以白桦派为代表的理想派和人道主义者不满先前自然主义者的评价,又试图对国木田独步进行再评价;此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战争时期,国木田独步又被描述成一个帝国日本对外扩张的鼓吹者;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竹内好等人又在他的作品中追认某种体现了东亚各国连带感的人道主义要素,这一点也成为当代日本研究者对国木田独步文学的基本态度。
诸如此类围绕国木田独步的文学论争,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旧有文学史写作的需要,出于叙述的方便往往要对作家作品给出一个定论;另一方面,在看似已有定论的前提下研究者之间的论争却又从未停止。在笔者看来,比这场在话语上围绕国木田独步的争夺更为重要的是,其中暗示着国木田独步文学的难以化约性和历史复杂性。
明治一代的迷茫青年
国木田独步(1869-1908)出生于1869年9月17日,比北村透谷(1868-1894)和德富芦花(1868-1927)小一岁,比夏目漱石(1867-1916)小两岁,比二叶亭四迷(1864-1909) 小五岁。而在他之后出生,年龄相仿的还有高山樗牛(1871-1902)、田山花袋(1871-1930)、岛村抱月(1871-1918)、柳田国男(1875-1962)等。在明治维新(1868)前后出生的这一批文学家正值日本在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上实行广泛改革的时期,他们虽然有诸多不同,但大都是在明治维新后的新式中小学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并且在《大日本帝国宪法》(1889)颁布前后数年间接受西方式的大学教育。可以说,他们是随着明治国家一同成长起来的,加藤周一将这一代人称为“1868年的一代”。这一代人不得不面临的共同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自我”与“国家”“社会”“传统”“西方”之间的关系。
与少年时读“左国史汉”,接受汉学教育的夏目漱石不同,国木田独步的中小学时代都是在日本西南部山口县的新制学校度过的。与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在自由民权运动中度过中小学时代的国木田也深受中村正直的《西国立志编》(1871)、福泽谕吉的《劝学篇》(1872-1876)等所谓启蒙畅销书的影响。而身为山口县法院一名下级官吏的长子,他自然也背负着“出人头地”的使命。由于生来头脑灵活、性格敏锐,国木田在山口中学校的成绩一直优异,在十余门功课中尤以历史、地理、绘画和外语见长。据他后来回忆,自己在当时也是“一心想成为贤相名将、想要名留千古”。所以,当他1888年5月考入东京专门学校(现早稻田大学)时选择了英语普通科,两年后又升入英语政治科,主修政治经济学和历史。
与此同时,当国木田独步开始大学学习的时候,政治与社会的形势进入了明治维新后的第二个转变期。1887年12月《保安条例》颁布,刚刚写完《三醉人经纶问答》(1887)的中江兆民和其他五十多人被驱逐出东京,紧接着《大日本帝国宪法》(1889)、《教育敕语》(1890)又相继出台。明治政府的这一系列举措宣告了自由民权运动时代的终结。有意思的是,根据前田爱的考察,明治政府在明治15年(1882)后逐渐意识到了《西国立志编》等书对青少年的鼓动作用,遂迅速将其从教科书中剔除出去了。这一做法与自由民权运动走向低潮是同步的。在运动失败后,出人头地主义的路线迅速变窄,大批青年进入了目标丧失的状态。而在精神上填补了这个空白的则是基督教、德富苏峰的平民主义和政教社的国粹主义。
北村透谷在运动失败后转向了基督教并且以文学的方式继续斗争。德富苏峰(1863-1957)虽然也是基督教徒,但是作为横井小楠的外甥,他继承了横井的实学传统,并且在英国功利主义经济学的知识基础上写出了《将来之日本》(1886)与《新日本之青年》(1887) 两本书。他在书中将福泽谕吉(1835-1901)那一代人称为“天保的老人”,认为他们已经成为过去,代之而起的则是“新日本的青年”,日本社会也已经从政治斗争的时代进入了生产建设的时代。这种观点在舆论上迅速转移了青年们的注意。“青年”话语在此时的集中出现扭转了明治维新以降的政治实践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德富苏峰成立的民友社(1887)和国民新闻社(1890)在整个明治二十年代(1887-1897) 起到了意见领袖的作用。此前激进的政治行为逐渐被充溢着苦闷和虚脱感的文学行为所取代。
二叶亭四迷也是在这一年出版了小说《浮云》的第一编(1887)。主人公内海文三是一个青年公务员,正在因被免职而苦恼,但更让他苦恼的是自己倾心的恋人却移情别恋,内海文三的无力感充斥全篇。森鸥外在德富苏峰的劝说下写出了《舞姬》(1890),发表在《国民之友》上。主人公太田丰太郎要在德国恋人和回国工作之间做出选择。当他回到日本之后,内心又自责不已。宫崎湖处子的《归省》(1890)同样由民友社出版,讲述了一个青年学生自东京返乡后的经历,作者在结尾处表达的对未来生活的迷茫也绝对不是个例。
经历战争,转向自然
与此时一边在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英文科念书一边写汉诗的夏目漱石不同,国木田独步通过民友社下属的青年文学会结识了德富苏峰、坪内逍遥等人。1891年初在抗议校长的活动中退学后,国木田同时加入了基督教会。此后他通过德富苏峰和牧师植村正久继续学习,但是读书的兴趣由从前的政治经济学转为华兹华斯、卡莱尔、爱默生等代表的英美文学。在基督教思想和英美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下,国木田开始梦想成为一名诗人。需要注意的是,目前为止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国木田独步的文学观念很多直接来自德富苏峰,但是二人在文学观点上也存在不少分歧。国木田独步的确经由德富苏峰和民友社获得了英美文学知识,但是他的文学观的确立却是从批判德富苏峰开始的。
此外,国木田独步虽然兴趣转向了文学,但这并不是说他完全放弃了此前的政治理想。在大分县做了一年乡村教师后,他再次回到了东京。此时甲午战争刚刚开始。国木田在德富苏峰的邀请下兴奋地踏上了甲午战争的战场,为国民新闻社写战争报道,他也因为精彩的战争报道一举成名,并从此开始了正式的文学写作。在《将来之日本》中宣称倡导和平主义的德富苏峰在战争中写了《大日本膨胀论》(1894),平民主义迅速转为倡导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今的研究者都习惯于将国木田描写成一个甲午战争的受害者,但是一个自明的前提往往都被忘却了,即国木田独步首先是一个战争报道的写作者,是战争的积极参与者。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甲午战争作为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帝国主义性质的对外战争,不仅改变了东亚乃至世界近代史的格局,而且日本政府在战争中以全国总动员的方式最大化地运用了新兴的活字印刷媒体——新闻报刊。1869年2月明治政府颁布《新闻纸印行条例》之后,民间报刊的发行得到许可;从此时至甲午战争爆发的25年间,除官报和无数地方报纸外,以东京和大阪东西两大都市为中心涌现出了几十家全国性的新闻报社,如《朝日新闻》(大阪1879,东京1888)、《读卖新闻》(1874)、《每日新闻》(1872)、《东京日日新闻》(1872)、《报知新闻》(1872)、《二六新报》(1893)等。另外,像福泽谕吉、德富苏峰等知识界的名人同时也都是重要的媒体人,他们分别创办了《时事新报》(1882)和《国民新闻》(1890)。
新闻媒体作为一种现代的信息传递方式,它不仅仅可以跨越时空将消息从一地传递到另一地,更影响读者对新闻事件的认知。新闻作者的写作方式、报纸的刊载和传递方式等都决定着读者对消息的理解和认知。具体到战争报道,它决定着远在日本国内的数千万读者对战争的全部信息。一方面,政府在战争期间会更加严格地管制战争消息的发布,我们在国木田独步的日记中也能看到他在出发前领取许可证件的记录。因此,虽然甲午战争期间是新闻媒体最为繁荣的时期,但同时也是各类新闻条例颁布最多、被查处的报刊社最多的时期。另一方面,官报和民间报刊也想尽各种办法进行战争报道的写作。最先的战况报道由官报发布,其次战地记者再以速报的方式跟进报道战斗的概况、死伤人数等,再次是记者根据战况开始将报道故事化,写成长篇报道,最后还有对士兵的直接采访,或者刊登士兵的见闻等。此外,民间报社派驻的大量从军记者的身份也是多样化的,画家、诗人、小说家都有。国木田独步更是以写作家书这种新颖的方式为《国民新闻》吸引了大量读者。正是各媒体在战争报道上的一系列发明使得报纸的销量短时间内迅速增加:《国民新闻》从战前的每日7000份增加到两万份,《大阪朝日新闻》从76000份增加到117000份,《东京朝日新闻》每日增加到76000千份,《万朝报》增加到50 000份,而在日本东北部偏远地方的《岩手公报》也由每日1500份增加到3000份。报纸销量增加的背后是无数个被战争报道动员起来的读者(国民),战争带来了媒体的发达,媒体反过来也在创造战争。用小森阳一的话说,这俨然是一场“活跃在报纸版面上的活字战争”。
对战争报道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于文本本身,更要看到写作者的书写行为是整个国家战争报道体系的一部分。书写首先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它将写作者本人和读者都编织进文本的网络之中。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日俄战争中,已经成为近事画报社主编的国木田独步再次创新了战争报道的方式,他采用的素描、照片、文字相结合的方式又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他10年前写的甲午战争报道也是在日俄战争后被结集为《爱弟通信》再次出版。对国木田独步与战争的关系的研究不能离开这个历史背景。
甲午战争结束后,内村鉴三幡然醒悟,转而反对战争,提倡和平主义。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毕业的高山樗牛(1871-1902)很快凭借写作文艺评论成了《太阳》杂志的主编,开始倡导“日本主义”(1897)。德富苏峰也接受政府的聘请成为内务部敕任参事官(1898)。而幸德秋水作为中江兆民的学生,同安部矶雄、片山潜一起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与此同时,在战争中内心受到挫折的国木田决定移民北海道以重拾信仰,但是计划没能实现,他最终住在东京郊外的涩谷村,此后根据在那里的自然观察写出了著名的《武藏野》(1898)。
在同时代,国木田独步对“自然”的观察和描写行为并非个例。地理学者志贺重昂在甲午战争中出版《日本风景论》(1894)以降,文学和美术领域向“自然”的转向即呈现为一种集体行为。除国木田独步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有高山樗牛的《自然的诗人》(1896)、田山花袋的纪行文集《日光》(1899)、德富芦花的《自然与人生》(1900)等。此外,《太阳》杂志在这一时期还特别开设了纪行文专栏,内容涉及日本各地的风物描写。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纪行文是与同时代地理学知识的增长同步的。后者往往成为前者得以展开想象的知识前提。地理(国家领土)与纪行文(风景)之间有怎样的内在关联?为何两者会同时出现在甲午战争之后的日本?这都是本书要解答的问题。

国木田独步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国木田独步自1891年开始就对华兹华斯、爱默生、卡莱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梦想着成为他想象中的“自然之子”。但是这个想法不论是在佐伯当乡村教师时期,还是在北海道的短暂旅行中,都未能实现。恰恰是《武藏野》实现了他的想法。但为何是甲午战争后的《武藏野》?是怎样的前提给了他对自然的自信?要知道,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在年轻时对法国大革命充满了憧憬,并且只身去了法国。回国后他搬家到乡间湖畔,之后与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一起出版了《抒情歌谣集》(1798)。当卡莱尔(1795-1881)写完《衣服哲学》(1831)、《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1841)等代表作的时候,英国已经在鸦片战争中打败了清帝国。出生在新英格兰地区的牧师爱默生(1803-1882)在拜访卡莱尔之后,回到美国写出了《论自然》(1836)和《美国学者》(1837)。此时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正处在上升期,而爱默生也正在展开对加尔文教的批判。问题是,是什么因素使得华兹华斯的“表现论”、卡莱尔的“自然的超自然主义”和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汇集到了国木田独步那里?是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勾连了四者的文学动机?国木田独步本人又对这三者做了怎样的取舍?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追问的。
自国木田独步发表《武藏野》之后,一种全新的、现代的对“大日本帝国风景”的观看方式和书写模式诞生了。并且,《武藏野》也被后世的文学史逐步确立为日本现代文学中风景描写的典范。但我们也注意到,在这种一般性的叙述层面的背后,鲜有研究者会去追问;写作者本人的内在动力与外在条件是什么?这种风景描写的语言特征是什么?它是在怎样的历史前提下得以出现并固定下来的?
当我们对国木田独步的文学与思想进行考察时,不能将其视作一成不变的实体,相反要将他放到其本来的历史语境中,充分发掘他与同时代的关系以及他的文学作品的历史纵深。通过上面的简单梳理可知,一方面国木田独步直接参与到了近代日本最为重要的一系列国家行为(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北海道殖民)当中,他的文学活动也是从甲午战争正式开始;另一方面他又通过华兹华斯、卡莱尔、爱默生等英美文学者以及基督教思想获得了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而这些新获得的知识又促使他在所身处的近代日本乃至东亚的历史推移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想法。个人与国家、社会、历史之间的复杂关联也体现在这里。因此,对上述问题的追问,绝不是对某一位作家的独立的研究,而是牵连到整个日本现代文学在明治时代如何发生并成立的问题。
……
“难忘的人”为何难忘?
如果说国木田独步写作《不欺记》的约四年时间是理论学习时代的话,那么他在涩谷观察自然及至写作诗歌和《武藏野》的两年多是对理论的反刍时代,而与《武藏野》同时开始的小说创作则是理论的经验化和经验的再理论化时期,因为此后的小说大多数都以他的个人经验和回忆为题材进行的再创作。这其中因为1898年秋季国木田再次结婚,此后几年又先后在民友社(德富苏峰)、报知新闻社(矢野龙溪)、时事新报社(福泽谕吉)、民声新报社(星亨)、敬业社(矢野龙溪)等报社工作,他的生活趋于稳定,小说创作也由此正式进入状态。
在柄谷行人的《风景之发现》被译成中文之后,国木田独步的《难忘的人们》(1898)已经为不少中国读者所熟知。在这篇小说中,无名文学家大津向无名画家秋山讲,所谓“难忘的人未必是不应该忘记的人”。
“总之,像父母、子女,或者朋友知己等曾给予过自己关照的老师、前辈不仅仅是难忘的人,他们是不应该忘记的人。而此外还有一种和我们既无恩爱又无情义、完全毫不相干的人,本来即便把他们完全忘掉也不会伤及人情事理,然而终于还是无法忘掉。我并不是说在世间的普通人那里都有那样的人,但至少我是有的。恐怕你也有吧?”
首先,国木田在这里区分了两种“难忘的人”:一般意义上的和这篇小说中所特指的。前者是指与自身有着现实的血缘或伦理关系的人(经济关系应该也包括在内),所谓“不应该忘记”就是指这种现实关系的不可否定性,他的逻辑核心是“理”。而后者则是指与自己不存在上述现实关系的人,但是“我”却难以忘记他们,“我”的逻辑核心是“情”。而国木田独步在这篇小说中要讨论的就是后者。但要注意的是,他并不是说前者不重要,相反很重要,因为前者“不仅仅是难忘的人”,只是他在此处不讨论。
其次,国木田独步紧接着列举了三个“难忘的人”,第一个是他从东京专门学校退学返回故乡途中,在轮船上看到的远处山坡上的捡柴人,第二个是他后来与弟弟在赶路时,夜晚在阿苏山脚下的树林中偶遇的马车夫,第三个是去佐伯教书时,他在四国三津滨的街市上看到的弹琵琶的和尚。之后他又一带而过地提到了北海道歌志内的矿工、大连湾码头的青年渔夫。每一个“难忘的人”都是在作者实际经验中存在过的人,是作者观察过的人,但是又都寄托了作者的浓重的感情因素在里面:
“总之,我不断苦恼于人生的问题却又被自己对未来的大愿望所压迫着,是一个自找苦吃的不幸的男人。
而像今夜这样独自对灯坐着,使我感到了此生的孤独,催生了让我不堪忍受的哀情。这时我的主我之头角嘎吱一声便折断了,人也变得怀念起来,想起各种往事和友人。这时油然浮上我心头的就是这些人,不,是望着这些人的时候,立在周围光景中的人们。自我与他人有何不同?大家都是在天之一方、地之一角享受着此生,悠悠行路,又携手共归于无穷的天国。想到这里,我便不知不觉地泪流满面。这时实际上是无我无他的,任何人都变得令人怀念了。”
作为经验和客观对象的捡柴人、马车夫、和尚、矿工、渔夫对应着一个“主我”,但是这些客观对象最终又像武藏野的自然风物最后消解在自然与社会的“中间物”中一样,被“哀情”“天”“地”“无穷的天国”所回收,“自我与他人”变为混沌不分的“无我无他”。客体对象成了“我”进入“无我无他”之境界的方法。柯尔律治在回忆自己与华兹华斯一同写作《抒情歌谣集》时说道:“华兹华斯先生给他自己提出的目标是:给日常事物以新奇的魅力,通过唤起人对习惯的麻木性的注意,引导他去观察眼前世界的美丽和惊人的事物,以激起一种类似超自然的感觉;世界本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可是由于太熟悉和自私的牵挂的翳蔽,我们视若无睹、听若罔闻,虽有心灵,却对他既不感觉,也不理解。”这里所说的“超自然的感觉”就是“无我无他”的状态。
……《华兹华斯对自然的诗想》一文恰好与《难忘的人们》发表在《国民之友》同一期上。国木田在其中不仅提取了华兹华斯和卡莱尔的自然观中的共同因素,而且在小说中通过经验的讲述实现了将过去的自己相对化。他借用华兹华斯之口说道:
“我已经与没有思想的儿童时期不同,现在学习如何观察自然、倾听人情的幽音悲调。此刻我感觉到了贯穿于落日、大洋、青空、苍天、人心的某种流动的东西。”
那个“流动的东西”就是国木田在《不欺记》中所说的“赤条条的大感情”(sincerity),也可以说是“超自然的感觉”。那个被相对化了的、曾经“不断苦恼于人生问题”的自己此刻在内心获得了某种安定感。在同时期创作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佐伯乡村里寡居的老船夫(《源老头》,1897)到东京电话局接线员(《两个少女》,1898)、从涩谷青年夫妇的日常生活(《别离》,1898)到一个不断思索着“无穷之生命”的十二岁少年(《无穷》,1899),还有携带华兹华斯诗集和少年画家在林中漫步的“我”(《小阳春》,1900),其中都贯穿着“赤条条的大感情”,都在尝试“给日常事物以新奇魅力”。华兹华斯著名的诗歌《水仙》(又译《我独自游荡,像一朵孤云》)写道:
我独自游荡,像一朵孤云
高高地飞跃峡谷和山巅;
忽然我望见密密的一群,
是一大片金黄色的水仙;
它们在那湖边的树荫里,
在阵阵微风中舞姿飘逸。
.........
因为有时候,我心绪茫然
或沉思默想地躺在床上,
这水仙常在我眼前闪现,
把孤寂的我带进了天堂——
这时我的心被欢乐充满,
还随着那水仙起舞偏偏。
华兹华斯说:“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它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对过往经验的“回忆”是情感“流露”的前提,但是“回忆”本身也是一个对经验进行再加工的实践过程,所谓“强烈情感”是这个实践过程的产物。不过国木田和华兹华斯都将其视为一种先验的存在。而且较之华兹华斯对自然的强烈的乐观和自信,国木田独步在《武藏野》之后的小说中表现则更多是感伤的“哀情”和“幽音悲调”。较之华兹华斯的优美,国木田追求的更多是崇高。
不过,柄谷行人从政治批判的角度所要否定的就是这种自洽于孤独内心的安定感,进而认为作者“对眼前的他者(不应该忘记的人)表示的是冷淡”。这个观点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招致了许多研究者的批判。如木股知史批评柄谷的论述过于形式化,从而缺少对“作为表现的‘风景’”本身的历史考察。铃木贞美从同样的角度出发,指出国木田独步和华兹华斯一样,所要描写的精髓都是“万物的生命”。
诚如木股所言,柄谷论述中的盲点在于他在否定之前并没有对国木田独步所要真正讨论的内容本身进行考察。但是木股和铃木等人基于表现论的批评也有问题,在他们的意识中,国木田独步始终是被作为一个先定的实体看待,这样实际上也没有体现上文所梳理的国木田独步的思想运动过程,因此就更不会将其放在政治和历史的关系中分析,而只能闭锁在文本的内部。相反,柄谷的论述则始终以一种关系性为前提。
国木田在四年后发表的《空知川畔》(1902)的灵感来自1895年9月在北海道的短暂旅行经历。七年前的自己被描述为一个面色苍白、孤单不语、沉浸在自我“幻想”中的青年。这个青年“从没有思考过应当如何在社会中生活。他始终苦恼的问题是如何将此生托福于天地之间。所以同车的人在他看来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与他们之间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此刻身处的大森林成了他寄托“幻想”的最佳空间。幻想世界和现实社会是平行存在的。这一点实际上印证了柄谷的观点,只不过木股和铃木所要厘清的是“幻想”世界本身,而柄谷则站在现实社会做关系性的分析。一方是纯文学的,另一方则是政治的。实际上,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在国木田独步而言,都是基于既成的世界观来对自己的人生和身处的社会做出价值判断,纯文学中的思想认识也需要富有洞见的人的实践来完成。
有意思的是,《难忘的人们》中被一带而过的“北海道歌志内的矿工”在《空知川畔》中再次出现了:
我定睛一看,一栋平房依山而建,对面还有一栋。弹唱的歌声从平房里传了出来。一栋平房分成了好几家,家家都关上了拉门,门上映着灯光。三弦狂乱的调子、激越的高歌和欢笑声混杂在一起。在这牛棚一般的小屋里,谁能想到一群矿工能在深山幽谷中求得欢乐之境。
……啊,虚幻的人生啊!他们数年前流落至狗熊酣睡、群狼寄居的溪谷,在此落定,在此忙碌,在此沉沦。月光冷冷地映照着这一切。
我经过那里之后又回过头来,静静地立着,这时近旁的一家门突然开了,出来一个男子。
“呀,月亮出来了!”
和《难忘的人们》一样,在这里与其说描写的是矿工,不如说是在写自己的情感。艰苦的矿工生活被描写为一种“欢乐之境”。但是实际上北海道的矿工作为一个历史性的存在却要复杂得多。日本政府从明治初期开始就形成了所谓“集治监”政策,到了1891年7月又制定了北海道集治监官制。这个政策是将日本本土各地的监狱囚犯转移到北海道监狱进行集体管制,而数量庞大的囚犯被强制进行矿山开掘、道路铺设等殖民开拓事业。国木田独步1898年9月所到达的北海道空知地区是当时因犯数量最多的地区,空知监狱的人数在这一年达到了1700多人,而这些囚犯被安排的工作就是开采煤矿。集体强制劳动同时伴随着极其恶劣的生活条件和高死亡率。另外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囚犯中还有一少部分是曾经在自由民权运动中被政府逮捕的抗议人士。可见明治政府在颁布宪法、开设议会之后为了加强社会管制,不断地将权力内部的异己因素驱赶至整个结构的最边缘部分。国木田独步正是在国家权力的末端发现了这些被流放的“异己者”,我们无法证实他对这些“异己者”的历史是否知晓,但是这些历史在上面那段描写中是完全被屏蔽的。矿工的生活在“我”眼中甚至成了“欢乐之境”,矿工与“我”中间存在一层隔膜,他们在文本中是无法言说的。
相反,同样是描写矿工,夏目漱石的《坑夫》(1908)则将矿工在同时代的社会属性描写得淋漓尽致。受过中等教育的主人公阿安因为偶然的犯罪事件沦落为一名矿工,他对同样出身不错却也沦为矿工的青年“我”说道:“若是日本人的话,还是从事一些能为日本做贡献的职业比较好吧。有学问的人做了矿工是日本的损失。所以你还是趁早回去吧。从东京来的话就回东京去。然后做些正当的——适合你的——对日本没有损失的事。”受明治时代教育成长起来的阿安将“矿工”与“日本人”看作完全对立的两极,认为做了矿工便是“堕落”。小森阳一从阿安对矿工的蔑视中看到了其与明治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共谋:“把这种职业贬低到非人地位的局限于国家内部的思维方式,就为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基础,将支撑明治日本的底层角色原封不动地强加到中国、朝鲜和东南亚头上,这也是事实。”
指出这一点不是为了批评国木田独步没有对矿工做历史性的思考,也不是要说他与阿安之间可以画等号。在国木田独步而言,他始终处在自我意识的球体之中,社会则处在这个球体之外。从主观角度讲,他试图以自己的信仰来取代或超越社会权力关系:“宗教、政治、文学、历史、国家、国民福祉以及所有语言名目的世界都消失吧!一切都从我这里消失吧!……我只祈求真的信仰。”他采取的是取代策略,而非与社会展开正面搏斗。他的精神世界和现实社会是平行的存在,他则在两者之间来回穿梭。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就在国木田写下这些小说的同时,他在现实生活中反倒有意识地靠近国家权力的中心。在报社工作的几年间他通过各种途径接触到了福泽谕吉、矢野龙溪、星亨等人,并且在1901年3月曾试图与时任东京市议会议员的星亨联合进行竞选活动。这也是为何他在《难忘的人们》中说:“我不断苦恼于人生的问题却又被自己对未来的大愿望所压迫着,是一个自找苦吃的不幸的男人。”
芭芭拉·L派克在分析以爱默生为代表的美国超验主义文学时曾说:“超验主义绝对信仰完整的精神直觉真理;当这些直觉真理与已经确立的制度相对立时,超验主义就显得异常革命。但是超验主义不懈地追求精神利益,并从而蔑视知性世界,因此,当改革者试图赈济饥民或是解放奴隶的时候,超验主义几乎根本不可能直接发挥作用。实际上,这一运动所助长的淡泊无为和它所鼓励的自我专注有利于业已存在的制度,甚至有利于超验主义者批判的制度。而且,有效的政治行为所必需的团体原则是超验主义者深深厌恶的,因为在折中和谈判中必然不会有完全的真挚。”这似乎也适合国木田独步,只是他要比超验主义者处在更深的自我苦闷之中。因为与超验主义者不同的是,他所追求的超越性不是以对现实的否定为前提的,相反他始终没有放弃过对现实政治的积极参与,他的焦虑所在是如何在这两者之间达成统一。正如他在《爱弟通信》中所面临的内心苦斗一样,这与其说是他个人的自我矛盾,不如说是同时代的知识人在日本走向帝国主义民族国家时都必须面对的抉择。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