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张青仁评《统治与抵抗的仪式》|在仪式中理解墨西哥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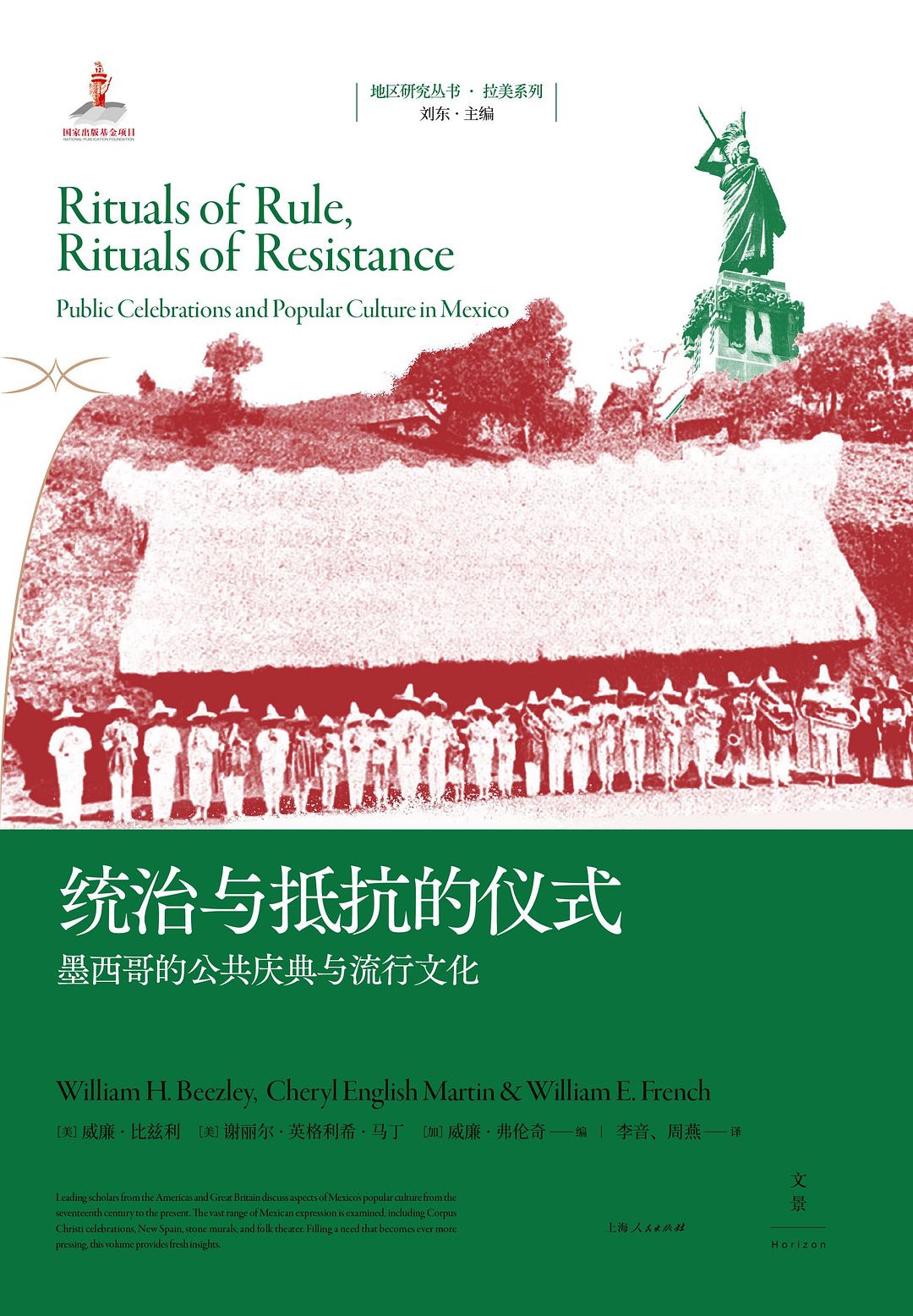
《统治与抵抗的仪式:墨西哥的公共庆典与流行文化》,[美]威廉·比兹利、[美]谢丽尔·英格利希·马丁、[加]威廉·弗伦奇编,李音、周燕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7月出版,512页,149.00元
仪式是人类学研究的经典议题。功能主义理论强调仪式社会整合的功能,主张集体参与的仪式可以为个人提供归属感、认同感,增强社会的凝聚力。然而,如果没有共同的世界观、共享的象征意义,仪式的整合功能显然无法实现。特纳从象征层面上,提出了支配性象征符号与工具性象征符号的概念,将仪式置于社会、政治和宗教的权力网络中,实现仪式静态功能与动态运作分析的联结。虽然特纳注意到社会历史变迁对仪式象征意义的影响,必须承认的是,经典人类学对仪式的研究,多聚焦非洲、澳洲等无文字、无历史的土著社会,表现出较为强烈的共时性取向,由此使得仪式的运作呈现出均质的、集体主义的取向。
在历史悠久、有着深厚文明积淀的复杂社会,仪式往往呈现出多重的、复杂的面貌。仪式象征意义的多重性随着这些社会卷入全球化、现代化的进程而越发加剧。殖民主义对亚非拉地区的渗透,西方文明和以西方社会为主体性的现代性开始在全球暴力扩张。在对西方文明的抵抗中,非西方社会逐渐成长为独立的、成熟的政治主体。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对地方社会的支配,在横向层面上加剧了区域社会的分化,推动区域社会多重政治主体性的生成。在区域社会内部,技术的进步与劳动分工的出现,推动着社会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的转换,造成社会结构的分化。为了维系自身的统治,不同时代的统治者们通过对仪式传统的参与、建构,借用仪式传统的权威属性,并通过新元素的挪用与植入,表达、宣扬自身的价值观,在象征层面上确认新秩序的合法性,这一进程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越发明显,由此形成了传统“贯彻某种共同体的社会凝聚力,贯彻某种权力关系和贯彻某种意识形态的类型”的面向。地方社会的仪式在延续历史传统的同时,呈现出动态的、历时性的演变进程。这正是霍布斯鲍姆所言的“传统的发明”。然而,对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地方社会而言,社会结构的分化、多重权力主体的生成使得统治精英对仪式的挪用不具备整体主义的效应。精英之外的多重权力主体,亦会通过仪式的操练,表达他们自身的诉求,甚至与精英抗争,赋予仪式“弱者的武器”的属性,由此构成了仪式变革与抵制变革的双重取向。这正是《统治与抵抗的仪式:墨西哥的公共庆典与流行文化》的理论基础。
《统治与抵抗的仪式:墨西哥的公共庆典与流行文化》聚焦的正是十六世纪至二十世纪,从殖民主义时期到独立战争时期,再到现代化与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墨西哥社会大众仪式经历的种种变化。殖民时期的哈布斯堡王朝、波旁王朝以大众宗教、公共庆典的方式,宣扬殖民力量对墨西哥社会的支配,形成了基于殖民主义基础之上的国家权力结构。在摆脱西班牙人的殖民统治、实现独立后,统治精英超越殖民主义、宗教传统和地区主义的束缚,以建筑物、歌曲、景观等多种象征再造的方式,实现国家认同的再造。这一对公共仪式再造的行动,在十九世纪波菲里奥·迪亚斯统治时期得到进一步强化。现代化工厂的设立,作为现代化象征的改革大道的建立,从各个方面确定着现代化对墨西哥社会的重塑,以及自由主义神话在这片古老文明土地上的兴盛之姿。二十世纪墨西哥大革命后,在革命民族主义思潮的支配下,革命制度党政府试图通过节日庆典、公立学校和博物馆的设立以及革命宗教运动,确立革命制度党政府与殖民时代和独立时期政府的连续性与统一性,推动统一国家秩序的建立,实现民族国家的秩序生成。在殖民时代以来社会历史剧变的情形下,少数族裔、工人、知识分子、宗教人士、女性与农民等群体也以对仪式的参与,表达着他们对政治态度与政治参与。就此而言,《统治与抵抗的仪式》以微观的、底层的视角,系统地呈现出仪式的统治的和抵抗的双重面向,勾勒出殖民体系以来墨西哥社会历史变迁的图景。
十六世纪以来,墨西哥社会仪式的发展、变化与丰富,固然呈现出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墨西哥社会分化的事实,然而不同阶层、不同区域的民众对仪式传统的借用,却在相当程度上实现着仪式灵活性与实用性的再生产,丰富着仪式的象征意义,并在新的历史语境下赋予仪式生命力与活力。更为重要的是,多重主体对仪式的参与、借用,亦在墨西哥地方社会的整体性情境中,在时间、空间、文化与认识论的多个维度上,勾勒出具备区隔的、差异性的主体以仪式为路径完成的互文性意义的再生产进程。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与现代化将原本统一的墨西哥社会分割为精英、权贵和资本代表的现代性的墨西哥和由农民、土著、女性代表的传统的墨西哥,造成了墨西哥社会持久的割裂。通过对仪式传统的借用与共享,仪式在空间、时间和感知的维度上,实现了墨西哥从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政治生活的转变。通过对共有传统的仪式的共享,超越不同主体狭隘的诉求,由此在墨西哥社会多元主体之间重构着文化与身份的联结。在丰富仪式的内涵,实现仪式象征动态演变的同时,作为传统的历史记忆与仪式超越地方社会的界限,生长为区域社会的联结机制。这也正是墨西哥现代民族国家生成的基础,也形塑了墨西哥社会仪式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赋予了仪式在墨西哥社会中持久的生命力。
在微观案例之上,《统治与抵抗的仪式》呈现的是墨西哥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现代性生成之路。无论殖民时期,抑或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时期,宗教仪式都是本书中举足轻重的部分。宗教仪式在不同时期政治统治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显示出墨西哥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现代性的生成逻辑。现代性被普遍认为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合理化的进程。经济自由主义的生长,以及在此基础上人类对理性、自由的探寻与天主教代表的精神领域保守主义的冲突构成欧洲社会现代性生成的基本动力,由此使得欧洲社会现代性的生成表现为宗教在世俗生活领域的不断退缩,逐渐内化为个人事务的世俗化进程。然而,在拉丁美洲,社会的结构性矛盾表现为纵向维度上土著的文化传统与殖民时代以来欧洲文明、横向维度上的多元族群及其文明之间的杂糅与并列。因此,拉丁美洲现代性的生成并非对历史传统的替代与革命,而是在历史与当下、多元与差异并存的情形下建立联结,确立彼此之间的关系与秩序的进程。作为社会生活重要组成的宗教仪式,恰恰是超越阶层、种族之间的区隔,实现社会联结的重要路径。由此,在墨西哥,现代性的发展并不表现为对宗教的否定与拒斥,而是国家权力与秩序以对宗教仪式的借用与挪用,将宗教仪式纳入到社会发展的进程,推动宗教本土性的生成,实现社会整体发展进步的过程。多元主体对于仪式的挪用,更赋予了宗教仪式及时回应社会变迁的能力,使其成为墨西哥乃至拉丁美洲现代性生产的重要主体。
在宏观层面上,《统治与抵抗的仪式》呈现出一种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民族国家建构的理念。在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影响下,殖民者与自由主义时期的政治精英敌视墨西哥社会的本土传统,试图通过文化传统、科学技术、价值观念与劳动控制的引入,以欧洲文明重构墨西哥社会的文明传统。然而,天主教对于混血相对包容的态度,以及早期殖民者多为男性的现实造成了混血现象在拉丁美洲的普遍发生,推动着拉丁美洲杂糅文化的生成。这一包容多元族群诉求的杂糅文化更在墨西哥独立运动中起到了基础性的政治动员的意义。在二十世纪后,民族主义支配下,立足于墨西哥社会杂糅文化的特征,统治精英一方面承认了西班牙文明对于墨西哥社会的贡献,更将墨西哥本土的阿兹特克文明视为民族国家的基石,以此完成民族国家的再造,实现一种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美洲的民族国家的建构之路。羽蛇神与上帝平等地共处于这片太阳子孙的土地,作为民族文化融合的瓜达卢佩圣母成为这个新生的民族国家的象征。源远流长的阿兹特克文明、玛雅文明也在民族主义的关怀下得到了延续。
本书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出对墨西哥文明主体性与独立性的认可,但这一认可却并不彻底。《统治与抵抗的仪式》聚焦的是十六世纪至二十世纪墨西哥社会仪式的发展变化,在时间的选择与分析态度上呈现出与“传统的发明”旨趣相似的后现代的仪式观与认知观。这一观念认为,仪式并非是过去传统的延续与遗留,而是对当下社会现实的回应,是为了创造政治身份而对历史传统的动员与建构。这一论点的背后是世俗化论调的风靡。世俗化理念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真实的民族,所谓民族的历史叙事就是对通过历史文本以及某些神话、特定符号重新解释的结果。由此,本书关注的重点是“统治的仪式”与“抵抗的仪式”,没有过多着墨于阿兹特克文明与玛雅文明中的仪式,也没有对仪式传统的真实性,以及仪式的本原意义进行讨论。事实上,这些古老文明的仪式传统一直存续于地方社会之中。作为一种特定类型的政治经济学和特定类型的认识论,这些仪式、习俗与规范,恰恰是定义“我们是谁”,定义“我们身份来源”的关键。本书的作者之一埃里克·范·杨在结语《作为吸血鬼的国家——墨西哥的霸权计划、公共仪式与大众文化(1600-1990)》里做出了委婉的批评,认为本书缺乏一种族群的、地域研究的视角。在我看来,问题的根源却在于本书是一个从西方为中心,自上而下的视角审视第三世界国家的墨西哥卷入世界体系、完成民族国家重建的历程,缺乏彻底的本土主义立场对墨西哥社会与文明的整体性认知,以及对墨西哥社会语言、生活与习俗的系统性呈现。事实上,这正是墨西哥经典人类学研究的重要主题。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