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李伯重谈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与写作

李伯重(章静 绘)
经济史学家、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伯重的英文新著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新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史》)近日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录了二十六篇关于中国经济史的英文论文。李伯重教授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批文科博士学位获得者之一、国际著名经济史学家,长期从事中国经济史方面的研究。这些文章发表于不同刊物、不同场合,最早的写于1986年,最晚的发表于2021年,涵盖了李伯重教授三十五年的学术历程。应《上海书评》之邀,经济史学者周琳近日就本书对李伯重先生做了四次采访,李先生分享了他五十年来的学术研究与中英文写作经验。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李伯重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23年10月出版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这本书的篇章是怎么选择的?在内容上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吗?
李伯重:这本书分为两个部分,收在两个部分中的文章都是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没有在内容上做特别的区分。但是这本书的确有一个主线,就是我个人的经历。
在我这一代的学者中,我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比较特殊的,其中一个方面就是有相对较多的海外工作经历。在海外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必须运用英语,因此我从1986年开始,就不断用英文写作学术论文以及讲演文稿。三十多年来,写了几十篇,现在选出二十六篇结集出版,成为本书。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海外一些学人对我的研究有兴趣,希望能够对我的研究多有些了解,另一方面是对我自己过去的工作做个总结,同时也给国内外青年学者提供一个如何成长的例子,作为他们探索学术人生时的参考。因此这部论文集的两个部分,都是依照文章写作的时间顺序编排的。姑且不论其学术含量如何,年轻学者可以看到我是如何学习英文写作的,从最初那篇比较幼稚的写作,到后来相对成熟的表述,经历了很长的过程。
年轻学者需要了解的一点是:我的英文是到了成年以后才从字母表开始自学的。我在中小学时,唯一能学的外语是俄语。到了“文革”时期,我被送到边疆农村,作为“知识青年”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时才开始自学英文。学习是在一天农田劳作之后回到住处,晚上在油灯下进行的。不仅没有老师,而且也没有课本,更不用说录音带等学习设备了。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一本苏联出版给苏联人学英文的教科书,于是我就用这本书进行自学,当然走了许多弯路,而且学的只是“哑巴英文”。这个学习不仅费时费力,而且还招致了风险(我在一篇文章中谈过此事,该文已收入拙著《良史与良师:学生眼中的十位著名史家》)。由于当时全国青年的英文水平都非常差,所以我在1978年考厦门大学的研究生时,英文居然考了第一名。到了厦门大学,才开始正规的英语学习,由厦门大学外语系郑朝宗教授等学者担任老师。郑先生是著名英国文学专家,他为这届研究生开的课是读英国著名文学作品(如莎士比亚、夏洛蒂·勃朗特等)的原著选读,这对于我们这批英文基础很差和对西方文化了解甚少的研究生来说,难度实在太高,因此学习兴趣也不太高。而且那时也没有多少英文的中国史著作可读,因此对英文没有予以特别重视。再加上我们的专业是中国古代史,那时认为日语对研究更有用,因此我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来学日语,在英语方面花的精力就少了。
直到1986年,经吴承明先生推荐,我到美国参加学术会议(这也是我第一次出国),才开始用英文写学术文章。限于当时的条件,我仅读过寥寥可数的几本海外学者写的中国经济史英文原著。特别是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教授的《中国农业发展:1368-1968》(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69),这本书对我的学识和英文有重大影响。我读得非常认真,每个生词都查了字典,在写作时尽力模仿他的文风和表述。在工具书方面,我也只有当时国内出版的英汉辞典和汉英辞典各一本,对经济史的英文写作帮助有限。我想请一位精通英文的经济史前辈学者来指导英文写作,但也无法找到。因此只好硬着头皮,尽力写这篇文章。这次写作非常辛苦,以致病倒。文章写好后,借来一台英文打字机,从头学习打字。好不容易把文章打完,送还打字机时,不料打字机从自行车上掉落摔坏,只好用几个月的工资去购买一台新打字机还给人家。这次会议结束后,蒙黄宗智先生邀请到加州大学做一个短期访问,随后又请我于1988年去那里教书一个学期。自此之后,开始不断到美国、英国和日本的一些名校和研究中心教书和做研究。在这些教学和研究中,我不断努力提高英文,最后才能够参加国际经济史学坛的许多重要会议和活动,并且在一些重大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做主旨报告。这个过程表明:一个人只要努力,即使起点低,条件差,仍然还是能够做出一些事来的。现在的年轻学者各方面的条件,比我这一代学者要好太多了,我相信他们只要努力,肯定能够做出比前辈学者大得多的成就。
写作本书第一篇文章的时候,也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您为什么会选择生产力研究?这好像并不是那个时候的很多学者会选择的研究方向。
李伯重:1949年以后,中国学界几乎没有人谈生产力。这是因为有一段时间政治上“极左路线”的影响,人们所理解的“革命”就是变革生产关系,因此学界也批判“唯生产力论”,连研究现实经济的人都不敢深谈生产力的问题,所以历史上的生产力的研究几乎没有人做。我年轻的时候也没有条件接触海外的经济史研究成果,因此完全不知道海外经济史研究到底研究些什么,以及怎样进行研究。当时只能读马列著作,在“文革”中,我读了《资本论》三卷,觉得马克思对生产力也是相当重视的。此外,我也读过一些1950年代翻译过来的苏联经济史学家的作品,像梅伊曼、斯卡兹金、波尔什涅夫等,觉得这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比国内大多数学者要深,但他们也还谈到了生产力问题,这就和当时的国内研究很不相同。国内学者长期说“生产关系”,说来说去就是那么一套,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讲,所以我就想试试新的东西。
到了1978年,我考上了厦门大学的研究生。这时刚好改革开放了,可以找到一些海外出版的学术著作来读。我读得最熟的一本就是上面提到的德怀特·珀金斯教授的《中国农业发展:1368-1968》,这本书研究的最重要对象是“经济成长”。经济成长当然与技术、人口、资源合理配置等因素密切相关,所以我就从这个角度开始探索,越做越觉得有意思。而且国内改革开放以后,风气也有所转变,但是做这方面研究的学者还是不太多,所以我想尝试一下新的问题和新的方法。我的硕士论文做的就是与生产力相关的问题,虽然现在看来比较幼稚,但是我觉得能够从此开始一个新的道路那就很好。
当然,生产力的研究有它的局限性,我们还是要从“经济成长”的角度,把经济当作一个系统进行研究。过去我们把“经济成长”划分为“生产力”“生产关系”两个范畴,我觉得还是应该更全面地来看。古典经济学以及之后经济学的发展,为我们还是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研究框架。所以我后来逐渐不再强调“生产力”,而是更关注“经济成长”。
在这本书涉及的三十五年中,您的研究课题、研究方法和写作风格一直在转变,请您谈一下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促使您这样做的动力是什么?
李伯重:这的确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我1986年第一次到美国去参加罗斯基教授和李明珠教授组织的工作坊。这个工作坊的目的是让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对话,经济学家能向经济史学家学什么,经济史学家需要经济学家提供什么?当时我英文很差,开会也不怎么听得懂,所以带着一个很简陋的录音机,录下来反复地听。之后,我去美国教书、做研究,一开始接触的大多是汉学家,后来接触研究欧洲史的学者越来越多。接触越多,眼界越宽,风格也就会改变。而且作为一个学者,你写东西要让人家看得懂,不单是语言的问题,整个思维和表述方式,必须是能够进入主流,才能与大家一起讨论问题,加入争论,提出新观点。如果仅仅是把国内照样翻译过去,是不会有多少人注意的。因为想看这些著作的人,如果是汉学家,他们看你的原文就行了,而不是汉学家,人家就很难理解你所说的东西。所以我的转变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从1986年算起,大概也有几十年了吧,风格一直在改变。像《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那本书,风格就和早期截然不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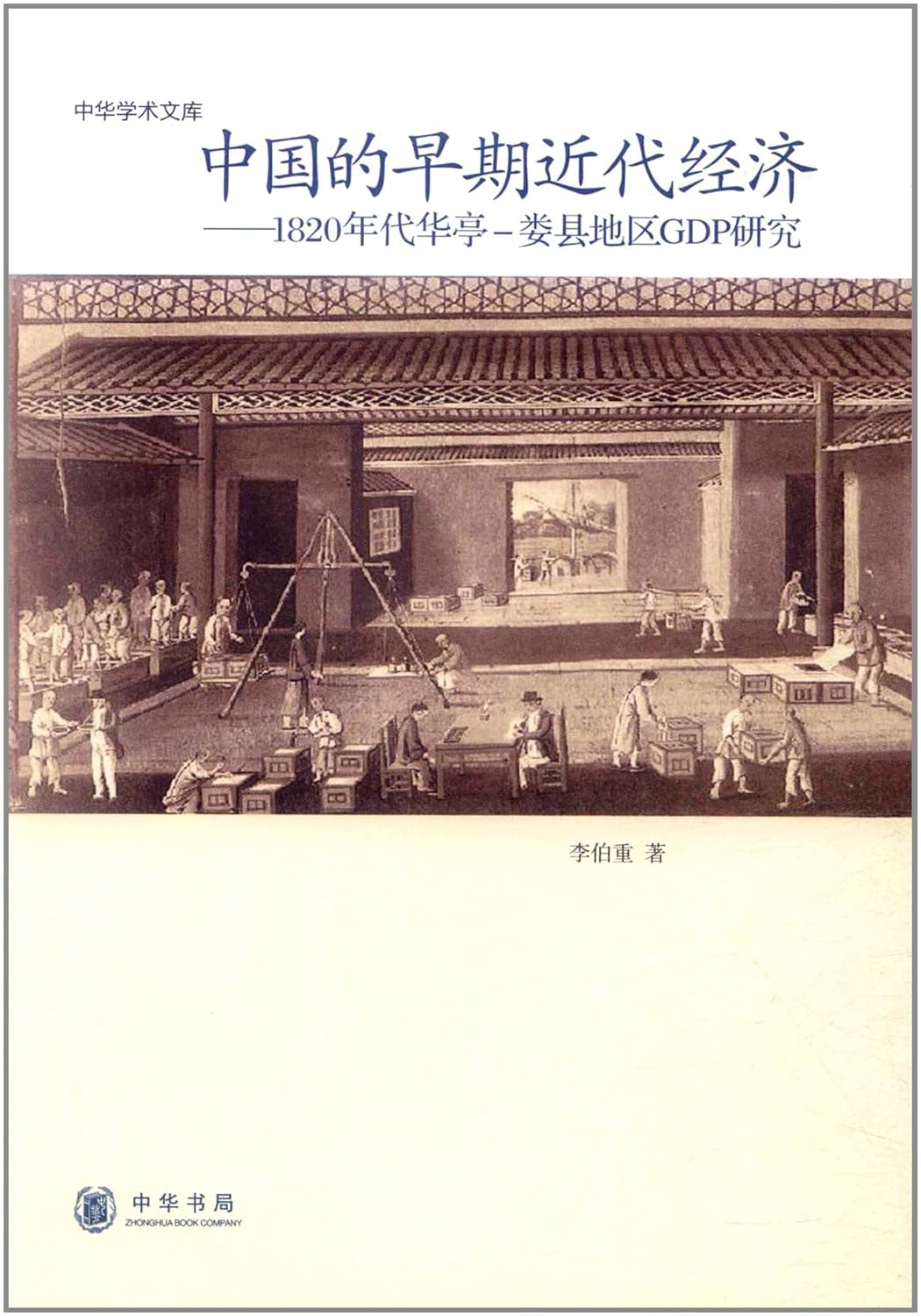
《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李伯重著,中华书局,2010年5月
中国的现代史学是从国外引进来的,经济史学更是这样。中国传统中没有经济史学,只有“食货学”。像欧洲过去有“政治算术”,但那也不是真正的经济史学。经济史学是从亚当·斯密时代开始出现的。经济史研究必须有一套理论体系、分期构架、丰富的史料,对历史有比较深切的了解,做出来的成果才能算做真正的经济史,从而也才能真正用中国的情况去参加更广泛的讨论。如果一个中国学者不太肯花时间去了解外面的动态,闭门造车,这是对自己很不利的。
这本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所收文章,以中国经济史(特别是明清江南经济史)为主,因为这是我毕生治学的重点。但是随着见识增长,我越来越深地体会到要做好经济史,绝不可把眼光仅只盯着自己有限的研究领域。英国经济史学者克里吉(Eric Kerridge)说:“经济史是从通史或总体史中抽取出来的,而农业史、工业史、商业史等又是从经济史中抽取出来的。这种专门化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集中思考总体史的某一具体方面,以揭示整体的发展。其他诸如政治史、宪政史、宗教史、法律史、药物史、海洋史、军事史、教育史等等,其目标都是这样。但现在各门专业壁垒高筑,互不理会,经济史也沾上了这种毛病。首先,经济学家渗入经济史学带来了一种非历史的观念(unhistorical cast of mind)。其次,统计学家的侵入也使经济史变得面目可憎。最后,经济史也受到‘历史假设’的困扰,‘历史假设’不仅违背事实,也违反最基本的常识。要摆脱这些困扰,经济史家与社会史家应该联合起来,开始新的综合。只有整合的历史才能使我们穿越现时,看到那已逝去的我们不熟悉的世界,更重要的是运用这种对那个已逝世界的知识,与当今世界做出对比,从而加深我们对现实的认识,这才是历史学家最伟大、最崇高的目标。”我觉得他说得很好,道出了今天许多学者的共同心声。因此,我一直不断扩大自己的研究领域,努力从社会史、生态环境史、自然地理史、文化史、政治史、全球史等方面,来观察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变化。作为结果,我也用英文写作了一些用这种新眼光引导的文章,收入了本书。我希望年轻学者也体会克里吉上面那段话中说的“整体的历史”的意涵,并将其作为自己治学的一个目标。
您的英文写作是怎么练出来的,这个过程中要经历些什么?
李伯重:我自己的体验是:熟能生巧,用一种外语写作,必须常读、常写,才能写好。前面说到,我学习英文写作得益最大的就是德怀特·珀金斯教授那本《中国农业发展:1368-1968》,那是我最早读的英文书,我很喜欢那本书,后来和珀金斯教授的关系也很好,我的《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的长江三角洲》英文版(An Early Moden Economy in China: The Yangzi Delta in the 1820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0),也多蒙珀金斯教授惠作序。我把他的《中国农业发展:1368-1968》这本书读得很熟,从而模仿他的风格来写,那本书的写法是非常正宗的经济史写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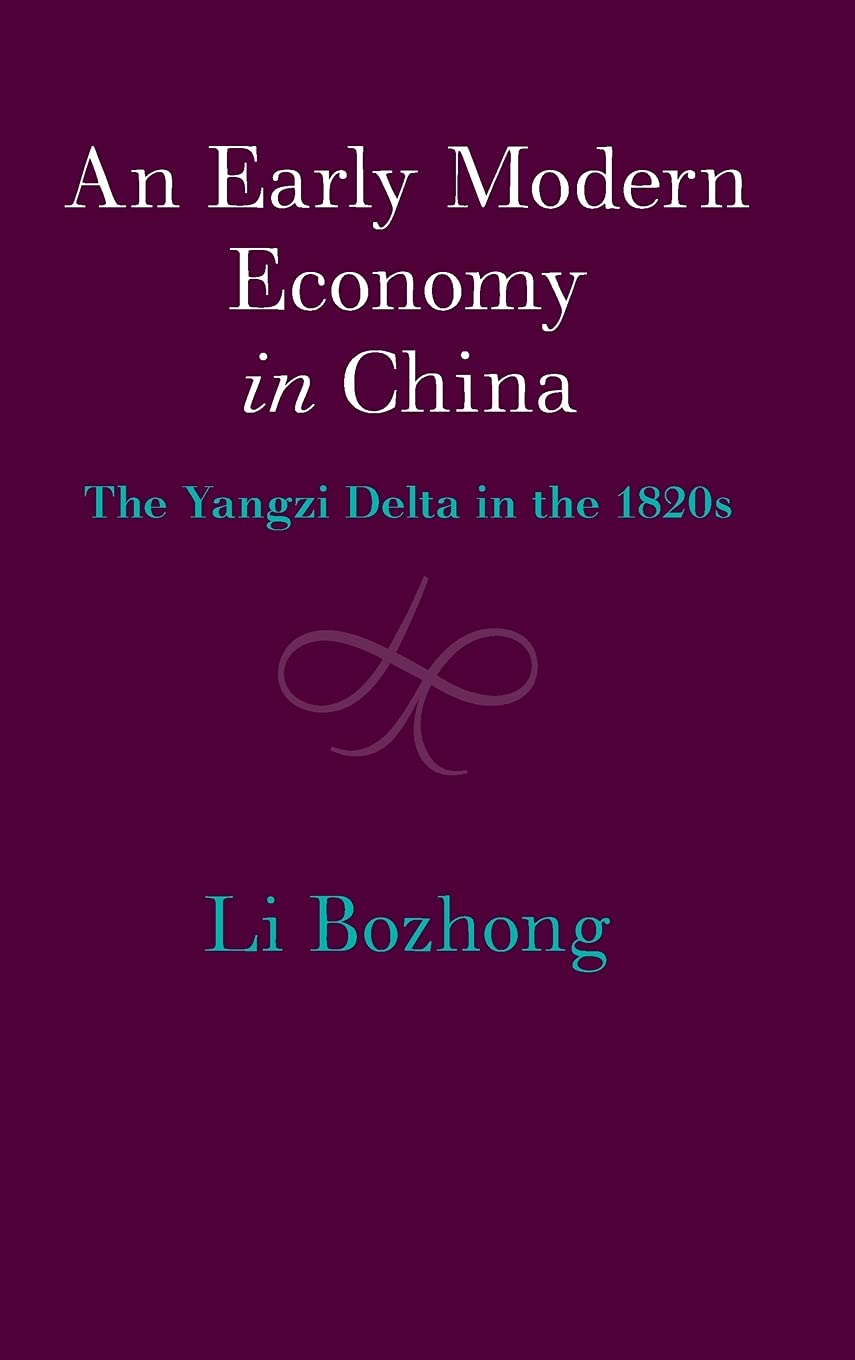
李伯重著《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的长江三角洲》英文版( An Early Moden Economy in China: The Yangzi Delta in the 1820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0)
我认为,学习任何东西,必须要先模仿,然后才能慢慢建立自己的风格。如果年轻学者向我问点英文写作的经验,我建议找一两本分量也不太大、写得很好的英文专业著作,读得很熟,模仿着写。当然也不需要完全模仿,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渐渐地把自己的风格加进去。珀金斯教授的那本书,我当时读得熟到这样的地步:书中的一个句子,我大概能记得它出现在哪一页。这样,写作时遇到表达同样意思时,自己没有好的表达方式,就可以翻开看看珀金斯教授是怎么写的,然后调整自己的表述。先父李埏先生是一位经济史学家,他从前写过一篇谈读书的文章,说读书一定要有主次轻重之分,就像古代的大将打仗都有自己的亲兵,就是在身边最得力的一个小部队。读书也是这样,需要熟读几本书,将其作为自己的“亲兵”(李埏:《读书和灌园》,收入《李埏文集》第五卷“札记与杂文”,云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
每个人的兴趣和研究方向不同,所以你需要自己去发现这样一两本书,你喜欢的,值得你花很大的力气去学的书。
在为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写书评的过程中我专门数了一下,到现在为止您自己写的书(不包括被翻译的)已经有十六本了,这着实让我很吃惊。因为我自己常常遭遇写作时的卡顿和自我质疑,所以我很想知道您的写作速度和流畅程度是怎样锻炼出来的?
李伯重:其实我虽然写了十来本书,但我的写作已经持续了近半个世纪,我的第一本书是1975年出版的(千里、延之:《北宋方腊起义》,云南人民出版社)。半个世纪写十来本书,平均四五年才写一本,这个速度已经不算快了,对不对?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我在这半个世纪中的写作,一开始很慢,到了后来写作速度也有所加快。首先,写作与积累的关系很大。如果你心目中有一个主线,那么你做的每一步工作都是一个积累。这样积累下来,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发生变化,就像水烧到一百摄氏度就会沸腾。那个时候你头脑中涌现出来的新想法,就会相对来说比较成熟,因为持续的研究和思考可以为你新的想法提供支撑。如果没有这个积累,哪怕你有很多好想法,找不到支撑,要把它用学术的方式表现出来,当然就会比较费劲。
其次,就是我刚才说的,心目中一定要有一个主线。我从做研究生开始,心中关切的主线就是“近代化”的问题。我最早是做唐代经济史研究,过去对唐代的评价,多半是从“大唐帝国的辉煌”“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民不聊生”这些角度来谈。这些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课题,但是如果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唐代留下的遗产与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选择的就是“江南”。这个地区相对受战乱影响比较少,经济相对比较稳定,它特有的一些秉赋也使它成为一个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的地区。宋代江南的历史我没有专门研究,但是我讨论过“十三、十四世纪转折”的问题,也可以视为对唐代江南经济研究的一个延续。这些都为我后来的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因为任何重大历史变化,都是长期发展的结果。我从攻读博士学位开始就研究明清江南经济史,一直到今天。这样一步一步的积累,都是围绕着“近代化”这条主线的。
明代中期以前的经济史,基本上可以视为“近代化”的前史,但是到明代后期,“近代化”的端倪就开始显现出来了。以往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现在经常讨论的“晚明社会转型”“晚明大变局”问题,实际上都是在告诉我们,应该把明代后期看成中国近代化的起点,虽然它有“前史”,还有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但它确实是开始。后来到了清代,一般认为清代中国经济受了很大的挫折,这是事实。但是另一方面,清朝也为中国创立了一个空前统一、长期安定的局面,并形成了全国性的市场体系。江南因为各方面的因素,在这个市场体系中是受惠最大的,所以在“斯密动力”的推动下,江南市场经济就更向前走了一步。所以从我最初的经济史研究,一直到2020年出版的《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的长江三角洲》英文版,实际上就是一步一步地往这个方向深入。
另外我一直有一个感觉,要研究中国近代化的问题,就中国谈中国,就江南谈江南,是不行的。你说江南出现了近代化,他说没有出现,关键是“近代化”一定要有一个标准,否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讨论就不能继续下去。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只能是其他地区得出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共同规律。这个共同规律最典型地显现在英国的近代化过程中。这是因为,在世界历史上,英国在近代化过程中走在最前面。因此,对于近代化的历史而言,研究英国的经验具有特殊的意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由于英国的这种特殊地位,所以成为世界近代化研究的重点。而作为曾经长期存在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英国可以为英国经济史研究提供最好的条件,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就是在英国写成的。到了二十世纪,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和文化中心,汇集了众多各国优秀学者,因此在近代化研究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英文是我用得比较多的一种语言,改革开放后有了条件,我就大量阅读英国经济史的文章和著作,特别是工业革命前后的研究,这就改变了我的视野。心里面有了一个“什么是近代化”的概念,再回过头来看看江南,哪些是对江南适用的,哪些是不适用的?这样的话,就更加能够思考江南的近代化究竟有哪些特点了。
当然,和英国比较只是第一步,第二步还要看到世界格局的改变对江南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对全球化做了非常好的论述,所以刘明华等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认为,《共产党宣言》中的全球化思想非常重要,对今天也有很大意义。如果有了全球史的知识背景,就不会只是单纯地看英国,或者看某一个其他国家,而是将问题扩展到:十六至十九世纪中国的外部环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时候阅读范围就更加扩大,一步一步走下来。
但是在尝试使用全球史视野来研究中国的过程中,我始终坚持经济史的问题主线是“近代化”。到今天我们还在这条路上走,我觉得这对于我们了解中国的昨天、今天、明天是至关重要的,就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Douglass C. North)说的:“历史是联结过去和未来之间的桥梁。”不把历史研究清楚,我们对今天的很多情况也是看不清的。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对历史认识的偏差,我们已经吃了很大的苦头,走了很多的弯路。所以以近代化为主线,把中国经济史放在更大的空间范围中进行研究,是我长期的学术研究主旨。有了这个主线,就不会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一下子搞这个,一下子搞那个。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所有人的聪明程度差别也不会太大。但是在一条路上,用半个世纪的力量去做,总还是可以做出一点事的。
在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这本书中,有一些文章批评了既有的研究,质疑一些具有共识性的说法,比如“选精、集粹”“13、14世纪转折”“丝绸之路”等。其实学术批评怎么说都是一件沉重的事,您是怎么去做的?
李伯重:这与个人性格有关,我自己学问浅薄,所以非常尊重其他学者的研究,但我也不迷信权威。对于其他学者的看法,我认为正确的就接受,不正确的就质疑、批评。另外,学者之间的批评应该是,而且也可以是友善、积极的,就像我在《“何伟亚事件”和“亚伯拉罕案件”——从“人口史风波”谈学术规范、学术纪律与学术批评》(刊于《中华读书报》1998年10月7日)一文中所说的那样。我自己力求这样做,就像我在“选精、集粹”那一篇文章中,对我非常敬重而且和我关系非常密切的斯波义信先生、伊懋可(Mark Elvin)先生,还有我很尊重的梁庚尧先生的观点都做了批评。文章发表之后,我寄给他们看,请他们批评指正。他们读了我的文章后,都有积极的回应。伊懋可先生原来认为中国历史上技术的发展到明清就基本停止了,而我不同意他的看法,他后来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我,提出了他在对我的文章做了思考之后的新看法。我觉得他的新看法非常好,也使我对技术进步问题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所以在我在后来的文章里几次引用他的信。斯波义信先生认为我谈的是对的,而梁庚尧先生不同意我的批评,我就说那请您最好写一篇文章和我辩驳,这样让读者更加了解他的思路。他真的写了一篇文章,文章中首先就提到,这是我鼓励他写的。
我觉得学术就是要大家一起通过讨论甚至争论,才能进步。像傅衣凌先生、吴承明先生、斯波义信先生都是我非常景仰的前辈学术大家,我一向把他们视为自己的老师。而作为史学大家,他们都不会固守自己的观点。傅先生在晚年改变了学术观点,认为中国不应该是一个“封建社会”,而是一个多元结构的“传统社会”;吴先生在晚年也放弃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认为应该是“市场经济萌芽”。我也曾写文章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对吴先生先前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但是吴先生并不因此就感到不快,相反还会接受我说的合理的部分,进一步去做积极的讨论。这种真正的大家风范,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的。
在您五十年的研究生涯中,有没有觉得遗憾的部分?
李伯重:遗憾当然是太多了,比如外语的能力。由于时代的特点,我从小学开始学俄语,学了两年停了,中学又学了四年,俄语水平已经可以读一些原著,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类的书。但是后来六十多年不再接触,几乎全都忘了。现在我也看当年在“国际经济史学会”开会时认识的一些俄罗斯经济史学家的作品,比如鲍里斯·米罗诺夫(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иро́нов)。原文我现在也读不了,但我偶然看到中译本(Б.Н.米罗诺夫著,张广翔等译:《帝俄时代生活史:历史人类学研究,1700-1917年》,商务印书馆,2013年),觉得写得很好,不仅与苏联时期的研究风格完全不同,而且使用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做了很好的量化分析,讲俄罗斯帝国时期人民的生活、经济发展。像这样的著作,对于我们认识我国最大的邻国、且对我国近代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俄国,会有很大帮助。但是限于语言能力,我已无法从他的其他著作中获取知识了。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学日语比较多,在当年的学习班里还考第一名,我的硕士论文所引用的文献,日文文献占了很大分量。我也曾翻译过日文的论文,如日本的中国农史大家天野元之助先生《中国农业史上的耕具及其作用》(译文刊于《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239-259页)。但是后来日文也生疏了。原来读过的东西还勉强可以读,新的东西却已经读不了了。
日本学者在日本经济史研究方面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像速水融、斋藤修等学者的研究,都是一流的。在中国的近代化历史研究方面,日本的近代化经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照物。同时,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在经济、文化方面联系非常紧密。不了解日本的经济史,就不能更深入地看到中国在近代化历程中的特点。日本学者在研究东亚经济史方面,也做得非常好。比如十六世纪以后日本和中国、东南亚之间贸易的研究。其中有一个问题让我感触很深,就是关于东亚海域的金属贸易问题。中国是日本最大的金属出口对象国,但是中国在这方面的资料远比日本少。而且此外,日本商人、武士在东南亚也非常活跃,与中国商人也有很密切的合作,这也是从全球史视野出发来研究中国经济史所需要掌握的。但我现在只能翻翻这些研究,大致了解一下,自己要认真来读这些著作已经比较困难。所以觉得是很大的遗憾。
另外,虽然自己也认真地读了一些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的著作,但是没有受过系统的训练,我也觉得挺遗憾的。
您可否谈一下您最近正在进行的工作?
李伯重:最近有两本书稿即将完成。一本是《什么是经济史》,讲经济史研究的各种模式、范式,经济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等等。书稿已经基本完成了,还需要查阅一些引文和出处。另外一本是《16-19世纪中期中国的对外贸易》,这本书涉及明清政府对中国海外贸易抱持的态度以及背后的原因,也涉及现在学界的一些争论。做这个研究,不仅需要看许多中国的材料,还要看许多国外的材料。我写这本书的出发点还是“近代化”,我认为这是中国近期历史中最重要的事。在这个时期中,有许许多多事情发生,都对中国“近代化”过程的艰难曲折起了作用。除去各种外部原因外,当然更有内部的原因。因此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中国人自己是不是都做得很好?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