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普通人的自然|穿行汗马:在自然保护区,它们发现了我们
一路向北四千公里,转机、驱车、长途奔袭的过程中,目睹着山河地貌的变化,雪也层层递增,渐渐显像。冬雪漫漫,随着时间推移,一切消隐其中,城市的轮廓如同谜题,只能等到春日才能拆解。

汗马自然保护区的森林。本文图片均为作者提供
今年冬天,东北成为一片令人趋之若鹜的土地,除了雪的魅力,更多是由热梗频出的文旅营销带动的。与催生出流量人格的“尔滨”相比,同样地处东北的“兴安岭”,更像一种来自语文课本的复古记忆。有趣的是,追溯课文的本源,上世纪60年代的课本里写的是大兴安岭冬日林区紧张的伐木作业,而当下的课本里则是描摹小兴安岭中紫貂、黑熊与松鼠的踪迹。这也恰恰说明中国林区的时代变化。
林中激流:何为自然的原真面目
大兴安岭拥有大片寒温带森林、自然奔腾的河流和广阔的湿地,8万平方公里的林区被称为是中国最北生态安全防护屏障。自1964年开发建设以来,大兴安岭地区累计为中国提供商品材1.26亿立方米;但2014年开始,大兴安岭地区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正式进入转型。

汗马自然保护区的牌子。
而我此行要进入的汗马自然保护区(后简称“汗马”),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根河市金河镇境内,地处大兴安岭北段西北坡原始森林腹地,这也是中国保存最为完整最为原始寒温带明亮针叶林区。“汗马” 在鄂温克语中有“源头”之意,即激流河的源头。激流河是额尔古纳河重要支流之一。在地图上看,额尔古纳河的众多支流水系犹如蔓延舒展的叶脉,沿着大兴安岭的主脊通向大地的心脏。因汗马从未曾受到人为干扰,这里也是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汗马自1954年被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批准为“禁伐禁猎区”,1996年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15年被正式指定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

塔里亚河,额尔古纳河的一级支流激流河的源头。
对我而言,也因这次参与青野生态的行程,才开始深入了解自然保护区的概念。青野生态立足于四川唐家河自然保护区,由最初白熊坪保护站的站长刁鲲鹏创立——“刁站”也是这次行程的领路人之一。
更奇妙的是,在我的家乡肇庆市18公里外,地处珠江三角洲平原边缘的鼎湖山,实际就是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这里有近400年记录历史的地带性原始森林──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和其他多种森林类型。当然,如果说对自然保护区的认定,是从“禁伐禁猎区”的标志开始,那么这个“第一”到底归属何方,在汗马也时有争论。在我的记忆中,鼎湖山更多是作为休闲旅游景区呈现:童年时与爷爷奶奶住进山中的疗养招待所,因蚊虫而彻夜难眠;刚学会游泳时,也斗胆在驰飞的瀑布间畅泳;再长大后,与同学赤足溯溪而上,登顶后在庆云寺外吃一碗豆花;这些山中记忆都长存在我的心底。唯一对于原真自然的敬畏,也来自一则都市传说:本地人将自然保护区内的森林腹地称为“老鼎”,认为那里险象横生,想要入内的登山者需先到派出所报备。直到近年来,经由自然教育而开展的各类活动,终于让我了解鼎湖山在旅游景观之外的另一种面目。

根河小镇。
回到汗马,这里显然不是一个易于和日常产生联系的区域。当下即便拥有现代的交通工具,一路跋涉也并不从容。从海拉尔机场落地后,驱车三小时才到根河市,还需辗转三小时才能抵达保护区的管理站,步行进入保护区的缓冲区域。冬季昼短夜长,下午四点前,大家就要开始返程,再经历三小时奔波,回到根河市。因为低温,整个车身都在挂霜,窗外的风景犹如一团浓雾,盘旋不散。也因为冻土,路途颠簸,四驱车像一团奔驰的火种,向着林深冲刺。

进入保护区的管护站。
汗马的冬日最低温度可达零下五十度,但被积雪覆盖的汗马却正值野生动物调查的最好时间。落叶泰加林已然撤走了防护色,林间成为最大的曝光区,大雪正正是动物的显影剂。如今,保护区内已布设红外相机84台,可监测到驼鹿、猞猁、棕熊、黑嘴松鸡、紫貂等珍稀濒危的野生动物影像。除了动物方面,气候变暖对冻土的影响、老头林的生长速度监测等工作、火烧迹地植被恢复的调查等,都在自然保护区内进行。
此次作为领路人之一的马健,是汗马自然保护区生态科普宣教的干事之一,他与工作伙伴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林间穿梭,监测、记录、统计。当然,最令人兴奋的时刻,必然是发现。在我们进入保护区的前一周,他们就通过驼鹿与狍的尸体,发现是猞猁将其猎杀,从而架设红外相机蹲守拍摄。大自然里,孤寂与奖赏,似乎永远都是等价交换。
雪岭逐鹿:是它们发现了我们
因文旅营销,今年东北亚地区的少数民族也纷纷在聚光灯下“营业”。鄂温克本意为“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原始猎民保持“逐鹿而居”的生活习惯。但1965年开始,鄂温克人结束游牧和狩猎生产,开始了定居的生产生活方式。2003年8月,首批使鹿鄂温克人和他们的驯鹿从大兴安岭腹地搬迁至位于根河市郊的敖鲁古雅,敖鲁古雅意为“杨树林茂盛的地方”。为保证驯鹿的觅食,鄂温克猎民迄今仍保持着频繁迁徙,常以驯鹿食用的苔藓丰富、群山环抱、河流分布的地区作为“猎民点”驻扎。我们到达其中一个猎民点时,大部分驯鹿已外出觅食,剩下与蒙獒相处甚欢的那只一岁半的小鹿,实际是一只母鹿的弃子,被鄂温克人用牛奶养大。

鄂温克族人养的驯鹿。
与性情温顺的驯鹿不同,驼鹿是野外的巨兽。在未正式进入保护区内的老头林边,我们其实已在雪地上发现了驼鹿的脚印踪迹与粪便。即便未见其真身,但已然能想象出它们奔袭的场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鹿科动物,满语被称为“堪达罕”的驼鹿,肢长、头大、面长、鼻形如驼。驼鹿是典型的泰加林居民,栖息于亚寒带的原始针叶林或针阔混交林中,中国的驼鹿目前仅分布于东北地区的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阿尔泰山一带,其中,大、小兴安岭分布区的驼鹿,不仅是亚洲驼鹿分布的最南部边缘种群,也是世界驼鹿最南分布的种群之一。2016年,汗马保护区设置的红外相机同时监测到6只驼鹿,在中国尚属首次。
如果放眼全球,驼鹿在不同地区不仅有不同的名字(北美洲称为“moose”; 欧洲称为“elk”),也有着全然不同的生存境地。挪威经典的三角警示标志正是提醒司机,驼鹿作为“马路杀手”的存在。据统计,2003年至2017年间,美国缅因州发生了7,062 起与驼鹿的碰撞事件。打开一位加拿大猎人创建的网站“All about moose”时,不仅可以看到与驼鹿息息相关的信息,甚至还有他编撰的一本捕猎驼鹿的技巧指南与食谱。

雪地上的动物脚印。
与此同时,颁布于1989年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时隔32年后于2021年进行首次更新调整,在这次更新中,驼鹿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升级为国家一级。对野生动物而言,它们的名字是否进入名录、在名录的等级都会直接影响其种群的发展命运。但如何定义其“稀缺”与“珍贵”,则始终在争论之中。如因民间认为药用价值高而被大量捕杀的黄胸鹀(俗称“黄花雀”),被污名化的蝙蝠等,是否值得关注,都一再成为议题。
在《动物社群》一书中,两位加拿大动物权利家提供了一种主权思路:野生动物易受人类活动影响,其形式不仅有直接的暴力、破坏栖息地与无意的伤害,同时还有积极的干预。书中强调动物的自主权利。这要求我们思考,对野生动物的积极干预义务需要在一个合适的框架内进行,“并非为了倡导建立某种制度性机制,而是阐明那种会在背后推动制度变革的人类-动物关系图景。”

保护区内被废弃的站点。
虽然只能在林间短暂停留几个小时,但鼠兔隐匿在灌丛中的干草窝,在厚雪中修筑的交错隧道;紫貂与狍子在林间雪地上的跳跃痕迹;被压弯但实则伺机行动的偃松;五十年树龄才生长到一米七的老头林;从中都能感受这座森林之间的暗藏的生命搏动。一切像是没有发生,但一切已尽然发生。回程的路上,天色渐暗,车窗外灰蒙蒙,大家也昏昏沉沉睡去。司机一个急停,惊呼了一声,发现了早上驼鹿踪迹的来路,几只巨大的黑影在林边停驻,我们静默相望,试图理解地球上属于他者的种群。车辆再次轻轻启动时,黑影敏锐地消隐于林中。
事实上,是我们闯进了它们的领地,被它们生活的世界所震慑。那个暮色将近的夜晚,是它们发现了我们。

保护区的植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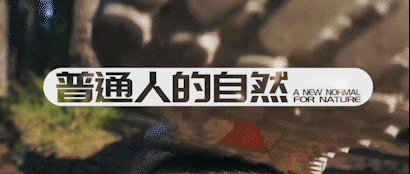
个人能为环境做什么?普通人如何在自然中自处?
“普通人的自然”(A New Normal for Nature)专栏记录普通人与自然相遇的故事。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