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年夜饭往事:少不了的那道菜,是家味,也是乡愁|何以为家①
【编者按】
对中国人而言,春节是一场盛大的回归,朝着“家”的方向。从家人到家族,从家乡到家味、家俗,这些传统的风物、习俗,情感关系,形塑了我们。澎湃新闻推出“何以为家”春节策划,追寻我们的精神谱系,发现何以为“家”,何为“乡愁”,又何为“我们”。
明朝博物学家谢肇淛曾在《五杂俎》中提到带鱼,说它“诸鱼中最贱者”。
确实,现今每年60万公斤的产量和发达的物流系统,足以把带鱼运到远离河海的内陆甚至深山。一斤十来块,再普通的人家过年也能靠它维持着“山珍海味”的朴素门面;它做法多样,烹饪方式丰俭由人,每家都有自己的带鱼秘籍,怎么做都好吃。
而我从小吃了那么多年带鱼,它已经如基因一样深植在我的记忆之中,走到哪里,都是我心里放不下的乡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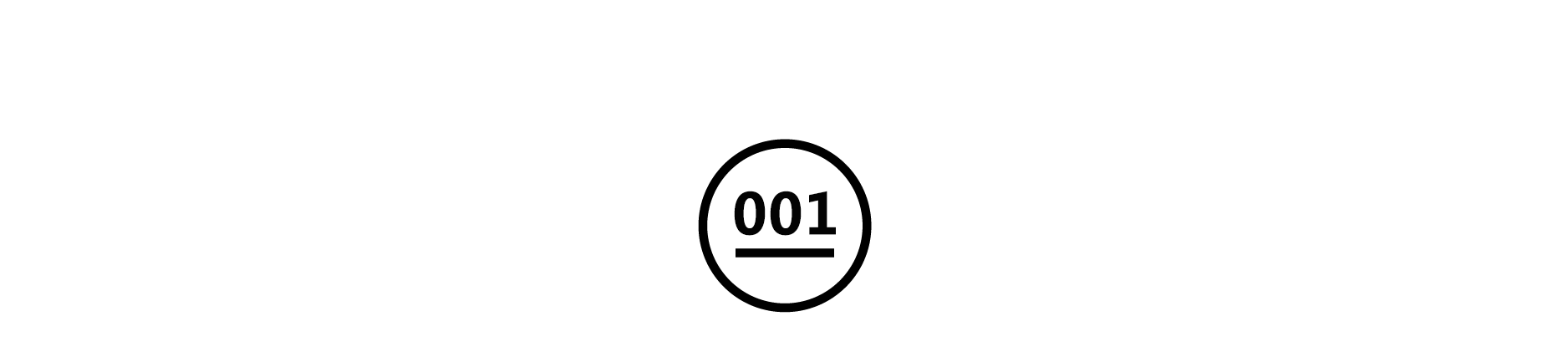
记忆中的年味
2023年的新年,是我结婚后在婆家的第一个新年,和老公大华以及他父母去海南新家过。我兴奋不已,计划直接“杀”到市场采年货,年夜饭我们自己回去做海鲜大餐。
大华却说不用那么麻烦,直接去饭店。他家过年毫无氛围:大扫除请钟点工,玻璃物业给擦,年夜饭全靠买,连人也不全乎——爸爸为了挣单位的“三工资”已经缺席好几个春节……
小区附近的四五家饭店的年夜饭都供不应求,大华大手一挥,点了“迎春接福”套餐,马鲛鱼、椰子鸡火锅、白灼花螺、比手还长的大角虾……全是鲜货,我山猪吃不了细糠,一个也吃不惯。回想起来,过年吃海鲜的记忆,只有我妈做的炸带鱼。刚炸出锅时外面蛋液面糊脆脆的,一咬下去还会发出滋滋的声音;带鱼点汤炖上绵软烂乎,香飘十里,一抿肉就化了,汤汁瞬间溢满口腔。

家里的炸带鱼
此时弟弟给我发微信:第一个你不在的新年,有点不习惯。我不知不觉就红了眼眶,我才惊觉原来习以为常的生活竟再也回不去了。
小时候过年是我和弟弟最盼望的事,一放寒假,我都会以最快的速度写完作业,再帮家里干活儿。我爸妈比较胖,眼不好,一爬高就头晕,家里擦玻璃、上房、扫院、抬上倒泔水,都是我们两个小的活儿,我们俩忙前忙后,村里谁见了都夸能干,心里乐开了花。
那时候过年我们还要自己做豆腐,冰天雪地,我蹬着自行车去奶奶家带新打的黄豆,回家后把瘪的烂的杂毛豆荚挑出来,交由我妈,她再带去麻将馆,放到沟南头张老二的车上。他好打麻将,但他家祖辈做豆腐。等豆腐做回来冒着热气儿,沉甸甸、肥塌塌的,直接放塑料硬桶里,搁在院角,凉夜里一直放着直至冻成硬砖头,吃的时候切上几刀,能储到过年。
二十三,灶王爷爷也上了天;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做豆腐……零几年的山西农村,我们仅遵着年节,越到年根儿,需要忙活的事情就越多。结伴去澡堂洗澡、找老姑父拿对联儿、问二妈家拿钱罐儿(对联儿上的五彩装饰)、还要去山上捡柴火,等到三十下午垒旺火。
整个腊月,我妈要置办从初一到十五接待亲戚的食材,一刻不能停。炸丸子、包饺子、炸油糕、蒸馒头、炖鸡腿,有一年还和我二妈一起买了个大猪头,找人压了吃猪头肉。不过,这里面的重头戏还是一年只吃一次的炸带鱼,这是北方人过年独特的集体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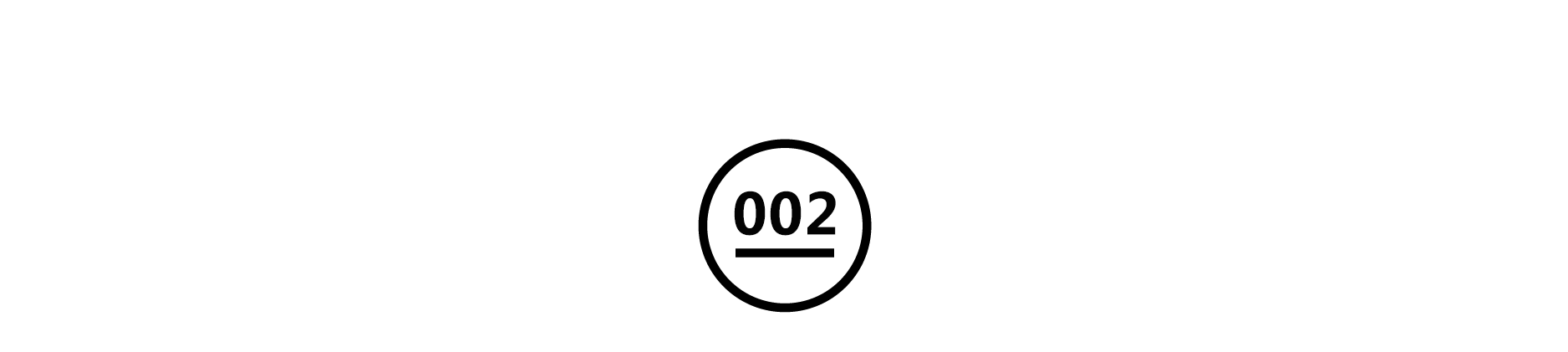
家家户户炸带鱼
带鱼似乎是天生为过年而生的食物,渔汛期大约从二十四节气的小雪开始,持续三个月左右,正好就是春节前后。这也是我小时候唯一接触的海鲜,只是我见到它的时候多是从东南沿海一代捕捞上岸,经历千里迢迢运输,来到我们村集会上时,早就冻成邦邦硬的鱼棍儿了。
腊月二十五以后会有一个礼拜天,这个礼拜天对全村人来说都很重要,是采购带鱼的日子。那时没有车,我爸骑上摩托,要把我家、我姑妈家、婶娘家的一并买齐,整整三四盒,一盒十来斤,绑在摩托车后座的钢架上,浩浩荡荡地送人。
带鱼对我们来说是硬通货,送亲戚准没错,但是却要包装好的。有一年我三舅单位发了不少,让我进城去取。我挤上11路,手里挂着十来斤鱼,怕人给挤坏了索性一手抓吊环一手搂着鱼。不一会儿我的手就感觉一阵热流粘手,原来是带鱼的獠牙把我刮破了,还把别人的衣裳给勾住了。即便如此,我们仍爱带鱼,这玩儿意儿不好放,要储在没有火炉的冷家里。趁大人不在,我和弟弟会拔出带鱼当刀剑开战,砍得满地冰碴子。
做带鱼的时候,每家都得放一天假,因为实在太麻烦了。我妈要烧上好几暖壶水,腾个洗衣裳的大铝盆,架起搓板,摆好带鱼,用钢擦把外面那层银色脂皮仔仔细细搓干净。一条十来分钟,洗好再流水线递给我爸,他胆子大,敢拿剪子豁开肚皮用大拇指把内脏刮出来。然后剪头、去尾、扔到清水盆里再洗一遍。半晌工夫,一箱能看见“全尸”的带鱼就变成待俎的鱼肉了。

切好的带鱼
切剁之后的腌制,最考验技艺。每家都有不同的配方,而我妈手生,做饭充满创意性,料酒、白酒、葱姜蒜料、陈醋、糖盐,各种材料都放一点,腌得能看见上色就开始准备挂面糊油炸。油炸她有秘方:淀粉和面勾芡的水糊糊里放几颗鸡蛋,这样能增加带鱼的香味和口感。
炸带鱼时烟大,冷锅热油,门帘得撩架在门上散味,一下锅,那滋滋作响的声音和飘出的香味,整条巷子都知道了。邻居美英大娘总会顺着信号来和我妈聊天,再尝下头锅带鱼给出专业点评。她家以前给人送液化气罐,条件不错,比我们常吃鱼,我妈总调侃“看人家美英多会活”。
我们两家关系很好,我妈不在时我爸就带我俩去大娘家蹭饭。过年也是,她家要炸带鱼,我妈也过去。我们就围在火炉前,捡着吃炸好的鸡蛋糊,脆脆的,像饼干一样,大人轰都轰不走,有时候被溅起来的油点烫了一下,疼得吱哇乱叫。我妈就说,“这下就歇心(安生)咧哇!”
炸好的带鱼两面金黄,在不锈钢大盆里堆得小山一样,各个饱满肉厚,像一个鼓囊囊的钱包夹子。我们只许吃一个解解馋,剩下要留着过年吃。带鱼刚出锅时很烫,端住两个小角小口一抽,一侧的鱼刺就出来了,我非得把鱼刺全捡出来才肯大口一咬,满当当的肉进了嘴里,外酥里嫩,有蛋香有鱼香,嘴角流油,别提多好吃了。而另一边的鱼刺,也被我剃得光溜溜,没挂一点残渣。整个过程里,我一句话也不说,神圣得就像进行某种仪式,而不是为了简单解馋。
这口吃完,就只能等过年了。

炸好的带鱼

农村里的大正月
年初一天还没亮,村里就被此起彼伏的炮声淹没了。我妈爬起来安顿我们穿好衣裳,随即做饭。我们那里年夜饭不隆重,反而是这顿年初一的接神饭无比神圣。饭边做,我爸边展大门,点旺火,放鞭炮通知天上神仙进门,来我家吃饭。
我和弟弟则在旁边玩儿小花炮,礼花、手举喷花、烟雾、各种小动物造型的旋转升空花,每点一个我都要跑进西厨房撩开门帘,喊做饭的妈妈快看。小手冻得通红,一说话全是哈气,也不嫌冷。玩累了我和弟弟就烤旺火站沾福气,有时候还会不小心把头发燎了。整个天空到处印着烟花,看也看不过来。
屋里满满一大桌子菜肴,要趁天亮前吃完,背景音乐是重播的春晚,我挑嘴,但带鱼和饺子必吃,寓意年年有余、团团圆圆。此刻的炸带鱼经过再回锅后已经没有了刚出锅时的干脆利落,多了一份温婉缠绵,一筷子夹起,腾着热气,里面渗满了汤汁,已经完全进化成了另一种食物,吸一口,满满鱼香……
吃不了几口就有小伙伴穿戴整齐来拜年了,我也被勾引着要出去。大街上满地鲜红的鞭炮纸屑能淹了鞋,空气中全是硫磺的味道,家家户户红彤彤,旺火架得大的人家还没烧完。我们挨门挨户串挣压岁钱,我表弟鬼点子多,去孤寡老人“贵小爷爷”家拜年,带上帽子进去挣了一块钱,脱了帽子又挣了一块。

小时候长大的院子
从初一到十五,我们要每天走不同的亲戚,隔几天又轮流做东,一起两大桌子,男人一桌,女人小孩一桌,四五十个盘子重重叠叠。人类的活动促成大山大海之间食物的聚合,食物的流转也调动人类的聚散。鱼一般是压轴菜,一上来就能看出这家女人的烧菜手艺。
带鱼是海洋给平民的馈赠,量大、肉美、营养高,还适合各种操弄。我们的鱼都是带鱼,有些人家炸好放冰箱冷藏,再拿出来还能有鲜脆口感;有些人家直接炖,烂乎乎的夹不起来;我大姑喜欢把带鱼烩在杂菜中,等大家在吃菜时寻到惊喜。我们也会比谁剃的最干净,我和我二表姐总是冠军。
所有带鱼的做法中,我最喜欢的是表哥的烧带鱼。他是乡厨,常年跑南郊的流动饭店。每年去他家吃饭总有种蹭馆子的享受。表哥烧带鱼用干辣椒煸炒,出香味了煨高汤焖出浓郁的鱼汁儿。吃饺子我不喜欢蘸醋,拿鱼汁当佐料有别样风味。我表嫂是河南人,喜欢吃馍。他家宴席上还有大馒头,用馒头蘸碗底的鱼汁,我能把盘子擦得干干净净。剩下的带鱼吃时一蒸,又是美美一餐。这些是鱼的味道,年的味道,也是人情的味道。
下午大人们就上了麻将桌,小孩子满口袋新钞票进了小卖铺,从未有过的富足。我们买摔炮、洋片、泡泡糖和辣条,当然,也要提防大一点的哥哥来骗你钱。幸运的话,他诈了你的钱还会带你去网吧潇洒一把,登录他的账号耍一下跑跑卡丁车,能高兴一下午。
整个正月,全村都沉浸在喜悦当中。大人们能好好歇歇,孩子们无尽疯玩儿。要是压岁钱上交了手头没钱,胆子大的还会闯入陌生人家拜年,有幸也能挣点。等到初十村里准备闹元宵报名,我们总央求父母给自己报,凡是报名都能给家里挣上床被子、电饭锅、电饼铛,学生娃娃还有新书包。从没觉得自己这么有本事过,无比自豪。
这样的年节从我出生到十五六岁,每隔265天就上演,我们永远过不腻。不过,随着2014年棚改开始,过去的岁月全都和炸带鱼一起,留在了回忆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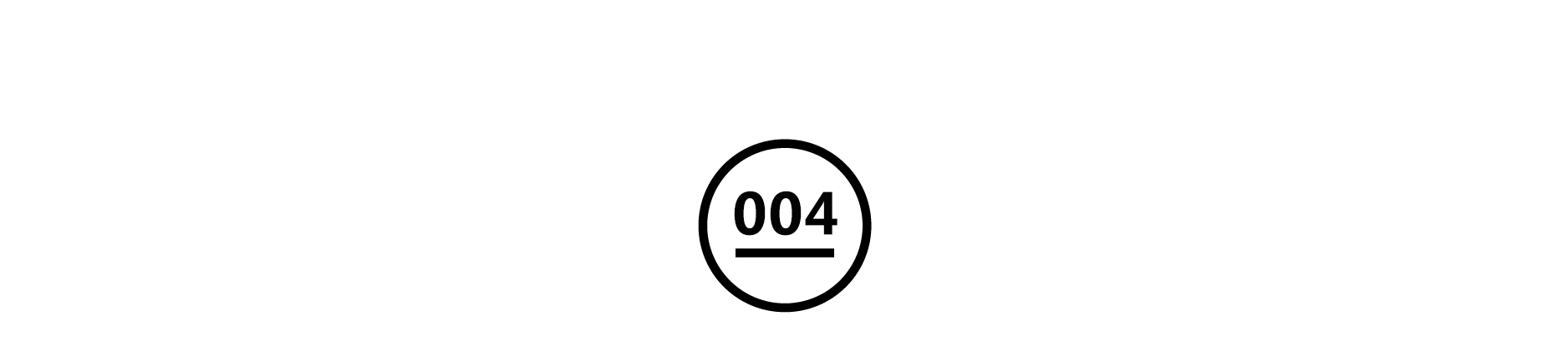
回不去的乡愁
2014年我正好高三,我们市浩浩荡荡的城镇浪潮袭来,原来的城区要扩大一倍。为了修建一条机场快速路和拓宽原先的国道,身在县乡连接点的我们村大半得搬迁至新修建的村集体新楼。
我家离大马路还有段距离,没赶上这泼天的富贵。我妈一边羡慕人家算下不少钱,一边又替他们没了老院子而可惜。在村里,最理想的状态是冬天能上楼取暖,夏天能回村避暑。后来我们不少人家都实现了。按照村里每人12.5平米的福利补偿,家里只要添十来万都能住上小产权楼房,那几年村民们陆续上了楼。
而美英大娘家,却因为给她看病花光了积蓄,独留在村里。6月份的夏天,我高考前回家,在巷口看见拉棺材的板车和很多人,一回家看见边缝十字绣边泣不成声的妈妈,才知道美英大娘走了。肝癌,从发现到人没只用了半年。半年前正好快过年,她在家做牛肉,炸带鱼,好好的突然吐了一口血。去医院检查我们只当是小毛病,还等着回来吃她做的鱼,没想到一住院就住了几个月。
后来我去广东上大学、工作,又出了国。一年回来一两次,也都待在小区,很少再回村里。听妈妈说,美英大娘走后,我们那条巷子再也没有热闹过。邻居们都离开了,只剩二保大爷(美英老公)每天在院子里放个收音机解闷,家不成个家,她看见都唏嘘不已。
而我妈自己身体也不好,前两年做了肝囊肿手术、痔疮手术后,无心操劳,家里过年也变得糊弄。买点串串灯,只贴一张对联。吃上也简单,买一大堆火锅食材,谁来也带你们涮锅子。至于带鱼这种复杂菜式,她兴致起来了弄下,大部分时候我只能去大姑家解解馋。这样想来,没有年味的家好像和大华家也区别不大。

海南沙滩上放烟花
海南年夜饭吃完,我和大华在沙滩上漫步,有人弹吉他,有人围放烟花,还有人用手机和老家人视频,听到有个东北口音的大姐说“这儿过年和咱老家完全不同,真想带你们一块儿过来!”是啊,我哪有想过穿着裙子、吃着新鲜海鲜过年,回想小时候竟感觉像上辈子一样遥远。
看着漫天烟花,闻着空气里的硫磺味,我和大华一致认为,这才是年味儿。

海报设计 白浪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