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被取悦者到带货偶像:女性消费品广告中的男性形象变迁
“双十一”电商促销活动让国内的互联网生活热闹得有如“淘莱坞”,从电商促销页面到社交网络平台,到处是大明星小偶像给各种品牌做宣传的忙碌身影。明星宣传年年有,今年嫩男特别多——越来越多的以女性为主要消费群体的商品起用男性明星偶像宣传推广代言。
上世纪九十年至今,女性消费品广告中的男性逐渐从抽象的性别符号逐渐转变为更加具象的、商品化的推销员形象,推销的范围逐渐缩小,最后集中在名为粉丝的一小部分群体身上。推动这个演变过程的是名为资本的无形大手,一只负责生产过剩商品,一只负责绑架粉丝为泡沫市场买单。

穿华丽的服装,为原始的渴望而站着
出现在女性消费品广告中的男性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女性取悦的对象;一类是女性的取悦者;第三类则是在广告中扮演男友角色的大明星小偶像。
奢侈品广告中的男模特长期扮演着女性取悦对象的角色。男性形象频繁、大量地以女装、配饰等为展示核心的广告中,充当支配者和审视者。广告中的女性身体裸露程度较男性更高,姿态妖娆,眼神迷离鲜有聚焦、神态富于挑逗性,在整体构图中处于下方,人物关系中处于被支配地位。许多广告中,女模特的姿势决定了她们需要仰赖男模特的支撑获得平衡,女性对男性的依赖与可支配性通过简明的视觉呈现变得一目了然。

这种充满性暗示的广告在商业上十分奏效。以古驰(GUCCI)为例,1994年美国设计师汤姆·福德接手这个意大利奢侈品品牌时,它负债累累、岌岌可危,采取性暗示广告策略后的第二年,收益增长了90%,到2004年汤姆·福德离开时,这个一度赤字的品牌已经成为资产上百亿的国际一线大牌。汤姆·福德离任同年加入法国奢侈品品牌伊夫·圣罗兰,品牌广告策略仍延续古驰时期的性暗示风格,商业收益同样可观。为了追逐商业利益,其他奢侈品品牌也相继结合自身定位效仿这种广告模式。香奈儿、路易威登等不以性感形象为主营路线的品牌,广告中的女性仍然被窥伺、被支配、衣着也更加暴露。
然而,美国伊利诺伊大学2017年的相关研究表明,性暗示并不直接带动销量,但包含色情、暴力内容的广告更博眼球。奢侈品广告中的性暗示成分成功地塑造了品牌特质:极尽奢华、爱欲横流、风骚撩人。这类广告以“女性是取悦男性的被窥视对象”为出发点,意在通过创造一种光鲜亮丽、异常浪漫的场景重塑女性消费者的自我认知,即借助穿妆彰显自身魅力,而魅力的集中体现则在于吸引男性、得到男性的垂青以及征服男性。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就有文化学者针对广告中的性别问题展开批评,然而直到2015年左右奢侈品广告中借助男性完成性暗示的风潮才有所遏制。除了饱受文化界人士批评外,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次信贷危机导致的经济不景气迟迟未出现转机,以欲望为原动力的奢靡的过度消费风潮疲软,新一轮女性主义运动酝酿中,女性消费者对那些为博眼球不断探底裸露尺度的广告感到厌倦嫌恶。即便如此,一些走下坡路的奢侈品品牌为了扩大品牌效应仍然没有放弃“窥视女性”的广告策略,在2016年秋冬广告中,美国网红模特Gigi Hadid仍然重复着十年前前辈的故事。

建立性别符号但不以客体化女性为目的的广告亦有之,男性在其中不再是被取悦者,而是要竭尽所能博得潜在对象的欢心。例如2010年九月由加拿大多伦多广告商为卫生巾品牌娇爽(staryfree)拍摄的系列广告。该系列三则广告的主角是三个精壮的、具有专业人士身份的白人男性,广告开场便脱去上身衣物赤膊上阵做家务,之后切入主题用娇爽卫生巾与其他匿名产品做比较,得出该品牌吸附量更大、效果更好的结论。
这款广告尽管在创意上具有突破性,但制作非常粗糙。它试图通过塑造理想顾家的男性形象,取悦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事业型独立女性,却因手段拙劣、表达露骨成为舆论媒体批评的对象。观众甚至发现广告中所谓“医学博士”的证书墙上有认知障碍患者教育机构的毕业证书,精壮裸男卫生巾广告很快沦为笑柄。但在家居、女性个人护理等消费品广告中,贴心顾家男的形象仍然屡见不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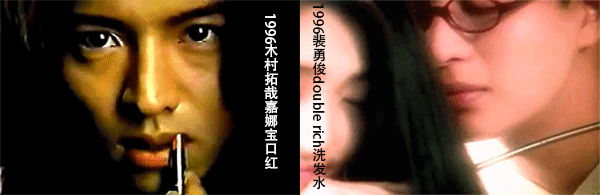
当代人最熟悉的是在广告中模拟男朋友的演艺明星。在东亚,这种模式最早可以追溯至1996年日本偶像组合SMAP成员木村拓哉为日本品牌嘉娜宝(kanebo)口红做广告。木村拓哉是年首次担当富士电视台招牌月九档主演,《悠长的假期》收视率火爆,是当之无愧的当红小生。嘉娜宝口红广告一式两款,背景音乐使用SMAP当年2月推出的单曲《胸さわぎを頼むよ》的高潮部分,歌词大意是“拜托不要停止我内心的骚动”。一则广告中,木村拓哉先是给自己涂口红,再给不露脸的女模特涂;另一则以睡眼惺忪的木村拓哉开场,镜头拉远出现不露脸的女模特涂口红,两则中木村拓哉和女模特都在模拟情侣亲密关系。广告播出后,嘉娜宝口红两个月卖出三百万支,成为绝对爆款。
1996年起,韩国女用洗发水品牌也开始起用安在旭、裴勇俊等男明星在广告中扮演男朋友的角色,1997年裴勇俊出演的韩国个人护理品牌“水果之乡”广告则更为直白,将皮肤好的女性描述为理想型后开始推荐产品。从此,韩国男明星以理想男友形象出现在为女性消费品做广告中开始成为一种新的常规手段。随着“韩流”在亚洲地区的进一步扩散,尤其是2013年以后若干韩国偶像剧在中国成为热门,李敏镐、金秀贤、宋仲基等一度被奉为“国民老公”的韩国男性带动了韩国女性消费品品牌在中国的商业成功,国内外品牌在华纷纷效仿这种模式,起用中国男星推广女性消费品。
眼下的男性大明星小偶像仍然延续着九十年代日韩男星在广告中假扮理想男友的角色设计,但在实际的商业策略上大相径庭。九十年代的木村拓哉、裴勇俊是名副其实的国民明星,几年前的金秀贤、宋仲基也有现象级电视剧作为人气支撑,但眼下中国女性消费品广告中的男性不同,他们的影响力和知名度都十分有限,许多只能仰赖粉丝爱的供养。
除了你以外,还能倚赖哪一个
2014年“小鲜肉”成为舆论热词的同时,男明星/偶像也开始成为女性时尚刊物封面、女性消费品广告上的常客,且出现频率和数量逐年递增。仅2018年上半年就有十八个女性护肤彩妆品牌起用男性明星/偶像为品牌宣传造势,这些年轻的面孔对于公众显得十分陌生,他们的出现既不能为品牌的优越性背书、也不能扩大品牌的知名度,只是单纯为了搭建起品牌利用粉丝经济的桥梁。
“双十一”活动开启前后,某品牌美发洗护产品线起用因主演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而人气大涨的青年男演员邓伦担任“品牌大使”,制定了五步流程,每步需要以消费者完成一定的购买量或者提高商品舆论热度,回报是邓伦为品牌拍摄的主题广告。由于没有实现店铺十万粉丝关注的目标,品牌通过微博宣布阶段任务失败。“公开处刑”引发了邓伦粉丝不满,品牌方很快删除了“宣布失败”的微博。今年的营销大战中,类似事件不是孤例。

国内广告商开始仿照“韩流”模式时,快速发展的互联网已经推动社会进入分众时代,娱乐文化领域几乎无法生产出“国民级”的明星。与此相映成趣的是粉丝群体的快速成长,韩国式粉丝应援机制先韩国式偶像运营机制一步进入中国,并为国内的演员、歌手的粉丝群体所继受。2017年8月,杨洋粉丝为电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锁场”事件暴露了粉丝经济的弊端,然而事件虽为社会广泛热议且评价趋于负面,却没有冷却粉丝的消费热情,也没能转移资本对粉丝经济的注意力。随着国产影视行业寒流过境,文化商品消费空窗期的出现反而为资本利用粉丝经济激活增长迟滞的消费品市场提供机会。
今年春夏《偶像练习生》、《创造101》两档偶像养成网络综艺的火爆让国内原本自发组织形成的粉丝应援活动和资本的关系更加紧密。由于国内缺乏完整的偶像产业链条,凭空出现的小偶像不得不在混乱的资本游戏中野蛮生长。任何一种游戏都需要资本,在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看来,资本总是在特定的场域中有效,既充当武器又是斗争的利害所在。明星偶像的人气指数、“带货能力”都被纳入资本游戏,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需要粉丝付出真金白银刷数据。数据不理想不仅会使粉丝群体在与其他粉丝群体的比拼较量中落于下风,更可能直接遭到来自品牌方的嘲讽。随着影视行业税收政策收紧,商业代言成为明星偶像们攫取商业利益的兵家必争之地,而明星偶像在圈层中所处的位置反过来又决定了粉丝群体所处的位置,依照布尔迪厄社会阶层划分与文化资本分配具有连贯性的观点看来,追星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情感付出,更有追逐文化资本的意味在里面。
无论是演员、歌手、愈发职业化的本土偶像还是粉丝,需要的都不是一组组大量注水的数据和某些大众并不关心的榜单,而是拿得出手的作品。只有天性热衷于制造过剩需求、生产冗余的资本需要这些数据泡沫,为此资本不惜通过绑架偶像、扭曲爱与喜欢的意义来胁迫粉丝,通过构建一个虚拟的战场来制造紧张空气迫使粉丝相信“和哥哥有缘,全得靠掏钱”的规则,将粉丝消费意愿转化为消化过剩生产的过程,从而将为爱追星的粉丝变成资本的奴隶。
处于链条下游的粉丝并非对被奴役的处境毫无知觉,然而粉丝的反抗大多是短暂的、零散的,严重分化的粉丝群体也无法因为共同的利益联合起来改变游戏规则。资本制造的虚拟的明星偶像焦灼的竞争局面使得粉丝忙于行动无暇思考。在布尔迪厄看来,行动者在实践中并不会充分考虑自己所处的情境,不管这种考虑表现为某种自理的理性算计还是对于某种规则的遵从。一些行动能够在事后被问及动机时提供某种解释,但这种解释未必是行动的真实逻辑,而往往只是一种事后分析。观察任何一个粉丝群体的“业绩宣传”都不难发现,粉丝的事后分析仍然沿用资本提供的逻辑。这意味着,资本将粉丝经济“薅成葛优”之前,恐难停止薅毛纺线的进程。
在这场纯粹的资本游戏中,受众范围有限、对象更为明确的男明星/偶像仍然在广告中致力于模拟情侣关系中的情感体验,这种虚情假意的表演只有在粉丝的阐释下才能升华成真情实感,它暴露了消费主义文化的浅薄和低级:浅显易懂、轻松易得。资本支撑的消费主义文化已经懒得通过构建文化符号进行间接奴役,它从贩售廉价情感中得到了真金白银的甜头,察觉到扩大受众的工作显然要比圈养奴隶更加辛苦,尽管现实生活中的哥哥应有尽有,但在资本眼中,“哥哥就只有粉丝”了。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