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活动回顾丨龚万莹×金理×陈嫣婧:闽南之南是永不陷落的故乡
闽南之南,有捎带着潮气的温热的风,有暴雨夜轰然倒塌的老厝,有散发清香的芒果树,有神秘的皇帝鱼......众生永不陷落的故乡潜伏在生命暗流的记忆中,时代喧嚣的入侵改变了许多事,岛民的命运相互交织,悼亡的迷雾与明日的微光恒久如常地同时降临。
1月13日,鼓浪屿岛民龚万莹携首部小说集《岛屿的厝》与《岛屿的厝》责编王辉城、教授金理,以及青年评论家陈嫣婧在上海上生新所茑屋书店,畅聊从外企高管到作家的职业转变、成长中不同人格对写作的帮助、写作中真实与虚构的距离感、方言在写作中的妙用等话题,向我们展示了岛屿女孩的成长时光簿和一幅活色生香的闽南风情画卷。
【活动回顾】
王辉城:《岛屿的厝》是青年作家龚万莹的新书,也是我工作遇到的第一本书。我拿到稿子时非常惊喜,脑中就突然进来了“这个作者会非常了不起,她会拿到不少的奖项”的念想,果然2023年底的时候,她的小说《出山》入围了小说排行榜。所以我觉得她的第一本书会收获非常多的认可。

现场照片
01 | 从外企高管到作家,龚万莹的第一部小说值得细细品读
龚万莹:我2012年在静安寺一栋很豪华的大楼里面工作,在外企和国外都待过一阵,但心里一直觉得写作是我比较想做的事情。我在公司里做的最后一场商业活动花了大概500万,结果我现在这场活动花了不到500块,这两个行业实在是差别太大了:一个行业很有钱,一个行业很朴素。但在外企里学到很多时间管理、艰苦奋斗的这些东西,对我的写作都有帮助。
王辉城:请介绍一下这本书《岛屿的厝》,这个“厝”是什么意思?
龚万莹:我很担心《岛屿的厝》这个名字会耽误我卖书,第四个字本身就是闽南的一个生僻字,叫做cuò,闽南语叫做cǔ,它的意思是房子,岛屿的“厝”意思就是岛上的房子。这本书主要是讲了9个故事,有中篇,也有短篇。这9篇故事里面的人物是互相交错在一起的。

闽南古厝|图片来源网络
陈嫣婧:我对龚万莹的好奇有这么几点。第一点是她是87年的,如果大家关心当代小说的走向,会发现90、95后已经出了作品集,很多时85后已经被看成是前浪,龚万莹现在才出了第一本小说集。第二个点是她是福大毕业的,我是福师大毕业的。我们两个人读本科时就在同一个大学城,其实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是有交集的。福州大学是以工科和商科最出名,然后她本人也从事和文学没有任何关系的市场工作。到了人生的节点上,坚决地辞掉外企的工作,去做文学创作这样一个说实话没有很多物质回报,看上去没有前途的事情。我带着这样的好奇去读她的作品。
陈嫣婧:我觉得龚万莹的小说不是现在很年轻作家所追求的在形式上要求很先锋,或者在想法上很与时俱进的作品。她的作品和她的人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当下的文化氛围和文学创作的主流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她不是写那种第一秒钟就很吸引人的小说,或者马上就能让你看到所谓先锋性的东西。所以我反而觉得挺独特的,这是我的初步印象。
金理:我与黑伞情况一样,一开始确实是辉城大力推荐。当时我受邀写过《收获》的综述,所以读了龚万莹的小说。我觉得这个小说确实像黑伞刚才所讲的,不会是那种一下子特别出挑的类型。《岛屿的厝》蛮多的第一人称叙述,也是在写自己的家乡,以少女的口吻叙述。所以初看上去会让人觉得是一部青春文学、成长小说。但是读完整部小说以后,我觉得这部小说其实蛮有难度的,是要分析的。
金理:比如《鲸路》我觉得是写一个女性沉浸在创伤当中,但是最后她有了一条新生的路。《鲸路》这个标题也起得蛮好,后面有一个震撼的情节——那条鲸鱼爆炸了,鲸鱼体内的血就像雨一样,从天空中降落下来,形成血路。女主人公的新生之旅,如何从这个创伤中走出来,是通过鲸爆形成的奇观反应的。里面写到一句话,“天空中下起了鲜红血雨,宝如的头面都被血浇透了”。大家可以想一想这样的场面:鲸爆这样的奇观,降下了一场鲜红色的血雨,血雨浇在此前沉浸在创伤中难以自拔的女主人公的身上、头上、脸上。这样一段之后,她又写了这样一句,“血路跨过沙滩,绵延到海里,此时,有白色的海豚跃出海洋,一面面旋转的白色旗幔”,这时候她写到海豚跃出海洋,这一笔是非常打动我的,这让我感觉到与青春文学不太一样的包容性。

鲸跃出海面 | 图片来源于网络
金理:我心目中青春文学比较擅长在一个点上发力,而成熟的文学的感官完全是敞开的,关注到了人类经验的明暗交织和辩证转化的关系。《鲸路》中第一个细节是讲鲸爆所形成的血雨,血雨是从天空中降下来的。然后她又写海豚、白色的海。这之中其实有很多对比,一个是颜色,前面红颜色的血雨和后面白色的海豚。还有一个下降和上升的对比,雨是从天空中降下来的,但是海豚是跃出海面是往上升的。女主人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她一定是挣扎地、蹒跚地。但是海豚跃出海洋的律动站出现了衰亡与生机的张力。这是领悟生死之间互相辩证转化的画面,所以我觉得《岛屿的厝》超脱于一般的青春文学。
金理:第二点是这个作品叙述者经常会是一个小女孩。但是这个“我”是立体的,其实当中包容了两个“我”,第一篇小说中的小女孩鹭禾有一个很调皮的表哥,他喜欢把那种小昆虫、小蛾子、小蚊子拿到电蚊香上去烤。她讲了细节之后,就说“她表哥后来长大了以后开餐馆,他的天赋大概从小的时候已经显露出来了”,这句话其实有点幽默的,但是也透露给我们一个信息,叙述者也已经知道了后来的事情,她不只是一个在成长现场的小女孩,她其实已经知道了未来所发生的这些若干事情。这个小说中的叙述者,其实它包含了两个“我”,一个是一步步走向未来的“我”,还有一个“我”已经有后见之明了,她已经完全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金理:这个小说虽然像青春小说一样经常采取第一人称,但其实里面包含了比较困难的处理的两个“我”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个是最考验作家的地方:一方面你需要有一个成长过后的“我”来对成长过程的我进行某种审视,甚至节制,但同时你又不能过度地去干涉还在成长过程中的“我”。
金理:论语当中有一句话叫“绘事后素”。对这句话的解释我比较信服的版本是,一张纸上用各种各样的颜色涂,涂完之后最后你会归到素白、纯白,但是这种绘事后素的“素”,跟本来无一物的“白”是不一样的。你已经过尽千帆,已经遍尝百味之后再恢复到白,跟一个小孩子真的是心里面没有什么东西的那种白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我要说的是这两种白都好的。小说中既保持了一个少女在成长现场的那种实际的感受,有一个旁观者,对当年的“我“进行打量、审视、甚至是自我限制,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我提供刚才两个细节来表达,《岛屿的厝》有青春小说的外貌,但其实是一部有难度的小说。
02 | 人生不同的阶段中会出现许多人格
龚万莹:我作为一个写作者,从来都是自己写东西,2021年之前我的小说从来没有在期刊上发表过,所以我一直没有想过批评家是怎样去看一个小说的。9m88有一首歌叫作《九头身日奈》,这首歌的意思就是每一个女生的身体里面有九个女孩,然后这九个女孩都有不同的个性。

9m88的《九头身日奈》专辑封面|图片来源网络
龚万莹:我在18岁以前,在鼓浪屿上面没有人叫我龚万莹,通常家里人都是叫我阿莹。所以阿莹可能是在岛屿上面很快乐的一个人格。但是到18岁,出国读书,再到来上海,我的朋友们和爸妈都叫我Liz,这个人格是被学校和公司体制教育出来的一个人。30岁之后我发现突然间出现了另外一个人格,一个颓丧的中年人。我以龚万莹这个名字开始写作的时候,就感觉这件事情严重了,我开始真正要面对自己的生命的全部,但是与此同时,在写作中的小孩又活过来,这是作为作者本身的人格。
龚万莹:我觉得很多人身上就是九头身日奈,不只有一个性格、一个人,而是好几个人同时在你的身上。现在我在应对大家的时候,Liz的性格就会跳出来,就假装自己很会说话之类的,但其实内心小女孩早就已经跑掉了。再到写作的人格里面,刚才金理老师也讲到说有一个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其实在写作的时候有意识地会发现自己有些时候用第一人称写文章会更顺,而有些时候用第三人称文章会更好推进。比如说《出山》,我来回从第一人称改到第三人称,再改回来,来回切了五遍,我才找到合适的那个人称。
龚万莹:当我想把内心的戏剧张力喷薄而出的时候,我用第一人称会更加的顺手。文学有一件很美妙的事情,就是我们作为人是有一个线性时间不断的在向前的,在《浓雾戏台》里,我练习写一个小男孩;到《菜市钟声》的时候,我学着写中年人;然后再到《出山》的时候,我学着去看老年人的思维。有趣的是,当我把这些年龄段人都写完了之后他们同时的存在在我的世界里,因为在文学的世界里,这些角色不存在线性时间,这些角色可以在作者的脑中同时存在,并且我可以同时将他们召唤出来。一旦我把他们塑造完成之后,我觉得这是写作给我一个的非常快乐、奇妙的体验,在写作当中的时间可以从这些人身上抽离,小孩一直是小孩的状态,中年人是中年人的状态,他们可以并存,你可以体验很多的性别与不同的年龄,所以我觉得这是写作给最美妙的感觉。

现场照片
龚万莹:我也没有想到大家对我的好奇是为什么我会在18年辞职,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已经是6年前的事情了,我的船已经离岛了,所以我很少去想这件事情。我知道市场营销是一个非常棒的工作,也看过整个行业里最顶尖的人,我在外企这么多年,虽然发展也非常顺利,但是我逐渐感觉到我是一只在奋力耕地的梅花鹿。我每个同事和老板是如此矫健,好像一头公牛,他们可以耕地,然后有按时的土产,可以让他们饱足。我作为一只梅花鹿,我也要和他们一样,撸起袖子加油干。这个过程中,我去参加了一些写作课,遇到了一群同样很有创意的朋友,不管在伦敦还是其他地方,我一直遇到这样的朋友,一次又一次确认中,我突然就意识到我已经遇到了另外一群梅花鹿。我不能够再假装我自己是一只耕牛了,我只能奋力一跃,从有固定土产的这一块田地跳出去,跳到未知的森林里面。
龚万莹:梅花鹿吃的东西是没有固定的产出,小蹄子也不一定能够给果树带来什么样的帮助。你可能只能在林子里穿行,然后捡到一些小果子,你可以吃,或许会饥一顿饱一顿,可是你终于发现你是一只梅花鹿,并且不愿意再否认了,所以所以其实辞职的过程是很自然而然的。我是大部分时候是一个理性的人,可是在某一个时刻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感性会帮助你做信心的一跃,这一跃之后世界就不再一样了。
03 | 真实与虚构之间的距离给小说带来新的生命
王辉城:刚刚万莹回答了她为什么要写作,她把朴素的文学创作比喻成了很浪漫的梅花鹿刨地。我觉得听她一讲,或许文学创作真的不那么辛苦。她这段话是特别让我想起了王小波的一句话,“文学是一条光荣的荆棘路,它又苦但是又光荣”。接下来的问题我想问一下黑伞。龚万莹小说里的福建、闽南跟你的记忆中的闽南有相重合的地方,或者有差别吗?
陈嫣婧:我是上海人,生养在上海,但是我大学是在福建师范大学读中文系,可以说福建是我第二个故乡。其实很多时候,无论是搞文学评论还是搞创作的人,我们都会非常珍惜一个东西,就是距离。她有一种纵深感,这种纵深感是一个你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的人所不能够表现出来的,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产生文学性的一个东西。所谓的文学性在我来看,其实是一种距离。一个文学纯度越高、文学性越强的作品,它的作者跟它的文本之间的距离是处理是越好的,处理得越好就越有文学性。龚万莹的作品就是非常成熟的,如果说你愿意从文本的角度,从内部去挖掘它,你就能够看到文本本身的价值和文学性。
陈嫣婧:我刚才在翻这个目录,我发现这部小说你从她的每一个小说的意象当中,都可以感受到她对于文本的把握,她基本上每一篇小说都有一个核心意象,比如第一个小说叫《大厝雨暝》,老房子就是她的意象,《浮梦芒果树》芒果树就是她的意象,然后像《夜海皇帝鱼》,皇帝鱼就是她的意象,皇帝鱼看上去只有半条鱼一样扁,这个鱼是它的意象。《浓雾戏台》里面出现的莲花是它的意象,《菜市钟声》时钟是它的意象,然后《出山》,其实就是出殡”的意思,出殡就是它的意象。一个作家在小说叙事过程当中对核心意象的把握,一个创作者对意象的把握越好,这说明的不是她的想象力,而是她的概括力。我觉得她对意象能够挖得越深,展现得越好,说明她对于文本的概括力就越强。她站在文本之外去看她所写的世界,她对她所写的世界有一种掌控力,这就决定了她对意象的挖掘程度。
陈嫣婧:第二点,我觉得这本书在结构上有点像《都柏林人》。我觉得是这样,她的每一篇小说,其实人物会在另外一篇小说里面会出现。有一些人物在这个小说里面是主人公,到了那边就变成了一个配角,在这篇小说里面是配角的,在那边成为了一个主人公。在第一篇里面是小孩的,到了第三、第四篇小说,她成长成为了少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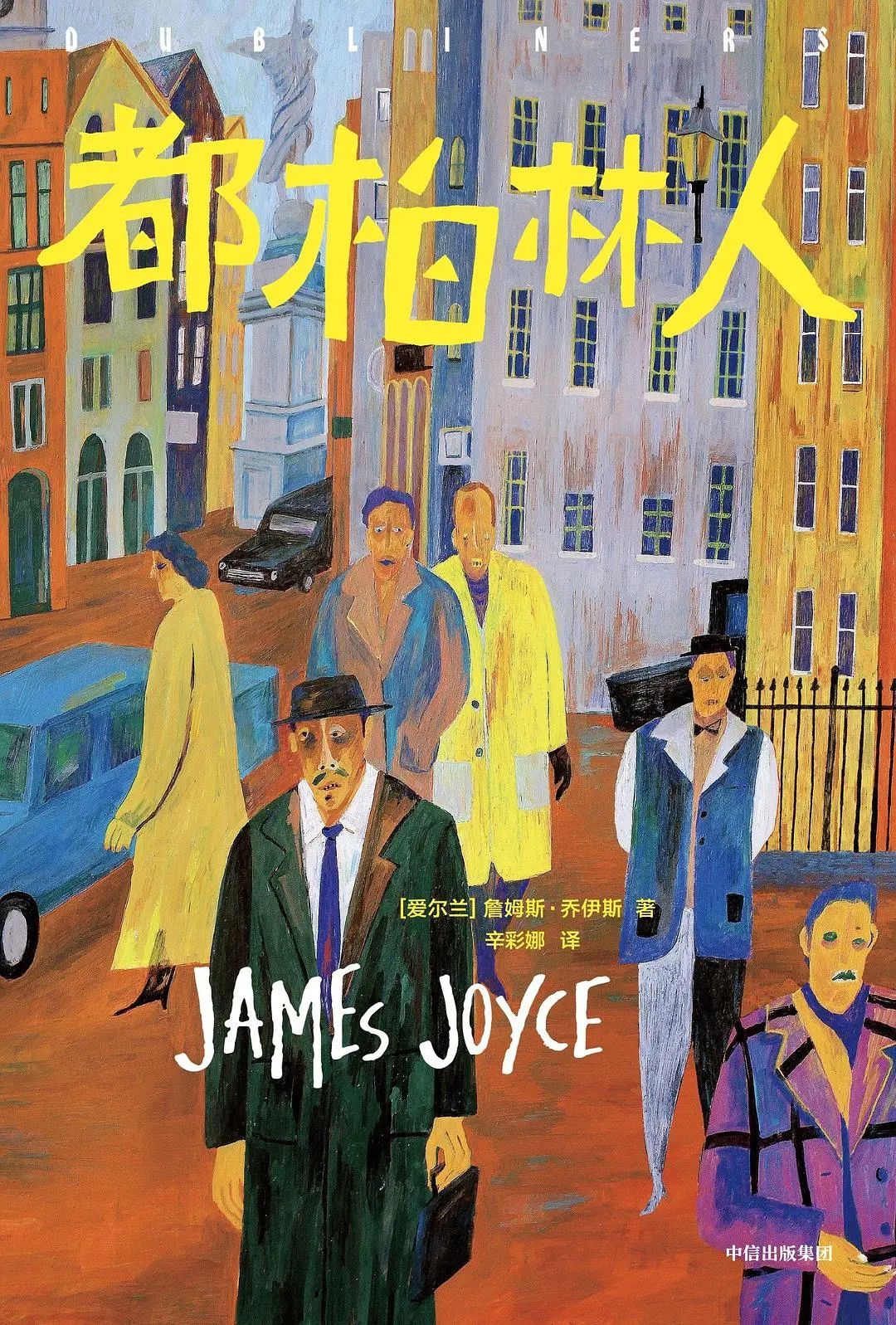
《都柏林人》书封 | 图片来源于网络
陈嫣婧:其实整个的小说的集合的结构,并不是一篇篇独立的中短篇小说合起来。整个小说的结构是有一个整体性的。她笔下的鼓浪屿不是真实的鼓浪屿,她笔下的鼓浪屿、这样一片土地给她的小说的结构带来了一种生命。它已经不再是现实当中的鼓浪屿,我08年第一次去鼓浪屿的时候,其实和她小时候的鼓浪屿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现在更加没有关系了,已经完全商业化了。我们游客走到的那个地方肯定也跟她小说里面的鼓浪屿千差万别。
陈嫣婧:你进入文本的时候,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了文本里的一个空间。它已经不是真实的空间了,是有距离的。距离产生美,作为现在的龚万莹去写的她从小生活的地方的人和事,包括空间上、时间上的这种距离,我觉得是她小说产生文学性的基础。如果没有这种距离,没有对这种距离感的把握,我觉得她的作品就把控不好。所以在这个程度上说,其实所有的文学创作,从现实的角度来讲,都是后置的,肯定都是在现实发生的事情之后的。创作会重新给予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一种新的生命,就可以看到能够把生命演绎到什么样的程度——鲜活度也好,深度、广度也好,不是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再写一遍,就能够写得好的,可能恰恰是写不好的。后面有很多作者的巧思在里面,它恰恰是一种有距离的凝视。这种有距离的凝视,然后一种更新,而不是一种重现,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把握龚万莹的小说,首先要和真实的背景有一定的距离才可以。
龚万莹:非常感谢黑伞刚刚讲到的虚构岛屿的概念。很多人读了我的作品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读者有些时候会把小说里的人物往作者身上对比。其实我自己比较自信地说一句,小说里每一篇故事都是我编的,包括里面所有的地点。我不想写一个完全按照鼓浪屿,甚至是过去的鼓浪屿的故事。在我的心里面虚构就应该是虚构,而不是写我的回忆录。
龚万莹:所以即使是第一本书,我也不认为应该把我的经验进行一个完完全全的还原。我很同意北师大张柠老师说过,“我们作者的记忆是一颗酵,能让一团面团全部都发起来”。但是作为一个好的写作者,不应该干嚼酵母,也就是说,我不能够对我过往的经历进行一个断层式的开采。比如说《大厝雨暝》里面会讲到一个老宅,然后老宅倒塌、妈妈跟奶奶吵架,这种东西都是我从未经历过的。三年前我住在苏州河旁边,每天晚上都有非常多老爷叔沿着苏州河锻炼身体,我就跟着他们一起在走,然后天气很热,我就想去买一根珍奶棒冰,走去711的时候突然下大雨,雨打到地板上,起来一个潮湿的味道。我闻到那个味道之后,脑中突然就出现了一个景象,一座老宅,而且我是从上帝视角从上往下看,看到里面有人。但是我从小没有在闽南老宅居住的经验,所以我还特意去请教了一位台湾的建筑师,我就问他几进、几个户厝,究竟架构是怎么样,住在哪里的人地位为尊,因为我要安排这几个爸妈、奶奶住的位置。把这些都安排好了,故事就自动上演。

《苏州河》电影剧照| 图片来源于网络
龚万莹:我知道我之前写的小说可能能力有限,但是在我写出《大厝雨暝》之后,我突然间发现这是一个有气味的东西,一个活的东西,就像杜夫海纳说的,“它是一个活物、一片森林”,森林是以它的氛围被人感知到的,树木会影响我们看到森林。所以我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先感受到的是它的氛围,然后我就知道我要写一个潮湿的东西,我希望别人在读完之后他的面庞、他的指尖能够留下一些湿度。我就带着这个感觉就开始去写,奇妙的是从这里去衍生出来了整座岛屿的故事,而且虚构的岛屿为什么每个故事之间人物,你会发现它是交错的。因为我不像老师们这么有文化,我原来学的是商科,我原来也没有读过《米格尔大街》或者《都柏林人》,但是后来我读到之后,我就心中一喜,原来人家也是这么干的。后来我自己发明了一个理论,我想是不是“岛屿思维”。鼓浪屿的巷子是乱来的,让人晕头转向,但是想去的地方还都能到,乱绕就能绕到。在巷子里乱绕的时候,你就一会见这个人一会见那个,大家又都互相认识。我觉得这个会影响到一个作者,《米格尔街》也是在岛屿上面的故事,因为岛上的人就是互相认识,所以我在想可能这种人物互现也是一个岛屿的思维影响。
04 | 方言适度进入文本会增加小说的风味
王辉城:刚刚黑伞提到说龚万莹的作品中是一个虚构的鼓浪屿,这个鼓浪屿只存在她的记忆或本文中。写小说,事实上就是重建我们现在的生活。我自己平时也写点东西,但是在写自己家乡的时候,我常常会出现失语,老家里的那些方言很多我已经不知道怎么说了,但龚万莹的小说里有很多的方言,我就想问一下龚万莹在写作之中会出现失语的状态吗?比如,方言里你知道这个音,但是无论如何你都想不出一个普通话或者书面语来表达。
龚万莹:我的闽南语并不好,经常会卡壳,然后开始讲普通话。写《岛屿的厝》的时候,我就感觉90年代岛上的人大家还都讲闽南话,突然之间开始讲普通话的时候,会给人“装起来了”的给感觉。如果你要让岛上的人去完全讲普通话,就会非常得怪。我希望用闽南语带来一些风味,但是不造成太大的阅读影响。因为我大部分的朋友都不是闽南人,写的文章我会给他们看,如果很多人都不能理解某句话,我就会把这句话改掉。
龚万莹:闽南语,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活泼的语言来源,就是闽南语歌曲。闽南语歌曲曾经横扫全国,我会把闽南语歌曲分成三大类别:一类就是你好坏,一类就是我好拼,还有一类是大家都好惨。你好坏主要是女性视角,例如《爱情恰恰》,闽南语歌曲诞生在俗称“牛肉场”的地方(声色场所),代表歌曲有《舞女》《舞女泪》《爱情的骗子我问你》等。第二种就是“我好拼”,有《爱拼才会赢》和《世界第一等》。还有一种就是“大家都好惨”,因为牛肉场里除了舞女和生意人之外,还有大哥,大哥出来之后混社会,就“大家都好惨”,于是就有了《人生海海》这样的闽南语歌曲。
龚万莹:闽南语歌曲拥有强大历史、文化积淀,还包括了闽南人的诙谐,所以我不会失语,我张口就唱,但是我也会控制自己,我不希望把它变成一个土特产,从头到尾都是闽南语,然后设置很多障碍。我一直觉得小说有阅读者参与才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所以我不太想设置太高的障碍。我唯一任性就是到整本书的最后《白色庭园》我会采用比较自我的写法,《白色庭园》可能会是阅读障碍比较大的一篇,但是总体上我是会考量的。

闽南古大厝|图片来源于网络
王辉城:金老师成长的时候应该也听了很多的闽南歌,因为这个小说里有很多闽南话,有些我们是做了注释,你在阅读的时候会觉得陌生吗?
金理:这个我刚才就想插话。因为讲到方言在小说当中的存在,它能够为小说增添多少,或者是带来局限,这其实是我蛮疑惑的东西。我们看过最极端的地方性的写作,它的注释会成倍于正文,会要加很多的注释。但是万莹既想用方言增加一点地方风味,又很照顾一般读者。所以我蛮好奇的,是因为这小说当中有注释的,但是极少量。里面讲到一个词叫“免惊”,像我这样的读者会停下来考虑一下。这个既有方言的意思,好像又有古色古调的味道。
陈嫣婧:福建方言好多文言文的结构。
金理:上海话里面有一个词“牵丝攀藤”,望文生义的话就是一种很缠绕、很纠结的状态,这些词加入的时候会在阅读时候产生额外的惊喜。但有时候我又觉得比较苦恼,读有些所谓的地方性写作,就会大量加注释。我不知道一个作家创作的时候,会考虑吗?有没有尺度?
陈嫣婧:这个问题我想接着说一下。我原来参加过一次任晓雯老师的读书会,任晓雯老师她写《好人宋没用》的时候,她说了和龚万莹基本上一模一样的话,她说她写上海话的一些方言的时候,她会给她其他地方的朋友去读一下,他们读出来有不适感的话,她就放弃,跟龚万莹说的话一模一样。
陈嫣婧:我今天又听到了一遍之后,我觉得其实方言写作最大的考验作者功力的地方。如果说用得太多或者太缺乏普遍性的话,就会把这个小说变成民俗小说,会缺乏一种阅读上的认同感的。但是如果完全不用方言,就会让人觉得你的小说是不落地的,没有文化方面的特色。我们都知道文学和文化是分不开的,文学是文化的一个表达方式,如果说文化这个东西你完全没有去触及它的特色的话,其实是会降低小说价值的。所以方言用得怎么样,其实这个东西非常的讲究。在表达过程中穿插这么一点方言,我觉得最大的用处是能够增加小说里面说话人的节奏感,其实是为叙事服务的,让小说的叙事和人物表现出更多的生命力和活力,我觉得这个是用得最好。用的最不好的,就是读起来被方言给缠住了,你也不关注这个人物了,也不关注叙事了,也不关注小说的主题、价值,你只去关注这个语言。
龚万莹:我也想补充一下,我好喜欢老师们两位老师的分享。我就觉得,对于写作者的角度,其实方言是一个素材库,我要在里面拿出来漂亮的词句。比如说,我里面讲到阿嬷,闽南语有叫方言“叫做嘴唇一粒珠,讲话不认输”,就嘴上面长一颗痣的人,可能比较会吵架。这句话用普通话不难理解。包括“免惊”就是不要怕,应该大家都能理解,所以会有这样一个掂量。包括我现在已经在开始写自己的第二个书,是一个长篇。里面有些时候会用到杭州话,我就发现杭州话好像有一个词“疲疲塌塌”,用方言表达更贴切。
龚万莹:但是作为写作者,我可能不会从批评的角度去思考,但是对于写作来说,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库。对我来说,因为这本书主要是发生在鼓浪屿上面的,但是如果我写上海、杭州,写别的地方有美好的这种词句“疲疲塌塌”,我也要用。普通话本身有限制,普通话并不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湖泊,它依然需要有小小的河流往里面灌注。现在我们就算做文学的人不做这件事情,网络上照样在做,比如说“小土豆”大家懂了。“磕秃噜皮”,我一个南方人我都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词汇包括方言里面那些带劲的词是一直会被人翻出来去使用的,写作者有我有何不可。
05 | 作家对角色的把握反应了对历史的态度
王辉城:方言的写作其实还是挺难的,有些态度确实会过犹不及。其实我最近两天在读黎紫书的《流俗地》,我觉得龚万莹里面的小说里面人物,我读的跟《流俗地》的风情还是有点相近,《菜市钟声》有一个人物非常典型。她的丈夫走了,拿着她的钱花天酒地,她就想凭什么他可以这样,我不能这样。她点了一顿很好的水鲜之后,觉得海鲜也不怎么好吃,这个事情就过去了。这种健朗、积极的心态,在青年作家之间,很少有这么健康地处理一个女性或者一个人物面对灾难的反应。她没有往让她继续往下沉,也就是像金老师一开始分享的分析的那样,她有上升,下降。我就想问一下两位老师,你是怎么看小龚万莹小说里女性形象,比较狭隘的问题,女性形象。
陈嫣婧:这个也是我比较喜欢这个小说的一点,我觉得我们我们这个时代的审美,有一种颓废的基调,好像比较虚无的、颓废的、向下走的那种,会感觉比较的有腔调,有深度,然后所谓的积极的、蓬勃的、向上的生命力,就给人感觉说好像比较庸俗,意识形态上比较的浅。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能一概而论,特别是在一个作品里面,不能以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先入为主的价值取向去判断这个小说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小说是一个完整的作品,价值取向方面的东西,需要在整个小说里面去看的。
陈嫣婧:龚万莹的小说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她的女性身上有一种向上的东西。首先我觉得,你要去看她这种向上的东西是怎么在小说里面呈现出来的。比如说阿霞,她的坚韧不是作家给她设置好,她的坚韧不拔、她的人性的所谓的这种光辉这一面,是在她整个叙事过程当中慢慢被呈现出来的。比如阿霞后来为什么没跳崖。其实很多时候她在这个小说里面呈现出来形象,她坚韧的形象,不是说“我不想去死“,而是说这个人物有一个必然的文化和生存的背景,使她没有办法去死。人物的更大背景的命运的走向上,如果她去死了,反而是违背叙事的逻辑的,没有死、活下去,反而是合乎她叙事的逻辑的。比如说阿霞,我对这个人物其实蛮喜欢的,她的丈夫跟人跑了,去享受了,她也花钱去吃了一顿,但是因为她是闽南人,她到舟山去吃很贵海鲜又没有鼓浪屿上的海鲜那么好吃,她就觉得很郁闷。我花了那么多钱吃,还没有我在家的时候吃得好,我为什么还要去死?我为什么还要去沉浸在我的这种悲伤当中?我就算非常消极地活下去,至少还能吃到一顿鼓浪屿上的海鲜。她的人物逻辑是这个层面上建立起来的,所以这个人物到最后活出那样的一种形态是有一种必然性的,是叙事逻辑导致的一种必然性。
金理:我蛮喜欢妙香这个人物,她也是一个贯穿式的人物,她身上也有很挣扎向上又坦荡的一面,所以她是鼓浪屿的性格。讲到女性我们会觉得好像这种人物像“地母”一样,这有这种生命力在里面。这不是一个完全的现代性想象的小说。我觉得这部以鼓浪屿、一个岛为背景的小说当中,好像这些人身上有一种屡仆屡起的力量在里面,我觉得这种特质可能是这部小说所描写的对象所赋予它的。
金理:我觉得有一个地方万莹是把握的挺好的,以我的观察,近些年来我们中国地方性写作当中,有一个蛮危险的地方,特别喜欢沉浸在某种所谓的“原乡神话”当中。把书写的地方想象为一个密闭的、封闭的、静止的又特别美好的空间,所有的苦难都是外来的。当原乡神话建立起来之后,就开始唱挽歌,这样一个原乡,它终有一天会破裂的,会消失的。这个创伤事件怎么会发生的,这个时候就会以这样的一种笔调、逻辑来描述断裂的事件的发生,表现为那些来自外部的罪恶伤害了无辜的我们,或者现代世界打断了田园牧歌,侵蚀了过往的美好。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蛮糟糕的想法,一点反省能力都没有,灾难真的是从天而降的吗?我们从来都是无辜的吗?我们原乡内部就没有任何的罪恶曾经发生吗?
金理:这部小说集中有一篇蛮独特的,就是《送王船》。我觉得整部作品中,这一篇好像风格蛮沉郁顿挫的。里面有一段并不美妙的历史记忆,里面有恶意的同盟对人的伤害,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地方性写作的时候需要写的。你能够感到龚万莹对自己的家乡,不管这是现实当中的鼓浪屿,还是一座纸上的岛屿,她都是那么的爱。但是我觉得如果我爱一个人,我一定会正视他身上的错误和问题,我不会去纵容他。她能够写到岛上曾经恶意的同盟,我甚至有一种我无意识当中也曾经过参加过这种对恶意的同盟的感觉,一种平庸的恶,然后对身边的某个个体造成一种伤害,这种事情在我身上可能就发生过,我们每个人时时刻刻又有要有自省在里面,我觉得这才能够真正的营造出一种和谐的共同体,也是你对你所身处的共同体的一种真正的爱。
陈嫣婧:金老师的思路让我也看到了这个小说里面对于历史的态度,其实是蛮特别的。我就拿第一个小说举例子,里面写了一个老人,这个老人我看前半部分我觉得跟一般的小说套路没什么区别,老人沉浸在老房子带来的回忆里面,她不允许人家去修老房子,也不允许外地游客去看老房子。我当时其实一开始看的时候,我觉得也就挺正常的一篇小说,逻辑都是这个逻辑。我觉得最惊艳的是什么地方,最后这个房子塌了,然后老人就去给自己买了块墓,然后带着他的孙女去看这块墓,然后在墓碑前拿录音机放赞美诗,然后祖孙俩一起在墓前玩耍,我看了这个小说之后,我就知道作家可能非同一般,因为她处理的逻辑就跟一般的不一样。

《我们俩》电影剧照 | 图片来源于网络
陈嫣婧:前半段看上去就是我们一般人对于历史的理解,就是老人他沉浸在过去的世界里面,对传统的鼓浪屿的文化生活,有万般的不舍、恋旧,这种对过去时代的缅怀,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但是这个老人当她可见的依靠,就是老房子在一夜之间倒塌了以后,这个小说里面竟然没有过多地去写到她的留恋,只说她大病了一场,然后这个房子重新就修好了,然后就开始做起了干果生意,就开始对游客开放了。一瞬间,历史在这个房子里面发生了扭转,但是这个老人竟然没有继续在她的回忆里面沉溺下去,她选择了把最后的归宿墓地买好,然后在墓地里面放赞美诗,有一个永恒的指向,这个小说就结束了。
陈嫣婧:我就觉得这个是作家很不一般的地方,她对于历史的态度是有轻也有重的,她并不一味地沉溺于一种个人史的缅怀和对个人史的追忆当中,她也不是非常肤浅的去畅想未来,畅想永恒这些东西。她重中有轻、轻中有重,而且节奏把握得很好。这个小说的前3/4都在写这个老人的执拗,她的那种像一个过去的符号一样放在里面,但是符号随着老房子一夜之间坍塌之后,这个符号就这一页就翻过去,就这样无声无息的就翻过去,老人也就似乎没有太大的挣扎,就重新去面对了她的人生,也重新面对了历史的记忆,我觉得这个写的蛮好。这就跳出了就金老师所说的那种模式化的,时间对我只有创伤、我就是要缅怀过去,她就把这种这种格局给打破了。
龚万莹:我很喜欢刚刚老师们提到对于时间、对于历史的处理,其实最终我觉得是一个写作者对于时间的观念,如果是线性的时间,它结束了就结束了,或者说在线性的时间里,一件事情是无可挽回。我觉得我在写这个小说的两年里面,一直在思考的关于生死的问题。我写小说的时间是2021年到2023年,而且我自己是会逼迫自己去看大量的信息,因为我想把所有东西都记住,再进行一个处理。所以我当时满脑子想到的都是痛苦跟生死,但是我没有想到很多人读完之后,感觉到的是一种超脱,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写作者是一个好撒玛利亚人,你看到有一个人受伤倒在地上的时候,你看在他脸上是看到自己的脸,你看到他流的血就是我自己的血,因此好撒玛利亚人才会去缠裹他,去帮助他,因为那个人就是我的邻舍。我一直觉得对于写作者来说,读者就是我的邻舍,因为你愿意花时间去读这个书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就有一次交谈,我觉得这是很近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要去做缠裹,哪怕我自己有很多事情还没有想明白。包括前面说的,如果你把很多事情放在永恒的坐标去考虑的时候,看这件事情的角度就会不一样。你把死亡当做一个句点,或者是把它跟永恒的参照系去做对比,你看出来的世界观会不一样,或许会体现在文本里。

现场照片
【相关图书】
《岛屿的厝》
龚万莹 著
中信出版·大方 2024年1月
一座南方小岛上的九个故事,如同交错的窄巷般纵横关联。在悠长的往日时光里,岛民们的人生轨迹互相交织。
就像没想到年久失修的老厝会在一个雨夜坍塌、庭院里的老芒果树会被砍断,少女阿禾从没想过妈妈也会老、阿嬷也会离开人世;岛上最厉害的女人阿霞跟着客源变化改了几次经营方向:海鲜饭店、咖啡馆、饮品店、民宿,一个人把生意做得吓吓叫,但其实一直有个软软的阿霞,躲在杀气腾腾的外表下;菜市钟楼的大钟早已不再报时,多年后钟声再次响起,玉兔和天恩已抵达不同于父辈的成人世界,他们终于不再畏惧传说中的绿眼睛幽灵;油葱伯和老仙女妙香姑婆老来作伴,做起了殡葬一条龙的生意,两个总是为他人疗愈心伤的老人,却背负着不为人知的伤痛……时代的喧嚣入侵,岛屿上许多事情都变了,而南来的风依然温热潮湿,悼亡的迷雾与明日的微光也将恒久如常地同时降临。
END
文案丨龚万莹 金理 陈嫣婧 王辉城
编辑、排版丨邵雨婷
摄影丨Jian
原标题:《活动回顾丨龚万莹×金理×陈嫣婧:闽南之南是永不陷落的故乡》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