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温春来:滇铜取代洋铜的过程
清入关之初,币材主要依赖国内既有的铜器,康熙二十二年(1683)开海以后,铜材大部分取于日本,自康熙五十四年起,随着日本对铜出口的限制趋于严厉,清王朝逐渐面临铜的短缺问题,压制国内矿业的政策逐渐被放弃。滇铜在雍正年间产量激增,最终在乾隆初年成为全国最主要的铜材来源。学界对此早有明确认识,但滇铜取代洋铜的具体过程,仍然有诸多值得探究之处。
必须明确,并不存在日本严厉铜禁之后滇铜立即取而代之的简单因果关系,造成这种复杂局面的因素至少有以下三点。第一,日本的铜禁并非一种越来越严厉的线性过程,只是在总体趋势上如此。例如日本于康熙五十四年颁布正德新令,将出口至中国的铜额削减一半,并限制贸易资格,康熙六十年又向中国商船额外需索金片,致使中国办铜更加困难,但到雍正九年(1731)前后,办洋铜又变得相对容易,以至朝廷决定多办一百万斤。第二,云南铜矿业虽然早在清政府大量商船赴日之前的康熙二十一年就已开始发展,但直到雍正中期之后才引人注目,此时距日本严行铜禁(即康熙五十四年)已有十多年。滇铜到此时才显得兴旺,既与矿业本身发展的实际情形相关,也与地方官员的长期隐瞒相关。第三,就质地而言,滇铜无法与洋铜竞争,就运输而言,沿海省份办运洋铜不但快捷,而且运费相对便宜。在以上因素的制约下,铸钱主要靠洋铜成为清代长期的主流认识。到了雍正十三年,皇帝还认为:“总之办铜之难不止一端,除令日本不致留难、不抬价值之外,实别无良策。”

康熙时期的铜钱
康熙四十四年(1705)贝和诺总督滇黔,一下子题报了云南十八家铜厂,并且设立官铜店收铜。而当时滇省铸局全数停铸,这些铜斤一方面卖给本省百姓,一方面运至本省的剥隘、沾益、平彝等几处交通要道,供湖南、广东商贩承买。购滇铜商贩的身份记载很少,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应是承办京局额铜的商人,或者办铜省份所派出的差官。例如,因进口洋铜艰难,承办京师铸局铜材的内务府商人无力办铜导致亏欠,遂于康熙五十四年改为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东八省办铜;八省中,至少赣、豫、粤、闽等四省不再单纯依靠洋铜,而是差官往江南、浙江、云南等处采买。康熙五十五年九月,江西巡抚佟国勷在谈到承办京铜的困难时,亦云“铜产云南,聚于湖广、江苏”。云南布政使金世扬也明确称八省办铜后,各官为了考成,“官商多赴云省购买”。严中平等学者认为滇铜供给京运始于雍正初年,显然是不大准确的。
随着滇铜铜产的丰旺,铜斤无法售完,康熙五十九年(1720)十一月由贵州布政使升任云南巡抚的杨名时奏请每年从云南解铜一百万斤到京,以供铸钱之需。王大臣会同户部讨论后认为,为节省运费起见,不如将此项铜斤留滇铸钱,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得到皇帝批准后,云南于雍正元年(1723)在省城、临安府、大理府、沾益州开铸局,分别设炉二十一座、六座、五座、十五座,按照铜六铅四配铸,每年开铸三十六卯,遇闰加三卯,每年共用铜、铅1692000斤,按铜六铅四的标准,用铜1015200斤、铅676800斤。铜的来源有二,一是按二八抽课抽收的税铜,二是按官价收买的铜斤,铅则向贵州购买。
大量铸钱很快就导致钱价下跌。雍正三年(1725)五月,云贵总督高其倬称滇省市场上每银1两可换钱一千一百五六十文,远高于法定的1000文。为谋流通之法并提升钱价,他与抚臣杨名时商议,将制钱运往湖广销售。但外销数量有限,效果并不理想,云南钱价继续下跌。次年三月初八日,布政使常德寿称银每两可换钱1350文,铸钱不但无利可图,而且还亏损。他访得广西钱价较贵,每银1两换大钱400文,因此建议将滇钱运至与广西交界的剥隘,上船水运至广西,还可再达广东,在此二省销售钱文。皇帝认可扩大滇钱销路的措施,让常德寿与新任总督鄂尔泰商议。常德寿上奏之后仅仅十余天,三月二十日,总督鄂尔泰也奏称滇省现在每银1两已换钱1400文,要求为日渐壅滞的制钱谋一流通之法,并暂停鼓铸。皇帝不同意停铸,要求考虑减铸之法,并另商流通之策。鄂尔泰回复称,抚臣杨名时申请于滇省四大钱局共47炉之内减去11炉,已获户部同意,但减炉不如减局,建议裁去大理、沾益二局,因为前者离省城太远,制钱除搭放兵饷外别无流通之处,后者虽然运销黔楚较为方便,但“驮脚必由省雇,往返反致多费”,不如将二局裁去,省城钱局则加4炉至25座,临安钱局加炉5座至11座,这样算下来实际上也等于减炉11座。省局铸出之钱不但易于在本地流通,而且可以运至贵州、湖广乃至江南。临安局临近广西,所铸之钱可由剥隘船运至两广,两局每年总共外销制钱四万串。显然,常德寿将钱运至两广的建议得到了总督的赞同。
综上可知,云南官方通过课铜与低价收铜,将铜材聚集于官铜店之内,先是直接销售,无法售完,遂开局铸钱。最初设炉47座,耗铜1015200斤、铅676800斤,因钱贱减11炉为36座之后,每年共用铜、铅1296000斤,其中铜777600斤,铅518400斤。减炉意味着每年铜的需求少了237600斤,铜斤销售的困难随之增加。但比减少需求更为麻烦的是,云南的铜厂产能突然大增。雍正四年的东川归滇与矿厂的整顿,使滇铜很快迎来一个产量高峰(详见第一章第二节),铜斤销售的压力迅速增大,云南官方甚至难以筹集低价购买税后余铜的银两。以前云南每年鼓铸需铜100余万斤,满足此项用途后,滇省每年余铜不过二三十万斤,但据鄂尔泰雍正五年五月初十日的估计,该年铜产大旺,鼓铸之外,可余铜200余万斤,官方无力收购,因此建议动用盐务盈余银两收铜,转运汉口、镇江,供承办京局铜材的江、浙、湖广诸省采买。
就在云南急觅铜斤销路之时,全国钱局正陷于新一轮铜荒之中。因为日本的铜禁,办铜之内务府商人无法完成任务,康熙五十四年(1715)遂将京局铜材改交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东八省承办,而内务府商人则于康熙五十五年办旧器废铜133万斤,协助八省;因铜价昂贵,康熙五十七年,不得不增加办铜的价格。康熙五十八年,因为收买旧铜而导致京城的投机活动,清廷中止了废铜收买政策。康熙六十年,朝廷想当然地认为,铸钱用洋铜,江苏、浙江二省有地利之便,于是将八省之铜归并二省承办,其结果可想而知。雍正二年(1724)清查的结果,康熙六十一年有84万斤铜根本没有运送,而雍正元年更欠铜200余万斤,而且地方官员公开宣称这些欠额很难补上,因为商人“完旧不能办新,办新不能完旧”。与此同时,因为江、浙二省出洋购铜而不赴滇,云南铜斤大量积压。
可以说,如果不依靠正好供远大于求的滇铜,清王朝的铸钱将无以为继,我们用一个直观的数据来说明这一论点。雍正二年十一月,署江宁巡抚何天培奏称,因为日本的限制,每年仅可进口洋铜一百三四十万斤,而朝廷分配给江、浙二省承办的京铜总数为4435200斤,其中江苏承担2772000斤,江苏仅完成额定任务的约一半,浙江巡抚吴叔琳也直言所办洋铜不敷京运之数。朝廷不得不承认失败,推出了五项措施:
(1)减江苏办铜额数,所减令福建、广东承办;
(2)减浙江办铜额数,所减令湖北、湖南购买滇铜补缺;
(3)鉴于办铜省份不能如期办铜,重新允许收买旧铜;
(4)鼓励商人自备资本收买废铜交纳;
(5)预将银两发至钱局,钱局随时采买交与户部。在这些措施中,开辟滇铜作为京局币材来源不但重要,而且具备较强可持续性。
在铸钱因铜荒而陷入困境之际,鄂 尔泰建议收买200万斤余铜发卖的奏折一上达就引起了朝廷重视,经部议决定滇省动用盐务银6万两收买余铜,将100万斤运至汉口,供湘、鄂两省采办,100万斤运至镇江,供江苏采办。皇帝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同年,他命令在京陛见的云南按察使张允随专门带话给鄂尔泰:“鄂尔泰奏称铜厂甚旺,请将铜运到湖广、江南卖与各省采买的官员,狠〔很〕好!再着他将铸的钱多运些到湖广行销,只要国宝行销流通,即费些运脚亦属有限,即每串几分亦不妨开销。”接到加大钱文销售量的指示后,鄂尔泰于雍正五年十月初八日向皇帝算了一笔账,全省36炉共铸钱134780串,发给兵饷、匠役工食等用去71955串,已运销外省4万串,尚余22000余串,可设法继续运销外省。
就在君臣二人规划滇钱外销之际,赣抚布兰泰奏称江西制钱钱质低劣,不敷用,请每年往汉口买滇钱1万贯,皇帝欣然同意,指示于鄂尔泰奏准外销的4万串钱内,拨1万串专供江西 但鄂尔泰认为4万串是专供其他省的,建议滇省另外多运1万串供赣省采买。
滇省雍正五年(1727)铜产的实际情况比鄂尔泰估计的还要好。当年全省办铜400万斤零,比鄂尔泰的预估数多了近100万斤,这样,最终运赴湖广110万斤、镇江160万斤,又因广东办洋铜困难,又卖给20万斤。如此大规模的外运,引起了雇觅驮脚方面的困难。雍正六年,因为夏秋之间厂地“时气盛行”,厂丁“难以存住”, 只办铜270余万斤;雍正七年,环境一恢复正常,产量立即又上升至400余万斤。承办京铜的鄂、湘、粤三省对滇铜表现出了更大兴趣,湖北派员到四川永宁接运滇省运来之铜,湖南、广东直接派员入滇采购,而广西则要求多购云南制钱,从2万串增至62000串。
鄂、湘、粤赴滇购铜进京在雍正八年被批准为定制,这反映了滇铜地位的崛起与洋铜地位的进一步衰落。广东购滇铜的直接原因就是东洋“并无片铜至粤”, 江苏尽管在雍正二年由福建、广东分担了部分办运京铜的任务,但专办洋铜的江苏仍然感到困难,在规定广东等三省办滇铜的同一年,清廷又令安徽、江西分担江苏办铜任务,俱赴江南海关募商出洋购铜,这样又形成了八省办铜的局面。其中,买洋铜者浙、苏、皖、赣、闽,额共2772300斤,买滇铜者鄂、湘、粤,额共1663200斤。但滇铜外售的数字实际上远过于此,至少有两个事实需要考虑进来。首先,雍正十年,因陕西钱价昂贵,皇帝指示云南多铸钱文,每年运售10万串至陕,这一指示于雍正十一年开始执行,加上广西购买的6.2万串,云南每年销售制钱多达16.2万串,含铜85.05万斤,这样,云南每年向外运售的铜数(包括制钱含铜数),已多达2513700斤。其次,雍正九年,令江、浙二省兼办滇铜。可以说,滇铜的外售数量已与洋铜数量相当甚至略有过之。
就质地和办铜成本而论,滇铜远不能与洋铜竞争,滇铜成色相对较差,像金钗厂的产品完全不能解赴京局,只能招商发卖,后来各省大开鼓铸,在不得不使用金钗厂铜的情况下,一些省(如湖北)只能设法在市场上购铜掺用从而降低金钗厂铜的比例,并且在全国改铸加黑铅的青钱时请求仍然只用白铅,因为金钗厂铜品质欠佳,加黑铅后恐“钱文黑暗”。汤丹厂的铜斤品质在滇省首屈一指,但同样“铜质浇薄”, 办滇铜的省份常常需要将从云南所购毛铜重新熔铸成纯铜才能解京供铸。而且云南僻居西南一隅,崇山峻岭,日本虽属异国,却水路快捷,优势巨大,特别是对滨海省份更是如此。例如浙江沿海到日本长崎,顺风只需五六日,遇风阻也不过一个月。这样,办滇铜的成本远超洋铜。按户部规定,江、浙办铜每百斤给银14.5两,而办洋铜每百斤只需支付13两,算下来节省了1.5两(节省银)。节省银存入省司库,在办铜时预先扣除,所以办铜的价格就变为每百斤只能支出13两。而办滇铜则每百斤需13.2两(滇铜官价9.2两,加上由滇运到镇江的脚费4两),还是成色不足需重新加工的毛铜,且“平秤稍轻”。江苏办滇铜,只能参照办洋铜之例,按13两/百斤向户部核销,办铜官员就唯有赔补一途。所以鄂尔泰奏准将铜100万斤运镇江供江苏采买后,江苏官员宁愿顶着不能如期办洋铜而受处分的风险,也不愿遵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雍正九年,户部命令江、浙督抚除采买洋铜外,再预发银两往云南购铜,如果有成色不足及“平秤短少”,即用节省银补算,布政司发价时,不得预扣节省银,但每百斤铜的价格也不能超过户部规定的14.5两/ 百斤之数。这14.5两,其实仍然不足。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江苏通过滇洋兼办缓解了办洋铜的压力,但仍然不能完成洋铜方面的任务,于乾隆元年(1736)奏准将洋铜额再减少数十万斤,这进一步证明了不得不办滇铜的苦衷。严中平指出,滇铜实不能同洋铜竞争,如果不是进口洋铜不断减少,云南铜矿业能否大大发展起来是很值得怀疑的。
乾隆皇帝继位后,滇铜与洋铜地位逆转的趋势进一步强化。乾隆元年,因为日本铜出口至中国的数量更少,“洋商亏空甚多”,朝廷不得不采取鼓励措施,令商民可以自行出洋采铜。又以制钱重量已经从每文重一钱四分改为一钱二分为由,议减京局办铜额数至400万斤,其中滇、洋各200万斤。较之雍正八年(1730)的规定,洋铜额减少了近80万斤,而滇铜额增加了近40万斤,滇铜在数额上已经取得了与洋铜平等的地位。仅仅过了一年,滇铜又以更迅猛的势头彻底将洋铜从京局币材中驱逐出去。这一年,云南总督尹继善奏称,洋铜积欠太多,即使停办一年,也不能全清旧欠,而云南铜厂大旺,仅汤丹等厂就可年产铜六七百万斤,需设法招商销售,不如令江、浙二省额办的洋铜200万斤,从乾隆三年起悉数入滇办解。如果滇铜产量偶有不敷,则令海关采洋铜补足。乾隆二年,云南巡抚张允随奏称,现在京师钱局及滇、黔、川三省铸局铜材已由滇铜供给,而苏、皖、浙、闽等省应办铜斤亦系赴滇采买,应设法接济厂民工本,“以备各省每年额办之数,并可以停办洋铜”。
乾隆三年(1738)还同时出台了两项重大政策。第一,雍正十二年(1734)确定将鄂、湘、粤三省解京额铜留在云南,由滇省开广西府局鼓铸成钱后解运北京。因广西百色一段运输有不少困难,决定停广西局铸钱,相应的铜材也不经广西,而是直运四川永宁,沿长江至汉口,北上解京。第二,就像办滇铜的鄂、湘、粤三省因种种不便,最后将所承担京铜任务全数归滇省直接负责一样,在直隶总督李卫的奏请下,江、浙两省也将所承担之京局额铜改归云南办解。乾隆三年不仅大体确立了京局鼓铸全用滇铜,而且规定京铜全由滇省派员办解,这一局面此后维持了一百多年。在清代铜矿史与铸钱史上,乾隆三年均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
除京局外,各省铸局也大多依赖滇铜。按乾隆十二年张允随的计算,云南每年解京局铜633万余斤,此外,本省、川、黔、浙、闽、赣、湘、鄂、桂、粤等省俱赴滇买铜供铸,滇省每年需要提供铜900余万斤才能满足所需。随着各地铸钱量增加等原因,需铜量不断上升,乾隆二十二年,滇抚刘藻声称,全国每岁需铜约一千一二百万斤,而云南各厂所出在八九百万至1000万斤,因此京铜虽有保障,各省却常面临不足。乾隆三十一年,云贵总督杨应琚则称滇省每年已可办铜一千二三百万斤,供应全国之后所余不过数十万斤,奏请今后各省采买滇铜应按乾隆二十九年以前规定的额数执行,有多买者概不准行。但仅仅两年后,巡抚明德就奏称云南出铜渐少,不敷全国之用。
总之,滇铜即使在最旺的年代,满足全国所需都是很勉强的,这样,洋铜仍然是一个重要补充,并且在一些省如江、浙的铸钱中依然具有关键地位。陕西铸局也通过官商,每年采买洋铜五万斤供铸。事实上,当时许多官员认为国内铜产难以同时满足铸钱与铸器之用,导致民间偷偷毁钱为器,因此仍然鼓励商人出洋购铜以增加铜斤供给。
(本文选摘自《矿政:清代国家治理的逻辑与困境》,温春来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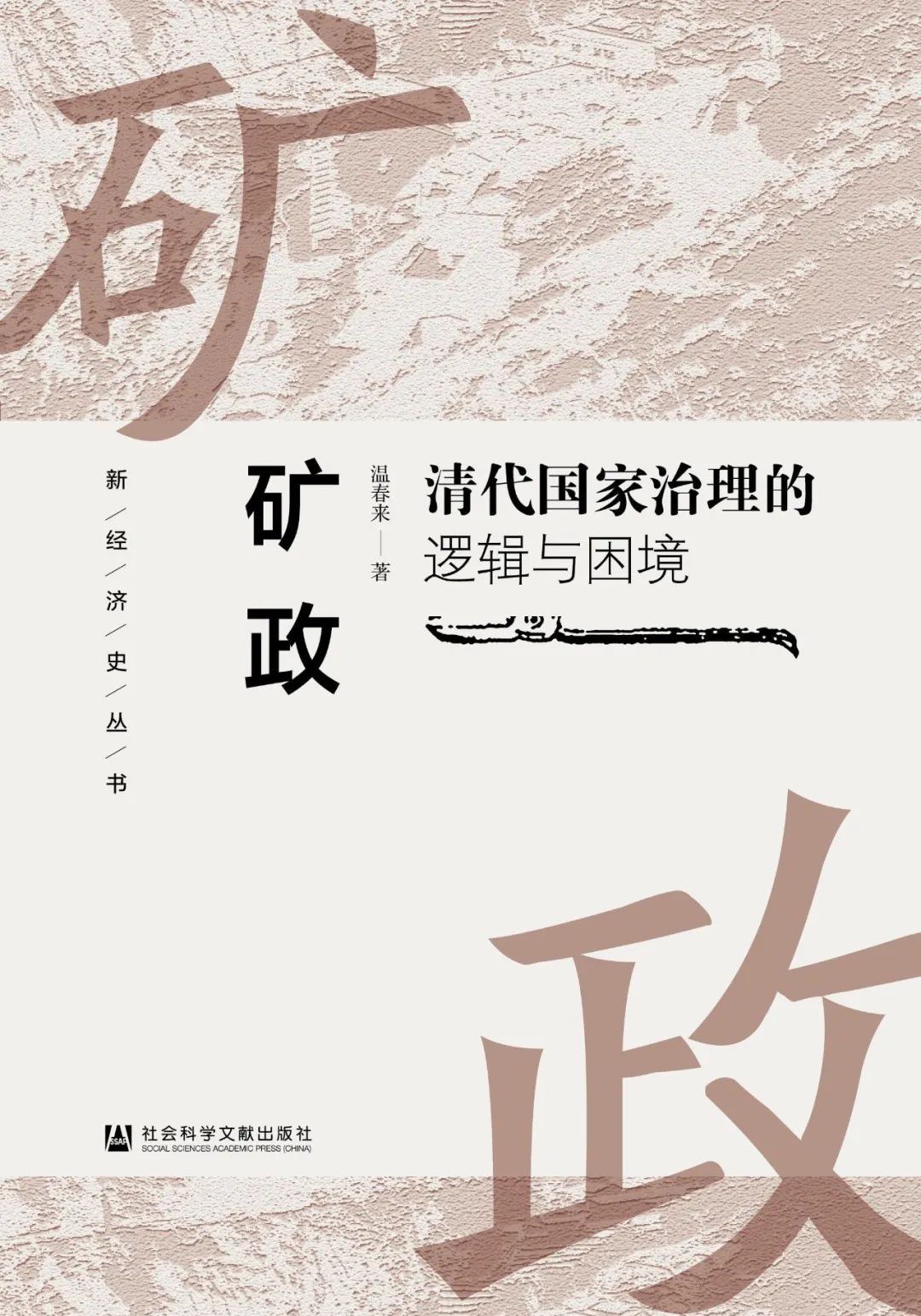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