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回看2023,作家们在读什么?
2023年,胡安焉等素人作者的流行,给了我们清晰而乐观的提示。
像胡安焉这样的作家,他们很容易被标记为投合于时代的营销品,但细读胡安焉的履历与作品,这并不成立,他有十余年的写作经验,且他始终把握着对写作发自内心的本能,娓娓道来。正是长期的、不装(不炫技)的、专注的、自立的、体面的写作,才使他获得了越来越苛刻与焦灼的读者的几乎一致激赏。需提及,在胡安焉之前,中国作家少有自己谋生的案例,文化圈也绝少吸纳他们入场。
而2022年获诺奖,并在今年持续流行的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也反复提醒我们:中国经验与实践存在着向真实,也向思想开放的内容,只需轻轻转化,拨开那些屏障与冗余。新面目和新迹象已足够预指了某种新时代,然而文化界多少还泥足于旧传统,尤待整体内在再塑后的“重头”“做人”。而回到具体的个体,我们又见证了几多卓越的人格、美好的实践、峥嵘的写作,他们又怎样去面对这个复杂的时代?
为了呈现中国文化的历史痕迹,我们策划了阅读史这个访谈项目,邀请不同的文化从业者,谈谈他们作文作法、所想所梦。2023年,我们邀请七位作家和学者——韩博、李黎、李建春、三三、苏怡杰、王威廉、赵志明,与他们交流一年来的变化和感悟。这七位作家和学者,在最近一年大多有新书出版。

韩博,诗人、艺术家。新书或新作有《从波斯湾到大西洋》等
韩博:写作的过程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全身心搏斗
2023年,你出于什么需要、怀着何种感受,阅读或重读了哪些书籍,并促成了几多写作或实践?
韩博:这一年我主要阅读古希腊戏剧,尤其是欧里庇得斯的作品,把能够找到的现存剧本都读完了。这种阅读当然有功利目的,因为我正在写一本书《雅典娜之城》,我希望在尽可能了解古希腊黄金时代的基础上完成这部作品。今年我也的确完成了这本书的初稿。受益于欧里庇得斯良多。以往,我借阿里斯托芬之眼看待欧里庇得斯,因为喜剧诗人总是嘲笑这位悲剧诗人,但一俟沉浸入欧里庇得斯所勾勒的希腊,你就知道他有多么伟大。实际上,他的作品,完全不比现代的任何戏剧作品弱——我甚至认为相反。

《欧里庇得斯悲剧集》, 罗念生、周作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0年10月版
学者张旭东在与我的一次交流中提及了类似“二十世纪的终结”的说法,大意是,中国二十世纪史层叠了多个世纪层,八十年代是中国二十世纪的“中点”,中国二十世纪仍未结束,或者说某种意义上二十世纪正在终结。那么我想,刚刚发生的二十一世纪应该是完全不同的世纪,而看看眼下,世界太新,我们大概需要成为某种新的人,书写某种新的文学、文字。那么,你筹备自己或期待“我们”写的究竟是什么?
韩博:世纪的说法可能只是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时间归类,自娱而已。的确,每一具体时间中的人都有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描绘世界的方式,但去写可能更重要,因为写作的过程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全身心搏斗。而坐在桌前去想怎么写只是一个理性的过程,非常有限。

李黎,作家,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新书有《夜游》
李黎:对层叠状态的呈现
2023年,你出于什么需要、怀着何种感受,阅读或重读了哪些书籍,并促成了几多写作或实践?
李黎:2023年,以及此前几年,我的阅读一直勉强为之,很差,困顿。主要就是忙,阅读成了最容易被牺牲和忽略的事情。时间往往也有,但因为不断被各种事情切割开,所以篇幅较大的阅读几乎没有,成体系的更谈不上。有时候也因为知道某个具体的晚上、某个周末会有很多事情,所以干脆不去看书。相反,看手机倒总能见缝插针,有时候一个晚上刷视频累计好几个小时。有一次我大概是有点警醒,反问自己,我是一个图书编辑,我怎么能以整晚刷手机的状态去做书然后期待很多人去买呢?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所以,我把家里的“小书”都整理出来,想着尽可能一本本看完。“小书”就是字面上的意义,薄薄的、一百多页的那种书,几万字,往往一个晚上就可以看完。
在这个过程中我继续看了安妮·埃尔诺的几本书,《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男人的位置》《年轻男人》《另一个女孩》等等,她的写作思路给我很大的启发。我写小说二十来年,脑子里已经有着深刻的印记,就是短篇、中篇和长篇,每次新写一篇,脑子里会告诉自己,这个写成短篇、这个写成中篇或者长篇。虽然事实会有变化,而且我也是以短篇居多,长篇几乎没有,但这种几乎本能的对作品篇幅的规划,经过多年实践已经去除不掉了。更为关键的是,在中国写小说似乎有一个必经之路,那就是短中长,依次来,以长篇乃至大长篇地位最高。大量的作者在规划写作时也是按照篇幅来安排,例如最近几年写中短篇、这几年开始写一个或者几个长篇,等等,然后再去结合内容。埃尔诺的写作不是这样,可以看出,她只是以内容作为取舍标准,值得写的、想去写的,就去写,并且往往以难以定义短中长的篇幅完成,以自身理解的篇幅完成,往往一个作品搁置很多年,但写出来还是短短的一两万字。
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即在以往,长篇小说承载着呈现一个完整世界的功能,无论是现实世界,还是内心世界,长篇小说作为相对完整的呈现方式,是独一无二的,也诞生了大量的经典,尤其是从发掘、揭秘、陌生化、异质化、震撼等角度看。今天可能不是这样,几乎无穷的信息、无尽的个人写作、无穷的社交举动,已经让世界的一切都不再陌生,很难有一部作品可以呈现出一个让人觉得彻底陌生以至于大为震惊的世界。写作可能更多往共情方向发展,写共同的难以言表和幽暗晦涩,共同的悲喜交加等等,埃尔诺作品里大量的“留白”就是这个效果。极端一点说,客观世界可能无需文学来整体描述,大家都知道,而个人如何身处其间才是要去写的。

安妮·埃尔诺作品全新修订版(《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男人的位置》),郭玉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版
今年的阅读主题大概是诗歌,这既是长期的喜好,也是应对比较碎片化时间的方法。但其实并不理想,貌似可以,但诗歌,尤其是诗集,也一样需要一个相对完整的时间安静地读。今年另外的阅读,其实是阅读当前的出版。意思就是,我买了很多很多的新书,但仔细看的不多,堆积在那里混在很多书里找不到了,甚至记不得买过又买重复了。这里面既有职业的需要,更多对当前倔强不屈的出版业的阅读,一个个新作者涌现,你就会知道这件事依然蓬勃。很多书单独看或许还不够好,但永远好过另外的写作和图书。
二十世纪在终结,二十一世纪在展开,但相对无言。你筹备自己或期待“我们”写的究竟是什么?
李黎:层叠这个词很精确,世界越来越新很赞同,但二十世纪终结的说法我个人不太赞同。这个层叠在后续还会继续,或许整个二十一世纪都会是这个状态。例如一部分人已经主要生活在虚拟空间里,也创造了不少的虚拟形象,而另一部分人可能还在被催婚催生,被家庭找关系安排进入某个稳固的机构,被教诲关于礼貌的细枝末节以此获得人脉,甚至这个情况会在一个人身上发生,不知道他是新人还是旧人。
我理解所谓的世界越来越新,无非就是曾经只是少数人思考的哲学问题,越来越普遍地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科技促成这种普遍思考,也可以阻隔这种思考。我筹备自己写的,就是对层叠状态的呈现,例如,一个用最新的手机行三拜九叩大礼有一天又毅然一去不返的人。
2023年有两本流行好书,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王计兵的《赶时间的人 : 一个外卖员的诗》。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第一个版本是副本制作由彭剑斌特约编辑的《派件——一个通州快递员》;《赶时间的人 : 一个外卖员的诗》第一次对大部分读者露面是通过短视频、社交媒体。可以说,艺术书或自出版所代表的新同仁体系,以及尽管被商业寡头篡夺了主体与利润但仍保持着其真实与活力的社交媒体体系,几乎成了很多读者的出口,也几乎关联上了大部分作者的观念、实践、成长,以及种种策略。此类现象还有很多。您对这个现场有何看法?有何期待?
李黎:这个问题本身特别好,感觉不需要回答什么了。能够在相对固定的秩序中出现意外之喜,任何年代和地方都是让人欣喜的事,何况这两位作者其实和我们息息相关,并非什么特殊行业、特殊身份,他们也是潜行已久的写作者,首先是靠自己而不是靠外力才得以身在其中、不止于此。
不敢谈什么期待,多多益善就好。
同上,目前文化的活力似乎再次回归具体的个体,在这个境遇下,抛开主流的审美、回归“同仁”与自己的判断,似乎更加重要了。那么,你推荐哪位(哪几位)作家(文体不限,包括学者),理由是什么?
李黎:首先是韩东,他最新的中短篇小说以及他苦行僧般的写作本身,是对一切流行事物的抵抗。任何时代都有其话术,可以影响塑造很多人,让很多人深陷其中且得意洋洋,例如跨年演讲这个那个的。韩东的小说,小说的语言和背后看待世界的方式,是一种去伪存真,是对华而不实、居心叵测、交出自我、幻像错觉的层层剥离。他的小说像针,刺破了“文学”,也在刺痛中带来了趣味和幽默,可以看他的中篇《临窗一杯酒》。
另外推荐大头马,前文说到新人,游戏是一个新的方向,大头马是亲身深入到诸多游戏,并且反复写游戏的青年作家。以专业的态度再现游戏,又带出文学所要求的人生、人性、喜怒哀乐等等,独特而且果决,足以让她和不少“接班人”式写作的青年作家拉开巨大的差距。

李建春,诗人,评论家,湖北美术学院副教授。新书有《李建春诗选》《物篇》
李建春:如果写诗不像写遗嘱,就没有明白问题所在
2023年,你出于什么需要、怀着何种感受,阅读或重读了哪些书籍,并促成了几多写作或实践?
李建春:我完成过去三年的“见证之书”《物篇》后,由于身体受损,2023年上半年停止了写作。经过几个月的锻炼,恢复到正常的渐老,而不是断崖式下降。我体验到,所谓的见证,其实就是牺牲。之前我一直是有道气加持的,我是个读经人。但在那些艰难的时刻(我羞于提“苦难”),我根本就不想读经。被上帝抛弃才是真正的见证。写作状态和生活状态,哪个在先呢?2023年[对我来说],按照看篮球的一个说法,是进入“垃圾时间”了,我不再“见证”,但也回不去了。
我希望找到一种“破”的力量。新书《物篇》已达成一种成熟,和所谓的“境界”。杜甫:“老去渐于诗律细”,但我不甘心、不信任“境界”,所以要“破”。在这个背景之下,停笔几个月后写的第一句是:“我也没有苍凉……”“当远山由青绿转为墨色,薄暮的朋友/相约踏着溢到岸边的浪纹。”拒绝沉重,想让自己舒服、放松一点。
2023年是我的柏拉图年。读完王太庆译的《柏拉图对话集》和商务印书馆的《理想国》,就下单了刘小枫主编的《柏拉图全集》。我早年读了老一代人译的几乎全部古希腊悲剧,但那是文学。读柏拉图却给我打开一个陌生的世界。居然有这样的“思路”:不靠启示、不靠禅悟,也不算知行合一,居然全凭逻辑在爱智的思辨中认识神。通常认为诗歌是哲学的彼岸,我在“到达”彼岸之后,回过头来读一位著名的反对诗歌的哲学家。我不在意他的观点,正如不在意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否道德的问题,因为我只会写诗。仅仅惊讶就可以构成读书的理由——惊讶是反境界的嘛。

《柏拉图全集》,刘小枫/主编,华夏出版社,2023年5月版
另一个要推荐的或许不是作者而是译者:刘皓明。这些年一直在咀嚼他译的《荷尔德林后期诗歌》。他是一个主张硬译、直译的西方古典学者。作为读柏拉图的调剂,我就读他译的古希腊诗人品达的《竞技赛会庆胜赞歌集》。刘皓明译品达时的语言意图,或许是想把中国古典与希腊古典对应,用了大量来自“四书五经”和《昭明文选》中的词汇,但他的句子又是当代汉语的。这就很有意思了。我一直感到当代诗在表达情景和情感的词汇方面有枯竭的趋势,刘皓明的译文让我看到了运用当代汉语的另一种可能。

《荷尔德林后期诗歌》(上中下),刘皓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版
二十世纪在终结,二十一世纪在展开,但相对无言。你筹备自己或期待“我们”写的究竟是什么?
李建春:我曾认为自己是一个二十世纪的人,因为我读的都是二十世纪的经典。但近年的一些国际事件让我意识到,正是二十世纪的经验和观念给我们带来麻烦。比如索尔仁尼琴围绕他的大俄罗斯思想构成的批判意识,他的“说真话”的力量,也成为《物篇》的动机之一。索氏在当代俄罗斯是一位广受尊重的作家,我认为他的“说真话”可取,那么,是否有必要为“说真话”重新构建一个前提或“土壤”?相应地,当我们思考“天下”的概念时,“文化兴亡即天下兴亡”,为此,有必要使地域性的经验理所当然地进入普遍,脱离它土地的形状。不是文化为了土地,而是土地为了文化。
虽然世界仍然坚固,但是活力正在从边边角角涌现,它将我们的现实塑造为晶莹的多孔结构。你对这个现场有何看法?有何期待?
李建春:活力源自于身体对时间光谱的截取能力。不同的年龄阶段,或者说在不同的时间光谱中,被现实和对现实的塑造是不同的。诗人、艺术家首先要把自己的光谱点亮,然后才能与现实对刺,在坚固的世界中为生命打一个孔洞,使世界可爱。
你推荐哪位(哪几位)作家,理由是什么?
李建春:柏拉图,孟子,品达,贺拉斯,维庸,古希腊三大悲剧家。有始终在场的,孟子。有读不懂的,柏拉图。有细读第二遍的,品达。有正准备读的,贺拉斯和维庸。而三大悲剧家似乎是近年才译齐,已入我囊中。

三三,作家。新书有《晚春》等
三三:“真实”的文学
2023年,你出于什么需要、怀着何种感受,阅读或重读了哪些书籍,并促成了几多写作或实践?
三三:说几本重读的书,对自己的写作也多有启发。
首先,张爱玲《易经》《雷峰塔》。基于古典文学修养,张爱玲年轻时的作品就非常成熟,但这种完整多少仰赖于巨作的照拂。而晚年写自传三部曲(另一本为《小团圆》),或许也有跨语言的缘故,张爱玲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法。读译本,也能感到她的简洁、精准,时间也已筛选出最重要的记忆。从技艺而言,我更喜欢《雷峰塔》,但《易经》有更难能可贵之处,即张爱玲在这本作品中直面了她一生的劲敌与伤害来源:母亲。即使母亲去世后,她仍在为母亲留下的怪圈挣扎——这当中有无尽勇气的起落。

《雷峰塔》,张爱玲/著 赵丕慧/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青马文化,2016年7月版
第二,小白《封锁》(包含《封锁》与《特工徐向璧》)。极具才华的作品,过去初读时,难免追着一些情节来读,再读则留下了细节。在《封锁》中,即使只是一个审慎、耽于观察的叙述者,叙述者“马先生”仍然非常吸引人,散发着欲言又止的感怀。小白曾谈到写作时,先要虚构一个作者,用他的话语和节奏去写作——是不信任感将那个真正的创作者与文本隔离吗?我不知道,但和许多读者一样,着迷于这些面相复杂的声调。
第三,董说《西游补》。如果说《西游记》中隐蔽的宿命论调具有一定现代性,那么《西游补》中关于意识层面环环相扣的幻境,更接近现代主义的产物。整本《西游补》,都是悟空的一场梦。其中有许多瞠目结舌之事,比如悟空化作虞姬却因本身的男子身份而推诿项羽,比如悟空到地下发现阎王死了,被迫代职半天,比如悟空见到了另一个自我(不同于六耳猕猴的模式),再读仍然感叹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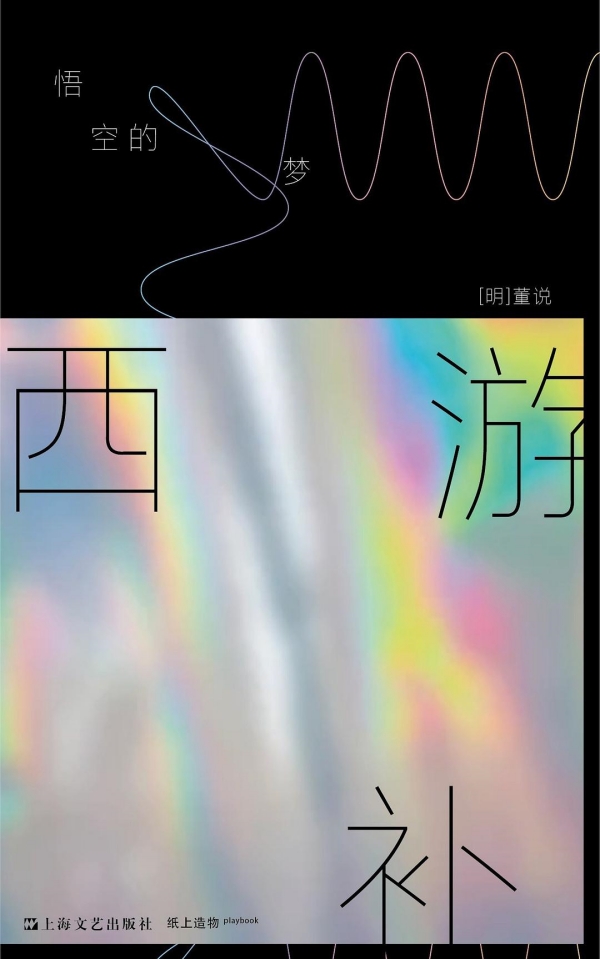
《西游补》,董说/著,上海文艺出版社·纸上造物,2022年7月版
二十世纪在终结,二十一世纪在展开,但相对无言。你筹备自己或期待“我们”写的究竟是什么?
三三:永远是“真实”的文学,作者真正在意的、带有作者体验或(退一步而说)情感的文学。无论这种“真实”以什么题材或形式呈现,都可以。今年读了一本非常动人的作品,丹尼尔·门德尔松的《与父亲的奥德赛》,虽然被分类为非虚构,但我以为这是一本跨越文体边界的作品。其实没什么“新”和“旧”的对比,标准是唯一的,只是我们对于“真实”的认知会随时代而变化。很庆幸的是,至少这一百年里,我们始终是在进步的。

苏怡杰,非虚构作家,网易人间工作室独家签约作者
苏怡杰:1997年、1998年生人和上一代画出了一条线
2023年,你出于什么需要、怀着何种感受,阅读或重读了哪些书籍,并促成了几多写作或实践?
苏怡杰:非常杂,也谈不上什么层次,基本属于应激刺激的产物,比如某人去世,重读了一遍《斯通纳》,在另外一个地方获得了事实性的冲击,就重读一遍何伟,一戳一蹦跶,如此种种,重读过很多遍康赫的《人类学》。

《斯通纳》,【美】约翰·威廉斯/著 杨向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16年1月版
二十世纪在终结,二十一世纪在展开,但相对无言。你筹备自己或期待“我们”写的究竟是什么?
苏怡杰:我能非常明确地感知到,出生于1997年、1998年以后的写作者在什么地方已经和上一代画出了一条线,我完全不能在精神上觍着脸说离他们更近,在语言上无疑也不属于他们。但围绕我们成长或带领我们启蒙而产生的那种叙事、文字,在现实的更替间已经接近不成立了,去怪某个人,自然没问题,但里面也有必然性。有的情况是美好的仗已经打完了,因为发生了比较明显的现实更替,所以很容易看出来,而有的情况是谋取利益。
虽然世界仍然坚固,但是活力正在从边边角角涌现,它将我们的现实塑造为晶莹的多孔结构。你对这个现场有何看法?有何期待?
苏怡杰: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总有些文化产品出来,除了伴随作品本身的讨论,还有让人暴跳如雷的功能,同样也是一戳一蹦跶,主打一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以为自己在搞报复,要骂他或者去解释去辩论吧,人家又顾左右而言他,如同游走在越位线半米处的前锋,再等两年过去万一你作品也卖得不错,就过了保护期了,非常头疼。
你推荐哪位(哪几位)作家,理由是什么?
苏怡杰:想到了一个不相干的问题:2018年,有人指责东北作家贩卖奇观,2023年,也有人指责东北作家贩卖奇观,大家猜这是同一批人说一件事还是两批人在说两件事。

王威廉,作家,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创意写作教研室主任。新书有《你的目光》《我们聊聊科比》
王威廉:尊重自己,也尊重他者的艺术
2023年,你出于什么需要、怀着何种感受,阅读或重读了哪些书籍,并促成了几多写作或实践?
王威廉:今年因为ChatGPT 4.0的迅猛发展,逼着我读了不少人工智能方面的书籍。但是我发现凡是这方面已经出版的书,尤其是欧美出版再翻译到中国的书,面对新的发展态势,实际上都有些落后了。它们对我来说构成了一种参考系,让我在写作中有一种问题意识。
二十世纪在终结,二十一世纪在展开,但相对无言。你筹备自己或期待“我们”写的究竟是什么?
王威廉:如果从技术及其应用的角度来说,二十世纪是终结了,但从文化文明以及民族国家的角度来说,二十世纪正在以新的方式构成了我们世界的内在结构。我们是在新与旧之间徘徊,等待被撕裂的一代人。我们应该写出这种撕裂感。
虽然世界仍然坚固,但是活力正在从边边角角涌现,它将我们的现实塑造为晶莹的多孔结构。你对这个现场有何看法?有何期待?
王威廉:一个我们天天打交道却永远沉默于制服内部的群体突然开始对我们开口说话,而且还是以诗歌的方式坦陈他们的内心,这当然会打动我们。这充分说明了文学和艺术永远是人类生活中相当重要的部分。但这也昭示出一种危机,那就是在世界的表面被摄像头复制的时代,人们陷入到了内在的沉默当中。这种沉默是不容易打破的,是不容易交流的。自媒体上的喧哗,并不是这种沉默的表达,而恰恰是对这种沉默的遮掩与扰乱。这种沉默唯一的表达渠道就是艺术。这种艺术的根本价值就在于证明我们依然存在着,还活着。所以我对未来的期待就是,当我们真的打算表达自身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艺术。一种尊重自己,也尊重他者的艺术。
你推荐哪位(哪几位)作家,理由是什么?
王威廉:艺术的尺度可能会有位移,但是始终在高处。这是我坚信的。文学方面,我觉得陈晓明先生今年出版的8卷本文集相当震撼,给予纯文学以及文学的未来以守望与展望。我还喜欢赵汀阳先生的一系列文章,他对于人工智能在哲学伦理上做出了很多思考。

《陈晓明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1月版
你的年度书单是?
王威廉:赵汀阳《人工智能的神话或悲歌》。陈晓明《陈晓明文集》八卷本。

赵志明,作家,坏蛋文学独立出版发起人。新书有《石中蜈蚣》《秦淮河里的美人鱼》等
赵志明:在这个新世界感受到的新生活
2023年,你出于什么需要、怀着何种感受,阅读或重读了哪些书籍,并促成了几多写作或实践?
赵志明:2023年,我读的小说很少。一方面是因为从原来供职的杂志社离职,出于工作需要对小说稿件、同行期刊的阅读大幅减少;另一方面,则是发觉经历了很多事情后读小说不过瘾,无论是外文小说还是中文小说,都很难抚慰我,但返回去读诸如《悲惨世界》等,又觉得隔的时间太长不应景。于是,我转而去读一些文化读物,诸如《世界文明史》《恐怖景观》《木材的流动》《兴隆场》《世说俗谈》《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三言二拍”《子不语》等。读《木材的流动》是因为小说家张万新对这本书非常推崇,他的文学鉴赏力我一直奉为圭臬,读后果然大有所获,也向好多朋友安利过。读《兴隆场》和《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是因为我在写关于河流的系列小说,已经完成《长江引航员》《在河之洲》等。读“三言二拍”《子不语》等,是因为我在2017年出版了《中国怪谈》,随后去中国人民大学读创造性写作研究生,中断了,现在想继续写下去。我曾自诩为无怪不欢之人,其实我很胆小,此举或许是叶公好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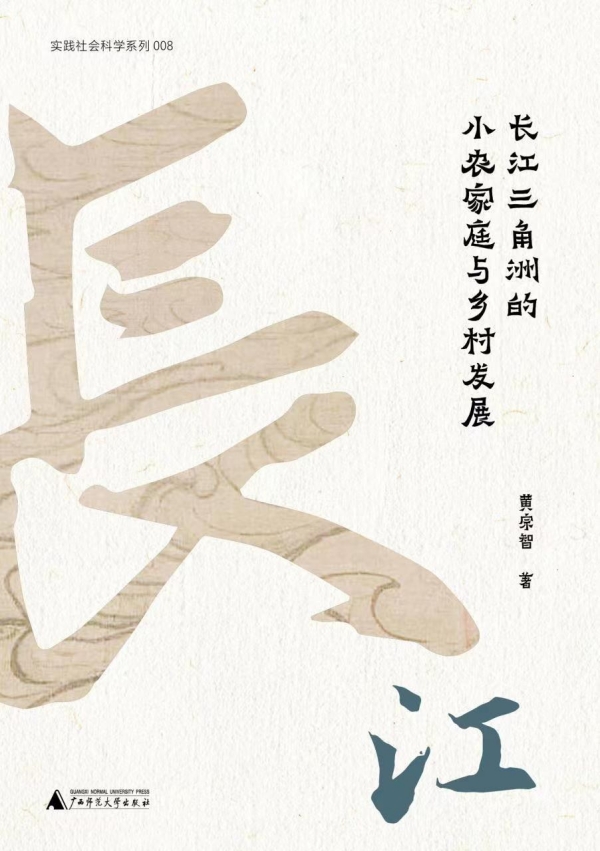
《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黄宗智/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2月版
二十世纪在终结,二十一世纪在展开,但相对无言。你筹备自己或期待“我们”写的究竟是什么?
赵志明:我们大概生活在一个车轮上的世界。至于车轮滚动的方向,既不为我们掌控,作为乘客的我们可能也难以查辨。随着车轮滚动,新是必然的呈现。哪怕遇到旧风景,虽似曾相识,但毫厘千里,也不妨视为新。既如此,成为新的人,书写新的文学、文字,责无旁贷。当然新的文学、文字都会因人而异,这种多面性本身也在新的范畴之内。我个人对自己的期望是,尽量写一些温暖但不矫情的文字,哪怕让几十个人读了觉得我写出了他们真实的心声,也比炮制一些虚假繁荣好。至于对“我们”,我希望主要还是年轻人吧,写他们在这个新世界感受到的新生活,包括城市、乡村、家族、家庭、同学、朋友、情侣、工作、同事、网络、科技等,不要对身边事视若无睹,因为离开这些,人能感受到的无论多么丰富、伟大、崇高的感情,都很难经得起推敲。
虽然世界仍然坚固,但是活力正在从边边角角涌现,它将我们的现实塑造为晶莹的多孔结构。你对这个现场有何看法?有何期待?
赵志明: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我视为非虚构写作。当然,胡安焉本身是一位很认真的写作者,他曾在黑蓝论坛发表作品。黑蓝论坛当年以先锋著称,现在依然深有影响的作家有赵松、顾湘。王计兵的《赶时间的人:一个外卖员的诗》,在一定程度上有出版方包装的嫌疑。诗人的身份是独一无二的,在王计兵诗人身份外强调他的“外卖员”身份,首先是出版方的不自信。我们说卡夫卡,不会强调他的银行职员身份;说圣琼·佩斯、米沃什,也不会刻意强调他们的外交官身份。当然,对出版方的营销,我们不应苛求,事实上,我们应该为出版方慧眼识珠,出版这些作品而致敬。有些生活,有些情感,有些命运,不身在其中,很难共情,没有这些写作者,便会被无视。他们为他们发声,找到出口,引来关注,于个体和群体都是一种善。例如余秀华、范雨素、丁燕、陈年喜等,都要向他们致敬。
你的年度书单是?
赵志明:虚构类(5本):张楚《云落图》、颜歌《平乐县志》、谈波《大胆使用了绿色》、李宏伟《信天翁要发芽》、李黎《夜游》。
非虚构类(5本):王敏《苏报案研究》、张应强《木材的流动》、易小荷《盐镇》、奎多·托内利《时间:从霍金到量子纠缠》、沃尔特·艾萨克森《埃隆·马斯克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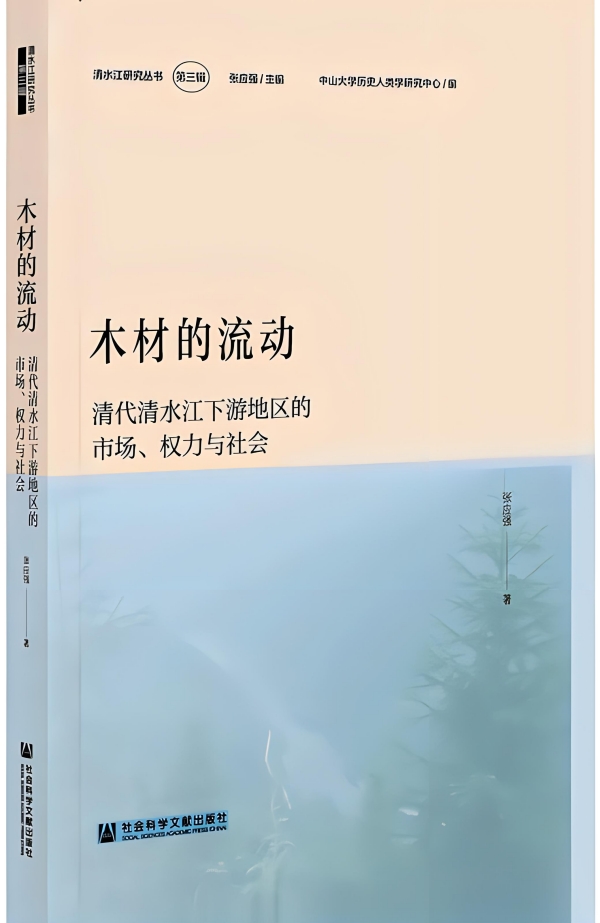
《木材的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张应强/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8月版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