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乌格雷西奇:木匠留给我几页手稿,原来写作的冲动困在无数人身体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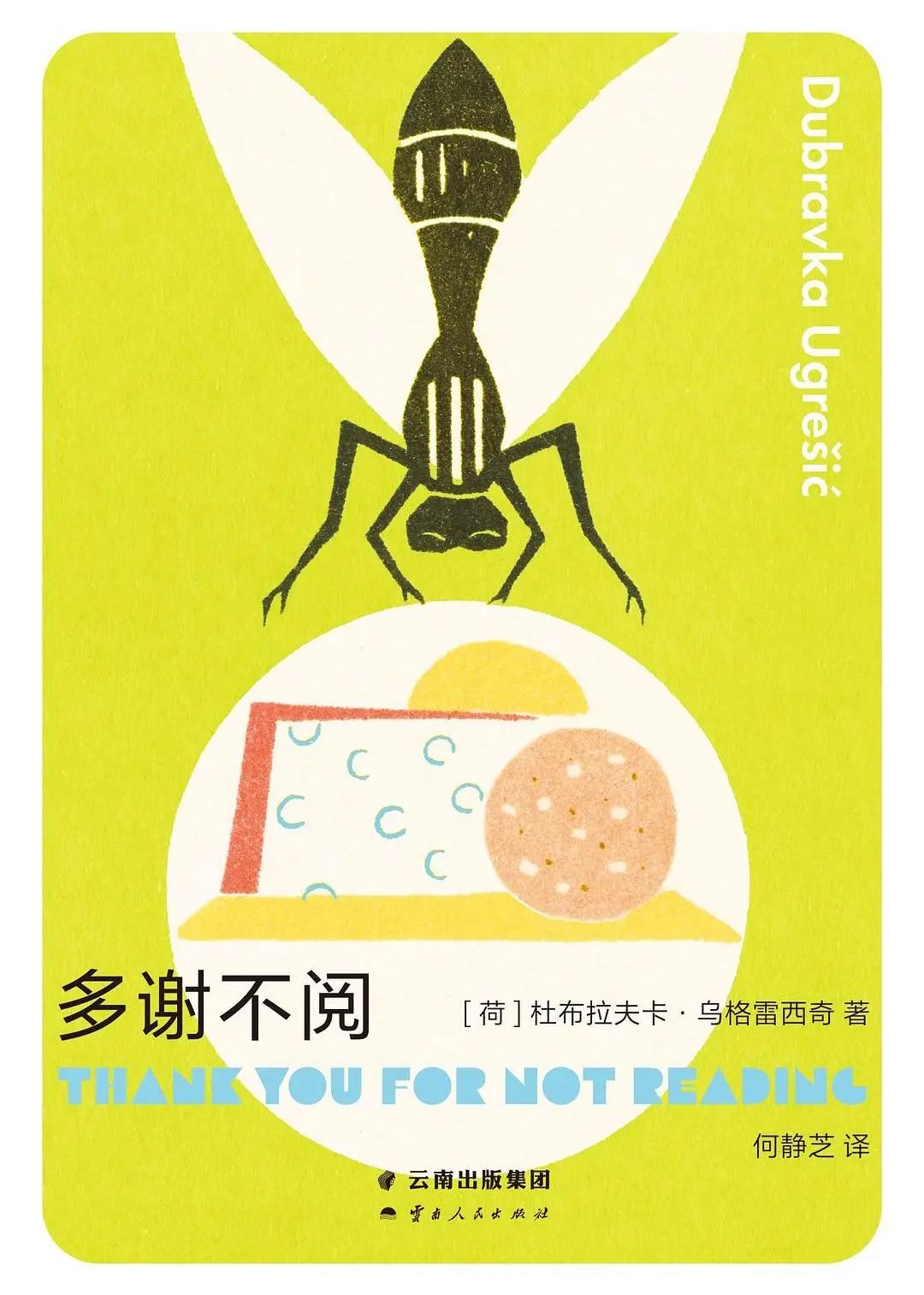
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
进入本报2023年度好书榜的《多谢不阅》,来自克罗地亚裔荷兰籍作家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假借一个被英美文学市场冷落的东欧人之口吐槽文学世界的诸多乱象:隔三差五就会横空出世的文学新星;被反反复复“重新定义”的文学;本末倒置的版权运营模式;宛如超市与咖啡馆结合体的书店……她一直不断追问“语言”“文字”与“内在记忆”之间的关系,试图像保护野生动物一样保护文字。2023年3月17日,杜布拉夫卡因病逝世,享年73岁,而她留给我们了一条可以深潜入文字和记忆的小径。
今天夜读选自《多谢不阅》结尾部分,在和装修工人打交道过程中,作者遭遇了许多烦恼,但其中一个工人悄然留下的小说稿,让她对这个时代坚持写作的意义有所参悟。
尾声
第七颗螺丝钉

▲ 电影《帕特森》(2016),下同
第一个来我家的工人叫弗兰克,是个荷兰人。
继弗兰克之后,本带着宝拉与洪萨一起来了。
洪萨是捷克人,身形高大,足有七英尺,主张息事宁人,时不时来一次阿姆斯特丹,赚几个非法的荷兰盾。
宝拉女士特别壮实,长着软软的唇髭。年轻时开过卡车,酷爱重型机车,曾屡次同美国机车爱好者一起从纽约骑到洛杉矶。
本则是电工,且精通自己的手艺。除了爱搞电气外,他对奇怪的人怀着一份特别的好感。这些奇怪的人通常都比他更高更壮。这是我后来认识了本的女朋友以后知道的。
罗伊是谁替我找来的我已经不记得了。他与跟我同是克罗地亚人的尼基和达弗尔同期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尼基是个影迷。与罗伊这位来自布鲁克林的美籍意大利人一起工作,叫他十分激动,其程度无异于同罗伯特·德·尼罗一起刷墙。罗伊还酷爱帆船,这也让尼基着迷。罗伊身上总带着一本目录,上面列着各种型号的帆船和它们的价格。达弗尔也没去过美国。所以罗伊轻而易举就点燃了两人的想象力。罗伊是木匠,尼基与达弗尔则从刷墙到铺瓷砖什么都干。
一开始我对罗伊不太信任。他报的时薪是我给尼基和达弗尔的两倍。此人诡计多端,一心想着赚钱,浑身上下没有一处老实的地方。但当时工人很难找。而尼基与达弗尔又都一力保举他。
到了傍晚,大家随便弄了点饭吃,拿出一两瓶酒喝,有关罗伊生活的一些噩梦般混乱的细节才浮出了水面。

据说他来阿姆斯特丹已经一年了。留下来是为了一个荷兰女孩。他在美国做的是工程承包,曾数次赚到百万美元,但一次都没守住。他说在美国赚到一百万很容易,但守住却很难。他曾钞票成堆,像个国王。他曾为美国的有钱人装修房子,见过各种世面。
他曾有一妻一儿。他经常给儿子打电话。但跟他真正亲近的只有他妹妹。他妹妹也组建了家庭,有两个孩子,和一个酒鬼丈夫。再苦的生活,他妹妹都能熬得住。
他的妹妹是他唯一的依靠。他们,他和他的妹妹,他们一起计划未来。这些计划都很大。他们要举家搬到蒙大拿州,在那里造一幢房子,永远住在一起。他妹妹都计划好了,他们要养马为生。再说几年后会发一场洪水,美国会从地球表面消失,他妹妹跟知情的人打听得很清楚,只有蒙大拿州能幸免于难。
他的一生比小说还精彩。只要写下来就一定会大卖。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他自己就会提起笔。也许是在蒙大拿州的农场上,那时候他肯定更老了。他以前读书时在学校写作文还获过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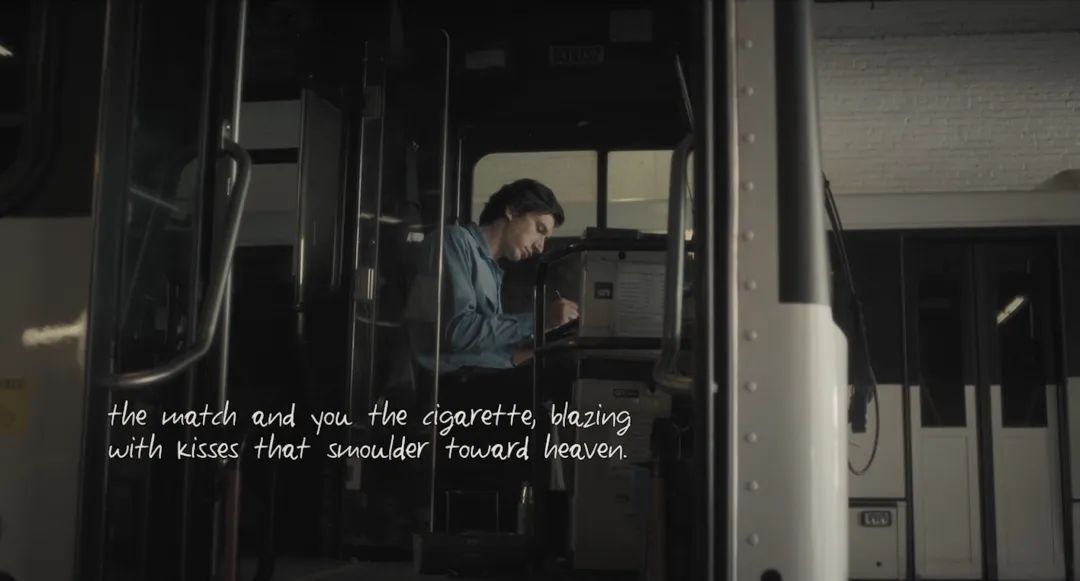
没过多久,罗伊变得越来越叫我紧张。他傲慢,仿佛自己是被迫劳动的王子,他脾气大,情绪多变,他以难以想象的速度,用他情感的暴风雨裹挟了我们,仿佛我们自己没有情感似的。
有一回,我看到他手里拿着一把吉他。正在为尼基与达弗尔弹唱一首据说是为我而作的歌曲。我为这场表演付给罗伊许多钱。因为他以小时计费。从此罗伊越来越多地怠工,竟至无法完成自己开了个头的那些工作。他在厅里铺瓷砖,才铺了三块就跑到厨房去刷墙。刷了一半又去干别的。他开始越来越严重地迟到和早退。他要求工资日结,有时甚至要求预支。只要我稍有微词,他就会觉得我在针对他。一切小事都会让他觉得别人在针对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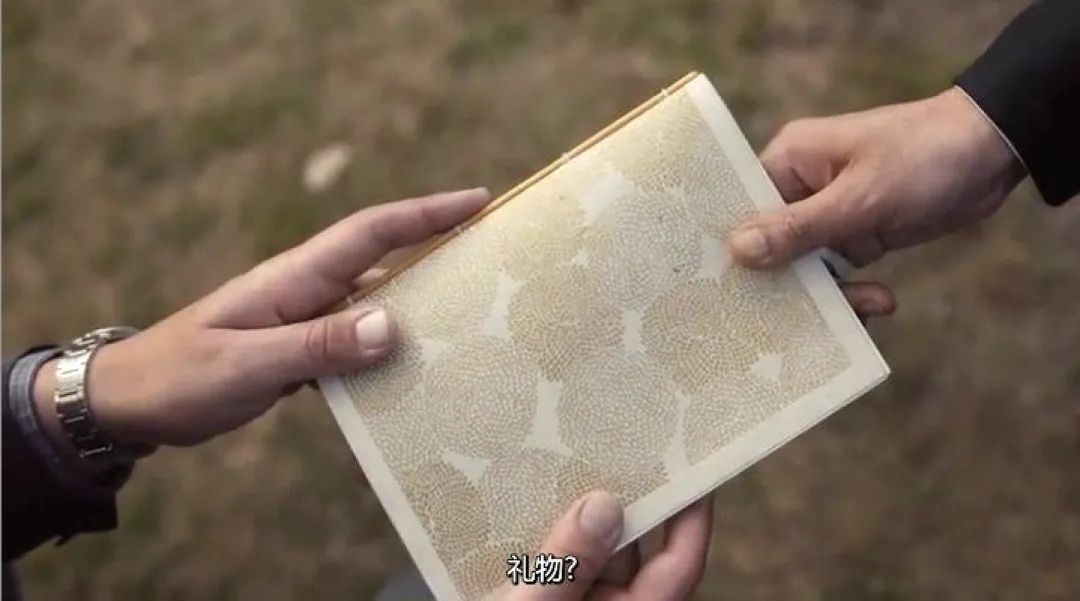
一天早晨,罗伊来我家,告诉我们他前一晚上通宵写成了他的小说《七颗螺丝钉》的序章。
“我念给你们听好吗?”他说着,从兜里拿出两页纸。
“念一念有何妨,是吧?”尼基和达弗尔说着都看向我。
那一刻,我正双手很脏地跪在地上,给地砖缝灌浆,这是罗伊前一天留下没干的工作。我登时火冒三丈:“七颗螺丝钉?!”还有完没完了!
当时,我是个自由职业者,赚的钱刚够维持生计,装修住房已经让我负上了一笔不知该怎么还的债。我自问究竟在做什么。是不是彻底疯了。几天来我干活干得精疲力竭,一行也写不出,把钱都扔在了一个我连姓什么都不知道的浑蛋身上,图的是什么呢?就为了让他写一本关于他人生的小说吗?这他妈不是噩梦吗?
我站起身,气喘吁吁地从牙缝里挤出一句:“你被辞退了,罗伊。”
我当时看起来一定很吓人,因为罗伊一句话也没说,夹着尾巴就走了。尼基、达弗尔和我一起完成了装修工作。罗伊走后我们都松了一口气。连对他表现得最通情达理的达弗尔也不例外。他跟我提过罗伊一两天内就要把房子退了搬去跟他住的事。
装修接近尾声。最后的工序是铺地板。板材已经买好了。但尼基与达弗尔都不会铺。我到处找工匠,打电话跟朋友打听。谁都没有时间。唯一能来的也要到三个月以后。我陷入了绝望。
达弗尔小心翼翼地提议,何不问问罗伊?反正再过几天他就要去法国然后回美国了。我同意了;我别无选择。我要求他们三个在两天内完成工作。
第三天我回到家,地板铺好了。罗伊脸上洋溢着喜悦之色。尼基和达弗尔像打了场胜仗。我又能呼吸了。
罗伊问我,能不能把我的电子邮件告诉他妹妹。当然可以,我说。
“她要是给你写信,请一定告诉她我是个好人,告诉她我铺的地板有多棒。”他语带请求之情。突然我为他感到难过。他看上去仿佛还是个孩子。
第二天早上,虽然已经没有工作,罗伊还是穿着工作穿的溅满油漆的牛仔裤和T恤衫来了。除此之外他还穿了一件剪裁过时的阿玛尼短上衣。
他又待了一会儿,彻查空房子,看看地钉有没有钉牢。
“挺好的吧?”他看着地板问。
“挺好的。”我说。
“剩下的板材我还能做一个书架……”
此话不假,剩下的板材还有很多,而且我的确还没想到该怎么处理。

那一整天,我都在看罗伊做书架。在刚漆了墙壁、刚铺了油亮的轻木地板的空房子里,阳光从窗外洒进来,罗伊看上去光辉伟大。他一刻不停、全神贯注地工作着。在罗伊那双巧手里,剩余的木料成了一个高雅的书架。
“这是我给房子的礼物!”他拍着胸脯说。
罗伊去巴黎了。他问达弗尔借了两千多个荷兰盾。说好一到美国就安排达弗尔过去。美国是个能赚钱的国家。他罗伊有人,那都是些追风的工匠。哪里有飓风,他们就卷起工具追到哪里。
罗伊消失一年后。
罗伊在厕所里用防水木板做了一根假梁,好把难看的管道和自来水总闸遮起来。梁在一个高得够不着的地方。我突然想到自己从来没检查过总闸的确切位置,于是爬梯子上去够了够,在总闸后面,塞着一方纸。
那是罗伊小说《七颗螺丝钉》的头两页——确切说是一页半。罗伊一定是来跟达弗尔和尼基一起铺地板时把它塞在那里的。就好像他既希望我能找到它们,同时又不希望我找到它们一样。除非房子出了问题,需要切断水管总闸,不然的话,谁也不会去看他藏这两页纸的地方。
我坐下来,仔细读起了罗伊的这两页稿纸。

一开始罗伊写道,自己注意到自己正迅速步入中年,希望他的忏悔能为自己与他人在自己身上所犯下的不公做个见证。或许,通过写作,他能够赶走心中日夜折磨自己的恶魔,因为他,罗伊,已经不认识自己了,他究竟是个影子,还是曾经的自己死后留下的鬼呢?他请求读者理解自己将在后文中公布的事,虽然他知道这些事全是诉苦与自怜,因此他不打算为自己讨一个原谅,但请大家原谅那个曾多么希望被爱、被接受的男孩子吧。
后文的故事本应关于那个男孩,关于七个在布鲁克林寻找出路的男孩如何拿走了本不属于他们的东西,关于他们如何亲得像一个人,只有死亡能将他们分开。
小说为什么叫《七颗螺丝钉》?
那是因为其中一个男孩在骨科手术后从腿上取下的钛合金螺丝钉。七颗钉子分别给了七个男孩,七个男孩长成了七个无所畏惧、凶猛彪悍的男人。七颗钉子有着七种不同的命运……
罗伊在序章中不断做这样的重复,仿佛它是早已铭刻在心的咒语,而他无法从中逃逸。可当读到最后一句话时,我还是禁不住动容了。
你很快就会看到,我写下这个故事,是要为这几个不惧怕犯下天理难容之暴行的年轻人做一个见证。同时,在写的过程中,我将解放自己的灵魂,愿它找到平静。因为我不只是一个人,我也是那第七颗螺丝钉。
文章就此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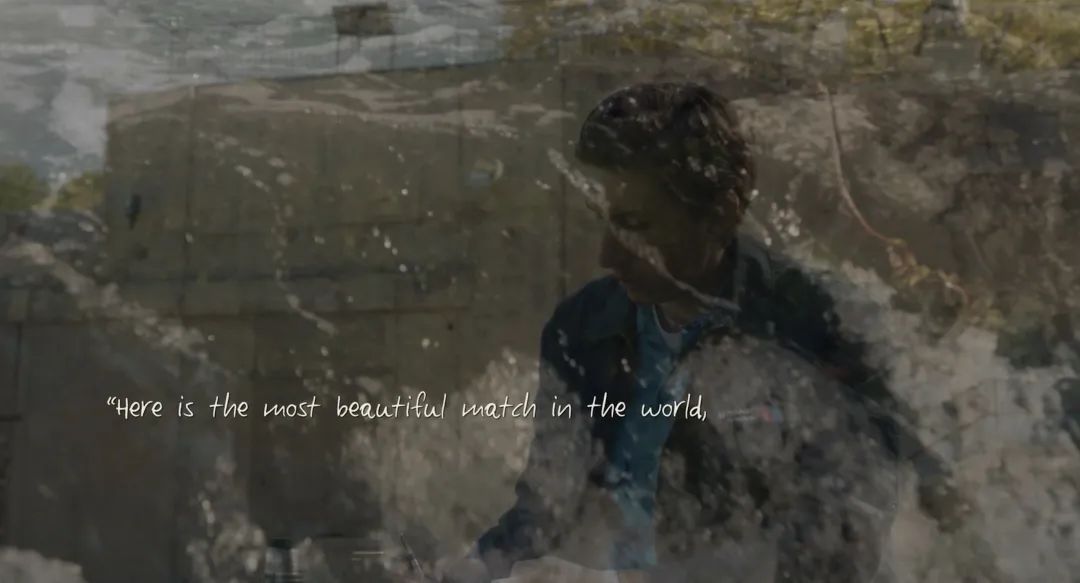
最后,不可回避的还有一个问题,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从装修房子到神经兮兮的木匠——与书籍和文学有何关系?罗伊与本书的主旨有什么关系?
单凭他亲手给我做了一个书架这件事就足够了。
不过,还有别的理由。罗伊把文稿藏在一个他知道我一下子不可能发现的地方,实际上是留下了一个漂流瓶。罗伊洇水的文稿是用一架电动打字机打成的,我想应该不会再有副本。如果罗伊出了什么事,如果他像从我的生活中消失那样从他自己的生活里消失了,我书中的这些只字片语,将证明他曾经存在过,证明他的确曾想留下一系列事件,来见证自己何以沦为一个过去的影子。这是我给他的让利,免费的,是对他手做书架的象征性的回馈。
罗伊的故事也像一则寓言,体现了知名与不知名的差距在分毫之间。两种状态随时可能互换。难道我不是曾经做着罗伊的工作,而罗伊一时间取代了我的位置吗?难道双膝跪地、满手灌浆剂地劳作,不是我对自己之为一个作家的过度自负所做出的象征性惩罚吗?
实际上,罗伊小说的开头完全可以作为出版提案的一个完美范例。它充满了为人熟知的元素——数字七;布鲁克林七武士;鬼魂、暗影、恶魔等浪漫的意象;以呼唤读者原谅作者罪行为开篇的传统手法——作为提案非常有效。没有什么比提请读者一起去发掘秘密叫人更欲罢不能的诱饵了。尼基、达弗尔和我自己,不也正是因此而咬钩了吗?对我们来说,罗伊仍然是一个谜。
罗伊的故事其实也反映了所有故事之为故事的原因。鲍里斯·皮利尼亚克曾说:狐狸是狡诈和背叛的图腾。狐狸是作家的图腾。要写成他的忏悔,罗伊必须从其他或存在或根本不存在的人身上寻找灵感,所有作家都是这么做的。我写罗伊时,也正像一只狐狸般滑步上前,只从他身上悄悄偷取一小块素材。也许那两页被留下的稿纸并非瓶中信,而是诱饵。
在他列举的所有写书的原因中,罗伊曾提到对正义的寻求。无论成品在艺术上是否有价值,我们对寻求正义的信仰——无论是美学上的、文学上的、政治上的还是个人生活中的——都是导致我们提笔写作的最有力的动机之一。我自己似乎也在追求某种正义。
只要世上还有貌似必须要写的事,只要读者(作者也是读者!)在阅读时产生了必须重写这些事的心,书籍就会一直存在。至于文学艺术本身,谁知道呢,也许艺术的机巧,就藏在一个职业木匠写出我不只是一个人,我也是那第七颗螺丝钉,而你并不发笑的那一刻。
(《多谢不阅》[荷]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著,何静芝/译,理想国·云南人民出版社2023年9月版)
新媒体编辑:郑周明
配图:电影剧照

原标题:《乌格雷西奇:木匠留给我几页手稿,原来写作的冲动困在无数人身体里|此刻夜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