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夜读丨朋友不响
送老友返广州,来得有点儿早,坐在人不算多的机场旅客休息区,两个话不多的人,大眼瞪小眼。
尽管我自己是个飘忽的浪人,但一开始确实很讨厌这种送别。成年人擅长的,就是嘴上说些“常联系”之类的鬼话,然后此地为一别,别后你哪位,怪令人伤心的。
后来四处流窜多了,再后来某日发现微信好友稀里糊涂加到三千多需要删掉两千多,突然福至心灵,看淡关系。人其实没多少能力管理许多情感和关系,但好的关系似乎又不怎么需要管理。
跟这个朋友多年前在另一个朋友家沙发上认识,聊了几句,一起跑了两次步,彼此默认成为老友记。到上海之后,她住处和公司均离我公司只有几百米,数十天也不见一面。偶尔我临近下班收到条消息:给你调了杯酒,来带走。
有时见面频繁点,活动范围和行程又一百年不变。总之,我们如两台量产低配AI,行动默契,行为刻板。
在此之前,她说了句相识多年最肉麻的话:“因为你在上海,我才来的。”而我在她用闲谈口气说出离开上海的决定时,心中也悄然塌掉一角。
然后我们面不改色挥挥手,成为对方口中“我广州/上海的朋友”。但我们同时又在分别中再次确认,对方其实更像家人。
刻板寡淡之外,有很多建立起家人般情感的事,细密,很难拿出来说,却在经年累月间让关系变得牢靠。日本人常常把人与人之间命运般的交织称之为羁绊,简直是对这种关系最好的注释。和亲缘不一样,这是人自主选择的羁绊,见证它成立,几乎像是人生的命题。
我在不同城市有几个这种同款朋友,不是发小,不是闺蜜,没受过“不要和同事做朋友”的限制,也不常联系。有的甚至忘了是怎么认识的。但不知什么时候起,就成为了大方交出家门密码或是叮嘱对方钱不够花时要吱声那种关系。
二十啷当岁时在某酒局上,听一个刚知天命的老大哥掏心窝子:“小刀啊,我到这年纪没啥野望,就是哪天入睡前担心自己醒不来,盘一盘有可以托付妻小和身后事的朋友,就够了。”
我自小受的教育其一,便是不要给人添麻烦,连七月半在先人们牌位前祭拜都会默念“就不许愿劳烦你们了,在那边要轻松愉快”,听到大哥这话只能苦笑:当你朋友负担够重的。
这些年被朋友们频频洗脑,开始意识到人就是要彼此麻烦,才会建立起亲密关系。这世界上白首相知犹按剑的故事确实很多,但依然有些人,天生就长了张可以被麻烦的脸。也偏偏是他们,有着该死的迷人的分寸和边界感。
王家卫说上海话“不响”是留白,朋友通常都不响。
最不响的朋友,也许姓顾。三百多年前,江苏人吴兆骞被诬下狱抄家,流放宁古塔(今天的黑龙江牡丹江市海林市),顾贞观许下“乌头马角终相救”的诺言。顾贞观自己其实都长期郁郁不得志,且人微言轻,却为救老友奔走十数年,只是都没啥结果。
他在太傅明珠家为其子纳兰容若授课时,收到吴兆骞吐槽戍边苦况的信,写下著名的《金缕梅》相赠:“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
这是下半首,即便加上上半首也是通篇只感念朋友的苦困,作相救的承诺,对自己的付出只字不提。此诗让原本懒得救人的纳兰容若泪流满面,忍不住出手相帮,被流放20年的吴兆骞才得以回京。
吴兆骞这个人脾气挺臭,流放了这么多年依然臭,回来见到老友,聊天时还是会急赤白脸。有次在明珠府和顾贞观吵起来,纳兰容若看不下去,将吴领到内屋,白墙上能看到一行题字——顾梁汾为吴汉槎屈膝处。(梁汾和汉槎分别为二人的字)
吴兆骞才知道这个闷声不响的朋友都为自己做了什么,扶墙大哭。
当代人没什么机会要救流放宁古塔的朋友,友情很难搞得这么哀感顽艳。羁绊归羁绊,今人更爱彼此身心轻盈。但在飞驰的人生轨道上,在一次次告别中,生命的雀跃和凋敝却很雷同,所幸有不响的朋友,见证了彼此这一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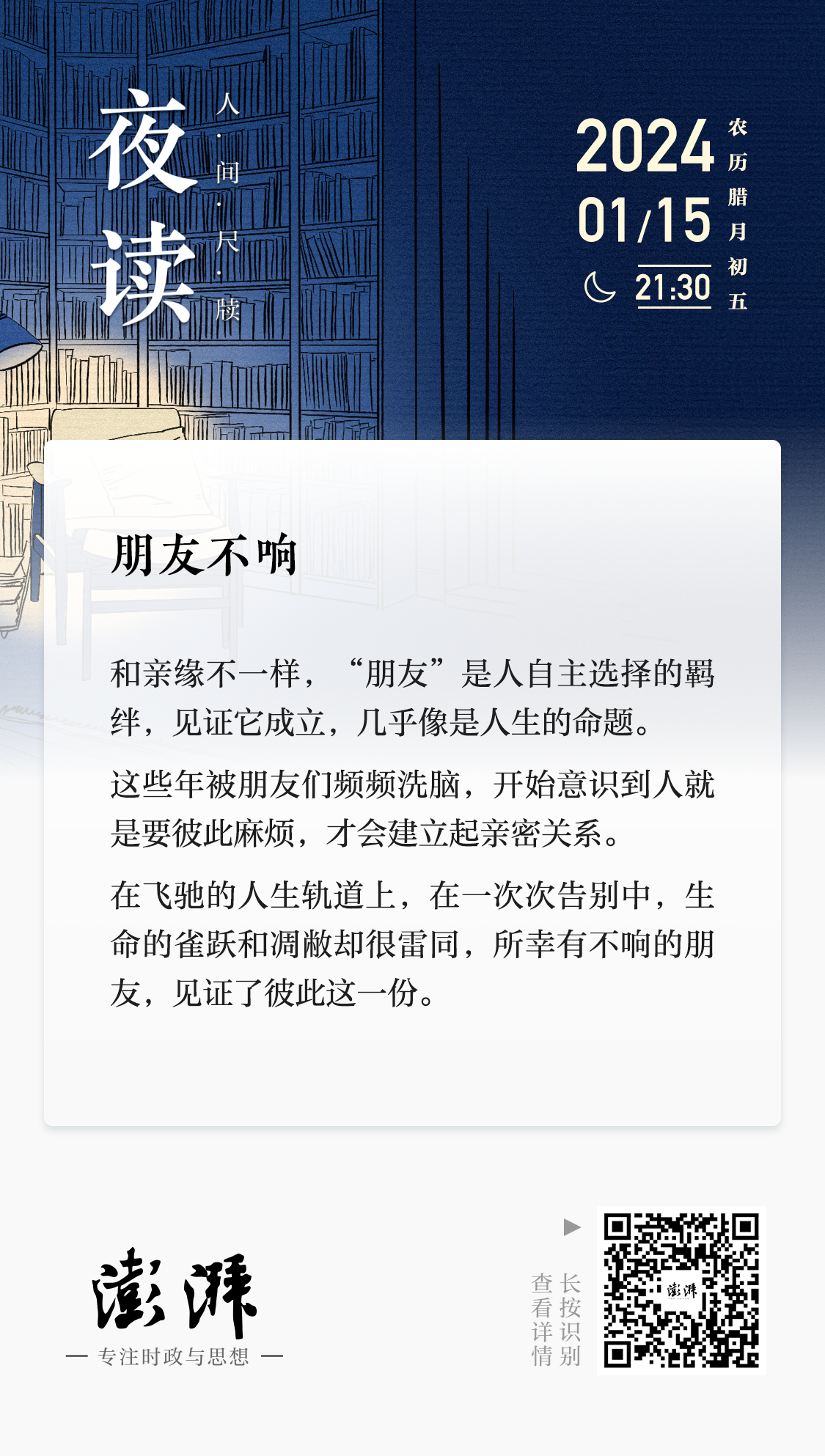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