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游戏论|游戏逻辑的逆转与《完蛋!我被美女包围了》的否定性——兼与邓剑、武泽威、彭天笑商榷
2023年10月红极一时的真人影像恋爱模拟游戏《完蛋!我被美女包围了》(以下简称为《完蛋》)在12月16日入围2023年steam最佳剧情奖,这款在玩法设计和故事讲述上都难称精致的游戏,凭借大量玩家的支持得以和《博德之门3》、《生化危机4:重制版》等老牌大作同台竞技。指责《完蛋》物化女性的群体和强调《完蛋》之真情实感的群体在各个公共平台激烈论辩,《完蛋》则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坐收渔翁之利。

《完蛋!我被美女包围了》
《完蛋》不仅在互联网社群间引发了争论,也在严肃的学术研究领域激起了涟漪,仅在《澎湃新闻》“游戏论”专题就已有三篇相关文章发表:肇始于邓剑的《<完蛋!我被美女包围了>与美少女游戏剧的文法》,文章认为《完蛋》的原型乃是日本美少女游戏,但其改变了美少女游戏的根本逻辑,不再提供实质的否定性,仅以纯粹的肯定性构建出一个看似是乌托邦的“母性的敌托邦”,以“母性的暴力”削弱、麻痹最后捕获玩家;武泽威随后发文与邓剑的观点进行商榷,指出《完蛋》是对“自恋孱弱”的美少女游戏逻辑的接合而非逆转,同时认为《完蛋》相较于美少女游戏更具有现实主义维度,其故事结构也制造了否定性,并非邓文所说的只有肯定性;之后彭天笑也发文参与到了这场商榷之中,以详细的故事分析质疑邓文关于《完蛋》提供了一种“无条件的爱”的观点,指出游戏中的爱是有条件的,并且在选择机制下提供了肯定性和否定性的双重体验。武文与彭文虽然切入角度有所差别,但其基调都是反对邓文的论点,笔者将在基本认同邓文观点的基础上,通过更加具体的游戏分析回应武文与彭文提出的质疑,并以女性玩家的身份提供看待《完蛋》的另一种视角。
首先要声明的是,笔者作为一名女性玩家在从“云”到“玩”的过程中经历了体验的变化,正如邓文所说,笔者以现实逻辑“云”《完蛋》时只觉得它逻辑不通、莫名其妙,但以游戏逻辑“玩”游戏时,游玩的代入感加强了游戏故事的合理性,自己甚至也被其中一些情节所打动。比如笔者也有自己最喜欢的角色:每一分钱都精打细算、过生日吃大家剩的蛋糕、生活拮据也愿意帮“我”付房租的肖鹿。不过,这种“真情实感”并不代表《完蛋》没有“物化女性、消费男性”(邓文语),恰恰相反,它通过巧妙的“现场主义”暗中置换了“现实主义”,并借此生产出以想象拯救现实的幻觉。关于这个问题,笔者会在文章最后作进一步阐述。
叙事媒介or游戏媒介?
当我们面对围绕《完蛋》展开的争论时,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在前面:《完蛋》在媒介层面究竟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作品?游戏的steam界面介绍自己是一款“互动影像作品”,而玩家则将它作为“电子游戏”来接受,这之间的差别实际上比看起来大得多。“影像”的基础是观看,而“游戏”的核心是游玩,如果将《完蛋》视为一个影像,那么所有“云玩家”都可以算作它的受众,因为即使没有互动,作为观看的核心体验也未消失。可一旦将之视为一款“游戏”,则非“玩”不能理解其根本。
邓文中这样说道:
正是与社会现实的相悖,以及对游戏现实主义的接近,使(云)玩家与玩家之间产生了分歧。由于《完蛋》将二次元纸片人转换成了真人影像,一部分(云)玩家会用现实世界的逻辑去认识这部游戏剧,认为这部短剧物化女性云云,另一部分玩家却能从剧中感受到“游戏现实主义”的召唤,将各种匪夷所思的桥段理解为与社会现实不一样的、美少女游戏特有的游戏性现实。

《完蛋》进入游戏页面
这看似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发言:你没玩就不要评价。但细观之,邓文说出了《完蛋》争论的核心矛盾:叙事媒介or游戏媒介?若是将《完蛋》看作叙事媒介,那它只是用一个不那么新颖的形式讲了一个不那么出色的故事,观者当然可以将之视为“科幻”并大加斥责。实际上,大部分围绕《完蛋》的争论都是就其剧情逻辑展开的,连彭文这般坚持为《完蛋》进行辩护的论述都执着于分析故事本身的合理性。笔者认为,邓文最精彩的地方就在于作者把《完蛋》从叙事纠葛中解放出来,将它优先看作是一个游戏媒介,虽然没有进行具体的玩法分析,但其眼光从未离开过游戏领域。相较而言,武、彭两文又回归到了“叙事思路”,因此对邓文的观点产生了许多误解。
逆转游戏逻辑:《完蛋》的好感度系统与流程设计
《完蛋》究竟有没有改变美少女游戏的根本逻辑?这是武文同邓文的第一个冲突点。邓文认为美少女游戏是“玩家主动索取与占有女主的充满野性的游戏”,《完蛋》则是在被动地“被包围”中“自恋却孱弱的游戏”;武文却认为美少女游戏本身的逻辑就是“顾影自怜的,自虐式的堕落”,并指出邓文用来阐释《完蛋》的关键概念——宇野常宽的“母性敌托邦”——也是在御宅族文化(包括美少女游戏在内)环境之基础上提出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根本逻辑”看成是叙事逻辑,武文的质疑无疑是成立的。从故事结构和内容上来看,《完蛋》和美少女游戏并没有本质区别:魅力平平的废柴男主、多个女性莫名的青睐、几女争一男的“修罗场”情节…...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邓文一直强调《完蛋》和美少女游戏的“游戏”属性:“《完蛋》转换了游戏这一新媒介的象征秩序,即把其从‘死’的媒介——游戏的一般本质便是玩家不停地在游戏中死去——转换为‘爱’的媒介。”显然,所谓的“根本逻辑”并非叙事逻辑,而是游戏逻辑。
因此,邓文不是在文化层借用“母性敌托邦”,而是在算法层重述了这一概念。美少女游戏或许在叙事上一直都代表着“母性敌托邦”的文化,但是只有到了《完蛋》里,当游戏逻辑发生根本改变的时候,游戏媒介才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从“死”的媒介到“爱”的媒介。
《完蛋》的好感度系统设计和流程设计,正是其逆转游戏逻辑的表征。
好感度系统是美少女游戏的核心玩法,它在游戏里呈现为一系列选择,玩家作出的选择会影响不同女性角色的好感度,游戏故事的结局则由好感度决定。比如在《完蛋》第二章里,沈彗星问男主角是否记得小时候的事情,回答“记得”,沈彗星的好感度就会提升,回答“不记得”好感度则会下降。第四章时如果沈彗星的好感度达标,男主角就会要求和她一起去见沈父,从而达成“郎骑竹马来”的结局。
虽然同样采用好感度系统,《完蛋》并未顺承美少女游戏的设计惯例。美少女游戏通常以单个角色的好感度为基础推进游戏进度,《完蛋》却设计了一个总好感度,每章结束后需要所有角色好感度的总和达到一定数值才能进入下一章,这让很多玩家陷入了“卡好感”(被好感度要求卡住游戏进度)的窘境。仅专注于某一个角色的好感无法让总好感度达到游戏的要求,必须尽量提升每个角色的好感度,才能顺利地开启下一章节。

《完蛋》第四章好感度结算页面
与这种特殊的好感度设计相匹配的是《完蛋》的流程设计。美少女游戏通常会在游戏开始的“共通线”中安排玩家认识所有女主角,并在“共通线”的最后根据单个角色的好感度让玩家进入某一个角色的“个人线”。“共通线”的流程很短,其作用仅在于介绍女主角并交代故事背景,故事与恋爱的真正展开是在“个人线”里。“个人线”集中刻画了男主角和单个角色的关系进展,同时“个人线”也具有排他性,只会出现一个“女主角”,其他角色在女主角的“个人线”里会被弱化和工具化。比如游戏《日在校园》著名的桂言叶“个人线”结局“鲜血的结束”中,虽然男主角的伴侣是西园寺世界,但这条故事线的女主角和叙述视角依然是桂言叶。
《完蛋》没有将“共通线”和“个人线”进行游戏阶段的明确区别,而是将两者掺杂在了一起:“共通线”贯穿始终,“个人线”以碎片化的形式穿插在游戏流程里:玩家在第一章认识郑梓妍、李云思和肖鹿;在第二章认识沈彗星;第三章可以达成郑梓妍结局“比翼远行”和“幽幽坟茔”、沈彗星结局“双向奔赴”;第四章认识林乐清,并可以达成沈彗星结局“郎骑竹马来”;第五章认识钟甄并可以达成钟甄结局“农夫与蛇”和肖鹿结局“一语成谶”;第六章可以达成所有角色的其他结局。“个人线”不再是一条故事线,而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人情节”,这里没有女主角,故事也不具有连贯性,只提供与某人共处的“现场感”。
这种流程设计让玩家不得不游走在各个角色之间,在第三章和肖鹿的温馨日常丝毫不影响在第五章和钟甄甜蜜幽会,简单来说,玩家可以在一次游戏流程里获得与不同角色恋爱的感觉,而在总好感度的要求下,“可以”就成了“必须”,只有与不同的角色同时步入恋情,游戏才能顺利推进,其间的逻辑让人难以置信——与其他角色的甜蜜相处竟是攻略目标角色的必要条件。
恋情“增殖”:《完蛋》与纯粹肯定性
《完蛋》的好感度与流程设计构成了它最夺目的观感——包围。
“完蛋!我被美女包围了”的魅力不只是美女,更重要的是“包围”。游戏宣传片和海报重复使用六个角色同时出现并看向镜头(观众)的画面,好像观者已经被她们团团围住。男主角被“包围”的频率高得离谱,游戏总共有6个章节,每章分为十数小情节,每隔几个小情节就会出现“包围情节”,也就是玩家们俗称的“修罗场”:多个女性坐在男主角对面,让男主角在她们之间做出选择。 “共通线”的延长最大化了“包围情节”出现,无论在游戏设计上还是表层叙事上,这都是美少女游戏极其罕见的状况。

《完蛋》中的“包围情节”
与此同时,玩家需要重刷其他角色的好感度以提升总体好感度,这个过程必然会让玩家进入与其他角色的“个人情节”,这是一个以持续发生的“爱”——恋情的“增殖”——推进的过程。
为了实现这种“增殖”,《完蛋》甚至不惜牺牲自身的所剩不多的合理性,造成了很多故事“硬伤”:比如在第二章的“赚钱计划”一节,玩家可以选择去李云思家住,第四章的“郑重辞别”一节,玩家会从李云思家离开,但是由于“共通线”和“个人线”的混乱穿插,即使玩家前面没有选择去李云思家住,后面还是会有从她家离开的剧情。《完蛋》对恋情“增殖”的执着已经超过了对合理性的诉求,以开放性的创口泄露了自身欲望的秘密。强迫玩家以“海王”的姿态沉浸在持续“增殖”的恋爱体验——还有比这更强大的对纯粹肯定性的渴求么?
当武文和彭文通过故事分析说明《完蛋》中存在否定性的时候,指的是这样一种“否定性”:故事的演绎背离了玩家的愿望。比如彭文以“孤家寡人”和“男闺蜜”两个结局说明《完蛋》的“否定性”维度:
故事进行到第六章时,如果玩家不能坚定地选择与某一位女主确立关系,就会因为自己的拖延和花心遭受到严苛的惩罚…...也就是说,设计师从根本上否定了齐人之福的可能性,即便让那些希望左拥右抱乃至开后宫的玩家如坠冰窖。
在彭文看来,玩家的愿望是“齐人之福”,游戏的否定是“惩罚花心”,但是在这之中存在着一种假设,即所有玩家都想“开后宫”,不能“开后宫”的体验就是“否定性”的。按照这个逻辑,游戏的“否定性”显然因人而异。极端点来说,如果一个厌女男同玩家玩这款游戏,那么女性角色的追求行为本身对他来说可能都算“否定性”体验。
邓文所讲的否定性,乃是游戏逻辑上的否定——游戏系统将玩家设置为自己的对立面,即“玩家被分配到一个对抗性的行动位置”(邓剑《“放置RPG”批判——当代游戏的社会想象力问题》)。在美少女游戏中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种否定性:系统让玩家一次游戏流程只能达成某一个结局,玩家为了达成其他结局不断存档回档重新进行选择。这种策略在游戏爱好者之间被称为“S/L大法” (即Save/Loading),也是美少女游戏的可玩性所在。Save的节点至关重要,如果没有把握好Save点就要经历更长时间的重复剧情才能到达目标结局,可能每个美少女游戏爱好者都体验过忘记存档或存错档的痛苦,因此美少女游戏攻略的主要内容就是告诉玩家应该在哪里Save。“S/L”是系统给予玩家对抗自己的武器,正是在S与L的重复中,玩家与系统博弈并走向自己所期望的结果。
有趣的是,《完蛋》并没有存档系统,所有情节以树状图的方式展开,并且允许玩家跨过任何情节进入目标情节。比如玩家的目标是刷满肖鹿的好感,ta就可以先点击一个肖鹿好感度相关的情节支,做完选项后退回到树状图页面,跳过之后所有与肖鹿好感无关的情节支,再点进下一个肖鹿好感相关情节支...…系统贴心设置的树状图把自己变成了玩家的“金手指”,玩家不用思考在哪存档、不用经历重复剧情、不用制定S/L策略,就算解锁了不想要的结局也无需面对任何游戏层面的惩罚。这才是邓文所讲的“否定性”层面,也因此,邓文强调《完蛋》转换的是“游戏这一新媒介的象征秩序”,而不是故事本身的象征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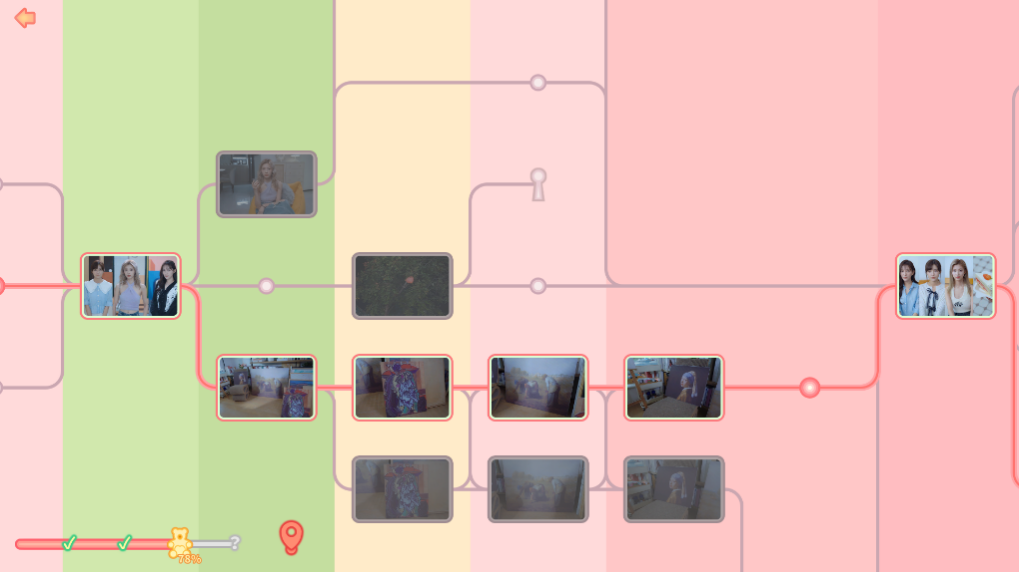
《完蛋》第四章树状图(局部)
《完蛋》是一款电子游戏,其魅力不仅来自角色和故事,更重要的是玩家从玩法之中获得的东西。如果《完蛋》是一部影视剧,它还能获得同样的热度和支持么?
“母性异托邦”:《完蛋》及其“现场主义”
笔者在各大平台围观《完蛋》玩家的相关评价时发现,中国的《完蛋》玩家与宇野常宽笔下的日本动漫文化受众确实有所区别,正如制作组所说,这款游戏的受众是那些“只专注于现实生活的男性们”,而不是美少女游戏玩家(二次元)。因此,与其说《完蛋》是“母性乌托邦/敌托邦”不如说它是“母性异托邦”,其中区别可以通过下面这条评论看到:
你们都说这游戏烂,烂不烂我不知道吗,现实生活中我就是一个臭×丝,现在难得有一款对我主动的游戏了,好不好我不知道嘛,我是真心动了哥,哥几个也别骂我了。我现实就一个丑×丝,只能上游戏找找乐子,算我求你了哥,别骂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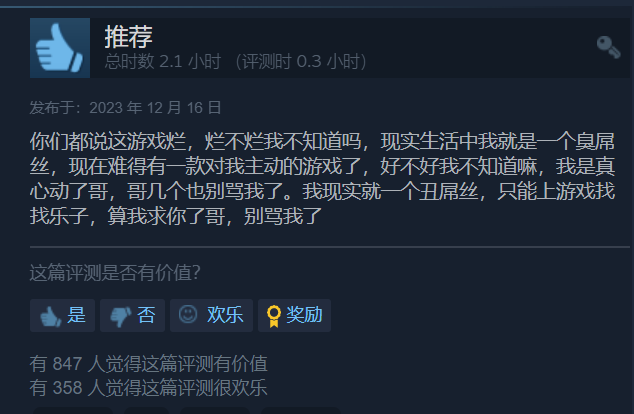
《完蛋》steam平台评价
这条评论可以看作是对《完蛋》玩家观点的总结:首先,他们清楚地知道游戏不过是黄粱一梦,同时,他们并未将之看作一个完全虚构的乌托邦空间,而是真实存在的异托邦空间。福柯针对乌托邦概念提出了“异托邦”,乌托邦是不存在的,异托邦却是“一种的确实现了的乌托邦”,是一个被认为确实存在于现实中的空间,它有权力将不能共存的场地在想象中并置为一个真实的场所。将《完蛋》看作是一个异托邦空间,意味着它不是这条评论中的“我”所处的空间,因为“我”只是一个“臭……”或“丑……”,在现实中不会有人“对我主动”,但“我”相信一定存在着这样的位置,一定有一个男人正在被美女“包围”。
这是和美少女游戏受众完全不同的想象结构,“二次元美少女”是作为一个纯粹的幻想被其受众所接纳的,她永远不会被放置到现实的空间中而只存在于她所在世界的想象里。但是《完蛋》的玩家却持续表达着将角色“现实化”的冲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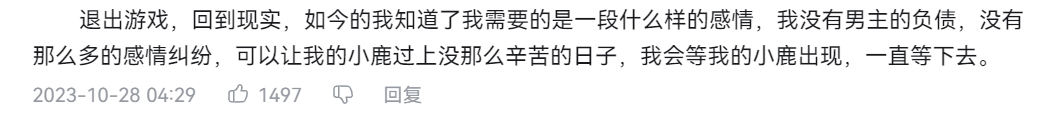
B站《完蛋》攻略下的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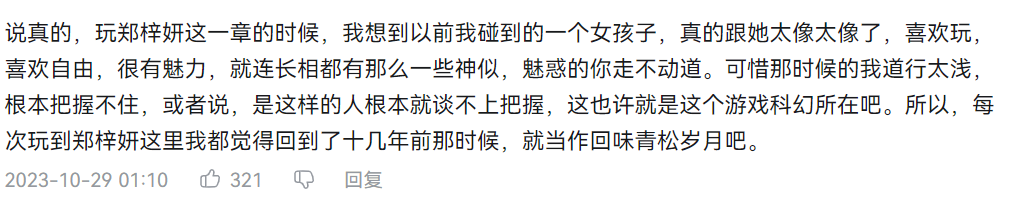
B站《完蛋》攻略下的评论
上面两条B站评论一个是“想要拥有”,一个是“曾经见过”,两者遵循着同样的逻辑——想要把角色和现实联系起来。我们不能说美少女游戏角色完全没有现实的影子,但是其社群确实并不着意于在虚拟和现实之间构建桥梁。齐泽克对弗洛伊德“原始父亲”(primeval father)概念的重述精准描绘了这个异托邦空间:在男性的欲望结构中存在着这样一个例外,他的代表是原始部族中的族长父亲,他拥有所有的女人并能够实现完全的满足。角色“现实化”的执着意味着玩家不单纯是沉溺在虚假的幻象之中,更想要借此设想一种拯救现实的方式:即使我得不到,“被美女包围”的经验也是可能的。
《完蛋》提供的“现场感”成为玩家们对角色进行“现实化”的主要依据。制作组在采访中表示,游戏的很多情节是创作团队人员的亲身经历,确实,游戏中与不同角色的相处瞬间也让很多玩家似曾相识,但这并不代表《完蛋》具有现实主义维度。总的来看,《完蛋》只是精挑细选的生活“现场”和精心编排的快感“幻象”的集合,所有“现场”都需为“幻象”服务。《完蛋》呈现了现实中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这并非现实主义呈现,只是用现场言说现实,以现场代替现实的“现场主义”摹写。与其争论《完蛋》是否具有现实维度,不如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完蛋》只呈现这类“现场/现实”?
显然,《完蛋》的任务不只是让玩家沉湎于虚妄的想象中,更重要的是以想象拯救现实。“母性异托邦”带来的不仅是玩家积极行动可能性的丧失,更制造了以情感化客体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幻觉,仿佛男性的痛苦是由一个个不够完美的女人带来的,而一个充满肯定性的伴侣,就足以拯救破碎的人生。
有人会质疑,这种女性明明就是存在的,为什么对她的摹写不能算是现实?这种女性存不存在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完蛋》的玩家一定要相信存在这样的女性,即使我不能拥有,她也一定在某个地方被别人拥有着,就像李云思不和顾易在一起也一定要成为其他男人的“所有物”。在《完蛋》里,女人作为男人的症候魅影浮现,暗示着男性主体的精神分裂。正如拉康所说,一个每天跟踪妻子怀疑她出轨的丈夫,就算妻子真的出轨了,他也依然是一个神经症患者。或许给玩家造成创伤的不仅仅是现下的社会状况,还有那些反对《完蛋》,不再愿意扮演“母亲”的女人们。
参考文献
邓剑,游戏论:《完蛋!我被美女包围了》与美少女游戏剧的文法,澎湃思想市场,2023年12月2日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5468981
武泽威.游戏论:《完蛋!我被美女包围了》与美少女游戏批评:兼与邓剑商榷,澎湃思想市场,2023年12月23日https://mp.weixin.qq.com/s/lwR778qj4oeMrg9vhzuGQQ
彭天笑.《完蛋!我被美女包围了》与美少女游戏:兼与邓剑、武泽威商榷,澎湃思想市场
邓剑.“放置RPG”批判——当代游戏的社会想象力问题[J].文艺研究,2023,(10):124-135.
宇野常宽著,屋顶现视研译,零零年代的想象力。https://www.douban.com/note/823670424/
宇野常宽著,屋顶现视研译,母性的敌托邦。https://www.douban.com/note/854825211/
齐泽克著,《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郭英剑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