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答辩·《吴宓的精神世界》︱文化保守主义的当下阅读
【按】“答辩”是一个围绕文史类新书展开对话的系列,每期邀请青年学者为中英文学界新出的文史研究著作撰写评论,并由原作者进行回应,旨在推动文史研究成果的交流与传播。
本期邀请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副教授周轶群与三位青年学人讨论其新著《吴宓的精神世界》(商务印书馆,2023年6月),本文系评论文章之三。
早在本世纪之交,余英时已指出五四新文化所具有的多重面向性与多方向性,并提醒大家注意文化保守主义在五四文化矛盾体中扮演的角色。近二十年来,以梅光迪、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杂志同人译介美国新人文主义、绳愆纠缪新文化运动激进反传统的功绩逐步得到厘清。但关于保守主义与诸如政治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伦理相对主义、个人主义之间产生了怎样的化学反应,又如何作用于知识人、普通民众的精神世界,如何影响中国现代化之路等问题,尚留阐释空间。周轶群教授(以下敬称略)的新著《吴宓的精神世界》(商务印书馆,2023年,以下引文出自该著者,均只随文标注页码)着重于阐明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吴宓(1894-1978)的精神面向,部分回应了上述思想命题。该著沿着吴宓与宗教之关系这一线索,联系吴宓在世界文学、《红楼梦》研究上的建树,以及吴宓自身的伦理道德、宗教信仰实践,为探寻一个身处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下跋前疐后的近代知识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了样本。该著另一值得瞩目之处在于将吴宓与其他新文化人的文化、文学实践联系起来考察,二者的并置有力地证明了八、九十年代由乐黛云提出的文化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实际上“殊途同归”的说法。
本文对该著的探讨一方面延续周轶群联结吴宓与其他新文化人的包容视角,另一方面对周轶群有所涉及但未能深入挖掘的吴宓的“现代性”进行阐发,并试图指出周轶群所深耕的吴宓的宗教性背后的时代思潮脉络。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我将基于自身对吴宓的理解,并联系周轶群指出的吴宓“在复古中创造未来”这一特质,阐发吴宓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第二、我将从“现代性”本身具有的启蒙与反启蒙二重性出发,在当时蔓延东西方的“情理辩证”思潮中定位吴宓的宗教性。第三、在周轶群的启发之下我提出从“实践”角度对吴宓的宗教性进行解读的方式。最后我试图探讨,该著为我们在当下应如何阅读文化保守主义给出了一种解答,而我们应该如何回应这种解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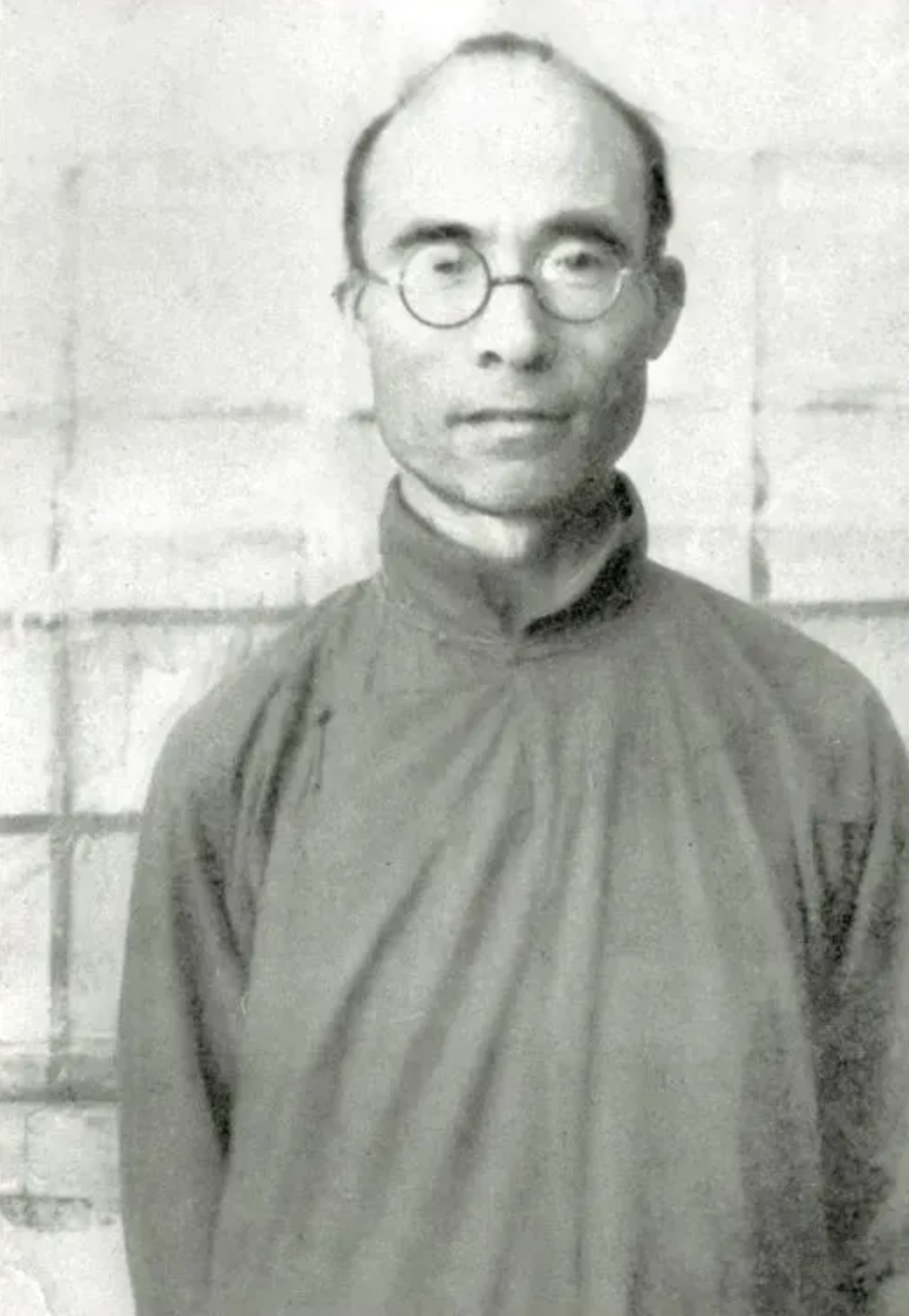
吴宓
吴宓的“现代性”
王汎森近年提出尝试使用“confused period”(模糊阶段)来解释像五四这样巨大的历史运动。处于“confused period”的五四运动呈现出两条线索相互交织的现象:一条是由新思想推动者引领“真信者”实现时代轴心挪移的A线索;另一条(或多条)则是模糊、顿挫、悬疑的B线索,存在其中的多半是“半信者”;五四是由“半信者”与“真信者”一起合奏的乐章。吴宓既不是五四的信徒,或许也难称其为“半信者”,但他在诸如爱国精神、尚批评、以西方为镜等方面又呈现出与“一般意义上”的五四新青年相同的特征。可以说,缺少了对如同吴宓这样“犹疑者”所演奏出的低音的论述,将无法描绘五四的全貌。正如钱钟书所称,吴宓与新文化阵营如同一场足球比赛的敌对两方,双方的竞技(也是合作)塑造了近代中国的走向。借用竹内好的“鲁迅回心说”,保守主义似构成了反传统的激进主义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一种线性的进化史观)上的“回心”;二十世纪的历史证明了中国(抑或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域)在现代化道路上那些未能轻易剥离掉的传统因素、非理性(或称之为反启蒙)因素随时可能“卷土重来”。然而,这些因素并非负面因素,遏制历史的前进,而是“现代性”本身所包含的复杂、混沌等特征的体现。
吴宓先生压根不是一个迂腐的保守派。任何一个对他那个时代有一丁点了解的人都不可能不看见他本质上的现代性。(《钱钟书英文文集》)
周轶群在结语部分“吴宓的悲喜剧”中援引的这段话(第482页)写于一九三七年,是彼时钱钟书对吴宓的评判。在近一个世纪之后,我认为钱钟书仍旧是最敏锐地揭露出吴宓本质的论者。那么应该如何理解吴宓的“现代性”(modernity)呢?周轶群在其著作中借用乌那牟那对堂·吉诃德的形容来刻画吴宓的特质,而我认为这段话正可以用来解释吴宓的“现代性”:
每一个为了任何理想而奋斗的人,即使他的理想可能看起来存在于一个过去的时代,都是在将世界向未来推进,唯一的反动派是那些安然活在当下的人。每一个据说是复古的行动都是在创造未来。(第481页)
“在复古中实现对未来的创造”用来形容绝大多数的保守主义者并不为过。他们看似排斥“进步”,但事实上是在用与“进步主义者”不同的方式创造未来。以吴宓崇敬的文人、学者为例。一九二八年,吴宓译介了法国诗人保罗·瓦雷里(Paul Valery)的诗论,与梁宗岱几乎同时注意到这位法国诗坛的巨擘。梁宗岱这样描述瓦雷里的诗歌实践:“哇萊荔(即瓦雷里)是最遵守那最谨严最束缚的古典诗律的;其实就说他比马拉美守旧,亦无不可。因为他底老师虽然采取旧诗底格律,同时却要创造一种新的文字……他则连文字也是最纯粹最古典的法文,然而一经他底使用,一经他底支配,便另有新的音和义……就是提倡自由诗最力的高罗德尔(Paul Claudel,现译克洛岱尔)也赞他不特能把旧囊盛新酒,竟直把旧的格律创造新的曲调,连旧囊也刷得簇新了。”对于与法国现代诗歌无涉的吴宓来说,翻译瓦雷里的理由更多在于瓦雷里用“旧囊”盛“新酒”的诗歌实践与吴宓自身的诗歌创作理念相合,两人都试图在遵守古典格律的同时书写新内容、创造出新风格。另一个例子则是吴宓一生最为喜爱的英国诗人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被视为继柏克(Edmund Burke)之后在文化批评领域奉行保守主义理念的阿诺德在白璧德的笔下却同样具有“本质的现代性”(白璧德对阿诺德的评价与钱钟书对吴宓评价之间的“暗合”值得注意)。而在白璧德的阐释下,“现代”并不意味着“最新的事物”, “......现代精神是乐观和批判精神的代名词,是拒绝接受权威的精神。”
借助以上的“现代”解释,吴宓始终坚持与五四“正统”保持一定的距离、对堕落颓唐的悲观主义保持警醒的态度或许可以说正是现代知识人的一种体现。面对20世纪初前途未卜的中国,思考借鉴何种西方理论(或是融合何种东方思想)、苦于在生活与实践中奉行何种伦理道德,不随波逐流,而是践行一种具有反思与批判精神的生活态度对于多数人来说并非易事,但却是现代知识人的应尽之义。
周轶群在其著作中也展现了若干片段,似可证明面对艰难时刻,吴宓无不表现出这样的“现代精神”。举一个例子,周轶群描绘了吴宓在抗战最艰苦时期选择向大众讲演《红楼梦》的心态。在方法论层面,吴宓表现出与重科学、兴考据的近代学术的差距,看似回到颇为“传统”的义理之学,然而在这背后,却蕴含着吴宓对于“《红楼梦》‘乐观而积极’的精神能够在至暗时刻给国人带去一点光明……通过点燃他们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热爱,激发他们团结一致、奋起救国的决心”( 第427页)的期待。事实上,我认为吴宓对“传统”的处理与其精神导师白璧德相似,并未“沉醉”于古典世界,而是试图架起古典与现代的桥梁:
“就古典文学而言,与其说把它们当作孤立的现象,不如阐明它们与当今社会的多方面联系,弥合古代生活与现代生活之间心灵无法逾越的鸿沟。因此,古典文学教师的重要职能之一应该是架起古希腊罗马世界与当今世界之间的桥梁。”(白璧德《文学与美国的大学》)
理解了这一点,过往贴在吴宓身上的诸如反对白话文、拒斥新诗、尊孔复古、泥古不化等标签都值得重新省思。例如,周轶群在书中重点处理了吴宓对孔子以及孔教的态度。与当时一昧抨击儒家伦理的激进主义者自是不同,与拒斥一切西方思想、“热心孔教,力主读经”的读经团、孔教会人士也颇有不同(第328页),吴宓借助柏拉图理念与经验世界的二分法,经由对诸如基督教等宗教“内质”与“外形”的思索,重新考虑儒家思想的精义(内质)与桎梏人心的风俗、制度、礼仪(外形)之间的本质差异。吴宓视儒家伦理、佛教、基督教、古希腊哲学为“四大宗传”,四者之关系错综复杂,但根本道理是一致的:使“人性获得本质的升华,以臻天性”(第227页)。吴宓对儒家伦理的阐释融合了东西方哲思传统,其新颖之处可见一斑。
吴宓的“赶时髦”、与世界思潮接轨展现在方方面面。例如我翻阅吴宓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刊载的翻译作品后发现,他是中国极少数译介英国现代主义流派旋涡主义(Vorticism)创始人温德姆·路易斯(Wyndham Lewis)的思想之人(吴宓《路易斯论治术》、吴宓《路易斯论西人与时间之观念》)。他与欧洲现代主义的关系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展开,他关注其中对于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反思的部分,或者说他关注那些并未对世界前进的轨迹怀抱完全的信心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他试图寻找的是与他类似的对于转动时代轴心的A线索抱有怀疑之人。他自然不会是启蒙的坚信者,而是在一场注定失败的斗争中“伶仃苦斗”之人,有着如吴宓自身偏爱的堂·吉诃德的气质。
吴宓将堂·吉诃德的精神阐释为“偏于浪漫而趋重理想”,而周轶群则在吴宓的“乐观主义的悲剧精神”中发现了宗教的力量。周轶群著作最大的贡献之一,即作者指出在阅读吴宓时宗教这一角度的重要性。周轶群梳理了吴宓自一九一四年清华时期到一九七〇年代生命终结为止与宗教的交涉。在这期间,吴宓在儒教、基督教、佛教之间徘徊,时而融会贯通三者。借助吴宓日记,周轶群呈现出宗教是如何在文学创作、学术活动以及生活实践中给予吴宓影响的。
为了更好地理解周轶群所论及的吴宓的宗教性以及这一发现的学术意义,我认为有必要联系当时蔓延东西方的“情理辩证”思潮,对其宗教性做出解读。所谓“情理辩证”思潮,与我上文论及的吴宓身上的“现代性”有关。当凭借理性认识世界的企图走到绝境之时,情感、想象、精神的力量绝处逢生。理性主义与唯情论一直是现代思潮中重要的两极,在这两极的纠缠中诞生的欧洲思想家对中国五四时期的思想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接下来我将在情与理的辩证这一脉络中思考周轶群对吴宓宗教性的解读。
情与理的辩证
在《唯情与理性的辩证:五四的反启蒙》中,彭小妍对1910年代左右即在中国酝酿并于1923年“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轰动一时的反启蒙思潮进行了探究。所谓反启蒙思潮,即“主张情感启蒙(Enlightenment sentimentality),挑战启蒙理性主义(Enlightenment rationality)及科学主义(scientism)”。彭小妍指出‘反启蒙’(Counter-Enlightenment)并非反对启蒙,而是启蒙的悖反;情感启蒙论述与启蒙理性主义并辔齐驱,两者都是欧洲启蒙时代以来的产物,是一体的两面。”最早探索欧洲反启蒙思潮的是以赛亚·柏林,他将维柯、赫尔德、卢梭、谢林、施蒂纳、尼采、克尔凯郭尔等欧洲思想家纳入这一谱系中。而彭小妍聚焦这一思潮在亚洲的跨文化成果。彭小妍串联起倭鏗(Rudolf Eucken)、柏格森、罗素与张君劢、张东荪、梁启超、梁漱溟、蔡元培、朱谦之、方东美、西田几多郎等人,她称“反启蒙思潮是一场跨国家与时代的运动,其核心人物各持不同立场、极具多样性,却有共同的敌人,即科学主义和理性启蒙主义。”另外丘庭杰在其《情感与理性之间:五四启蒙个案的跨文化省思》中则提出另一种在地的反启蒙,即黄克武在其《迷信观念的起源与演变:五四科学观再反省》中探讨的从宗教、迷信等角度出发的反启蒙。丘庭杰强调:“非理性并不是不理性或没有理性,而是对于唯理性的逆反。它从情、志等面向思考和补充理性之不足,但并非完全否定理性的功能和价值。”(丘庭杰《情感与理性之间:五四启蒙个案的跨文化省思》)
过往的吴宓研究者往往强调吴宓受到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影响,其中如内在节制(inner check)、摒除动物性、追求有节制的自由等观点,都是启蒙精神与理性主义的表现。吴宓的诗论、文论也表现出自身服膺于“以理制欲”的信条之下。例如探讨马修·阿诺德的诗歌时,吴宓认为:“安诺德固深信宗教之不可缺,但谓宗教须破除迷信及旧规,而不悖于理智。然何以臻此,则安诺德亦实无办法。……安诺德之诗,即专写此种伤感者也。……动辄厌世,以死为乐。……作者自以众醉独醒,众浊独清,孤寂寡俦。”作为吴宓最崇敬与喜爱的诗人之一,阿诺德用理智替代宗教信仰的追求、以及求之不得的伤感深得吴宓的认同与同情。从吴宓在诗作中自比阿诺德来看(“我是东方安诺德”,《挽阮玲玉》,《吴宓诗集·故都集下》),他对于现代社会的痼疾与良方的认识应与阿诺德类似:宗教已然失去其应有的力量,惟有理性能解救近世弊病。
然而,在阅读了周轶群对吴宓与宗教之间关系的论述后,我发现吴宓在对待理性与宗教的功用上呈现出的复杂性。首先,周轶群从吴宓的两位新人文主义导师之间的区别出发(“盖白师以道德为言,穆尔先生以宗教为勖。”“宓之受穆尔先生之影响,恐尚过所受于白璧德师者”),指出吴宓的宗教气质受到穆尔(Paul Elmer More)的影响更大而非白璧德(第9页)。同为新人文主义阵营,穆尔与白璧德在宗教问题上有不小的分歧,不像白璧德“认为人文主义可以独立承担起宗教在前现代社会履行的功能”,穆尔“坚信人类的现代问题必须依靠宗教信仰才能解决”(第9、13页)。
其次,周轶群指出吴宓对宗教的态度与穆尔的类似之处:他并不认为宗教在现代社会已经失去其力量;尤其对于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来说,唯独依靠理性是行不通的。吴宓敏锐地看出宗教当中所蕴含的情感的力量。但是吴宓也没有完全放弃理性的部分,他区分理性(人文道德)与情感(宗教)所承担的不同功能,有时则试图融合二者。
人文道德主于适可而止,用相当之克己工夫,调剂均平,无使冲决横溢,便为满足。凡此皆以证明理性成之。而宗教则主根本铲除罪恶,期上帝之援引,底于绝对之至善,方为完功、凡此乃以丰富之想象及激烈之感情致之。(吴宓《文学与人生》)
所谓宗教,乃融合(一)深彻之理智(二)真挚之感情……(吴宓《空轩诗话·曾宝荪女士》)
对于宗教所利用的是想象与情感的认识使吴宓得以对宗教中迷信、仪式抱有宽容的态度。对于诸如《新青年》的孔教与宗教批判运动,吴宓自是不赞同成的,但他也不认同五四时期试图用哲学去“净化”宗教的做法。
宗教之功用……在利用人之理智想象及感情……以其根据人之想象及感情,故不能以科学批判宗教。以其利用想象,故必有神话迷信。以其为达实用之目的,感化人为善,故其神话迷信乃有益无害之物,不宜一概痛斥。
佛教固为理智最发达之宗教,然绝不废想象及感情。……今之学人,志在阐扬佛教,而因时代思潮,重科学而鄙迷信,有所顾忌,遂专以哲理言佛教……此其意固佳而行则未善……试一读佛经全藏……亦可见其中神话之繁多,想象之富丽,诸佛之转生,轮回之定程,诸天之奇景宝光,地域之恶苦残毒,我佛说法之奇效巨功,圣灵异迹。凡此皆佛教本身之一部,去之而空谈之中所含之一二哲理,非佛教也。(吴宓《孔教之价值》)
周轶群对吴宓主张保留宗教信仰中的“仪式”部分有如下解读:“仪式的根本性质就是一种习惯性的、用以表达感情的行为而已……儒家礼仪的起源本身就是古代中国人对表达感情的习惯行为的需求,这种需求是亘古不变的,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一个重要的外在标志就是,一代一代,他们都自然而然地通过同样的仪式满足这一需求”( 第316页)。“仪式”通过情感在人身上发生作用,我认为吴宓能认识到这点说明他对“唯理性至上”已有了反思。
吴宓虽然并未直接参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但从他1923至1924年间撰写《我的人生观》、三四十年代开设“文学与人生”课程等等举动来看,他对于当时的论战应有一定程度的关注。周轶群指出吴宓“表达的对科学局限性和人生观解决方法的理解,都与“玄学派”有很多相似之处”( 第230页)。而王昌伟(Ong Chang Woei)则认为“张君劢等‘新儒家’学者受柏格森的影响,将直觉体认视为达到天人合一状态的有效途径,而追随白璧德的学衡派却认为这种观点会导致对本能的放纵,真正需要的是下功夫控制人心中趋恶的一面。”(转引自周著、第230页)
接下来,我将试图追溯周轶群没有深入挖掘的伯格森与吴宓之间的关系。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在五四的反启蒙思潮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彭小妍就认为“五四的唯情论一方面是对柏格森的响应与批判,一方面以柏格森创化论的角度重新审视传统学术(包括儒释道)……五四唯情论的主要来源是柏格森与传统中国学术……”但正如王昌伟指出的,吴宓与诸如张君劢等深受柏格森影响的唯情论者之间有不小的区别。我想这种区别或许正来自白璧德、阿诺德对经由理性形成的伦理道德的坚持。而吴宓游移于唯理与唯情之间的态度在那个时代属于异数,对他的阐释或许能够丰富已有的关于情理辩证谱系的书写。但值得注意的是,吴宓的主张(或者说白璧德的主张)也是当时在欧洲如日中天的柏格森哲学所激荡起的回音。
1928年,吴宓译介了两位欧洲思想家(拉塞尔Pierre Lasserre、路易斯)的柏格森批评。拉塞尔关于法国浪漫主义流弊的判断被认为影响了白璧德《卢梭与浪漫主义》的写作。在拉塞尔所写的《柏格森之运命》(Le destin de Bergson)一文中,拉塞尔指出“柏格森指行事与学说,均未教人以率尔成事,任心性之所趋而为之也。世谓柏格森主“直觉”之说。用此直觉,则人类所能知之最深最贵之真理,可以一种神秘之启示,忽然顿悟,岂不妙哉。又谓直觉既与思虑相反,故最不用思虑工夫之人,亦最多凭直觉而得真理之希望云云。然而柏格森氏之意则大异于是。盖柏格森氏所尊重之直觉,乃辛苦为学及思虑之结果及报酬,决难不劳而获。惟已潜心细究各种已有之问题事物,而按定法思虑退考者,始能有顿悟之望。吴宓为此段话写下一个批注:“按明心见性,原系格物致知之结果,相连并存,而不能废。程朱陆王,门户纷争,如此判决,一语得真。今古今东西学说流弊,有同慨也。”无论拉塞尔对于柏格森“直觉”的阐释是否正确,也暂且不管吴宓将拉塞尔的论述挪至理学心学之争的类比是否准确,吴宓融合理性与直觉的企图可见一斑。
宗教作为精神自救之术
周轶群注意到宗教的力量对吴宓的悲观主义起到了调和的作用,这造成了他与阿诺德截然不同的特质:“他拒绝极端理性导致的枯索悲苦和怀疑嘲讽,企图通过宗教的力量在衰世和绝境中为中国和世界找回信仰、热诚、意志和想象力。”(第366、367页)但周轶群并没有点明吴宓为何选择从宗教中获取力量,以及这一选择是如何与同时代的其他青年有所分歧,却仍然反映了同一种时代精神的。纵观吴宓一生,这种身处苦境却仍旧积极向上的精神,或许来源于吴宓的个人气质,但也是他对以烦闷、抑郁为特征的时代精神的一种反抗。这引出我的另一个思考角度:在阐释吴宓身上的宗教性时,我认为试图解释他是如何在学理上对“四大宗传”有所推动或许是次要的,重要的应是通过追溯吴宓的宗教信仰,我们得以近距离观察一位近代中国知识人是如何通过宗教实践成功抵抗“苦闷”的。
关于五四时期青年的“苦闷”,王汎森在其《“烦闷”的本质是什么——“主义”与中国近代私人领域的政治化》中谈及五四时期思想界所起的一个重大变化,即当时的国人倾向于将人生与日常生活“问题化”。
近代中国所经历的空前变局,使得国家、社会等观念都成了“问题”。晚清以来中国人的生命世界添加了许多旧社会所感到陌生的概念,如“国家”“社会”“团体”。当时一般人对这些新东西每每感到莫名所以,即使是到处向人们讲解这些新观念的青年们内心中往往也一样困惑。过去对皇帝、对朝廷、对家庭应该采取的态度是非常清楚而确定的,现在加进这些新的“国家”“社会”“团体”,使得生活变得有些陌生起来,本来可以不假思索的变得很不可理解。
另一方面,什么是“人生”也成为一个问题。茅盾(1896-1981))在《我走过的道路》中就说五四点醒青年思考“人生”是什么,但是并未给定答案。五四确实一再说文学应表现人生且指导人生,但并未明确说明“人生”是什么。
这种“问题化”的倾向造成当时社会普遍的焦虑情绪,或表现为精神衰弱、自杀等症候,或表现为文学创作中的“苦闷的象征”、“世纪末的哀愁”。与诸如郁达夫等新文学家一样,表现“苦闷”也是吴宓诗文创作的一大主题,只是他使用的是中国传统古典诗歌的形式。他直言自己的诗作表达的是“现代全世界知识阶级之痛苦”(吴宓《释落花诗》)。吴宓与众不同之处是他敏锐地意识到这种困惑与迷茫的精神状态并不局限于中国,处于近代这一转折期的知识阶层都感受相同的苦恼。例如其精神导师白璧德写下的:“在许多人身上,当过去的一切形式都被摒弃之后,精神上产生了巨大的孤独感、空虚感和荒芜感;生活似乎不再对他们有任何中心或意义。旧秩序失去了对他们理性上的控制,但在他们的想象力中仍然保持着影响力”。
为了对抗这种“时代的焦虑”,当时的青年人纷纷寻找得以解救精神苦闷的途径。王汎森指出,由于“‘社会科学’取得了新的权威,所以许许多多青年人,原先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是渴望研究文学、哲学的,现在纷纷转向,希望研读‘社会科学’”,而即使“当时各家各派:儒家、佛家、道家、基督教乃至通俗宗教,都提出形形色色的人生观……在各种人生观的竞逐中,左派的理论体系显然胜出”。
而吴宓与当时大多数的知识青年一开始选择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思潮,后来又选择左派理论、社会科学的各种“主义”作为精神解药不同,他选择从人文主义以及各大宗教教义的阅读中获得力量。周轶群指出的穆尔对其影响在此背景下体现出来:
知忧患之必不可逃,则当奋力学道,以求内心之安乐,是谓精神上自救之术。欲救人者,须先自救……古今之大宗教,若佛若耶(孔子之教亦然),其本旨皆重自救而非救人者也……故宓现今亦惟当力行自救之术。但宗教自救之术,皆须弃世,佛、耶皆然……而于国家社会,种种责任,则目前似尚有不能放弃者存,故不得不求折衷两全之术……宓彷徨疑虑,经年而不知所措手者,今读Shelburne Essays(VI)而竟得其术,宓之惊喜可知已!其术维何?……以一语概括之曰:Work without Attachment.”直译之,则为“日日做事,但须无所附丽” ……决不为一学派、一教宗、一科门、一时代所束缚、所迷惑……
从“‘日日做事,但须无所附丽’ ……决不为一学派、一教宗、一科门、一时代所束缚、所迷惑……”来看,吴宓并不追求对某一宗教教义精深的钻研,而是将各大宗教信条抽象成其对抗这个变动不居世界的行为准则。一方面固然由于吴宓本身并不想局限于某一种特定的宗教,而是力主融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基督教、佛教、儒教;另一方面他更像是一名普通的“信徒”,尤其在生命后期,他通过诵经、祭祀、叩拜行礼回复内心的安宁。另外与二十世纪初佛教、孔教现代化运动向外的力量(诸如参与政治运动、社会改革)不同,吴宓的宗教信仰是向内的(“欲救人者,须先自救”),这在周轶群论述的吴宓对于读经团“被政治利用……向政府和政治人物寻求支持和庇护”(第333页)感到不满中体现出来。
因此在理解吴宓的宗教性时,首先应承认他的宗教信仰具有的功用性。他与同时代的众多青年一样受困于“苦闷”的时代氛围之中,宗教是万千解药中的一剂而已。第二,吴宓身上的宗教性具有强大的辐射力。周轶群指出对吴宓的理解应具有“文学、道德、宗教所构成的统一体”这一视野。吴宓虽然是一名文学研究者,但离开道德与宗教的角度则不能完全理解吴宓的文学事业。周轶群对吴宓《红楼梦》研究的阐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周轶群指出吴宓虽认可王国维借助西方悲剧理论对《红楼梦》进行阐释,但并不赞同王国维将其解释为“由生活之欲带来的痛苦以及这种痛苦的消极解脱”。与王国维借用叔本华不同,吴宓经由西班牙哲学家乌那牟那的《悲剧的人生观》一书,将宝玉与黛玉的悲剧阐释为“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姿态奉行他们的理想。在绝望中坚持和奋斗,虽痛苦而无怨无悔”。吴宓的悲剧观以其中积极和乐观色彩与王国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种乐观主义正是来自于吴宓对“四大宗传”的理解。吴宓认为“宗教的超越是一个‘离幻趋真’(世俗与物质为幻)的过程”,而“《石头记》指示人生,乃由幻象以得解脱(from Illusion to Disillusion),即脱离(逃避)时间之种种虚荣及痛苦,以求得出世间之真理与至爱(Truth and Love)也”(吴宓《〈石头记〉评赞》,转引自周著,第398页),正与宗教的超越有着相同的宗旨。
因此在宗教与道德观念影响下的吴宓的文学观,绝非近代以后才在西方兴起并对当时文坛产生了巨大影响的“纯文学”观。他视文学批评为一种义理之学:“古今东西各国各时代之文章著作”……应具有“支配人生、影响实事”,“造成一种普遍的、理想的、绝对的、客观的真善美之标准”,不仅仅是“文学艺术赏鉴选择之准衡”,也是“人生道德行事立身之正轨”(吴宓《浪漫的与古典的(书评)》,转引自周轶群,第1页)。
周轶群对吴宓宗教观的梳理十分详实,她利用《吴宓日记》以及吴宓所写的旧体诗中的心灵剖白,为我们呈现了一位世纪末知识人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以及他追寻精神解药的轨迹。近年,宏观视角下的思想史书写走向衰颓,注重知识分子个体精神史书写的微观角度利用“心理史学”、“情感史”等分析尺度试图关注以往思想史未能注意到的面向。我认为对吴宓宗教性的理解应从这一角度入手,将吴宓具体且颇有些朴素的宗教信仰实践作为连接精英层面的思想史与民众宗教文化史之间的桥梁。
文化保守主义在当代
周轶群的著作还有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角度,本文仅从吴宓的“现代性”出发,联系近代以来“情”与“理”的二元辩证,指出周轶群挖掘吴宓“宗教性”的意义,探讨背后的学理脉络。在此书的最后一部分,周轶群试图通过吴宓追问一个更加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即“当中国已经以激进喧嚣的方式告别传统社会,并在现代化的路上疾走了一百年之后,曾经‘误导’了吴宓的新人文主义者终于可以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良方了吗?”(第484页)
这个问题背后实际上隐藏着这样一个预设: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并非坦途,且暴露出许多问题,其中就有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在“全盘西化”过程中将主体性完全让渡的问题。九十年代以来学界重新发现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价值,正是出于对中国现代化道路中激进主义的反思。但是文化保守主义所提出的诸多具体议题在当下是否具有有效性?这一问题似乎被悬置了。以吴宓为例,我想提出以下疑问。
第一、吴宓一生秉持他对世界上的各大宗教颇为圆融的态度。然而,无论是四大宗传(基督教、佛教、儒教、希腊思想)殊途同归的想法,还是区分宗教精神(一)与宗教形式(多)的理念在当下原教旨主义盛行、宗教纷争不断的现实里有着明显的理想主义(甚至是空想)色彩。脱离各大宗教信仰的具体土壤去谈平等与文化多元对于解决实际问题似乎并无益处,应如何评价吴宓的宗教理想与现实的关系?
在谈及宗教之功用时,周轶群指出吴宓在1926年提出“宗教乃根于人之天性,故当人类之存,必不能废”的论断,“可谓是洞察人性,对人类在情感和精神上的需求有着非常现实的了解和判断”(第365页)。虽然她援引西方研究者提出的“宗教在当代世界强劲回归,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去世俗化’的过程”作为证据,然而“宗教的回归”是否与中国的实际语境相符合?周轶群在书中提及的吴宓亲历了两种“仪式”的并置这一片段十分值得玩味。(第318-319页)宗教在当下中国的缺失,意味着吴宓所渴望看到的融会贯通四大宗传之精华或是对孔子与儒家伦理道德的尊崇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宗教所代表的“非理性”在当下的继承或许是以领袖崇拜与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为其表现。
第二、那么吴宓等文化保守主义者所坚持的(儒家)伦理道德与当下社会真的符合吗?例如儒家社会中十分具有争议性的性别问题,应该怎么得到解决?具体到吴宓的性别观,他在解读《红楼梦》时,导入西方的浪漫爱传统,为曾经“以贤妻良母为唯一理想女性角色的中国传统社会”增添了新的元素。这种将女性视为“才女、智媛、美人、巧匠、交际家”,并从中生发出爱与尊敬的浪漫爱传统将女性从其社会性身份(贤妻良母)中解放出来,似乎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如果仔细阅读吴宓诗文中对女性的描写,例如他对陈寅恪夫人唐筼的吟咏注重其与陈寅恪之间的婚姻和睦(“蓬莱合住神仙眷,胜绝人间第一流”《贺陈寅恪新婚》吴宓诗集卷九),将女学生描绘成依附于男子的小鸟依人姿态(“依人小鸟态憨痴”南游杂诗吴宓诗集卷十),都难以令人信服他真正尊重女性的主体性。而他将吕碧城的诗词创作理解为“不外作者一生未嫁之凄郁之情”而引发吕碧城的不满,以及他对于自身与毛彦文之间情感纠葛的言说与后来毛彦文视角之间的龃龉,都表明吴宓在面对当时女性主体意识觉醒上的捉襟见肘。
第三、吴宓赋予文学以神圣基础和崇高目的文学观也与当下格格不入。思考文学在当下的位置,不仅不复神圣与崇高,其对社会的影响力一再减弱,更不用说吴宓认为文学应该承载道德与宗教的观念,在当代世界更是难以得到响应。
最后,我想从文化保守主义对激进主义“纠偏”这一角度入手,思考应如何连接学衡派在过去历史中做出的功绩与当下的现实状况。近年来的吴宓研究都指向一个事实,即吴宓、梅光迪等《学衡》同人对西学的掌握并不亚于“新文化阵营”。他们为当时中国的知识界提供了一个具有西方人自反性的异样的“西方”叙事,而他们的版本往往更加审慎与准确。在这一意义上,学衡派的确在履行一个“纠错”的职能。但问题是,是否“更准确”意味着“更正确”?对当时中国诸如鲁迅等激进反传统主义者来说,并不那么准确的“西方”叙事更有益于塑造国人对于未来的想象,他们有意通过一个“简化”后的西方叙事呼吁国人实现中国真正的“改变”。这一对“改变”的热望立足于当时中国实际存在的诸多问题。而这似乎道出了文化保守主义在当下的阅读困境,即我们如何处理逐渐跃升为主流的“中国传统”叙事与仍旧在上演的“问题”?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