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答辩·《吴宓的精神世界》︱比较视野之下的“新”吴宓画像
【按】“答辩”是一个围绕文史类新书展开对话的系列,每期邀请青年学者为中英文学界新出的文史研究著作撰写评论,并由原作者进行回应,旨在推动文史研究成果的交流与传播。
本期邀请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副教授周轶群与三位青年学人讨论其新著《吴宓的精神世界》(商务印书馆,2023年6月),本文系评论文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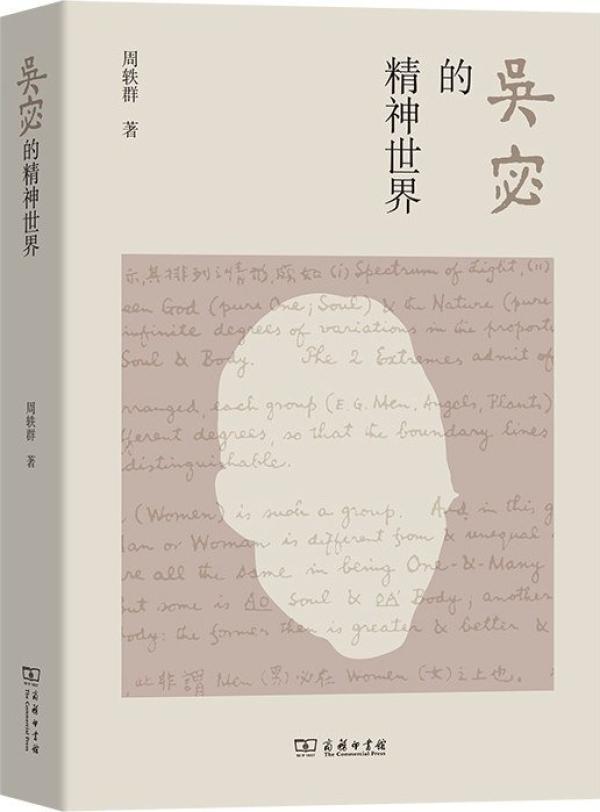
《吴宓的精神世界》,周轶群,商务印书馆,2023年6月
新文化运动期间,以吴宓、梅光迪为代表的学衡派多被冠上“复古”、“保守”的帽子,其思想主张也多被批判、遮蔽或遗忘。近些年来,伴随着对新文化运动范式的反思和对中国文人“世界文学”构想的再思考,吴宓成为有待关注和重估的研究对象。
与过往研究不同,周轶群教授的新著以吴宓的自我师承定位为出发点,利用吴宓日记、年谱、刊载在报刊杂志上的文章、书信、课程讲义、授课大纲、诗集、诗话等研究材料,围绕文学、道德和宗教三大主题为吴宓描绘了一幅新的精神画像。该书以“吴宓”为中心人物,以“文学与宗教”的讨论为核心,或对未来相关研究有新的启发,也有助读者打开更为广阔的思考空间。
全书共分三章,分别为吴宓与世界文学、吴宓与宗教和吴宓与《红楼梦》三个部分。第一章主要结合吴宓的《世界文学史大纲》、《希腊文学史》、课程讲义、日记、聆教者的回忆片段、散见在报刊杂志上的一些文章等材料来构想吴宓的世界文学史书写,并侧重分析吴宓的世界文学理念和方法、编纂标准等,并将其与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郑振铎的《文学大纲》进行对比,分析其中更深层次的同与异。由于吴宓讲授世界文学史的讲义至今无法发表,作者在第一章文末特别增加了一个附录,对吴宓的长诗《海伦曲》进行评注,希望借此探索出一种特别而有效的方法,增进我们对吴宓在古希腊文学方面的学养和他在事业和人生方面的理想与困境的了解,并在附录的分析中引入对宗教的讨论。
吴宓多年来孜孜不倦地专注于“四大宗传”,但既往研究只注重讨论吴宓与儒家思想及柏拉图主义之间的关系,对宗教在吴宓的生活、学术研究、思想中所扮演的极为重要的角色关注较少。第二章将结合吴宓“文学与人生”课程讲义、协和医学院英文演讲、报刊杂志上刊载的系列文章等材料,在吴宓新人文主义四大宗传的框架内讨论和分析他与宗教的关系、他对宗教的态度、认识以及相关实践。作者以时间为线,大致梳理出吴宓与四大宗传的关系及其发展变化。实践和发展角度的引入是该研究与现有研究之间的一个显著区别,对四大宗传融合的讨论和分析也是该章独特之处。

1921年吴宓在东南大学
吴宓尤为重视古籍名著、经典传统和文本细读,第三章则聚焦于《红楼梦》,以《红楼梦》作为文本个案,集中展现文学、道德、宗教如何作为一个整体定义了吴宓的事业和人生,以及比较视野在形成这一整体中所起的重大作用。《红楼梦》对吴宓的意义不仅仅是文本本身,而是寄托了吴宓对文学、宗教和道德的理解。吴宓对《红楼梦》的阐释与理解迥异于当时影响巨大的索隐派和考证派,也不同于王国维。通过分析吴宓对《红楼梦》的评介文字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吴宓对《红楼梦》以及文学的看法。吴宓也尝试将自己融合四大宗传的努力应用于对《红楼梦》的解读之中。
比较的视野一直贯穿吴宓的文学史写作,也贯穿于周轶群教授的新著《吴宓的精神世界》中,“比较”的研究方法勾连了吴宓和周轶群的文学书写。时至今日,我们还未能看到吴宓的世界文学史讲义,只能透过《希腊文学史》、散见于报刊杂志上的文章、日记等材料来构想出吴宓的世界文学史。在《希腊文学史 第一章 荷马之史诗》中,吴宓将荷马史诗与中国的《封神演义》《三国演义》《左传》《西游记》《镜花缘》等小说、史书进行对比。比较的意义也跃然纸上,一是可以加深和丰富读者的阅读和审美体验;二是能为吴宓的世界文学史书写提供一个清晰的中国视角,这也正是郑振铎、周作人等五四知识分子在文学史书写中缺失的一个重要部分。郑振铎的《文学大纲》虽给予中国文学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但仅是将其与西方文学进行并列论述,并不能看出其中深层次的关联。在讨论宗教和《红楼梦》的文章和评论中,吴宓也延续“比较”这一方法,比如在《世界文学史大纲》和刊发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的文章中将《圣经》与四书五经相提并论,这一比较可以加深读者对《圣经》和四书五经的理解。在《<石头记>评赞》中提出可将《红楼梦》与西方文学进行比较,如柏拉图《筵话篇》、加斯蒂里辽《廷臣论》、斯当达尔《爱情论》等。也正如周轶群教授所言:吴宓对《红楼梦》各个层面的分析与阐释,都没有离开比较文学的视野。
而“比较”这一方法也贯穿于周轶群教授的新书写作之中,在“在中国书写世界文学史”一节,周教授将周作人编纂的《欧洲文学史》、郑振铎撰写的《文学大纲》与吴宓编写的文学史进行平行比较。得出“周作人只罗列各阶段文学史中的各项简单史实,如主要作家和作品等;郑振铎的《文学大纲》以德林克沃特的《文学大纲》(The Outline of Literature, 1923)为蓝本;吴宓却坚持要考虑博学、通识、辨体、均材、确评五条编写要素,通过编写文学史来匡正国人对西方文学零星片段、轻重倒置的了解,对西方文学有较为总体的把握”这一结论。通过浏览吴宓的《希腊文学史 第一章 荷马之史诗》,我们也可以初步了解并感受吴宓文学史写作的具体主张和文学实践,即秉持“博学、通识、辨体、均材、确评”五条编写原则,在“博学”和“通识”上,吴宓也展示了远胜中国同时代文学史作者的把握、综合、分析西方文史专业知识的能力。结合吴宓1945年在成都燕京大学为《文学与人生》课程所设定的评分标准,从中也可以看出吴宓对待“钞录、编辑文学史”的态度,这也体现出吴宓与郑振铎等人的最大不同。除此之外,周轶群教授还将郑振铎、吴宓二人的世界文学体系书写进行对比,将《海伦曲》和《壬申岁暮述怀》进行对照阅读等方式来论述吴宓的文学、宗教和人生,从而展示出文学和宗教在吴宓身上密切而深刻的联系。
该书的创新之处首先在于作者详细分析了吴宓留下的书信、日记、诗文、诗话等一手材料,史料翔实,全方位展示了文学、道德和宗教如何作为整体塑造了吴宓的学术生涯和文化事业,并且尤其注重发掘宗教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也试图弥补现有研究中宗教视角的缺失,为理解吴宓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先行者和一个无法抹杀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打开一个极为重要却一直被忽视的视角。在周轶群教授的分析之下,宗教和文学不是两条平行线,而是相互连通,贯穿了吴宓的一生。我们也可以从吴宓的文化事业、世界文学史大纲、报刊杂志上刊发的文章等材料中加深对吴宓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先行者”和“开创者”这一称号的理解。
其次,既往研究过多关注白璧德对吴宓的影响,而忽视了穆尔。周轶群教授的研究并不是想在白璧德和穆尔之间分清孰优孰劣,辨析出究竟谁对吴宓的影响更大,而是想说我们不能忽视穆尔对吴宓的影响这条发展线,尤其是在分析宗教和道德的关系上,来自“以宗教为勖”的穆尔的影响恐怕超过“以道德为言”的白璧德。
总的来说,作者在“吴宓与宗教”一章用力甚勤,对四大宗传共存与融合的分析也较为清晰,特别是展现出吴宓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和思想变化。作者选择以时间为线,以《学衡》时期、西南联大时期为分析节点,勾勒出1921-1949年期间吴宓对基督教态度的发展变化,材料详实,论述得当。该章还结合吴宓的诗集进行分析论述,也为吴宓的宗教研究提供一些具体的文字依据。但可能四大宗传的共存与融合较为复杂,尤其涉及到分析不同时期吴宓的文章和诗文,某些小节读起来可能还是有些晦涩难懂,尤其牵涉到不同学科背景的读者,该章阅读难度较大。
略微遗憾的是,我们并不能亲眼所见吴宓所撰写的十余册世界文学史讲义和大纲,只能根据现有零碎材料构建出吴宓的世界文学史实践与构想。除在附录增加对长诗《海伦曲》的评注外,笔者建议还可以关注吴宓对世界文学史的翻译和评注,可以以刊载在《学衡》上的《世界文学史》(Literature of the World)一书为依据,分析吴宓的世界文学史构想。其次,根据吴宓的课程讲义、日记、书信等材料,我们能否看出吴宓讲授课程之间的细微变化(因为吴宓讲授宏观文学史年限长达十一年,前七年课程名为“欧洲文学史”,后五年改为“世界文学史”),比如从“欧洲文学史”至“世界文学史”,课程内容是否有细微的变化,还是仅如作者所言是将“欧洲文学史”当作“世界文学史”来处理?从课程内容和名称的变化是否能看出吴宓看待世界文学的视角和理解方式的转变?是否有可能将吴宓的课程讲义/日记与翟孟生编写的《欧洲文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European Literature)进行对比,分析出其中的改写与超越?
此外,在将周作人、郑振铎与吴宓撰写的世界文学史(吴宓的世界文学史主要以《世界文学史大纲》的课程结构和课时安排看出不同文学所占的比重)进行比较时,我们能否从各国文学所占的比重出发,来反映出这一时期文学史书写的倾向性和探究背后更为深层次的缘由。我们也可以思考从周作人、郑振铎再到吴宓,这一文学史书写是否跳脱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学世界观。最后,笔者想以周轶群教授在168页发出的思考作结,在外国文学研究(或世界文学史书写)中,中国文学应该置于何种位置?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